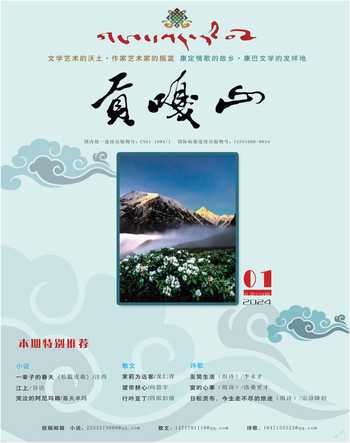河水之虞(外一章)
符纯荣
在人的一生中,青春年代是一首澎湃的歌,每一个音符都能迸开绚烂的星火,起搏壮阔的惊涛。这个过程有十六年吧。几乎每个日子,我都要头枕河涛美美地进入梦乡,又在它的小声呼唤中悠悠醒来,把五千多个日夜寄放在一座山坳小镇,安谧而舒适,温暖而踏实。
一直以来,我都很羡慕和向往那些能够自由行船的“大河”,哪怕小小木船并非做到真正意义上的“航运”,只是在空间有限的固定河段往来过渡,为两岸民生提供着出行的便利,但只要河面上有那么一艘船,就足够了。我觉得,对于一条河而言,不仅要有滔滔激流、船歌悠悠,还要有鱼翔浅底、水鸟翩跹,更要有放逐远行和迎候归来的水码头,它的生命才算是鲜活的、完整的。
而老家那条囿于群山围堵的小河实在太过小巧,小得几个箭步就能纵跳而过,根本不具备自由行船的条件,也就不存在所谓诗意的水码头了。那些身形曼妙的小木船,咿咿呀呀的桨橹声,宛若絲绸般滑过的流水,还有水雾迷蒙的晨昏依依送别的某个背影,便只能借助书页的翻动进入梦中,为一个山乡少年的心间添上一丝说不清道不明的愁绪。
十三岁那年,也就是小学即将毕业的前一个月,我到镇上供销社工作的父亲身边读书,认识了这条穿越小镇而过的河流。对于山里人而言.镇子比乡里的小街繁华多了,有着更长的街道、更多的楼房、更为琳琅满目的店铺,更重要的是,还有一条更加宽阔的河流。那天,我背着书包从村前涉水而过,沿着公路徒步去往镇上。那条小河仿佛是遵照母亲的嘱咐,一路上,默默地陪护着我,直到在五公里后把我托付给另一条河流。
这是距离老家不到十公里的一条“大河”,名叫碑牌河。谓之“大”,确实有着大的本钱:它宽一百多米,水量尤为充沛,河床两边是丰茂林木,郁郁葱葱连绵不绝,充满了勃勃生机。一年四季,河水都是丰盈的,临近场镇的数公里河段,有着大山里难得一见的深水长滩,这条河便又叫作长滩河,非常适合航运。于是,许多年来,河面上船只穿梭,成为美不胜收的绝妙风景。船的形态各异,有飞箭般敏捷的柳叶船,有水老鸹蹲立舷首、身形瘦小的打鱼船,有宽身子、笨拙拙的铁皮船,还有一种以汽车轮胎绑上木板做成的简易小船。专门用于航运的,是那种长十多米以铁皮包裹的木船,载客量大,使用的柴油机动力颇为充足,运行起来发出突突突的声音,虽然看着慢吞吞的样子,却别有一番韵味和可爱。
在小镇生活十多年,究竟多少次乘船出行,实在说不上来了。记得第一次是学校组织大家到上游磴子河水电站去春游,一行十多条机动船,满载着叽叽喳喳闹个不休的同学们,浩浩荡荡地向着前方进发。由于负载过重,船舷吃水深度眼见就到了临界点,船体行进时激起的水花不断飞溅,打在同学们的手臂或脖颈上,立时引发一阵充满了欢快的尖叫。但在那个时候,谁也没有意识到危险,有的只是心情的放飞和追逐自由的快乐。六公里水路结束,前方河段怪石嶙峋,已不具备通航条件了。大家兴致勃勃地下船,沿着河边小路继续前行,鲜红的旗帜在阳光下迎风飘扬,嘹亮的歌声飞过了云端。
我相信,所有人的心情都是快乐的。一直以来,我们蜗居于大山深处,在群峰环峙的山坳小镇学习和成长,外面世界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都是那么生动和新鲜,一次看似普通平凡的乘船出游,打开的却是书本上没有的崭新天地。哪怕是这样一座建在深山里的小小水电站,给我们带来的新奇感受也是从未有过的。
那座名叫磴子河的水电站,在当时看来颇为高大上。我们第一次听到排水沟、导流洞、取水洞、溢洪道、闸门等类似专业词汇,第一次看见弯成弧形的石拱大坝将万千流水拦截下来,再逐一导入预设的沟渠之中,以地势落差形成一股股强大的冲击力,然后将隐藏于水中的电能抽丝剥茧般提取出来。尽管水电站很小,设施设备很是简陋,发电装置和技术手段也相对落后,但丝毫不影响我们面对这些新鲜事物发出一阵阵不可思议的惊叹。
是的,日常生活中本该无比平凡的流水,居然可以靠着与生俱来的、属于本能的流动方式,做出如此神奇而伟大的事情。那么,大地上的事物到底还藏匿着多少妙不可言的潜能,等待着人类进一步的探究、发现与利用?
后来,听说还是出于对安全问题的担心与后怕,上面领导严厉批评了校长,那次春游之后,学校再也没有组织过类似大型集体出行活动了。
事实也是如此,漠视安全终会带来刻骨铭心的教训。就在当年夏天,小镇逢场日,由于船老板太过贪心,一艘客运机动船里三层外三层塞满了赶场的人,远远超出核载承受能力好几倍。当机动船突突突地喘着粗气驶离码头,即将进入航道时,由于船舱两边的乘客重心偏移而失去平衡,船体一头偏了过去。刹那间,几十人纷纷落水,那惊慌失措、大呼小叫的场面实在令人触目惊心。好在码头临近河段水位并不算太深,大家施以援手的行动也很迅速,最终没有出现伤亡的恶性事故,也算是不幸之中的万幸了。
多数时间,流水平和,一副与世无争的温顺模样,实则不然。自古以来,乡下就有“欺山莫欺水”的说法,在那暗流涌动之下,潜藏着不知什么时候,即有可能给人重重一击的巨大危机,让忘乎所以的人们懂得,对待万事万物,真的要有足够的敬畏和尊重。
十七岁那年,我在达县城里读中专,中秋节的晚上,同学们相约去小中坝赏月。小中坝是州河之中一个美丽的小岛,除了洪水季节会被淹没一段时间,一年中的大部分时段,岛上苇草茂盛,飞鸟起落,郁郁葱葱的草坪吸引着人们前往。尤其到了秋冬时节,州河水量锐减,从学校这边河岸到小中坝,只需要穿过一片鹅卵石河滩,涉过一段深不过膝的浅水,不曾遭遇任何障碍便可以轻易登上岛去。这样一个休闲好去处,人们自然是趋之若鹜。
入夜,一轮圆月准时上升,清辉浩渺无际遍洒大地,真的没有辜负人们千百年来对它的喜欢。那轮大月亮可以说是我们当时看见过的最大的月亮了,我们甚至感受到大片淡蓝色的月光在身边铺展开来,涌动着按捺不住的兴奋,二十多位男女同学在岛上草坪围成一个大圆圈,唱歌、跳舞、吃月饼、诵诗、赏月,尽情施展才艺,释放青春的激情。时近午夜,大家仍然兴致高昂,谁都没有想要离开的意思。直到有人突然感觉身下湿漉漉的,很快又看见一只鞋子漂浮起来,我们这才惊骇地发现,河水不知何时涨潮了!
对于河水毫无征兆说涨就涨这一蹊跷事件,我们事后找到原因。两年前,上游三十公里处的宣汉县城,有一座当年全省最大的地方中型水利电力项目——江口水电站建成投用,并非阴雨天气却半夜涨潮,正是电站开闸放水所致。而那些年通信条件实在落后,安全防范机制并不完善,加之人们自我保护意识也太过欠缺,倘若再晚一点发现,极有可能酿成令人不敢想象的严重后果。
当一场近乎灭顶之灾的巨大危机骤然来到身边,所有人都慌乱起来。特别是不会游泳的同学,望着浩浩荡荡席卷一切的河水,更是惊恐不已。值得庆幸的是,从小中坝退回河岸这段河滩,总的来说是平顺的,无较大起伏的深潭水坑,同学们常来河滩玩耍,对这里的地形都很熟悉。当然,最重要的原因还是在于发现及时,确保大家能够手拉着手,一步一步踩着高过腰际的河水,最后有惊无险地脫离困境。
当所有人终于安全上岸,回头望去,不断上涨的河水已漫上小中坝,我们刚刚还在狂欢的这座小岛很快就被完全淹没,只剩下几丛纤细芦苇在水面弱不禁风地摇摆。随着上游水量不断加码,气势汹汹的洪流一波连着一波奔泻向前,持续发出令人后怕的咆哮之声。
在这个旷远而美妙的中秋之夜,曾经沉稳持重而诗意盎然的州河,性情却突然变得那么地躁动不安,面孔是那么地丑陋狰狞。那惊涛骇浪接二连三狠狠撞击河床的声音,惊扰我们的梦境很多年。
大火之殇
那是一个夏日的上午。头天,我与几个小伙伴去后山玩耍,刨开泥土,发现红苕长得比大拇指大了一些,吃上一口颇为脆甜,便缠着父亲到地里挖一些红苕回来吃。
在镇上供销社工作的父亲是头天回来的,与往常一样,他不只是带回糖果、饼干等好吃的,更带给了我好心情。那天的阳光早早便出来了,照着大地,也照着我比平时更加放肆的任性和撒娇。放牛、割草、捡柴等苦力自然是哥哥、姐姐每天的必修课,我只需要提上一袋糖果,屁颠屁颠地跑前跑后,或者爬上父亲肩头“打马肩”,一道去地里挖红苕。
走的时候,灶房堆满了柴草,一只生蛋的母鸡安静地蹲在角落里,塘里的余火也被一贯细心的母亲用冷灰覆盖。每天这样的过程实在是太平常不过了,至今我都能清晰记起:柴草有序堆放在火塘边,那只争气的老母鸡每天按时产下一颗圆滚滚的蛋,黢黑铁罐放置于木架上,热腾腾的火塘归于短暂的冷寂……
从后山坡看过去,我家土墙房隐没于大院子,只能见到连成片的青色房顶以及伸出头来的烟囱。到了后山坡,母亲径直走进红苕地割猪草,父亲也将我从肩上放下来,查看哪一厢红苕更成熟一点,便于下锄。起初,我兴奋地站在旁边胡乱指挥,后来也感到枯燥了,便爬上一块大石乱涂乱画。没过一会儿,也乏味了,便躺在石板上,吃着糖果,望着半山腰充满生气的山村,幼小心灵被一种幸福感完全填满。
其实,山间的雾气并未完全散去,还随风飘扬着一层淡淡的白纱。我甚至能看见那层薄纱被阳光稀释的样子,依依不舍地围绕着山村,久久不肯离去。鸟儿在其中飞来飞去,开心地嬉戏。几只鸟儿飞累了,在烟囱上面短暂歇息一阵,很快又回到鸟群追来赶去。
如果时间更早一点,雾气萦绕的村庄更像置身于宽广海洋,一幢幢土墙房恰如冒出海面的礁石,那些鸟儿自然也就是低回盘旋的美丽海鸥了。不知不觉,那层雾气做的白纱被鸟儿舞弄着,竟然带到了我家的房顶上。过了一阵子,它们逐渐在烟囱四周聚拢,然后一点点变白,慢慢掩盖青黑色的瓦片。我像看电影一样津津有味地欣赏着这奇妙的变化,看着白纱开始泛青、变黑,最后变成一股浓烟漫过房顶。
就在懵懂的我百思不得其解时,火光开始冲上房顶,原本安宁的大院子出现了嘈杂的呼喊声。正在地里挖红苕的父亲抬起头来,已有人跑到大院子外面,急急地、高声地喊着父亲和母亲的名字。俩人迅即扔下锄头、镰刀,飞快地向大院子跑去,将我一个人丢在了山坡上。
我第一次目睹这种灾难,而且与自己息息相关。那惨不忍睹的破碎场景,令我至今感到揪心和后怕。
大院子一角,从我家房屋蹿上天空的大火,露出一张肆虐而张狂的狰狞面孔。木门木窗燃烧的声音,杯盘碗盏爆裂的声音,房梁瓦片折断和砸落的声音,火势突破房顶仍要吞噬一切的呼啸,急促而杂乱,气势汹汹,撼人心魄。邻居们第一时间迅速赶来,紧跟着,更多后援力量也陆续加入,一时间,挑水的挑水,接力的接力,急不可待的泼水声,桶或盆的碰撞声,相互提醒的呼应声,不绝于耳。
在大人们善意的驱赶下,娃儿们只能退到安全的院外,观看火势与人们顽固对抗,聆听嘈杂而焦急的呼喊,为人们不断抢救出一些弥足珍贵的物件而感到高兴。没过多久,外出捡拾柴火的大哥二哥和割草的姐姐,听到消息后也跑了回来。在村口,我们泪眼相对,再也止不住巨大的悲伤,相拥着痛哭起来。
那场大火烧毁了我家仅有的两间土墙房,除了锅、碗等一些不易完全损毁的物什外,瓦砾遍地,满眼狼藉,基本上没有留下一点什么。幸运的是由于发现及时,赶来救火的人很多,在大家共同努力下,大火最终被完全扑灭,邻近房屋未受到多大损伤。而那只喜欢蹲卧于灶房一角每天都在生蛋的老母鸡,在火中自然也就变成一堆灰烬。后来我才知道,那场致命的灾难,正是它在生蛋之后的觅食过程中刨燃塘里余火造成的。
不知怎的,我从来没有记恨过这个始作俑者,相反,我时常记得母亲将鸡蛋一个个积攒起来的那份喜悦以及用鸡蛋换回油盐酱醋的那种满足感,从而对它的悲惨遭遇深感同情和痛心。
那一年,刚满五岁的我,懂得了白手起家的真正含义。
那一年,我开始收敛任性,学会了与父亲一样沉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