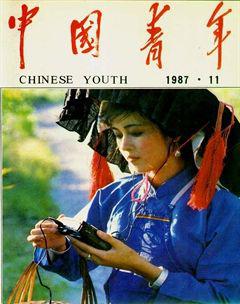灰色的年轻人(小说)
初次见面是在夏末的一天。我们下班回去,发现他在宿舍里。
“哦,你们刚下班。”他微笑着,“我是到这里住的。”
看上去他30出头,中等个子,宽肩膀,挺壮实,一身灰色衣服,一双方口布鞋,头发黑中见白,面目端庄。
“听说了,你就是办公室新调来的吧?”
他点头微笑,给我们让烟对火,动作十分老练。“刚报过到,以后就请两位老兄多加关照。”
“不敢当不敢当,老兄有30了吧?”王雷问。
“咱们差不多吧,我24。”
24岁?比我们还小?我们感到吃惊。横看竖看,他的相貌与年龄还是不相称。
他有些不好意思:“哦,看上去我是大了点,初次见面的时候,就有人叫我老魏。哦,我叫魏方印。”
以后我们的宿舍里就成了三个人。我在组织部。王雷在团委,他原来是学医的,能写会讲,五四青年演讲会上被团市委发现了,就调了过来。
魏方印从省师大毕业,毕业后被市委定为培养对象,在县里锻炼了两年多,入了党,现在又调上来。相处一段,觉得他跟我们很合得来。
他学的是中文,古文底子厚实,一肚皮的春秋,又象是活的辞书,常常能准确地道出一个词句或典故的出处。生怕我们不相信,还总把书本搬出来,直到得到印证为止。
这层楼上住有不少年轻人,大都是这几年分配来的大学生,时间长了,楼道里邋里邋遢的,谁也懒得打扫,靠楼梯还积了一大堆垃圾,方印来后就把它清除了。以后每天早起他都要把楼道打扫一遍,洒上些水,清清爽爽的。我们屋里的开水总能保证足量的供应,方印打得最勤。伙计们常常端着空杯来喊“劳驾”,“你们整天劳驾!”王雷有些不平了。方印却总是笑脸相迎,有时还会往他们的茶杯里拈上一撮毛尖。谁要是有个头疼脑热的,他就会说:“又不得劲了,来,我这里有药。”他常备有几种普通药,还有一支体温表。只要有求于他,他都热心地为你奔跑,成不成都会给你个交待,哪怕是极小的一件事情。
大家都乐意接近他,有了什么好吃的也不会忘记他。有人身子不舒服了还闹着要他推拿,有人一时高兴了还会扑到他背上搂脖子打秋千,有了什么苦衷也都愿意向他诉说。他静静地听,话不多,只听他常常说:“不要急,慢慢来,解决一个是一个。”他俨然成了我们的兄长,我们也当真不论大小叫开他灰哥了,他还挺客气地接受了这个称呼。
说他灰,那是因为他和我们相处一年多,衣着大都离不开灰色,夏季浅灰色,春秋银灰色,冬季青灰色、铁灰色,甚至我们还觉得他的脸是灰色的,头脑也是灰色的,且有一种沉重的精神力量,渐渐地给我们形成了一种老大哥式的威压。
一下班伙计们就要热闹一阵,听录音机、弹吉他、猜空拳、无端地怪叫。他不满地瞟你一眼或是咳嗽一声,我们就会条件反射似地打住。熄灯后我和王雷躺着闲扯,他在床上晃两下,我们就不得不住口。后来王雷弹吉他,就躲到外面的洗脸间。
老同志反映,这层楼里最近规矩多了。
灰哥似乎整天都在忙着工作,用“勤勤恳恳”“孜孜不倦”一类的词儿来形容他,一点也不过誉。他的饭碗就放在办公室,早饭后,当人们对着空碗聊天或在院里转悠的时候,他已经在办公楼里忙开了,扫地、拖地、刷痰盂、抹桌子、打开水,干得很带劲。晚上当我们躺下看书的时候,他才从办公室回来。上班时间碰见他总是行色匆匆的,跟你搭个腔也总是“哦,我到那边去一趟”,也不知道他在干些什么大事情。
一天晚饭后,我拉住了他:“灰哥,来!咱们杀一盘,我还没领教过你的厉害哩。”
“你算是找到家了,我连棋子都叫不准,还是你们来吧,我去办公室。”他说着就走开了。
我要看看他到底在忙些什么,就来到他的办公室。他正在台历上写着什么。
我拿过台历,随手翻了几页,见上面写着:牛主任换煤气罐:郜主任找电扇箱;罗书记的鸡饲料……“你今天挨训了吧?”灰哥客气地从我手上拿走台历。“说了几句。”办公室上午来人检查岗位责任制执行情况,发现考勤簿上全是空白,部长批评我没做好考勤员。
“你工作应该认真些。”
“什么岗位责任制,狗啃麦苗一一装羊(洋)。上下班好多少?还不是一阵风就过去了,我懒得给他们画道道。”
“那怎么行?人家怎样说咱就怎样干,打边鼓随大调,领导要你怎样做你就怎样做,手要勤快些。”说着,他拉开一个抽屉,里面有好几个笔记本,“领导讲话啦,布置工作啦,给你谈个话什么的都要记下来,笔头懒了不行。”
“嗬,对领导可够尊重的。才几个月你就记了这么多。”我把抽屉拉开些,灰哥又给关上了。
年终总评灰哥被评为优秀工作者,出席了市里的先进表彰大会,抱回了奖状和奖品。奖品很实惠,是一双流行式皮鞋,后来我们还在羡慕呢,却见他用锯条锯着鞋跟,“发给这玩意,现在真是男尊女卑了,比女式鞋跟还要高。”
“灰哥,你也是二等残废呀,”王雷说,“现在的娘儿们怪得很,先瞅你身高,相貌再好也白搭。”
“啥虫拱啥木头,我不怕这个。男人穿高跟鞋显得轻浮,君子不重则不威嘛。在机关里……当然穿鞋戴帽各有所好吧。”他看到王雷脚上的高跟鞋,不好意思地改了口。
君子不重则不威,盖灰哥服饰举止之大要也。有一次他理发回来,发式整齐,面目焕然,我们都为他叫好,可他倒象生了一头虱子,又抓又挠,嘟嘟囔囔:“那个理发员真是的,说是给我吹干,谁知他就来上了,我给他说不吹风。”他用热水烫了又烫,白白送了几毛钱。
王雷说灰哥是蛀了的青皮果子,可惜了。
机关食堂前有个小石坛,是专为棋迷们设的。饭后这里少不了摆几盘。罗书记是这里的常客,饭后常转到这里来过过棋瘾。这天晚饭后,这里又热闹起来了,后来不知怎么的我就和罗书记对上了。
“请你先走。”我说。
“红先黑后,输了不臭,我就先走了!”罗书记呵呵笑两声,摆了一枚当头炮,我跳了一步马。开局和中局,双方旗鼓相当,下至残局,高潮跌起。对方马炮双卒士象全,我是车炮双兵仕相全,对方略占下风,但并不着急,一枚炮、一枚马、一枚过河卒,均压在我方一翼,形成进攻之势。
我开始挠头了,伙计们指手划脚地都成了军师。
“啪!”我拈起将要沉底的兵,打在对方的象眼上。我步步紧逼,沉底炮高出车,直取对方的底象,几步棋走过,已是胜利在望。
罗书记坐不住了,他还从未被逼成这般惨状呢。
“走这儿。”冷不防灰哥插手退了一步老将,危局缓解,紧接着又跳马逼将,刹时我方城下失火,九宫骚乱,老将在对方炮支马背的威势下,只好举手投降。
“哈哈哈……”罗书记大笑,手点了点灰哥,“你这个年轻人呵,哈哈哈……”大伙也嘻嘻哈哈地走散了。
我追上了灰哥:“你不是不识棋子么?”
他停下来,左右闪两眼,一本正经地说:“罗书记那次掀棋盘的事你不知道?年少气盛,不识几微,你还没吃过这亏。一开始你就让人家先走,这就亮你有实力,太不谦虚了。罗书记的话你没听出来?”他又宽厚地笑了笑,“我这人是不爱多手多脚多口舌的,你在组织部门工作,我相信你这人不会错,我可没有把你当外人看。”
我能够理解灰哥对于我的好心。可王雷不。
宿舍的墙壁上,王雷布置了一张很大的半裸黄发美人年历,无论在哪个角度,那双叫你心旌摇曳的明眸都会瞟着你,这常常使灰哥感到不自在。他说再有出息的男人在体面的女性面前都会变得中气不足,这种玩意儿会把男性软化的,晚上脱裤都不好意思。
王雷认为灰哥这话富生活哲理。
“哎,王雷,把这揭下吧。”灰哥乘势说。“你看看,换上这挺不错。”灰哥展出了一个锈黄色的条幅。
“在哪弄的,这字咋看不懂?”
“这是郑板桥的字,难得糊涂”。灰哥念道:“聪明难,糊涂难,由聪明转糊涂更难。放一着,退一步,当下心安。”
“算了算了,”王雷一摆手,“这玩意,贴你床头好了。”
“你别看这几个字,其中的奥妙多着呢。”说着,灰哥抬手要揭年历,王雷挡了一下。
灰哥有些难堪,脸沉了下来,“你贴这让外面的人怎样看我们?这是我们大家的事,影响不好。”
“啥影响?你别拿官场上的那一套来吓唬人。”王雷公鸡斗架般地梗着脖子,眼睛斜着灰哥。
灰哥垂下了眼,苦笑一下,不再说话。
“走,到外面走走。”王雷碰了我一下。
“走吧灰哥。”我拽了他一把。
灰哥迟疑了一下,跟我们一道出去了。我们沿着街一直朝前走,谁也没有说话。灰哥在小摊上买了3包瓜子,一人一包,我们吃着走着,走到了影剧院,两边摆满了自行车,人们络绎不绝,正赶着场。
“《青春万岁》,今晚好电影。”王雷指了指片名。
“灰哥,看看吧……就这一晚上。”我说。
灰哥看了看表,摸着口袋。 “我有零钱。”王雷抢去买票了。
电影开始了。我们深深地被银幕上那欢跳的营火、青春的热情、坦诚的友谊、少女的倩影感染了。灰哥情不自禁地抓住了我的手,握得死死的,他脸上有两道泪光。“灰哥。”我轻声叫他。“我这人不能激动,一激动浑身起鸡皮疙瘩。”我朝他袖管里一摸,乖乖,他的皮肤沙纸一样蹭手。
“看这片真过瘾,就象我们在大学,那时的生活多动人。中秋节,我们把开学时带的好吃的都拿了出来,围坐在林中草地上,也有篝火,我们那个女辅导员很年轻很活泼,月光下,我们吃着说着笑着,想唱就唱想跳就跳。”灰哥说得很动情,都有点结巴了。
当我们出了影院在一个馄饨摊前坐下来的时候,灰哥好象还没有回到现实中来。他眼睛闪着光亮,不住地抽烟,掏手帕揩头,眉眼乱动弹。转眼王雷从饭馆里提了一瓶酒,抱了一大包牛肉片,“来来,干脆来几两,难得坐一块喝。”
“好,来就来,”灰哥动身坐正,“怎样来?”
“你说。”
“一门一。”
“好,倒酒!”王雷出了拳。
“哥俩好呀、再好好、好到老……八大仙、包拳包……”
我们大呼小叫,对着瓶子喝,眨眼下去了多半瓶酒。过往的行人象看希罕,摊主倒上劲,“来,使这个。”老太太给我们放了3只空碗。
“好,来就来个痛快。”灰哥掏出钱夹,冲王雷“啪”地一拍,“去,再来一瓶。”
灰哥要过酒,冲着3只碗一气倒光,“我看你们还欠着点,干了算了。”他端起了碗。
我们惊疑地看着他。
“看我脸红了不是?一会儿就过去了,来,酒是粮食精,干!”他一饮而尽,又亮了亮碗底,我们趁机泼去多半。
“真是真人不露相,灰哥门高量大,真没想到。”
“这是硬功夫,在下面练出来的。”灰哥脸上透着红光。
“基层就是锻炼人。”
“那当然,要不,我还是个孩子呢。”王雷朝我一笑,递给灰哥一支烟,擦着火柴:“灰哥,听说你原先在县委呆过一年?还听说他们称你是90年代的年轻人?”
“那时太年轻了,天真得很,啥都看不惯,他们也看不惯我。开会积极发言,有人说你比领导表态还快;学习文件指正他们的错别字,有人说你露*能……”灰哥目光滞涩。“那时候我跟头栽得多了。就说那次五四青年联欢会,我是组织成员之一。那次汇报演出非常成功,特别是男女对舞节目一推出,满堂喝彩,我晕晕乎乎地跳着,就象多喝了酒。谁知第二天一上班领导就把我叫去了。说那个节目是你搞的?尽出洋相。我说这有什么,城市都热几年了,很快会普及到下边的,也很受观众欢迎么。欢迎什么?观众是看稀罕哩,你听到下面议论了没有,你把我们单位的牌子也送出去了!”
“后来呢?”
“后来?”灰哥沉痛地拍下桌子,“缩着头,不敢动;不甘心,还想动,又不敢动。真折磨得够戗。就这样弄了个偏头疼。”灰哥拍了拍脑袋,露出痛苦的神情。
我要了3碗馄饨汤,灰哥端起来手打颤就放下了。
“省里抽调人去看守犯人,领导找我谈话,我哭喊着不去,结果就被调到了档案局。我的脑筋算是转过来了。在社会上混不住人不行。我就脱胎换骨地改造自己,规规矩矩老老实实,香的臭的都能要。我还学会了抽烟喝酒,和老同志坐下来吹旱烟袋,我连眼镜也摘掉了。不瞒你们说,我还给局长家里拉过煤球买过面粉,甚至还给他擦过自行车,跟着赴酒场当他的酒坛子。”灰哥扔掉烟屁股,一气把酒喝光,站了起来。
我们一起走了。酒喝得多了不敢晃,一晃就想吐,我们走得很慢。迎面吹来一阵风,浑身清爽,天上繁星抖了抖,有一颗站不住脚,划道亮光跌下去了。
“怪不得你眯着眼睛看人,不戴眼镜还要发展哩!”
“戴它与人合不来,别人看你别扭。”
“管他那么多。我明天还要穿西装哇!”王雷打赌似的。
“你穿我也穿,咱们一起穿。”我也来劲了。
“穿那个大开口,我会感冒的。”灰哥摸摸衣领。
“穿件西装你感冒,跟老婆睡觉你还伤风呢!她是谁?你老灰真是黑瞎子敲门熊到家了。”王雷手一亮,竟是个姑娘的照片。
想不到灰哥还真有一手,照片上的姑娘正是他的对象,是在高中就谈好的。她中专毕业后在县医院当护士。为了注意影响,灰哥守口如瓶,调来快一年了,也没让姑娘来过一趟。这事暴露以后,我们谈起男女之间的事情,灰哥也不再那么正经了,也时常爱插话,有时还滚到床上闭住眼。我们建议让姑娘来一趟,让弟兄们欣赏欣赏。
姑娘还真的来了,不过是她找上门的,她来市里短期培训。姑娘一进门就把我们给镇住了,她长得很好看。说好看不如说耐看,这主要与她的气质有关,垂两条长辫,自自然然大大方方。她把兜里的柿子掏出放在桌上,一人递一个,微微一笑,说:“吃吧。”声音很顺耳,不高不低柔柔和和,就跟她人一样。
一直到很晚,我们还没有睡着,灰哥送姑娘回来了:
“老灰,这个了吧!”王雷在被窝里拍拍自己的嘴巴。
“明天还让她来吧灰哥,在一块多坐会儿。”我说。
“算了算了,碰到好多熟人,要惹闲话。我是跳门进来的,裤裆挂破了。”他一屁股蹾在床上,压得床嘎嘎响。
我们一直劝他赶快结婚,结了婚就不显眼招人了。
灰哥果真宣布要结婚了。
灰哥旅行结婚,伙计们都给他送了礼。这个老灰,总有满腹的心事,都要做新郎官儿了,还没一点喜气劲,反 倒显得更深沉了。
行前的一天晚上,他把我们请到附近的一个小酒馆,点了菜,把带的好烟好酒什锦糖往桌上摆着。不知怎么回事,他今晚话很少,格外严肃。
“灰哥,是先回去还是就打这儿起程?”
“打这儿,票已经买好了。”
“路线定哪儿?”
“走着说吧。”
“明天嫂子来吧?”
灰哥停住了。他的目光停在桌上,面色阴沉。
“灰哥,你精神也不要太紧张了。”
“你是不是有什么难处?”“我觉得这事不说对不住你们,今晚正要谈谈,”灰哥抬起了头,板着脸,“我后天跟小罗走。”
“什么小罗?”
“工会的资料员。”灰哥的嗓音变了。我们面面相觑。
“你是说那个小茶壶?罗老头的小姐儿?”王雷沉声问。
灰哥没有吭声,他额头上有了些碎汗。我们谁也没有说话。那个小茶壶我们都很讨厌,又矮又胖,走起路来还好一手叉腰,扭屁股摆肩膀,一张口就是俺爸俺爸,在舞会上谁都不愿跟她跳。
“咱们怎么一直不知道?”
“一个月前才说的,说现在就要结婚,我也感到突然。”
“你是看中闰女啦还是看中老子啦?”王雷站了起来。
“大树底下好乘凉吧。”
“苟富贵,莫相忘啊。……”伙计们都站了起来。
灰哥脸色苍白:“我怎么说好呢,罗、罗书记托人说的,你、你们让我咋办,我们都在这里工作……”他忙给我们让烟,手抖抖的。
“好一个驸马儿!”王雷一下把烟打开,抄起桌上的一瓶酒“啪”地摔碎在地,掉头就走,我们都往外走。“哎哎,别走别走,菜都开始上了。”店主老头端着盘子拦住,“恶心,熊包!”王雷冲他一吼,小老头缩身跳开了。王雷转身有板有眼地说:“我们大家一致祝你,一路顺风,四脚朝天。”
“你们走吧。”一声低沉的呻吟。我们回过头来,灰哥紧绷着嘴唇……我们还是走了。
灰哥搬走了,他当上了秘书科科长,成为市委领导的贴身人,不少人都知道市委有小小科长。
不久,市委班子进行了大调整。新来的市委书记还不到40岁,操普通话带变色镜,老牌大学毕业生,真是个硬梆梆的铁手腕,一到任他就来了几板斧。一板斧,使电业局占用市郊耕地正在兴建的家属大楼停工扒掉;二板斧,将搬迁户作难而变成三掉弯的新兴大道一线取直。接着三板斧四板斧撤换调动了一批领导干部,在全市引起了震动。
灰哥脸上的微笑不见了,他又整日心事重重的。于是机关里又有了关于他工作调动的传闻了。
作者简介张秉峰,男,1963年生,现在郑州大学中文系秘书班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