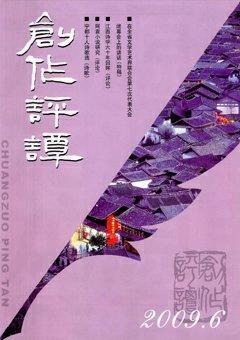生命的底色
邹 艳
我是一口气读完《星空肖像》的。起初是怀着“读读看”的心态,随后就转为一种敬意,迫不及待,挑灯夜读,直至最后一个字。傅菲的散文,总能给人亲切感,让人情不自禁地产生共鸣。我想《星空肖像》之所以让我着迷,应该归功于作品中传达出来的最质朴、最真实的生命底色。
人们常说人生百态,傅菲笔下的人生却是如此的简单。人活着就是为了“碗”,为了“米”,人生的归宿就是被我们天天踩在脚下的“泥”。《星空肖像》中的生命是一种不用雕琢、不用掩饰、更不需要欺骗的原生态,好比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人生在世,没有比吃饭更幸福的事,也没有比吃不下饭更痛苦的事。”(《米语》)“生活在枫林的人都知道,碗就是生活的全部。”(《碗啊碗》)“泥给了我们家园,又被我们抛却。泥是我们的父母,又让我们难以启齿。”(《泥:另一种形式的生活史》)。傅菲的散文就是这样,用最普通、最平凡的物象,传达最深刻最恒久的哲理。褪去一切功利,撩开所有虚荣,还原人类最原始的面目,是傅菲散文给人最大的感受,也是最令人产生共鸣的地方。六朝时吴均笔下的富春江“风烟俱净,天山共色”,天地之明净足以让“鸢飞戾天者,望峰息心;经纶世务者,窥谷忘反”。傅菲的散文同样如此,净化人的精神,让心灵得到休憩疗养。就如长期生活在水泥钢筋结构里的人们,走出四面围墙的空间,看到扑面而来的绿色,欣喜而不狂热,宁静而致远。
傅菲散文中抒写的是生命的底色,是人之初的纯真与明净,不带任何杂质与邪念。当上古的哲人厌烦了战火纷飞,寻找生命与宇宙的真谛时,他们为人类构想了理想社会,不论是老子笔下的小国寡民还是庄子笔下的至德之世,都呼唤人类本性的回归。一千多年前陶公笔下那个令无数文人墨客折腰的桃花源不也是“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么?
然而,傅菲散文中的生命原生态不是平静地铺叙,是透过沧桑、不动声色而成的,让人很不经意间就被感动与震撼。感动于文字的精致灵巧,震撼于字里行间流露出的“责任”。那种责任应该是“原色的,强大的,锋利的”,“具备担当时代苦难的责任”,而不是“杂乱,虚弱,伪情”,也不是“飘浮,简单,词语化”。傅菲的散文“适度地删除语言的诗意而保留生活的诗意,多写些人物命运的作品”(《郑小琼:在斑斓的画布上歌唱》)。《星空肖像》中描绘了一大群下层人物。如《米语》中视米如命的米馃叔叔,《是什么潜伏在我们的胸膛》中视生活比贞节更重要的酒馆老板娘,《碗啊碗》中没有文化,疏于管教儿子,而一味地压榨女儿的大姑,被母亲嫁了两次的爱香,《泥:另一种形式的生活史》中一辈子都在泥坛里打转、下葬时连坑都不用挖的老八伯,《蓝调小镇》中因离婚而被贬入小镇的庞,《米语》中为了孩子不挨饿,与男人相好一次就收一斗米的杀猪佬老婆……散文采用故事串联的方式写出了这些小人物的喜怒哀乐。为了“米”,杀猪佬让自己的女人与其他男人相好,全县第一支笛子的庞变得连歌也不唱了。在琐屑的甚至是卑琐的事情中读者感觉到的是扑面而来的生活气息。
《星空肖像》中不仅仅展现乡村的恬静和谐与人情味,也把农村生活中的“苦难”的一面真实地展现出来,完成了文艺作家对“真”的追求。正如傅菲说的,作家要让作品充满人性与苦难的光辉,照耀自己也照耀他人。因为苦难本是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具有生命最初的活力,这种活力足以让“苦难”这一主题获得永久的艺术魅力,《星空肖像》正是追求这样的永恒。书中写道:“我常问自己:人活着有什么意义……我用笔解剖人生。结果一无所获。但我已知道生活的艰辛,人性的黑暗。”傅菲对那个自己热爱的村庄也带着一个“想寻找什么”的愿望,“执着地把家乡一层层剥开”(《葵花的正午》)。文学创作崇尚真善美,崇高伟岸固然美,丑陋甚至畸形也能给人震撼而成就美。《巴黎圣母院》中的敲钟人加西莫多独眼驼背跛足耳聋,是一个极丑之躯,但他却抢救了被克罗德陷害的吉卜赛女郎,并把魔鬼克罗德推下了塔楼,加西莫多外貌的丑陋不仅没有损害他的美,反而衬托了他的心灵美。庄子笔下那个“颐隐于脐,肩高于顶,会撮指天,五管在上,两髀为胁”的支离疏身体残缺不齐,却代表了庄子追求的最高境界——自由的境界!苦难与丑陋畸形一样,在震撼人的同时成就着伟岸与永恒。
傅菲笔下的生命原生态还是诗性的,是用诗化的语言呈现出来的。《星空肖像》“声色字句间都氤氳着强烈的诗性,精致而深婉”(江飞《傅菲散文:个体精神与底层情怀》),如“低低的屋檐下站着数雨珠的童年”(《葵花的正午》),“小镇等待一只手,穿过记忆的甬道,触摸它隐藏的根部”(《让我们在拥抱中回忆》)等等。书中更令人无限好奇并向往的是那些充满诗情画意的江南的乡村风物,以及那份游荡在其间的少年的乐趣:
“春天拖着一双草青色的鞋,一路小跑,来到古城河边。我们分不清哪是读书声,哪是雨声,它们都同样的稚嫩,清脆,曼妙,像河边柳树密集的新芽……狭长的街道上,有迷蒙的黄昏黯然降临,店铺陆陆续续关门,一湾河水漂浮着几片绯霞。”
“六月的古城河是那样的肥美,河边的荆条花和野刺梨开出一丛丛的花,都是那般淡白,小朵。柳树浓绿,依依,披挂下来。穿条、鲅鱼、鲫鱼,在逐浪,不时地跃出水面,鱼鳞闪耀阳光的光泽。”
“我们也总能把课余活动扩充到古城河的北岸。北岸是古城山,山下有一片葱绿的菜地,和一个石灰窑厂。菜地种着黄豆,地瓜,番茄,玉米,黄瓜,红薯,远远看去,色彩浓郁,瓜香扑鼻。正午或晚自习前,我们就像一群特务,侦察好地形,呈扇形钻进菜地,饕餮一番。古城山并不高,海拔不到四百米,却岩石壁立,山腰上有一个长约百米的溶洞。山脊中间刀劈一般开裂,形成高约五十米长约两百米的一线天。这是我们的乐园。它是永远被我们破解不了的神秘,成为我们逃学的理由。我们带着菜地里偷来的地瓜番茄,带着小锄头,梦想着在溶洞里发现宝藏。塘底的村民说,有一天夜里,雷把山上的巨岩劈裂,房子大的石头滚落下来,全村人居然没有一个听见。这是一座神山,他们说。对于我们而言,这是一个迷宫。”
——《耳畔萦绕的雨声》
崇尚生命的本色,是傅菲散文的主旋,怀旧则是另一基调。傅菲在书中写道:“历史书上说,蒸汽机把我们推向工业时代,而我固执地认为,是水泥消灭了我们的庄园,楼房像叠起的火柴盒,水泥路是我们永远无发愈合的伤疤。我仇恨水泥。瓦在消失,窑成了废墟,作为村庄的胎记和摇篮,我们失却了。我们无法寻找歌谣扩散的地方,无法寻找那条出生的河流,虽然它有着哀与痛,血与泪。”(《烈焰的遗迹》)现代都市生活常常会令人感怀过去,渴望回归。当人们享受着现代文明带来的便捷和刺激时,常常也会为其困扰。就如,网络缩短时间和空间的距离,将整个地球变成一个村落,给我们带来便利也会带来毁灭,隐私的泄露、色情与诱骗,都可能将乾坤颠倒。随着作家从乡村到镇上,再到县里,怀旧的情结也越发的浓厚,“小镇没有变,变的是生活。小镇,我很少去了。伤感是难免的。这种伤感,不是说小镇给我带来了多少不快,相反,它给我的快乐,远远多于我寻找快乐的本身。它是我们青春期的见证,是祈祷词。我不忍回头再看。它过于美好。”(《油漆桶里的落日时分》)《星空肖像》中,怀旧是一种感恩,是一份恬静。
《星空肖像》是傅菲自《屋顶上的河流》之后的第二部散文集,为他的饶北河散文系列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星空肖像》共有22篇,除了上述所引用的篇目外,还有《异乡人的记忆源头》、《液态的山岗》、《水波一样散去》、《是什么使我不由自主地仰望星辰》、《棉花,棉花》、《不要像我如此悬浮》、《一条没有归宿的河流》、《草叶上的雪》、《胎记和釉色》、《务虚者的饶北河》、《南方的忧郁》。书中写的仍旧是那个生他养他的村庄,写那里的人们的悲欢离合,写作者的成长的足迹……“我血液的上游,是一条河流的出生地,它是我观看、审视这个世界的坐标原点。虽然那里慢慢暮色四合,露水从草尖涌出,灵山低垂慵倦的额头,木质的小窗里传来轻轻的咳嗽,是那般的唯美,但我能从他们每一个人身上看到生活战车碾过的痕迹,或者说,他们是战车的本身,手是他们赤膊战的唯一武器,我愿意把这本书献给他们”(傅菲)。
洋溢着浓浓的传统气息,很美,但有些深沉,芬芳醇厚,耐人寻味,这就是“70后”作家傅菲的《星空肖像》。
(作者为南昌大学中文系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