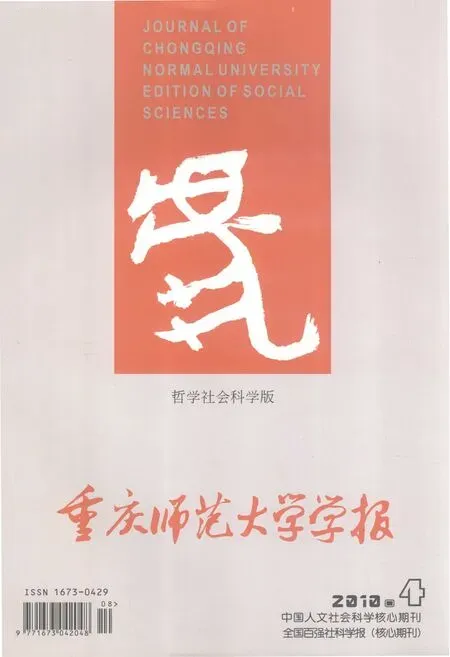“致良知”视野下的教育思想
廖 小 波
(重庆师范大学 发展规划处,重庆 400047)
“致良知”视野下的教育思想
廖 小 波
(重庆师范大学 发展规划处,重庆 400047)
教育可以为社会成员提供合乎社会目标的社会价值观和社会行为模式,可以调适人际关系,制约和指导社会成员的社会行为,它是社会控制的手段之一。王阳明以“致良知”作为其教育思想的核心,致力于将社会民众培养为符合封建准则的理想角色,在一定时期和一定区域内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王阳明;“致良知”;心即理;教育思想
王阳明(1472~1529),原名王守仁,字伯安,祖籍浙江。生于明宪宗成化八年(公元1472年),死于明世宗嘉靖七年(公元1529年)。因他在距越城不远的阳明洞结庐讲学,后又创办阳明书院,因此学者称他为阳明先生。王阳明是明代的思想家、教育家、军事家和政治家。从其“心即理”的哲学思想出发,王阳明总结了一套自己的教育思想并加以具体实施,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教育思想体系。
一
教育理论是通过教育的概念、判断或命题,借助一定的推理形式构成的关于教育问题的系统性的陈述,是对教育现象或教育事实的抽象概括,具有系统性的特点。作为教育思想的出发点,它决定了教育的目的、方法与手段。王阳明的教育理论就是其心学思想的基础,即“心即理”。
程朱一派把宇宙万物都归结为“理”,使“理”成为一种超越的绝对。在他们的思想体系中,人被某种外在的原则所规定,人的道德本性由绝对的天理从外部植入。所以在本体论上,程朱是以“性”来界定的,“盖所谓性,即天地所以生物之理,所以维天之命,于穆不己,大哉乾元,万物资始者也。”[1](《答李伯谏》)朱熹认为“性”,是人物所以生的“理”,是“生物”的资始。由此,他所谓的“性”,即“理”,是万物之所以产生发展的根源,是世界的本体。与正统理学一再提升性体并将其形而上学化不同,王阳明的关注点首先是心体。王阳明理论体系的最高范畴是“心”。他承认理学的共同前提,即“天地万物”与人是一体的。但他认为宇宙统一的基础并非绝对的天理,而是“心”。他说:“人者,天地万物之心也。心者,天地万物之主也。心即天,言心则天地万物皆举之矣。”[2](《答季明德》)他断言“心”是天地万物的主宰,是宇宙万物的本原。对此,他解释说,“天下之事,虽千变万化,而皆不出于此心之理,然后知殊途而同归,百虑而一致”[2](《约说》)。王阳明认为:“心”包含了天地间一切事物的条理,能变通天下之事的千变万化,因而是世界的本体。为了证明“心”具有本体地位,王阳明又提出了“意之所在便是物”的命题,以此来作为佐证。他说:
身之主宰便是心,心之所发便是意,意之本体便是知,意之所在便是物。如意在于事亲,即事亲便是一物;意在于事君,即事君便是一物;意在于仁民、爱物,即仁民、爱物便是一物;意在于视、听、言、动,即视、听、言、动便是一物。所以某说无心外之理,无心外之物。[2](《传习录》上)。
在王阳明看来,“心”是宇宙万物的本质和存在的依据,要先有“心”,才有“意”,也才有“物”,才有世间的一切。他将“心”从主体意识提升为宇宙本体,天地间一切事物都是“心”的表现,所以“心外无理,心外无事”[2](《传习录》上)。
在将“心”规定为宇宙本体时,王阳明又提出了“心即理"的命题。他说:“心即理也。天下又有心外之事,心外之理乎?”[2](《传习录》上)“心也者,吾所得于天之理,无问于天人,无分于古今”[2](《答徐成之》)。
王阳明以“心”为宇宙万物本体,消除了绝对精神“天理”与主体精神“心”之间的隔阂,凸显了主体的自尊自善,这不仅是理论模式的转换,而且具有更直接的现实意义。所谓“心即理”,这个“理”实质上就是儒学一贯强调的纲常伦理,即仁、义、礼、智等道德原则,也就是“良知”。王阳明认为,道德不是外在的强制,不需要通过某种绝对观念植入人心,它直接就是每个人先验的本质,只要扩充固有的良知,也就能成就至善的品格。
因此,王阳明在教育理论上认为:宇宙万物的本原是“心”、“理”或“良知”,这个本原含有先验的道德律,又是存在于每一个体之中的。这样一来,王阳明认为由于“心”产生一切,因而在社会变迁中,世人的种种言行不一,生活世俗化等对封建纲常造成冲击的意识和行为也是由他们的“心”发出来的,要控制住他们的这种思想和行为,必须着重于从教育上控制住他们的“心”,教育民众在他们的内心下功夫,去启迪他们每个人心中的“良知”,让他们体认到内心良知,也就自然地控制住了他们的思想和行为。“心即理”即封建统治的伦理纲常应该是根植于人心中永恒不变的绝对真理。通过这个“心即理”的理论,王阳明确立起了他对社会各类成员实施教育的目标和依据,而通过何种方式达到此目的,这又是一个必须回答的问题。
二
为封建统治提供一套治国治民的理论,探寻人按一定秩序和谐相处的途径,建立合乎道德的社会体系,维系社会的稳定与延续,是历代儒家不懈索求的理想。王阳明所追求的教育目标就是要人们以封建道德规范作为思想和行为的准则,按封建伦理纲常和封建等级制度来和谐共处。通过对世人的教育,把个体培养成符合“天理”的规范,达到所谓的“大同世界”。
理学诞生的标志是二程正式提出“天理”的概念。他们认为“吾学虽有所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体贴出来”[3](《河南程氏外书》卷十二)。“天理”这个概念,据张立文先生考证,始见于《庄子·养生主》“依乎天理,批大御,导大寂。”是指解牛的道理或天然的分理。[4](523)二程说是“自家体贴出来”的,其原因就在于他们赋予了“天理”以新的内涵:“天理”即是三纲五常。后来,朱熹继承了二程的观点,对“天理”的内涵加以肯定,他说:“所谓天理,复是何物?仁、义、礼、智岂不是天理?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岂不是天理。”[1](《答吴斗南》)
因此,理学家所说的“天理”即是指封建社会的伦理道德,之所以称这为“天理”,是企图将封建伦理说成是先验的、永存的。这种天理,既是封建专制主义和皇权进一步加强在思想理论上的表现,又是地主阶级封建专制主义政权的精神支柱。“天理”代表着封建政权和封建等级秩序,对“天理”的肯定和维护,就是对封建专制政权的认可和巩固。
与其他的理学家一样,王阳明属于明中期封建政权中的统治阶级,坚信代表封建纲常伦理和其政权的“天理”是万古不灭的“真理”,对其的权威性从未有过丝毫的怀疑。明朝中期频繁的农民起义,对封建政权造成不断冲击,而当时世人趋利而行、道德沦丧的种种现象也使得封建纲常日益丧失了约束力,“天理”在这种社会变迁中隐隐地显露出了危机。在这种状况下,王阳明挺身而出,自觉地肩负起了维护“天理”的重任。他一生讲学、办学校,建“事功”,追求的就是这个“天理”。
从王阳明的学术思想来看,他认为“天理”是为学的最高目标,读书做学问的最终目的就是要达到对这个“天理”的体认。曾有弟子问他为学“主一”应主在什么地方,他回答说:“好色则一心在好色上,好货则一心在好货上,可以为主一乎?是所谓逐物,非主一也。主一是专主一个‘天理’。”[2](《传习录》上)他认为一心用在“天理”上,这才是真正的“主一”。在回答学生另一个关于“立志”的问题时,王阳明也是强调“天理”的目的性:
问立志。
先生曰:“只念念要存天理,即是立志。能不忘乎此,久则自然心中凝聚,犹道家所谓结圣胎也。此天理之念常存,驯至于美大圣神,亦只从此一念养扩充去耳。”[2](《传习录》上)
王阳明认为“志”于心中立,心在理中存,心中不离天理,这就是圣人之志,圣人之志不离天理。
理学家认为“天理”是纯善的,而人有私欲;为保持“天理”的纯洁性,将人们的思想和行为控制在封建纲常之下,就必须“存天理,去人欲”。出于同样的目的,王阳明在为学、讲学中,也主张“存天理,去人欲”,强调“天理”、“人欲”不并立。他说:
心即理也。此心无私欲之弊,即是天理,不须外面添加一分。此心纯乎天理之心,发之事父便是孝,发之事君便是忠,发之交友、治民便是信与仁。只在此心去人欲、存天理上用功便是。[2](《传习录》上)
王阳明认为要使人们的行为控制在封建纲常规范之中,使人们对父“孝”、对君“忠”、对友“信”、对民“仁”,就要在“存天理、灭人欲”上用功,以“天理”为控制目标,要求世人体认“天理”:
要此心纯是天理,须就“理”之发见处用功……。如发见于事亲时,就在事亲上学存此天理;发见于事君时,就要在事君上学存此天理;发见于处富贵、贫贱时,就在处富贵、贫贱上学存此天理……。至于作止语默,无处不然,随他发见处,即就在那上面学个存天理。[2](《传习录》上)
王阳明一再强调在“天理”上用功,无论何时何处,都要以封建道德律作为行为的准绳,将自身的一言一行都控制在“天理”上,他认为这才是实施教育的最终目的。
从王阳明生平的每一步来看,他无时无处不是将“天理”放在其社会政治生活的重心上。他一生所努力追求的,就是要以“天理”作为教育目标,要世人“存天理,去人欲”,做封建社会的顺民。在这一点上,他和所有的宋明儒家是一致的。
三
教育的目的和功能,就是要帮助人从现实习性回归到自然的善的本性,把坏人变成好人,把恶人变成善人,这就是成功的教育。
在王阳明看来,“良知”不仅是停留在人们的思想中,而是要具体地展现于事亲事君等封建道德践履之中。正是在事亲事君、“应事接物”的活动中,它才具体地转化为“孝”、“忠”等人内在的自觉意愿。因此要人们“致良知”,则应是“致良知”于事事物物之上。他说:
格物致知云者,致吾心之良知于事事物物也。吾心之良知于事事物物也。吾心之良知,即所谓天理也;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则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致吾心良知者,致知也:事事物物皆得其理者,格物也,是合心与理而为一者也。[2](《传习录》中)
王阳明认为,只有在与外界事物的接触中,良知才能发用流行,才能显现出来;而人的私欲是否已经克去,良知是否已经回复,这同样要在接触、处理事事物物中才能得到验证。所以“致良知于事事物物”,就是要人们按照“良知”行事,以封建道德律作为行为规范,抛弃不按“良知”、不遵守封建伦常的“不良行为”。由此出发,对于广大的民众而言,王阳明特别强调在日常生活中为善止恶,去除“人欲”,他说:
举业辞章,俗儒之学也;薄书期会,俗吏之务也;……君子之行也,不远于微近纤曲而盛德存焉……公以处之,明以决之,宽以悟之,恕以行之,则不远于薄书期会而可以得古人之政,是远俗也。[4](《远俗亭记》)
“不远于微近而存盛德”,意即在日常社会生活中保持“德性”,即封建伦常。由于道德规范总是存在于社会生活中的各个方面,而每个主体又总是处于某种既定的社会环境中。对于主体来讲,前者是一种不可选择性的环境,而主体行为则具有选择性。主体在道德实践中的能动性恰恰在于:在不可选择的环境中自主地通过日用常行进行修养,将封建道德展现于具体行为中。王阳明“即俗而远俗”,“不离微近纤细而盛德存”的观点,显然含有这方面的意思。
王阳明“致良知于事事物物”的主张,落实到社会控制上,也就是要求世人不论是做官、读书,还是劈柴担水、行走买卖,不论是高高在上的统治阶级,还是卑微的贫苦农民,不论是在内心对社会规范有违背念头的“心中贼”,还是聚山为王、落草为寇的“山中贼”,都应保持其内心的“良知”,并在进行社会实践中都要将心中的“良知”发挥出来,即“致良知”于具体行为中,做到随时随地以封建道德律为行为准绳,以将行为主体控制在封建纲常伦理之中。因此,王阳明的教育对象不分贵贱、贫富,也不分“良”“善”。教育活动则贯穿于他的从政生涯,成为他施政、建“事功的”最重要方法之一。
(2)针对辨识内容要准确把控好三种时态,即过去时态、当前时态以及未来时态。事件的演变是在不断向前发展的,危险源识别时需要对过去时态进行明确,对当下时态进行研究、对未来时态进行判断,从而有效衡量企业生产的真实状态,并对危险因素是否存在进行准确判断。
四
教育方法是指在教育思想指导下形成的用以实现其教育目标的途径,运用正确的教育方法,对能否提高教学质量,实现教育目标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从思想行为学来看,人的思想是在教育和受教育的过程中形成、发展的,人的行为是其思想的外部表现,明显地要受个人思想状况的支配和调节。一般来讲,思想是行为的原因,行为是思想的结果。一个人有什么样的思想,就表现为什么样的行为方向和行为方式。王阳明从“心即理”的思想出发,主张通过外部诱导——教化,让众多的民众诚心诚意地“格”去“心”中的“欲”,去其“心”之“不正”,从而自觉遵从封建规范。这种方式也就是要通过道德教化,把封建价值观念和封建社会规范内在化,使人民自觉地用之以指导、约束和检点自己的行为。虽然人人都难免有违背社会道德的冲动,但通过教育,使得封建社会规范一旦内在化了,行为主体就可以心甘情愿地抑制这种冲动,将心中的“人欲”念头“格”去。因此王阳明认为,教育措施是最长久的、最有保证力的控制手段,他一生致力于对民众的教化和讲学,将教育作为施政的重要手段,就是由此而引发的。
在实践教育的过程中,王阳明针对当时实际,提出了自己有别于世俗的教育方法。他突破了当时士大夫认为只有通过读书识字才可以成为圣人的观念,一反传统教育以知识作为衡量人格的标准,提出通过“致良知”把人的内在精神转化为道德自愿,以人人成其“圣人”为目的。在教育内容上,王阳明认为先要人“成德”,学校教人体认天理,认同于封建规范。这其实是他“正心”的格物思想在教育上的反映。因此,王阳明在谈论教育内容时,往往只讲人伦道德,不谈知识技能,并认为“三代之学,其要皆所以明人伦”,“非若后儒所谓充广其知识之谓也”。[5](《大学问》)由此看来,王阳明在教育思想上首先将教化对象由读书之人扩大到全社会所有阶层,又将教育内容仅限定为封建礼义,强调以封建道德教育为主,具有很强的阶级性和功利性,其教育目的完全是从社会控制出发,为封建政权服务。
王阳明这种教育思想也是他从实际政治生活中得来的。王阳明一生曾多次领兵镇压农民起义和少数民族起义,深深体会到仅用刑治是不足以统治人民的,必须对民众进行礼义道德的教育。他认为只用刑法,是“以火济火”,无益于治,“若教之以礼,庶几所谓小人得道,则易使矣”[2](《牌行南宁腑延师讲礼》)。此外,面对明中期社会上重“利”轻“义”、封建纲常淡漠的种种现象,王阳明认为要从人“心”上下功夫,主张“教民成俗,莫先于学”[2](《批立社学师老名呈》)。因此,王阳明以自己的心学思想为指导,通过以下诸方面致力于教育。
1.讲学。王阳明一生讲学不辍,以宣传他的心学思想,启发世人的“良知”。1507年,徐爱等三人正式拜他为师,“及门莫有先之者”[6](卷十一《浙中王门学案》),由此王阳明开始正式收徒讲学,宣扬其心学。被谪龙场,王阳明成立了他自己第一个书院——龙冈书院。书院规模虽不大,但在边鄙之地,却产生不小的影响。王阳明在讲学之余所作诗中,已有“门生颇群集”的描述,可见当时求学者已不少。为使书院规范化,王阳明还制定了学院的规条,“一曰立志,二曰劝学,三曰改过,四曰责善”[2](《南游三首》)。龙冈书院的讲学,使得王阳明的才识逐渐为人所知。1509年,受贵州提副史席书相邀请,他到府城文明书院,开始宣讲他的知行合一学说;1512年王阳明任南京太仆寺少卿后,讲学规模逐渐扩大,在滁洲督马政问学的人大增,“日与门人游邀琅琊瀼泉间,月夕则环龙潭而坐者数人”[2](《年谱一》1236)。此后,他先后在赣州、南宁、浙江创办了濂溪书院、南宁书院、稽山书院,收徒讲学,此时其弟子已众多,“环先生而居此屋者,如天妃光相诸刹,每当一室,常合食者数十人,夜无卧处,更相就席,歌声彻昏”[2](《传习录》下)。在稽山书院时,弟子来自四面八方,以至于“宫刹卑隘,至不能盖环坐而听者三百余人”[2](《年谱三》1290),达到了讲学的高潮。王阳明不仅一生致力于讲学工作,弟子甚多。而且他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其学说日益简易精微,施教方式日益真切高明;他既能折服奇才异能之士,也能深入普及,启发一般的田野俗人。当时顽强如王艮、王畿,傲慢如唐尧臣,位高如方献夫,年老如董萝石等等,都对他拜倒,愿称弟子。王阳明通过自身收徒讲学来宣扬其“致良知”,力图影响当时的学风和社会风气,重振纲常。
2.兴办社学。王阳明为让众多民众体会“致良知”的思想,一生讲学不止。但相对于全国范围来讲,影响毕竟有限。因此王阳明一边建书院讲学,一边在全国各地兴办社学,向民众宣讲封建伦理道德。如他在广西思田、赣南完成军事镇压后,认为“民风不善,由于教化未明”,要各县“兴立社学,延师教子,歌诗习礼”,[2](《年谱一》1253)用封建道德礼义来教化民众。王阳明之所以这样做,是企图将封建价值观灌输进民众的内心,使之成为他们内在的道德品质,从而达到既“革面”、又“革心”的目的,用封建纲常来控制社会。
据《年谱》记载,王阳明在赣南结束军事镇压之后,并未一走了之。“先生谓民风不善,由于教化未明。今幸盗贼稍平,民困渐息,一应移风易俗之事,虽未能尽举,姑且就其浅近易行者,开导训诲。即行告谕,发南、赣所属各县父老子弟,互相戒勉,兴立社学,延师教子,歌诗习礼。出入街衢,官长至,俱叉手拱立。先生或赞赏训诱之。”这次办学非常成功,效果很好,“久之,市民亦知冠服,朝夕歌声,达于委巷,雍雍然渐成礼让之俗矣”[2](《批立社学师老名呈》)。
王阳明这种将封建价值观念和社会规范内在化于民众中,使他们心甘情愿地用之以指导、约束自身行为的教育措施,是根源于他“致良知”的哲学思想,力主从人“心”上做功夫,施教化。其目的就是希望在世人心中激励起他们的封建道德荣辱感和羞耻感,让他们重新树立起封建价值观,从而引导世人“存天理,灭人欲”,做封建社会的圣人、顺民。
4.制定乡约。为了加强对封建社会最基层的教育,王阳明采用了乡约模式。正德末年,王阳明镇压了江西、福建、广东、湖南四省交界之处的农民起义后,“以为民虽格面,未知格心,乃举乡约,告谕父老子弟,使相警戒”,要他们“和尔邻里,齐尔姻族,德义相劝,过失相规,敦礼让之风,成淳厚之俗”,[2](《年谱一》1256)并亲自撰写了《赣南乡约》颁布各地。其《乡约》的基本内容是:用封建道德纲常教育村民族众,防止农民图谋“不轨”,保证封建国家的财政收入和地主阶级的剥削,用舆论和道德的力量劝诱民众改过从善。这种乡约组织十分严密,王阳明还规定要公推年高有德为众敬服的一人为约长,二人为约副,四人为约正,四人为约史等,管理全约及民众。
王阳明的乡约方案,极大地影响到整个明代中后期社会的伦理道德、价值观念、行为规范以及群体关系、社会结构、政治体制、行政管理等许多层面。嘉靖、万历年间,乡约己在全国推广。这种乡约模式,作为巩固明代政权基础——乡村社会的精神武器和组织工具,发挥了重要作用。
王阳明以“心即理”的思想为出发点,形成了自己的教育思想体系。将对民众的封建道德教育作为其主要的施政,主张对全社会的民众进行普遍的道德教育,并且自己一生讲学、办社学、建书院,将这种思想转化为了具体的行为措施。从当时的状况来看,这种思想也确实为巩固封建政权起到了一定的效果,先人评价为“故尧汤相禅全在事功。孔孟无事功,为千秋大憾,今阳明事功,则直是三代以后,数千百年一人”[7]。
[1] 朱熹.朱子文集[Z].商务印书馆,1936.
[2] 王守仁.王阳明全集[Z].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3] 程颢,程颐.二程集[Z].中华书局,2004.
[4] 张立文.朱熹思想研究[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5] 叶绍钧校注.王文成公全书[Z].上海商务印书馆,1927.
[6] 黄宗曦.明儒学案[Z].中华书局,2008.
[7] 毛奇齡.王文成传本[Z].台北:新文豐,1989.
B248
A
1673-0429(2010)04-0043-05
2010—05—08
廖小波(1970—),男,重庆师范大学发展规划处,副教授。
重庆市教育规划项目“王阳明教育思想及其体系研究”(项目编号:08-GJ-2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