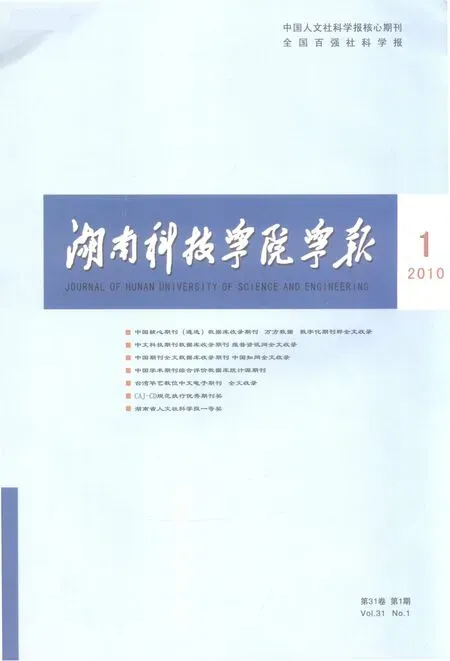胡瑗《周易口义》对儒理的阐发
黄 曦
(福建师范大学 文学院,福建 福州 350007)
胡瑗《周易口义》对儒理的阐发
黄 曦
(福建师范大学 文学院,福建 福州 350007)
胡瑗是宋代易学儒理宗的代表人物,其治《易》以“阐明儒理”为特似。而《周易口义》是其以易学阐明儒理的代表着作,颇为程子、朱子所推崇。文章通过分析《周易口义》注重人事、博引群经、排斥老庄等三个特点,体现《周易口义》乃至宋代儒门易学对于儒理的重视程度,对胡瑗的易学进行了初步的研究。
胡瑗;《周易口义》;天道与人事;儒家经典;老庄
胡瑗(993~1059)字翼之,世称安定先生。泰州如皋人。为宋初三先生之一。颇为历代学人所矜式。其《周易口义》是宋代重要的易学著作。邵伯温《闻见前録》记程子(程颐)与谢湜书,言读易当先观王弼、胡瑗、王安石三家。盖因为三家不论互体,文义坦明。而宋易学的一大特点,便是能够“急乎天下国家之用”[1]《四库总目易类提要》曰:“王弼尽黜象数,说以老、庄,一变而胡瑗、程子始阐明儒理。”[2]考之《周易口义》,其易说或因易理阐发儒理,或借儒理以解释易义,或以天道言及人事,或藉人事阐发天道。以义理为宗,开伊洛之先。今拟就《口义》一书阐发儒理的特色略陈固陋,体现其义理易学特色、及对王弼义理易学的发展。
一 天道与人事的贯通
以天道比拟人事,是义理学派阐释《周易》一大特点。《繋辞》曰:“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说卦传》曰:“昔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孔颖达《周易正义》曰:“先儒皆以上经明天道、下经明人事,然韩康伯注《序卦》破此义云:‘夫易六画成卦,三才必备;错综天人,以效变化。岂有天道人事偏于上下哉’”[3]
《易》之为书,广大悉备,可推之以天道,可切于人事。《周易口义》正是把握了《易》的这一特点,多以《易》言及人事,发挥圣人之旨。《周易口义 发题》曰:“文王有大圣之才,罹于忧患。观纣之世,小人在位,诈伪日炽。思周身之防,达忧患之情;通天人之渊藴,明人事之始终。遂重卦为六十四,重爻为三百八十四。”这里开篇即明《易》为“通天人之渊藴,明人事之始终”而作,而在《周易口义》中也多见“以人事言之”、“言之人事”之注解方法以明圣人之旨。
王得臣《麈史》曰“安定胡翼之,皇祐、至和间国子直讲。朝廷命主太学。时千余士日讲《易》。余执经在诸生列。先生每引当世之事明之。至《小畜》以谓‘畜,止也。以刚止君也巳’。乃言及中令赵公相艺祖。日上令择一諌臣。中令具名以闻。上却之弗用。异日又问,中令复上前札子,亦却之。如此者三,仍碎其奏掷于地。中令辄怀归。他日复问,中令仍补所碎札子呈于上。上乃大悟,卒用其人。”[4]按:“赵公相艺祖”即宋初名相赵普。此藉赵普之事以释《小畜》,今虽不见诸《口义》,然考之其书,以人事释《易》之法却极为普遍。兹抽取数条为例:
(一)因阴阳以言人事之例
如:释《坤》初六“履霜坚冰至”曰:
于履霜之时则是其迹已见,故可以推测其必至于坚冰也。以人事言之,则人君御臣之法。此其始也。牛人之深情厚意,不易外测。故大奸若忠是也。然为臣而佐君必有行事之迹,于其始,善善恶恶可得而度之。故在人君早见之也,见其人臣之间,始有能竭节报效,则知终必有黄裳之吉,乃任而用之。使之由小官至于大官。则为国家之福。若奸邪小人,其有谄佞之状,一露则知。积日累久,必至于龙战之时。故当早辨而黜退之,则其恶不能萌渐也。若使至于大位,以僭窃侵陵则恶亦不易解矣。是由履霜之积,积而不已,终至坚冰。是 辨之在始也。
按:“履霜坚冰至”为阴气始生之象,阴气开始凝积,故可推测坚冰必将到来。这里以阴比喻人臣,以履霜之象言人君御臣之法,当防微杜渐,辨之在始。举竭节报效之贤臣,黜谄佞之奸臣。
(二)因上下二体以言人事之例
如:释《小畜》卦辞“小畜:亨;密云不雨自我西郊”曰:
牛阴阳交则雨泽乃施。若阳气上升而阴气不能固蔽则不雨。若阴气虽能固蔽而阳气不交,亦当不雨。犹若釜甑之气以物覆之则蒸而为水也。牛东震、北坎皆阳方。其阴气上交于坤位则雨矣。南离、西兑皆阴方,其云气不能为雨。今言自我西郊,是云气起于西郊之阴位,必不能为雨也。以人事言之,则犹君之邪恶已形,而又有便佞之臣,左右逢迎其志。其间虽有一二牛正之人,亦必不能止矣。牛君欲既行而谄谀以滋之,臣又不能止畜,则膏泽何从而下哉?
按:《小畜》卦下乾上巽。而巽之为体柔顺,必不能止御下乾之上进。胡瑗因上下二体的特点以发明人事:以便佞之臣喻上巽,又以邪恶之君喻下乾。臣不能止君之邪欲,则君之膏泽不可得而下也。
(三)因爻位关系以言人事之例
如:释《井》九二“井谷射鮒,瓮敝漏”曰:
“谷”者, 谷也。“鲋”,即鲋鱼也,积秽之所生。“肯”者,停水之器。凡井之道所以汲取以济于物。今九二处下卦之中,上无其应而下比于初,犹 之水下注射于积秽之物;又如肯之犹败,其水下漏。是皆言其功不能上济于物也。以人事言之,君子之人有仁义之术可以济于天下,为生民之福而潜身晦迹,以自卑下,不务升进以行其道。其泽不能及于物,以是天下之所共不与者也。
按:《易》中凡例,对应之爻为一阴一阳则可交感,谓“有应”。若俱为阴爻,或俱为阳爻,必不能交感,谓“无应”。《井》九二与九五皆为阳爻,故九二不能上应,而与初六相亲比。胡瑗据此申之人事,以潜身晦迹之君子而喻九二,以戒君子不当以潜隐为德。
以上所举之三例,各从阴阳、二体、爻位出发,先释卦爻之大意,而后立以人事以明之。综观《周易口义》中所论之人事,多涉圣贤之事、君子之行、君臣之道、夫妇之序。胡瑗推天道以言人事,此种解《易》方法体现了其“明体达用”的治学特色。藉由这种解《易》方法,《周易》中的道理变得更切于实用,更贴近儒理。与汉儒注《易》多以训诂、阴阳候灾变为主的特点相较,更体现了宋代易学对义理、儒理的重视。
二 博引群经以释《易》
《宋元学案》谓胡安定十三岁已通五经,常以圣贤自期许。[5]考诸《口义》,知胡氏之释《易》,于《诗》、《书》、《礼》、《春秋》、《论语》、《孟子》诸经皆有征引。故以儒家经典明《易》理,是《周易口义》阐发儒理的又一方法。
考《周易口义》所释之六十四卦,其征引诸经者凡四十六卦,计八十七处、一百零八则。其中引《书》者十则、引《诗》者八则、引《礼经》者二十六则(含《周礼》、《仪礼》、《礼记》)、引《春秋》者十五则(含《左传》、《公羊传》、《谷梁传》)、引《论语》者二十三则,引《孟子》者二十三则,引《孝经》者一则,引《老子》二则。除引《老子》第五章“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两处之外,其余一百零六则,八十五处所引之经皆为儒家经典。
《口义》博引群经以释,其旨分为二:一、举群经中相类之文,以解释《易》中文字;二、籍群经中相关之理,以阐释《易》中奥旨。
引经以释《易》中文字者,如:释《蛊》卦之卦名:
“蛊”,坏也。按《左传·昭公元年》云:“皿虫为蛊, 之飞者亦为蛊”盖言三虫食一皿,有败坏之象,故云“皿虫为蛊”。又言 之积久坏坏者,则变而为飞虫,亦蛊败之象。故云“ 之飞者亦为蛊”。
辨《睽》六三“其人天且劓”之“天”当作“而”:
“其人天且劓”者,天当作“而”字。古文相类,后人传写之误也。然谓“而”者,在汉法有罪
其鬓发曰“而”,又《周礼·髠人》:“为笋 作而”,亦谓 其鬓发也。
释《萃》卦《大象传》“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
“除”,去也。言君子之人当此汝聚之世,民既和说,海内晏然。于是之时不可复用其兵。是必韬藏其弓矢,偃息其戈矛,以示天下不复用兵也。故昔者武王昔商之后,载 弓矢,八载干戈;归马于华山之阳,放牛于桃林之野。是所谓除去戎器者也。
(按:“载櫜弓矢”出自《诗经·时迈》,“倒载干戈”出自《礼记》,归马于华山之阳,放牛于桃林之野”出自《尚书·武成》)
以上三则分别引用了《左传》、《周礼》、《诗经》、《尚书》以释《易》中的文字。由于这些儒家经典皆出于远古,在文字上与《周易》有共通之处,故胡瑗在《周易口义》中常常引用这些经典以解释《易》中之辞。
引经以阐《易》中奥旨者,如:
释《否》六二“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亨”曰:
“大人否亨”者,若大德大才之人则不然。居是时也,以其道塞而不通,故能以正自守,韬藏其仁义,卷怀其道德,不为世俗之所变而不杂于小人之中。于否之世,行否之中道,所以全身远害也。《中庸》曰:“国有道,其言足以兴;国无道,其默足以容。《诗》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盖否之时不可进用,但以义而自处全身远害而已。《中庸》又曰:“素富贵行乎富贵,素患难行乎患难,君子无入而不自得焉。”是言大人君子,于否之时行否之道,所以亨也。故曰:“大人否亨。”
按:“包承”指《否》卦中六二顺承包容于九五,这是小人之道,而君子否定此道。胡瑗在此特引二则《礼记·中庸》之语以释其中奥义。认为君子当此之时,应当以自守正、全身远害。由于爻辞中所言之理尚有未尽之处,故引《中庸》以发挥其中奥旨。
无论是发挥义理还是名卦中之物,胡瑗所引典籍中,用得最多的还是儒门经典。可见胡瑗留意经籍,用功深厚,《周易口义》作为纯粹专精的义理易学,其思想是以儒家经典为根本的。
三 对王弼老庄思想的改造
胡氏《周易口义》受王弼之影响极深。朱彝尊《经义考》引董真卿之说曰:“胡氏著《周易口义》十卷,《系辞》、《说卦》三卷授其弟子记之。大抵祖王弼”。然《四库总目易类提要》谓王弼之释《易》说以老、庄,而胡瑗则阐明儒理。由此可知,安定易学源于王弼《周易注》,而对于王弼所阐发的老庄思想却弃之不用,代以儒理言之。前述其征引诸经者一百零八则,老子之语仅见二处,已可证胡瑗对老庄思想的排斥。今略举王注与《口义》所释数卦以相比较,则二人思想倾向易别矣。
(一)坤卦六二爻辞“直方大,不习,无不利”
《王注》:居中得正,极于地质。任其自然而物自生,不假修营而功自成。故不习焉而无不利。
《口义》:“不习无不利”者。言坤有三 ,自然而物生。故不待修习而后能。以人事言之,则君子之人,其德素蕴,其行素着。圣牛之事业已习之于始。至此用之朝廷之上,随时而行之。且非临事而乃营习。故无所不利。是以孟子四十不动心者此也。
按:王弼认为六二“不习无不利”的原因是六二自然具有“直方大”的特征,故不须后天的修饰。而胡瑗则以为六二“不习无不利”,并非自然而然,而是因为“圣贤事业,已习之于始,非临事而乃营习”。并以孟子四十不动心为例申之。
(二)《讼》卦《大象》“天与水违行,讼。君子以作事谋始”
《王注》:“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无讼在于谋始,谋始在于作制。契之不明,讼之所以生也。物有其分,职不相滥,争何由兴?讼之所以起,契之过也。故有德司契而不责于人。
《口义》:天之运行,则左旋而西。水之流行,则无不东流。以天与水所行既相违悖,则不相得。是讼之象也。君子之人当法此讼卦。凡作一事,必须谋其始而图其终。使争讼之端无由而起。以之居一家兴一事,则皆谋虑其初,使上下和睦,而绝闺门之讼。以之居一国,凡造一事,必须谋度其初,使人民和同,而绝一国之讼。若此之类,皆于其始慎虑之,则忿争辨讼自然可以息也。故孔子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其狱讼之事,得明牛之人听治之,而又谋之在始。则刑可期于无刑也。
按:二人释此《大象》,俱引《论语》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都肯定了《易》中“无讼”的观点。但是对于如何达到“无讼”的目标,二人看法却不一致。王弼认为,要达到“无讼”,在于“有德司契而不责于人”。而胡瑗则认为,要达到“无讼”在于“谋虑其初,使上下和睦、使人民和同”。《王注》的观点出自《老子·和大怨章第七十九》曰:“和大怨,必有余怨,安可以为善?是以圣人执左契,不责于人。故有德司契,无德司彻。天道无亲,常与善人。”而胡瑗的观点则来自于儒家“治国齐家”思想。
(三)《革》卦上六爻辞“君子豹变,小人革面。征凶,居贞吉”
《王注》:改命创制,变道已成。功成则事损,事损则无为,故居则得正而吉。征则躁扰而凶也。
《口义》:牛为革之道,必须以孚信固结于民。故九五之爻,为革之先倡。以革变其天下之暴乱。有才有位,文章显着,而又可于也。今上六体是爻过于九五而革道已成。且在上卦之极,履非首倡。又承水火变革之终,是臣民之位也。既在臣民之位,则当尽其至正之道以辅从于九五,则得为革之义。使君子居之于此位,则能辅于五,亦能同为变革于天下。虽使文章光显,亦不及于五,不可谓之虎变,但谓豹变而已。言其变革之文蔚然,其文采威 次于虎者也。“小人革面”者,以君子居之则能豹变,以小人居之则必包藏狠戾之心,但饰其外文,柔顺其道,以从于上。故曰“小人革面征凶”。“居贞吉”者,征,行也。言上六在卦之极,过于九五。盖在臣民之位当辅从于君,不可诗有所往。若以臣民而行,则必有猜疑之祸。是有凶之道也。苟能居是位而守其正,则得其吉。
按:二人所释“征凶,居贞吉”一句,区别明显。王弼以为上六居革之终,功成事损则无为。此与老子“功成、名遂、身退”思想吻合。安定则谓臣民之位当辅从于君,不可更有所往,是儒家纲常的思想。二人各由儒、道思想出发以明进退之道。
比较上所列王注与《口义》所释数卦,可知胡瑗的《易》学虽根源于王弼易注,但却能一扫隐含在《易注》内的老庄思想而站在纯儒立场。胡瑗务实际以矫虚浮,严师弟子礼以立根基。故《口义》虽祖王弼,却能发挥纯儒思想。
由上所列之三点分析,可以得出结论:胡瑗的《周易口义》的主旨在于阐发义理,而其所阐发的义理,又以儒家思想为主。故四库馆臣认为宋代义理《易》学诞生于胡瑗的看法,是非常中肯的。
[1][宋]李觏.易论(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
[2][清]四库馆臣.四库全书总目提要[Z].北京:中华书局,1997.
[3][唐]孔颖达.周易正义(阮刻十三经注疏本)[M].北京:中华书局,1980.
[4][宋]王得臣.麈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5][清]黄宗羲,全祖望.宋元学案[M].北京:中华书局,1990.
(责任编校:王晚霞)
book=23,ebook=71
B221
A
1673-2219(2010)01-0023-03
2009-11-05
黄曦(1983-),男,福建福州人,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2007级古典文献学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经学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