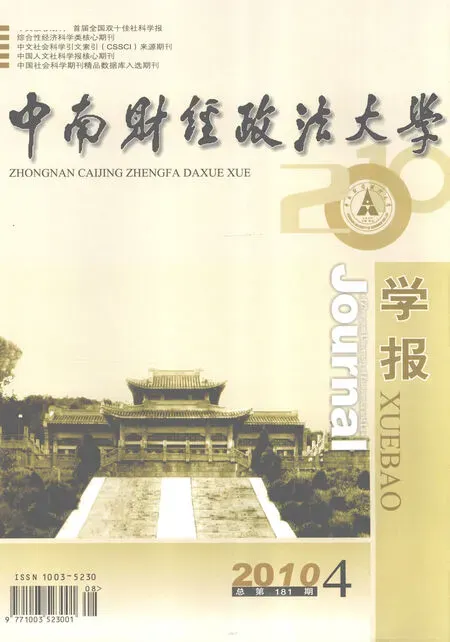公共品私人自愿提供决策的实验研究
龚 欣 刘文忻 张元鹏
(1.哥伦比亚大学 教育学院,纽约10027-6902;2.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北京 100871)
一、引言
人们普遍认为公共品的非排他性和非竞用性必然会造成“搭便车行为”的产生,进而导致私人对公共品提供的无效性和由政府来供给公共品的必然性。这样,只有政府才可以有效地提供公共品似乎已成为传统经济学中的一个理论教条和现实经济活动中政府的一个天然使命。然而,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现实中由私人提供的公共品大量存在。据统计,全世界每年有数以千亿美元被无偿捐赠给一些慈善机构、政治组织和文化团体,用于社会公共事业的发展。在美国,用于教育、卫生和救济的慈善捐赠10%来自企业,5%来自大型基金会,85%则来自全国民众的自愿捐助,全国志愿服务参与率为44%。在新加坡、我国台湾地区等地,则是积极提倡市民组成志愿小组免费提供消防安全、住宅安全、成人教育等公共服务。据我国民政部门统计,仅2008年1年,我国企业和民众慈善捐款捐物价值过千亿元,志愿者数千万计之多。上述一系列数据说明,在现实社会中,除了由政府提供公共品外,私人也会自愿(甚至是无偿)提供一定数量的公共品。那么,私人为什么会自愿提供公共品?或者说作为理性经济人的个人为什么在公共品提供问题上选择合作而不是“搭便车”?许多经济学家都对此进行了研究,并提出了诸如纯利他主义、光热效应以及个人的道德和社会责任感等方面的解释,但这些理论研究尚不能有效地解释现实中的许多疑问,比如,为什么在中国由私人提供公共品的比例不及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其影响因素何在?为什么中国的私人自愿捐助往往需要政府或社会团体的号召和发动,而国外单纯自愿的程度却较高?这些问题传统理论分析无法解释,需要用来自中国的现实数据进行实证研究。
近年来,利用实验经济学方法来研究经济学问题已呈流行之势。通过实验,研究者可以模拟现实的决策环境,细致考察所关注对象的行为,并通过可操控的方式直接考察相关参数的影响,有时甚至能够达到与“自然实验”研究相似的效果。在这之中,公共品的自愿捐献实验即是一项最典型、也最为基础的实验。基于实验数据而进行的公共品实证研究已在国外得到广泛发展,并且形成了一些特征化的典型事实[1],尽管各方在理论解释上尚未达成一致。在中国,这方面的实验研究尚在起步阶段,相关研究文献更为缺乏。为此,笔者进行了一系列公共品私人自愿捐献机制的实验研究,试图通过对实验数据的分析,研究我国私人自愿提供公共品的影响因素及其相互关系,并探讨如何通过激励机制的设计来提高我国公共品的私人供给水平,有效解决现实中我国公共品私人供给不足的问题。
二、实验设计及其参数设置
本文的实验项目采用了与Sonnemans等的经典实验——自愿捐献机制(voluntary contribution mechanism,以下简称VCM)实验——相类似的实验设计方案[2],即参与实验的被试者被分为若干个小组,每个小组中的每个被试者被给予一定数量的初始禀赋,各被试者被要求将其初始禀赋中的一部分捐献给某项公共事业项目,捐献完成后所有被试者贡献出来的公共项目总量乘以一个被试者事先知道的固定的捐献效率参数A(A>1)作为总收益,总收益在各被试之间平均分配。需要说明的是,这是一个在国际学术界公共产品私人提供实验中使用最多的设计方案。
我们于2008年12月6日在北京大学经济科学实验中心组织了84名自愿报名的同学参加VCM实验。实验分上午和下午完成。具体的实验参数设计如下:
1.被试人数与分组。参加实验的84人中,有14名留学生,中国学生和外国学生的比例为5∶1。所有被试者由电脑随机分组,每4人形成一组,即小组成员数N=4。上午10组,下午11组,小组成员在整个实验期间固定不变。
2.初始禀赋。每个被试者在每期实验之初都拥有20单位的货币。这是其参与公共品自愿捐赠时所能捐献的最大数量。
3.实验期次和各期次实验中的参数设置。本次实验总共分为3个阶段,每阶段包含10期次,相应的参数设置见表1。被试者在最初聆听实验指导的时候会被告知本次实验总共包含3个阶段。

表1 各期次实验参数的设定
本次实验特别对“捐献效率系数”和“交流”两个参数在实验不同阶段进行了不同的设定。这里的捐献效率系数A是指实验开始前由实验组织者设定的每个小组捐献总额的放大乘数,意指由私人自愿捐献货币而形成的公共事业项目对社会而言可以带来更大的效果。与其相联系的参数——公共品投资的私人边际回报率MPCA=A/N。在本实验的前两阶段(1~20期),被试者并不知道自己的组员是谁,不能相互交流,而在第三阶段(21~30期),实验主持人公布出各组的成员构成,并允许小组成员在实验之前相互交流与讨论,并可以私下制订合作协议。
4.收益函数①。被试者在每期做出捐献决策后可以获取的收益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从20单位的实验货币中捐献给公共项目一定数额(gi)后余下的数额(20-gi);第二部分是所在小组成员(4名被试者)都做出捐献决策后每个被试者可以从公共项目账户(即小组成员捐献的货币额之和乘以捐献效率系数A)中均分到的货币额。这样,被试者i在给公共账户捐献gi的情况下可以得到的收益为:

三、实验数据分析和有关特征事实的实证检验
从理论角度看,在公共品私人供给博弈中,由于每个利己的个体都面临搭便车的激励,每个博弈局中人的占优均衡策略是选择搭便车而不愿意提供任何公共产品。但是,一些著名公共品实验研究表明,社会成员的免费搭便车动机是有限的,大多数人在实际中自愿提供的公共产品数量要比理论上认为的自利的个人提供的公共品数量要多得多,公共品的私人自愿供给能够达到一个可观的且稳定的水平[1](Isaac和Walker等经典实验证明其比例一般在40%~60%之间[3])。
我们的实验,除了对目前学术界所关注的有关公共品自愿捐献机制的经典特征事实进行检验外,还发现了一些新的特征事实和实验结论。
(一)对公共品实验的一些经典特征事实的检验
1.特征事实一:非零捐献均衡和自愿供给的存在性
本次实验数据表明,无论从全部,还是小组的实验数据来看,被试者的首期捐献数额都为正数,整体平均的首期捐献比例为15.4%;1~10期、11~20期以及21~30期的平均捐献额亦为正,并且比例都在40%以上。我们还发现,实验中一个单位都不捐(即常说的完全搭便车者)的人次非常少。
上述结果验证了公共产品私人自愿提供的现实存在性。这可能与被试者内在的社会偏好(利他主义、荣誉感或社会责任)有关。另外,在我们的实验里,在报酬激励上设计了小组竞争环节,为了保证小组的相对收益,即要取得小组的相对优势地位,组内成员之间更容易达成合作。
2.特征事实二:捐献率随实验重复次数增加而有下降的趋势
通过考察上午和下午两组实验的第1个和第2个控制阶段(这两阶段小组成员不允许交流)(参见图1中第1~10和第11~20时段的情况),我们可以发现,随着每一阶段实验重复次数的增加,每个阶段的平均捐献率在短暂上升后都呈现出下降的趋势。不仅如此,即使在第3阶段(图1中第21~30时段,此阶段允许交流),平均捐献率下降的趋势也较为明显(尽管下降幅度不大)。

图1 上午、下午两组实验平均捐献率变化趋势
这一特征事实验证了在公共产品自愿捐献的重复博弈中,由于学习效应的作用,随着实验重复次数的增加人们变得更加“聪明”,也更加“理性”地决策,从而“搭便车”行为频繁发生。
3.特征事实三:存在有限次重复博弈中的“最后一期效应”
通过观察被试者在每个阶段最后一期(如第10、20和30期)的行为,可以看出,捐献率下降的幅度比前面的时期大很多(参见图1)。即使在允许交流的第3阶段,最后一期的平均捐献率也有一个较大幅度的向下跳跃。由此可知,最后一期往往是搭便车行为的高发期。这种现象很可能是由于人们意识到在最后一期(没有后续合作)搭便车将不会引起其他组员的惩罚,即搭便车成本较低,于是有相当一部分被试者在最后一期加入了搭便车的队伍,这一事实符合有限次重复博弈的逻辑结论。
4.特征事实四:公共品投资的私人边际回报率(MPCR)的正效应
直观来看,当投资公共品得到的私人边际回报率从0.5增加至0.75时,无论整体捐献水平、小组的初次捐献额度,还是个体的每期次捐献水平及其合作倾向都有较为明显的提升。
(1)对小组捐献总额的影响:成对样本均值的t检验
如表2所示,无论是研究整体样本,还是单独分析上午和下午的样本,成对样本均值的t检验结果表明,MPCR的增加会显著(至少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提高小组的平均捐献额(第2阶段的小组平均捐献额C2>第1阶段的小组平均捐献额C1),提高了小组的合作水平。

表2 统计检验:MPCR变化对小组平均捐献额的影响(样本观测值=10+11)
(2)对个体每期捐献水平的平均影响:随机效应模型分析
个体是决策行为的基本单位,不同实验阶段的私人边际回报率(MPCR)的变化首先会影响个人的决策行为,进而才会对整体的合作捐献水平产生影响。由于本实验中的84位被试者每人都参与了30期的捐献决策,可以将其看作面板数据,基于此可以进行计量分析。因为本实验采集的个人特征变量不多,且组内差分的固定效应无法将不随时间改变的个人特征变量的系数估计出来,同时考虑到个体异质性特征可能与我们关注的解释变量(如实验控制变量MPCR、交流)关系不大,我们选用随机效应模型②来估计个人捐献行为,最后的结果见表3。

表3 面板数据随机效应模型的估计结果(被解释变量:个体的当期捐献额)
通过随机效应模型1可以发现,当效率系数由2变成3时,个人的捐献额会增加约2.388个货币单位。另外,考虑到实验参与者可能以上一期其他组员的平均捐献水平作为决策参照系,笔者将这一因素加入到自变量中(模型2),其影响代表互惠偏好的效应。此时,MPRC效应仍为正值,尽管不显著。这都验证了私人边际回报率MPCR对私人捐献水平的正向作用。
5.特征事实五:交流的正效应
在实验设计时,第3阶段的特点是在第2阶段结束后允许小组成员在实验之前相互交流,因而直接比照两阶段的差异可以了解交流对捐献行为的影响。通过比较第3阶段和第2阶段的捐献情况(见图1)可知,从整体上看,第3阶段达到了比较高的合作水平,接近满额,比第2阶段的各期捐献额高很多。另外表3中的虚拟变量“交流”的估计系数非常显著地大于0,体现了交流的正效应。
交流之所以能起到这么大的作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交流部分消除了不确定性(被试者之间通过沟通和交流,事实上已经达成了某种口头协议或默契),为捐献行为指明了一个“聚点”(focal point)。而且,这个聚点之所以能够克服搭便车动机,不仅仅依靠口头契约或书面契约④,笔者认为主要原因是“声誉效应”:由于参加实验的同学都是同一个课堂上的学生,他们中的许多人彼此相互熟知。对于他们而言,这次实验仅仅是他们的一次合作,以后的合作机会还有很多。正是预期到这一点,大家大多不愿违约。如果声誉确实能够发挥作用,那么在其他条件不变时,熟悉环境中的公共品投资水平应该比陌生环境中高(虽然这一检验目前在经验研究上还没有达成共识)。本文发现的颇为显著的“交流正效应”可部分算作“声誉效应”的一个证据。
6.特征事实六:被试者的个体特征(性别、国籍等)的影响与效应
关于实验对象的个体特征,本文发现,性别对个人捐献水平有显著的影响。随机效应模型的估计结果显示,在保持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女生平均而言要比男生少捐0.80~1.45个货币单位(参见表3),表现出更加利己的行为。这与Dawes等的结论正好相反[4],笔者认为这可能与两个实验均未控制不可观测的个人特征有关,其中社会偏好和风险态度的异质性也有可能促成了这种结果。此外,外国留学生的捐献水平高于中国学生,这可能是由于中外学生不同的文化背景和价值观所致。
综上,考虑到实验设计的差异,我们无法直接在量上将这些结果同国外实验进行对比,但从以上特征事实的检验结果可以看出,对于同一类实验项目的研究发现是不分国界的,人们的捐献行为特点具有相似性。这种相似性的焦点是,现实生活中人们的行为与理论上预测的结果产生了偏离,改进实验设计可以提高人们的合作水平。
(二)本项实验中新的发现和启示
此次我们在中国高校中所做的实验不仅验证了一些经典的公共品实验的特征事实,而且还获得了一些颇具中国特色的新的特征事实和发现,并得到一些启示。
1.新发现之一:期初平均捐献水平较低
与Isaac和Walker等经典实验的40%~60%相比[3],本次实验在第一阶段(重复10期)的首期平均捐献率较低,只有15%左右。这可能与我们的实验对象是经济学专业的学生有关。事实上,在参加实验之前,多数同学对公共品理论或多或少地有些了解。这会帮助他们更好地理解实验要求,更清楚这个实验中的理性选择,所以平均而言会比一般人的捐献水平低一些,这也同许多现有文献的发现一致。但是,专业知识并不能解释全部现象:第一,为什么捐献程度很低但不是0?第二,同是经济学专业的学生,他们在实验里的捐献行为为什么有很大的差异?如有的完全不捐,有的却多次全额捐献,有的波动性非常大,有的一直保持稳定的捐献额度。笔者认为,这些问题都需要从社会偏好和个体的预期异质性上寻找答案。
2.新发现之二:口头协议效果显著
实验在第3阶段与第2阶段的捐献路径上存在的巨大差异并不令人惊讶,但是这种极高的合作水平和较低的违约率(只有上午的第7小组出现了特殊情况)在效果上超过了传统的研究。Isaac和Walker指出,交流之后的捐献率通常能达到80%以上[3],我们的实验却得到了高达96.74%的捐献率(平均额度为19.349个货币单位),且很多小组(一半以上)在10期内都保持了100%的捐献率。
如何解释这种高效的合作?熟悉基础上的信任和声誉效应是一个理由:如前所述,我们的被试者来自同一个班级,后续的合作机会非常多,他们很可能不愿意表现出不合作行为。这一点在实验之后的补充问卷里得到了验证,大部分同学告知笔者,他们之所以会签订口头协议而不规定惩罚措施、不签订书面协议,是因为“几个人都互相认识,预计今后也常碰面,违约被看作是不理性的行为,最后也没有人违约”或者“碍于面子应该不会捐少”。个体固有的合作动机也可能是另一原因,如有些个体具有利他主义的倾向,愿意合作,并且其行为也影响了其他人;而那些违约的小组可能因大家的想法差异性过大而无法维持长期合作。
3.新发现之三:经验分享存在积极作用
本次实验的一个独特之处在于,笔者可以恰巧得到一种检验“经验分享”作用的“自然实验”——严格来说是在人为设计实验之外偶然出现的一种“处理(treatment)”。由于我们的实验分为上下午两个时间段,下午实验的同学就会或多或少地通过各种有意的或无意的途径(比如谈话、未名BBS上的信息共享)获知有关上午实验的一些信息,甚至关于行为策略的信息。也就是说,下午实验的参与者可以吸取上午实验的经验教训。这种经验分享对于合作的效应可能是正向的,因为通过分享经验,参与者可能对“集体理性和个人理性的矛盾”更为清楚,更愿意在实验中表现出合作行为。
而实际结果验证了这一点,从图1中可以很明显地发现,下午实验的各期平均捐献率均高于上午。虽然不排除有上下午被试者分布差异的影响,但是随机效应模型1和模型2的结果验证了这种差距的显著性,在这两个模型中虚拟变量“afternoon(是否为下午样本)”的回归系数都显著为正(参见表3)。
4.新发现之四:简单地在整体(全部参与者的每期捐献)或小组的层面上展开平均意义上的观察(以平均值作为考察指标)可能掩盖小组内部差异化个体的交互作用⑤
传统上人们大多是从整体平均的角度来分析个人的合作捐献行为,而这种分析方法所反映的是宏观的结果,对微观行为的解释力度有所欠缺。我们更需要知道导致小组合作失灵或成功的原因,这就要求我们的分析指向个体维度,而且,传统针对个体行为影响因素的分析(包括本文前面的探讨)也相对比较笼统。例如随机效应模型估计实际上是一种混合分析,可能会忽视一些过程和细节,尤其是个体之间的差异性,忽视其可能展现的特定的行为类型;对于同一个阶段内个体行为的一致性和变动性(阶段内效应),随机效应模型估计也只能给出若隐若现的结果(包括表3在内的计量回归从本质上也只能得到一个平均意义上的估计结果)。更为重要的是,如果只分析个体在每一期的行为,而不考虑同一小组内部不同个体之间的交互作用,我们也无法解释小组的合作程度为什么会存在差别。所有这些都说明需要研究者透过个人的社会偏好差异性来分析捐献水平的差异,进而深入分析提高合作水平的路径。
四、结论与建议
本文通过对公共品私人自愿提供实验数据的分析,验证了公共品私人提供博弈中的多个经典特征事实,此外,我们还获得了一些新的发现与启示。对于如何提高我国公共品私人供给水平,我们给出如下建议:
(一)通过公德教育和榜样示范培养人们良好的社会偏好和合作意识
从实验结果来看,表3说明了“上期其他组员平均捐献水平”显著的正效应,说明很多被试者都会参照上一期该组成员的决策做出自己本期的捐献决策,这就是所谓的“榜样的力量”导致的个体合作倾向的“社会偏好”。同样,公德教育可以帮助人们强化其固有的社会偏好,因为诸如利他主义之类的“公德”在社会中具有良好的榜样示范作用。在实施具体的公共品捐献活动时,可以考虑将某些积极合作者安排在集体内,这样可能使最后的合作承诺得到落实⑥。
(二)建立长效机制,固化自愿捐献者的“荣誉感”,以此克服随时可能发生的“搭便车”现象
实验中的数据尽管支持了公共品自愿捐献的“现实存在性”,但毕竟还存在诸如“捐献率随重复捐献次数增加而下降”、“最后一期不合作效应”等现象。另外,由于不确定性的广泛存在,随着捐献经验的积累和自利型搭便车行为的暴露,对他人行为的预期可能发生向下的调整,从而也会导致合作程度的降低。为了强化人们的合作意愿,避免潜在的“不合作行为”发生,在具有“俱乐部”特征的公共品的供给机制选择上,充分体现个人的利益相关性,通过设计出与参与者未来收益挂钩的奖励机制来让人们认识到以后的合作机会很多,以提高大家的合作意愿。
(三)创造条件,促进公共品潜在供给者之间正式(或非正式)的交流,增强其合作的倾向
本次实验第3阶段所表现出来的高合作水平说明了交流与沟通的意义。签订口头的或书面的合约对于防止合作破裂起着重要作用。另外,为防止口头协议破裂(实验中已经出现类似的情况),还需要有一些保证措施,比如让参与者预期到提供公共品后可享有收益的长期性(相当于无限次),从而有助于减少“最后一期效应”。1978年安徽凤阳小岗村17户居民签订契约书的例子非常形象地说明了合约约束力的重要性。在集体合作中,很有必要通过交流和契约给参与者施加一定的约束。
需要注意的是,如果交流是无成本的,就像本次实验设计的那样,交流的正效应是比较有保证的。然而,在现实生活中交流可能遇到各种问题,比如集体规模太大,协调困难,即交流是有成本的。这就需要通过各种方式降低交流的成本(比如视频会议),群策群力促进公共品的有效提供。
(四)公开参与者的捐献信息,尤其是正面的信息,提高社会成员的捐献水平
同样是鉴于具有互惠偏好的条件合作者的大量存在,公开良好信息的作用非常显著。有些实验者已经发现,信息不完全及预期出错可能导致“低水平均衡”。对捐献者的合作程度排序也是一个较好的办法。例如,定期公布人们在各种慈善募捐中的捐款数额(包括个人捐款和企业捐款),对于引导人们的爱心合作也是非常有益的。
注释:
①被试者被告知,他们的实验课成绩将与此次实验所获取的收益相联系。这是针对以学生为被试者的实验专门设计的激励机制。考虑到被试者的学生身份,这一激励基本能保证被试者认真对待实验,较好地模拟现实中的公共品供给决策行为。
②笔者也利用STAT A软件中的x ttest0命令检验了是否可以用混合回归方法,结果表明不可观测的个体异质性显著存在,不能简单采用pooled regression。
③因为模型2是考虑了“上期其他小组成员的平均捐献水平”因素后构建的模型,其估计样本要去掉每一阶段的第1期数据,这样3个阶段共计有3期次的数据要在模型2中去掉,最后就剩下27期次的样本数。
④据笔者事后进行的补充问卷调查,大部分小组订立了口头契约,要求大家一致捐献20,并且没有什么惩罚规定。
⑤笔者认为,在今后的研究中,很有必要将分析的重点转向个体行为,尤其是个体的异质性,而且异质性的行为类型应当是在动态路径上定义的。
⑥实际上,互助合作社的成立和维持所依靠的一个关键因素是领导者。带头人不仅可以发动群众自发捐献,还可作为代表,负责运营合作投资所形成的公共品。
[1]Ledyard,J.O.Public Goods:A Survey of Experimental Research[C]//Kagel,J.,Roth,A.E.Handbook of Experimental Economics.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5:111—194.
[2]Sonnemans,J.,Schram,A.,Offerman,T.Strategic Behavior in Public Good Games:When Partners Drift Apart[J].Economics Letter,1999,(62):35—41.
[3]Isaac,M.,Walker,J.Communication and Free Riding Behavior:The Voluntary Contribution Mechanism[J].Economic Inquiry,1988,(26):585—608.
[4]Dawes,R.M.,Mctavish,J.,Shaklee,H.Behavior,Communication,and Assumptions about Other People's Behavior in a Commons Dilemma Situation[J].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1977,(35):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