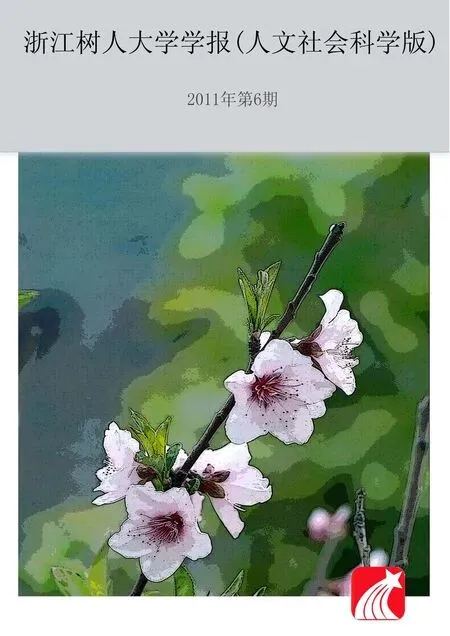二战后日本文化论的变迁
任萍
(浙江树人大学外国语学院,浙江杭州310015)
纵观世界各国文化,没有哪个国家文化比日本文化更加引人争议,也没有哪个国家的文化研究像日本文化论这样多种多样。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经济的高速发展受到世界各国的关注,引发了以研究日本经济发展原因为主题的世界性的日本文化论热潮。日本人和外国人都围绕“日本人的性格”、“日本文化的本质”展开了深入的研究、探讨。
一、日本的日本文化论
二战后日本经过短暂的恢复期,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社会、经济开始全面发展,面对新的政治、经济局势,日本知识分子多次提出“何谓日本”、“何谓日本人”的问题,探究日本民族以及日本文化的本质特征,以期重新认识并界定日本在世界中的地位。加藤周一与梅棹忠夫是战后早期的日本文化论的代表人物。加藤在1955年6月发表了《日本文化的杂种性》一文,提出日本文化的“杂种性”。梅棹在1957年2月发表了《文明的生态史观序说》,提出西欧与日本的文明是“平行进化”的。
1976年加藤将自己1957年至1964年撰写的文章整理成《何谓日本人》出版。书中除了论述日本人及日本文化的特征外,还分析了日本的天皇制以及日本知识分子的特点。加藤认为以天皇为中心的世界的崩溃,造成了日本国民不相信一切权威的态度。日本的知识分子年纪偏轻,且多为男性,他们在历史感觉上比较迟钝,对本国文化的兴趣较为薄弱,表现在文化上缺乏自信。加藤之所以在上世纪70年代出版此书,用意是显而易见的。他指出“何谓日本人这一问题之所以被反复提出来,无疑是因为‘日本人意味着什么’这一点并没有弄清楚。而‘日本人意味着什么’之所以弄不清楚,实际上是因为我们作为一个民族希求什么这个问题没有弄清楚。”[1]战后日本经过20年的发展,经济上跃居世界强国之列,但政治上仍处于相对孤立的地位。加藤认为这源自日本的双重结构,即在经济上的成功和在文化上的缺乏自信。因此日本所希求的就是树立文化上的自信。
1986年梅棹将以往应邀赴美国、法国等地的讲演稿整理成《何谓日本》出版。书中论述了日本文明的坐标与位置,近代日本文明的形成、发展及其历史延续性。梅棹指出,日本的近代文明并非始于明治维新,而是发端于“德川体制的天下太平时期”,并且可以追溯到中世纪日本封建制的建立。他把世界分为两大地区,认为西欧与日本同属第一地区,虽然遥遥相对但却非常相似,表现出与第二地区(其他国家)截然不同的发展模式。梅棹指出,日本的近代化过程虽然以明治革命为契机得到推进,但与之前的历史密不可分,因此不能无视日本文明的历史连续性。
加藤与梅棹的著作既是两人多年研究成果的核心内容,也是各自日本文化论研究的发展轨迹。可见,同一时期不同学者的日本文化论差别迥异,不同时期同一学者的日本文化论也不尽相同。战后出现了众多的日本文化论著作,呈现出多元的日本文化研究视角。根据1978年野村综合研究所的调查,从1946年到1978年出版“日本文化论”方面的论著有698部之多。[2]27日本学者鹿野政直1978年在《史学杂志》上发表了题为《日本文化论的历史》的文章,总结了近代以来至20世纪70年代末日本文化论的发展历史。1990年,日本文化人类学家青木保出版了《日本文化论的变迁》一书,对战后日本文化论的变迁做了较为详细的论述。
鹿野政直之所以发表《日本文化论的历史》,有两个原因。一是受到当时思想界纷繁的日本论、日本人论及日本文化论的触发;二是想将文化问题作为从思想史研究转向生活史研究的途径。鹿野将日本文化论分为“近代日本起步期的日本文化论”、“‘大国’日本发展期的日本文化论”、“战后社会的文化论”等三个阶段。根据日本近现代史的发展又进一步将其分为文明开化期(19世纪70年代前后)、国粹主义期(19世纪90年代前半期)、帝国主义期(20世纪10年代前后)、法西斯化期(20世纪30年代)、战后出发期(20世纪40年代后半期至50年代前半期)、新安保体制期(20世纪60年代)以及70年代的安保以后期等七个时期。鹿野认为,日本文化论盛行的各个时期不仅是日本受到外部世界强烈冲击以及大众运动相对沉寂的时期,也是知识分子处于优势的时期。对于日本近代的知识分子来说,日本文化论发挥着坐标轴的作用。同时,不断涌现的各种日本文化论也体现了知识分子在信赖大众方面的动摇。知识分子通过对日本文化的总结,发挥了他们固有的作用。因此,日本文化论不仅可能成为一把双刃剑,也是在看似封闭的环境中开拓未来的锁钥。
青木保撰写《日本文化论的变迁》的目的是“想通过探讨‘日本文化论’的变迁来重新思考战后日本的‘文化与身份’问题。”[2]18战后世界特别是美国迫切需要认真研究日本,以便其确立对日本的支配权,而日本国内也存在着重新认识自己的渴望。青木指出“在战后日本的发展中,自《菊与刀》以后的这些‘外部’视线的存在,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日本人对日本的定位。”[2]76青木把美国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的《菊与刀》作为战后日本文化论的起点,将战后日本文化论分为“对特殊性的否定性认识”(1945~1954)、“历史相对性的认识”(1955~1963)、“肯定性的特殊性认识”(1964~1983)以及“从特殊到普遍”(1984~)等四个时期。这四个时期分别与日本经济的发展时期相呼应,一直是日本人借以谋求国家复兴的舆论导向。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世界政局发生重大改变。“日美关系”陷入不曾有过的严峻状态,而且很难找到有效方法来改变这种局面。青木保之所以在90年代初期对战后日本文化论的变迁进行回顾,也是希望在“国际化”的动荡局势中,人们能够摆脱“日本文化论”所陷入的封闭怪圈,作为一种展望更加开放的新世界的“世界论”,并作为日本人从90年代至下个世纪的行动支柱,发挥出积极的作用。[2]156
青木保的观点有值得肯定的一面,即他看到了一个国家的文化研究不应该局限于国内,而应该放在更为广阔的视域,也就是要有国际化的视野。但另一方面其仍然摆脱不了前人日本文化论的局限,即并没有客观的分析日本文化的形成、发展与变化,而是受到时局的影响,将日本文化作为日本人的国际定位以及日本经济的发展对策加以研究。
从上述两位学者的研究来看,近代以来的日本文化论,特别是战后日本文化论的变迁,与日本政治、经济的发展密切相关,并受到世界局势的影响。正如我国南开大学日本研究中心赵德宇教授所指出的,虽然“学者们的研究提出了许多发人深省的观点,不仅为日本研究提供了大量有益的启示,而且为宏观的文化学研究领域提供了发展的养料。”但“对日本文化的褒贬始终是随着日本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日本国内外形势变化而变化的,即大多是试图用文化研究来说明当时日本社会的状况,这种以今论古的逆向研究的思维方式,似乎是学者们在论述日本文化时的一个不可逾越的误区。”[3]
日本学者深泽彻在《日本文化论的两大难点》中指出,“一个是在与‘中国’‘欧美’的比较中,日本文化经常不得不甘于处在二流水平,容易陷于二者之中的双重约束状态;另一个是身为日本人,不知道如何超越在论述自己归属的日本文化时产生的言及自己的悖论。”[4]也许正是由于这两大困惑,才使得日本学者虽然在世界文化的普遍性与日本文化的特殊性之间寻找平衡却一直未有定论。
1989年PHP研究所出版了山本七平的《何谓日本人》①,此书被认为是继《菊与刀》之后又一部引起世界性关注的“现代日本学”论著。山本依据江户时代末期伊达千广在《大势三转考》中的分期标准,从“骨的时代”、“职的时代”、“名的时代”以及“伊达千广的现代”等四个时期通过对日本历史各个发展时期的回顾,对日本文化的特性展开分析。从对绳文时代的远古日本人的追溯,到对明治近代化成功的解析,山本认为日本近代化的成功是在漫长的日本历史文化的发展过程中实现的。山本的日本文化论避免了加藤指出的日本知识分子的弊病,②通过史实分析、再现日本文化,与其说是一部文化论著作,毋宁说是一部文化史著作。
2002年岩波新书出版了日本历史学家村井康彦的《日本的文化》。村井认为,从日本文化形成的历史来看,它是杂种文化;从日本文化形成的地理条件来看,它是岛国文化。日本文化的本质特征是生活文化,也就是在身边寻找素材,以一定的形态将其培养成为艺术,即日常性的非日常化。村井的日本文化论可以看作是从“现象”到“本质”的回归,即试图从来源于生活的文化最本质的层面中探寻日本文化的特征。不再是将日本文化与他国文化进行比较,而是从文化形成的根源上探求日本文化的本质,这对于日本文化论的发展来说是很大的进步。
2003年日本比较文学家大久保乔树出版了《日本文化论的系谱》一书,认为二战后日本出现了两种典型的日本文化论:一种是以丸山真男《日本的思想》为代表的,从战后民主主义立场出发,以西欧近代市民社会为榜样,批判日本社会存在方式的日本文化论;另一种是以土居健郎的《“依赖”的构造》为代表的,重新审视不同于西欧近代市民社会的日本社会的存在方式,对其给以积极评价的日本文化论。[5]战后的日本,在军事、文化、思想等方面均处于美国的统治之下,日本人的民族自尊心迫使以土居、丸山为代表的知识分子一方面学习西方文明,增强自己的实力,一方面执着于寻找自我,寻找日本民族存在的意义。丸山真男与土居健郎的日本文化论反映了战后日本知识界对于自我评价的“否定”到“否定之否定”的过程。与青木不同的是,大久保没有依据战后日本经济的发展对日本文化论进行分期,而是从比较文化的视角对日本受到西方文化剧烈冲击的时期,即明治时期以来的15位思想家、学者、作家的代表性日本文化论进行解读,从而阐释了近代日本人的自画像。
二、西方的日本文化论
青木保在《日本文化论的变迁》中指出美国文化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的《菊与刀》是日本文化论的典范,此后的“日本文化论”都多少受到了这本书的影响。[2]31《菊与刀》最初是美国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奉美国政府之命,为分析、研究日本社会和日本民族性所做的调查分析报告,旨在为美国管制战败后的日本提供参考。这部书不仅受到日本学术界的批判,也受到世界各国日本研究者的关注。
本尼迪克特首先指出自己作为“他者”研究日本文化的优势,即“一个日本人在描述日本时,往往会忽视掉真正重要的东西,他对这些东西熟悉到了就好像对他所呼吸的空气一样,以至于习以为常,视而不见。”[6]6作者虽然没有踏上日本的国土,却可以利用作为文化人类学家的优势对日本文化进行研究,即从“所发现的异同之处找到理解日本人生活的线索。”“能够把日本和其他一些同属于一种伟大文化传统的国家进行比较。”[6]7同时,将“其自身的文化与另一种文化之间的巨大差异”“及其制约性和后果的关注充分地运用到对日本的研究中去”。[6]280也正因为如此,《菊与刀》被认为是一部解构美国文化的“日本文化论”。作为关于“日本何以成为日本民族”的“假设性观点”,本尼迪克特向日本人揭示了两个问题,即作为日本人社会组织原理的“集团主义”以及作为日本人精神态度的“耻感文化”。此书1946年出版,1948年被翻译成日文。1949年5月日本著名评论家川岛武宜在《民族学研究》杂志上发表书评,对《菊与刀》给予充分的肯定,但也指出“著者的分析没有考虑问题的历史一面”“‘日本人’是被作为同质的人的总体出现于著者面前的。著者几乎忽略了日本人中还存在着阶级、地域和职业等具体的差别。”[6]281
美国社会学家罗伯特·贝拉在1956年出版的《日本近代化与宗教伦理》中,把日本的“近代”与西欧的近代相比较,认为其中存在着一种“平行现象”。贝拉的观点与梅棹的论点不期而遇,对日本文化孕育近代文明的可能性给予积极评价。青木认为“作为表现出对于‘西欧’之间‘相对性的历史性认识’,贝拉的观点的确可以被评价为代表这一时期的论点。”[2]75
经过战后20年的恢复,到20世纪70年代,日本经济跃入世界经济强国之列。这又一次催化了西方的日本文化论研究热潮。1979年美国哈佛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埃兹拉·沃格尔的著作《日本名列第一:对美国的教训》被认为“是比本尼迪克特更加明显的‘为美国人’而撰写的‘日本社会论’”。[2]11420世纪70年代的另外一部代表性著作是美国历史学家,曾出任美国驻日大使的哈佛大学教授埃德温·赖肖尔的《日本人》。赖肖尔在序言中指出“日本的历史长河奔腾流急,而在每个转折点上,这个国家都显示出一种新的面貌。”[7]1书中大肆宣扬了美日之间的友好伙伴关系,宣称此书是帮助美国人了解日本人的著作,“如果说日本人同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的人民已经取得了一种真正的伙伴关系,那就是同美国人。”[7]465日本和美国“已经发展起来的关系,是跨越把世界分割开的巨大文化和种族上的鸿沟而在平等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广泛而深入的合作关系,这样的例子在世界历史上还未曾有过。”[7]474赖肖尔看到了日本在“自然灾害问题”、“社会内部的结构问题”、“世界生态和资源问题”及“国际贸易和世界和平问题”等方面已取得的成绩和面临的挑战,认为“在寻求二十一世纪人类所面临的问题方面,日本很可能是在先驱者之列——甚至可能是个最卓越的先驱者。”[7]474
由于日美贸易摩擦的出现,西方人开始重新审视日本。1982年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查默斯·约翰逊出版了《通产省与日本奇迹——产业政策的成长》。作者通过对大量事例的分析,认为日本出现经济奇迹的真正原因不是国民性与受到美国的援助,而是日本实行的产业政策,即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青木保认为“这本书乃是真正研究日本官厅的著作,并贯穿着‘批判’的视点。”[2]1251986年出版的澳大利亚的日本学研究者彼得·戴尔的《日本式的独特神话》则是一本“通篇充满了批判‘日本文化论’色彩的过激‘论著’”。[2]126
荷兰著名文化学者伊恩·布鲁玛在20世纪80年代出版的《面具下的日本人》被认为是继《菊与刀》之后又一部轰动世界的现代日本学巨著,和《菊与刀》并称为“20世纪最重要的日本文化著作”。与《菊与刀》的作者本尼迪克特不同,布鲁玛有着多年旅居日本的经验,借助电影、漫画等形式,窥探日本人精神生活中异样的正常、分裂的统一,探索日本人性格两面性的成因。
对于越来越激烈的日美贸易摩擦,美国内部出现了两种声音,一种是要求美国在经济上对日本进行制裁,另一种则是希望美国更深入的了解日本,以求“睦邻友好”。前者的代表作是美国记者杰姆斯·法劳兹的《封锁日本》,作者认为日本排外的经济体制是“金权交易”造成的,企业和行业向议员捐助政治活动金,议员利用手中的权力来保护他们的利益。美国政府应该从维护自由贸易制度和美国人民的利益出发,对日本实行经济封锁。[8]105后者的代表作是美国哈佛大学人类学博士西奥多·贝斯特的《邻里东京》。作者对当代日本都市邻里的社会结构和内在动力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的探察。从题目来看,美日之间的关系已经跨越了地域的影响,成为邻里,日本对美国人来说是既熟悉又陌生的存在。此书研究了日本东京一个普通社区的微观生活,从生活中发现日本文化,应该说是对之前被政治、经济蒙蔽了的日本文化研究视野的矫正。
从上述内容不难看出,西方日本文化论的变迁与日本国内日本文化论的变迁基本是同步的,也与日本经济的发展相呼应。可以认为西方的日本文化论是在日本经济发展的不同时期,为西方提供应对日本决策的指导书。日本英知大学教授罗东耀在《战后日美两国日本文化论研究的分歧及其意义》一文中,以1979年前后为界,将战后日美两国日本文化论研究分为两期,前期日美两国学者都以日本人和日本文化为研究对象,但到后期,美国学者转向日本社会、特别是特殊的结构,而日本学者却依然守在日本人和日本文化方面。罗教授指出,尽管两国学者研究的对象不同,但研究目的都一样,都是为了维护本国的利益。美国学者的研究目的是揭露日本的特殊结构和贸易保护政策,扩大美国对日出口,日本学者则想通过夸大日本人和日本文化的特殊性来为特殊结构的形成和发展寻找合情合理的理由,继续保持对美贸易的不平衡。[8]106不论文章对于战后日本文化论研究的分期是否合理,不能否认的是日美两国各个时期出现的日本文化论都是两国学者从自身利益出发,受到国内、国际局势的影响,试图将现实合理化、将现象理论化的著作,在从人类历史发展的角度把握日本文化论的方面都表现出不足。
三、中国的日本文化论
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邻邦,中国人很早就开始关注日本人及日本文化。戴季陶的《日本论》被视为研究日本的重要参考著作。戴季陶在《日本论》中,不断以日本比中国,在阐述日本文化的同时,指出其对中国文化的借鉴和教训意义。可以说戴季陶论日本,最终着眼点在中国。日本著名学者竹内好认为,“在中国人的日本论中,戴季陶的《日本论》、黄遵宪的《日本国志》《日本杂事诗》和周作人关于日本的随笔,均具有独特的历史目光和洞察力,与西洋人的日本论相比毫不逊色,他们是中国日本学研究的三杰”。[9]
周作人研究日本文化的代表作是《日本管窥》系列。在谈到西方人研究日本文化的不足时,周作人指出,“西洋人看东洋总是有点浪漫的,他们的诋毁与赞叹都不甚可靠”。[10]也就是说西方人的研究往往太过感性,因而看不到事物的本质。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胡令远教授认为,“管窥”系列其实是周作人对此前自己关于日本文化认识的深刻反思。周作人认为日本以其固有的民族特性,融会、调剂中西文化的精神,创造出自己的文明。因此,其文化也具有独立的地位与价值。[11]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历史与现实的原因,中国的日本学研究迟迟没有展开。中日邦交正常化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涌现出一大批研究日本文化的优秀学者。但与战后日本及西方的日本文化研究相比,我国的日本文化研究显得相对滞后。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崔世广教授指出:“由于历史上中国文化对日本文化长期处于强势地位,日本文化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受到中国文化的巨大影响,使中国人形成了不少对日本文化的误解,这直接影响到中国日本文化研究的深化和国人对日本文化的理解。”[12]浙江工商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王勇教授也指出“‘日本无文化论’渗透在中国民众的潜意识里,或许可以追根溯源到封建时代的‘华夷思想’,显然落后于时代,不可助长之。”[13]
纵观近年来我国的日本文化研究,学者们的研究视角各不相同。例如,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卞崇道教授在《关于岛国日本文化论的思考》一文中提出共生文化论,认为日本文化的发展走的是“共存—融合—共生”的道路;日本文化的最显著特征可以概括为“生活文化”,即在日常生活的层面上来理解事物,并且在个我的层面上加以展开。接受外域文化并使之变形而融入自身文化之中,成为岛国文化的一个共同规律。[14]
王勇教授在《日本文化论:解析与重构》一文中,通过对日本学者提出的“杂种文化论”、“变形玩偶”文化论、“洋葱文化论”、“组装文化论”等进行分析,认为这些文化论虽然都有合理的部分,但都不能完全概括日本文化的特性。他认为日本文化是一种“再生文化”,是借助“书籍之路”长期受到中国文明熏陶的结果,“他们创造出的文化,看似眼熟,未必就是模仿;即使陌生,亦非全部独创。”[13]此文可以看作是作者对早年提出的“嫁接文化论”的进一步发展。
四川外语学院日本学研究所所长杨伟教授2008年出版了《日本文化论》,指出“尽管文化的构成具有诸多的复合因素,但只要人们生活在某一片土地上,就不可能不受到那片土地所具备的风土特征的影响。”“日本民族,其与日本列岛的自然之间所构成的关系,乃是一种极其基本的、甚至具有决定性的因素。”[15]可见,作者关于日本文化论的观点受到了日本哲学家和辻哲郎“风土文化论”的影响。
综上所述,战后在日本经济发展的不同时期,日本国内和西方各国都出现了大量日本文化论研究的著作。日本以及西方的日本文化论的变迁是与日本经济的发展以及国际政局的变化相适应的,虽然其中有不少合理的地方,但更多是借助文化的外衣为日本经济、社会的发展寻求理论支持。日本和西方的日本文化论是对文化“特殊性”与“普遍性”的反复论证,其背景是日本经济的发展以及日本在世界舞台上的地位变化。日本国内的日本文化论的目的是通过不断重新审视自我,寻求日本在世界舞台上的位置与话语权;西方的日本文化论则是通过对日本社会结构特性的研究,寻求应对日本的策略。
相比之下,中国学者的日本文化研究虽然相对滞后,但却更为客观。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的日本学研究者正力图挣脱“政治形势”的影响、或“意识形态化”研究的束缚,而达到方法论上的自觉。卞崇道教授在《融合与共生》一书的前言中指出,“要客观地认识他者,首先要客观地认识自己;自己中包含他者,他者中也包含自己。树立他者意识,站在他者立场,客观地认识、研究日本思想文化,是笔者在本书中试图提示的一种方法论视角。超越中日两国的域界,从东亚视域乃至全球视域来认识日本或中国的思想文化,则是建构21世纪东亚哲学的前提。”[16]这种方法论不仅是21世纪东亚哲学研究的前提,也是日本文化以及日本学研究的正确方法。
注释:
①1992年PHP研究所出版了《何谓日本人》文库本(上、下),2006年祥传社出版了《何谓日本人》(单行本)。
②加藤周一在总结日本知识分子特点时指出,他们“虽然对一切新鲜事物非常敏感,但对传统事物的历史感觉却较为迟钝”“他们的立场多为理论性的而不是实际性的,抽象的而不是具体的。”(加藤周一著,彭曦、邬晓研译:《何谓日本人》,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15-120页)
[1]加藤周一.何谓日本人[M].彭曦,邬晓研,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10.
[2]青木保著,杨伟,蒋葳译.日本文化论的变迁[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8.
[3]赵德宇.战后日本文化论流变[J].日本研究,1998(1):69-70.
[4]深沢徹.日本文化論の二つのアポリア[C].国際文化論集,2000(22):149.
[5]大久保喬樹.日本文化論の系譜-「武士道」から「『甘え』の構造」まで[M].東京:中央公論新社,2003:207-237.
[6]鲁斯·本尼迪克特著,孙志民等译.菊花与刀——日本文化的诸模式[M].北京:九州出版社,2005.
[7]埃德温·赖肖尔.日本人[M].孟胜德,刘文涛,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
[8]罗东耀.战后日美两国日本文化论研究的分歧及其意义[J].苏州科技学院学报,2005(3).
[9]徐冰.戴季陶的日本观[J].日本问题研究,1994(3):71.
[10]钟叔河.周作人文类编·日本管窥[M].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15.
[11]胡令远.周作人之日本文化观——兼论与鲁迅之异同[J].日本学刊,1994(6):113.
[12]崔世广.基于<菊与刀>的新思考[N].北京日报·理论周刊,2005-08-01:读书版.
[13]王勇.日本文化论:解析与重构[J].日本学刊,2007(6):87.98.
[14]卞崇道.关于岛国日本文化论的思考[J].浙江海洋学院学报,2005(4):8-13.
[15]杨伟.日本文化论[M].重庆:重庆出版社,2008:1.
[16]卞崇道.融合与共生——东亚视域中的日本哲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