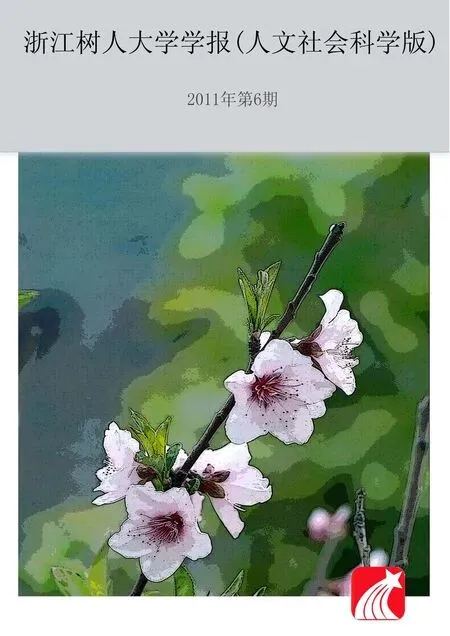分离与建构:西西《我城》与香港意识
王强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北京100875)
《我城》是香港作家西西的代表作,西西在这部长篇小说中表现出明亮光彩的色调和乐观快乐的品格,在语言风格、叙事手法、小说结构及人物塑造等诸多方面均可谓开香港现代小说风气之先,同时,作为香港意识的发轫之作,也使得这部小说具有了从香港意识考察的重要意义。
关于小说体现的香港意识,赵稀方指出,“20世纪六七十年代,随着新一代本土港人的成长,‘香港意识’浮出了历史地表。新一代港人或者生于香港,或者生于外地,但都成长于香港,他们不再有父母一代的浓厚的‘北望’情结和‘过客’心态,相反,他们以香港为家,以香港都市的繁荣为自豪,他们的青春体验凝聚于这个城市的发展中,故而他们对香港自觉地产生了认同感与归属感。西西写于20世纪70年代后期的《我城》,代表了新一代本土作家对待香港这一城市的认同态度。”[1]徐霞认为:“西西开始了新题材新手法的试验,而背后亦和香港社会的本土意识抬头相辅相成。其实,自1971年港督麦理浩上任以来,香港福利、城市建设等各方面都快速发展,香港人开始意识到‘我城’的存在,本土意识愈趋明显。”[2]
发轫于20世纪70年代的香港意识——“我城”意识作为香港本土新的社会历史意识,有其时间起点、主体、心理建构等多层面的架构,作为较早在小说创作中体认并阐释“我城”意识的小说家,西西《我城》的书写本身即是一场面对旧的传统的分离与建构的仪式。这种分离与建构可以从四个层面加以考量:第一,新的社会历史意识是《我城》书写的逻辑起点,同时书写本身标志着西西前一创作时期的结束和新的创作时期的开始;第二,《我城》将焦点对准20世纪70年代香港年轻人群像,既是为“我城”意识主体代言,也是与老一辈港人主体的分离;第三,通过对香港本土经验特质性的书写,建构本土作家的心理与身份,并以此与南来作家分离;第四,投诸小说书写形式,《我城》在形式上对“我城”意识作出呼应。探勘这四个层面,西西《我城》的书写实将自身写作和个体生命融入“我城”意识的阐发之中,水乳交融,不分彼此。
一、“我城”意识的逻辑起点
《我城》从出殡与搬家写起。关于这种较异于惯常小说的写法,论者有不同的看法,如何福仁指出:“《我城》写于1974年底,从出殡、搬家写起,不是没有意义的,反叛过去的旧,迎接面临的新;但新和旧,却又不能截然割裂。”[3]凌逾指出:“西西不断在小说、电影、戏剧艺术样式中思考如何叙述丧礼,思考死亡,目的在于寻找超越规则、破除陋习的叛逆精神”。[4]罗贵祥则指出:“故事一开始所写的是继承——阿果一家因父亲的死亡而继承了一座古老大屋。承继大屋,也承继了那种家庭观念。”[5]108
西西用意究竟为何?通观全书,何福仁的看法更为可取,出殡、搬家意味着开始或者重新开始,更多指向新而非旧或继承,年轻一代送别旧的时间、地点、事件,在新的时间、地点开始新的活动和思维,“我城”意识是在新的时间、新的地点上发端的新的社会历史意识,这是“我城”意识的逻辑起点。20世纪70年代以来香港居民逐渐认识到香港作为“我城”的存在,更加注重香港的本土性、个体与香港的本质关系:香港的文化既不是完全传承中国的传统文化,更不是英国的殖民地文化,而是属于自己城民(本土)的文化,并逐渐确认香港“城籍”的身份,完成香港居民的心理建构。这种发端于新的时间、地点,归结为本土性的集体意识,宣告了与以往无意识的断裂和新的社会历史意识的诞生。西西《我城》的书写正是为“我城”意识立言,借助文学叙事,体悟香港本土经验,把握香港城市发展的特质性,进一步表达香港居民的共同经验。
西西作为香港城市的一分子,敏锐而自觉地从主体地位出发,在香港文学史上较早书写对“我城”的归属和认同,台湾学者施淑指出,“正是在这‘我城’的归属感下,她和她的小说人物,在不排除中国,也不排除世界的情况下,摆脱了外加于香港人身上的有关殖民地的道德裁断,有关曾经是、不久又将是中国的一部分的意识纠缠,使香港以它自己的地理人文面貌,香港人以现代都市居民的历史条件,活跃在她的文字世界”。[6]
结合西西小说创作实绩来看,西西对“我城”意识的体认也意味着她前一创作时期的结束与新的创作时期的开始。西西曾说:“对我来说,《我城》是一个分水岭,以往我写的是存在主义式的小说:《东城故事》《象是笨蛋》《草图》等等,都相当灰色……这小说不同,看事物抱持另一种态度,开朗多了,收结也充满希望……当然,仍不免有存在的意味,不过这个‘存在’,很不同了。”[7]198
二、“我城”意识的主体
关于《我城》创作的引起动机,西西托名“胡说”在全书第17节中以后设小说的方式予以解答。
找寻字纸的老人问胡说,“怎么开始的呢?”
胡说答,“是这样子的,在街上看见一条牛仔裤。看见穿着一条牛仔裤的人穿了一件舒服的布衫、一双运动鞋、背了一个轻便的布袋,去远足。忽然就想起来了,现在的人的生活,和以前的不一样了呵……还有,因为天气,晴朗的季节。看见穿着一条牛仔裤的人头发上都是阳光的颜色,红酒也似的脸面如一只只熟透的龙虾。大家都已经从那些苍白憔悴、虚无与存在的黑色大翅下走出来了吧,是这样开始的。”[8]225-226
西西曾说:“那时,香港也有许多这样的青年人,活泼,充满朝气,穿牛仔裤唱民歌,难得的是相当明白事理,有正义感,但这种正义感不会放在嘴边,对生活的要求很踏实,很朴素……他们做的不过是卑微的工作:看守公园,修理电话,没有什么了不起,生活环境却困难重重,可都努力去做,而且做得快快乐乐。这小说是献给这些无名英雄的。”[7]201
《我城》中西西创造出阿果、阿髮、阿游和麦快乐等众多乐观向上的年轻人,他们并非虚构、移植、拼贴的人物形象,而是西西在生活中眼见耳闻、亲身接触的年轻人;并非以某一个年轻人为主要角色,勾勒爱情、友情、事业、生活的种种,而是不分主次轻重刻画年轻人群像;并非聚焦倚重卓越才能或技术水准而位列经济收入高端的少部分年轻人,而是倾心于甘心平凡工作、自食其力、乐观向上的大部分年轻人。西西因为当时的年轻人而引发创作动机,为这些年轻人记录与立传,说到底是为她体认的“我城”意识立传,为“我城”意识的主体立传。再进一步,西西为她体认的“我城”意识和“我城”意识的主体立传,何尝不是也将自己纳入了其中的书写?或者,正是因为并非他者的身份,《我城》的书写是一场包括作者在内的城民向“我城”自曝胸怀的心灵史写作。
这些年轻人有着各式各样平凡有趣的职业,看似西西无心插柳,实是着意而为,并非有论者认为的“阿果找工作不过是为了有点有趣的事情做,在报纸上见到消息后,阿果做了一些‘填字游戏’就被录用了”,以此“表明作者在香港这个城市中的自信而怡然自得的态度”。[1]7-8阿果和麦快乐的职业是电话维修工,阿游的职业是电工和海员,这些职业固然是所谓蓝领阶层,更是一个现代资讯社会不可缺少的基层工作人员。何福仁引用社会心理学家英格尔斯及史密夫的观点,列出对新经验开放、准备接受社会变化、重视专门技术、愿意根据技术水平来领取报酬等十二项现代人格的条件质素,若以这些条件质素衡量《我城》中的年轻人,自然会另有一番结论。
三、“我城”意识的心理建构
1950年,12岁的西西随父母南迁香港。作为第三代香港作家,西西与南来作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1949年前后来港的第一批南来作家包括刘以鬯、徐訏、曹聚仁、金庸、梁羽生、倪匡等成名作家,他们的小说创作渗透香港严肃文学和通俗文学各个领域,尤其文坛名宿刘以鬯长期担任《香港时报·浅水湾》《快报》《星岛晚报·大会堂》和《香港文学》等报纸副刊和杂志的主编,西西的《象是笨蛋》《草图》和《我城》等重要作品都发表在《快报》副刊上。刘以鬯曾说:“我将这一类属于纯文学范围的文章‘挤’入版面,根本是违反报馆当局所规定的方针的……也斯写的专栏、西西写的小说、施叔青写的专栏,在《快报》副刊发表时,也常常被报馆中人指为‘难懂’或‘不为读者所喜’……我在香港编了三十多年副刊,一直在做‘挤’的工作,将严肃文学‘挤’入文字商品中。”[9]
虽然亦师亦友受其知遇,西西与第一批南来作家在心理建构上存在相当大的差异。论者多集中用“中原心态”、“家园想象”、“去国还乡”、“情感疏离”和“身份焦虑”等关键词来概括第一批南来作家的心理状态,而对西西而言,生长于斯的本土经验,不存在经验断裂和重组的困境,中国人或香港人的身份辩驳并没有给她带来足够影响的身份焦虑,这些身份、心理上的不同定位和状态从根本上决定了她与南来作家乃至上一代香港本土作家之间,在对待香港社会现实、大众文化等诸多方面存在的大相径庭的认知和态度。对西西这样的年轻一代本土作家而言,书写本土经验的特质性以及本土经验与南来作家香港经验的殊异之处成为他们进行心理建构的有效方法。
袁良骏指出:“《我城》不写残酷的商战,不写冷酷的人情,不写上层社会的勾心斗角、尔虞我诈,也不写下层社会的啼饥号寒、乞讨卖淫。作家用一颗童心看世界,她有意避重就轻,她把扰攘人世写成一片祥和,从而展现自己的理想和爱心。她用的是‘净化法’、‘蒸馏法’。”[10]西西固然是用童心看世界,《我城》何尝不写商业文化对人的异化(如开店设厂的阿东)、杀人越货(如麦快乐被抢劫)、社会动荡(社会暴动中的自制炸弹“土菠萝”)、饥饿贫穷、水灾难民?只是西西在书写中一方面没有将冷酷社会现实作为批判内核,另一方面没有采取传统写实主义手法,而是创立了“童话写实”的创作方法将社会现实“陌生化”、“奇特化”。袁良骏“不写……不写……”的否定式评论句式恰恰证实了她与南来作家经典批判叙述形态的不同,西西通过书写本土经验的特质性以及本土经验与南来作家香港经验的殊异之处,有效进行了本土作家的心理建构。
《我城》也对南来作家热衷批判的另一阵地——香港大众文化进行了本土经验不同的书写。罗贵祥比较刘以鬯的作品《酒徒》、崑南的《地的门》和《我城》对大众文化持不同态度时指出:“即使刘以鬯已经比较积极认识这个城市的状况,愿意理解两个空间差异的原因,但在处理新事物新题材如大众文化时,却不可能放弃既有的道德标准和信念,反而将这些标准视为个人的原则,以一个冥顽不灵的主体去抗衡大众社会的流行价值观……在西西的小说《我城》里,我们似乎不能看到类似在《地的门》或《酒徒》中,那种对大众文化或商业社会流行意识的浓烈厌恶情绪,也没有发现任何敌视社会的主体存在。《我城》里的人物对大众社会的态度,是认同和接受,多于反叛或对抗的。”[5]101,104
西西曾说:“一般小说都写成年人,悲哀愁苦,板起脸孔,写十分严肃的问题。为什么不写写青年人的生活,活泼些,从他们的角度看问题呢?”[7]200在谈论《玻璃鞋》等作品时这种宣告意味更加浓烈,她说:“我比较喜欢用喜剧的效果,不大喜欢悲哀抑郁的手法。写小说,我希望能够提供读者一样东西:新内容,或者新手法。现在的情况是,当悲剧太多,而且都这样写,我就想写得快乐些,即使人们会以为我只是写嘻嘻哈哈俏皮的东西。”[7]158
四、“我城”意识在小说形式上的呼应
《我城》第17节岔出主体叙述,描写了一个用尺来衡量小说优劣的故事,当尺们碰到有着阿果、阿髮、麦快乐、阿傻的字纸(即《我城》)时:
一把弯弯曲曲的尺首先说,这堆字纸不知道在说些什么,故事是没有的、人物是散乱的、事件是不连贯的、结构是松散的,如此东一段西一段,好像一叠挂在猪肉摊上用来裹骨头的旧报纸……
一把非常直的尺把头两边摇了三分钟,不停地说:我很反感,这是我经验以外的东西。
有一把尺是三角形的,是一把作不规则形状非等腰形的三角尺,它努力在字纸中间寻找各式各样的形状,结果找不到自己的三角原形,连圆形、长方形、六角形也没有,就叹了一口气。[8]225
故事、人物、事件、结构……这些都是传统小说要求必备的要素,西西早在行文之初便预想到日后评论界、读者的质问,遂以后设小说的方式在本文中为自己新的小说创作观立言,事实确如西西的预想一般,小说发表后遭到不少评论者和读者的质问。小说形式与内容的内在关联,小说家应该运用怎样的叙事手法表现新的内容、新的社会历史意识,不是此处探讨的重点,却如同黄继持指出的:“某个地区文学个性或曰‘主体性’的形成,就作品来看,大抵有两大端。一是本地经验之写入,从表层的地方色彩、生活方式,到深层的社会心态、价值取向。这从作品内容而言。另一则是‘形式’的突破,新形式带出对生活的新的切入,从而对当地经验与心态作出更多的折射,并为此地的‘生存情境’作出形式与内容统一的艺术揭示。”[11]西西作出小说形式的突破,为自己的创作观立言,不仅仅谋求小说形式的标新立异,其行为本身即是香港本土经验的表达与表现,是“我城”意识“形式与内容统一的艺术揭示”。
[1]赵稀方.西西小说与香港意识[J].华文文学,2003(3):7.
[2]徐霞.文学·女性·知识[M].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08:161.
[3]何福仁.《我城》的一种读法[M]//西西.我城.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257.
[4]凌逾.跨媒介叙事[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69.
[5]罗贵祥.几篇香港小说中表现的大众文化观念[M]//他地在地.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08.
[6]施淑.两岸文学论集[C].台湾:新地文学出版社,1997:352.
[7]西西,何福仁.时间的话题[M].台湾:洪范书店,1995.
[8]西西.我城[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9]刘以鬯.从《浅水湾》到《大会堂》[J].香港文学,1991(7).
[10]袁良骏.香港小说流派史[M].福建:福建人民出版社,2008:162.
[11]黄继持.香港文学主体性的发展[M]//黄继持,卢玮銮,郑树森.追迹香港文学.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8: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