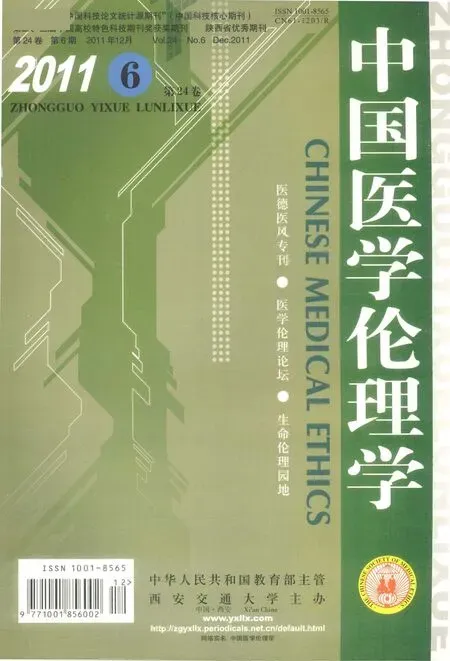促进科学与伦理的良性互动——国家人类基因组南方研究中心伦理学部工作体会
沈铭贤,丘祥兴,胡庆澧
(国家人类基因组南方研究中心伦理学部,上海 201203)
1998年国家人类基因组南方研究中心成立之初,时任中心主任陈竺就考虑组建南方中心的伦理、法律和社会问题研究部(简称伦理学部)。经过一年左右的筹备,伦理学部于2000年开始运作。这是我国第一家生命科学研究机构建立的伦理学组织。伦理学部由非理事单位(上海社会科学院)推荐人员出任主任,由南方中心各理事单位(包括中科院上海生命科学院、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第二军医大学等)推荐人员出任副主任,成员包括伦理学家、法律专家、生命科学家和医学专家,基本上把上海生命伦理学方面的力量联系组织起来了。同时,聘请国内外知名专家,成立了顾问组。
根据陈竺的意见和多年的实践探索,我们主要做了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1 开展生命伦理前沿研究,为主管部门制订政策和规范提供参考
近十余年,生命科学硕果累累,克隆羊“多利”横空出世、胚胎干细胞研究的突破、人类基因组计划提前完成,提出了诸多棘手的伦理问题,使生命伦理成为世人关注的热门话题。[1]从当时上海在胚胎干细胞研究上有较好基础又无伦理规范可依的实际情况出发,我们主要做了胚胎干细胞研究伦理问题的探索,提出了《人类胚胎干细胞研究的伦理准则(建议稿)》,[2]共20条。基本观点是:支持胚胎干细胞的研究,人胚胎干细胞研究是可以得到伦理辩护的,但一定要遵守严格的伦理规范。建议稿提出不久,上海市科委明确表态:上海就按这个准则做;科技部和卫生部颁布的《人胚胎干细胞研究的伦理指导原则》也吸纳了我们的相关成果。2004年,国际知名权威刊物——美国《肯尼迪伦理学研究所杂志》全文发表了该建议稿。最近,我们准备根据新的情况和问题,进一步修订和完善这一文件。
近两三年,受卫生部医学伦理专家委员会的委托,我们把主要精力放在了成体干细胞的研究和应用的伦理问题上。通过广泛的调查研究,九易其稿,形成了《人类成体干细胞临床试验和应用的伦理准则(建议稿)》,共26条,并附附件。这一建议稿已经由卫生部医学伦理专家委员会通过。在一些会议和学术活动中,我们的建议稿也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和共鸣。目前,有关保护基因隐私,防止基因歧视的课题已立项,我们也准备草拟一个建议文稿。
同时,通过有关渠道,积极向党和国家领导人反映情况、提出建议。原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和原副总理吴仪分别就基因研究和器官移植作了批示,对我们是极大的支持和鼓励。
2 普及生命伦理知识和理念
陈竺很重视生命伦理的普及,经常鼓励我们做好普及工作,认为不仅要向广大社会公众普及,而且要向科学工作者、医生和有关管理人员普及。确实,没有生命伦理知识和理念的普及,得不到相关人员和公众的理解与支持,再好、再完备的规范也难以实施。为此,我们采取了开设相关课程和讲座、发表文章、编写书籍、举办研讨会等多种形式进行生命伦理知识普及,十余年坚持不懈。
在上海交通大学生命科学技术学院的支持下,高等教育出版社于2003年出版了我们编著的《生命伦理学》一书。在此基础上,上海交通大学生命科学技术学院开设的生命伦理学课程受到大学生的欢迎,荣获上海交通大学教学成果特等奖。我们还承担着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院硕士和博士研究生的生命伦理学培训工作。
除在《科学》等京沪报刊开辟专栏,发表系列文章外,近年我们还出版了《基因伦理学》(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等著作。在此,我们想特别推介今年8月在上海书展上推出的《生命的困惑丛书》(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丛书由胡庆澧、沈铭贤主编,第一辑包括6本书:《生命伦理飞入寻常百姓家——解读生命的困惑》(沈铭贤)、《谁主基因——基因伦理》(张春美)、《面对死亡——死亡伦理》(徐宗良)、《小小鼠和多利羊的神话——干细胞和克隆伦理》(丘祥兴)、《控制生命的按钮——生殖伦理》(涂玲)、《白衣天使的翅膀——医患关系》(王德彦)。这些书的共同点是基本上用故事、用案例说话,还配了插图;力求通俗易懂,喜闻乐见。这是我们普及生命伦理知识和理念的新尝试,希望得到各位专家的支持和指导。
电视可能是比书籍更直接、更广泛的普及渠道。每当发生重大的生命伦理事件,上海的电视媒体往往会邀请我们去“解疑释惑”,与公众交流。中央电视台和英国、德国的电视媒体也来沪录制过专题节目。利用一年一度的科技节,还举办过两次公众自由参加的生命伦理讨论会。普及工作虽然收不到“立竿见影”之效,但我们相信,“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持之以恒总会有所收获。[3]
3 参与伦理评审,推进伦理委员会建设
伦理学部的成员,基本上都是一个或多个伦理委员会委员,参加涉及人的生物医学研究项目的伦理评审。目前,上海各大生命科学研究机构和各大医院的伦理委员会,我们基本上都参加了。
参与伦理评审,使我们对生命科学研究和医疗实践有了更多更深切的了解,交到了不少科学家、医生朋友,增长了知识,拓展了眼界,受益匪浅。同时也是传播和实施生命伦理规范的一个“理想平台”。
伦理学部也是南方研究中心伦理委员会的基础,开展独立的伦理评审。其中影响最大最广泛的可能是2003年对人-兔嵌合体囊胚的伦理评审。以盛慧珍教授为首席科学家的一项胚胎干细胞973项目,把人的皮肤细胞注入去核的兔卵母细胞,在国际上首次成功培育出了以人类为主的人-兔嵌合体囊胚,得到人的胚胎干细胞。这一消息当时在国际生命科学界不胫而走。但由于涉及敏感的伦理争议,国际知名刊物一再拖延发表,以致有可能危及其首创性。于是决定由我国的英文科学期刑《细胞研究》发表,并由我们作伦理评审。根据国际人类基因组组织关于克隆的声明,我们认为盛慧珍的工作作为基础研究是可以的,并不违背伦理,但不能应用于临床。结果该成果得以顺利发表,并产生了广泛的良好影响。
在伦理评审工作中,我们也深切感受到我国伦理委员会建设还存在诸多问题,需要大力推进。特别是胡庆澧教授,以他作为国际生命伦理委员会委员、卫生部医学伦理专家委员会委员、上海市医学伦理专家委员会主任和世界卫生组织前副总干事的身份和影响,2009年和2010年,分别主持了由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瑞金医院举办的以伦理委员会建设为主题的国际研讨会和由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举办的以多中心试验的伦理审查为主题的国际讨论会,请来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卫生组织以及美、英、德等国的专家。我国卫生部、药监局以及一些知名学者也参加了,成为我国伦理委员会建设的两次高层次高水平的盛会。
4 开展国内外学术交流
我们和国内一些生命伦理或医学伦理研究机构、专家学者关系比较密切,和《医学与哲学》、《中国医学伦理学》两大重要学术阵地也保持着良好关系。同时,还参加了“香山会议”、“东方论坛”、“院士沙龙”等以科学家为主,涉及伦理的一些活动。我们认为,这也是生命伦理学术交流的重要方面。
有一段时间,国家人类基因组南方研究中心伦理学部可以说成了国际上了解我国生命伦理情况的一个窗口。我们曾先后接待英国《自然》、《经济学家》,德国《焦点》,美国《华盛顿邮报》等报刊的采访。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以及卡普兰、魏德勒等著名学者也来沪和我们交流。这些有助于澄清“东方野蛮生物学”、“伦理真空”之类的误解,可能更重要的还在于平等的学术研讨。如我们与法国学者关于“克隆人”的伦理与法律问题的系列讨论(2001~2003)。今后,我们希望更多地登上国际学术舞台,特别是在国际权威刊物上发表成果。
综合上述工作,我们的体会集中到一点,就是伦理学家与科学家携手合作,共同促进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的良性互动。[4]长期以来,科学被认为属于“事实判断”,而伦理属于“价值判断”,伦理学家不关心科学问题,科学家不关心伦理问题。但现在生命伦理科学的发展,却几乎不由自主地渗透进伦理领域,提出许多新的棘手的伦理问题,事实与价值的截然两分,已难以成立。不过,由于传统的惯性,一些科学家和医生难免会担心,伦理的“介入”会不会束缚、妨碍科学发展,过去没什么伦理规范,用不着伦理审查,不也很好吗?何必“多此一举”?而伦理学家和法律学家则往往对科学不太熟悉。在这种情况下,特别需要科学家和伦理学家相互尊重,取长补短,携手合作。用我们顾问组老组长陈仁彪的话说,就是:高举团结的旗帜。不仅在伦理学部内部这样,我们在研究制订相关规范时,也十分重视吸纳科学家和医生参加,认真听取他们的意见。我们认识到,生命伦理并不是要阻碍生命科学的发展,而是力求科学健康有序地发展。因此,在我们的建议中,总是对科学研究抱支持的态度,努力为科学研究搭建“伦理平台”。在伦理审查和监督中,我们也尽可能地把科学与伦理统一起来,确保研究的科学性。正如世界卫生组织所强调的,“科学上不可靠的研究必然也是不符合伦理的。”
这样说,决不意味着不重视伦理,做科学的“尾巴”。现代生命科学的“主体性”不断推升——这种“主体性”主要表现在两方面:①研究对象日渐深入到“人”这个主体,直达基因层次;②研究成果日益发展到变革、改造“人”这个主体,直至可以设计人、制造人。科学在造福人类的同时,也可能带来前所未有的危害。因此,我们总是强调生命伦理是内在自生的,不是外部强加的;强调基础研究要宽松、临床试验要规范,医疗准入要严格;[5]强调要区分临床前研究,临床试验和临床应用;强调要规范伦理委员会建设,提高伦理审查的质量。
当然,科学与伦理总会存在矛盾和冲突,科学与伦理的良性互动是一个持久的、动态的、艰难的过程,我们愿继续为此而努力。
[1]胡庆澧,陈仁彪,沈铭贤,等.关于设立国家生命伦理委员会的建议[J].中国医学伦理学,2005,18(2):25-26.
[2]中国国家人类基因组南方研究中心伦理委员会.人类胚胎肝细胞研究的伦理指导大纲(建议稿)[J].中国医学伦理学,2001,14(6):8 -9.
[3]沈铭贤.生命伦理学正在走近我们[J].中国医学伦理学,2002,15(1):28 -30.
[4]丘祥兴,沈铭贤,胡庆澧.科学家的社会责任[J].中国医学伦理学,2007,20(6):3 -7.
[5]胡庆澧,丘祥兴,沈铭贤.干细胞研究与应用的伦理思考[J].中国医学伦理学,2010,23(6):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