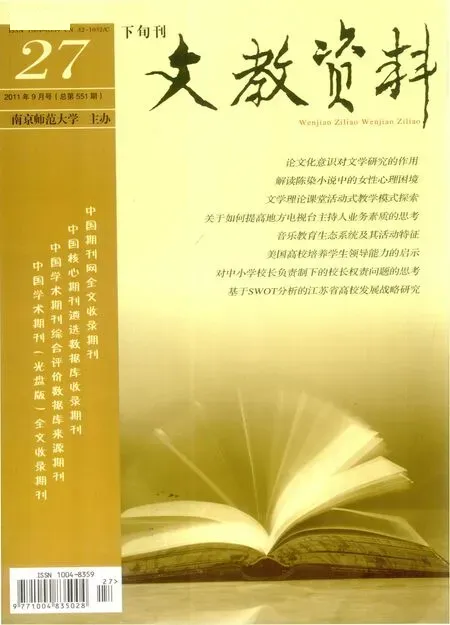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遥远的救世主》解读
任文汇
(苏州职业大学 教育与人文科学系,江苏 苏州 215104)
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北方小城——古城女刑警芮晓丹受好友肖亚文之托,为其老板丁元英在古城租一套临时住房。丁元英清华大学本科毕业,并取得了德国柏林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利用德国金融公司的资金和自己的头脑运作私募基金公司,在中国股市进行了掠夺式的经营。可就在私募基金盈利的最高点,丁元英突然以冻结自己资金三年的代价宣布终止合作,暂时隐居古城。在与丁元英的接触中,芮晓丹被他的叛逆、奇特、不循常规和不可预测的个性深深地吸引,对他产生了眷恋和爱慕。为了明白丁元英所论述的文化属性,也为了有更多的时间与之相守,芮晓丹决定向丁元英要一件特殊的礼物:让丁元英在贫困县里的贫困村——王庙村写一个脱贫致富的神话。就在丁元英用“杀富济贫”的方式将要完成对神话的书写时,芮晓丹在一次与通缉犯的偶遇中被炸毁容,她开枪自杀,而丁元英伤心吐血,最终黯然离去。
故事的结局是丁元英精心设计的格律诗音响公司强行进入市场,成为品牌,而“被劫”的乐圣公司在官司中败诉,董事长林雨峰驾车自杀,肖亚文出任格律诗的董事长兼总经理。为了利益,乐圣被迫与格律诗在王庙村合作,而媒体则围绕得救标准与得救之道展开了激烈的辩论。
一个商战故事,一个爱情故事,互相交汇又各自独立。本书最牵动读者的是主人公丁元英,无论从哪个层面看,他都可以说是一个“高人”,不管是小说开头即放弃的私募基金,还是对王庙村的扶贫,都显示了他对其时社会形势极为精准的判断,说他运筹帷幄一点都不为过。他在股市运作中得心应手,短短几个月就挣得将近两倍的利润,似乎完全破解了股市的密码。把北京格律诗音响公司和王庙村音箱生产基地设计成两个法律上相互独立的实体则表现了他极高的智慧。通过对中国名牌乐圣公司采取一种“杀富济贫”的方式来完成扶贫“神话”,在此过程中,将要发生的诉讼官司,以及胜诉的必然,格律诗几位股东的淘汰出局,刘冰因心术不正而走向灭亡,与乐圣公司的最终合作等都在丁元英的预料之中。他对自己及周围人的判断几乎无一不准,而判断的准确甚至让他对芮晓丹的未来具有某种预见:“你应该辞职,请注意,是你应该,而不是我希望。只要你一分钟是警察,你这一分钟就必须履行警察的天职,你就没有避险的权利。”[1]丁元英的这段话几乎准确预见了芮晓丹的死。他的朋友韩楚风、知己芮晓丹都说他“是个明白人”,助手肖亚文这样评价他:“是魔是鬼都可以,就是不是人 (凡夫俗子,平庸的人)。认识这个人就是开了一扇窗户,就能看到不一样的东西,听到不一样的声音,能让你思考、觉悟,这已经够了。 其他还有很多,比如机会、帮助,等等。 ”[2]近乎一种高山仰止的崇拜。就连他的对手林雨峰都不得不叹服他有着“严谨的思维和对繁杂事物的精准判断”。而在王庙村农民的眼里,他更是全知全能的基督耶稣再世,他们把得救的希望全部寄托在丁元英的身上。难怪他从本质上总是把自己放在一个较高位置,以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俯视他眼中的芸芸众生,“他的每一个毛孔里都渗透着对世俗文化的居高临下的包容”。
作者试图把丁元英设计成“进不去,出不来”的高人形象,一个救世主的形象,可是翻开历史看看,哪一页哪一行能找到救世主救世的记录?没有,从来就没有。从来都是救人的被救了,被救的救了人。如果一定要讲救世主的话,那么符合和代表客观规律的文化——强势文化才是救世主,而丁元英正是作为此种文化的载体出现的。作为强势文化的代表,丁元英对“文化属性”有着自己的深刻解读,他认为:“透视社会依次有三个层次,技术、制度和文化。小到个人,大到国家民族,任何一种命运归根到底都是那种文化属性的产物。强势文化造就强者,弱势文化造就弱者,这是规律,也可以理解为天道,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3]丁元英对强势文化和弱势文化进行了解释:“强势文化就是遵循事物规律的文化,弱势文化就是依赖强者的道德期望破格获取的文化,也是期望救主的文化。”在丁元英眼里,中国传统文化不过是“皇天在上的文化,是救主救恩的文化”,“传统观念的死结就在一个‘靠’字上”。[4]由此他分析:如果一个民族的文化从骨子里就是弱势文化属性,怎么可能去承载强势文化的政治、经济?衡量一种文化的属性不是看它积淀的时间长短,而是看它与客观规律的距离远近。五千年的文化是光辉、是灿烂,但传统和习俗得过过客观规律的筛子。丁元英对人的社会文化属性问题的见解是如此独到与精辟,他认为正是独特的文化属性造就了许多长期处于愚昧麻木之中的社会人,导致他们永远贫穷落后。丁元英是明白的,也是孤独的,正如尼采所说:更高级的人独处着,这并不是因为他想孤独,而是因为在他周围找不到他的同类。
丁元英认为强势文化的魂就是遵循规律和法则,正是基于这种认识,他在设计格律诗音响公司和王庙村音箱生产基地的相互关系时将两部分各自独立,对发烧友组成的音响公司采取股份制方式进行制约,通过强力作用的“杀富济贫”使得格律诗强行进入市场。对王庙村音箱生产基地则采取“用小农意识治小农意识”的方式,在产品生产各道工序的农户之间实行小农经济的买卖关系,现金交易,一环制约一环,谁出问题谁担责,不影响别人的利润。允许弱势文化背景下的农民有一个适应的过程,让市场去纠正他们,最终用经济杠杆来解决产品质量和生产成本问题。丁元英不是神机妙算,也不是能力超群,只是尊重市场规律和自然法则,他让市场规律打开农民的眼界,让市场的无形之手抑制他们的小农意识,让那些向来只知道神和上帝是救世主的王庙村村民明白要富强不能靠别人,摆脱贫困的救世主就是他们自己。而他本人不过是在已经缘起的事情里顺水推舟,借英雄好汉的嗓子喊上两声而已。至于这些农民是否明白市场规律这个“道”,则完全取决于他们自己是否能觉到悟到,正如丁元英说的:“允许几个股东去扒井沿,能不能爬上来取决于他们自己,对农户,从基础设置就不给他们期望天上掉馅饼的机会。我救不了他们,我能做的就是通过一种方式让他们接受市场经济的生存观念,能救他们的只有他们自己。”是的,对王庙村的农民来说,真正的救世主不是丁元英,而是认准市场,吃别人吃不了的苦,受别人受不了的罪,做别人做不到的成本和质量。扶贫的本质在一个“扶”字,如果你根本没打算站起来,老天爷来了都没用。扶贫扶什么,扶的就是一种精神,是一种观念。它既不是简单的市场竞争,又不是简单的授人以鱼,而是基于一种社会文化认识的自我作为。有人认为几个股东退股,林雨峰驾车坠崖,刘冰跳楼自杀都是丁元英设计的,事实并非如此,是他们的虚荣,他们特有的文化属性,以及他们自私的性格属性决定了他们的结局。正如冯世杰自己所说,他们是“烂泥扶不上墙的货”,扒着井沿看了回外面的天,又都掉了下去。冯世杰还有改变家乡贫困的念头,还有与王庙村的关系,所以最终能够进入格律诗成为股东,而叶晓明的小农意识则注定他只能在小本生意里打转转,终难成大器。刘冰呢,虽说他只是为衣食奔忙的常人,虽说“小人无咎”,但小农意识再加上极端自私贪婪的元素最终导致他自杀。这三种人似乎昭示着三种不同的道路:本质善良还有出路,目光短浅只能在小河里游游泳,而心术不正必将走向灭亡。丁元英给过他们机会。他们“扒着井沿看过一回天”就是明证,后来的坠落不是他所设计,但在他的意料之中,所谓性格决定命运,只是自然规律所致,并非他料事如神。
在扶贫的整个事件里,丁元英没有任何能让人感到“神”或救主的招式,每一件具体的事都是普通人都能做到的普通的事,他的的确确是在公开、公平的条件下合理合法的竞争,没有任何秘密和违法可言,所谓“神话”就是这么平淡、简单。神是什么?神即道,道法自然,如来。丁元英说过,这世上原本就没有神话,所谓神话不过是常人的思维所不易理解的平常事。诚然,他所设计的神话无非是遵循了事物的客观规律,无非是超越了常人所能理解的因果关系而已。
原来能做到实事求是就是神话,能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就是神。由此观照现实社会,要做到实事求是,需要的是一双“天眼”,一双剥离了政治、文化、传统、道德、宗教的眼睛,然后再如实观照政治、文化、传统,把被文化、道德颠倒的真理、真相再颠倒过来。用这双“天眼”去观照文化属性和命运的因果关系,人们才能超越常规的因果思维,才能比较容易看到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当然这还需要当事人自身的悟性。事物的规律本身存在,许多人却视而不见,而能否看见取决于个体的观念和认识,取决于个体的经验和建构,取决于个体能否觉到悟到。从觉到悟到这一点而言,丁元英显然高于一般人。他不是神,不是救世主,但他做到了其他人做不到的事,同时影响了身边一群人的改变,仅此而已,也许这就是强势文化的意义。
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想拯救全人类的人骨子里是寂寞,现代社会每个人更重要的使命是自我救赎,以及拒绝被人乱拯救。
[1]遥远的救世主.作家出版社,204页.
[2]遥远的救世主.作家出版社,6页.
[3]遥远的救世主.作家出版社,15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