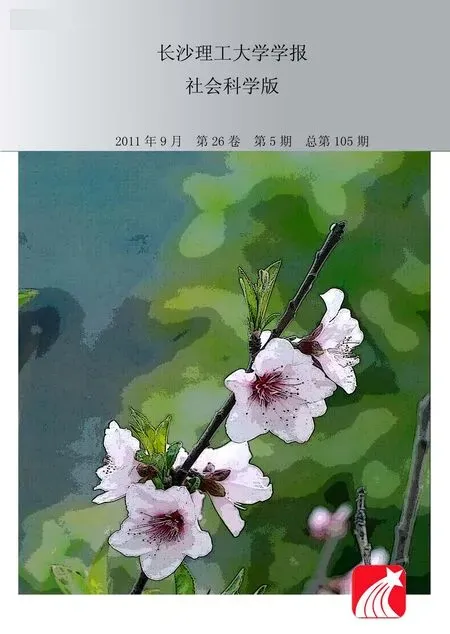技术哲学“发展”综述
王 飞
(大连理工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辽宁 大连 116024)
一、技术哲学分期与发展期的成就
通常,从沃尔夫(Christian Wolff,1679-1754)的《逻辑学》(1728)以来一直到19世纪六、七十年代就被称为技术哲学的诞生期。此后的技术哲学进入了大约一百年的漫长积累期,直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技术哲学的建制化发展才真正开始。表现为论文、刊物、专著的数量大幅度增长;发达国家如德、英、法、美、日、前苏联等国相继成立了一系列技术哲学学会和研究机构;出现了大批知名专家及论著,如德国H.马尔库塞的《单面人》(1964)、H.贝克的《技术文化哲学》(1979)、G.罗波尔的《技术系统论》(1979)、F.拉普的《分析的技术哲学》(1978)等,美国L.芒福德的《机器的神话》(1967、1970两卷本)、C.米切姆的《技术和哲学》(1977),法国G.弗里德曼的《关于人和技术的七次讨论》(1969)、西蒙顿的《技术对象的存在方式》,日本中村静治的《技术论论争史》(1975)、三枝博音的《技术哲学》(1977),加拿大M.邦格的《建立一种哲学》(1966),捷克46位学者撰写的《十字路口的文明》(1967)等,[1]技术哲学得到了社会的公认。
与先前的诞生时期和后来的兴盛时期的发展状况相比,处于中间阶段的技术哲学发展时期,确实看起来似乎“沉寂”了。这表现在,技术哲学没有引起强烈的社会反响,没有得到社会的公认,作为一门学科它的体系也没有建立起来,从这方面讲技术哲学好像没有什么进步。然而这一近乎漫长的时期,正是技术哲学积累孕育阶段。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世界上的发达国家德国、英国、法国、日本、美国等国都相继展开了技术哲学研究,并且形成了不同的思想流派,技术哲学史上最为著名的几位大家几乎都在这时酝酿成熟了自己的作品。德国著名哲学家、早期现象学运动中仅次于胡塞尔德的第二大师、知识社会学和哲学人类学的开创者舍勒(Max Scheler),源于对人的命运与地位的深切关注,在《知识社会学》(1924)[2]与《人在宇宙中的地位》(1928)[3]两书中,技术被解释为人类低等的精神因素“本能-冲动”运作的产物,技术在人的生存价值体系中被列于金字塔的最底层。著名的历史学家斯宾格勒(Osward Spengler)在1931年发表了他的一本技术哲学的小册子《人与技术》,[4]在这本书中,他从历史文化哲学的和人类学两个角度对技术社会进行了悲观主义的诠释。同年由卡西尔(Ernst Cassirer)发表的《技术与形式》,[5]同样在历史文化的框架下对技术进行了界定,然而技术在此却获得了自由的象征的光荣身份,因此技术虽然内藏危险,但却是人类必须追求的,技术是人的本质内容之一。葛奥格·容格(Friedrich Georg Juenger)写于1939年的《技术的完善》(发表于1946年)[6]一书中,提到现代技术对自然的“榨取”、“逼迫”和“折磨” 以及对人的剥夺,把技术解释为由笛卡尔思想引发的、由人的力量意志推动的妖魔式发展的力量。存在主义的大师海德格尔(Martin Heidger)首先在1949年11月的报告《集置》(后来以《对技术的追问》于1954年为题发表的)[7]中把对技术的思想起源的追问推进到柏拉图,指出了现代技术的形而上学本性(或者反过来说也可以,即形而上学的技术本性),①及其现代技术引起的人类认识手段和生存地位的转变。海德格尔的学生存在主义的第二代代表人物、历史学家雅斯贝斯(Karl Jaspers)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完稿后来在1931发表的《现时代的人》(又译为《时代的精神状况》)[8]对处于科学技术时代的现代人的生活和精神状况进行了生动地描述;发表于1949的《论历史的起源与目标》[9]又从历史发展的大尺度上考察了当前科学技术时代的现实状况和未来走向。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工程的技术哲学领域最著名的人物德韶尔也在这一时期就发表了他的代表作《技术哲学》(1927),[10]在这本书中他首次提出了“第四王国论”,把技术看作是至少不低于科学、道德、艺术的人类活动的第四领域;为了回应当时人们围绕他的理论进行的争论,1956年他对这部著作进行了重新地补充,并以《关于技术的争论》为题发表。[11]法国埃吕尔(Jacques Ellul)的《技术社会》(1954)[12]把技术作为一个文化现象进行考察,指出我们目前的社会已变成一个技术社会,在这样一个社会中,任何东西都出自技术,为技术而存在,他因此被称为技术决定论的代表。日本关于技术本质认识的“手段说”(户坂润)、“适用说”(武谷三男)[13]也在这一时期形成。美国芒福德的“两类技术论”是在他著名的作品《技术与文明》(1934)[14]中提出来的。
二、两次技术哲学国际会议
上述著作的发表在技术哲学史上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这些著作大多被奉为技术哲学的经典著作,是后来的研究技术哲学史的人的必读之作。然而遗憾的是,当时仍旧缺乏学者之间直接交流与讨论,所以当时没有形成社会普遍的反响。技术哲学走向大众,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事情。为此,我们必须要提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开始的技术哲学会议。在德国,确切地讲是1947、1952年达姆施塔特城举行的两次国际会议和1950年开始的德国工程协会(Verein Deutscher Ingenieure或VDI)举办的差不多每年一届的技术哲学会议。两次达姆施塔特城会议的突出特征是它的国际性和多专业性,来自10几个国家的10几个专业的代表参加了会议。德国工程师协会举办的会议相对区域性强一些、也更专业一些(主要是德国工程师协会的成员,当然德国工程协会本身的成员就把包括来自多个专业的专家),但这些会议直接促使德国工程师协会于1956年成立了《人与技术》的研究小组(德国技术哲学建制化发展的重要标志之一)。②
1947年,在德国被第二次世界大战毁坏了3/4的达姆施塔特城举行了首次技术哲学的国际会议,会议的主题为“关于工程师教育的国际会议(Internation Kongress Ingenieurausbildung)”。来自瑞士、英国、美国、立陶宛、中国、希腊、荷兰、伊朗、奥地利、罗马、瑞典、泰国, 捷克斯洛伐克等十几个国家的不同专业的代表(工程师、科学家、哲学家、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历史学家、犹太学家、宗教学家、艺术世家、政治家、经济人士、技术人员)500人参加了会议,会议日期长达十天(7.31-8.9),围绕三个主题:“技术是伦理和文化工作(Technik als Ethische und Kulturelle Aufgabe)”、“世界工程师教育的对象和发展趋势(Stand und Entwicklungstendenzen der Ingenieurausbildung in der Welt)”、“学生和社会中的突出问题(Auslese der Studenten und Soziale Fragen)”,会上听取了37个报告,更多的与会人士参加了讨论。很明显,在这里第二个主题,即“世界工程师教育的对象和发展趋势”是会议的主要目的,但是对这个问题的讨论必须建立在对工程师的工作及其承担的责任的正确认识之上,因此第一个主题“技术是伦理和文化工作”作为一个理论前提是必须探讨的,它是第二个问题的起点和根据。围绕第一个主题,会议达成以下共识:
1. 不管每个人的立场如何,我们大家都深刻地认识到,技术从来必须是一项伦理和文化工作,而不应该是别的,每个人特别是每个工程师都对完成这个工作负有责任。
2. 每个人的道德与人道责任是首要的价值取向,这一价值中必须包含所有的技术活动,必须在技术中得到体现,因为技术是文化创造者和文化载体。
3. 根据这一观点,我们不应继续指责技术本身破坏了内在价值和外在价值。
4. 工程师的创造活动中所显示的神圣理念的火花显然并不比诗人作品中的少,应当得到崇敬。
5. 滥用技术的是敌视文化的力量,不是技术内在的力量。
6. 每个个人都必须通过所有的手段阻止那些不利于社会的、对技术以及技术提供的手段和可能性的滥用。
7. 对于世界上所有的工程师来说,一个迫切的任务是在这方面寻找合适的途径。一个重要的任务是提高工程师参与立法与执法行为的自觉性。
8.毫无疑问,在年青人决定从事工程师职业之前,作为基础必须接受一个坚实的教育理念。
9. 教育的目的,是满足这些要求,在全部的工程师培养教育过程中不断引导他们认识与接收这一职业所具有的伦理与文化义务。[15](P498-499)会议得出的这些结论,表现出强烈的理性和乐观主义特征。大多数人(包括普通大众)乐于接受这样的观点,特别是工程师,因此会议的精神影响了当时和后来整个工程行业的发展,特别是在德国;就当时来说,它还是会议得以继续的保证,是第二个主题继续进行的保证,就这一方面,可以肯定地说,会议实现了它如期的愿望,达到了它的目的。当然就技术哲学本身的发展来看,会议的最主要贡献是对工程师责任的认识。它们突破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莫里森(George S.Morison)、普鲁特(Henry Prout)和胡佛(Herbert Hoover)的普遍责任,是工程师责任的进一步具体化,当然这些要求仍然透露出一些一般的因素和理想的性质。
对第二个主题“世界工程师教育的对象和发展趋势”,得出的结论如下:
1.把年轻人培养为能够进行科学思维的工程师,使他们有能力在技术进步中取得尖端成果,这样的教育理念与欧洲高等学校的传统相符。只有在学生的数量相对较少的情况下才有可能继续坚持这一传统。
2. 特别是在美国,人们习惯于培养数量众多的能干的工程师从事开发和企业活动,在欧洲完成这一任务的首先是高等专科学校。
3. 是否应该在这两种教育目标中求得某种平衡尚是一个有待探讨的问题。
4. 从事科学活动的工程师必须同时在自然科学专业方面受到扎实的基础教育,其中包括具体的操作。其专业化训练应当在高年级时中开始,甚至也许可以推迟到开始工作时。
5. 良好的基础教育可以提高从事职业活动的能力,并且确保完成一项任务时不同专家之间的默契合作。
6. 全面的基础教育也是理解伦理义务的必要前提,我们认识到了这是高于其他责任的首要价值。
7. 通过加大技术专科学校中的基础教育或者通过与大学的合作可以实现这一目标。
8. 在专业学习中挤出为此所需的时间,是对教师们提出的一个很高的要求。[15](P499-500)
回顾德国工程师教育的历史,“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是德国工程教育发展的一个永恒的主题,德国工程师协会在加强工程教育的理论化方面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正是在德国工程师协会的协调和推动下,德国工程教育由最初的注重实践的特点向着更高的学术水平和最终与传统大学平等的方向不断改革发展。德国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较为完善的高等工程教育,并在世界范围内享有较高的声誊。德国工程师教育的特点就是,“理论”与“实践”两方面特点都十分突出。今天德国工业大学里课程结构的形成,可能就是一种在理论和实践两极之间讨求平衡的结果:学生必须圆满完成基础学习(Crundstudium)和主科学习(Hauptstudium),③方可认为受到了理论及实践两方面完美的教育。这次会议形成的共识显然继续延续了德国工程师协会重视工程师理论教育的精神。
1952年的“达姆施塔特城对话”,会议的主题是“人和技术(Mensch und Technik)”。这个会议像上面的会议一样,具有国际性和跨专业的鲜明特征。与上一个会议相比这个会议更加复杂,会议涉及到“技术和人”、“技术与宗教”、“控制技术”、“技术的工业化”等题目,大会上的许多议题都悬而未决,无法获得一致性的认识。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事后进行简单的归纳和总结。我们可以把所有的对于技术与人的关系的观点归纳为两种倾向:一是对技术进行颂扬的乐观主义态度,相反的一面就是对技术的进行批判的悲观主义立场。
乐观主义者如胡本施德特(J.Hoppenstedt)、克拉爱莫(Otto Kraemer)、包括德韶尔等,他们认为技术不会导致对人性的奴役,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意识到技术对我们的危害,我们可以对技术进行有效的控制。“这一指责同样过时了,我们生活在技术控制的自我调节的时代”。[11](P373)相反,机器可以代替人从事单调重复的工作,因此我们有时间的可能也有物质的保障来从事想象、从事自由的创作和休闲。“技术是一个法则,但是是一个对自由人的法则。”[11](P378)而且标准化的流水线作业可以培养工人的秩序观念、勇气和合作意识,工人之间可以形成兄弟般的友谊。乐观主义者还企图在技术的工业化阶段,通过对“规划者”、“设计者”“制造模型的人”的教育和消费者的教育,控制技术的发展方向。相反的观点,如福特文勒(Franz Joseph Waengler)则认为,技术特别是流水线生产会压制人的个性发展、创造力的发挥,技术导致人的异化和自然的异化。特里迟教授(Tritsch)认为更具根本性的问题,就是人们企图用技术来修复技术造成的破坏。批判的悲观主义者并不能给我们提供解决问题的道路,毋宁说他们的特点就是破而不立。乐观主义者的观点又过于理想和浪漫,虽然它们本身最反对乌托邦主义。但是我们也必须承认,现在我们走的道路应当说基本上没有突破理性的乐观主义者所划定的范围。我们人类作为生物所具有的惰性和贪婪,使我们既没有勇气退回到从前的生活状态,也不可能放弃对眼前享受的追逐,这也是直到今天我们仍对之喋喋不休的争论不停的根本原因。[16]
三、德国工程师协会及其举办的技术哲学会议
1950年开始的德国工程协会举办的几乎每年一届的技术哲学会议(分别是:“关于工程师的责任(Ueber die Verantwortung des Ingenieurs)”(1950,卡塞尔)、“技术时代的人与劳动(Mensch und Arbeit im Technischen Zeitalter)”(1951,马堡)、“技术引起的人的变化(Die Wandlung des Mensch durch die Technik)”(1953,图宾根)、“技术场中的人(Der Mensch im Kraftfeld der Technik)”(1955,慕尼黑))基本上延续了达姆施塔特城会议的自由讨论风格和关注现实问题与理论思考并重的风格。
1950年在卡塞尔召开的会议主题是:“关于工程师的责任”[17](P849),从题目我们就很容易发现此次会议与1947年的达姆施塔特城会议的内在联系,它是1947年会议在“工程师的责任”这一问题上的深化。在这次会议中占主导地位的工程师们对未来的乐观倾向。当时德国工程师协会的会长普朗克(R.Plank)的观点具有代表性。他最后就整个会议进行总结时讲,人的道德、精神发展与技术发展的不同步,导致人类社会的不和谐,使整个社会处于失衡状态,这是当今的现实。但是他认为这种不和谐状态主要是因为精神的发展相对于技术发展的落后造成的,与技术本身没有必然的联系。他相信,具有服务者和奉献者精神的精英,可以为社会和技术进程的完善贡献力量,可以赋予它高质量。他也看到科学技术的发展对人类造成了威胁,技术具有非人的趋势,但他并不因此就对技术的未来发展持悲观的态度相反他认为科学研究、技术发展是不可以阻止的。他同时也强调技术自身不是目的,技术是听命于人的工具、是辅助的手段,技术的目的是人的精神,“技术必须从属于精神,机器必须是服从于人的辅助工具” 。[17](P849)在这一层意义上同样要求工程师的热忱和真诚。
会议的第一个发言人心理学家策德斯(A.Zeddis)的题目开门见山,他的报告的题目是“责任是人的本质特征” 。[17](P849)在论证他的题目时,策德斯从古老的人类的普遍认识出发,做了一个非常机智的三段式推论。他说,既然人的精神、灵魂是人的本质特征,是人区别于其它物种的本质属性,人的这一本质特征赋予人以判断力,那么人就是它的行为本身、就是他所做的。由此他得出结论,工程师应当承担责任和义务,应当行为谨慎、品性真诚。当然还有其他许多发言人都阐明了他们的观点,此处不宜一一赘述。比如金茨尔教授(Kienzle)和“标准化”问题的先驱黑米希(W.Hellmich)在谈到标准化问题时都反对标准化导致个性和自由的丧失的流行观点,相反他们主张来源于不同领域、人类的不同需求的标准事实上为技术活动提供了必要的行为的依据。“自由与约束之间的节奏是生活的旋律” 。[17](P855)
1951年3月马堡会议的主题是“技术时代的人和劳动”。在会议上,基督教神学家首先获得了表达自己意见的机会。基督教教士德林(Doering)承认技术人员和科学人员、诗人、文学家等的劳动具有同等重要的价值。他同时也强调技术本身不是目的、不是人类生存的意义所在,劳动必须接受神的照看。并且他认为技术人员进行技术创造的知识源于上帝创造世界的知识,得益于基督的启示。基督教神学家胡夫那(D.J.Hoeffner)在他的报告“人与技术”中,阐明了他的关于技术价值的观点。他指出技术在伦理的价值等级秩序中处于服务价值的层次。技术不是唯一的也不是最高的价值,技术的价值要服务于人的生活价值,真、善、美的精神价值和宗教的价值。技术与经济工作都是上帝所赐予的工作,他以其自身的内在特征嵌入价值体系。技术本身也不是恶的,相反,作为上帝之子的人的创造物,技术应当从属于上帝,它是善的。所谓的技术魔力,事实上是人对技术的滥用,是人心的魔力。展望未来,他充满自信,他相信物质世界将以新的、自由的、清晰的方式继续存在。
劳动与休闲问题是这次会议的又一个讨论热点。克拉爱莫教授(Otto Kraemer) 的观点具有代表性,他在报告“休闲的获得和运用”中指出,一方面,技术的迅速发展必然会带来休闲时间,有意义的工作会创造幸福。另一方面足够的休闲时间不仅可以消除疲劳,而且可以成为技术创造的动力。正义感、追求知识、制造的欲望和爱是进行技术创造的源泉。当然,他也警惕人们,不恰当的休闲可能导致对劳动的厌恶。
1953年图宾根技术哲学会议的主题是“技术引起的人的变化”。克拉爱莫教授在会后对会议内容进行了总结报道,文章认为,具有依赖性的人使自己从偶然性和危险中解放出来的愿望和行为是所有文化、艺术和技术的共同基础,回到老路上去是不可能的。为了生活得更好,必须使工程师具有更深的洞察力、更好的愿望,为此需要十几年的教育,需要工程师为自己的工作进行解释、采取行动、进行斗争。
会上,当时联邦邮政部长舒伯特(H.P.Schuberth)谈到了技术的群众化力量,提醒人们注意技术可能存在的泯灭人的个性的危险。他指出,人不是机器人,不是“计划——应当——完成”的人,人的本质是自由的,人具有精神和道德需求。但他同时也对今天大众具有的个性质疑,他问:今天这些反复被强调的个性是否太强了?为此他要求工程师必须对自己从事的活动要有更加清楚的认识,不仅对技术的应用问题,而且对工作和完成目标的整个过程都清楚明了。施密特教授(H.Schmidt)、瓦格纳教授(Wagner)、克勒教授(O.Kroh)、瓦尔特教授(Walter)的报告谈论的是控制技术。他们共同的倾向是对现实状况的接受和对技术具有魔力的观点的反对。普朗克教授讲,我们应当意识到,我们出生在技术时代,没有可能,只有现实。不管我们喜欢不喜欢,我们必须当作现实来对待。控制制造的主席艾卡特(H.p.Eckart),汽车为例,批判认为现代技术具有魔力的观点。他问,汽车本身具有魔力吗?不,汽车同小羊一样、甚至比小羊更形式化。但是如果他服务于有魔力的人,那么汽车就会变得有魔力而且邪恶。[18]
“技术场中的人”是1955年慕尼黑会议的题目和主导思想。会议的内容同样由克拉爱莫教授在会后进行了整理,并在德国工程师协会出版社出版。书的前言,是由克拉爱莫教授写的《形式的力量》一文,在这篇文章中,作者认为,我们应当在自我控制的意义上反思形式的力量,包括技术自身的变化和技术作用于人引起的人的变化。从古至今对技术发展起决定性作用的力量是共同的,即自然力和人类的两种力量的共同作用。今天现代技术发展造成的结局要求技术人员应当对现代技术的发展负责。布朗施瓦格(W.Vogel-Braunschweig)的报告同样以历史为线索,考察了冰期的石窟绘画、早期文化、古典文化和现代文化,探索造成这些变化的内在原因——技术。源于自然力和人对可能性的超理性信仰的共同作用,每天都产生了和正在产生着新的“被构造的世界”。莫瑟教授(Moser)的观点在哲学家、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当中具有代表性,他反对技术是创世者上帝委托给人制造产品的观点。这个理论问题涉及技术创造的动机、可能隐藏的危险、工程师的作用等一系列相关问题。[19]
在国际范围内,50年代初国际哲学会议的恢复,使技术哲学的建制化发展有了可能。第十一次世界哲学大会(1953)上,布林克曼(Brinkmann)作了著名的“人和技术”的报告。十二次代表大会(1958)意外地收入了一系列有关技术的论文。到了第十五次世界哲学大会(1973)会议的主题已变成为“科学、技术和人”。[20]可以说,在二战后的10多年的时间,这几次重要会议的举行是技术哲学建制化发展的带有前奏性质的决定性事件。
[注释]
①或者反过来说也可以,即形而上学的技术本性。海德格尔认为形而上学自诞生之日起,即从柏拉图开始直到尼采,便有技术的特征,即主客二立的思维方式和计算的特征。现代技术是形而上学发展的必然结果。
②这些会议召开直接影响了1956年即德国工程师协会成立100周年期间 “人与技术”研究组的建立。该小组下设教育、宗教、语言、社会学和哲学工作委员会,它吸收和培养了不少杰出的技术哲学家。西蒙·莫瑟、汉斯·伦克、冈特·罗波尔、阿洛伊斯·胡宁、汉斯·萨克斯以及弗里德里希·拉普等当代德国杰出的技术哲学家都是这个研究小组的成员。
③基础学习主要包括自然科学,意在发展学生的科学知识基础。基础学习的结束以通过前期考试(Vorpruefung)为准,通常需要两年半到二年的时间考试及格可得到“准学士位(Vordiplom)证明,“准学士”并非文凭,不会得到任何机构的承认。前期考试主要是检验学生是否在总体上理解了所学的基础科学知识。通过了前期考试方可进入主科学习,主科学习包括听课、试验室工作、小组课程设计和毕业设计等,最后也有一次相应的主科考试(Hauptpruefung)。这一阶段的可选课程,不管是数目和种类都是大量的,实践环节比重也较大。研讨课及项目设计的题目因为来自并将用于实际需要解决的问题,所以要求很高,是对工程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的锻炼和考查。通过项目设计学生往往能获得与工业界的接触机会,对未来的工作环境得到一些亲身体验。最后主科考试主要考查学生对所学专业领域的学习和研究的程度。主科学习的时间因人而异,差别较大,平均为二到四年。所以德国工程学生一般要经过五年半到七年的大学学习,才能拿到工程师文凭,以开始其工程师的职业生涯。
[参考文献]
[1]Christoph Hubig…(Hrsg.). Nachdenken über Technik: die klassiker der Technik Philosophie [M]. Berlin: Sigma, 2000.
[2][德]马克思·舍勒.知识社会学问题(艾彦译)[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3.
[3][德]马克思·舍勒.舍勒选集(孙周兴选编)[C].上海:三联书店,1999.
[4]([德]斯宾格勒.人与技术(董兆孚译)[M].商务印书馆,1938).
[5]Ernst Cassirer. Symbol, Technik, Sprache:Aufs tze aus den Jahren 1927-1933 /herausgegeben von Ernst Wolfgang Orth und John Michael Krois, unter Mitwirkung von Josef M. Werle[C] .Hamburg :F. Meiner,1985.
[6]Friedrich Georg Juenger.Die Perfektion der Technik[M].Frankfurt am Main: Vittorio Klostermann,1993.
[7][德]海德格尔.演讲与论文集(孙周兴译)[C].北京:三联书店,2005.
[8][德]卡尔·雅斯贝斯.现时代的人(周晓亮 宋祖良译)[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
[9][德]卡尔·雅斯贝斯.卡尔·雅斯贝斯文集(朱更生译)[C].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2003.
[10]Friedrich Dessauer. Philosophie der Technik[M]. Bonn: Friedrich Cohen Verlag , 1927.
[11]Friedrich Dessauer. Streit um die Technik[M]. Frankfurt: Verlag Josef Knecht, 1956.
[12]Jacques Ellul.The Technological society[M].trans.John Wilkinson.NewYork:Alfred A.knopf,1964.
[13]乔瑞金.技术哲学教程[C].北京:科学出版社.2006.66-67.
[14]路易斯·芒福德.技术与文明(陈允明,王克仁,李华山译)[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9.
[15]Walter Brecht. IKIA. Darmstadt: Eduard Roether Verlag[C].1949.
[16]Hans Schwippert. Mensch und Technik. Darmstadt:Neue Darmstaedter Verlagsanstalt Gmbh, 1952.
[17]Otto Kraemer. Gedanken Zur Kasseler Tagung“Ueber die Verantwortung des Ingenieurs” . VDI-Zeitschrift[J]. Duesseldorf. Bd.92,Nr.31,1950,849.
[18]Otto Kraemer.Die Wandlung des Mensch durch die Technik. ZVDI[J].Bd.95,Heft 32. Bericht ueber die Tuebinger Tagung des VDI.
[19]Otto Kraemer. Der Mensch im Kraftfeld der Technik. VDI-Sondertagung in Muenster. Duesseldorf: VDI-Verlag. 1955.
[20][美]卡尔·米切姆. 技术哲学概论(殷登祥等译)[M]. 天津:天津科学出版社,1999.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