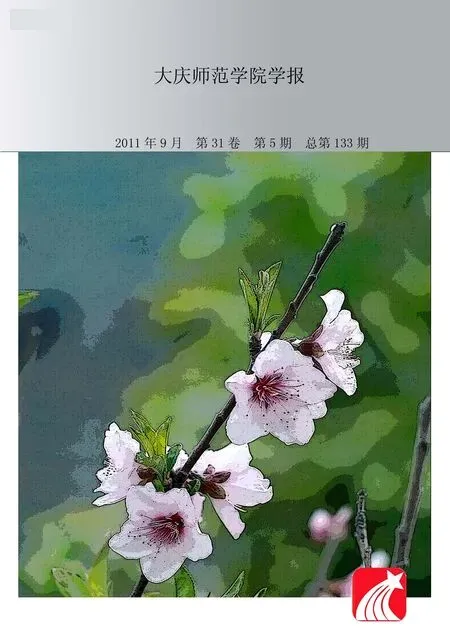论苏轼在密州的思想
乔云峰
(山东省诸城市超然台①管理处,山东 诸城 262200)
神宗熙宁七年(1074年)12月初苏轼来知密州,至熙宁九年(1076年)12月离任。[1]302、343在这两年零一个月的时间里,苏轼创作了诗歌126首,词18首,文59篇,共计203篇,这些作品体现出复杂的思想内容。游国恩先生在其《中国文学史》中说:“苏轼的思想比较复杂,儒家思想和佛老思想在他思想的各个方面往往是既矛盾又统一的。”本文拟对苏轼知密州时期的思想进行探讨。
一、超然思想
神宗熙宁八年(1075年)已是苏轼任密州太守的第二年,经过一年的努力,密州的社会状况大有好转,苏轼对城墙上北台进行了增葺,由他的弟弟苏辙取老子“虽有荣观,燕处超然”之意命名为“超然台”,苏轼亲自作《超然台记》。在《超然台记》中,苏轼正式提出“超然”思想,这是苏东坡思想走向成熟的标志。在《和潞公超然台次韵》中苏轼说过:“吟成超然诗,洗我蓬之心。”
王启鹏先生在《超然:苏东坡思想的精髓》[2]一文中对苏轼的超然思想进行了总结,他认为超然思想主要包括三部分内容:
一是游于物外,无往而不乐——东坡透彻的人生哲学思想。《超然台记》全文的核心是:“余之无往而不乐者,盖游于物之外也。”这是苏轼第一次较系统地提出的正确处理人与外物关系的哲学思想。这一哲学思想的确立,对苏东坡以后的人生道路起着很大的指导作用。这一哲学思想的提出,既是他在朝廷激烈党争中激流勇退的经验总结,又是他战胜以后人生道路上大大小小劫难的思想武器。纵观东坡一生思想的发展,“超然物外”是他的基本人生哲学思想。
二是凡物皆有可观,皆有可乐——东坡旷达的处世思想。“凡物皆有可观。苟有可观,皆有可乐,非必怪奇玮丽者也。”这一观点的核心是:要善于发现客观事物之美,并把自己的思想感情融注于这一富有美感的事物之中,忘却自己的得失和烦恼。这一观点,实际上就是苏东坡旷达处世思想的第一次形成,成为他在以后近三十年人生道路上战胜屡遭贬滴而带来的物质上和精神上的困顿和折磨的思想武器之一。苏轼就如同当年孔子曾称赞过的颜渊一样:“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论语·雍也》)
三是相与登览,放意肆志——东坡强调神似的超然艺术观。正如现代大诗人藏克家说的:“我们没有东坡的心胸眼界,看不到北边一百多里外的潍水,更想不到‘淮阴之功’;东向远视,群山云罩,不知道哪是卢敖居的‘卢山’所在;西望茫茫,哪儿是穆陵关?两千年前‘师尚父、齐恒公’的历史故事,我们同样也很茫然。”[3]828(《苏东坡的“超然台”》) 这实际上指出,苏东坡运用了艺术想象。
朱靖华先生在《旷世英才在密州》一文明确指出“超然”思想的本质是安遇顺性、不为物动。从苏轼登超然台凭吊历史人物陈迹的文字中可以看出,苏轼的“超然”是对现实中局促、龌龊一面的“超然”,他实是以一颗在形上层次中净化了的心灵返照现实。苏轼这种建立在力图摆脱政治挫折和尘俗羁绊,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并与民同乐的基础上的“超然”有着现实的积极意义,迅速地影响了他周围的一大批友人亲朋,形成了一种具有社会普遍意义的文化思潮与社会思潮。[3]411
二、民本思想
有人认为,苏轼到密州之时,是他的儒家淑世思想达到顶峰的时期。从他在赴密州途中写给其弟子由的《沁园春·赴密州早行,马上寄子由》词中可见一斑,其下阙云:“当时共客长安,似二陆初来俱少年。有笔头千字,胸中万卷,致君尧舜,此事何难?”来密州后作的“四十岂不知头颅,畏人不出何其愚!”(《送段屯田分得于字》)都表现出苏轼要一展治国雄心壮志与补天之才,争取在地方上做出一番事业的决心。苏轼在密州所作所为大都体现出明显的以爱民为中心的民本思想。
熙宁七年十二月初苏轼抵达密州。当时的密州旱蝗相继,自秋入冬,方圆数千里,久旱未雨,麦不入土,“民以蒿蔓裹蝗虫而瘗之道左,累累相望者二百余里,捕杀之数,闻之官者几三万斛”,灾情极为严重。面对密州严重的自然灾害,苏轼动员灾民踊跃捕蝗灭灾,大力倡导人们用“秉畀炎火”(火烧)、“荷锄散掘”(深埋)等多种办法消除蝗害。为激励百姓捕蝗抗灾,还用补贴粮米的办法来提高老百姓的积极性,取得了十分理想的效果。在号召百姓协力灭蝗的同时,苏轼率先垂范,多次与当时的密州通判赵瘐(赵成伯)亲自参加捕蝗抗灾,《和赵郎中捕蝗见寄次韵》一诗,就是这一情景的真实写照。由于苏轼的榜样作用,加之贴补粮米的激励措施,密州灾区到处出现了争先恐后、群策群力捕蝗灭灾的热潮。
苏轼来密州不久,在看到如此严重的灾情之后,立即连续给神宗和朝中重臣上了《论河北、京东盗贼状》、《上韩丞相论灾伤手实书》与《上文侍中论榷盐书》,请求朝廷派官员视察灾情,反对吕惠卿等人极力推行的“手实法”,减免盐税与赋税,并取得了较为理想的效果。面对因生活没有着落而出现的盗贼,苏轼镇压了罪大恶极者,对于其他盗贼则尽量招抚,而对于那些肆无忌惮,栽赃诬陷,戕害人命的衙役也进行的严厉的打击。同时,苏轼不但带头“洒泪循城拾弃孩”,还设法从官仓中拿出部分粮米专门用以收养弃儿。面对严重的旱灾,苏轼按照当地风俗赴城南常山祷雨。但他深知祭神求雨也不过是地方官的例行公事,只有兴修水利才是抗旱灭蝗的根本措施。因此,苏轼知密州时,曾在密州府治所在的诸城城南发动当地百姓筑长堤,以“壅邞淇水入城”,并计划在此修建大坝,既可蓄水以备天旱时灌溉农田,又可在连日淫雨之时阻挡“水至城下”。可惜,这一计划因苏轼调离密州而未能如愿。元丰八年(1085年)十月,苏轼再次来到密州,在诗篇《再过超然台赠太守霍翔》中对时任密州知州的霍翔提出建议:“愿公谈笑作石埭,坐使城郭生溪湾。”作为地方长官的苏轼如此重视兴修水利,体现了他对农业生产的关心和重视。刚来密州的苏轼在《后杞菊赋》记载了生活的贫困,其小序云:“余仕官十有九年,家日益贫。衣食之俸,殆不如昔者。及移守胶西(指密州),意且一饱,而斋厨素然,不堪其忧。日与通守刘君庭式循古城废圃,求杞菊食之,扪腹而笑。”在《超然台记》中也说:“而斋厨索然,日食杞菊。”作为太守,苏轼与民同忧共苦,过着清廉俭朴的生活,其中饱含着对老百姓的几多关心与爱护。
苏轼自幼所受到的报君恩、酬知遇的思想根深蒂固。入世以来,他深深感激仁宗对他的提拨和神宗在变法初期对他的信任,时时思报君恩于万一,以自己之所学,使民富国强。因此,即使在逆境中或者遭受打击,也未能真正归隐田园或者遁迹山林。在苏轼的密州作品中较多地流露出君恩难报的感慨,《和章七出守湖州》“只因未报君恩重,清梦时时到玉堂”等比比皆是。
三、黄老思想
面对严重的灾情,总揽军政大权的苏轼怎样治理密州才能给社会生产提供一个良好的恢复发展环境呢?他决意效仿先贤治理地方的经验,寻访遗贤故老,咨询治道。
而汉朝时密州正好有一位盖公,是继承“黄老学说”的集大成者,主张“贵清静而民自定”,以清静无为治国安民。当时曹参相齐九年间,就是依靠盖公的帮助与指导,以盖公的“黄老学说”理论为指导,约法省禁,与民休息,使混乱的社会秩序逐渐得以安定,使凋敝的经济慢慢得以恢复,农业人口也得到快速增长,齐国大治,曹参也被称为贤相。汉惠帝二年(公元前198年),汉丞相萧何病逝,曹参继任为丞相,他把治理齐国的经验带往京城,沿着萧何制定的规章制度,把盖公的“黄老学说”做为西汉初统治者制定政策的指导思想,推广至全国实行,给老百姓提供一个良好的发展环境而不挠民。这就是著名的“萧规曹随”。盖公的思想一直影响了惠帝以后的汉文帝刘恒、汉景帝刘启,连同他们的母亲窦太后、薄太后,他们都信奉盖公的黄老学说并以之治国,取得良好的政绩。
苏轼立足现实,决意效法盖公,借鉴道家学说,吸取历史经验,以达到医治社会创伤之目的。怀着对盖公的敬佩之情,苏轼派人查寻其墓及其后代而不得,慨然于怀,“思其为人,从未有如公者”,遂在州署中兴建盖公堂设位礼拜之,并特意作《盖公堂记》阐明自己反对扰民的政治主张。文章以寓言开篇,旨在以医药比喻治国之道。治身之道贵静而身自健,治国之道亦然,与民休息,清静无为而民自定。在《盖公堂记》中苏轼还称赞盖公:“夫曹参为汉宗臣,而盖公为之师,可谓盛矣。而史不记其所终,岂非古之至人得道而不死者欤?胶西东并海,南放于九仙,北属之牢山,其中多隐君子,可闻而不可见,可见而不可致,安知盖公不往来其间乎?吾何足以见之!”由此可见苏轼对盖公的思想德行的崇敬之情,以及采纳盖公的主张治理密州的决心。为此苏轼命画工摹写陆探微的名画挂在盖公堂中,苏轼亲自撰写了《盖公堂照壁画赞》和《盖公堂记》。
苏轼崇尚盖公“治道贵清静而民自定”的思想,主张为政应顺应自然,“必尽人事然后理足而无憾”(《墨妙亭记》)。从苏轼初来密州时看到的“斋厨索然,日食杞菊”,到后来的“处之期年,而貌加丰,发之白者,日已反黑”,说明他的政策奏效了。
四、爱国思想
由于北宋建国之初采取“守内虚外”的国防策略,导致边境空虚,北方少数民族政权辽、夏等屡屡进犯。宋真宗时辽进攻宋朝,竟然在获胜的情况之下与其鉴订了“澶渊之盟”,割地求和,纳币输银,成为罕见的耻辱。西夏也陆续侵占了今甘肃、陕西等大片土地,到了苏轼那个年代更是形成了战火连年的局面。与不少重臣的妥协苟安相反,苏轼一贯反对向辽和西夏妥协,力主抗击辽和西夏的侵扰,在密州的苏轼曾多次流露出报效国家的雄心壮志。
作为“知密州军州事”的最高军事首领,苏轼时刻不忘履行自己的职责,经常习射练兵,加强战备。他认为,若不利用“秋冬之隙致民田猎以讲武”,国家就会危在旦夕。所以,苏轼在密州时期每年都利用农闲之时,组织兵民与同僚会猎郊外,“习射放鹰”,以备随时领命奔赴边陲抗击来犯之敌。
熙宁八年(1075年)七月,辽主胁迫北宋王朝统治者“割地以畀辽”,“凡东西失地七百里”。苏轼闻讯,心情十分沉重。是年冬,苏轼满怀爱国激情,写下开抗敌爱国词先河的著名词作《江城子·密州出猎》。词集中表达了他本人渴望驰骋疆场、抗敌报国的爱国主义情怀。此时年届不惑的苏轼,渴望宋神宗像当年派遣冯唐“持节云中”重新起用魏尚那样,给自己一个捍卫国家、杀敌立功的机会。同时,苏轼还写了《祭常山回小猎》一诗,抒发其爱国情怀,诗的最后两句“圣朝若用西凉簿,白羽犹能效一挥”,表明他希望为国效力、收复失地的雄心大志。苏轼才华超群,却不为朝廷器重。在这种处境中,他仍用诗词反映他关心国家边防的心情和竭诚为国分忧的愿望,充分说明苏轼不愧是一位以国家安危为重、富有强烈的爱国报国精神的大诗人。
熙宁九年三月,四川因官府筑茂州城而与羌族人民发生了大规模的武装冲突,茂州将士死伤很多,新任成都知府冯当世采用招抚政策,顺利地平息了边乱。苏轼写下“西南自有长城”(《河满子·见说岷峨凄怆》)称颂之。这首北宋词史上最早反映边防民族战争的词篇,也流露出苏轼的爱国之情。
五、野性思想
苏轼的成长环境与所受教育决定其与生俱来的野性思想。八岁(按旧历)始受教于天庆观的道士张易简,所学内容,除传统的启蒙教育外,当有更多一些道教的内容。两年后苏轼回家就学,由母亲程氏执教,并未请私塾。程氏的教学更多的是讨论式、启发式,每读完一些文章后,母亲总要考问他古今成败的问题,小苏轼也常能脱口即出,出即能说到要害。苏家有“来风轩”作为读书之所,当时叫“南轩”,该亭院内草木茂盛,野生杂花遍地,甚有野趣。但苏家有不许杀生的禁令,一概不许捕取鸟雀,这成了孩子们心仪的地方,读书之余,苏轼与苏辙经常观察花丛中的小鸟,小鸟也与他们相安无事。这种极富野趣的生活环境对于他擅于反抗的野性人格精神的培养起到了不小的作用。后来初入仕途的苏轼曾写下这样的话:“春色已盛,但块然独处,无与为乐。所居厅前有小花园,课童种菜,亦少有佳趣。傍宜秋门,皆高槐古柳,一似山居,颇使野性也。”(《与杨济甫书》) 显示出对尔虞我诈的官场生活的厌恶。早在杭州,苏轼就写下了“我本麋鹿性,谅非伏辕姿”。知密州的第二年(1075年)三月,苏轼在《游卢山,次韵章传道》一诗说自己: “尘容已似服辕驹,野性犹同纵壑鱼。” 第一次响亮地喊出“野性”的口号,明确地提出了“野性”思想。朱靖华先生在《旷世英才在密州》一文中指出,野性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本质的难以驯服的向往自由的生性,一是热爱自然、乐居山川田野的习好。苏轼这种野性思想的形成和渐渐成熟与密州的自然、人文环境密切相关。[3]404苏轼自述来密州是“去雕墙之美,而庇采椽之居,背湖山之观,而行桑麻之野”,而自己又是“乐其风俗之淳”,这就难免会激发其与生俱来的野性了。野性思想的形成与成熟还与苏轼深入学佛习道相关。苏轼曾与其弟子由说:“凭君借取《法界观》,一洗人间万事非。”(《和子由四首·送春》)
知密州时期的苏轼经历了与变法派的矛盾而自请外任杭州等人生变动,入不惑之年的他对“野性”也有了更加理性的思考,把它与“尘容”对立起来进行观照,虽然表面上自己是一个“平生所惭今不耻”的俗吏,但苏轼还是一条时时要“纵壑”的鱼,在《刘贡父见余歌词数首,以诗见戏,聊次其韵》他就曾说:“门前恶语谁传去,醉后狂歌自不知。刺舌君今犹未戒,炙眉吾亦更何辞。”苏轼的这种野性思想对他在密州时期形成的“超然思想”和他以后的生活与人生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六、归隐思想
苏轼在密州也流露出较多的归隐思想。在密州创作的二百多首(篇)作品中,有35首作品36处使用“归”字,其中4处没有体现出明显的归隐思想,另有13处虽没有使用“归”字,但明显地体现出归隐思想。其中苏轼在密州创作的18首词中,有5首6次使用“归”字,还有1首《满江红·正月十三日雪中送文安国还朝》虽没有出现“归”字,但也体现了明确的归隐思想。
研读苏轼的密州诗词,我们不难看出,他此时所说的归隐,大体上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由思乡积虑而形成的买田归隐,一是远离现实的隐逸或者功成归隐。
为什么苏轼密州诗词中体现出明显的归隐思想呢?
首先是苏轼三教合一的思性决定了其作品归隐思想的存在。苏轼自古被评价为“三教统一”的代表文人。苏轼来到密州之后,由于深深地了解了新法推行不当给老百姓带来的危害,道家“治道贵清静而民自定”的思想成为他的理政指导思想。他寻找汉初道家思想的代表人物辅助曹参治理天下的密州人士盖公的后代而不得,于是建盖公堂,并作《盖公堂记》。作为道家思想的核心内容之一的“道法自然”的观点必然会对苏轼产生影响,从而在其密州诗词中出现了较多的归隐或者隐逸思想。
其次是密州地方文化的影响。以诸城为主的密州文化是正统的儒家文化。在经历了三国两晋南北朝至隋唐的沉寂与积淀之后,到宋代,密州儒学为主的文化再次复苏。儒家所积极倡导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处世原则也已经深入学者们心中。在密州的苏轼没有兼济天下的机会,那么只好在做好本职工作即治理好密州的同时而独善其身,向故乡、自然或者自己理想中的归隐之地寻找心灵的安慰了。再次是前面所论述的苏轼渐渐成熟的野性思想的影响。
正如李泽厚指出的那样,苏轼的典型意义在于他是地主士大夫兼济与独善矛盾心情最早的鲜明人格的化身,他把这种在中晚唐开始出现的进取与隐退的矛盾双重心理发展到了一个新的质变点。[4]261苏轼归隐思想的文化意义正在于此。
通过以上论述可知,知密州时期的苏轼已经对社会、人生、政治、文学等多方面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形成了一定的思想,并体现于其文学创作中。这一时期是影响苏轼一生的许多思想的初步形成期,是苏轼思想形成的重要阶段。
[参考文献]
[1]孔凡礼.苏轼年谱[M].北京:中华书局,1998.
[2]王启鹏.超然:苏东坡思想的精髓[J].惠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3):74-77.
[3]李增坡,邹金祥.苏轼在密州[M].杭州:西泠印社出版社,2007.
[4]李厚泽.美的历程[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1.
——评《苏轼密州诗文编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