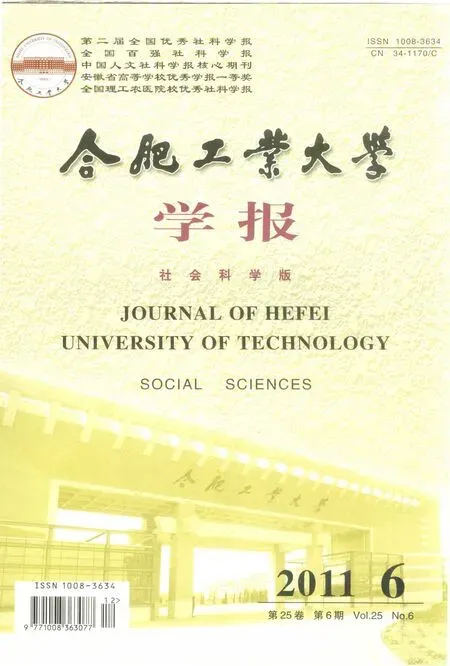西亚北非变局的反思
刘小勤
(昆明医学院社会科学部,昆明 650500)
西亚北非变局的反思
刘小勤
(昆明医学院社会科学部,昆明 650500)
引发西亚北非等国的政治动荡并不是偶然的突发性事件,也不是一些学者在早期所断言的“内生性事件”,究其原因,有西亚北非国家自身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矛盾的集中凸显,也有美国等西方国家推行改造中东、推行网络外交的外部诱因,是一场内外因素相互交织、综合作用下的社会全面动荡。西亚北非变局对于包括我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具有深刻的启示。
西亚北非;变局;反思
2010年底至2011年初,素有“石油心脏”之称的西亚北非地区进入到一个空前动荡、分化的历史时期,持续发生的政治动荡一时间使得国际原油市场价格急剧飙升,世界经济复苏进程放缓,由此引发了政治地震的连锁反应,不仅对中东政治板块产生冲击,也导致世界动荡不安。
一、西亚北非国家动荡乱象
西亚北非国家的动荡风潮始于有着“沙漠玫瑰”之称的突尼斯。在2010年底,一个26岁的青年人在自主经营的果蔬摊点遭遇城管警察的暴力执法后,选择以自焚方式以示抗议,继而引发国内各地持续28天的政治抗议示威活动,最终导致强势总统本·阿里结束其23年统治。
这场政治动荡迅速波及突尼斯的邻国埃及,在历经18天的持续抗议声浪后,埃及执掌政权近30年、被称为“非洲巨人”的穆巴拉克黯然下台。一代中东巨人穆巴拉克曾被真诚拥戴、支持他的民众誉为民族英雄,他也确曾为埃及政治、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倾尽心力,却以如此方式宣告其政治生命的结束。埃及在中东国家素有领头羊之称,其动荡风潮迅速扩散并蔓延到周边国家,巴林、也门、叙利亚、利比亚、伊拉克等国发生持续动荡。
一些西方媒体把西亚北非国家接连发生的政治地震称为“阿拉伯之春”,更多的英美媒体则称之为“社交网络革命”、“Facebook革命”、“Twitter革命”。随着信息网络技术的迅猛发展,网络对人类现代社会生活的渗透、影响不断扩大,从一定意义上来说,信息化、网络化时代的到来,不仅对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交流方式、思维方式产生影响,而且对人类社会政治生活产生影响,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关注。
尽管包括一些西亚北非国家在内并不认同“Facebook革命”、“Twitter革命”等称谓,但近年来西亚北非地区网民迅速激增,移动互联网、3G手机用户和智能手机用户不断上升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华盛顿邮报》援引一份阿拉伯社会化媒体报告称,在中东大约有2 100万人使用Facebook,仅在埃及就有500万人[1]。北非小国1 100万突尼斯人中就有200万Facebook用户。不容否认的是,现代社交网络媒体在这场政治地震中凸显了巨大的威力。
2008年以来,突尼斯、埃及等国就爆发过由网络引发的多起大规模群体性事件。2011年1月25日,埃及青年威尔·古尼姆通过Facebook在其创建的“我们都是萨伊德”(阿拉伯语意为“烈士”)网页上呼吁人们用和平方式表达对政府的不满,这个网页很快成为游行示威活动的中央指挥部。威尔·古尼姆成为革命英雄,他曾经低调地表示“事实上,我做的事情很简单,只是敲击了几下键盘”,并把胜利归功于Facebook:“这场革命是从互联网、从Facebook开始的。我们在Facebook上发布一则视频,几个小时之内就会有6万人分享”[1]。
但就是这样看似简单的点击鼠标、敲击键盘的动作从根本上突破了耗费大量人力、财力、物力、时间、精力的传统政治动员模式,几个小时就能引起网民的高度关注,在短短几天召集数万人走上街头,迸发出惊人的政治能量。社交网络似乎成了撬动一些西亚北非国家长期执政的政治根基的动因,但绝非唯一的动因。
二、西亚北非各国动荡的内因解析
在笔者看来,引发西亚北非等国的政治动荡并不是偶然的突发性事件,也不是一些学者在早期所断言的“内生性事件”,而是内外因素相互交织、综合作用下的社会全面振荡,我们必须对西亚北非国家自身政治、经济、社会发展诸多方面进行全方位反思。
第一,传统政治制度构建中宗教因素凸显,加上植入式民主制度的缺失构成西亚北非政治制度。
作为伊斯兰教的发源地,中东北非地区是世界穆斯林最为集中的地区,伊斯兰文明在社会各阶层有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大多西亚北非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摆脱英、法等国的殖民统治而获得民族独立,在政治制度设计方面,尽管政治体制表现形式不尽相同,但都具有伊斯兰教鲜明而深刻的政治烙印。中东各国普遍盛行权威体制,家族制、世袭制为主要的政治制度,一些国家徒具民主议会、民选总统、权力制约等民主制度的形式,但是民主文化、公民的民主素养均与现代民主有相当距离。
比如突尼斯在前总统本·阿里执政期间拥有积极、稳定的国际形象,但事实上他是通过历次宪政修订,维系了23年实质性的独裁统治。突尼斯政府与人民之间达成一个默契:民众以牺牲政治、社会权利为代价,以表面的平静和顺从换取基本生存条件,即所谓的“面包契约”。埃及前总统穆巴拉克在国内为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通过宪政制度修订刻意提高总统候选人条件,从而使得历次总统大选既谈不上竞争,也没有任何悬念。穆巴拉克在位近30年,历经5次总统选举,声势浩大的总统选举只不过是为其统治披上一件合法外衣而已,始终是穆巴拉克“一个人的游戏”;在选任副总统问题上,穆巴拉克违背埃及政治传统,迟迟不任命副总统,刻意扶植二儿子贾迈勒·穆巴拉克的政治影响力,试图沿袭中东国家世袭制、家族式统治的模式,激起国民的强烈不满。
第二,在一些西亚北非国家,政治体制陈腐僵化,领导人长期执政,耽于享乐,任人唯亲、裙带关系现象严重,官员贪腐行为严重,长期忽视民众民主诉求,缺乏改革动因。
早在二千多年前,亚里士多德就在《政治学》中明确指出:“凡当权的人行为傲慢又贪婪自肥,公民一定议论纷纭,众口喧腾,不仅会指摘这些不称职的人,而且也批评授权给这些人的政体”[2]。无论本·阿里家族还是埃及总统穆巴拉克家族均涉嫌掠夺惊人的巨额财富。维基解密网爆出的突尼斯总统女婿宴请美国驻突尼斯大使戈代克的奢腐细节,以及穆巴拉克家人的奢华生活一经披露都激发起民众的强烈的心理失衡和不满。
穆巴拉克在其近30年的执政期间一以贯之地实施《国家紧急状态法》,最初实施的初衷是为了打击伊斯兰极端宗教势力的渗透、影响,后来却逐渐发展成为打击政治异己、强化专制统治、剥夺公民权利的利器。在高压的社会氛围中,民众政治参与渠道受限,民主诉求难以引起当局重视,表面维系的稳定是以牺牲民众的政治参与为代价,这是一种“僵尸式”、“木乃伊式”的稳定。但这种长期被掩盖的社会矛盾一旦在特殊情境下找到宣泄渠道,就会裂变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催化剂,爆发出的政治能量不可小觑。
第三,中东地区民主化进程也受制于经济发展水平,除海湾地区少数国家外,大多经济水平低下,产业结构单一、畸形,农业萎缩,经济发展停滞,失业率居高不下,社会矛盾突出。
尽管突尼斯自2007年被世界达沃斯经济论坛连续评为非洲最具有经济竞争力的国家,但人均GDP 4 000美元对很多普通民众来说不啻为遥远的虚拟数字财富。“一个社会的稳定与否并不取决于经济发展的增长速度和社会财富总量增加的状况,而是最终取决于社会底层群体的风险承受能力和生活改善状况。”[3]据突尼斯官方统计,突尼斯失业率高达14%,青年群体失业率更是高达52%。在抗议示威活动中人们高呼的政治口号从“要面包,要工作”转而“要面包,不要本·阿里”的变化中可以感受到人们已经从基础生活条件的满足转而发展为明确的政治诉求。由于社会分配不公,贫富悬殊、社会各阶层矛盾突出,笼罩在“稳定”表象下的社会危机四伏。而由于社会贫富悬殊巨大,阶层隔膜严重,普通民众长期生活在高通胀、高物价、高失业率带来的巨大的阴影之下。埃及20%的富裕阶层和中间阶层掌着社会财富的82%,而80%的低收入阶层、贫困阶层仅拥有社会财富的18%。由于阶层分化严重,阶层固化趋势明显,贫富悬殊巨大,民众的生活形成强烈反差,而严格的社会管控使得社会矛盾被掩盖,甚至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保持社会的平稳运行。但是,当民众的政治、经济、社会利益难以得到保障,民愤、民怨得不到宣泄,当矛盾和压力不断积累、尖锐、激化时,随着民众政治参与意识逐渐增强,民众对政府提出的一些要求无法在现有的政治体系之内得到满足、难以走出困境时,他们就会铤而走险,必然转向非制度化的渠道,采取“街头革命”、“广场风暴”等等方式与政府对抗,造成政治局势不稳定,最终酿成大规模的社会动乱。
三、西亚北非各国动荡的外因解析
第一,在经济全球化的影响下,一些国家原有经济结构的弊端进一步暴露,政府应对乏力,难以扭转发展颓势,经济危机演化为社会危机。
全球化带给世界的影响具有双重意义,“一方面,它能扩展繁荣与稳定;另一方面,它也将贫困和动荡传播到全世界。对于应对和影响外部环境能力较强的发达国家,全球化提供了谋取利益最大化的有利条件……而对于欠发达甚至比较落后的国家,全球化既是借以实现经济繁荣的机会,更是遭受灾害、危机和导致多种矛盾激化的根源。”[4]
在全球化浪潮中任何一个国家都难以逃避世界经济浪潮的冲击。金融危机使欧洲、美国等国遭到激烈冲击,但由于其经济基础雄厚,在全球化浪潮中牢牢掌控着世界经济的主导权,善于利用世界经济博弈政策,转嫁危机、化解风险的能力较强,逐渐走上经济复苏之路。但是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全球化常被视为一种冷酷无情的力量,它极大地破坏了普遍百姓和无力自卫的社群的生活。”[5]在金融风暴冲击下,西亚北非国家边缘化迹象更为明显,经济结构单一、畸形,政府应对危机、扭转经济颓势的能力不足,加上社会管理形态相对封闭,容易受到世界经济的强烈冲击。如突尼斯出口创汇的旅游、鲜花出口、磷酸盐等支柱型产业在2009年发生的金融危机中就曾遭受重创;埃及国家经济结构中农业基础薄弱,工业缺乏大规模生产、制造业的产业支撑,同样基础薄弱,单纯依靠旅游业、侨汇、运河管理、石油产业为主要经济增长点,以至财政赤字、贸易赤字严重。在金融风暴的影响下,埃及、突尼斯旅游业成为重灾区,侨民收入锐减、民生凋敝,难以走出经济困境,经济危机逐渐演化为社会危机。
第二,在世界政治民主化浪潮的冲击下,公民的政治参与热情被大大激发,一些国家社会发展和制度管理滞后,民主意识的增强往往导致社会民主化过程中自由化倾向突出,政府控制乏力。
民主化通常是指政治变革的一系列过程,具体表现为权威政体向民主政体的演进,从而达到公民参与政治,并对政权进行有效监督与控制的目的[6]139。在西亚北非国家,国家政治体制僵化,自上而下的改革动力不足,已经阻碍了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发展、进步。“中东北非国家的民主模式存在很大的局限性,表现为一方面赋予人民有限的参政权,而另一方面固守伊斯兰教法,强调当权者的统治和臣民对当权者的绝对服从。两者之间的深刻矛盾导致伊斯兰国家民主化进程举步维艰”[7]。
由于中东国家在制约政治发展的关键因素——政权产生方式上并没有实质性突破,因此中东地区共和制国家普遍存在最高统治者独揽大权现象,它与现代政治民主化是根本对立的。无论是独裁统治、强人政治还是老人政治,主宰政坛的当局都面临着空前严峻的挑战。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网络为公众提供了政治参与的平台,大大地激发了民众政治参与的热情,民众的公民意识和权利意识明显加强,人们对政治制度的弊端普遍不满甚至质疑,继而将这种不满和质疑指向了国家的最高统治者。“现代政治民主化的发展,以及技术推动下网络等新媒体的出现,导致网络民主的新闻表达已经超越了现实民主的实际发展。”[8]
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曾用“政治参与/政治制度=政治动乱”的公式试图说明当政治制度化滞后于民众的政治参与热情时,必然导致大规模的政治动荡。由于社会发展和制度管理滞后,而民主意识的增强往往导致社会民主化过程中自由化倾向突出,社会危机发展为政治危机。
第三,美国实施大中东改造计划的政治遗产的负面影响,以及在此次北非中东变局中美国的动荡摇摆,引发了众多西亚北非国家的不安和疑虑。
“9.11事件”以后,美国认为要从根本上改善美国的国际安全环境,消除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和恐怖主义产生的土壤,避免以后针对美国的恐怖主义事件的发生,就必须在西亚北非各国建立自由、开放、民主的政治制度。以“民主卫士”自居的美国,面对当下中东一些国家接踵而至的“民主化运动”,在高调支持民众的民主诉求的同时采取多重标准,即针对不同国家做出完全不同的外交反应。符合其利益需求的便贴上民主的标签,而不符合美国战略利益需求的,要么视而不见,要么百般指责。美国智库卡托研究所防务和外交政策副主席泰德·卡彭特说,“美国自二战以来的政策一直是:如果在一个民主、但敌视美国的政府和一个专制、但亲美的政府间进行选择,美国将选择后者。”[9]在此次中东北非国家中最鲜活的例子是,美国对伊朗、利比亚等国民众希望尽快通过“民主”改变颜色乐见其成,对于巴林这样的国家由于美军军事基地的存在关乎其反恐大计,美国则采取“有序引导”的策略,竭力避免出现政权更迭进而危及美国自身利益的情状。
无论美国对中东国家的民主政治进行选择性“引导”、“干预”或“淡忘”,还是采取双边下注的方式,在对传统的“专制主义”盟友显示“力挺”的姿态的同时又与反对派势力接洽。美国对待传统盟友的摇摆动荡一方面不仅大大降低了美国在中东北非国家维护秩序的威信,使一些传统盟友不得不重新审视美国的政治信誉,以致以色列有媒体发出“以色列是否在埃及之后成为美国下一个抛弃的盟友”的担忧;另一方面,一些亲美、亲西方的国家在未来的外交决策方面必然面临更大的政治压力,从政府到民间对美国的疏离倾向越加明显。
美国竭力在中东北非国家鼓吹、输入西方民治制度模式,并没有使中东国家实现真正的民主,给这些国家带来和平与稳定,相反却使这些国家陷入更进一步的动荡中。在抢占全球战略的道德制高点的同时又难以掩饰其为自身战略利益服务的利己主义、实用主义本性,这一点连美国自身都难以回避,他们承认其“战略的目标是理想主义的,手段是现实主义的”[6]144。美国在应对中东乱局时表现出摇摆不定的多变面孔,就其根源来说,就是要在乱局中努力掌握主动,以进一步分解反美力量,扶植亲美势力,力求巩固和扩展美国在中东地区的既得利益。
第四,美国等西方国家借助网络媒体开展网络外交,鼓吹所谓网络民主,加强对中东地区意识形态、民主价值观的渗透和输入,是诱发西亚北非国家持续动荡的重要外部因素。
N.尼葛洛庞帝曾经断言:“每一种技术或科学的馈赠都有其黑暗面”[10]。网络是人们通过数字化方式构建的虚拟空间,由于网络环境、网络行为主体的虚拟性,每一个人都能成为信息的制造者、发布者、传播者,而对一些敏感事件,网络媒体因具有聚集效应、放大效应、扩散效应的特征,而容易成为覆盖面广、传播速度快、低成本的免费“政治动员工具”,为民众提供了政治参与的可能性与现实性。近年来,美国利用互联网自由为其外交政策和战略利益服务,利用网络空间的技术优势,把网络作为推广西方民主价值观念、意识形态的新手段。目前美国主宰了互联网相关产业链的所有环节,从芯片到操作系统,从根服务器到域名管理,并借助英语语言优势掌控话语权为宣扬其意识形态服务。网络已经成为一个事实上的“政治动物”,西方信息大国通过其政治、文化资源的垄断优势,实施有意识的价值强制和规范设定,信息传递速度的加快和网络承载量的急速发展形成的工具理性改造着中东北非国家的传统政治文化基础,因此这种改造和冲击具有全面性、渗透性、长期性、隐蔽性的特点,能够在潜移默化中使社会的基础价值体系逐渐发生倾斜和扭曲,这是一个值得高度关注的问题。
2011年2月15日,希拉里在华盛顿大学演讲时宣布“美国将采取外交与技术手段互相配合的方式推进互联网自由”,加强对互联网社交网络的利用,并公开声称“利用新媒体发挥美国‘巧实力’并扩大交流,对实现美国外交政策目标至关重要。”[11]在西亚北非等国发生持续动荡的风潮中,针对一些国家和政府相继采取封网、断网等措施,美国采取一系列政治施压的手段,声称对一些互联网服务提供商受政府指使攻击美国互联网的用户事件深表关切;同时利用自身在网络技术方面的垄断性优势,公开提供各种技术支持,协助当事国网民突破网络封堵,例如美国政府资助开发的洋葱路器技术迅速更新、帮助网民登录被禁网站等行动。为实现在中东北非国家动乱中取利,美国“网络外交”已不再甘心居于幕后而是直接跳到前台,直接为反政府势力提供直接的技术支持。
四、西亚北非变局的反思
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改革、发展、稳定是在实现社会发展进程中必须面对的课题。西亚北非国家发生的政治动荡,为发展中国家如何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提供了一个悲剧性的负面教材。
第一,必须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之间的关系。对于中国来说,稳定是整个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和保证。我国几代领导人对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关系都高度重视,均有重要论述。邓小平关于“稳定压倒一切”的论述对我们今天“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创造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江泽民同志强调,改革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必然要求进行利益调整、体制转换和观念更新。因此,要始终正确把握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并强调这是现代化建设的一项重要领导艺术。胡锦涛总书记则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强调将促进改革发展同维护社会稳定有机结合起来,“必须把维护社会稳定和治安稳定、保护人民的合法权益作为重要任务。”[12]树立和落实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坚持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承受的程度统一起来,在社会稳定中推进改革发展,通过改革发展促进社会稳定。
近年来,中国持续的经济增长为社会的稳定提供了基础性条件;党和政府对民生问题的关注力度明显增加,社会自由度、包容度进一步提高,逐步关注与异质思维的有效沟通和对“沉默的声音”的倾听,在社会管理方面趋于成熟、自信;在社会心理层面人心思安,维护稳定大局成为人们的普遍共识。
第二,在全球信息化的挑战浪潮中,必须高度重视网络政治参与的特殊性与互联网监管问题。马克思曾经指出:“国家制度无论如何只是人民存在的环节。”[13]国家在政治生活中的职责就是保障和实现公民的权利。网络平台一方面赋予了民众进行政治参与的权利,另一方面对网民政治参与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必须冷静客观地看待汹涌袭来的网络信息,进行必要的信息筛选、甄别,保持一定的政治敏感度和政治辨别力。必须看到,网络世界是一个虚拟空间,但虚拟空间折射出西亚北非各国政治、经济、社会生活发展过程中的诸多现实问题;网络空间没有国界的划分,但是在这个虚拟空间中却清晰地演示着当代国际社会政治斗争的复杂性、尖锐性和残酷性;网络技术是中性的,我们应该坚持对互联网采取有效监管与妥善疏导相结合的方针,一方面网络为民众政治、经济、社会的利益诉求提供合理渠道,为社会稳定提供必要的“安全减压阀”,缓和社会矛盾;另一方面,建立和完善网络监测的社会预警机制,最大限度地化解互联网的负面效应,趋利避害,以真正保障国家的安全与稳定。
[1]江 玮:从Facebook到解放广场[N].(2011-02-26)[2011-09-20].http://www.21cbh.com.
[2]亚里士多德:政治学[M].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232.
[3]钱 进,王友春.公共安全危机策论[M].南京: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19.
[4]高祖贵.美国与伊斯兰世界[M].北京:时事出版社,2005.
[5]杨立英,曾胜聪.全球化、网络化境遇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60.
[6]唐宝才.伊拉克战争后动荡的中东[M].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7.
[7]唐宝才.伊斯兰世界的今天和明天[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45.
[8]叶 皓.政府新闻学——政府应对媒体的新学问.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
[9]新华网.中东动荡暴露西方两面派手法[EB/OL].(2011-02-28)[2011-09-01].http://news.sina.com.cn/n/2011-02-28/110822026862.shtml.
[10](美)N.尼葛洛庞帝.数字化生存[M].胡 冰,范海燕,译.海口:海南出版社,1996:26.
[11]美国国务院国际信息局.国务部长希拉里·克林顿以“互联网的是与非:网络世界的选择与挑战”为题发表讲话[EB/OL].(2011-02-15)[2010-09-01].http://chinese.usembassy-china.org.cn/021511remarks.html.
[12]孙承斌,邹声文.胡锦涛在新疆干部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N].光明日报,2009-08-06(1).
[13]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281.
Reflections on the Upheaval of West Asia and North Africa
LIU Xiao-qin
(Department of Social Sciences,Kunming Medical University,Kunming 650500,China)
Political unrests triggered in the countries in West Asia and North Africa are neither unexpected events,nor“endogenous events”declared by some scholars in an early period.It results from the conflicts in the political,economic,and social development of the countries in West Asia and north Africa,and the outside inducement of the Middle East reforming policy and the network diplomacy propelled by The United States and other western countries.It is an all-round social oscillation intertwined with internal and external factors.Reflections on West Asia and North Africa upheavals have deep enlightenments on the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the developing countries,including our country.
West Asia and North Africa;upheaval;reflections
D643
A
1008-3634(2011)06-0107-06
2011-09-08
云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基金项目(2009教Y070)
刘小勤(1970-),女,重庆开县人,副教授,硕士。
(责任编辑 蒋涛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