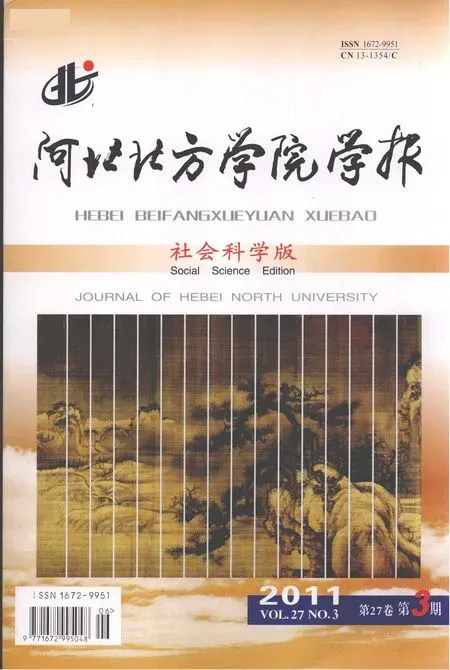《诗源辩体》中的唐代七律诗论
秦军委
(郑州轻工业学院易斯顿美术学院,河南郑州450008)
有关七律在唐代发展演变的整体情况,是明代唐诗学关注的热点之一。大部分明代诗论家标举“近体学唐诗”的主张,并由此(怎样学)为出发点开展唐诗研究。就七言律诗而言,大抵只有盛唐、中唐属于他们讨论的范围,其所标举的唐诗“七律正典”也仅限于盛唐名家的作品。但他们在唐诗论上却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就。对于盛唐“正典”名作,明代诗论家们做了较深入的研读。比如他们将盛唐七律与中晚唐时期七律进行了对照、比较,并关注其间七律的发展变异。“正、变”比较的工作以及建立在此基础上的对唐代七律史的构建工作,则是在明代后期诗论家许学夷手里才得以最终完成。
一、许学夷之前诗论家零星的唐代七律史论
律诗包括五律、七律。其中,七律是中国古典诗歌中最晚成熟的一种诗歌体裁(唐朝武后年间),然而却是最受唐代诗人欢迎的体式。关于唐代不同时期各体诗的数量,施子愉先生曾就《全唐诗》中存诗一卷以上诗人诗作进行统计,就唐代的七言律诗而言,初唐有 72首,盛唐有300首,中唐有 1 848首,晚唐有3 683首(资料援引自《东方杂志》第四十卷第八号)。在唐初盛中晚个时期中,盛唐七律作品比重虽然不多,但是却代表了唐诗的最高成就。其之所以被看重,主要原因是七律这一诗歌体裁表现范围极广,几乎各种题材都可以用七律来表现。正如王世懋在《艺圃撷余》中所说:
盖至于今(唐),饯送投赠之作,七言四韵,援引故事,丽以姓名,象以品地,而拘攀极矣,岂所谓之极变乎?[1](P21)
创作者关注七律,诗歌批评家亦是如此。而这与历代唐诗选本有一定的关系。明代之前,宋元时期流行的诗歌选本,如周弼的《三体唐诗》、元好问的《唐诗鼓吹》等,七律都占了很大的比重。
明代唐诗选本也是如此。明代最著名的唐诗选本是高棅的《唐诗品汇》。可以说,高棅的《唐诗品汇》是明人对唐诗态度的一个缩影。在90余卷的《唐诗品汇》一书中,所收七言近体诗近20卷,其中七绝10卷,七言排律及七律10余卷,收入的传统七律作家共163人,诗527首(数据来源于《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八十九·集部四十二·总集类四》)。
元代以后的诗学思想大致是沿着《沧浪诗话》开创的道路而发展演变的。明代人对唐代七律在不同时期之变化的关注与研究也可以溯源到严羽《沧浪诗话》那里去。严羽说:
盛唐人诗亦有一二滥觞晚唐者,晚唐人诗亦有一二可入盛唐者(严羽那时并无四唐之分,他所谓的晚唐即是明人眼中的中晚唐)[2](P143)。
这段话虽然简单,但其眼光却是发展的、辩证的。严羽并没有把唐代各时期的诗歌割裂开来,也没有相互比较其成就的高低,而是探讨它们之间的联系。作为明代唐诗学的奠基人,高棅也有类似的话。高棅对唐代七言律诗的发展演变过程有其系统的概括。他在《叙目》中将七律按时代顺序和成就大小分为9卷,按时代顺序将七律分为正始、正宗、接武、余响四部分,正好对应唐代初盛中晚4个时期。
高棅唐诗论中最值得注意的一点是他以盛唐为正宗,以盛唐为“正声”的诗学标准。这一标准被其之后的诗论家赞同并严格遵守。
对于七律在唐代的演变,杨慎大致只做了一个简单的概括(杨慎对六朝诗的兴趣远大于他对唐诗的兴趣)。他说:
七言律自初唐至开元,名家如太白、浩然、韦、储诸集中,不过数首,唯少陵独多至二百首。[3]P855
杨慎谈唐代七律,只论初、盛唐而不提中、晚唐,这一点与高棅的崇“盛”倾向一脉相承,也代表了大多数明代人的观点。
王世贞根据七律发展源流的一些现象,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说:
六朝之末,衰飒甚矣。然其偶俪颇切,音响稍谐,一变而雄,遂为唐始,再加整栗,便成沈宋。人知沈宋律家正宗,不知其权舆于三谢,橐钥于陈隋也。诗至大历,高、岑、李、王之徒,号为已盛,然才情所发,偶与境会,了不自知其堕者。[4](P1107)
王世贞认为,六朝诗气象衰飒,但声律优美,初盛唐诗正是在此基础上发展而来,大历以后,诗人气象、风骨渐弱,诗歌又具备了不同的面貌。他的解释方法其实背后有一个假设,即六朝诗与唐代的沈宋诗、盛中唐诗等同属于一个大系统。也就是说,历代诗歌源于同一源流,但又各具特色。它们的关系是,前者“变”成了后者,同时变动的前后又生成了促使变动的因素。
在此基础上,王世贞更是提出一套自己的解释诗歌演变的原则。他说:
衰中有盛,盛中有衰,各含机藏隙。盛者得衰而变之,功在创始;衰者自盛而沿之,弊繇趋下……胜国之败材,乃兴邦之隆干;熙朝之佚事,即衰世之危端。此虽人力,自是天地间阴阳剥复之妙。[4](P1107)
可见,王世贞已有了发展的眼光。王世贞的弟弟王世懋在《艺圃撷余》中的一段话,可以作为对王世贞此论的进一步补充。
唐律由初而盛,由盛而中,由中而晚,时代声调,故自不必可同。然亦有初而逗盛,盛而逗中,中而逗晚者。何则?逗者,变之渐也,非逗,故无由变。如诗之有“变风”“变雅”,便是《离骚》远祖 ,子美七言律之有拗体,其犹“变风”“变雅”乎?唐律之由盛而中,极是盛衰之介。然王维、钱起,实相酬唱,子美全集,半是大历以后,其间逗漏,实有可言……学者固当严于格调,然必谓盛唐人无一语落中,中唐人无一语入盛,则亦固哉其言诗矣。[1](P776)
王世贞、王世懋不仅看到唐人七律某些时期杂有与另外一些时期相类的现象,更是从整体发展的角度去解释了这些现象,可算是较具系统性的观念,但还略嫌浑沦肤廓。
后期复古诗论家胡应麟、胡震亨等人和许学夷继承了明代前、中期诗论求广博的特点,并进一步发展到了求全备的阶段。同时,因为有前人的评论作为基础,他们对唐代七律的研究就更加深刻细密了。
在明代前中期诗论家高棅、杨慎、王世贞、王世懋等人的著作中,已经有了初盛中晚“四唐”的唐诗分期观念,但在他们的正式讨论文字中,却没有对唐代七律在初盛中晚4个时期的整体发展过程做全面的论述。到了胡应麟这里,终于出现了对四唐诗歌的完整讨论:
唐七言律自杜审言、沈佺期首创工密,至崔颢、李白时出古意,一变也。高、岑、王、李,风格大备,又一变也。杜陵雄深浩荡,超乎纵横,又一变也。钱刘稍为流畅,降而中唐,又一变也。大历十才子,中唐体备,又一变也。张籍、王建略去葩藻,求取情实,渐入晚唐,又一变也。李商隐、杜牧之填色故实,皮日休、陆龟蒙驰鹜新奇,又一变也。许浑、刘沧角猎排偶,时做拗体,又一变也。至吴融、韩偓香奁脂粉,杜荀鹤、李山甫委巷丛谈,否道斯极,唐亦以亡矣。[5](P84)
这段引文可以说是当时对唐代七律演变最为系统的论述,不但在宋元时期从未出现这类完整且具历史眼光的讨论,而且在明代的胡应麟之前,类似论述也仅散见于高棅的《唐诗品汇》中七律的《序目》各条中(若将《序目》中的各条合并而观,大概会有与胡应麟的论述有相近的观点)。批评史上说高棅的《唐诗品汇》有着极具诗史规模的架构,但它的影响力在明代中期以后才渐渐显现出来,这一点是批评家的共同意见。而胡应麟的《诗薮》正是这一共同意见的绝佳例证。在这一段对唐代七律演变系统描述之下,紧接着还有3条补充的论述:
初唐律体之妙者:杜审言《大酺》,沈云卿《古意》、《兴庆池》、《南庄》,李峤《太平山亭》,苏颋《夜宴安乐公主新宅》、《望春台》、《紫薇省》,皆高华秀赡,第起节多不甚合耳。
盛唐王、李、杜外,崔颢《华阴》,李白《送贺监》,贾至《早朝》,岑参《和大明宫》、《西掖》,高适《送李少府》,祖咏《望蓟门》,皆可竞爽。
中唐如钱起《贺李员外》、《寄郎士元》,皇甫曾《早朝》,李嘉佑《登阁》,司空曙《晓望》,皆去盛唐不远。刘长卿《献李相公》、《送耿拾遗》、《李录事》,韩翃《题仙庆观》、《送王光辅》,郎士元《赠钱起》,杨巨源《和侯大夫》,武元衡《荆帅》,皆中唐妙唱。[5](P90)
重要作家及重要作品的被罗列引证,正是“七律正典”以“七律诗史”的模式存在于胡应麟意识中的具体表现。用举例的方法,胡应麟将自己以为初盛中唐值得注意的作品都包括其中,让人可以据此了解唐代七律的优劣和特质。《诗薮》曰:
初唐体制浓厚,格调整齐,时有近拙近板处。盛唐气象浑成,神韵轩举,时有太实太繁处,中唐淘洗清空,写送流亮,七言律至是,殆于无可指摘,而体格日卑,气运日薄,衰态毕露矣。[5](P100)
胡应麟的这段论诗大致是“体以代变,格以代降”理论的具体案例。胡震亨在《唐音癸签》第十卷论七律部分将胡应麟的这则诗论引用了十之七八,内容基本相似,观点基本相同。除了初盛唐成就特高而引起复古派的一些关注外,对于中晚唐诗歌,他们仅仅止步于只言片语的论述。所以,构建唐代七律诗史的工作未能在他们手中完成。
二、许学夷系统的唐代七律史论
在前人和时人诗论的基础上,许学夷完成了构建唐代七律史的工作。见下表。

艺 术 特 征正宗 沈宋入圣 王孟杜、沈、宋三公体多整栗,语多雄伟,气象风格始备,为七律正宗。七言绝,在王卢骆再进而为杜沈宋三公,律始就纯,语皆雄丽,为七言绝正宗。王摩诘孟浩然才力不逮高岑,而造诣实深,兴趣实远,故其古诗虽不足,律诗体多浑圆,语多活泼,而气象风格自在,多入于圣矣。七言惟崔颢黄鹤雁门为极诣,高适岑参王维李颀虽入于圣而未优。盛唐七言绝,太白、少伯而下,高岑、摩诘亦多入于圣矣。七言绝,太白少伯意并闲雅,语更舂容,而太白中多古调,故又超绝。大历 中唐诸子,造诣兴趣所到,化机自在,然体尽流畅,语半清空,其气象风格,至此而顿衰耳。正变 子厚上承大历,下接开成,乃是正对阶级。然子厚才力虽大,而造诣未深,兴趣亦寡,七言律对多凑合,语多妆构,始渐见斧凿痕,而化机遂亡矣,要亦正变也。开成元和柳子厚五七言律,再流而为开成许浑诸子。许才力既小,风气日漓,而造诣日卑,故其对多工巧,语多衬贴,更多见斧凿痕,而唐人律诗乃渐敝矣,要亦正变也。开成七言绝,许浑杜牧李商隐温庭筠,声皆浏亮,语多快心,此又大历之降,亦正变也。大变 唐末郑谷七言绝较之开成,句语亦不甚殊而神韵益卑,唐人绝句,至此不可复振,要亦正变也。罗隐李山甫才力既小,风气日衰,而造诣愈卑,故于鄙俗村陋之中,间有一二可采,然声尽轻浮,语尽纤巧,而气韵衰飒殊甚。唐人律诗,至此乃尽敝,要亦正变也。
据上表可知,许学夷认为,唐初,经过四杰的酝酿,杜审言、沈佺期、宋之问三人的七律体式整栗,语言雄丽,具备了唐诗应有的气象风格,是律诗的正宗;盛唐,王孟、高岑的七律是圣体;中唐大历时期的七律仍是正体,但气象、风格已走向衰落;再发展到柳宗元手里,作者虽然还有一定才力,但造诣、兴趣减少,作品中渐有雕琢痕迹,已属于变体;开成年间的七律,如许浑才力又小,加上时代风气不好,作品中多有雕琢痕迹,但声律、语言方面仍有可取之处,也属于变体。唐末,郑谷、罗隐等人的七律,间有可采,但总体上声韵轻浮、语言纤巧、气韵衰败,也属于变体,七律此时已走到了尽头。
许学夷没有像胡应麟、胡震亨那样专门用一大段文字讨论唐代七律的演变过程,但他的观点和态度在各卷各条分述时是相互呼应的,可见他是有着与胡应麟、胡震亨相同的动态发展意识的。他论诗的卷次是按时代顺序编排的,论唐诗也依照高棅的“四唐”说分卷次,以下摘录的几则引文可见一斑:
七言律……至初唐诸子尚沿袭梁陈旧习,唯杜、沈、宋三公体多整栗,语多雄伟,而气象风格始备,为七言律正宗(原注:转进至高、岑、王、李、崔颢七言律)。律诗至此(高岑诸人)始为入圣,下流至于钱、刘诸子五七言律。
(钱刘)下流至柳子厚五七言律。
元和柳子厚五七言律再流而为开成许浑诸子。
开成许浑七言律再流而为唐末李山甫、罗隐诸子。[6](P243-244)
从表1和几则引文看,与胡应麟、胡震亨等人相同,许学夷对七律在唐代的演变过程也有其整体看法。自初唐到晚唐4个时期,他各罗列了若干名他心目中的重要诗人诗作为代表,以展现唐代七律的演变脉络,这一点正与胡应麟、胡震亨等人相同。若仅看上面所列几则引文,许氏之说似乎比胡应麟、胡震亨粗疏,但事实并非如此。因为本文此处所引的仅限于各期代表人物,对于与这些代表诗人同一时期的诗人,他也有很详瞻的论述。例如,在以柳宗元为代表的元和时期诸诗人,他有如下论断:
大历以后,五七言律流于委靡,元和诸公群起而力振之,贾岛、王建、乐天创作新奇,遂为大变;而张籍亦入小偏。唯子厚上承大历,下接开成,乃是正对阶级;然子厚才力虽大,而造诣未深,兴趣亦寡……七言律对多凑合,语多妆构,始渐见斧凿痕,而化机遂亡亦,要亦正变也。[6](P245-246)
对柳宗元同时期的七律作家,如韦应物、韩愈、贾岛、王建、姚合、张籍、白居易、元稹等人的诗作,他都有专门讨论。尤其对于王建的七律,他的论述颇为详尽。他说,王建的七律“句多奇拗,遂为大变,宋人之法多出于此”;同时,又举出王建的“怪恶”、“村陋”之句,说他“实为杜牧、皮、陆唐末诸人先倡;沿至宋人,遂变为常调矣”[6](P243)。
先不论许学夷的褒贬抑扬有多少处与今人的观点一致,这也不是其诗论的主要价值所在。其诗论最值得人们注意的,应该是许学夷在论证过程中有意识形成的规模与体系。许学夷的最大贡献便是他的评论包容广泛、讨论细致,几乎将前人留下的空白都填补了。以唐代七律为例,许学夷在明代前中期诗论家评论的基础上,将唐律发展演变的脉络清晰地勾勒了出来。可以说,最终在许学夷手里,明代人的唐代七律史建构工作得以最终完成。
[1] (明)王世懋.艺圃撷余(历代诗话本)[M].北京:中华书局,1981.
[2] (宋)严羽.郭绍虞校.沧浪诗话校释[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3] (明)杨慎.升庵诗话(历代诗话续编本)[M].北京:中华书局,1983.
[4] (明)王世贞.艺苑卮言(历代诗话本)[M].北京:中华书局,1981.
[5] (明)胡应麟.诗薮[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6] (明)徐学夷.杜维沫校点.诗源辩体[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
[7] 袁行霈.中国文学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8] 闻一多.唐诗杂论[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9] 陈伯海.唐诗学引论[M].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3.
[10] 李泽厚.中国美学史[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5.
[11] 陈国球.唐诗的传承[M].台北:学生书局,1990.
[12] 孙春青.明代唐诗学[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13] 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M].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