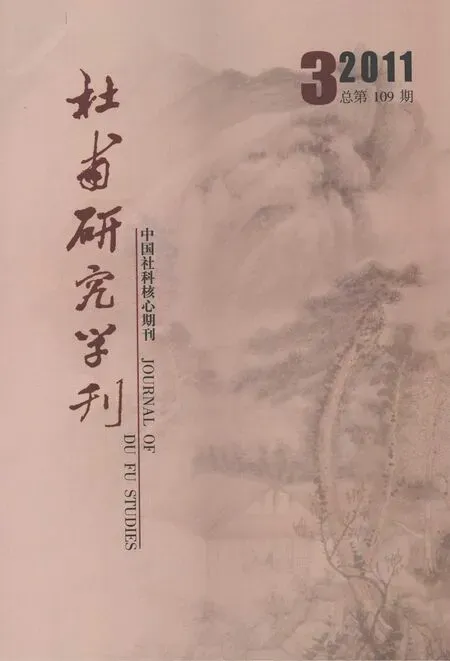杜甫对古代少数民族诗人的影响 (下)
徐希平
刘大杰论马祖常“其诗才力富健,颇多关怀民间疾苦、反映现实生活之作”,并认为其《踏水车行》等有白居易新乐府的精神⑧,如其《石田山居》:“无麦夫何极,吾忧陇亩空。岂能驱盗贼,得忍鬻儿童?荼蓼充肠熟,樵苏救口穷。无端县小吏,招役到疲癃。”所谓疲癃,即年老多病者,《汉书·高帝纪》:“年老疲癃勿遣”,而此处却指无端征召,全诗让人不由想到杜甫著名的《石壕吏》“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老翁逾墙走,老妇出门看”的凄切苦景。
类似于此的作品很多,特别擅长于以对比手法写出贫富悬殊和阶级矛盾,一方面《室妇叹》等,赞美了祖国各族人民的勤劳和勇敢,同时也写出了阶级压迫的现实。他有两首内容基本一样的关于马户的诗,即《马户》和《六月七日至昌平赋养马户》。二诗描写了一个寡妇养马,卖尽了田地房屋,衣不蔽体,食不充饥,马养得不壮,还要受到官吏的鞭挞。再如《古乐府》:
天上云片谁剪裁?空中雨丝谁织来?
蒺藜秋沙田鼠肥,贫家女妇寒无衣。
女妇无衣何足道,征夫戍边更枯槁。
朔雪埋山铁甲涩,头发离离短如草。
诗人所刻画的众多贫苦妇女形象,很容易使人想到杜甫《白帝》诗中“戎马不如归马逸,千家今有百家存。哀哀寡妇诛求尽,恸哭秋原何处村”之悲惨情境,内在渊源不言而喻,十分明显。
此外《宿迁县》诗描写在天灾人祸中,农民四处逃亡、嗷嗷求食的悲惨景象。都是同样令人同情。另一方面,他又写那些大官僚、大商人们荒淫无耻骄奢淫逸的生活。如:《湖北驿中偶成》:
江田稻花露始零,浦中莲子青复青。
楚船祠龙来买酒,十幅蒲帆上洞庭。
罗衣熏香钱满箧,身是扬州贩盐客。
明年载米入长安,妻封县君身有官。
另有《绝句十六首》(之一):“西江画舸贩盐郎,白轻衫两袖长。不肯一钱遗贫士,却弃双玉买歌娼。”这都是当时历史的真实写照,也可以看到“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批判精神的传承和影响。另如送别友人的《送董仁甫之西台幕》诗:“西南万里地,诏属大行台。秦树浮天去,巴江带雪来。山河无用险,邦国正需才。台幕风流美,书签想尽开。”不仅感情真挚,且又加以勉励,颇有杜甫《奉送严公入朝十韵》“公若登台辅,临危莫爱身”之意。
余阙 (1303-1358)字廷心,一字天心,党项羌人 (一说色目人),世家河西武威 (今甘肃武威),生于庐州 (今安徽合肥)。生于元成宗大德七年,卒于惠宗至正十八年,年五十六岁。元统元年(1333)第进士。累官参知政事。守安庆,死陈友谅之难。阙为政严明,治军与兵士同甘苦,有古良吏风。明初,追忠宣。阙留意经术,五经皆有传注,文章气魄深厚,篆隶亦古雅。著有《青阳集》四卷,《四库总目》传于世。
余阙的诗歌表达的也多为积极进取的精神意趣。如《送康上人往三城》:
尝登大龙岭,横槊视四方。
原野何萧条,白骨纷交横。
维昔休明日,兹城冠荆扬。
此祸谁所为,念之五内伤。
明当洗甲兵,从子臣石林。
康上人要归卧三城,诗人也有临渊之羡。但现实社会却是一派“白骨纷交横”的动乱局面。如朱玉麒先生所论:“诗人此际的感受是与李白‘莫谓无心恋清境,已将书剑许明时’、杜甫‘非无江海志,潇洒送日月,生逢尧舜君,不忍便永诀’的感情有着共通之处的。他们都希望将自己的经纶理想用之于世间;而余阙乃在国家危亡之际,表现出这种入世的思想与渴望和平、功成身退的志向,不能不说是更有进取性的。”⑨
在战乱中与朋友聚会时同样想到的是百姓暂得安宁,《安庆郡庠后亭宴董佥事》云:“鲸鲵起襄汉,郡邑尽烧残。兹城独完好,使者一开颜。……主人送瑶爵,但云嘉会难。岂为杯酒欢,乐此罢民安。……”可惜太平宁静日子短暂,“魄渊无恒彩,清川有急澜。明晨起骖服,相望阻重关。”
泰不华,色目人,字兼善,原名达普化,元文宗御赐其名为泰不华。其父乃御林军低级军官,后出台州 (浙江临海)任职,所以泰不华是在当地长大。十七岁时,泰不华江浙行省乡试第一,转年廷对赐进士及第,后任监察御史等职。泰不华平生作诗甚多,有《顾北集》等,但大多散失,泰不华自幼受儒家思想熏陶,积极入世,忠君爱国,他的《送琼州万户入京》一诗,“男儿堕地四方志,须及生封万户侯”,展现他为国建功立业的迫切心情。其名篇《卫将军玉印歌》,艺术性较高,全诗以汉朝卫青功名为比兴,主旨是揭示“一将成名万古枯”的主题,也对汉武开边的气魄表示出赞赏。但后半阕语意直转,叹息命运的无常与历史的吊诡,诗风沉郁,下笔有力,颇有杜甫《兵车行》之寓意。
元代著名诗人乃贤 (1309—?),字易之,号河朔外史,合鲁 (葛逻禄)部人。合鲁部人东迁,散居各地,乃贤家族先居南阳 (今属河南)。后其兄塔海仲良入仕江浙,他随之迁居四明 (治今浙江宁波)。乃贤淡泊名利,居四明山水间,与名士诗文唱酬。至正五年 (1345)离浙北上,达齐鲁,西进中原、山西,次年至大都,旅居约五年。在大都期间,他广结名流,研习典章制度。至正十一年(1351),南下返回吴越。当时浙人韩与玉能书,王子充善古文,乃贤长诗词,并列称“江南三绝”。他博学能文,气格轩翥,五言短篇,流丽而妥适,七言长句,宽畅而条达,近体五七言,精缜而华润;又善以长篇述时事,故亦有“诗史”之称。著述有《金台集》、《河朔仿古记》。后人又编有《乃前冈诗集》三卷 (明万历潘是仁刊宋元四十三家集)。
乃贤深受中原文化熏陶和影响,保持儒家操守。目睹社会疮痍和吏治的腐败,多次察访下情,希图以诗讽谏,匡正时弊,在诗文中对百姓苦难的同情之心不时有所流露。北上的前一年,黄河南北遭受饥荒,次年又瘟疫肆虐,民死者过半。乃贤以当时亲历见闻写成《新乡媪》、《颍上老翁歌》等长诗,真实反映了当时贫富悬殊的社会现实。前诗写百姓生活,“蓬头赤脚新乡媪,青裙百结村中老。日间炊黍饷夫耕,夜纺棉花到天晓。棉花织布供军钱,借人碾谷输公田。县里公人要供给,布衫剥去遭笞鞭。两儿不归又三月,祇愁冻饿衣裳裂。大儿运木起官府,小儿担土填河决。茅櫩雨雪灯半昏,豪家索债频敲门。囊中无钱瓮无粟,眼前只有扶床孙。明朝领孙入城卖,可怜索价旁人怪。骨肉分离岂足论,且图偿却门前债。数来三日当大年,阿婆坟上无纸钱。凉浆浇湿坟前草,低头痛哭声连天。”另一方面则是富贵人家的豪奢:“银铛烧酒玉杯饮,丝竹高堂夜歌舞。黄金络臂珠满头,翠云绣出鸳鸯裯。醉呼阉奴解罗幔,床前爇火添香篝。”对比十分鲜明,形成触目惊心的巨大反差。后诗反映“赤地千里黄尘飞”、 “疫毒四起民流离”的惨状,并透露出农民被逼揭竿而起声势浩大的史实。结尾表达出诗人的愿望:“老翁仰天泪如雨,我亦感激愁歔欷。安得四海康且阜,五风十雨斯应期。长官廉平县令好,生民击壤歌清时。愿言观风采诗者,慎勿废我颍州老翁哀苦辞。”诗歌为当时现实的客观记录,而又满含真情,故产生较大影响,当年担任御史亲历其事,并曾提出赈灾建议的著名诗人余阙读之曰:“览易之之诗,追忆往事,为之恻然!”⑩监察御史太朴危素评道:“易之此诗,格调则宗韩吏部,性情则同元道州,世必有能知之者。”(同上)其实这种写实的传统和悲悯胸怀与“安得广厦千万间”的杜甫诗史以及白居易的新乐府精神皆同一机杼。
其同僚盖苗亦评曰:“右《新鄉媼》一首,余同年塔海仲良宣慰君之仲氏廼賢易之之所作也。其詞質而□,豐而不浮,其旨蓋將歸於諷諫云爾!昔唐白居易为樂府百餘篇以規諷時政,流聞禁中,即日擢为翰林學士。易之他詩若《西曹郎》、《潁川老翁》等篇,其關於政治,視居易可以無愧。而藻繪之工,殆過之矣。況今天子聖明,求言之誥,播在天下。當此之時,易之之詩,或經乙夜之覽,則其眷遇,又豈下於居易哉!故余三復之餘,謹識其后以俟。”(《南臺中執法濮陽蓋苗耘夫書於京師寓舍》)
其同类诗作《卖盐妇》诗也写出了下层妇女的辛酸:“賣鹽婦,百結青裙走風雨。雨花灑鹽鹽作鹵,背負空筐泪如縷。三日破鐺無粟煮,老姑饥寒更愁苦。道傍行人因問之,拭泪吞聲为君語。妾身家本住山東,夫家名在兵籍中。荷戈崎嶇戍吴越,妾亦萬里來相從。年來海上風塵起,樓船百萬秋濤里。良人賈勇身先死,白骨誰知填海水。前年大兒征饒州,饒州未復軍尚留。去年小兒攻高郵,可憐血作淮河流。中原封裝音信绝,官倉不開口糧缺。空營木落烟火稀,夜雨殘燈泣嗚咽。東鄰西舍夫不歸,今年嫁作商人妻。绣羅裁衣春日低,落花飛絮愁深閨。妾心如水甘貧賤,辛苦賣鹽終不怨。得錢糴米供老姑,泉下無慚見夫面。”在揭露时弊之后诗人写道:“君不见绣衣使者浙河东,采诗正欲观民风。莫弃吾侬卖盐妇,归朝先奏明光宫。”希望以诗上达朝廷,改变民生疾苦。
在大都时,乃贤于友人处得到南宋遗民诗人汪元量诗集,感慨万千,作《汪水云诗集二首》,序中谓“水云之诗,多记其国亡时事,与文丞相狱中倡和之作。……及余至京师,因徐君敏道得《水云集》,读而哀之,偶成二律以识其后”,其二云:
一曲丝桐奏未休,萧萧笳鼓禁宫秋。
湖山有意风云变,江水无情日夜流。
供奉自歌《南渡》曲,拾遗能赋《北征》愁。
仙人一去无消息,沧海桑田空白头。
诗中以杜甫赋《北征》诗来比喻汪元量作品的诗史性质,可谓深得其旨,汪元量曾与文天祥在狱中做集杜诗,以杜甫精神自励,乃贤可谓其知音也。
北行期间,他对沿途山川古迹、衣冠人物、断碣残碑以及宋金疆场之变更,均留意察访,并结合图经地志和蓍老口述详加考订,每有感触,便作诗歌述志言怀。在大都期间,他广结名流,对典章制度无不研习精到。至正十一年 (1351),他经原路南下,返回吴越。反映中原十万百姓被驱迫修河而再遭凌轹的《新堤谣》,即写于归途之中。诗前有序云:“近歲河決白茅東北,氾濫千餘里。始建行都水監于鄆城以專治之。少監蒲從善築堤建祠,病民可念,予聞而哀之。乃为作歌。(黄河决道時,有清水先流至,名曰漸水。曹濮之人見此水,皆遷居高丘預避。)”诗曰:
老人家住黄河邊,黄茅縛屋三四椽。
有牛一具田一頃,藝麻種穀終殘年。
年來河流失故道,墊溺村墟决城堡。
人家墳墓無處尋,千里放船行樹杪。
朝廷憂民恐为魚,詔蠲徭役除田租。
大臣雜議拜都水,設官開府臨青徐。
分監來時當十月,河水塞川天雨雪。
調夫十萬築新堤,手足血流肌肉裂。
監官號令如雷風,天寒日短難为功。
南村家家賣兒女,要與河伯營祠宫。
陌上逢人相向哭,漸水漫漫及曹濮。
流離凍餓何足論,只恐新堤要重築。
昨朝移家上高丘,水來不到丘上頭。
但願皇天念赤子,河清海晏三千秋。乃贤是位深受中原文化熏陶和影响的西域人士,作为世家子弟,他较严格地保持儒家操守,身处末世而仍不忘报效元廷。在优游山水古迹的同时,目睹社会疮痍和吏治的腐败,因而多次察访下情,希图以诗讽谏,匡正时弊,在诗文中对百姓苦难的同情之心不时有所流露。如其《羽林行》:
羽林將軍年十五,盤螭玉帶懸金虎。
黄鷹白犬朝出游,翠管銀筝夜歌舞。
珠衣绣帽花滿身,鳴騶斧鉞驚路人。
東園擊毬夸意氣,西街走馬揚飛塵。
湖南昨夜羽書急,詔趣將軍遠迎敵。
寶刀锈澀金甲寒,上馬彷徨苦無力。
□人牽衣哭向天,將軍執别泪如泉。
安得天河洗兵甲,坐令瀚海無塵烟。
君不見关西老將多戰謀,數奇白发不封侯。
據鞍矍鑠尚可用,誰憐射虎南山頭。诗末显然用杜甫“安得壮士挽天河,净洗甲兵长不用”(《洗兵马》)之意。
又如發大都所作《上京紀行》: “南陽有布衣,杖策游帝鄉。憂時氣激烈,撫事歌慨慷。天高多霜落,歲晏單衣裳。執手謝親友,驅車出塞疆。雲低長城下,木落古道旁。憑高眺飛鴻,離離盡南翔。顧我遠遊子,沈思鬱中腸。更涉桑乾河,照影空彷徨。”诗中措词命意分明可以看到杜甫《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的影子,想起“杜陵有布衣”、“岁暮百草零,疾风高冈裂。天衢阴峥嵘,客子中夜发”诸诗句。可以感受到其对杜诗之熟悉。另在《次段吉甫助教春日怀江南韵》中的诗句也明显得自杜诗:
花底开尊待月圆,罗衫半浥酒痕鲜。
一年湖上春如梦,二月江南水似天。
修禊每怀王逸少,听歌却忆李龟年。
由此可见其受杜诗影响之深远。
丁鹤年 (1335-1424),字永庚,号友鹤山人。回族,武昌人。元末明初著名诗人。丁鹤年出身官宦,父职马禄丁官至武昌达鲁花赤。丁鹤年自幼聪颖,勤奋好学。就读于南湖书院,学习儒家经典,十七岁即精通《诗》、《书》、《礼》而负盛名。博学广闻,精通诗律,其诗取材广泛,以忧国忧民、关心人民疾苦为主要内容。曾自编《海棠集》,在明清两代均有流传。后人集为《丁孝子集》,收诗346首,铭5篇。《丁鹤年集》集一卷,《四库总目》传于世。
丁鹤年的诗在元末明初独树一帜,广为流传,不仅在我国少数民族文学史上有重要地位,在整个中国文学史上也有较大影响。后人对他的诗有较高评价,如我国现代著名史学家陈垣先生在他的《元西域人华化考》一书中说:“萨都剌之后,回回教诗人首推丁鹤年。”丁鹤年有四卷诗流传至今,分别是:《海巢集》、《哀思集》、《方外集》、《续集》。鹤年诗集存诗三百首左右,丧乱诗居十之三四,是精华所在。《元诗选》编者戴良谓其诗“措辞命意多出杜子美”。并用清人赵翼《题元遗山集》诗句评其诗。当然丁诗并无杜诗沉郁浑厚之气韵;转拟晚唐诸人,则又不如彼之纤细孱弱,因其深得中土文化精髓,又有本人之特殊际遇与民族血统,遂形成其特殊风格。这与元好问学杜又有其切身感受有相似之处,同样是所谓“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如其《岁晏百忧集》二首:
岁晏百忧集,独坐弹鸣琴。
琴声久不谐,何以怡我心。
拂衣出门去,荆棘当道深。
还归茅屋底,抱膝《梁父吟》。
岁晏百忧集,击节发商歌。
商歌未终调,泪下如悬河。
故乡渺何许,北斗南嵯峨。
有家不可归,无家将奈何。
又如《兵后还武昌二首》云:
避乱移家大海隈,楚云湘月首频回。
归期实误王孙草,远信虚凭驿使梅。
天地无情时屡改,江山有待我重来。
白头哀怨知多少,欲赋惭无庾信才。
乱后还家两鬓苍,物情人事总堪伤。
西风古冢游狐兔,落日荒郊卧虎狼。
五柳久非陶令宅,百花今岂杜陵庄。
旧游回首都成梦,独数残更坐夜长。
风格与用典皆近于杜少陵。再如《送人归故园》中写道:
故国闻道已休兵,客里哪堪送客行。
老去别怀殊作恶,乱余归计倍关情。
孤村月落群鸡叫,绝塞天清一雁横。
到日所亲如见问,浪游江湖负平生。
抒发了他有志难酬的苦闷心情,表现出他关心祖国命运的思想。另有《寄胡敬文縣尹》、《自咏十律》等,此类作品,处处感受杜甫的影子。
丁鹤年的诗风格独特,善于“画龙点睛”,即往往在最后两句中,抒发其思想感情,使主题得以深化,以达到发人深思的目的。如《登北固山多景楼》诗:“风月无边地,乾坤有此楼。城随山北固,潮蹴海西流。眼界宽三岛,胸襟溢九州。阶前遗恨石,谁复话安刘?”前六句描写登北固山多景楼所见景色及感受,而最后两句却通过凭吊历史遗迹,表达出他对国家命运的关心,谴责元朝政府的腐败无能。
丁鹤年的这种忧国忧民的思想,一方面是当时社会矛盾日趋尖锐后,正直的文士对国家人民命运的关心的产物,另一方面也是诗人继承了《诗经》以来中国诗歌的“比兴”、“美刺”的传统,并在当时的具体社会环境中加以张扬的结果。作为元代徙居中原,学习汉文化并运用汉文进行写作的少数民族诗人之一,丁鹤年以他的创作确凿地表明:诗歌创作应当反映社会现实生活,必须关心民众疾苦。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丁鹤年的这类作品反映了其创作的主体价值取向,奠定了他在元明诗坛,尤其是中国少数民族诗坛上的地位,使他和他的诗,经元、明、清乃至今天,赞誉之声经久不衰。
贯云石 (1286-1324),本名小云石海涯,号酸斋,又号芦花道人,畏吾尔族著名作家,以散曲著称,诗风豪迈,主要学习李白,但也有一些创作显然学习杜甫。如《岳阳楼》诗首联:“西风催我登斯楼,剑光影动乾坤浮。”显然用杜甫《登岳阳楼》诗“乾坤日夜浮”原句。
朝鲜族散曲作家李齐贤《洞仙歌·杜子美草堂》曰:
百花潭上,但荒烟秋草。犹想君家屋乌好。记当年,远道华发归来,妻子冷,短褐天吴颠倒。卜居少尘事,留得囊钱,买酒寻花被春恼。造物亦何心,枉了贤才,长羁旅、浪生虚老。却不解消磨尽诗名,百代下,令人暗伤怀抱。
“朝鲜高丽时期,随着汉文学的进一步普及,杜诗在其思想性和艺术性两大方面都成为了高丽文人学诗写诗的重要典范。高丽文人学杜诗不仅学其精湛的诗艺法度,而且还注重考究其审美把握和营造意象的门径。从而 ,各种版本的杜甫诗集和注疏杜诗的工作应运而生。在这种氛围中,杜甫伟大的现实主义创作精神和艺术手法影响了整整一代高丽人。”11
韩国学者全英兰《杜诗对高丽、朝鲜文坛之影响》一文“从两个方面考察了杜诗对高丽、朝鲜文坛的影响。第一个方面是就高丽、朝鲜所刊行之杜诗著作而考察杜诗的影响;第二个方面是根据高丽、朝鲜的诗话书而考察其影响。高丽文坛的主流文风虽然是以东坡为中心的宋代诗文,但也有覆刻的杜诗书,当时文人对杜诗的评价也很高。到了朝鲜时代,在王室倡导之下编辑了杜诗注本,接着翻译了杜诗。因此朝鲜诗话书上也很多有关杜诗的记录 。”12其文主要从诗话角度考察朝鲜文人对杜诗的理解和评价 ,以及杜诗对朝鲜文坛的影响,具有积极的意义。
元代还有著名的西域学者兼诗人辛文房,约生活于至元、大德年间,居于豫章(今江西南昌)。作为西域进入中原人士,他酷爱唐诗,自谓“遐想高情,身服斯道。”13虽然其诗散佚殆尽,但所著之《唐才子传》却堪称唐诗研究之不朽力作。该书记载了397位唐五代诗人传记并做评价,其中,杜甫传评曰: “观李杜二公,……语语王霸,褒贬得失。忠孝之心,惊动千古。骚雅之妙,双振当时,兼众善于无今,集大成于往作,历世之下,想见风尘。……昔谓杜之典重,李之飘逸,神圣之际二公造焉。”表现出对诗圣的无限景仰,也标志着元代少数民族作家学杜达到高峰。
三、明清时期少数民族诗人学杜概况
由于特定历史环境,明代见于记载的少数民族诗人相对不多,但不乏学杜之作。尤其在西南地区,比较集中。
首先比较突出的是壮族诗人群,壮族地区与中原文化接触交流历史比较久远,从先秦开始,历代皆有汉族文人前往南方壮族地区,传播汉族传统文化,而杜甫自然是其学习的重点,如学者们所指出:广西壮族文人“普遍受到杜甫思想及作诗技法影响,深言忧患意识”14,而且在杜甫接受史上还十分可喜地“出现了文学性与审美因素方面的变化。他们一般不仅接受和肯定杜诗的思想价值、艺术价值和审美价值,并且还把杜甫的诗歌思想和审美艺术视为他们学习的重要摹本和规范,“诗法少陵”15。因此,在清代壮族诗人中,学习杜诗成了一种文化时尚。出现了一大批学杜有成的诗人。郑献甫、张鹏展、刘定逌、黎建三、韦丰华等著名诗人都很大程度地受到杜甫的影响,也学习杜甫和杜诗。
壮族诗人王桐乡 (1420-1505),海南临高人,深受儒学影响,关心民瘼。有《王桐乡诗三百首》,其《纵横虎短歌》诗,对当时以人饲虎的恶俗进行批判。诗歌题目及首句皆化用杜甫“人今罢病虎纵横”而来,悲愤填膺。诗云:“纵横虎,罢病几家遭虎苦。食了儿孙食父母。”
壮族诗人以各种形式表达他们对杜甫的仰慕、学习和借鉴,其例不胜枚举。雍正年间的刘新翰“五律学杜”,仿杜诗而作《秋兴》八首16,黄焕中已有《秋兴八首用杜诗原韵》来感怀、纪实,李彦弼《翱乎寥阳之清政和七载丁酉七日上浣日》云“文英子建声华煊,少陵尝咏波澜阔”17,蒋纲《舟次抒怀》云“翻同老杜别无家”18,韦丰华《今是山房吟余琐记》曰:“老杜之所以冠绝古今者,有真性情故也。”张鹏展的《〈带江园诗草〉题词》认为“杜少陵一生忠爱,发于天性,亦由抱负使然”,郑献甫的《观伎人舞刀戏》显然从杜甫《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得到启发而又有所借鉴和变化。
王红先后发表《跨民族中的创新:清代广西壮人对杜诗的接受研究》19、《整合与创新:清代广西壮人接受杜诗的变异学研究》20,对清代广西壮族诗人自觉接受学习杜甫的过程及概况作过较为深入的论述。指出:“壮族文人一方面广采博纳杜诗,一方面又对杜诗加以发展,以本民族的文化特质与地域精神对其整合创新;也就是说壮族文人对杜诗并不是简单的复制与摹仿,而是富有创新性的进一步发展,这个发展对整个中华民族来说,无疑是一种融合性的推动。”确如其言,这在少数民族作家学杜方面可以说具有较为普遍的积极意义。
白族诗人赵辉璧 (1787-?),字蔺完,号苍岩居士,云南洱源凤羽人,存《古香书屋诗抄》,诗歌内容较为广泛,也反映出对传统文化的继承。称赞杜甫“鲸鱼擎沧海,鸾凤游大荒;巨浪动坤轴,高驾排天阊”。表现出对杜甫的景仰,在评介陆游时,也赞其对杜甫精神的传承,“少陵歌后谁知己?南渡英雄此一人。”21
赵廷枢,清代大理地区白族诗人,“白族赵氏作家群”代表人物,有诗集《所园诗集》四卷,现存诗505首,曾任江西省安福县、萍乡县县令,后因事免职。其诗歌作品内容广泛,多有摹写自然山水制作,又以之透出其个性与风格,如其《登苍山中和峰》,在景物铺叙中又以群臣拜见君王来比喻形容群峰环绕苍山主峰中和峰的壮阔景象,气势恢宏,蔚为壮观。清人袁文搂、袁文典《滇南诗略》评为:“气体苍浑,波澜壮阔,风格自近少陵。”22其《携徐曙东游九鼎寺》:“振策寻招提,松径羊肠绕。落落九鼎山,叠翠尘目嗦。高岭独岩晓,旁峰亦窈窕。琳宫聚蜂房,耸时青冥表。凿崖嵌层楼,标阁凌飞鸟。小憩雨花台,仰娣穷幽吵。大空怪石撑,罗细孤云袅。颇饶结构奇,不厌丘壑小。日夕卜山来,回看青未了。”诗人偕同好友徐曙东一起游览九鼎山中的寺庙,写出了山的巍峨、雄奇、俊秀的特点。诗篇的末尾“日夕卜山来,回看青未了”,“化用了杜甫诗句,自然有风味”23。
还需特别提到的是清代闽中回族诗人萨玉衡,据《清史稿本传》记载:萨玉衡,字檀河,福建闽县人,乾隆五十一年举人,曾官陕西洵阳知县。有诗集《白华楼诗钞》。关于其文学成就过去研究较少,宁夏大学学报1988年1期曾有袁宗一的《论回族诗人萨玉衡》有初步探讨,可以参考。萨玉衡,著述甚多,但除《白华楼诗钞》四卷外均遗失不传,其诗题材丰富,体裁多样,尤长于七律,其创作广泛吸取前代文学精髓,特别自觉继承杜甫诗,意在表达其与杜甫的精神相通,其《兖州城楼故址次杜韵》即步杜甫《登兖州城楼》原韵而作:诗云:“满目纷多感,吾生愧遂初。一年过东兖,双剑自南徐。作赋思文考,分封想汉余。杜翁临眺处,怀古益踌躇。”正如袁宗一先生所论:“萨玉衡对杜甫不只是崇拜,而是深深地理解”,24这可以从其《自奉先历彭衙邠鄜诵少陵诗各系一绝句》感受到,诗人沿着杜甫当年的行迹,结合自己的遭际去体会杜甫的心境。其一:“率府狂歌老,胡然南县来。平生饥溺意,十口诉人哀。”其二:“喜见故人孙,来依舅氏门。高斋定何处,剪纸与招魂。”其三: “凤翔徒步回,邠郊地最下。足茧愁荒山。且借特进马。”其四: “丧乱山川客,苍茫八月归。邨看西日落,泪进北征衣。”
侗族诗人杨廷芳在《鸿哪贵音》中真实而生动具体地反映了封建统治阶级压迫剥削给劳苦大众带来的深度疾苦,对贫苦农民和穷苦知识分子寄予无限同情,诗歌的人民性特色十分鲜明。从《逃难》、《难中度日》、《行乞》、《遭难以来》诸首可见一斑。《应差粮》一诗深刻揭露了封建统治阶级不顾老百姓饱受兵灾流亡之苦,不管百姓死活,无情地征兵差役征粮的罪恶:
饥寒辗转叹流亡,欲保余生返故乡。
草舍未完预召役,荒田初辟便征粮。
请工计食愁难补,贷种衍期愧未偿。
勤动终年仍自苦,几时身世得安康?
从《鸿嗷遗音》中我们可以看到清代咸丰同治年间贵州古州厅地域一部真实、生动、具体的军事史和社会史,诗集有较高文学欣赏价值和史学价值。其《逃难》:
井里邱墟付虎琅,余生逃出窜他乡。
夫妻自顾难兼顾,父子同方忽异方。
老幼价门悲乞丐,饥寒终日叹流亡。
当年无限膏梁胃,饿革沿途更可伤。
《行乞》:
从来行乞最难言,况属良家益可怜。
饥火起来颜觉厚,啼儿苦促刻难延。
晨昏托林肠几断,铺吸残羹涕暗涟。
多少豪门空咄悴,徒教见食但垂涎。
当代学者认为“诗人字里行间对苦难同胞的同情心多么真切感人,这几首诗似有诗圣杜甫《三吏》、《三别》一样的教化效果。”25可谓知言。
直到晚清时期,四川羌族才子董湘琴应邀由灌县 (今都江堰)赴松潘,创作著名的《松游小唱》,在其序中诗人写道:描写沿途风景感受,以五七言诗赋之,而不顾忌裁对,“信口狂吟,自鸣天籁,音之高下,句之段长,在所不计”26,在随意点缀中,三次提到杜甫及其诗歌,如写羊店飞沙风“扬尘扑面,吹平李贺山,杜陵茅屋怎经卷?”写雁门关“边气郁萧森,江间波浪兼天滚。……明妃出塞最消魂,青冢黄昏”, “长途感慨多,无端怅触,又不是李白夜郎,坡仙海隩,杜陵忧国,宋玉坎坷。”可见这种影响之深远,已经直接与现代文学接轨,启迪着诗歌语言及形式的创新。
余论:综观历代少数民族诗人学杜历程,可以看出杜甫诗歌的巨大影响,各族诗人学杜特别注重对杜甫精神的继承。杜甫之所以成为中国最伟大的诗人,其最突出的特征是其对国家民族的深切关注,这是后代各族诗人学习继承的重要原因,少数民族作家也在这方面取得突出成就,而元稹和元好问堪称这方面的杰出代表。除了思想内容的继承和相通之外,形式方面的借鉴也是少数民族诗人学习杜甫的重要表现。前面所述的诗人中大多均在艺术形式上有所借鉴,如元稹的新乐府,元好问、萨玉衡的七律等,都与学杜有关,更有很多诗人在其作品中,往往以杜甫自喻,或大量化用杜甫诗句,表现出对杜诗的熟悉和喜爱。杜甫广泛学习和吸收各族文化,集人类精神文明和艺术之大成,沾溉后世,也被各族诗人广为接受,这一过程,从一个方面反映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也反映出各族文化交流融合对于中华文化发展流传的重要意义。
注释:
⑧ 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
⑨ 朱玉麒《元代党项羌作家余阙生平及创作初探》,《民族文学研究》1997年第01期。
⑩ (清)顾嗣立《元诗选·初集》引,中华书局2002年版。
11 李岩《朝鲜高丽时期文学中的杜诗》,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2年第3期。
12 (韩国)全英兰《杜诗对高丽、朝鲜文坛之影响》,《杜甫研究学刊》2003年第1期。
13 (元)辛文房著,傅璇琮主编《唐才子传校笺·引》,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1页。
14 马学良、梁庭望、张公谨主编《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下),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第370页。
15 (清)汪森编,黄盛陆等点校《粤西文载·都御史萧淮墓志铭》,广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16 (清)梁章钜:《三管诗话》,第104页,蒋凡校注,广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17 (清)纪昀主编《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465-69页,台湾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
18 (清)梁章钜:《三管诗话》,第93页,蒋凡校注,广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19 王红《跨民族中的创新:清代广西壮人对杜诗的接受研究》,载《民族文学研究》2007年第01期。
20 王红《整合与创新:清代广西壮人接受杜诗的变异学研究》,载《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6年第5期。
21 转引自马学良、梁庭望、张公谨主编《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第345页。
22 (清)袁文典、袁文揆辑《明滇南诗略》卷21,清嘉庆年间刊印。
23 周锦国《赵廷枢及其所南诗集》,大理学院学报2008年第3期。
24 袁宗一《论回族诗人萨玉衡》,《宁夏大学学报》1988年第1期。
25 邱宗功《清代侗族诗人杨廷芳的诗歌创作》,《民族文学研究》1997年第4期。
26 (清)董湘琴著,张宗品、张文忠画《松游小唱》,四川美术出版社2004年版。
——评王新芳、孙微《杜诗文献学史研究》
——以宋代蜀人三家杜诗注辑录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