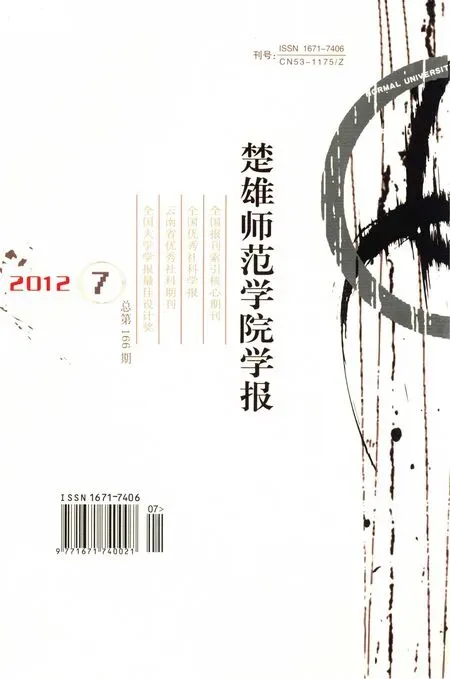读者在建构与突破中国文学史叙事模式中的作用*
陈志刚
(曲靖师范学院,云南 曲靖 655011)
一、读者与累积型的文学史叙事模式
中国文学史叙事模式经历了史学叙事模式、文学叙事模式和学科交叉叙事模式前后相继且相互弥补的历程。史学叙事模式吸取《史记》“纪传体”体例,以朝代、作家、作品的先后为序,联系历史上文学家的生平思想,注重揭示作品的思想意蕴及对后世文艺创作的影响,它在中国文学史叙事模式的成型过程中扮演着主要角色。文学叙事模式早已夹杂在史学叙事模式中,最突出的就是对作品艺术特色的鉴赏,它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文学史叙事模式中异常突出,原因是时代思潮剧变和西方思想学说的大量涌入。文学叙事模式以“独立的文学”及其对人类的终极关怀,作为评判历代作家、作品的根本标准,大力倡扬文学的纯艺术特性,对作品的人性特质作了新的开掘。相比前述两种模式,学科交叉叙事模式是进入二十一世纪之后才出现的,它主要以拓展中国古代文学的空间为宗旨,开始尝试关注中国古代文学与考古学、宗教学、传播学、美学等学科的关联,欲“重构我国古代文学新的研究方法体系,进而重构我们的东方学术研究体系”,要“为重写中国古代文学史奠定坚实而宽广的学术基础。”[1](P35)总体来看,中国文学史叙事模式经历了一个愈来愈注重历代文学自身发展规律的过程,与文学关联不大的因素逐渐被祛除,中国古代文学史的叙事模式不断地得以更新。可以说,中国文学史叙事模式是一个累积型的叙事模式,读者在其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以《诗经》为例。游国恩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更多关注《诗经》中的“国风”部分,认为“历代进步文人在创作中倡导‘比兴’、‘风雅’,实质上也就是倡导《诗经》的现实主义精神。”[2](P48)因为“国风”中的许多作品最初出自于下层民众之手,虽经采诗官加工配乐,但是它们以下讽上的浓郁的平民意识依然存在,后来陈子昂感叹“兴寄都绝”(《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白居易“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与元九书》)的关注现实的批判精神,就是《诗经》讽谏精神的延续。如此寻绎,既体现了著述者强烈的时代特色,又显现出他们特别关注《诗经》对后世文艺创作积极干预现实方面的作用。同时,《诗经·国风》鲜明的艺术特色势必会被这样的史学叙事模式所掩盖。应该说,此时期读者对《诗经》史学叙事模式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建构作用,他们特别注目于《诗经》作者所属的阶级、阶层,对相对处于弱势、边缘的群体的吟唱格外青睐,而于诗歌自身艺术特征的发掘则远远不够。陈平原先生指出:“30年代以后国人所撰文学史著,或多或少或明或暗都受到胡适描述的所谓‘文学史通例’的制约……将民间文学作为中国文学发展的原动力,这一颇有新意的假设,到50年代演变为‘民间文学主流论’,越来越暴露其理论缺失。时至今日,过分贬低‘文人文学’而高扬‘民间文学’,仍是研究者必须面对的‘五四’遗产——这一‘遗产’的创造者当然包括极力推崇‘白话文学’与‘平民文学’的胡适之先生。”[3](P173)
胡适先生的这个“文学史通例”就是将“古文文学”与“白话文学”对举,前者被目之为“死文学”、“文言文学”、“庙堂文学”、“贵族文学”;后者被认为是“活文学”、“白话文学”、“平民文学”、“民间文学”。胡适将政治革命和历史进化的理论套用到对中国古代文学的叙事中去,形成了特色鲜明的史学叙事模式,就连鲁迅、郑振铎都受其影响。陈平原先生说:“故最能代表胡适创见的,当属‘历史进化的文学观念’。”[3](P176)可见,中国文学史的史学叙事模式未能从根本上认识文学自身的独特性,没有超越儒家将文艺当成宣扬政治伦理道德的工具的视野。中国文学史诞生初期,以史学叙事模式建构的中国文学史,普遍遭到后代读者的质疑、批评,读者视阈的转变预示着史学叙事模式将要被突破。
文学叙事模式的代表性著作为袁行霈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和章培恒、骆玉明先生的《中国文学史新著》。前者认为,“从《诗经》开始,就显示出我国抒情诗特别发达的民族文学特色”,认为“风雅”精神包含“真诚积极的人生态度”,“比兴”对促成我国诗歌“情景交融的艺术境界”和“含蓄蕴藉、韵味无穷的艺术特点”[4](P65—66)影响深远。诗歌与政教的关系被大大地疏离,著者更加关注《诗经》作为一种抒情诗歌的本色和《诗经》“比兴”手法对中国诗歌特色的影响。后者认为《诗经》“表现为诗歌内容的逐步广阔和深入:随着对个人命运的关心程度缓慢上升,既促进了对痛苦生活的申诉,导致了对统治集团的较明显的指责,也推动了对个人欲望的较直率的表达和对人生问题的思考;另一方面则表现了在艺术手段运用上的进步。”[5](P73)
上述对《诗经》的接受转变是对文学叙事模式的扩展和升华,即从详细探悉《诗经》的艺术特色到揭示《诗经》的人性特质,其中包含个人的命运、痛苦、愤慨、欲望及反思,文学的思想性第一次回到了文学本体的层次。史学叙事模式向文学叙事模式的转变,读者视阈的改变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国文学史新著》对“比兴”艺术内蕴的分析深刻了许多,不仅突破了“比兴”与讽谏的联系,超越了将“比兴”置于整个中国古代诗歌发展历程中加以考察的视野,主要探讨“比”的“直观性”特征和“调动读者想象力”[5](P74)的功能,以及“兴”的象征性艺术特点。总之,中国文学史叙事模式发展至文学叙事模式阶段后,文学史撰著者的认识、评论与读者对文学的认识更趋一致,能够引起更多接受者的共鸣。
读者渴求突破已有文学史叙事模式是学科交叉叙事模式出现,且日益增多的主要原因。比如:根据出土的汉代“鸟衔鱼”等材料,重新解读《诗经》中出现的“鱼”意象诗歌;借助新出土文物对屈原作品的认定等。[1](P44—45)这属于借助考古学材料、知识对中国古代文学的一些疑案进行辨析、考证。再有,将人文地理学运用于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中,“以人地关系为切入点,以区域和空间为研究主线。”[6](P19)而中国古代文学与佛学、魏晋玄学等相互结合的研究就更多了。
综上所述,自上个世纪初中国文学史学科诞生至今,逐渐形成了几个突出的叙事模式:史学叙事模式、文学叙事模式和学科交叉叙事模式;它们产生于各自所处的特定时代,均有其存在的理由。随着读者对文学的日益自觉和时代思潮、文化和学术环境的变迁,中国文学史叙事模式逐渐累积成以文学叙事模式为主,其他叙事模式为辅的格局。并且,从几个时代的中国文学史著述依次被取代的历史来看,读者在中国文学史叙事模式的建构与突破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
二、读者与精英、市民叙事模式
中国文学史读者的精英性,决定其精英叙事模式为主的格局。另外,城市经济的繁荣,导致了市民阶层的壮大和精英读者的反思,市民叙事模式一度在中国文学史叙事模式中占有一席之地,这亦是读者参与建构和突破中国文学史叙事模式的绝好例证。
第一,精英叙事模式的确立。
什么是精英叙事模式呢?它是指掌握着文学话语权的阶层和人士(比如:先秦的士、汉代的经师儒生、魏晋的名士及其以后因科举出身的官吏、士大夫等)理解、认识和创造的中国文学的历史。换言之,整个中国文学史就是以他们为主角的文学发生、发展和演变的历史。精英叙事模式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经得到确立,中国文学史学科诞生之后的史学叙事模式是对古人精英叙事模式的承续;精英叙事模式延续至今,一直是中国文学史的主流叙事模式。精英叙事模式的确立,集中显现于孔子关于《诗经》的相关认识和评论。《论语》提到《诗经》总共14次,列举主要的几次如下:
“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7](P11)
“子曰:‘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论语·八佾》)[7](P30)
“子曰:‘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论语·子罕》)[7](P92)
“陈亢问於伯鱼曰:‘子亦有异闻乎?’对曰:‘未也。尝独立,鲤趋而过庭。曰:学诗乎?对曰:未也。不学诗,无以言。鲤退而学诗。’”(《论语·季氏》)[7](P178)
“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於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7](P185)
孔子对《诗经》中许多下层民众创作的诗,作了符合儒家礼乐的正统理解。他认为《诗经》的思想纯正,只有学习《诗经》才能近持家、远治国,开阔视野,帮助一个人成为有担当的“文质彬彬”的君子。汉代儒生对《诗经》作繁琐的章句注解,将《诗经》看作是一本讽谏之作,确实源于孔子对《诗经》的评论、认识。因此,《诗经》“国风”中许多充满批判、反抗意识的作品被大大地曲解了,或者说是民众意识被精英化。中国文学史中的精英叙事模式,自儒家对《诗经》的精英化阐释而得以确立,当后继者撰述中国文学史《诗经》部分时,不管怎样努力,都难于摆脱儒家自孔子建立起来的这种精英叙事模式,只能简略地指出“国风”中下层民众怨愤、恋爱、婚姻的积极意义,但是终究难于彻底颠覆《诗经》的精英叙事模式。
第二,市民叙事模式的萌芽和成熟。
市民叙事模式在司马迁的《史记》中就有所显现。《史记》中市民叙事模式的萌芽,与司马迁个人的遭际和思想旨趣关系密切。《史记》是作为传记文学名著而置身于中国文学史的,除了为帝王将相列传之外,它还将许多下层人物写入书中,而这些人物有刺客、游侠、商人和方士等,他们都是城市繁荣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的喜怒哀乐正是普通百姓日常生活的缩影。正因如此,司马迁遭到了班彪、班固父子的批评。另外,《史记》还将项羽、陈胜等与封建正统观念相抵触的失败者、农民起义领袖,写成极富悲剧意蕴和反抗意识的英雄形象,这也深深地感染了广大市井细民,赢得了他们的肯定。可见,《史记》体现了司马迁对经历了痛苦、不幸人生的市民的广泛同情,后世读者在阅读、评论《史记》时,特别注目于《史记》的市民意识,故而在建构中国文学史叙事模式时,形成了一种与精英叙事模式相对的市民叙事模式。《史记》中萌芽的市民叙事模式之所以没有继续发展,根本的原因是诗赋一直居于我国文学的正统,而小说、戏曲的时代还远未到来。
自宋代出现说话和话本开始,元代杂剧繁盛,明清戏曲、小说在诗赋创作趋于停滞的情况下,迅速获得了读者的广泛认同,市民叙事模式随之成熟起来了,中国文学不再以高雅自居,而是以读者的认可作为评判标准之一。自宋代开始的中国文学史叙事不再停留于对诗歌、辞赋的鉴赏、评论,而是要给体现广大中下层民众情感意志的小说、戏曲预留足够的空间。《史记》曾被汉代统治者定为“谤书”,这人为地隔断了读者的接受和反馈,此种自上而下的市民意识显然不能促成市民叙事模式的成熟。自宋代始,城市规模日益扩大,市民阶层迅速壮大,相比以前,他们的文化修养有了很大提升,市民意识自民众中间蓬勃爆发,自下而上地改变着文学、文化格局,小说、戏曲成了市民们宣泄喜怒哀乐的最佳选择,市民叙事模式因而日趋成熟。
综上所述,从中国文学史叙事模式的切入点来看,的确存在精英叙事模式和市民叙事模式。精英叙事模式最早确立,由《诗经》的经学化和汉赋而达至顶点;市民叙事模式则经历了一个由自上而下到自下而上的萌芽、发展和繁盛的曲折过程。前者不时感受到来自后者的冲击、反抗,有时则动用了文学以外的手段才将后者压了下去,可是,读者的选择和推动让市民叙事模式渐成壮大之势,这也是以胡适《白话文学史》为代表的文学史著述高扬“白话文学”的原因之所在。其实,精英叙事模式和市民叙事模式蕴含着雅与俗、官方与民间、精英与平民等许多潜在的叙事背景,不论怎样,读者成为这两种叙事模式相互较量的一个重要砝码。
三、读者与“经典”叙事模式
经典叙事模式就是主要围绕中国文学史的经典文类、作家、作品进行中国文学史发生、发展、演进的叙述。建构经典叙事模式的第一类人是各个作家、作品产生时代的读者,他们绝大多数是著名的文士、评论家,当然也包括一些帝王、贵族。前述《诗经》的经典化建构即是很好的例子,再如屈原及《楚辞》的经典化过程。屈原开创的辞赋风格比较特殊,其中的爱国思想和崇尚美德的理想与儒家的思想是一致的,但透露出的基于个人价值实现的生命感叹和怨愤之情,却与儒家“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文学观念形成冲突,因此,屈赋在汉代并不被沉浸于繁琐章句的儒生们所看重,相反;只有那些遭遇人生、仕途坎坷的文人对其钦慕不已,如:贾谊、司马迁、东方朔、王逸等。可见,屈原及《楚辞》到底能否进入经典叙事模式的框架,至少在东汉以前是不确定的。
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说:“屈原放逐,著《离骚》”,他以同情之理解看待屈原及其辞赋,认为是“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的“发愤之作”,肯定了屈赋的价值。而班固对屈原及《楚辞》的认识与司马迁很不相同,《汉书·艺文志》载:“春秋之后,周道寖坏,聘问歌詠不行于列国,学《诗》之士逸在布衣,而贤人失志之赋作矣。大儒孙卿及楚臣屈原离谗忧国,皆作赋以讽,咸有恻隐古诗之义。其后宋玉、唐勒,汉兴枚乘、司马相如,下及杨子云,竞为侈丽宏衍之词,没其讽喻之义。是以杨子悔之,曰:‘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如孔氏之门人用赋也,则贾谊登堂,相如如室矣,如其不用何!’”[8](P1756)
班固以儒家政教文艺观为标准,指出屈原及汉代的一些辞赋家只顾驰骋文辞,失却了《诗经》的讽谏、劝谕;认为荀子和屈原写作辞赋时将个人荣辱凌驾于国家之上是不可取的创作动机。总之,班固一方面将《诗经》建立的儒家诗教观经典化;另一方面,欲将屈原及后继者的辞赋排除在文学经典之外。
东汉王逸作《楚辞章句序》,指出:“今若屈原,膺忠贞之质,体清洁之性,……夫《离骚》之文,依托五经以立意焉。……屈原之词,诚博远矣。自终没以来,名儒博达之士,著造词赋,莫不拟则其仪表,祖式其模范,取其要妙,窃其华藻。所谓金相玉质,百世无匹,名垂罔极,永不刊灭者矣。”[9](P54)
王逸不仅指出屈原及《楚辞》未违背五经宗旨,而且肯定屈赋为后代词赋之源。王逸对屈原及《楚辞》的肯定,纠正了班固站在正统立场上的保守、片面认识,使《楚辞》能最终进入到文学经典叙事模式的视野。而最终确立《楚辞》经典地位的是刘勰,他在全面、综合地分析了延续整个汉代关于屈原及《楚辞》价值、地位的争论后,说:“固知楚辞者三,体慢於三代,而风雅於战国,乃雅颂之博徒,而词赋之英杰也。……故能气往轹古,辞来切今,惊采绝艳,难于并能矣。”[10](P47)
司马迁、王逸、刘勰等不同时代读者的极力争辩,在屈原及《楚辞》进入经典文学史地位的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后来的人们认识到班固评论的落后、保守,也是屈原及《楚辞》能一直立身于中国文学史经典叙事模式中的重要保证。可见,有价值、有意义的作品能否传之后世而成为经典,读者的阅读、鉴赏、推崇至关重要。中国文学史学科诞生之后,关于中国文学史的经典知识其实大部分业已存在,撰著文学史的大学教员们只需将中国古代诗话、词话等文论中提倡的作家、作品拈出来,一部中国文学史就会呈现在人们面前。
当然,在新的文学事实、材料出现后,后代的读者也会突破经典文学史叙事模式。如对南朝文学的认识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学术界对南朝文学缺乏全面、深入研究之前,文学史著述中将之视为“形式主义文学”,这一直是经典的文学史叙事模式。近年来,南朝文学有了相当的深入研究,如:文体意识的辨析、永明体与律诗的关联、文学的娱情化倾向等。若不将上述研究成果融入到文学史著述中,那么,所谓的经典叙事模式就可能成为顽固不化、抱残守缺的代名词。再如,宋、元、明、清产生了大量市民趣味浓厚的小说、戏曲作品,而诞生之初的中国文学史著述并未充分重视它们的存在。后来,读者们逐渐认识到宋、元、明、清的诗、文、词、赋等已经走上一条徘徊不前的道路,此时期的文学史叙事模式必须将广大市民的审美趣味纳入其中,不能再局限于文人士大夫的褊狭视野里,之后的文学史著述才逐渐改变了这种经典的文学史叙事模式。现在,随着学术研究的深入和域外思想的引入,许多文学史著述又将考古学材料、外来哲学思想用于中国文学史小说、戏曲部分的叙事中,小说、戏曲的经典叙事模式正在成型。
总之,经典叙事模式形成于文学史学科诞生之前,后代的读者和文学史撰著者不断突破经典叙事模式的束缚,将特定时代读者们对中国文学史的体悟、理解融入到经典叙事模式中;建构经典叙事模式是读者的主要工作,而突破则为特定时代思潮和文化氛围使然,读者与中国文学史经典叙事模式的关系,绝妙地诠释了经典的流动性;读者在中国文学史学科诞生之前和之后,均发挥着建构和突破中国文学史叙事模式的作用。从叙述方法来看,中国文学史叙事模式是一个累积型的叙事模式,大致包括史学、文学和学科交叉三种叙事模式。从叙述线索来看,中国文学史叙事模式一直贯穿着精英、市民两种叙事模式,精英叙事模式为主,市民叙事模式是在质疑、反抗精英叙事模式中逐渐成形的。从叙述策略来看,中国文学史叙事模式始终存在一个经典叙事模式,读者的突破也几乎不能逾越这个经典叙事模式的框架。我们看到,中国文学史叙事模式的建构至今仍未终止,只要有不同时代的读者参与其中,且形成突破已有文学史叙事模式的力量,那么,“重写文学史”就会成为任何一个时代的呼声。
[1]郑杰文主编.中国古代文学跨学科研究[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
[2]游国恩,王起,萧涤非,季镇淮,费振刚主编.中国文学史(一)[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
[3]陈平原.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4]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一)[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6.
[5]章培恒,骆玉明主编.中国文学史新著[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
[6]周晓琳,刘玉平.空间与审美——文化地理视域中的中国古代文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7]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0.
[8]汉书·艺文志:卷三十[M].北京:中华书局,1974.
[9]郭绍虞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一卷本)[C].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10]范文澜.文心雕龙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