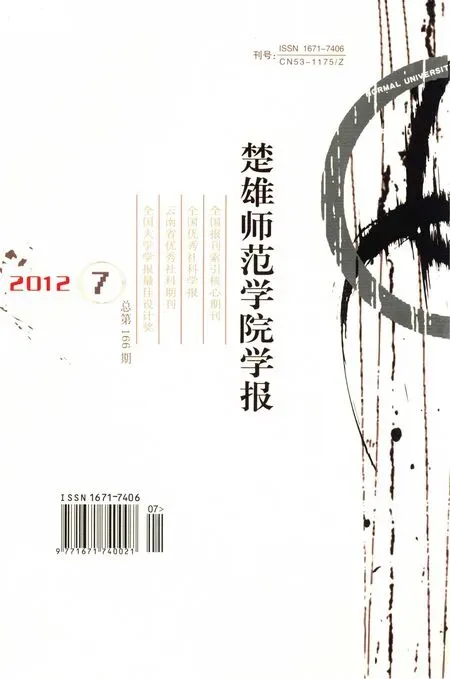试论《封神演义》的“重复”与“反重复”*
李建武孟华
(广东培正学院,广东 广州 510830)
《封神演义》(以下简称为《封神》)是一部富有争议性的中国古典小说,譬如在“重复”问题上。以下将尝试对这一问题作出一些论述。
一、重复:题材内容
钟伯敬评本《封神演义》第45回总评说阐教破“十绝阵”的打斗叙述几乎是一个模式:“破一阵,必先用一个赔偿性命的,此便是佛家轮回报应之说,执一而不可破。”[1]其实,这里涉及到中国古人美学取向上的重复原则。
首先,重复并不会影响作品成为经典文学,因为这涉及到民族风格的问题。中国人喜欢重复,并不排斥重复。比如中国人喜欢看热闹,喜欢多,一个人来了不够,人越多越好,所谓“多多益善”,用现今的话说,就是中国人喜欢“热”。80年代以来,中国内地兴起言情小说、武侠小说阅读热,琼瑶等创作了那么多大同小异、爱恨离愁的爱情小说,金庸、梁羽生等创作了那么多大同小异、豪侠俊杰的武侠小说。尽管作家在大量创作同一题材的小说,各种言情故事之间大同小异,各种武侠内容都是帮派斗争,但就是有那么多读者喜欢看。由于有这么多读者喜欢“热闹”,并不忌讳重复,也就形成作家们对此题材作品的绵绵不断的创作“热潮”。
现今的中国读者喜欢“热闹”,其实古代也是如此,诗词创作方面就是这样。山水诗、田园诗、赠别诗、咏史诗、写景咏物诗等各种题材都有接连不断的诗人在重复着写,并且效果也是异彩纷呈。词的创作一直以婉约风格见多,但并没有因为前人在婉约词方面作出了巨大成就,就不再有人问鼎这一领域了。从历代都有婉约词创作的杰出代表(如温庭筠、欧阳修、柳永、苏轼、李清照等)就可看出,作品的题材是可以重复的。小说也是如此。明代历史演义小说一大摞,并不会因为有了经典代表《三国演义》,其他历史小说就不看了;神魔志怪小说也是一大摞,不会因为有了经典力作《西游记》、《封神》,其他神怪小说就不看了,这里面有中国读者喜欢重复的审美趣向的原因。当然,从文学的长远发展来看,文学作品需要寻找突破口,寻求不苟雷同的模式,表现不同的文学趣味,而追求“热闹”、母题重复、模式相近的创作局面会制约文学的生命力,使文学创新形成“瓶颈”。
的确从根本上讲,回避重复,文学才会有新鲜的面孔。从文学文体来看,先秦诸子散文、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与戏曲等文学经典文体是在不断地变换着面孔,这激活了文学的生命力,而固守某一种模式和套路来创作,必然会制约文学发展的原动力。但从某个阶段来说,也并不完全如此,文学也不是完全排斥重复原则,有时重复反而是文学作品成为经典的必经之路。
中国古代就有很多结局是大团圆的叙事文学被奉为经典,如《西厢记》、《琵琶记》、《牡丹亭》,作家们在重复着大团圆的叙事模式,但观众和读者就是百看不厌。同一母题的文学创作,则更是中国古代文学经典化的一个重要途径。如李隆基与杨玉环的婚恋母题,唐代有白居易的诗歌《长恨歌》,元代有白朴的杂剧《梧桐雨》,清代有洪昇的传奇戏剧《长生殿》。这三种文学作品母题相同,但并没有影响它们成为李、杨婚恋题材文学的经典之作。再如张生与崔莺莺的母题,唐代本已有元稹的传奇小说《莺莺传》,金国已有董解元的《诸宫调西厢记》,但元代的王实甫还要写杂剧《西厢记》。这表面看似重复,但“王西厢”并非在原有文学作品的基础上简单重复,而是加工润色,进行再创造,致使“王西厢”成为崔、张爱情故事中最有成就的艺术作品。可见,其实重复原则把一些作品推到了经典文学的高度。
小说方面也是如此。中国古人写历史或历史小说也是一个接一个,关于各朝各代的史书都有,关于各朝各代的历史演义小说也很多。尽管各朝之间有很多相似的历史事件,如外戚专权、宦官专政等,但仍然有人写历史小说,仍有大量的读者要看这种近乎雷同的历史小说。作为经典小说的《三国演义》尽管在题材内容上,与史书《三国志》、小说《三国志平话》有许多重复之处,但这并没有影响它成为一部经典小说。它虽然实践着“重复原则”,如“三气周瑜”,“三顾茅庐”,“六出祁山”,“七擒孟获”,“过五关”,“九伐中原”等,但却有着“同树异株,同枝异叶,同叶异花,同花异果之妙”。[2](P14)这实际上涉及到小说创作中的“犯”与“避”的问题。“犯”是中国传统小说批评家们所用的一个概念,指故事情节或人物性格等方面的“相同或相近”,粗略地讲,就是指重复。毛宗岗赞赏《三国演义》的重复之妙,因为它们不是简单机械的重复,而是同中见“异”。《水浒传》也是如此。尽管它的题材取自于《大宋宣和遗事》和元代“水浒戏”杂剧,人物和故事都有些重复,但《水浒传》还是能在宋江起义题材的叙事文学作品中脱颖而出,成为一部经典小说。《封神》也是如此,尽管它在题材上取自于《史记》和《武王伐纣平话》、《列国志传》等,内容上与它们有些重复,但这并不影响它成为一部极受大众欢迎的神怪小说。因为它们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是既有重复,又有反重复。即重复的只是题材与母题或局部内容,反重复的是不同的细节、文体、文学表达(艺术价值)和整体情节等。正是因为作品有更多的创新——反重复,才赢得了很高的文学地位。
其次,有时模式化的叙事可以起到反复加强,给读者留下极深印象的积极作用,因为它贯注了循环美学的创作思想。如破十绝阵时的模式化描写是不是就完全是弊端?回答是却也未必。假若有人说《封神》写诸神和诸将打斗,很多次都是先由助周方“一人挺身”,然后是助纣方破口大骂,再引出一场唇枪舌剑,那这种看法是错误的,因为这样的叙述仅在阐教破十绝阵时比较突出,其他打斗叙述并非如此(后详)。当然,我们必须首先承认,破十绝阵时的模式化叙述确有弊端。托名李卓吾先生评本《三国演义》的评点者就抱怨:“读《三国志演义》到此等去处,真如嚼蜡,淡然无味,陈法兵机都是说了又说,无异今日秀才文字也,山人诗句也然。”(第110回评)这是为何呢?因为“读《演义》至此惟有打顿而已,何也?只因前面都已说过,不过改换姓名、重叠敷演云耳。真可厌也。”(第112回评)[3]显然评者是贬抑这种重复的。但是这就完全不好吗?其实是见仁见智。浦安迪先生则说这种“重复迭文”“倒不如说那是它所以成为不朽文学名著的关键手法。”[4](P384)浦安迪还肯定了循环美学作为早期经典化诗歌形式(如《诗经》)的标准。[5](P295)的确,《封神》中程式化打斗描写也涉及“循环美学”。循环美学讲重复,讲究“一咏三叹”,认为重复、叠用也是一种美。笔者认为在某些局部进行重复是可以的,尤其对于战争题材的长篇小说而言。事实上,《封神》的重复叙事也是局部性的,基本上只限于“十绝阵”的打斗描写,并非整部小说的战争叙事都是重复性、模式化的,这样就把它重复叙事的负面影响降低了许多,而呈现出来的更多的是循环美。这种体现循环美原则的叙事可以起到反复加强,给读者留下极深印象的积极效果。
当然,文学作品的循环重复是有限度的,这就需要反重复。尽管从局部看来,《封神》存在重复相似的神魔打斗,但从根本而言,它的艺术表现是反重复的。以下笔者将以意外叙事为例,论述《封神》反重复的成就。
二、反重复:意外叙事
《封神》的打斗描写看似重复,但其实并未真正重复。杨义先生曾提到“重复中反重复”的叙事谋略。[6](P52—54)《封神》打斗情节的反重复主要是靠意外叙事,也就是打破现有的叙事模式,制造令人意外的结果。正如托名钟伯敬评点的第45回总评所指出的那样,或许阐教在破截教摆的“十绝阵”时有些程式化、模式化的写作弊病,但综观其他回目的打斗描写,却有很多反重复的艺术价值,其结果往往出乎人的意料之外。
《封神》在叙事上还会使用饶有趣味的小技巧,插入小情节,笔者套用俗语形容之为“插一脚”或“插一杠子”。如第57回苏护父子本已决意向子牙投诚,却恰巧此时来了几位由申公豹请来的截教中人吕岳、周信等人,他们又来“插一脚”,致使苏护投诚受阻,后来又有殷洪等人的阻拦。直到第61回殷洪绝命,前前后后共跨了5回之多,苏护才完成投诚助周的心愿,这种叙述令读者感到意外。第71回写洪锦命斩胡雷,情节不长,本来一旦胡雷被斩首,此情节就结束了。结果读者意想不到的是辕门外又冒出来一个胡雷讨战,此乃是胡雷用替身法躲过杀戮。这种注意小技巧的点缀,使读者读来颇感趣味。该回纣将胡升本来将于第二天早上向洪锦投降,却恰巧当天晚上来了火灵圣母,要替门徒胡雷(胡升之弟)报仇,此又带来一阵是非厮杀与血战。
《封神》讲究战斗的多样性与复杂性。如第62回写助纣方羽翼仙就用栽赃的形式挑衅子牙:“你有何能对人骂我,欲拔吾翎毛,抽吾筋骨,我与你本无干涉,你如何这等欺人?”这与截教其他人与子牙阵营会战就迥然不同。而且这一回打斗,助纣方羽翼仙就根本没有先得胜,而是首先就被杨戬、哪吒、黄天化等人打得一败涂地,接着他施毒计、指望西岐变为渤海的阴谋也未得逞。可以说,羽翼仙一直是败退,并不像其他各回多有助纣方先获胜,次后是助周方反败为胜的模式。
第73回有周兵战纣将邱引一事。由于《封神》在叙述阐教破“十绝阵”时,往往是周方先是一名小卒失足牺牲,然后才是周方派一名大将战胜纣方将领,因此,一般读者本以为周方这次也会先失去一两名无名小卒,但结果并没有,而是纣方一味地失掉将领。这次却是邓九公先杀了纣将马方,次是黄天祥杀了纣将高贵,再是邓九公杀了纣将余成、孙宝。邱引还被黄天祥打得“吐血不止”,而周方毫发未损,没有丧失一兵一卒。这种结果也是让读者颇感意外的。
本来按一般逻辑,阐、截双方开战之前如果纣方有道人拜访,定是帮助他们灭周的,但有时也有不同。如第80回截教道士李平就是来劝吕岳放弃阻挠周武、姜尚的。而且,李平是心向周营的,按理应该最后投诚周营了,但是结果并非如此。本来阐教过了万仙阵,可谓大的战斗场面过去了,整个征战过程进入了尾声,但仍有零星的小战斗,这些小战斗的结果也出人意料。如赫赫有名、法力无穷,会使三千乌鸦兵的“哼将”郑伦竟死于名不见经传的“牛精”金大升手里,并且,最后帮助杨戬收服金大升、猿精袁洪的竟然是第1回出现的女娲娘娘。第86回读者本以为崇黑虎重回周营又会立下大功,可是结果并非如此,他竟然很快就被张奎夫妇战败致死了。
再如第42回末写到闻太师知道子牙会晚上劫营,故早作应对准备,读者满以为闻仲会打赢这场夜战。可是,出乎读者意料的是闻仲“退走往岐山”。这种激活情节、造成波谲云诡的意外结果,形成跌宕起伏的叙事在《封神》中还有很多。
第48回赵公明已知陆压用“钉头七箭书”射杀自己,故派陈九公、姚少司深夜去抢书。一般读者读到这里,以为赵公明会挽救自己一条性命,因为根据“对手看破一方的阴谋,往往另一方就失败了”的逻辑,结果应该如此。的确,接下来,陈、姚二人抢得了箭书,故读者会更加坚定自己的先前判断。然而令读者感到意外的是,陈、姚二人抢得的箭书中途又被周营人马抢回去了,最后赵公明是眼睁睁地看着陆压、姜子牙射死自己。第49回云霄等人誓为赵公明报仇,而且她们用混元金斗擒住了陆压,根据截教人物刚出场往往得胜的逻辑,读者会以为这次陆压没命了,可是出乎意料的是,陆压竟化作长虹逃走了。这种出其不意的叙事策略和手段,既造成绚丽多姿的场景效果,又能获得新奇多变的刺激和满足感,从而产生了吸引读者眼球的阅读效果。
再如,读者以为阐教破了“十绝阵”,就意味着反(纣王)征伐之大事业就基本告成,因为纣营中原本只有两人很有能力,即“文有闻仲,武有黄飞虎”,再就是两个佞臣费仲、尤浑比较重要。费仲、尤浑早在第39回就被姜子牙施“冰冻岐山计”斩首了,黄飞虎早在第34回就已投诚了周武王阵营,因而纣营有影响的就只剩闻仲一人了。“十绝阵”是闻仲邀请截教道友摆设的,可以说,阐教一破“十绝阵”就相当于破了闻仲。的确“十绝阵”一破,紧接着闻仲就在绝龙岭丧命了(第52回)。故此,读者一般会预感后来没什么大的战斗了,然而此后还有比“十绝阵”更厉害的“诛仙阵”、“万仙阵”。再如,作者有意赞扬阐教和周方,这是非常明朗的,致使许多读者以为阐教知名道士和周营著名将领都不会牺牲,但结果却出乎意料之外,他们中相当多的人都上了“封神榜”。
第72回洪锦夫妇俩被火灵圣母接连打败,于是向姜子牙求救,子牙说道:“此非我自去不可。”读到这里,读者往往以为子牙能降住火灵圣母。哪知紧接着的结果并非如此,而是子牙也被火灵圣母打得一败涂地,被“砍开皮肉,血溅衣襟”,又被一锤打中“后心,翻斤斗跌下四不象去了”。姜子牙这种命运就颇令人感到意外。在险象环生、遭此大难之际,哪知局势发生急速回转——广成子跑来相助,用番天印打死火灵圣母,救活了姜子牙。本来子牙在第72回已被火灵圣母打死过一次,读者或以为子牙可以安稳地过一段时光了,哪知就在该回,作者又插叙申公豹一“脚”:申用一颗天珠将子牙打死。一回之内子牙竟连死两次,这也是一般读者料想不到的。再如黄飞虎之死竟被作者安排在截教最大阵“万仙阵”之后(第86回)。因为第85回还在写邓昆、芮吉二侯归降周营,这意味着眼看就要胜利了,作者还借邓、芮二侯之口说道:“如今天时已归周主”、“今三分天下,周有其二,眼见得此关,如何可守?”“周日强盛,商日衰弱,将来继商而有天下者,非周武而谁?”然而就在这种形势下,黄飞虎等人却壮烈牺牲了。
最让人感到意外的是胡升被杀。本来在之前的叙述中,读者能深切感觉到胡升投诚于子牙的真诚心理,如第71回他劝胡雷投降子牙,后献降书给洪锦,让他转交子牙。这种叙述乍看起来,颇类同于苏护的投诚过程。那么,一般读者都会以为胡升最终会成为姜子牙的部将。尤其是读到子牙对洪锦等人说:“以我观胡升,乃是真心纳降也。公毋多言”时,按前面的叙事逻辑,读者都会轻易推断出:胡升投诚应该像苏护一样成功了。可是,结果恰恰相反,子牙说话出尔反尔,竟下令斩杀了胡升(第73回)。这种结果真令读者感到相当意外。从塑造人物的角度看,这有作者任意驱使笔下人物的嫌疑,造成人物思想、行为的割裂。但从反重复的角度看,它却是有积极意义的。正是这种不停地出乎意料的叙述形成了作品的反重复叙述,而这种反重复叙述所带来的变化莫测的命运和结果,会让读者普遍感到意外、新颖,从而吸引他们阅读。
或许在许多小说里,结果让读者颇感意外并不是件好事。譬如《红楼梦》的结局基本上早在第5回就已经预设好了,故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的最终命运都不会让读者感到特别意外,相反,还是意料之中的事。我们说,这是《红楼梦》在叙事艺术上的优点,它能暗设“草蛇灰线”,“伏脉千里”。那么,这种手法在重打斗或战争情节的小说里,是不是也适合呢?笔者的意见是:却也未必。笔者认为,不预设伏笔,让读者时时对事件的发展和结果感到意外,这种写法更适合于重打斗情节的小说的叙述。因为一旦打斗陷入一种模式,就会老是让读者想到结果,那就吊不起他们的胃口和兴趣,甚至会让他们感到厌倦,譬如《西游记》在这方面就要比《封神》逊色多了。《西游记》每一难的结果大多是孙悟空向观音菩萨求救,或是观音主动下凡收服妖魔来救他,得到观音菩萨的帮助最终才成功。这种叙述就有些模式化,让人感觉雷同。而《封神》就要好得多,它既有模式化叙述,让读者误以为它就是绝对的模式化打斗,但实际上又并非如此,它时不时地跳出和打破这种套路,让读者感到新鲜、意外,保持较旺盛的阅读精力与兴趣。这就是《封神》反重复和意外叙述的好效果,这种效果正如毛氏父子在《毛宗岗批评三国演义》第43回首评中所言:“文章之妙,妙在猜不着。”[7]
从上我们可以归纳出《封神》的意外叙事有这样几种: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置之死地而后生,身逢绝境,又出现生还的转机;生还之后,眼看胜利在望,但却意想不到的是又战死了。以上可见,作品某些局部看似有叙事上的套路,但其实它也经常变换叙事方式,力图回避模式化叙事,呈现出叙事过程的多样性和不可预见性。这是作品值得肯定的地方,也是它吸引读者的一大优点。
[1](明)钟伯敬.新刻钟伯敬先生批评封神演义[M].台北:天一出版社,1985.
[2](清)毛宗岗.读三国志法[A].(明)罗贯中著,(清)毛宗岗评订.毛宗岗批评三国演义[M].济南:齐鲁书社,1991.
[3]明清善本小说丛刊:第13辑·李卓吾先生批评三国志[M].台北:天一出版社,1985.
[4](美)浦安迪.明代小说四大奇书[M].沈亨寿译.北京:三联书店,2006.
[5]乐黛云,陈珏编.北美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名家十年文选[C].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
[6]杨义.中国叙事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