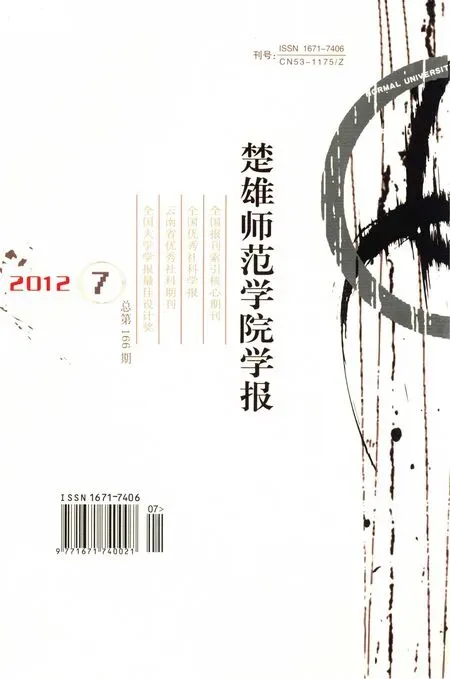论张承志创作的精神追求与文化转向*
唐丽君
(西南大学,重庆 400715)
从1978年发表第一篇小说《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到2010年的散文集《你的微笑》,张承志走过了三十余年的文学创作之路。随着宗教意识的增强,张承志的理想浪漫、浮躁凌厉之气在神秘玄奥、激烈深沉的宗教化叙述中消减,心灵踏上皈依宗教的回家之路。一直坚持特立独行之路是艰苦孤独的,享受鲜花掌声不是张承志的期许,他渴望听到的是各种文化齐奏出的和谐之音。张承志自称是一个流浪的旅人,他不安于一方,从北京到内蒙、新疆、西海固,从中国到日本、西班牙、阿拉伯、印第安美洲,寻着文化的痕迹,探究生命的尊严与意义。不安定的性格决定了他时刻待发的姿态,漂泊的灵魂却渴望得到安顿,对宗教的皈依不是张承志文学创作的终途,而恰是一个新的起点。
张承志的内心是充满矛盾的,“他一面赞美贫穷,厌恶富裕和豪华,另一面又诅咒恶劣的环境”。[1](P50)张承志对哲合忍耶的信仰无疑是真诚和坚定的,然而他的文学表达似乎又缺乏宗教的静穆与纯净,激烈的言辞是对现实世俗的十分在乎,其对现实的焦灼紧张、嫉恶愤怒、不同流合污正是在乎的表征。纵观其三十年来的整个创作,在浓郁的宗教情绪中流露的是作为知识分子对中心文化独奏的不满,对社会道德沦丧的愤怒;给予边缘弱小的极度关注(如蒙古牧民、哲合忍耶),体现的是张承志对人格尊严与正义公道的诉求。
一、青春岁月的牧歌
张承志在散文中表述说:“只是那个恼人的年代,它一下子就把人仍进草海”,[2](P206)“我们即便不是闯入者,也是被掷入者;是被六十年代的时代狂潮,卷裹掷抛到千里草原的一群青少年”。[2](P199)显然,张承志认为自己是被动地去亲近一个陌生的文化环境,以一个被抛入者的身份去审视自己的知青生涯。如果我们选择文学的方式去追忆过往的青春岁月,作品往往会过滤掉一些生活的苦痛,更多的是对曾经往事的浪漫记忆与理想追求。尤其是对一个返城后无法融入,也不屑去融入喧嚣都市氛围的孤高之人,面对浮躁社会的种种纷扰,以往质朴生活的丝丝温暖便会灌入心田。张承志的第一篇小说《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便是以知青生活为背景歌颂母爱的一曲赞歌,虽被作者说成是中学生作文习作,但这却拉开了他抒写草原的序幕。
插过队的知青都有着一本属于自己的知青史,不同的生活体悟和相异的性格气质会造成对特殊年代记忆的差异。张承志对草原生活的描绘有着独特的个体印迹,在辽阔草原的雄浑气势下抒写浪漫、英雄气概,在充满温馨叙述的话语中倾泻人生的忧愁,在面对自然灾难时感受生命的坚韧,这种叙述不同于全盘的控诉、批判。《春天》、《顶峰》、《铁儿罕·失刺》的主人公身上蕴藏着浓重的英雄主义气质,他们的目标是征服难以攀爬的人生高峰,即便是铤而走险也要一试。乔玛用自己的生命护卫了公社的马群(《春天》);铁木尔冒死把马群赶到了众人敬畏的“汗腾格里”(《顶峰》);铁儿罕·失刺用全家的性命做赌注,搭救后来得到成吉思汗称号的铁木真。青少年时期重走过长征路的张承志也是一派硬汉风格,这种刚强雄健在张承志对社会责任的担当与对公平正义的伸张中得以体现。当然强悍不是张承志的唯一气质,在草原额吉面前,他呈现的则是温和、含蓄的一面。
在张承志有关草原故事的小说中,大多存在一个带有作者身影的闯入者形象和一个慈爱、坚忍的额吉,如《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青草》、《黑骏马》、《金牧场》等作品。当张承志以一个外来知识青年的身份住进草原蒙古包,在与牧民的日常交往中,两种不同文化的碰撞火花被家庭化的关爱掩盖着。张承志的草原作品最打动人心的无疑是对那位宽厚仁慈、饱经沧桑、深沉缄默的额吉的诉说,这位草原女性使张承志模糊地悟到了禁忌,嗅到了神秘,这或许可以看作是张承志皈依哲合忍耶前的某种预兆。
无论是早期的小说还是后期的散文,蒙古草原已化作张承志内心的一种力量,张承志也坦诚地说草原是他文学生涯的诱因和温床,甚至是养育了他一切特征的母亲。[3](P84)的确,宽阔的草原、古朴的蒙古长调,温化了一颗狂躁不安、激越不定的心。张承志在大量的作品中深情地凝视曾经养育过他,给过他柔情关怀和生命触动的草原。《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既高歌赞颂慈善、伟大的额吉和润物细无声的亲情,又细腻刻画了牧民面对灾难时的坦然态度和平凡生命中蕴藏的一股韧劲。这篇小说虽然笔墨痕迹很重,情感倾泻直白,但作者对草原的真诚情感,牧民在自然灾害和生活灾难中的生命磨砺,却真真切切地触动人心。小说《青草》飘荡的是知识青年杨平向草原告别的离情别绪,杨平在草原上初尝了爱情的甜蜜与苦涩,他爱这片给过他心灵颤动的土地,但他又意识到自己终究不属于这里。正如千千万万的知青满怀壮志到乡下渴望一展身手,归来时载着一腔复杂情感沉入心底一样,杨平怀着对草原的眷恋和对都市的向往,对游牧生活的感念和对安定生活的追求的矛盾之心挥别草原。如果说离别草原是怀着对未来生活的朦胧期待,对草原文化还有着难以言说的隔膜、芥蒂,那么,在别后多年再次踏上寻找青春记忆之旅时,无论是之于作品中的人物还是之于张承志本人,曾经的痛苦和艰涩都化作心里的淡然,从前的文化隔阂也在岁月的冲击下打开。《绿夜》、《黑骏马》、《金牧场》等作品便有一条“闯入——离开——归来——离开”的人生历程,我们跟随小说的步调仿佛进入一个纯粹的寻梦之旅,然而梦却在变化了的现实中惊醒。也许梦的破灭不是坏事,梦的起点点染了年少时期的理想与激情,梦的终点止于对岁月更深层的现实领悟。美丽天使小奥云娜要长大,少女索米娅也要为人妻、为人母,这是亘古不变的生命定律。《绿夜》中的“我”悟出了只有奥云娜是对的,她比谁都更早地、既不声张又不感叹地走进了生活,她以不惊之态应对生活污沙的冲刷;《黑骏马》中的白音宝力格,愤怒于奶奶和索米娅用她们的宽容哲学对待黄毛希拉的暴行而离去,又在重游少年履历和目睹淡然面对生活的索米娅后,体味出了生命中的某些禁忌与坦然;《金牧场》中的“我”,在牧民坎坷、沧桑的人生中听出了生命中的玄奥和敬畏,在那首古朴的蒙古歌谣中沉醉:
黄羊的硬角若是断了
又有谁能接得上呢
命里的苦难若是来了
又有谁能躲得开呢[4](P272)
用养子与母亲的关系来表述张承志与草原的关系再贴切不过,张承志基本上是带着浓厚的汉文化印迹走进草原的,是草原文化启蒙了他,使他深藏在内心的民族文化意识苏醒,在某种程度上,他的宗教意识也被游牧文化中的神秘信仰所激活。额吉在张承志的内心已成为一种象征,她既是给予他知青年代无限关爱的慈祥老人,也是他成长道路上的一盏明灯。张承志确实是不遗余力地试图把“额吉”这个词输入汉语,在小说和诗歌中,温馨之情随着牧歌般的调子缓缓流出;在大量的散文中,草原额吉的形象在朴素的话语里触动人心。张承志从“草原额吉”身上所领悟到的宗教启示,在西海固得到淋漓尽致的实践。
二、信仰者的悲壮赞歌
如果对张承志入西海固前的社会处境和人生心境有所关注,便不会对他皈依哲合忍耶教感到突然和不解。带着对草原的敬畏与依恋,对都市的思恋与期盼,张承志返回了离别四年的城市。八、九十年代的中国正处在社会转轨期,市场化和现代化带来一系列价值观念的变化,当金钱与权力能够无限满足膨胀的欲望,精神追求在现实中破灭,理想、激情与正义、崇高在文学中消解,人就会容易走进绝望的深渊。面对现实世界与文学世界的双重危机,张承志选择宗教信仰作为抵抗精神堕落的一面旗帜。
张承志把与西海固的结缘看作是天命,他对主流意识形态和文学体制的有意疏离是向寄生与虚伪宣战,他试图从被人忽略的西北黄土高原寻找粗犷和本真的生命力。当然,张承志在一些作品中如《心灵史》、《离别西海固》等,用了过于绝对和偏激的话语批判了世俗化的生活,对常人合理化的平庸追求表示蔑视,这戳伤了众多凡夫俗子的心,毕竟选择世俗化的生活本来也无可厚非。然而张承志不愿随波逐流,不甘生活在价值涣散、信仰缺失的社会漩涡中,他必须找到一个支撑自己内心世界的立足点,使悬在喧嚣、繁杂境地中的灵魂得到安顿。他对社会风气堕落的愤怒,对知识分子沉默不语的申斥,正是一个肩负社会重任和承担心灵重负的知识分子的呼声。无论是哲合忍耶选择了张承志,还是张承志找到了哲合忍耶,仅从“为沉默的哲合忍耶立言”和“鄙视世俗、赞扬牺牲”这些层面,去理解张承志皈依哲合忍耶的行为和宗教化的文学创作,似乎又不能覆盖张承志为人与为文的丰富意义。不管怎样,张承志作为一个独特存在,他在现实中对信仰的执着,在文学中对信仰者的盛赞,就已经给这个信仰缺失的社会敲响了警钟。
从事过历史考古工作的张承志,对民族沧桑和人世沉浮有着更切肤的感受,冰封的大坂、炽热的沙漠、荒芜的戈壁都留下过他的足迹。恶劣的自然条件通常会叫人手足无措,但心中的信念却往往能使人绝处逢生。当然这种“逢生”不是战胜大自然,却是主动迎战后另外觅得的一种心境和姿态。小说《大坂》、《九座宫殿》既保持了草原作品中的浪漫激情,又在理想色彩的基础上,增加了生命残酷的强烈色调和近乎宗教的坚韧意志。《大坂》中的“他”,凭着惊人的意志力翻越了连探险家都望而却步的大坂;《九座宫殿》里的蓬头发和韩三十八,为寻找象征世外桃源的九座宫殿进过火狱般的沙漠,虽然都不得而返,但是那种亲身闯荡过才会有的心理积淀是旁观者所匮缺的。如果说《北方的河》、《大坂》、《九座宫殿》、《三岔戈壁》还只是对强韧生命意志的呼唤,《残月》、《黄泥小屋》、《黑山羊谣》、《海骚》、《错开的花》是张承志对宗教艺术化的表达,那么,《西省暗杀考》和《心灵史》则达到张承志文学宗教化书写的极致。
哲合忍耶在中国是一个沉默的群体,他们大多生活在自然环境恶劣的西北部地区,他们犹如一株被忽略了的野草,没有丰厚的养料,仅凭着一股对生命的原始信仰,便接过了一切磨难坚韧地存活下去。倘若张承志没有在作品中把哲合忍耶与清朝官方的百年抗争历史展现出来,没有把默默无言的哲合忍耶教徒写入文学,那么,在我们的视域中也就少了一个独特的文化参照系。张承志文学中的哲合忍耶,是否完全符合历史现实中的真实已变得不是那么重要,重要的是他向我们传达了一种信仰的力量:内心有念想的人,精神世界是富足的,只要生命中有所期盼,一切苦难似乎都可以承受。尽管宗教有时候会使人精神受麻痹,忘记了对现实的斗争,但是宗教的意义也正是在于它对人承诺了彼岸世界,这能增强人们向善的意念和承担痛苦的勇气。《残月》中的杨三老汉经历了流血斗争的日子,也度过了食不果腹的荒年。而人生就像那弯不圆的残月充满太多的缺憾和苦难,“若是心里没一个念想,谁能熬得住呢”,[5](P199)杨三老汉正是靠着心中这个珍贵的念想熬过了悠长的岁月。《黄泥小屋》中多次出现的“黄泥小屋”,正是内心美好信念的象征,老阿訇、苏尕三等人渴望的也就是一间能遮风避雨的心灵小屋,这是普通人对心理慰藉的正常需要。《黑山羊谣》、《海骚》、《错开的花》这三部诗体中篇小说,题材纵然是为人熟知的蒙古草原、西北黄土生活,然而张承志在文体上却作了一次新的尝试,《心灵史》难以归化的文体特征在这里已见端倪。张承志把沉淀在心底的过往进行重新编程,这三部诗体小说中的故事似乎在《黑骏马》、《金牧场》等作品中出现过,但是通过诗化的语言、神秘化的氛围、哲理化的叙述,其笔下的民间生活残酷却不乏美感,放纵又有所敬畏,容忍里凝聚反抗,这显示出的复杂、饱满的生命或许更能震撼人心。
《西省暗杀考》中教徒们为教殉命、提着血衣进天堂的信念,确实给不熟悉哲合忍耶群体的外人造成极大的心理冲击。小说主人公伊斯儿亲眼看着师傅、竹笔老满拉、喊叫水马夫当断则断地以身殉教,认为这三人“事情全美了”,而觉得自己活着是一种罪恶,他负疚于临终前也赚不上一件口换的血衫。“他们为了信仰的自由而一次次反叛,留下了让后世子孙敬仰的殉教者的拱北。”[6](P104)教徒以血为美、以牺牲为美的勇气和虔诚乃至狂热,令普通大众望而却步、胆战心惊。当然对哲合忍耶教徒的这些行为,我们可以表示不认同,但却不可轻视,他们对精神家园的追求和对灵魂信仰的坚守,令人敬重、引人深思。《心灵史》向世人展现了哲合忍耶两百余年的受难史、抗争史,七代导师面对的社会状况、时事局面不同,个人的性情气质、行为处事也各异,但是他们对哲合忍耶信仰的执着坚守与誓死护卫又是那么的一致。张承志选择了一个性格刚烈、充满血性的群体来阐释信仰、人性、人道、正义,这必然引起众人的疑虑和深思:殉教行为是教徒抢购天堂的入场券还是寻找生命的终极意义?为教牺牲与受命苟活是否具有同等的宗教意义?生活在俗界可否获得宗教的圣洁?当然,张承志凭六年与回民同呼吸的生活去讲述一个教派两百余年的历史,这有很大的难度,具体化到一些问题上难免存在可商榷之处,张承志在后来的散文中也多次更正原来的观点。在《心灵史》中,张承志的确对以苏四十三为首的流血圣战和哲合忍耶教徒在石峰堡集体殉教行为表示折服和赞叹,对十三太爷马化龙牺牲家族以换教徒性命表示钦佩,这也被一些评论家当作批评他有嗜血癖和暴力偏爱的明证。但是,不能忽视张承志在盛赞为信仰流血牺牲的行为时,敬重没有获得殉教者的名义和光荣的四月八太爷马以德,没有得到血衫活得卑微的汴梁太爷及把哲合忍耶劝导走向和平的宗教道路的沙沟太爷马元章;张承志也承认了哲合忍耶历史上的一类新人如李得仓,他就是一个生活在俗世的虔诚教徒。不是狭隘的民族意识和宗教情绪促使张承志的用语激越和用情激烈,而是张承志的性格气质决定了他选择表达责任与道义的方式,这种方式或许很多人不能接受,但是,请别轻易拒绝他为我们选择的文化参照系——哲合忍耶。
张承志带有宗教色彩的叙述不是要拒人于千里之外,而恰是渴望得到沟通;他对西海固的衷情不是狭隘,而是想敞开胸怀去拥抱更广阔的世界。其实,张承志对宗教的皈依并未阻隔他与世俗的联系,他对时弊的针砭,对文化霸权的反抗,对母体文化的反思,对和平、正义、团结的呼唤,都传达出了一个正直知识分子的忧思与担当。《心灵史》不是张承志创作的终点,而是一个新的出发点,《心灵史》之后,张承志告别虚构性的小说文体,而用真实、朴素、自由的散文展现他对社会、历史、文化的独到解读。
三、倾听文化乐章的多重奏
张承志小说主要抒写的是令他醉心的三块大陆——母亲般的蒙古草原、恋人般的新疆天山、父亲般的回民黄土高原,他的散文则把文化参照扩展到了世界各地。自从张承志宣告皈依哲合忍耶,宗教便成为审视和判断他为文、为人的重要尺度。然而张承志的意义绝不仅仅在于他皈依宗教的行为引人深思,而是他对文化痕迹的不懈追寻,对历史正义的不断追问,传达出他在谎言、歪曲、侮辱、不义面前不愿沉默的立场和姿态。他那颗躁动不安的心犹如一枚炸弹,随时都会被外界引爆。张承志是一个伊斯兰教徒,也是一个深具批判力的知识分子,这两重身份其实并不影响他对宗教的虔诚,也不阻碍他对俗世的关注,因为宗教与世俗并非完全阻隔。从1989年的《绿风土》到2010年的《你的微笑》,张承志的散文有12本之多,当然各篇的艺术水准参差不齐,有的缺乏节制,过于浮华激越,但是在消费化、平庸化的年代,其散文又以内容充满历史反思、文化批判和生命体验而显示出一种文学的审美深度和思想力度。
张承志对伊斯兰教的信仰从未动摇,对蒙古额吉的情感从未减弱,他在“后《心灵史》”时期,从未停止抒写给过他情感触动的土地。张承志的散文时间跨度长、地域跨度大,遍布世界各地的足迹正是他对真、信、美追求的痕迹。散文里频繁提到他在知青时期插队入住的一户牧民和到西海固时结识的一户农民,这些朴实民众的生活方式,让他深深地感到了贴近大地时的那种真诚。倘若说张承志的某些小说存在形象大于思想,主题先行的缺憾,那么,他在大量的散文中对挣扎在底层的边缘人血肉化的描写,则可作为了解草原、新疆、西海固人民真实生活的一扇窗。《二十八年的额吉》、《午夜的鞍子》、《与草枯荣》、《狗的雕像》、《公社的青史》等篇目是其草原情结的抒发,其中最感人的是跨越30年还隐藏在内心深处的情思,额吉已经过世,但草原留给作者的丝丝记忆却不曾离去;《夏台之恋》、《正午的喀什》、《面纱随笔》、《相约来世》、《嵌在门框里的耀眼绿色》等作品,是张承志在与维吾尔族、哈萨克族等兄弟民族亲密沟通中描摹的生命唯美画,倾泻出张承志对新疆神奇、魅惑的无法抵挡之情;《北方女人的印象》、《离别西海固》、《回民的黄土高原》、《旱海里的鱼》、《北庄的雪景》等散文,细腻地勾勒出贫瘠土地孕育的强韧生命,喷涌的是作者对回民黄土高原的情感热流。
不同地域的民族有着不同的文化底蕴,正是这种异质文化的魅力牵引着张承志奔赴各地。如果说张承志早期的作品因青壮年时期特有的热血豪情、硬健凌厉而缺少一些包容之心和节制之度,那么,经过岁月的打磨,近年来的散文在一贯尖锐、犀利的言辞中又多了几分有容乃大的气度。充满着长者关爱和希冀的散文《巴特尔和俊仨儿》,便是张承志对青年时代与蒙古族、回族两户家庭交往的追忆,他希望这两个不同民族的后辈能够进行文化沟通、交流。2005年的散文集《鲜花的废墟——安达卢斯纪行》和2009年的《敬重与惜别——致日本》,把文化的触角伸到国外,展示了张承志对安达卢斯文明和日本文化的历史洞悉力。
阿拉伯人把穆斯林治理下的西班牙唤作安达卢斯,《鲜花的废墟——安达卢斯纪行》主要抒发的是张承志的西班牙、北非之行的观感。他在开篇之作《两海之聚》中,对出自《古兰经》中的“两海之聚”这一宗教术语作了文化解读,认为“两海之聚”就是“和而不同”,对待不同的文明要持一颗宽容、平和之心。如《鲜花的废墟》、《恩惠的绿色》、《摩尔宫殿的秘密》等篇目,都是围绕这一文化心态的进而延伸。张承志走出了具体的教派、民族、国家的界限,更多地领略了伊斯兰文化的丰富内涵。散文集《敬重与惜别——致日本》,蕴含了作者对中国文化、日本文化存在的复杂、微妙关系的深思:“每逢与日本人相逢,总抑制不住——想即席清算甲午的屈辱、南京的虐杀;而每当和中国人谈及日本,又总控制不能——要滔滔讲解樱花的凋落、茶道的心境。”[7](P273)这便是中国人对日本难以言说的复杂心境。散文集子的第一章《引子:东苏木以东》,写了一位和张承志一样在东乌珠穆沁度过青春的日本老人服部幸雄,老人年轻时是日本关东军情报员,他以日本军人身份在内蒙古度过的生活已无法追溯,也没必要去追问,重要的是老人资助中国青海贫困孩子上学的行为显示出了人内藏的魅力。《三笠公园》反思了中国的“天朝大国”梦,日本对外的侵略行为和长崎、广岛所受的原子弹灾难向世人证明:在战争中没有胜者,人生再无别的前途,唯有自尊与敬人。《赤军的女儿》、《四十七士》、《亚细亚的“主义”》等篇章,也是用详实的资料给我们提出了一个思考的维度——日本的野蛮侵略史劣迹,中国的虚妄自大情节繁衍相互的不信任,日本曾是中国的毒药,也将是中国挽救自己文化的良方。正如一位日本作家对中日关系的形容:“我们相互握手,手掌之间渗出了血,即便努力忘却,还有不可忘却的东西”。[7](P276)
张承志的散文蕴含了浓厚的人文气息和强烈的社会担当意识,他痛感文明享受的狭窄,对热情与狂热、激情与危险作了反思。在2010年出版的散文集《你的微笑》的后记中他说“我却感到:并不像过去的少年说愁,我正当真地在把这本书——当作自己的最后一本来编辑。”[8](P256)这本散文的确带有总结性的意味,是张承志交给哺育了他的大地的一份答卷。《西海与东乌》写的是他最为惦念的两块土地——内蒙草原、西北黄土,其中,张承志对现代消费给传统乡土造成的文化信仰冲击表示担忧,指出文化的末路远比生计的难关可怕,文化和信仰一旦丢失就难以赎买。《太爷的拐杖》中,花寺派太爷的两根枣木拐杖留传在非花寺派教徒的手里,它饱含的深意之一是伊斯兰教的“和平”、“包容”精神。张承志在《救助自己》和《讲演河州城》中,对自己钟爱的西海固、中国穆斯林乃至整个伊斯兰世界提出大胆的批评和深沉的反思。恶劣的自然固然应当诅咒,但是在贫穷中丢掉尊严与高贵的精神,更是无法饶恕。《西马龙,西马龙》、《白磷火》、《游击时代》用语尖锐地对非人道的行为提出抗议,对为正义而战的人们表示了内心的敬重。
微笑是对待生活的一种心态,是在人生道路、生命历程中锻造出的坦然,张承志认为微笑更是战士的神情,因此,他在《你的微笑》中反复提到的那个“微笑”充满神秘的魅力。张承志在三十余年的文学创作中,对信仰、正义、自由、真知、美感的执着坚守无一丝本质的改变,最大的改变是他获得了宽容、和平的情怀。唱过了青春岁月的牧歌,谱写了信仰者的悲壮赞歌,在人生的暮年,张承志倾听着文化乐章的多重奏。我们说,寻找的文化参照系越多,作品的内涵就越丰富,正是在与不同文明的贴近中,张承志才生发出一种独立思考的能力和文学创作的魅力。
[1]邓晓芒.灵魂之旅——90年代文学的生存境界[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2.
[2]张承志.张承志散文[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3]萧夏林主编.无援的思想[M].北京:华艺出版社,1995.
[4]张承志.金牧场[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6.
[5]张承志.张承志作品精选[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6.
[6]何清.张承志:残月下的孤旅[M].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1997.
[7]张承志.敬重与惜别——致日本[M].北京:中国友谊出版社,2009.
[8]张承志.你的微笑[M].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