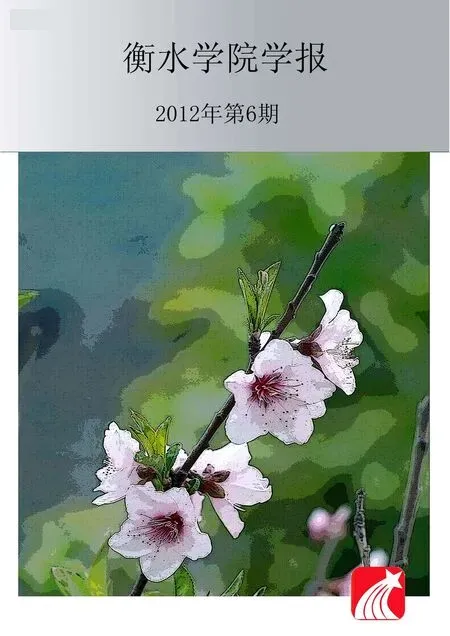董仲舒论学习态度与方法
周 桂 钿
(北京师范大学 哲学与社会学学院,北京 100875)
在学习上,董仲舒不主张只通一经。他认为只通一经,局限性太大,有些思想难以明白。而且各经有自己的特点,只通一经,就不了解其他四经的特点,同时也不了解这一经的特点。所谓“通一经”也就要打上引号了。是不是越博越好呢?也不是。书太多,学习不过来,负担太重,会产生厌烦情绪。而且,贪多嚼不烂,多则惑,没有思考的时间,死背硬记,不能理解。董仲舒主张以六艺为基本教材,所谓“简六艺以赡养之”,再辅以其他参考书,如《公羊传》等。对此,他说:“大节则知暗,大博则业厌,二者异失同贬,其伤必至,不可不察也。”(《春秋繁露·玉杯》)太博和太节,是两个极端,也是两种不同的错误倾向。循此错误倾向,必定会给学习带来伤害。正确的是介于两者之间,博节适度。究竟多少为适度?汉代以六艺为适度,宋明时代以“四书”“五经”为适度。可见这是随时代而变化的。如何研究,关系极大。汉时一些注经者注一经至百万言,少时入学,皓首才能穷一经。对于一般的学者来说,六经就太多了。所谓博节适度,只是一个原则,如何做到适度,何谓适度,都要视具体情况而定。不过,有一点则是需要肯定的,那就是要给学生留出足够的思考时间,因为“学而不思则罔”。
如何思考?董仲舒提出一个连贯法:“得一端而多连之,见一空而博贯之”(《春秋繁露·精华》)。他举例说:鲁僖公在乱世即位,亲任季子。“季子无恙之时,内无臣下之乱,外无诸侯之患,行之二十年,国家安宁”。季子“治内难以正,御外难以正”(《公羊传》鲁僖公元年),是个贤人。鲁僖公十六年三月,季子卒。以后鲁国乱难不已。到二十六年,派公子遂“如楚乞师”(《公羊传》鲁僖公二十六年)。鲁僖公没有变化而鲁国衰危,原因就是没有季子这样的贤人。鲁国是这样的,别的诸侯国也是这样。天下应该也都是这样。“此之谓连而贯之”(《春秋繁露·精华》)。他从这个连贯中得出结论:天下虽大,古今虽久,有一条共同的规律:“以所任贤,谓之主尊国安;所任非其人,谓之主卑国危。万世必然,无所疑也。”(《春秋繁露·精华》)。从此又推出,鲁庄公知季子贤而不能任用,导致国危;宋殇公知孔父贤而不能任用,自身遭弑。知贤不任,国危身弑。董仲舒对此深感痛惜,“此吾所悁悁而悲者也”(《春秋繁露·精华》)。此外,董仲舒还联系《春秋》中的逄丑父代齐顷公赴难,齐桓公执陈国大夫辕涛涂,鲁季子追庆父,吴王阖庐请吴季子任国君 4件事,阐述“贵志”的道理。董仲舒提出“志邪者不待成”“本直者其论轻”两项原则。董仲舒对逄丑父和祭仲的事阐述经与权的关系,以及行权的原则。董仲舒以春秋时代的史事进行联系分析,连而贯之,阐述一些理论问题,既有唯物主义成分,又含辩证因素,颇多合理性,因此,司马迁说:“故汉兴至于五世之间,唯董仲舒名为明于《春秋》,其传公羊氏也。”(《史记·儒林列传》)
学习《春秋》,董仲舒极端强调深入思考。圣人的思想是非常深刻的,不认真思考,就不能领会。所谓微言大义,就是在简单的辞的后面包含深刻复杂的意义。“辞不能及,皆在于指,非精心达思者,其孰能知之!”(《春秋繁露·竹林》)大史学家司马迁也有同感,他说:“非好学深思,心知其意,故难为浅见寡闻道之。”(《史记·五帝本纪》)浅见,是思想肤浅;寡闻,指所知古今之事甚少。好学深思与浅见寡闻是相对的。从此可见,董仲舒与司马迁都提倡深思好学。如果不好学,那就无法“多连”“博贯”地思考。有的人认为自己素质差,天赋不足,想不到那些复杂的问题。董仲舒引孔子的话说:“未之思也,夫何远之有?”(《春秋繁露·竹林》)只是没有深入思考,哪有什么达不到的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