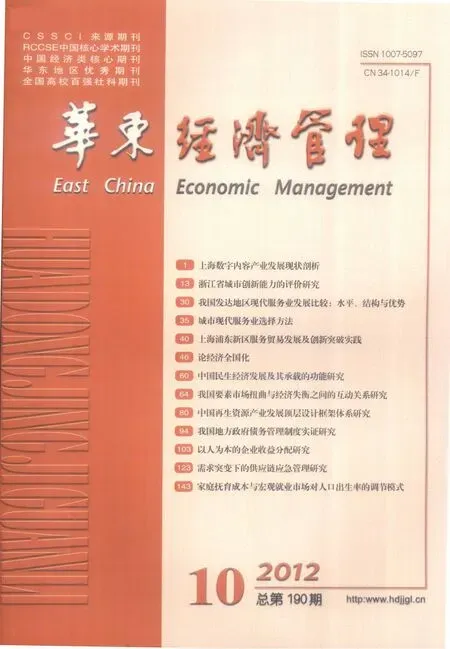我国发达地区现代服务业发展比较:水平、结构与优势
侯祥鹏
(1.南京大学 经济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3;2.江苏省社会科学院 财贸研究所,江苏 南京 210013)
一、引 言
理论研究与国际经验均表明,现代服务业发展水平是一个国家和地区经济、社会现代化程度的重要标志。早在1992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就做出了《关于加快发展第三产业的决定》。2007年3月,《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服务业的若干意见》[国发〔2007〕7号]出台,强调“重点发展现代服务业”。2011年3月,国家“十二五”规划提出“把推动服务业大发展作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战略重点”。在经济发展方式转型以及发展服务业上升为国家战略的大背景下,全国各地相继大力发展服务业尤其是现代服务业。但各地区的资源禀赋不同,在发展现代服务业的过程中必须基于自身优势,走因地制宜的发展道路。江苏、浙江、山东、广东四省是我国经济最为发达的省份,经济发展方式转型与服务经济发展理应走在全国前列。因此,分析这些发达地区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水平、结构差异与比较优势,不仅有助于认清发达地区自身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形势,而且对全国其他地区亦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二、现代服务业的内涵与范围
(一)现代服务业的内涵
“现代服务业”是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词汇。其最早出现在1997年9月中共十五大报告中。中共十五大报告认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产业结构转换特征是“由农业人口占很大比重、主要依靠手工劳动的农业国,逐步转变为非农业人口占多数、包含现代农业和现代服务业的工业化国家”。此后,2000年10月中共十五届五中全会提出,“要发展现代服务业,改组和改造传统服务业”。2002年11月中共十六大报告提出,“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提高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2007年10月中共十七大报告提出,“发展现代服务业,提高服务业比重和水平”。
随着我国经济转型升级过程中现代服务业重要作用的逐渐体现及其逐步上升为国家发展战略,现代服务业的重要性愈来愈被社会各界认识到,并成为学界研究的焦点之一。朱晓青、林萍(2004)[1];庞毅、宋冬英(2005)[2];王瑞丹(2006)[3];江静、刘志彪 (2009)[4];裴长洪 (2010)[5];闫星宇、张月友(2010)[6];任英华、游万海、徐玲(2011)[7];李大明、肖全章(2011)[8]等分别从不同角度阐述了现代服务业的内涵,尽管大家看法不尽一致,但关于现代服务业的“三新”、“三高”的基本特征几乎已是共识。“三新”指新技术、新业态、新增长方式,“三高”指高人力资本含量、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
总体来说,现代服务业与传统服务业的最大不同主要是两点,一是技术基础,二是微观管理基础。[9]本文认为,现代服务业就是利用现代技术手段和管理方式生产或提供服务的部门。在理解现代服务业概念时,尤其需要注意两点。一是融合性。即不能将服务业人为割裂为传统与现代[10]。看似传统的服务业也会包含现代的要素,例如零售业中的互联网零售方式;而看似现代的服务业有时也离不开传统的要素,例如现代物流在利用先进的技术、设备与管理的同时,仍然需要借助传统的运输方式甚至某些时候还离不了肩挑手扛。二是动态性。即现代服务业与传统服务业之间没有一成不变的界线[11]。传统服务业通过新技术、新管理方法改造后可以转化为现代服务业,而随着历史的推移和新技术的出现,“新”的现代服务业会不断涌现,当前的“现代服务业”也会逐步蜕变为“传统服务业”。
(二)现代服务业的范围
目前学界对现代服务业范围尚无统一的界定。从实证分析的角度出发,对现代服务业范围的界定必须同时考虑现代服务业的内涵和数据可得性。根据出发点的不同,可将现有文献对现代服务业范围的界定分为两种方式。如表1所示。
方式一,从现代服务业的内涵出发,兼顾数据可得性。即基于现代服务业的本质特征,整合现行统计体系的行业门类,形成现代服务业体系。这种界定方式更贴近于现代服务业的本质,但根据现有的公开统计数据,很难剥离出完全符合划分标准的数据,并且各自统计口径存在不一致的情况,因此这种界定方式在实际运用中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更多地是一种理论探讨,如徐国祥、常宁(2004)[12]对现代服务业统计标准的设计,或者适于地区和行业的个案研究,如朱晓青、林萍(2004)[1]对北京现代服务业的研究,而不适用于不同地区、行业的比较。
方式二,从数据可得性出发,兼顾现代服务业的内涵。即在现有统计体系的基础上,依据现代服务业的本质特征来选择和剔除部分行业,构成现代服务业体系。现行行业分类标准即《国民经济行业分类》将国民经济行业划分为门类、大类、中类和小类四级,尽管这种分类并非是以“传统”和“现代”为标准,但行业中类和小类在某种程度上更能体现“现代”与“传统”的区别。由于现有的公开统计数据基本以行业门类为主,这种界定方式也只能以此为据,因此所界定的现代服务业范围有过广之嫌。但由于数据可得性和可比性较好,这种方式在跨地区、跨行业比较中得到了较多的运用。为了能有效地进行地区比较,本文对现代服务业范围的界定也主要基于这一方式。
基于方式二,并结合前文的理论分析,本文将现代服务业界定为如下10类行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金融业,房地产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教育,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表1 现有文献关于现代服务业范围的界定
三、方法、指标与数据
(一)方法与相关指标
目前研究文献多以各类指数进行优势比较,其中使用最为广泛的是美国经济学家巴拉萨(Balassa)于1965年首创的显性比较优势指数(revealed comparative advantage index,RCA指数)。其计算公式为:RCAik(t)=Qik(t)/Qk(t)。其中,Qik(t)表示在t时期i地区k行业产出在i地区总产出中所占比重,Qk(t)表示k行业产出在全国总产出所占比重。如果RCAik(t)大于1,则表明i地区在k行业的生产具有比较优势;反之,RCAik(t)小于1,意味着i地区在k行业的生产具有比较劣势。但这一指标存在固有缺陷。正如Benedictis&Tamberi(2001)[21]所指出的,其值是非对称性的,这意味着衡量比较优势和劣势程度的标准不对称。为了克服这些缺陷,这里使用Dalum et al(1998)[22]的对称性显性比较优势指数。其计算公式为:RSCA=(RCA-1)/(RCA+1)。RSCA的值域为[-1,1]。RSCA大于0,表明i地区在k行业的生产具有比较优势;反之,RSCA小于0,则表明i地区在k行业的生产具有比较劣势。与RCA相比,RSCA是一个对称性指标,更有利于对各行业比较优势和比较劣势的程度进行定量比较。

(二)数据
2002年10月,国家统计局对旧国家标准《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与代码》(GB/T4754-94)进行了修订,其中重点是加强了对第三产业的分类,新增了大量服务业方面的类别,并将标准名称改为《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02)。2003年5月,国家统计局再次发布了新的《三次产业划分规定》(国统字[2003]14号)。考虑到统计口径的一致性,本文的分析时限为2004—2010年。数据主要来源于相关年份《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第三产业统计年鉴》《江苏统计年鉴》《浙江统计年鉴》《山东统计年鉴》《广东统计年鉴》等。另外,由于有些年份的统计年鉴未公布详细的行业数据,所以部分年份数据缺失。
四、苏浙鲁粤现代服务业发展水平与结构差异
(一)现代服务业的整体水平
从现代服务业增加值总量规模来看,四省占全国总量的35%左右。近年来四省排名基本保持广东、江苏、山东、浙江的顺序。如表2所示。2010年四省现代服务业增加值分别为广东12896.00亿元,江苏10273.54亿元、山东7751.80亿元和浙江7676.20亿元。四省中增长最快的是江苏,年均增速高达23.94%。
从现代服务业增加值占地区GDP比重来看,广东和浙江较高,2010年分别为28.03%和27.69%,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进一步地,这两省现代服务业增加值占服务业增加值比重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而江苏和山东占比稍低,但江苏增长很快,2004—2010年,江苏现代服务业增加值占地区GDP比重和占服务业增加值比重分别提高了5.91个和5.44个百分点;相比之下,山东提速则稍显缓慢,分别提高了2.66个和0.05个百分点。

表2 四省及全国现代服务业整体水平
(二)现代服务业的部门结构
现代服务业部门结构反映的是现代服务业内部各行业的构成及其比例关系。四省既有极大的相似性,又存在一定的差异。2010年四省比重居前三位的都是金融业,房地产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但是,江苏占比最高的是房地产业,从2004年的18.85%提高到25.32%;浙江和广东的金融业比重有大幅度提高,浙江从2004年的19.05%(位居第二)提高到30.31%(位居第一),广东则从11.46%(位居第五)提高到20.62%(位居第二);山东占比最高的是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但已从2004年的30.42%下降到25.43%。此外,省际比较来看,除了广东的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以及山东的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占比较为突出外,四省其他现代服务业部门构成差异不大。如表3所示。
为了量化四省现代服务业部门结构的差异,我们利用增加值份额计算了四省两两之间的K指数。如图1所示。K指数值最大为0.3997(2007年山东—广东),最小为0.1562(2004年江苏-浙江),这进一步表明四省之间现代服务业部门结构差异不大。这也意味着地区分工程度不高。从发展趋势来看,存在一个有趣的现象,江苏、浙江、山东之间K指数趋于上升,这也许暗示着这三省之间开始了错位发展。而广东与其他三省的K指数则趋于下降。

图1 2004—2010年四省现代服务业地区间专业化指数

表3 四省现代服务业部门结构(%)
(三)现代服务业的资本投入
我们从研发经费和固定资产投资这两个方面考察现代服务业的投入情况。
技术创新和研究开发是推动现代服务业升级的重要力量。如表4所示,2009年,广东现代服务业R&D经费投入总量最大,为91.67亿元;浙江现代服务业R&D经费占全省R&D经费比重最高,为15.98%;江苏现代服务业R&D经费与相应GDP之比最高,为1.31%;而山东各项指标均最小。尽管从总量来看,四省现代服务业R&D经费投入合计占全国总量的15.31%,但从投入力度来看,四省几乎都不及全国的一半,与发达国家服务业R&D投入强度[24]差距则更大。
从固定资产投资来看(见表5),广东总量最大,2010年为9470.35亿元,并且广东和浙江的投资占比均超过全国平均水平,2010年分别为60.62%和54.74%。而江苏尽管投资总量有所增加,但占比基本徘徊在40%左右,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之下,山东现代服务业固定资产投资可谓异军突起,投资总额直线上升,2010年比2005年增加了2.5倍,占比提高了11.2个百分点。

表4 2009年四省及全国现代服务业R&D经费投入

表5 2005—2010年四省及全国现代服务业固定资产投资
五、苏浙鲁粤现代服务业优势比较
(一)现代服务业整体优势比较
如图2所示,四省RSCA排序依次是广东、浙江、江苏、山东。只有广东历年RSCA均大于0,表明广东现代服务业在全国具有比较优势,而其他三省比较优势不明显。从发展动态来看,四省的RSCA均表现出显著的上升趋势。其中,浙江已于2008年越过零线,在全国表现出比较优势;江苏上升势头最快,从2004年的-0.1373升高到2009年的-0.0707;山东则上升较缓,从-0.1850升高到-0.1641。

图2 2004—2009年四省现代服务业RSCA指数
(二)现代服务业细分行业优势比较
我们计算了四省现代服务业各自10个细分行业的RS⁃CA。如表6所示,四省现代服务业大部分细分行业的RSCA小于0,意味着在全国不具有比较优势。
(1)四省之间比较。就四省而言,如果某省某一行业的RSCA平均值最大,则该行业为该省的优势行业;反之,如果某省某一行业的RSCA平均值最小,则该行业为该省的劣势行业。据此,广东有6个优势行业,0个劣势行业;江苏有0个优势行业,1个劣势行业;浙江有3个优势行业,1个劣势行业;山东有1个优势行业,8个劣势行业。详见表6。综合来看,广东优势较为突出,山东劣势较为明显,江苏和浙江发展则较为均衡。
(2)各省内部比较。我们以各省为分析单元,将其现代服务业细分行业的RSCA均值、占地区GDP比重均值、年均增速等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并根据是否大于0加以区分,如表7所示。各省现代服务业细分行业发展既有相同之处,又有一定的差异性。如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在四省均比重大、增速慢,但在山东处于相对优势地位,而在其他三省则处于相对劣势地位;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在四省均比重小,且处于相对劣势地位,但在江苏、浙江增速快,在山东、广东增速慢;金融业在四省中均处于相对优势地位,且比重大、增速快;与之类似的是房地产业,但江苏、浙江、山东增速快,而广东增速慢;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在四省均比重小、增速慢,但在广东处于相对优势地位,而在其他三省则处于相对劣势地位。

表6 四省现代服务业细分行业RSCA

表7 四省现代服务业细分行业发展特点
六、结论与建议
通过上述比较,我们对苏浙鲁粤四省现代服务业发展可以得到如下认识:一是四省服务业整体规模位居全国前列,但比较优势不明显;二是四省现代服务业投入略显不足;三是四省现代服务业部门构成差异不大;四是四省现代服务业细分行业在全国比较优势亦不显著,但发展各有特点。
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已是各地共识,今后必将掀起新一轮如同工业领域一样的激烈竞争。发达地区现代服务业投入不足,这大概主要缘于发达地区的高度工业化挤占了过多的资源,从而掣肘现代服务业的加快发展。各地应加大投入力度特别是研发投入力度,为现代服务业的加快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同时应因地制宜,重点关注那些现在比重小但增速快的行业,将其培育为现代服务业新的增长点。
[1]朱晓青,林萍.北京现代服务业的界定与发展研究[J].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04,(4):41-46.
[2]庞毅,宋冬英.北京现代服务业发展研究[J].经济与管理研究,2005,(10):40-43,80.
[3]王瑞丹.高技术型现代服务业的产生机理与分类研究[J].北京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1):50-54.
[4]江静,刘志彪.政府公共职能缺失视角下的现代服务业发展探析[J].经济学家,2009,(9):31-38.
[5]裴长洪.我国现代服务业发展的经验与理论分析[J].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10,(1):5-15.
[6]闫星宇,张月友.我国现代服务业主导产业选择研究[J].中国工业经济,2010,(6):75-84.
[7]任英华,游万海,徐玲.现代服务业集聚形成机理空间计量分析[J].人文地理,2011,(1):82-87.
[8]李大明,肖全章.现代服务业区域发展差异因素研究[J].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11,(4):17-22.
[9]顾乃华.对现代服务业基本内涵与发展政策的几点思考[J].学习与探索,2007,(3):123-126.
[10]徐旭.现代服务业理论分析框架初探[J].生产力研究,2010,(1):24-26.
[11]李江帆.产业结构高级化与第三产业现代化[J].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4):124-130.
[12]徐国祥,常宁.现代服务业统计标准的设计[J].统计研究,2004,(12):10-12.
[13]钟云燕.现代服务业的界定方法[J].统计与决策,2009,(6):168-169.
[14]张华平.河南省现代服务业发展评价及对策研究[J].经济经纬,2011,(2):65-69.
[15]赵惠芳,王冲,闫安,等.中部省份现代服务业发展水平评价[J].统计与决策,2007,(21):83-85.
[16]赵书华,王雅贞.北京与上海、广州现代服务业比较[J].江苏商论,2007,(2):84-86.
[17]曹建云.广东现代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研究[J].特区经济,2010,(11):34-36.
[18]赵琼,杨志华.我国现代服务业利用FDI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1997-2007年的数据[J].经济问题,2010,(5):45-49.
[19]朱茜,陈丽珍.长三角一体化背景下江苏省现代服务业发展对策研究[J].特区经济,2011,(11):54-56.
[20]陈丽珍,赵美玲,肖明珍.基于层次分析法的江苏现代服务业主导产业选择[J].商业研究,2011,(6):44-49.
[21]Luca De Benedictis,Massimo Tamberi.A Note on the Balas⁃sa Index of Revealed Comparative Advantage[R].Working Paper,2001.
[22]Dalum B,Laursen K,Villumsen G.Structural Change in OECD Export Specialization Patterns:Despecialization and Stickiness[J].International Reviews of Applied Econom⁃ics,1998,12(3):423-443.
[23]保罗·克鲁格曼.地理和贸易[M].张兆杰,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73.
[24]段小华,柳卸林.服务业R&D的投入强度及其国际比较[J].中国科技论坛,2005,(4):131-1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