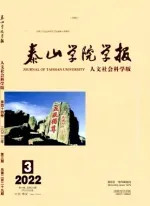人才茂盛——元代大都杂剧繁荣的必备条件
傅秋爽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北京 100101)
中国历史文学之高潮,总是以一两位或数位创作成就堪称巅峰的大作家为代表,与之相伴而生或稍前稍后,总是一批优秀作家集中涌现,他们相互辉映,共同组成一个时代璀璨的文学星空。元曲亦复如此,杂剧这种以宋杂剧和金院本为借鉴,集音乐、舞蹈、歌唱、朗诵多种艺术于一身的新兴文艺形式,金末元初终于成熟。无论是剧本创作,还是舞台表演,都臻于完美,出现了关汉卿、珠帘秀这样卓荦冠群的大家,他们分别为其各自领域之翘楚、为领军、为旗帜。在其周围,是一个群星荟萃蔚为壮观的群体。
钟嗣成《录鬼簿》著录的大都籍杂剧作家有20多位。在元大都围绕着关汉卿、马致远、王实甫这些杂剧创作大师周围,有庾天锡、王仲文、杨显之、纪君祥、费君祥、费唐臣、张国宾、石子章、李宽甫、梁进之、孙仲章、赵明道、李子中、李时中等一大批才情豪健的剧作家。他们相互砥砺,切磋技艺,启发思想,彼此促进,共同开创了大都杂剧艺术的鼎盛时代。
作为一门综合艺术,元杂剧与以往纯文学创作最大的不同是,作家个体无法独立完成,因为剧本只是杂剧艺术的一部分,必须与艺术家通力合作,通过念唱作打的舞台表演,观众接受审美,才能实现其完整过程。与这些优秀杂剧作家同时代、密切合作的是一大批同样优秀杰出的戏剧表演艺术家。这是一个人数众多、基础广泛的群体。夏庭芝的《青楼集志》称:“我朝混一区宇,殆将百年,天下歌舞之妓,何啻亿万!”《马可·波罗游记》称元初大都城中的妓女就有两万五千余人,其中相当部分是艺妓。这些数字或估算,未必精确,但当时艺伎之多,当是可信的。其中以杂剧表演艺术见长的不乏其人,他们集中在大都、真定、平阳、东平、杭州这些大中城市,为当时杂剧艺术的繁盛做出了杰出贡献。《青楼集》所记载的珠帘秀、顺时秀、南春宴、天然秀、国玉第、天锡秀、平阳奴、郭次香、韩兽头、赵偏惜、王玉梅、李芝秀、朱锦秀、赵真真、李娇儿、张奔儿、英蓉秀、翠荷秀、汪怜怜、顾山山、大都秀、帘前秀、燕山秀、荆坚坚、王心奇、李定奴、帽儿王等人都是杂剧表演的一代名伶。大都是鼎盛时期全国杂剧中心,集中了杂剧艺术家中最为杰出的一批。《青楼集》等文献记载,元时大都的戏剧艺人已知有44 人,其中绝大多数都是以搬演杂剧和吟唱散曲闻名。[1]他们是珠帘秀、张怡云、曹秀娥、解语花、南春宴、李心心、杨奈儿、袁当儿、于盼盼、于心心、燕雪梅、牛四姐、周人爱、玉叶儿、瑶池景、贾岛春、萧子才、王玉带、冯六六、王谢燕、王庭燕、周兽头、刘信香、天然秀、国玉第、玉莲儿、樊真真、赛帘秀、王巧儿、大都秀、一分儿、孙秀秀、燕山秀等。
这些杂剧创作者、表演艺术家的集中出现,既是元杂剧繁荣的标志,也是元杂剧繁荣的原因。专门人才的聚集、成长、合作,为大都杂剧走向鼎盛提供了充足的前提条件。那么,是怎样的机缘巧合使得这些优秀的杂剧作家、表演艺术家像种子一般,不约而同地撒落、聚集、停留在大都,这里有怎样的文化土壤和长成条件,提供了怎样的生态环境,使得他们能够就此落地生根,如雨后春笋般迅速长成。并以不同的创作个性,多样的表演风格,像一棵棵形态各异的参天大树,开花结果,共同组成蔽野森林,如云花海,将大都剧坛装扮得姹紫嫣红?
首先是杂剧创作人才。杂剧的创作人才大致分为两类,一种是“沉抑下僚”的文人,一种是书会教坊中人。来源有以下几种情况,一种是“楚才晋用”“借才异代”,位居“元曲四家”之首的关汉卿等即为由金入元之人。生长于大都,一生创作杂剧60余种,在当时杂剧界享有极高威望,王国维在《宋元戏曲考》中赞美他“当为元人第一”。与他同样情况的还有梁进之、杜善夫等。还有一种情况是“开放引进”。白朴、郑光祖这些最优秀的剧作家原籍虽非大都,但有许多创作活动也在大都。如白朴,祖籍山西,后来定居真定(今河北正定),但是多次前来大都,访游、会友,参与杂剧交流活动。郑光祖为元曲四大家之一,生活创作主要在山西平阳,但与大都杂剧剧坛同样联系紧密。第三种情况最多,即“本朝本土”作家迅速成长。创作了元代杂剧的颠峰之作《西厢记》的王实甫、创作有《汉宫秋》、《青衫泪》的马致远,创作了世界著名悲剧《赵氏孤儿》的纪君祥以及杨显之、王伯成、赵明道、张国宾、秦简夫、庾天锡、王仲文、梁进之、费唐臣、石子章等都是大都成长起来的著名剧作家。
他们共同成长于非常特殊的历史时代:金元交替,元兴宋亡。元朝是在草原游牧民族政权基础上,吸纳融汇了众多被征服国家和地域政治、经济、文化特色建立起来的强大帝国。它在消灭金、宋政权的过程中,由于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与中原传统政权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所以对于整个社会的震动比历史上任何一次改朝换代都要剧烈而深刻得多。社会生活的剧烈震荡,带来文化基因的突变。随着宋、金的覆亡,那些被征服地域腐朽、没落、僵化、专制、严密的传统统治思想格局遭到荡涤,蒙古政权适宜全国统治的新的思想统治格局尚未完备地建立起来。整个社会处在转型期,处在新旧交替的空白间隙,处在思想强权尚未建立的薄弱环节。新的政治制度,生产模式,社会管理方式,和由此产生的各种与旧有传统格格不入甚至完全相悖的新思想、新道德、新观念由此获得了滋生、发展、传播。与历史的以往是如此惊人的相似,这些新思想、新道德、新观念总会通过某种特定的形式在文学中表现出来,而恰在此时,成熟的杂剧形式成为时代的必然选择。如果说唯物史观的基本结论是时势造英雄,那么元代文学史,则是时代成就了一大批最优秀的杂剧作家。
燕京作为前朝故都,无论是辽之南京还是金之中都,它都是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数百年的历史中,其文化、教育、科技都得到了优先发展,尤其是历代统治者对于京城教育发展的重视,以及科举对人才的吸引,使得这里人们的文化素养得到不断的培育和提高,而且在吸纳人才的能力方面,有着其他地方无法比拟的优势。文化积淀已经比较深厚,文化人才比较茂盛。所以,这里不仅是行政枢纽,文化中心的地位也持续不断地得到加强。文坛不但人物荟萃,而且对社会风气影响深刻。李庭《送荆干臣诗序》(《寓庵集》卷五)通过评论诗人荆干臣,进一步对大都的文化氛围作了介绍:“干臣家世东营,虽生长豪族,能折节读书。幼游学于燕,夫燕,诚方今人物之渊薮也。变故之后,宿儒名士往往而在,干臣朝夕与之交,得以观其容止,听其议论,切磋渐染,术业愈精。一旦崭然见头角,遂为明天子所知……出使万里之外。”在中统、至元年间,大都不但有原金朝的社会名流以不同身份出入,南宋的大理学家赵复等也在此传徒授业。元世祖不断在辇下拔擢人才,并派大臣到新近的占据之地索罗各类英才俊杰,这使得大都科学、技术、教育、文化、艺术相当活跃,整体文化素养迅速提高。蒙古政权统治后,大都作为政治中心,作为一个迅速壮大的北方商业中心,是多种文化汇集融合的核心地带。这种环境对于具备一定文化素养、又较少保守思想,善于接受新生事物的年轻士子的转型、成长非常有利。他们只是需要一个契机,这就是新文化领军人物的出现。关汉卿、马致远、王实甫共为“元曲四大家”中人,他们的成功,不仅为这门新兴艺术开辟了前进的道路,作为杂剧领军人物,也对其他杂剧作家的成长树立了楷模,起到了示范的作用,带动了一大批作家的成长、成熟。这些领军人物的水准,决定着整个元代包括大都剧坛的地位与影响。这真是一个有趣的悖论:大都依靠科举吸引聚集人才收效甚微,但正是科举的崩坏,大都却前赴后继地成长起大批最优秀的杂剧人才。
杂剧创作中教坊中人历来很少受到关注,这是因为第一,他们的成就整体上要逊色于文化素养较高的士人,所以历史的身影长期为关汉卿等一代巨匠的光芒所掩;第二,受到某种偏见影响,史家不传。赵孟頫将杂剧作家关汉卿等士人目为“鸿儒硕士骚人墨客”,认为他们是“良家”,而对教坊中人一律视为“娼优”。[2]但他们对于杂剧成熟、发展的推动作用是不应该被忽视的。陶宗仪《辍耕录》中说:“金有院本、杂剧、诸宫调,院本、杂剧其实一也。国朝,院本杂剧始厘而二之。”元人胡祗遹在《赠宋氏序》中也说“近代教坊院本之外,再变而为杂剧。”金杂剧或曰金院本在体制上与宋代官本杂剧基本一致。《梦梁录》就曾说宋官本杂剧的特点是“全用故事,务在滑稽”。金院本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了这种特点。而将这些血缘基因传承下来的应该就是那些教坊中人。他们或者在金宋战争中被金从宋劫掠索要来到北方,将宋官本杂剧的体式带到了金朝,直接或者经过与金原有的戏剧形式相结合,形成了金院本,在传承的过程中,由于地域文化特色不同,审美习惯不同,不断融入新的元素,经过长时间的发展变化,就使得原本从宋官本杂剧移植或者借鉴而产生的金院本有了自己鲜明的有别于宋杂剧的特色。元杂剧的产生,虽然具有革命性的意义,但它同样并非天外陨石,瞬间划破元朝寂静的夜空,而是借鉴了金院本的体式,大力发扬了其“全用故事”部分,重视情节的曲折,人物的塑造,思想的饱满和内容情感的丰富充实,却极大削弱了其插科打诨“务在滑稽”部分。也就是说元杂剧虽具有崭新的革命性意义,但仍与金院本、宋官本杂剧有直接或间接的血脉联系。这种基因的保留与传承正是依靠那些教坊中人。从宋官本杂剧,到金院本,再到元杂剧,是一个漫长而曲折的过程,在这期间,不可能只有演员而没有编剧。事实上,各种史料对此也都有间接的透露。如《辍耕录》中就保留了大量的金院本名目,虽然院本本身并没有流传下来,编剧的名字也没有流传下来,但仅仅就是这些名目,就足以说明在整个中国戏剧发展史上这些编剧同样功不可没。虽然最终金院本为元杂剧所替代,但是并不能由此抹杀他们在传承中的作用,没有他们的前导,没有他们对“全用故事”的保留,元杂剧的辉煌可能还要迟到很多年。事实上,元代杂剧中有些剧目情节就保留了金院本的痕迹。《辍耕录》记载的“诸杂大小院本”中有《双斗医》的名目。元杂剧《西厢记》就直接借鉴了金代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甚至可以说,没有彼《西厢》,就难有此《西厢》,其中不少院本的痕迹还是很明显被保留了下来,如杂剧《西厢记》第三本第四折中写张生因相思成疾,老妇人让和尚去请太医,剧本中就特意注明:“洁引净扮太医上,双斗医科范,下。”说明扮演和尚的“洁”与由“净”这种行当所扮演的太医要表演“双斗医”的一段。即使在元代,许多地方仍有金院本的演出,如由金入元的杜善夫散曲在《庄家不识勾栏》中就写道:“前截儿院本调风月,背后么末敷演刘耍和。”而到元明之际,杂剧剧本《蓝采和》中,人物的场次中还有“旧院本我须知,论同场本事我般般会”之语可为佐证。“么末”同“麽么”,在《辍耕录》记载金院本时便有“院么”一项,可见也是金院本的一种。这说明从元初到元末金院本的演出并没有彻底销声匿迹,还经常在杂剧或者其他的演出场合作为前后或者过场点缀出现。同时也不排除这些金院本创作者中的一少部分人,也会转而进行元杂剧的创作。因为他们毕竟是行内人,对于艺术规律较之新入行的士人有更多的把握。
对杂剧创作产生重大影响的还有杂剧演员,《录鬼簿》就记载说艺人赵文敬、红字李二和花李郎等都有杂剧剧本创作。红字李二和花李郎都是金代教坊著名演员刘耍和的女婿,也都是书会中人,他们二人与马致远、李时中四人共同合撰了杂剧《黄粱梦》。生活在大德前后,艺名喜时营,又称张酷贫的张国宾(一作张国宝),是大都著名杂剧人士,曾任教坊勾管。擅长作曲,所作通俗易懂,民间生活气息浓郁。代表作《汗衫记》,讲述了一起谋杀案的前因后果,情节曲折,人物生动,是元杂剧中之名作。《太和正音谱》将其作列入“娼夫之词”,可见他还具有艺人的身份。杨驹儿是著名的艺妓,据《录鬼簿》(曹寅刊本)记载,杨驹儿不但是表演家,而且还曾经创作过杂剧《东窗事犯》。贯云石的[醉高歌过喜春来]和[凭栏人]等两组《题情》都是专为杨驹儿创作的,皆元曲名篇。大都杂剧艺妓中的许多人文化素养深厚,她们是否有完整的剧本创作未可知,但对剧本创作经常提供宝贵经验和意见当是意料中事。
因为杂剧艺术,是表演艺术,演员演出不仅是传达杂剧作者的思想和感情,更是一个再创作的过程,同样融入了演员对角色的理解感悟,融入了对人物的思想感情,价值判断。因而“除去大批文人参加了杂剧剧本创作外,在杂剧舞台艺术上发挥了更多创造的,则是众多的杂剧演员”[3]。“正是经过众多艺人的努力,才使得元杂剧在人民群众中日益扩大了影响。”[4]
元朝对于音乐、舞蹈等艺术的高度重视,为杂剧表演艺术家的成长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教坊是中国封建王朝管理宫廷俗乐的官署,其职能是管理祭祀等雅乐之外的音乐、舞蹈、百戏等事务,设置始于唐。据《唐书》记载,唐代属正五品,《宋史》记载,宋代“太乐署”从七品。而元代将其品级由从五品提高到了正三品,《元史·百官志》对教坊司品级沿革情况有明确记载:“教坊司,秩从五品。掌承应乐人及管领兴和等署五百户。中统二年始置。至元十二年,升正五品,十七年,改提点教坊司,隶宣徽元院,秩正四品。二十五年,隶礼部。大德八年,升正三品。延祐七年,复正四品。”元代教坊司地位之高,前所未有,标明元统治者对其重视程度超过历代。
从辽开始,到金、元,三个朝代不同的统治者们,都要通过战争等手段,从战败者那里不断索取、掳掠大批的音乐、舞蹈等表演人才,将这些色艺俱佳的艺伎优伶作为战利品,迁移、蓄积、集中到了政权的政治中心燕京,以供他们的国事活动和饮宴享乐。南宋徐梦莘编修的《三朝北盟会编·靖康》就记载金兵侵宋,不止一次地索要官本杂剧、说话以及各种百戏演员,动辄百人。如有“御前抵候方脉医人、教坊乐人、内侍官四十五人,露台抵候妓女干人。……杂剧、说话、弄影戏、小说、漂(口子旁)唱、弄傀儡、打筋斗、弹筝瑟琵、吹经等艺人一百五十余家”,又取“诸般百戏一百人,教坊四百人……弟子帘前小唱二十人,杂戏一百五十人,舞旋弟子五十人”[3]。这些人中的绝大部分被迫迁移到了当时的都城燕京,他们及后代,大多从此沉淀定居于此,之后又有被迫落籍者陆续加入。元灭金及灭南宋之际,有些原本汉族官宦子女沦为优伶。优伶真氏乃南宋著名政治家、理学家之后,其父曾官至户部尚书、参知政事。遭逢时变,父因官负债,女儿便被迫卖入娼家为艺妓。《元史》卷13《世祖纪十》记载至元二十二年(1285)正月,“徙江南乐工八百家于京师”。元代甚至有成批的士人沦落进入乐籍,《元史·礼乐志》就记载:至元三年(1266)“籍近畿儒户三百八十四人为乐工”,这使在籍乐人人数不断增加。
元朝实行乐籍管理制度,职业演员属于“系籍正色乐人”,法律身份为贱民。规定凡在籍的乐舞人,不得嫁娶良人,“乐人只娶乐人,其他人娶乐人为妻要治罪断离”[5]。又规定:“诸倡妓之家所生男女,每季不过次月十日,会其数以上于中书省。有未生堕其胎、已生辄残其命者,禁之。诸倡妓之家,辄买良人为倡,而有司不审,滥给公据,税务无凭,辄与印税,并严禁之,违者痛绳之。”[6]其本人、配偶甚至子女都将终生从事该行业。在《青楼集》中,记载女艺人与教坊管理者或同为教坊艺人缔结婚姻的比比皆是,一家几代数人从事此业的也不在少数。如著名杂剧旦角演员周人爱,其儿媳是艺人玉叶儿;瑶池景嫁给了教坊吕总管,以演出绿林杂剧见长的国玉第嫁给了教坊副使童关高,以多才著称的萧才子娶了艺人贾岛春;擅长小唱的牛四姐是京师唱社头牌元寿之的妻子。这种严格的乐籍管理制度显然有失人道,但从客观上却保证了艺术人才队伍的稳定,同时由于相互关系密切,利益相关,所以在技艺的传承、切磋方面更是毫无保留,有益于艺术的积累与提高。以歌唱闻名的宋六嫂,父亲和丈夫同为乐籍中人,其父是著名的筚篥演奏家,《青楼集》特别指出:“宋与其夫合乐,妙入神品;盖宋善讴,其夫能传其父之艺。”[1]张玉梅号“蛮婆儿”,其子刘子安艺术与母亲一样“擅美当时”,其女关关,被称为“小婆儿”,七八岁即已登台,颇得名声,这些都与家传密切相关。
当时艺人学习表演可能与后世戏剧、曲艺圈内师承的做法非常相似,须拜师,讲辈分。如赛帘秀、燕山秀都是珠帘秀的弟子,李娇儿被称为“小天然”,则是师宗闺怨戏大家天然秀。这种子承父业、师徒相继的模式,不仅使得演艺队伍不断扩大,而且各门技艺也得到了较好的传承。辽金教坊制度未见明确记载,但应该有相似之处。经过有进无出的数代不间断地补充、积累和繁衍,到元朝已经形成了数量非常庞大的乐人队伍。他们是元代杂剧演出的主力军和基础,也是杂剧艺术兴旺的人才保障。
乐人除了在重大的庆典和日常的宫廷或官方宴饮场合为统治阶层服务之外,为官员商人的家宴助兴,会相应地获得一定的报酬,应酬官派之外,还可以参加社会商业性质的演出,照章纳税即可。他们虽然社会地位低下,但是由于技艺精湛,赢得了观众和剧作家们的尊重。《青楼集》中记载了一百多位优秀艺妓的事迹,其中大都杂剧表演家占有相当大的比重。这些经过激烈竞争脱颖而出的优胜者,各擅其长,生旦净末丑各有分工,但也有些是艺术的多面手,珠帘秀“姿容姝丽,杂剧当今独步”,杂剧艺术“驾头、花旦、软末泥等,悉造其妙”[1]。胡祗遹在其《朱氏诗卷序》中有对她表演艺术的全面描述,说她扮演各式各样人物无不曲尽其妙:“危冠而道,圆颅而僧。褒衣而儒,武弁而兵。短(左边被左,右边决右)则骏奔走,鱼笏则公卿。卜言祸福,医决生死。为母则慈贤,为妇则孝贞。媒妁则雍容巧辩,闺门则旖旎娉婷,九夷八蛮,百神万灵,五方之风俗,诸路之音声,往古之事迹,历代之典刑,下吏污浊,官长公清”[7]不仅能够表现不同地位、职业、人物的特征,而且能够扮男、扮女、扮老、扮少,模仿不同民族、地域人的声色,更为可贵的是“九流百伎,众美群英,外则曲尽其态,内则详细其情,心得三昧,天然老成。”[7]由于其杰出的艺术才能和创新能力,受到文坛名流如卢挚、王恽、冯子振以及剧坛巨星关汉卿等人激赏,这些人都与她来往密切,并时有唱和。由于她是杂剧表演艺术全方位的开创者,所以也被杂剧表演界尊为祖师爷式的人物,人们尊称“朱娘娘”。其弟子赛帘秀,以杂剧歌唱闻名“声遏行云,乃古今绝倡”。珠帘秀的另一位“高弟”燕山秀,则以表演见长,“旦末双全,杂剧无比”。元朝后期的顺时秀“性资聪敏,色艺超绝”在大都享有盛名[8]。她与许多文人学士都有来往,如虞集、刘致、王元鼎等。张昱《辇下曲》对其更是赞不绝口,称:“教坊女乐顺时秀,岂独歌传天下名。仪态由来看不足,揭帘半面已倾城。”由于其杰出的表现,顺时秀常常到宫中应承,明初高启的《听教坊旧妓郭芳卿弟子陈氏歌》有言:
文皇在御升平日,上苑宸游驾频出。仗中乐部五千人,能唱新声谁第一?燕国佳人号顺时,姿容歌舞总能奇。中官奉旨时宣唤,立马门前催画眉。建章宫里长生殿,芍药初开敕张宴。龙笙罢奏凤弦停,共听娇喉一莺啭。遏云妙响发朱唇,不让开元许永新。绣陛花惊飘艳雪,文梁风动委芳尘。翰林才子山东李,每进新词蒙上喜。当筵按罢谢天恩,捧赐缠头蜀都绮。晚出银台酒未销,侯家主第强相邀。宝钗珠袖尊前赏,占断春风夜复朝。
“文皇”指元文宗。从诗中可以得知,这些优秀艺妓不仅为宫廷服务,同时为时所重,演艺活动非常频繁,所得报酬极为丰厚。顺时秀的弟子陈氏、宜时秀也都是教坊优人,名重一时,二人也都曾入宫表演①。大都城市的繁荣,经济的发达,杂剧的兴旺,演艺界人士令人瞩目的成功,经过人们口耳相传,耀眼的光环被放大,演变为一个个人生传奇,必然会吸引乡村、集镇更多具有潜质的人纷纷加入其中。
元代杂剧表演者中的不少人有着较高的文化艺术修养,如梁园秀,她本人就是个乐府作手,其〔小梁州]、[青歌儿]、[红衫儿〕等作品,“世所共唱之”(《青楼集》)。如一分儿,有人在酒会上吟“红叶落火龙褪甲,青松枯怪螃张牙”两句,让她用〔沉醉东风]词格续完时,她不假思索地应声接道:“可咏题,堪描画。喜献筹,席上交杂。答刺苏,频斟入,礼肠麻,不醉呵休扶上马”(《青楼集》)。她们的才情,受到世人赞赏,当时文人在诗词曲作序跋笔记中多有透露,胡祗遹在《优伶赵文益诗序》就记载了演艺世家赵氏一门的文化素养:“赵氏一门,昆季数人。有字文益者,颇喜读,知古今……故于所业,耻踪尘烂,以新巧而易拙,出于众人之不意。世俗之所未尝闻者,一时观听者多爱悦焉。”[7]许多演员不仅擅长歌舞表演,而且精通琴棋书画,甚至能够谱曲填词,在元代散曲中就经常能够发现她们与文人学士唱和的杰作。杂剧艺人张怡云“能诗词,善谈笑。艺绝流辈,名重京师”,著名的文学家艺术家赵孟頫、画家高克恭等曾为其作画;许多高官贵戚亲临其在大都海子(今北京积水潭附近)的居处,著名理学家姚燧、阎复等“每于其家小酌”[7]。此外她与大都文坛也有着广泛的交往,常以词曲唱和。卢挚、程钜夫等均有词作赞美其艺术。张怡云可谓“谈笑有鸿儒,来往无白丁”,自身文化修养、谈吐风度以及才思的敏捷都可见一斑。这种高雅的聚会、自由宽松的文化氛围和文化巨匠的密切交往,无疑对提高艺妓的文化水平和全面素养有很大的帮助,这是他们杂剧表演艺术不断提高的重要原因。
大都是人文荟萃之地,聚集着全国文化精华。其中不乏各个文化领域的硕人巨匠。他们对艺术有着超常的感受能力和极高的鉴赏水平,对表演艺术的欣赏、品评、归纳和理论总结,对于杂剧演艺水平突飞猛进的提高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使得教坊艺妓千百年来师徒相授、口耳相传的古老传承模式得到了最有益的补充和改进。赵孟頫、胡祗遹都以书画诗词散曲著称于时,为世人所称道,是艺术感受最敏锐、艺术素养最全面、最深厚的人,他们对包括杂剧在内的元曲艺术都有精辟独到的见解,胡祗遹更是通过一些序跋,对表演艺术进行了系统性的理论阐述。先后作有《赠宋氏序》、《朱氏诗卷序》、《赠伶人赵文益诗序》等3篇序文和两首七绝,主要谈演员应具备的艺术素质和表演艺术,他提出的“九美”说,最有代表性。大都杂剧所处的这种文化氛围当是其他地方都难以期冀的,可谓得天独厚。
当然,从事杂剧舞台表演的并非都是艺妓,《太和正音谱》引赵孟頫的话说:“良家子弟所扮杂剧,谓之行家生活,娼优所扮谓之戾家把戏。盖以杂剧出于鸿儒硕士骚人墨客所作,皆良家也。彼娼优岂能辨?故关汉卿以子弟所扮,是我一家风月,虽复戏言,甚合于理。”由此看来,元时文人墨客、良家子弟,不仅亲自撰曲,也有登台扮演角色的。这就透露出一个重要的信息,杂剧作家不仅能够进行文学创作,他们对于表演艺术同样精通在行,这反过来使得他们的创作更符合舞台表演规律,能够取得最佳观赏效果。他们这种献身艺术的精神和躬行粉墨的素养,恰恰是后世一些戏剧创作者的软肋,因为不少人的作品美则美矣,却只能止于案头阅读,难以排演登台。同时,元杂剧作家作为教坊外人,可能旁观者清,对演艺的提高或许更有独到见识。
杂剧鼎盛期,大都涌现出大批最优秀的杂剧作家、曲作家和表演艺术家,他们之间密切的合作,往往通过书会的形式来实现。所谓书会,就是剧作家与表演艺人的结社,属于行会性质的民间组织。“结社”一词见于文献记载始于南宋,周密《武林旧事》卷6“诸色伎艺人”条就列有书会名目。元代的书会组织更多,当时大都就有玉京书会、元贞书会和燕赵才人等,据《录鬼簿》记载其成员多为关汉卿、珠帘秀一类的杂剧作家、曲家、艺人。杂剧书会的兴盛,是大都杂剧繁荣的标志,因为优秀剧作家的成功,带动了创作群体的扩大,产生聚集效应。作家与作家,作家与演员,演员与演员之间关系密切,书会为同时代作家相互砥砺思想,切磋艺术,互相启发,交流竞赛,提供了平台,它能使杂剧艺术家们的创新之泉永不枯竭。例如杨显之,就因常为关汉卿修改剧本,补漏拾遗,获“杨补丁”之誉。王伯成与“马致远,忘年友。张仁卿,莫逆交”(贾仲明为王伯成所作吊词),一部四折《黄粱梦》由四个人一人一折共同创作,②这种带有文化产业化雏形的形式,当是戏剧商品化的一种表现。书会不仅密切了作家之间的联系,促进了合作,而且有利于杂剧人才的传帮带,有益于新的杂剧作家的成长和锻炼,为杂剧继承创新提供了很好的条件和环境。与以往作家与演员隔膜疏离的关系不同,元代的杂剧作家和演员保持着密切的合作关系,私交也比较好。珠帘秀等一批优秀表演艺术家在文坛受到普遍尊重。《青楼集》记载,当时大都还有以歌唱为主的结社组织“京师唱社”,其记载云:“李心心、杨奈儿、袁当儿、于盼盼、于心心、吴女燕雪梅,此数人者,皆国初京师之小唱也。”[1]
书会在杂剧作者和演员的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和影响,为杂剧作家和演员提供了一个得力的文化平台,使得作家新作能够及时推向舞台,演员不断有新剧可供排演,随着新剧的不断推出,演员艺术功力不断提高,名声愈大,号召力愈强。而且新剧越多,则越能将观众吸引到勾栏,这反过来又需要更多的创新作品满足人们的热切需要,这是一个良性的循环。因而书会对杂剧作家和演员个人发展都是极其重要的,并且其本身已经成为元代戏剧艺术成熟和繁荣的标志。有学者认为书会实际上成为“元杂剧之研究推行机关”,作家“以戏曲研究人而兼戏曲运动人”此言不谬。[9]但书会究竟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剧作家的作品是否只能交给他所属的书会,演员是否只能与一个书会有固定的联系?除了剧作家、演员之外,书会中还会有其他什么样的人物?他们各自的分工和作用是什么?谁来负责书会的日常管理和人员召集,书会为演员和作家提供怎样的服务和支持,相互之间的经济关系如何?书会选择剧作家和演员入会的标准有哪些?书会与书会之间的相互关系怎样?等等,这些都值得关注研究。
[注 释]
①陈氏事迹参见(明)高启《听教坊旧妓郭芳卿弟子陈氏歌》,宜时秀事迹参见(明)扬基《听老京妓宜时秀歌慢曲》。
②天一阁本《录鬼簿》贾仲明为李时中补写的[凌波仙]吊曲开篇中说:"元贞书会李时中、马致远、花李郎与红字公,四高贤合捻《黄粱梦》。"四贤中,李时中、马致远是官员,花李郎、红字公则是典型的艺人。
[1]夏庭芝.青楼集[A].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二)[C].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
[2]朱权.太和正音谱[M].台北:学海出版社,1991.
[3]张庚,郭汉城.中国戏曲通史(上册)[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06.
[4]徐扶明.元代杂剧艺术[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
[5]元典章[M].元刻本.
[6]宋濂,等.元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6.
[7](元)胡祗遹.紫山大全集[M].抄本.
[8](元)陶宗仪.南村辍耕录[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
[9]孙楷第.元曲新考[M].北京:中华书局,19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