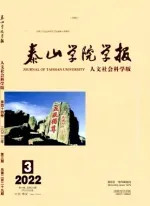论《全民国词话》的考索、编纂及其意义
曹辛华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江苏南京 210097)
近现代以来学者对词话整理与研究者,民国时期如况周颐、王文濡、唐圭璋等词学前辈曾用功甚多。其中,唐老所编纂的《词话丛编》最引人注目,收录词话达85种,可以说真正开了词话整理与研究的先河。而当前对词话整理与研究卓有成就的学者如张璋、王熙元、施蛰存、林玫仪、吴熊和、刘庆云、王兆鹏、孙克强、邓子勉、刘梦芙、谭新红、朱崇才等先生均有专门论著。其中张璋与人合纂有《历代词话》、《历代词话续编》等著收有词话128种(其中包括词选序15种,词选7种,论词绝句3种)。施蛰存与陈如江曾合纂《宋元词话》,并于《词学》栏目中编辑过不少稿本词话的整理成果。林玫仪有《词话七种考佚》[1],共辑《古今词话》、《词学筌蹄》、《升庵词话》、《百琲明珠》、《唐词纪》、《梅墩词话》、《词论》等七种。吴熊和先生《〈词话丛编〉读后》[2],文中提出增补唐老《词话丛编》的倡议,并增补9种词话,还提供了近40种论词绝句的目录。刘庆云《词话十论》为专门研究词话理论的著作。王兆鹏《词学史料学》[3]于“词论研究的史料”一节中专门对“历代词话专书”进行了述论。孙克强有《唐宋人词话》之纂,又有《清代词话简目》一文,收清词话77种(不含唐圭璋《词话丛编》所收者)。邓子勉《宋金元人词话汇编》搜罗了除专书外宋金元时期各个文人的各种论词的文献;刘梦芙《近现代词话丛编》[4]一书中收词话8种。谭新红《清词话考述》是继王熙元的《历代词话叙录》又一部专门考述词话的专著,著录清代以来之词话达到253种(《词话丛编》未收而为编者所经眼之词话132种,仅被征引之清代词话52种,加上唐圭璋《词话丛编》所收69种)。而朱崇才先生早在上世纪90年代就专研词话学,先后有《词话学》、《词话史》、《词话理论研究》等专著问世,1999年所著《〈词话丛编〉未收词话考录》(连载于《江苏文史研究所》1999年第2、第3期)中考录词话达134种。特别是新近朱氏还完成了《词话丛编·续编》这样大型的词话文献整理项目。然而,就现有人们对词话整理与研究的成果来看,对“民国词话”的全面整理与研究还未提上日程。如朱崇才先生的《词话史》中,所叙写词话的历史时间仅至“近代词话”,其于“近代后期”词话的论述中,仅罗列了王闿运、冒广生、叶衍兰、沈泽棠、梁启超、蒋兆兰、周曾锦、夏敬观、陈洵、潘飞声、蔡嵩云、郭则沄、陈匪石等晚清民国词人的词话[5],并未设立民国词话的章节。然而,民国时期不仅是词体创作的又一辉煌阶段,也是词话史发展的又一蓬勃阶段,民国词话也是词话史研究的重要内容,是研究民国词及其词学不可忽略的文献与史料。通过本人考索发现,民国时期出现的词话数量多达450余种。如此丰富的词话文献,值得我们进一步地全面整理与深入研究。近几年来,笔者承蒙南京师范大学钟振振、程杰、陆林等先生的指导以及人民文学出版社周绚隆先生、江苏凤凰出版社姜小青、王华宝等先生的鼓励与支持,已基本上完成了《全民国词话》的编纂课题中的搜辑、录入工作。于此本人先拟对《全民国词话》的考索问题与存在形态予以详论。
一、民国词话考索问题
目前,尚无对民国词话全面进行考索的论著出现,为编纂《全民国词话》,必须对与“民国词话”相关的术语进行界说。在此基础上搜辑、考索词话,进而辨别、体认、判定之。
首先要确定的是,“民国词话”的内涵与外延。顾名思义,所谓“民国词话”首先当指民国时期那些采用非现代论文式、基本以片段式表达出现的“话”词的论著或“话”民国词的论著。这里之所以用“出现”一语,因为有一些词话是在前代写成、在民国年间才刊刻印刷出版的,有一些是民国时期写作并且刊刻印刷出版的,有一些是民国期间写成却并未出版至今仍是稿本者,有些词话是民国时期为稿本后来被整理出版者。凡此四种情形出现的词话,本来都应当属于民国词话的范围。但是,鉴于前代写成的词话情形,在民国有几种传播方式:或是前代已刻印,至民国再出版;或前代写成为稿本,至民国才整理出版;或为晚清写成入民国后才刊行。因此,我们在判定何者属于“民国词话”时的标准,除了在民国时期写成一条外,当加上“以作者为生活时代为准”一条,即凡词话的作者有在民国时期有过生活经历才可将其写成的词话视为“民国词话”。这样有些虽是晚清时期写成但在民国时期才得以刊刻出版的词话,也当归为民国词话。还有一种写作过程“跨代”(或跨晚清民国、或跨民国与新中国)者,我们在划分时,将视之为“民国词话”。除此,如《铜鼓书楼词话》虽在民国得以报刊连载,然因为作者查礼不是生活在晚清,更无民国生活经历,故不目之为“民国词话”,但我们在论述民国词话时会运用此种材料佐证。最后要特别指出的是,还有一种词话虽然其谈论的中心是“民国词”,但由于其写作不是在民国,而是在新中国以来,按照民国词话一词当还有“话”民国词之义(如张伯驹《丛碧词话》、朱庸斋《分春馆词话》等即如此),也将视之为“民国词话”,只是在收录时从严纳入附编目录中。
其次,“词话”认定问题,是能否真正判定清楚“民国词话”的前提。通过对已有的各种词话专著进行归纳①,笔者以为,判断是否为“词话”的标准有三:标准一,通常那些明确以“词话”命名的篇目(除指话本、小说者外),自然是无庸多言。标准二,那些名称中无“词话”,但有如《词话丛编》等所收篇目含“词谈”、“词论”、“论词”、“词评”、“评词”、“谈词”、“读词”等字眼者,应仿《词话丛编》之成例,归入词话。民国时期属此类词话者尤多。标准三,凡属谈论词学方方面面问题的片段式论著,其本质在谈及词或词学者,当视之为词话;而类似以现代论文体例写成的词学论文或专著基本上不当视之“词话”,应将其归入“民国词学论文”与“民国词学专著”。②下面将遵照这三个标准具体说明如何判定那些处于模糊状态的民国时期出现的论词文献是否为“民国词话”。
其一,对那些已被后人或时人整理、且已冠以“词话”或视之为“词话”者,不宜再责其非而忽视,当在考述时予以辩证地承认。如谭新红《清词话考述》就将张璋《历代词话·补编》中自行汇辑、自行命名的《雪桥词话》(杨钟羲)、《遐庵词话》(叶恭绰)等列入,将钟振振师所辑《旧时月色斋论词杂著》(陈匪石)、李保阳所辑《梅花词话》(张諴)、《霜红词话》(胡士莹)等也当作词话著录。再如,朱崇才《词话丛编·续编》将原刊于当代《词学》为编者重辑的《花随人圣庵词话》列入,又将自己所辑、自行命名的《曼殊室词话》、《梦桐词话》收入。此种现象,虽然历史上并未出现以所收词话名称,均乃后世编纂、著录者所另立之名称,但至我们编纂时,由于已既成事实,当在叙录时说明之,仍视之为词话。
其二,结合以上三条标准,对论著题目虽不以词话名,而在当时刊出时列于“词话类”者,我们也当视之为词话。如《江苏文献》中收有隐蛛《跨鹤吹笙续谱》与泾南钓叟《善香室随笔》两种,虽名非词话,但在其目录中却标明为“词话”,可见,当时人们刊载时是视之为词话的。自然我们也当以词话收录。又如有一些谈词文章,题目非词话,内容为论词者,在刊登发表时也未标明为词话,但在民国时的索引、目录等文献著录条目中却列之为“词话类”者,笔者以为也当视为词话,如民国时期的《日报索引》(上海文化教育馆,1937年)刊物中词话类下收有《武汉日报》所刊朱光潜《王静安的浣溪沙》、《中央日报》上所刊《缥缈孤鸿影》、《李后主和他的周后》、《念奴娇被窃案》、《明人伪作陆放翁妻词》、《周美成词之混唐人句》等,对这些文献我们也依当时成例当作“词话”,只不过由于其零星状态,汇辑后以文献出处通称“××中词话”(如中央日报中词话)。
其三,当前对论词绝句、填词百法、常识、通论等论著是否为“词话”存在着分歧,该如何处理。如张璋等人所纂《历代词话》中就收有郑方坤、厉鹗、谭莹、朱衣真等《论词绝句》凡4种;朱崇才所著《〈词话丛编〉未收词话考录》中亦收录潘飞声的《论粤东词绝句》与《论岭南词绝句》凡2种。通常人们限于词话多为散体的观念,对“论词绝句”这样的话词样式多排除在“词话”之外,而事实上,笔者以为,论词绝句只不过是词话的“韵文”化表现,因此,我们在判定时,应当将其作为“词话”看待。在民国时期出现的还有论词词这样的“韵文”化词话(如朱彊村《望江南·杂题我朝诸名家词集后》、卢前《望江南·饮虹簃论清词百家》。在民国时期出现了介于现代专著与传统词话之间的著作,如顾宪融的《填词百法》、徐敬修的《词学常识》、吴梅的《词学通论》、汪东的《词学通论》等。当前如朱崇才、谭新红等即将顾氏所著列入词话目录,而张璋等人所纂则将吴、汪二人《词学通论》选择式地收入。这种做法有其不合理性,因为违背了前面词话界说的三大标准中“片段式”一项。但在民国时期还有一种虽名为“通论”、“概论”等,但由于被分散刊登在一种期刊或多种期刊上,对此种情况下出现的论词文献,以其与判定词话的“片段式”标准大体相侔,本着文献汇辑的精神,可以视之为“词话”,但当列入副编。另外,民国时期出现了不少“讲义”式词学文献,如况周颐的《词学讲义》、徐珂的《词讲义》、寿玺的《词学讲义》、《词学大意》、傅君剑的《学词大意》等。对况氏之作,张璋、朱崇才、谭新红等均已目为“词话”,却对其他几种因未能著录故未说明。于此,我们以为凡是以“片段式”出现、未能系统以书本形式出版者,当准况氏《词学讲义》之例,目为词话,列于副编中。
其四,专门的词人传记、书目是否可列入词话范围问题。民国时期有不少关于词人传记的词学文献,如唐老在编纂《词话丛编》时就收录有张尔田的《近代词人逸事》,周庆云《两浙词人小传》,谭新红即以词话叙录。而朱崇才所纂《〈词话丛编〉·续编》中收录有《历代词人考录》达27卷。可见他们都将此种著述当作词话的。对此笔者以为,传统词话中既有“纪人”一体,应当视为“词话”。但是,以其体例与传统以“词话”为题者存在差异较大,应列入副编中为宜。准此,像顾培懋《两浙词人小传》等,我们虽视之为词话,但也列入副编。词学书目是否当列入词话的范围呢?朱崇才先生在其《词话学》中指出“历代公私书目中对于词籍和词人的著录、评论,对词话研究有莫大帮助”,并认为《四库全书总目·集部词曲类》提要“诚为清代中叶考证兼论述类词话的代表之作”[6],显然是视之为词话的。其他像《直斋书录提要》中关于词籍的叙录部分,张璋等人所纂《历代词话》将其摘出命名为《直斋词评》收录;而像柯劭愍等人所编《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词籍提要》,谭新红《清词话考述》中也当作词话叙录。笔者以为,民国时像赵尊岳的《词籍提要》、《惜阴堂汇刻明词提要》(分别见《词学季刊》创刊号第1卷第1号、第2卷第1号)以及郑骞《三十家词选目录(附集评)》(见《文学年报》1940年第6期)等目录之作既具有话词的性质,自然也当视为词话。只是当列于附编。
其五,对民国时期包孕式词学文献的“词话”性质当如何判定问题。所谓的包孕式词学文献,即不是单独成篇、成册而是隐含或杂合在各种文献诸如词籍、诗话、笔记、文学史论著中的论词之语。民国时期含在词籍中评点之语为数不少,如夏敬观曾评点《彊村丛书》,范烟桥有《销魂词选》之评,汪东有《唐宋词选·识语》,唐圭璋、汪国垣、林庚白曾评点过卢前的词集《中兴鼓吹》③。如何判定其是否为“词话”呢?就目前整理词话者的态度来看,唐老曾将由张惠言等所编《词选》辑出评语名之为《张惠言论词》,将由《蓼园词选》辑出的评语,命名为《蓼园词评》;由《湘绮楼词选》辑出的评语命名为《湘绮楼词评》、由梁启超文集中辑出的论词之语命名为《饮冰室词评》,在编纂《词话丛编》时将他们与龙榆生所辑《彊村老人评词》等都收录了进去,显然在唐老那里,是视这些词评为词话的一种的。当代的词话整理中,张璋所纂词话著作,也大量地整理收录了各种评词之语。像夏敬观评《梦窗词》,李保阳辑出后命名《梦窗词评》,谭新红《清词话考述》一书目之为词话并叙录;乔大壮的《片玉集》批语,朱崇才《词话丛编·续编》亦作为词话收入。既然有这么多学者将重新汇辑出的评词之语视为词话,那么,就有必要在搜辑词话时将评点之语考虑在内。我们不能仅仅因为当时未有其书,怕混淆后人视听就置之不理。应当本着积极汇辑、慎重命名的精神,将众多评词或评词学之语汇辑出来,纳入《全民国词话》的整理范围。只是在编纂时不可径以“××词话”命名,当如唐老《丛编》之作法称“《××》评词”或“某某人评词”为佳。在民国时期,还有包含于诗话中或与诗话等合在一起的论词之语、包含于笔记中论词之语与包含于文学史中关于词学之语等,它们与词评的方式相似,都属于包孕式的。唐老在编纂《词话丛编》时,对这种现象的处理方法是,先辑出再重新命名。如将《能改斋漫录》中的论词内容裁篇辑出后命名为《能改斋词话》;从《苕溪渔隐丛话》中辑出的论词内容,命名为《苕溪渔隐词话》;从张侃《张氏拙轩集》中“拣词”部分裁篇题作《拙轩词话》;从《清稗类钞》中辑出者命名为《近词丛话》。唐老的这种做法是基于这些词学文献具有的“词话”性质,这是可取的。然而,由于“新命题目”易造成人们误以为是当时即有此著作或书籍。因此,当我们面对包孕式词学文献时,不可径建立新名,而是按“××(作者)论词”或“××(著作)中的论词文献”等拟书名或篇名,并标明出汇辑整理者的姓名、出处、成因等。笔者在搜辑民国词话时发现,如果惟单独成篇、成书者始为“词话”,才予以收录编纂,那势必遗漏杂、合、包、糅在各种民国文献中的具有词话性质的资料。如陈衍的《石遗室诗话》中就有不少论词之语,王蕴章《然脂余韵》中也有大量关于女词人的评论言语。可以这样说,民国时期出现的各种诗话、笔记与文史著作中都有可能隐藏着“话”词的文献,不可因未专门成篇、成书就无视。也就是说,“包孕”式词话也是《全民国词话》考索、整理与研究所关注的对象。
基于以上的界说,笔者在考索民国词话时先在求全的基础上,然后用以上关于“民国词话”、“词话”的判定标准进行辨别、判定,努力做到务实、求质(即以内容实际情况来断定是否为民国词话),陆续搜辑到题目以词话命名者有170余种;如《词话丛编》等所收篇目含“词谈”、“词论”、“词评”、“论词”、“谈词”、“读词”等字眼者,近120种;其他名目者有150多种。将笔者所考索搜辑的词话数量(450余种)与前述当代诸家论著、丛编中所收者相比较,笔者发现民国词话数量庞大得惊人。如张璋等《历代词话续编》所收民国词话仅114种(包括词序与论文在内),而谭新红所著《清词话考述》由于后出转精,几乎囊括了此前词话研究、整理者关于民国时期词话目录,收录民国词话之条目才120余种。即使将笔者所考索的民国词话中存在模糊待定的部分去掉,笔者所收明确为民国词话还有340种左右(此数目尚不含本人自民国各种文献中搜罗、裁篇、抽抄、汇辑而成“包孕”式词话条目)。由于篇幅限制于此不一一罗列其详目,好在笔者仿谭新红君《清词话考述》已另成《民国词话考述》初稿,作为编纂《全民国词话》的前期准备。
二、民国词话的存在形态问题
于此,笔者将对民国词话的存在形态予以描述。笔者在搜辑、考述民国词话时发现,与前代词话存在形态不同,民国时期词话在已有的形态基础上,又多出一些新形态。这就值得我们在搜辑时注意与说明。
其一,与前代词话相同的存在形态,如刻本、稿本,民国时期也照样有。属刻本者相对比较容易搜辑。而以稿本状态存在者,由于其传播不广,呈“孤本”状态,搜求难度相当大。此类词话或收藏于图书馆(甚至地方图书馆),或保存在收藏家手中,或以遗稿方式保存在词话作者后人手中。因此,笔者已搜罗到的稿本词话20余种。又由于是稿本,不少词话作者的生平相当难考察,有的甚至词话作者姓名也成了难解之谜。另外,不少稿本为行草或草书写成,也给录入造成一定的困难。虽然如此,由于稿本词话处于“被遗忘”的境地,不少是词学界同仁未能寓目者,其文献价值相对较大。如笔者已录入完成的稿本词话陈夔《虑尊室词话》是与《虑尊室词选》合在一起的,涉及了词乐、词人、词艺、词史等方面的问题。或以为此种稿本既然迄今不为人知、识,其影响既微,意义就不大,但是面临当前还原学术史、文学史“原生态”的精神,至少可补民国词话的缺失,对考察陈夔的词学创作也肯定是有助益的。对这些稿本,笔者拟先以《晚清民国稀见稿本词话20种》的方式整理,再将属民国词话者以存目的方式收入《全民国词话》中。
其二,铅印(石印)图书本是民国词话存在形态的常态。在晚清民国之际,随着铅印、石印等印刷物逐渐增多,以铅印本、石印本的形态存在的词话也为数不少。除了单行本外,一般来说,民国时有不少词话含在各种总集、选集或别集也以铅印、石印为多。此种形态的词话由于多属包孕式的,故最难搜辑。欲对民国词话进行全面考索,对铅印本、石印本包孕式词话的整理是关键。由于民国时期的纸张质量不如线装的宣纸,易损、易毁、易碎(虽然有一些已变为电子书,但大多处于待整理状态),这样,此种形态的词话不仅因其处于隐藏、杂糅状态难查找,又因此而加大了借阅难度。特别是,包孕在铅印别集中的词话,由于别集数量大,就要求我们只能采取“地毯式”考索,方可尽可能多地占有。
其三,油印本是民国词话存在形态异于前代的特别之处。因为油印是晚清民国以来印刷史上的新方式。特别是民国时期出现了大量的油印文献。词学论著在民国以此种方式面世者也为数不少。笔者曾撰《油印本词学文献考录及其价值》一文,其中也收录有多种油印本词话。如任卓的《三近居墨屑》即是以油印本出现,陈匪石《声执》也曾如此。词话有油印本,一方面表明作者经济有限选取了低廉的印刷方式,一方面又说明,此种词话已超越了稿本状态进入了传播链中。
其四,报纸、期刊本是民国词话存在形态的又一常态。作为新的传媒形式,各种报纸、期刊在晚清民国纷纷出现,与诗话等批评文体一样,有不少词话被刊发在报纸、期刊上。其发表形式多种多样。或长,或短,或文言,或白话;或一次刊完,或连载多期。这些词话不一定发表在纯文学刊物上,有时连军事、医疗、铁路、农学等专刊上也有词话的身影。如陶骏保《从军词话》发表在《南洋兵事杂志》上;李昌漫《词的浅说》即发表在《中国农学会丛刊》上。统计起来,民国时刊登词话较多的期刊为学报类,其次是娱乐休闲类。须指出的是,“报纸”形态的词话,以其量多且繁琐,是目前较难穷尽的一类。如笔者通过对《民国日报》进行排查,由其中得到词话有10种之多;通过对《先施乐园报》进行搜辑,得词话7种;通过对《中央日报》的排查,得词话有13种。其中唐老的《梦桐室词话》④曾不定期地连载,值得注意。目前来看,民国时期的一些期刊已有了电子影像,但报纸却还未全有。这就意味着,民国词话的编纂要做到真正的“全”,目前的难度更大。
其五,评点本。此种存在形态与前面各种因传媒方式而成的形态不同,是由于人们在阅读过程中的评点习惯而出现的。这些评点可以存在于稿本、抄本上,也可以存在刻本、铅印本上,有时期刊上也会出现。由前面我们对词学评点的“词话”性质的判定,民国时期的各种词籍评点的评语也是我们民国词话收录的范围。然鉴于不少词籍评点具有惟一性,要发现有评点的词籍也是有困难的。加上有些评点本词籍目前有可能还存在私人手中,要全面汇辑各种评词之语,就更为不易。好在一般能评点词籍者多为词学名家或专家学者,因此,要搜求词籍评点的评语,只须按民国词学学者存书的流向跟踪查寻,当有所获。
归结起来,民国词话的存在形态异于前代,增大了考索难度。我们在考索时,对民国时期的各种刻本、稿本、油印本类词话,当从古籍部图书中获得;对铅印本、石印本或部分期刊当从近现代图书中获得;对现代期刊、报纸中的词话,可凭借当代的一些电子期刊影像检索系统获得一部分。实际上,目前电子化的民国期刊数量还不够多,要查找还必须亲临其地不可。特别是一些地方图书馆中所存的民国图书数量与名称尚未真正的面世,遑论电子化,故更须亲临逐一排查,方能求全。关于《全民国词话》的价值、编纂意义及其具体编纂方式、手段等问题,笔者将在别处予以论述。
[注 释]
①关于“词话”的定义与外延等问题,朱崇才先生所撰《词话学》、《词话史》、《词话理论研究》三部专著中均有较为细致的辨析,孙克强先生也有《词话考论》专门论述,可参见。本文于此主要是结合民国词话的各种情形来重新界说的。
②此二者同属民国词学批评“三大文献”,已列入钟振振师与笔者所承担的民国诗词学文献整理项目(河南文艺出版社的出版基金项目)中的“全民国词学论文汇辑”与“民国词学文献珍本丛刊”。
③诸如此类的评点之语甚多,笔者曾专门就民国时期的词籍评点予以研究,抄录汇辑了一大批评语。拟作为《全民国词话》附录部分。
④朱崇才先生《〈词话丛编〉·续编》中收有《梦桐词话》,一为朱氏自己所汇辑,一为唐老原著《梦桐室词话》(发表在《中国文学》第一卷第一期,1944年)。而《中央日报》上所刊多与此不同。
[1]台静农先生八十寿庆论文集[C].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1.
[2]吴熊和.吴熊和词学论集[C].杭州:杭州大学出版社,1999.
[3]王兆鹏.词学史料学[M].北京:中华书局,2004.
[4]刘梦芙.近现代词话丛编[M].合肥:黄山书社,2009.
[5]朱崇才.词话史[M].北京:中华书局,2006.
[6]朱崇才.词话学[M].天津:天津出版社,1995.
——评陈水云教授新著《中国词学的现代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