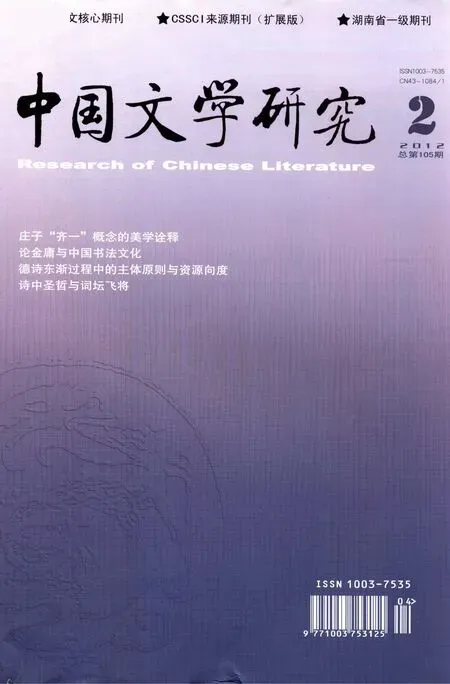诗中圣哲与词坛飞将
——再论杜甫与辛弃疾
赵晓岚
(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湖南 长沙 410081)
缪鉞先生曾说:“宋词之有辛稼轩,几如唐诗之有杜甫。”〔1〕(P50)这一比拟自然主要是着眼于其作品的内容、风格、表现手法等方面的因素,但除此之外,亦包含了对杜甫和辛弃疾所具备的诗史和词史地位,以及他们在各自领域中所具有的集大成和开风气之特点的判断。关于杜诗和辛词的比较,已有刘扬忠先生的《稼轩词与老杜诗》一文珠玉在前,故本文不拟作全面论述,仅择要从三个方面论之,以见杜甫这位“诗中圣哲”与辛弃疾这位“词坛飞将”在文学方面的相通之处。
一、“直陈时事”与“陶写之具”——诗史与词史
从文学言,杜诗全力反映安史之乱的社会现实,在唐即有“诗史”之称。孟棨《本事诗·高逸第三》云:“杜逢禄山之难,流离陇蜀,毕陈于诗,推见至隐,殆无遗事,故当时号为‘诗史’。”后人更有多方阐发:
甫又善陈时事,律切精深,至千言不少衰,世号诗史。〔2〕(卷二百一)
杜少陵子美诗,多纪当时事,皆有据依,古号“诗史”。〔3〕(P167)
直陈时事是公认的杜诗特点。当时经历过安史之乱的诗坛名家不少,但无一人能如杜甫那样全面深刻地反映客观社会现实和与这个社会息息相通的主观心灵世界。李白诗中固然不乏对平叛的向往甚至“为君谈笑净胡沙”的歌赞,但多是主观情志的抒发。而王维则由于陷入伪职几遭大难,故而后期半官半隐中,沉潜于禅心梵音,除去曾救他于大难的“万户伤心生野烟”等几首绝句尚有安史印痕外,其诗集中几乎找不到这场社会大动乱的印记。相较之下,杜诗的“直陈时事”,在唐诗发展中异军特起,自具面目。
辛弃疾在宋词发展史中,也具有同样地位。词本只长于缘情,苏轼以后,言志之作始多,亦间或涉及说理叙事,但终究以缘情为本位。而且,宋人的文体分工观念颇强,虽时有“破体”之作,但“尊体”仍为主流。故而南宋诗坛上反映靖康之乱及其后的社会现实非常广泛,如著名爱国诗人陆游,其包容万首的《剑南诗稿》,几可视之为宋诗中的“诗史”,其他如杨万里、范成大诸人,亦多反映时事之作;但是,陆游词中的杀敌复国之什就很有限,而出使金国不辱使命,曾写下72首爱国绝句的范成大,其词中却未见此行留下的痕迹。南渡以来的词坛上,虽颇多爱国志士的抗金复国之呐喊,如张元干、张孝祥、李纲、岳飞、向子諲等,但在表现手段上,仍是以抒情为主(尽管这“情”已非儿女之情),且因词作数量的限制,反映现实的面亦有限。
然而,这并不等于说,作为抒情文学的词就不能承担“史”的功能,具备“史”的意义。丹麦文学史家勃兰兑斯在《十九世纪文学主流·流亡文学》的引言中指出:“文学史,就其最深刻的意义来说,是一种心理学,研究人的灵魂,是灵魂的历史。一个国家的文学作品,不管是小说、戏剧还是历史作品,都是许多人物的描绘,表现了种种感情和思想。”〔4〕(P2)而从广义上来说,“诗歌的历史就是人类的心态史,是主体的心灵颤动、变化和表现的历史,它艺术地应和着创作主体在不同时期的不同心理波动,划出相应的心理曲线图”〔5〕(P313),因此,比诗歌更为直接大胆、更为强烈地抒发了宋人灵魂的词这一表现形式,肯定能更为集中地表现人的心灵史。
事实上,前人亦有从心灵反映社会这个角度来论杜甫“诗史”之涵义的,比如胡宗愈的《成都新刻草堂先生诗碑序》就说:
先生以诗鸣于唐。凡出处去就,动息劳佚,悲欢忧乐,忠愤感激,好贤恶恶,一见于诗,读之可以知其世。学士大夫谓之诗史。
与之相呼应,周济在《介存斋论词杂著》中亦从这一角度提出了“词史”概念:
感慨所寄,不过盛衰,或绸缪未雨,或太息厝薪,或已溺已饥,或独清独醒,随其人之性情学问境地,莫不有由衷之言。见事多,识理透,可为后人论世之资。诗有史,词亦有史,庶乎自树一帜矣。〔6〕(P1630)
按照以上解释,词的发展史上这顶“词史”的桂冠,唯辛弃疾可当之无愧。他对词体最大的改革恐怕就是“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7〕(P3690),变词之缘情为写志、纪事、说理,而他以词作为“陶写之具”的创作观念,使他所陶写的自是其抗金复国的胸怀,是他为此目标而奋斗的人生旅程,是他对整个国事的认识,与杜之以时事入诗近。
杜甫和辛弃疾于文学创作一道,几乎各自把全部精力分别投入到了诗和词上。正如同杜甫的“一切物、一切事、一切意,无非诗者”〔8〕(P464)一样,辛弃疾也做到了“一切物、一切事、一切意,无非词者”。翻开稼轩词集,举凡他进退出处的人生经历及其前因后果,人生几个阶段思想的发展嬗变,国事变化带给他的喜怒哀乐之情,朝廷主战主和斗争的激烈氛围……都在稼轩词中留下了印记。可以说,词坛上没有任何人象辛弃疾这样全力表现时代的风云变幻。笔者以为,如将前引胡宗愈的话改动几个字,则几如为稼轩写照:
先生以词鸣于宋。凡出处去就,动息劳佚,悲欢忧乐,忠愤感激,好贤恶恶,一见于词,读之可以知其世。
如此,不正是可以“号为词史”?至少是心灵史!笔者赞同刘扬忠先生的论述:“(辛弃疾)的词,不但是其作为英雄豪杰的人品的完整体现,而且还成功地展现了他作为活泼泼的复杂的人之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方方面面。在他长达四十来年的创作历程(指有作品可考的)中,他的确是做到了,有处于何时、何地、何种精神状态下的辛稼轩,就有与这种时、地、心境相一致的稼轩词。……从人间产生长短句歌词的第一天起,直至南宋时期,有哪一个词人能象辛弃疾这样,用这种抒情样式将自己无限丰富的心灵世界与精神面貌展示得如此全面复杂、深细曲折、生动感人呢?”〔9〕(P229—230)
总之,杜甫以其身与动乱,走出皇城,漂泊西南,再涉两湖,终老破船,使其诗深刻全面地反映了社会动乱、民生凋敝以及对唐室中兴、天下太平的热望,这一“诗史”之作,有论者甚至认为可补史载之不足。而辛弃疾也将花间尊前佐欢侑觞、以代言为主(男子而作闺音)的词,变为陶写之具,将苏轼的自道性情、表达哲理(多在人生解脱),发展为自身与政事、与出处息息相关的心灵、情感史,真正做到了“见事多,说理透,可为后人论世之资”。虽因文各有体,杜诗史所具的社会史、人民生活史的内涵,由于“心绪文学”的界限难以最终突破,但周济所云的“词史”意义是确实存在的。
二、“沉郁顿挫”与“变温婉,成悲凉”——创作风格
“沉郁顿挫”作为杜诗的风格特征,已成定评,而此语本出于杜甫的自评。《进鵰赋表》云:“臣之述作,虽不能鼓吹六经,先鸣数子,至于沉郁顿挫,随时敏捷,扬雄、枚皋之徒,庶可企及也。”明言“沉郁顿挫,随时敏捷”来源于扬雄和枚皋。《汉书·扬雄传》云扬雄“口吃不能剧说,默而好深湛之思。”刘歆《与扬雄求〈方言〉书》:“非子云澹雅之才,沉郁之思,不能经年锐精,以成此书。”而《文心雕龙·才略》亦云:“子云属意,辞人(作“义”)最深,观其涯度幽远,搜选诡丽,而竭才以钻思,故能理赡而辞坚矣。”杜甫自称“赋料扬雄敌”(《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以为“扬雄、枚皋之徒庶可企及”,则此处的“沉郁”,自然应是指扬雄的深湛、沉郁之思。安旗先生则以为“沉郁”可能是从《文选》中陆机《文赋》的“言恢之而弥广,思按之而弥深。播芳蕤之馥馥,发青条之森森。粲风飞而猋竖,郁云起乎翰林”而来:“沉者,深也,似有‘思按之而弥深’之意;郁者,积也,厚也,似有‘郁云起乎翰林’之意。……‘沉郁’二字是指作品既富于思想,又富于情彩,有蔚然深秀之貌。”〔10〕(152—153)杜甫本为广泛汲取前人成果的集大成者,其学问得力于《文选》者亦颇多,所谓“熟精文选理”者,因此既仰慕扬雄之深湛沉郁之思,又得力于《文选》的深沉厚积,自是不无可能。其实《春秋左氏传》所云“诗人感而有思,思而积,积而满,满而作”,已有“思按之而弥深”之意,何曰愈《退庵诗话》更明确指出:“子美以学力胜,故语多沉郁。”但这只是杜甫早期“沉郁”之解,与诗教的“温柔敦厚”还有近似之处。而“顿挫”,本出于书论,是指运笔中的停顿转折,不是一发无余,而是蓄力将发、待发,移用到文学上,也多指表达上的曲折变化(词之“留”而不“流”亦即此意),如安旗上文云“顿挫者,即曲折变化也。意境有顿挫,就显得深厚有味;语言有顿挫,就显得丰富多姿;声韵有顿挫,就显得铿锵悦耳。杜甫所说的‘顿挫’大抵是表示自己的诗文深于章法,也就是说,文字技巧很熟练的意思。”但这也只是杜甫早期“顿挫”之义。后期遭遇战乱和人生坎坷,其作品之“沉郁”的涵义倒是接近最早出现于屈原《九章》中的原始意:“申旦以舒中情兮,志沉菀而莫达。”“菀”同“郁”,即沉闷郁结之意。陆机《思归赋》亦云:“伊我思之沉郁,怆感物而增悲。”至于“顿挫”,亦不纯是章法之曲折变化了,陆机《遂志赋》云:“抑扬顿挫,怨之徒也。”皆与郁结幽愤之思有关,因此,笔者赞同安旗对“沉郁顿挫”的演变之意的理解:
杜甫早年的“沉郁顿挫”可以四字释之,这就是:“以学力胜”。中年以后的“沉郁顿挫”可以八字释之,这就是“忧愤深广,波澜老成”。〔10〕(P156)
“忧愤深广”指沉郁,即反映现实的广阔和深刻,以及表现出来的浓厚的忧郁色彩和悲剧气氛;“波澜老成”指顿挫,即由于内心郁结所表现出来的跌宕转折、拗怒不平等开阖变化,虽与早期顿挫有关,但已不纯是艺术手法的表现了。
以此来看,非有博大之怀、沉雄之思、浩荡之力,则不能为“沉郁顿挫”。而词的传统风格是婉约柔媚,是“虽小却好,虽好却小”〔7〕(P3710),辛之前的唐宋词大家多为此种路数:如温庭筠的绮艳,韦庄的清丽,晏殊的温润雅洁,欧阳修的深婉俊秀,柳永的旖旎尽情,秦观的婉曲深细,等等。贺铸虽有“悲壮如苏李”之风,但最为人称道的仍是“盛丽如游金张之堂,而妖冶如揽嫱、施之祛”〔11〕(P755);李清照词虽不乏丈夫气,但其“别是一家”的词论,决定其词仍是婉约正宗。
打破这一传统风格的自然是苏轼的“以诗为词”,是其“举首浩歌”,“指出向上一路”的清雄词风。但苏轼却少有沉郁之作,即使悲,也转向旷。
辛弃疾之前的大家,有“沉郁顿挫”之评的当首推周邦彦。陈廷焯极端赞赏杜甫的沉郁顿挫,《白雨斋词话》卷八云:“杜陵之诗,包括万有,空诸倚傍,纵横博大,千变万化之中,却极沉郁顿挫,忠厚和平。此子美所以横绝古今,无与为敌也。求之于词,亦未见有造此境者。”〔12〕(P3977)故他喜用沉郁论词:“所谓沉郁者,意在笔先,神余言外。写怨夫思妇之怀,寓孽子孤臣之感,凡交情之冷淡,身世之飘零,皆可于一草一木发之。而发之又必若隐若现,欲露不露,反复缠绵,终不许一语道破。匪独体格之高,亦见性情之厚。”〔12〕(P3777)虽然词中未能造杜甫沉郁顿挫之高境,但仍有得杜诗沉郁顿挫之妙者。北宋词人中,他于此对周邦彦评价最高,《白雨斋词话》卷一云:“词至美成,乃有大宗。前收苏、秦之终,复开姜、史之始。自有词人以来,不得不推为巨擘。后之为词者,亦难出其范围。然其妙处,亦不外沉郁顿挫。顿挫则有姿态,沉郁则极深厚。既有姿态,又极深厚,词中三昧亦尽于此矣。今之谈词者亦知尊美成。然知其佳,而不知其所以佳。正坐不解沉郁顿挫之妙。”〔12〕(P3787)同书卷五又云周“极顿挫沉郁之妙。”
的确,在稼轩之前的宋代词人中,周邦彦是学杜最勤者。据罗忼烈先生统计,《清真词》中用杜诗凡六十余处〔13〕(P20),远远超过用李商隐、李贺、杜牧、温庭筠等人,王国维甚至将“词中老杜”之桂冠授予周氏。陈廷焯论杜甫沉郁顿挫之因,虽然也肯定杜甫的“忠爱之忱”,但认为主要还是“由读破万卷,研琢功深”〔12〕(P3941)而致,因此他论周邦彦词的沉郁也主要是从思力之“厚”、手法之“留”着眼:“美成词极其感慨,而无处不郁,令人不能遽窥其旨。”他举《兰陵王》一词来说明:“‘闲寻旧踪迹’二叠,无一语不吞吐。只就眼前景物,约略点缀,更不写淹留之故,却无处非淹留之苦。直至收笔云:‘沉思前事,似梦里,泪暗滴。’遥遥挽合,妙在才欲说破,便自咽住,其味正自无穷。”又评《六丑》“为问家何在”一句“点醒题旨,既突兀又绵密,妙只五字束住。下文反覆缠绵,更不纠缠一笔,却满纸是羁愁抑郁,且有许多不敢说处,言中有物,吞吐尽致。”〔12〕(P3787)周济《介存斋论词杂著》云:“美成思力,独绝千古,如颜平原书,虽未臻两晋,而唐初之法,至此大备。后有作者,莫能出其范围矣。”其《宋四家词选·目录序论》又云:“清真,集大成者也。……清真浑厚,正于钩勒处见,他人一钩勒便刻削,清真愈钩勒愈浑厚。……清真沉痛至极,仍能含蓄。”亦主要从其构思的浑成、法度的精严齐备和能“留”来谈其沉郁顿挫。陈氏亦论周之顿挫:“美成词极顿挫之致,穷高妙之趣,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又云:“美成乐府,开阖动荡,独有千古。”〔15〕(P3723)认为其词“操纵处有出人意表者”〔12〕(P3789),“有前后若不相蒙者,正是顿挫之妙。”〔12〕(P3788)这主要是从周邦彦长调多层次结构之转折层深、开合动荡来论其顿挫。王国维《人间词话删稿》说:“先生之词,文字之外,须兼味其音律。……今其声虽亡,读其词者,犹觉拗怒之中,自饶和婉。曼声促节,繁会相宣;清浊抑扬,辘轳交往。两宋之间,一人而已。”〔16〕(P4272)则是论其声韵的顿挫。
从以上评述来看,陈氏论周之沉郁顿挫,王氏之以清真词比少陵诗,都主要着眼于其写作功力、技巧上的相似。综上而言,周词的沉郁顿挫,若以杜甫早期的“以学力胜”:富于情彩,有蔚然深秀之貌;深于章法,文字技巧熟练来比较,差为近之。但周氏学杜主要是从技法修辞等法度上下功夫,而思想、气度、人格却是不可强学而致的,且周氏严守“诗庄词媚”之界限,多以词抒写男女之情和羁旅之怀,因此只能在章法修辞上或局部的风格特征上得杜诗之一鳞半爪。而辛弃疾本身沉雄厚重、刚拙不驯的个性、坎坷曲折的人生经历以及悲剧性的时代氛围的浸染都与杜甫相似;尤为重要的是,他与杜甫都有致君尧舜、心忧天下的胸怀,且又以作诗的精神作词,表现自己整个的人格和志向,故而更多地学到了杜甫因全力抒写深厚博大的忧患感和责任感而形成的沉郁顿挫之风。因此若要论其“忧愤深广,波澜老成”,唐宋词人中,则惟稼轩词可以继之。
较之周邦彦,陈廷焯更多地以“沉郁顿挫”论稼轩,仅摘数例:
辛稼轩,词中之龙也,气魄极雄大,意境却极沉郁。〔12〕(P3791)
稼轩《水调歌头》诸阕,直是飞行绝迹。一种悲愤感慨郁结于中,虽未能痕迹消融,却无害其为浑雅,后人未易摹仿。〔12〕(P3791—3792)
稼轩词自以《贺新郎·别茂嘉十二弟》一篇为冠,沉郁苍凉,跳跃动荡,古今无此笔力。〔12〕(P3791)
稼轩有吞吐八荒之概,而机会不来,正则可以为郭、李,为岳、韩,变则即桓温之流亚。故词极豪雄,而意极悲郁。〔12〕(P3925)
感激豪宕,苏、辛并峙千古。然忠爱恻怛,苏胜于辛;而淋漓悲壮,顿挫盘郁,则稼轩独步千古矣。〔17〕
沉郁顿挫中自觉眉飞色舞。笔力雄大,辟易千人。〔14〕
郁勃肮脏,笔力恣肆,声情激越。〔14〕抑扬顿挫,跌宕生姿。〔14〕
除去明用“沉郁顿挫”作评语外,陈氏还有许多类似的评语,如“雄奇兀奡”、“跌宕沉切”、“骨力坚拔”、“其势崚嶒”等,尤其《词则》评《酒泉子》(“流水无情”)时,更是非常明确地说:“悲而壮,阅者谁不变色?无穷感喟,似老杜悲歌之作。”
从以上评语来看稼轩词,其“沉郁顿挫”之内涵,都极似杜诗的“忧愤深广,波澜老成”。蔡嵩云《乐府指迷笺释》则直接将辛弃疾比之于杜甫:“稼轩词沉郁顿挫,气足神定,于诗似少陵。”〔18〕(P78)
辛弃疾沉郁顿挫风格的根源与杜甫一样,如司空图《诗品》所强调的“大道日丧,若为雄才;壮士抚剑,浩然弥哀”,是由强烈的忧患意识所致。杜甫与辛弃疾显然都是为国而悲慨者,将杜、辛相提并论,既是强调他们在诗史、词史上地位的可比性,也是指他们在思想、创作风格上的相似性。辛词的沉郁顿挫,主要谓其丰厚的社会内涵与主体情志的契合,是壮志不得伸而形诸于文学的沉重和抑闷不快的底蕴。
稼轩词中,既多“壮士抚剑,浩然弥哀”的愤激悲慨之作,如《八声甘州》“故将军饮罢夜归来”;也多“裂竹之声,何尝不潜气内转”〔19〕(P3994)的沉雄郁积之作,如《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但最得老杜沉郁顿挫之“忧愤深广,波澜老成”神髓的,是他那些“敛雄心,抗高调,变温婉,成悲凉”〔20〕(P1643)的作品,此处仅举被称为辛词压卷之作的《摸鱼儿》为例,以见一斑。此词主旨乃忧国伤时之中叹己之壮志难酬,与杜甫晚年所作《秋兴八首》、《登高》、《登楼》诸作精神相通,却多了一层怨妒之意。全词以“春”为眼,总以“春归”之象寓忧国伤时之旨。劈头十三字“更能消几番风雨,匆匆春又归去”,势如风雨袭来,呼啸激荡,而国事已危,还能经得起几番摧残?屡遭挫折之志士郁积心底的忧国之情喷发而出,激切不平。陈廷焯以为“起处‘更能消’三字,是从千回万转后倒折出来,真是有力如虎”〔12〕(3793),其忧愤深广的沉郁之思而又以千回万转、波澜起伏的顿挫之力发之,更显夭矫多姿。尤妙在此词“肝肠似火,色貌如花”〔21〕(P108)的摧刚化柔伎俩:志士之愤慨悲郁是以儿女之惜春怨妒出之,而惜春之情也好,怨妒之意也罢,又不直抒,却吞咽宛转,灏气潜行。全词于落红芳草之凄美意象中寓忧国伤时之深情,于美人惜春怨妒之情中闻志士愤世疾仇之呼号,初遇之则缠绵悱恻,细味之则慷慨激昂,婀娜中特具刚健,妩媚中不乏遒劲,正是稼轩词“惊雷怒涛中时见和风暖日”〔12〕(P3916)的最好体现。无怪乎陈廷焯叹其“姿态飞动,极沉郁顿挫之致”〔12〕(P3793);陈洵称其“寓幽咽怨断于浑灏流转中”〔22〕(P4877);梁启超赞其“回肠荡气,至于此极。前无古人,后无来者”〔23〕(P4309),真可谓词中“沉郁顿挫”之第一奇篇。
三、“转益多师是汝师”与“书万卷,笔如神”——兼备众体开新风
杜甫作于上元二年(761)的《戏为六绝句》,比较系统地表现了杜甫的文学观:即主张兼取众长,对六朝以来的作家应该具体分析,而不应一律排斥;提出要广泛吸取前人创作经验,具备“别裁伪体”的批判精神;指出只有转益多师,镕今铸古,把艺术修养建筑在博大深厚的基础上,才能使完美的形式表现充实的内容。
杜甫《偶题》云:“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作者皆殊列,名声岂浪垂?骚人嗟不见,汉道盛于斯。前辈飞腾入,余波绮丽为。后贤兼旧制,历代各清规。法自儒家有,心从弱岁疲。……”明代王嗣奭《杜臆》评之曰:“此篇乃一部杜诗总序。”释之曰:“少陵一生精力,用之文章,始成一部诗集。……文章千古事,便须有千古识力。得失寸心知,则寸心具有千古。此文章家秘密藏,为古今立言之标准也。”“作者殊列,名不浪垂,……谓其所就虽有不同,然寸心皆有可独知者在也。”其实这里反映了杜甫的诗歌史观:他认为大凡一种诗体在兴起之初,多呈现“飞腾”之景,而后渐趋“绮丽”,后来者只有既兼收并蓄其“旧制”,又加以创新,体现自己之“贤”,才能有所发展,自成一家,并与历代前贤相并。这正是杜甫诗歌能集前代之大成而又能开一代之新风的基础。杜甫诗歌中常见对前贤及时贤的称颂,李白自然是其赞颂最多者:“白也诗无敌,飘然思不群”(《春日忆李白》),“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寄李十二白二十二韵》)。此外,庾信的“清新”,鲍照的“俊逸”(《春日忆李白》),王维的“最传秀句寰区满”(《解闷》),孟浩然的“清诗句句尽堪传”(《解闷》),高适、岑参的“高、岑殊缓步,沈、鲍得同行”(《寄彭州高三十五使君适虢州岑二十七长史参三十韵》),元结的“两章对秋月,一字偕华星”(《同元使君〈舂陵行〉》),都是他取法的榜样。仅在《解闷》五首中涉及的人物就有自汉而下李陵、苏武、曹植、刘桢、谢灵运、谢朓、沈约、范云、阴铿、何逊、孟浩然、王维、薛璩、孟云卿等十四人之多。
他的诗歌创作也忠实地实践了自己的诗学思想。元稹《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并序》说:
至于子美,盖所谓上薄风、骚,下该沈、宋,古傍苏、李,气夺曹、刘,掩颜、谢之孤高,杂徐、庾之流丽,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矣。……诗人以来,未有如子美者!时山东人李白,亦以奇文取称;时人谓之李、杜。予观其壮浪纵恣,摆去拘束,模写物象,及乐府歌诗,诚亦差肩于子美矣。至若铺陈终始,排比声韵,大或千言,次犹数百,词气豪迈,而风调清深,属对律切,而脱弃凡近,则李尚不能历其藩翰,况堂奥乎?〔24〕(卷五六)
自此论一出,便为世所公认,后继阐发者不绝。王安石曾言:“白之歌诗,豪放飘逸,人固莫及;然其格止于此而已,不知变也。至于甫,则悲欢穷泰,发敛抑扬,疾徐纵横,无施不可。故其诗有平淡简易者,有绮丽精确者,有严重威武若三军之帅者,有奋迅驰骤若泛驾之马者,有淡泊闲静若山谷隐士者,有风流蕴藉若贵介公子者。盖其诗绪密而思深,观者苟不能臻其阃奥,未易识其妙处。夫岂浅近者所能窥哉?此甫之所以光掩前人,而后来无继也。”〔25〕秦观《韩愈论》亦云:“杜子美者,穷高妙之格,极豪逸之气,包冲淡之趣,兼峻洁之姿,备藻丽之态,而诸家之作所不及焉。然不集诸家之长,杜氏亦不能独至于斯也。”〔26〕(P480)张戒《岁寒堂诗话》说:“(杜甫)在山林则山林,在廊庙则廊庙,遇巧则巧,遇拙则拙,遇奇则奇,遇俗则俗,或放或收,或新或旧,一切物,一切事,一切意,无非诗者。”〔8〕(P464)王世懋曰:“子美集中贺奇仝癖,郊寒岛瘦,元轻白俗,无所不有,此真杜诗也。”〔27〕(P1156)类似的论述还有不少,均推杜甫为最伟大的集大成之诗人,既集体式之大成,又集风格之大成。辛弃疾虽未有杜甫这样明确的文学主张的表达,但他对杜甫“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曾反复引用、化用,如:“书万卷,笔如神”(《鹧鸪天》),“胸中万卷藏书”(《汉宫春》),“叹诗书万卷致君人”(《满江红》),“绝编能自苦,下笔定成章”(《闻科诏勉诸子》)。对杜甫提及的许多大家,他也同样仰慕:“五车书,千石饮,百篇才”(《水调歌头》),“看君才未数,曹刘敌手;风骚合受,屈宋降旗”(《沁园春》),“儿曹不料扬雄赋”(《贺新郎》),“诗在阴何侧畔”(《西江月》),“文烂卿云,诗凌鲍谢”(《沁园春》),“尚能诗似鲍参军”(《和任帅见寄之韵其三》)。此外,还有对杜甫后的唐宋前贤及时贤的学习:“平生插架昌黎句”(《玉楼春》),“更着诗翁杖屦,合作雪堂猜”(《水调歌头》)。由此看来,他也是主张博览群书、广取养料、转益多师的。
而且,辛弃疾与杜甫一样,有着“转益多师”、兼学众体的实践。在他的词集中,有用天问体的《木兰花慢》(“可怜今夕月”),有用招魂体的《水龙吟》(“听兮清佩琼瑶些”),有效白乐天体的《玉楼春》(“少年才把笙歌盏”),有学花间体的《唐河传》(“春水,千里”),有仿朱希真体的《念奴娇》(“近来何处”),有学易安体的《丑奴儿近·博山道中》(“千峰云起”)……诸如此类,林林总总,难以尽列。
在广收众取的实践中,辛弃疾熔铸了多种风格体式。如果说,杜诗是一个众体兼备、涵汇万状的海洋,那么辛词则是一个横竖烂漫、倾荡磊落的天地奇观:豪放者如《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雄健者如《沁园春·灵山齐庵赋》),婉丽者如《祝英台近·晚春》,典雅者如《贺新郎·别茂嘉十二弟》,谐俗者如《沁园春·将止酒,戒酒杯使勿近》,素淡者如《清平乐·村居》,奇诡者如《兰陵王·恨》等等。吴衡照《莲子居词话》卷一云:“辛稼轩别开天地,横绝古今。论、孟、诗小序、左氏春秋、南华、离骚、史、汉、世说、选学、李杜诗,拉杂运用,弥见其笔力之峭。”这不仅是言其表现手法,而且还看到了其因取法多方而风格多变的特点。
杜甫又是开风气的先行者。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卷七云:“诗至杜陵而圣,亦诗至杜陵而变。顾其力量充满,意境沉郁。嗣后为诗者,举不能出其范围,而古调不复弹矣。故余谓自风骚以迄太白,诗之正也,诗之古也。杜陵而后,诗之变也。……昔人谓杜陵为诗中之秦始皇,亦是快论。”又说:“杜陵忠爱之忱,千古共见。而发为歌吟,则无一篇不与古人为敌。其阴狠在骨,更不可以常理论。故余尝谓太白诗,谨守古人绳墨,亦步亦趋,不敢相背。至杜陵乃真与古人为敌,而变化不可测矣。固由读破万卷,研琢功深。亦实为古今迈等绝伦之才,断不能率循规矩,受古人羁缚也。”近人胡小石同样也看到了这一点,他在《李杜诗之比较》中对此有进一步的阐发:“李守著诗的范围,杜则抉破藩篱。李用古人成意,杜用当时现事。李虽间用复笔,而好处则在单笔;杜的好处,全在排偶。李之体有选择,故古多律少;杜诗无选择,只讲变化,故律体与排偶都多。李诗声调很谐美,杜则多用拗体。李诗重意,无奇字新句,杜诗则出语警人。李尚守文学范围,杜则受散文化与历史化。从《古诗十九首》至太白作个结束,可谓成家;从子美开首,其作风一直影响至宋明以后,可云开派。杜甫所走之路,似较李白为新阐,故历代的徒弟更多。总而言之,李白是唐代诗人复古的健将,杜甫是革命的先锋。”〔28〕(P20)其他学者尚还有众多相似论述,兹不赘言。在开风气方面,辛弃疾也算得上是一个“革命的先锋”。虽然传统词风在苏轼手上开始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至有论者视其为豪放派在北宋的领军人物,但实际上,真正称得上“豪放”的作品在其词集中仅有一二十首,其他大量的作品都只能归于其他风格,不少词尚未完全脱离传统的窠臼。至辛弃疾,方以横刀跃马的“壮士”之志大量抒写英雄之词,从根本上改变了以婉娈风情取胜的“美人”之词,在南宋形成了一个以他为首的豪放词派。其开宗立派之功,以《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得最确:“稼轩词慷慨纵横,有不可一世之概,于倚声家为变调;而异军特起,能于翦红刻翠之外,屹然别立一宗,迄今不废。”陈廷焯誉其为“词坛飞将军”,可谓形容贴切。
概而言之,杜甫和辛弃疾以其忧国忧民的博大襟怀,因其壮志难酬、坎坷不断的人生际遇,加上过人的天赋和转益多师、敢于出新的后天学养及艺术追求,各自熔铸出了大量瑰丽多姿、深切动人的诗词作品,分别具备了“诗史”与“词史”的意义,并且在风格的沉郁顿挫以及集大成和开风气等方面表现出了很大的相似性。
〔1〕缪钺.论辛稼轩词〔A〕.诗词散论〔C〕.上海:开明书店,1948.
〔2〕宋祁.杜甫传赞〔A〕.新唐书〔C〕.四库全书本.
〔3〕陈岩肖.庚溪诗话〔A〕.丁福保.历代诗话续编〔C〕.中华书局,1983.
〔4〕勃兰兑斯.十九世纪文学主流·流亡文学〔M〕.张道真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1980.
〔5〕沈松勤.北宋文人与党争〔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6〕周济.介存斋论词杂著〔A〕.唐圭璋.词话丛编〔C〕.北京:中华书局,2005.
〔7〕刘熙载.艺概·词概〔A〕.唐圭璋.词话丛编〔C〕.北京:中华书局,2005.
〔8〕张戒.岁寒堂诗话〔A〕.丁福保.历代诗话续编〔C〕.中华书局,1983.
〔9〕刘扬忠.辛弃疾词心探微〔M〕.山东:齐鲁书社,1990.
〔10〕安旗.“沉郁顿挫”试解〔A〕.杜甫研究论文集(第三辑)〔C〕.北京:中华书局,1963.
〔11〕张耒.贺方回乐府序〔A〕.李逸安等点校.张耒集〔C〕.北京:中华书局,1990.
〔12〕陈廷焯.白雨斋词话〔A〕.唐圭璋.词话丛编〔C〕.北京:中华书局,2005.
〔13〕罗忼烈.清真词与少陵诗〔A〕.词学(第四辑)〔C〕.上海:华东师大出版社,1986.
〔14〕陈廷焯.云韶集〔M〕.转引自孙克强、杨传庆点校整理.云韶集辑评〔J〕.中国韵文学刊,2010(3).
〔15〕陈廷焯.词坛丛话〔A〕.唐圭璋.词话丛编〔C〕.北京:中华书局,2005.
〔16〕王国维.人间词话删稿〔A〕.唐圭璋.词话丛编〔C〕.北京:中华书局,2005.
〔17〕陈廷焯.词则·放歌集〔M〕卷一辛弃疾《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上眉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18〕蔡嵩云.乐府指迷笺释〔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
〔19〕谭献.复堂词话〔A〕.唐圭璋.词话丛编〔C〕.北京:中华书局,2005.
〔20〕周济.宋四家词选目录序论〔A〕.唐圭璋.词话丛编〔C〕.北京:中华书局,2005.
〔21〕夏承焘.肝肠似火,色貌如花〔A〕.唐宋词欣赏〔C〕.北京:北京出版社,2002.
〔22〕陈洵.海绡说词〔A〕.唐圭璋.词话丛编〔C〕.北京:中华书局,2005.
〔23〕梁启超.饮冰室评词〔A〕.唐圭璋.词话丛编〔C〕.北京:中华书局,2005.
〔24〕元稹.元氏长庆集〔M〕.四部丛刊本.
〔25〕陈正敏.遁斋闲览〔A〕.转引自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C〕卷六.廖德明校点.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
〔26〕秦观.韩愈论〔A〕.周义敢、程自信等.秦观集编年校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
〔27〕转引自仇兆鳌.杜诗镜铨·附录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28〕胡小石.李杜诗之比较〔A〕.杜甫研究论文集第一辑〔C〕.北京:中华书局,19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