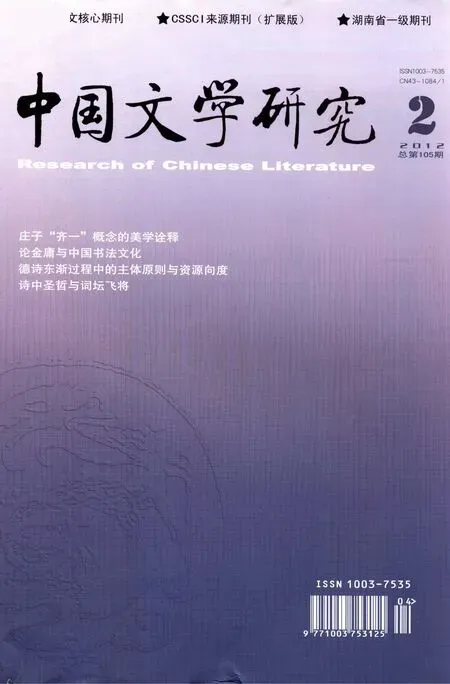论蒲风新诗理论的多重内涵
杨俏凡
(嘉应学院文学院 广东 梅州 514015)
在中国诗歌会中,蒲风是一位将诗歌理论与创作实践结合得最为紧密的作家,对诗人的责任、诗歌的任务与发展方向、诗歌的创作技巧、诗坛的现状与未来都有自己独立的思考,并将这些思考有机地融入自己的诗论建构和诗歌创作之中。他认为:“诗人,爱好诗歌的人,对于诗歌理论都不能漠视,反过来,要是诗人要想真正做个时代的诗人,他更加不能不有借重于理论的帮助。”〔1〕为此,他不余遗力地撰写诗论,以此来指导自己和影响他人。蒲风的诗论集中在其《抗战诗歌讲话》和《现代中国诗坛》两部著作中,还有一些保留在为他人诗集所写的序言或诗评中。笔者认为,蒲风的新诗理论内涵非常丰富,他提出了新现实主义的诗歌主张,全力倡导大众化诗歌,并对中国诗坛进行梳理和评论。蒲风的诗论在当时曾经起到过积极的效果,但也存在遮蔽乃至消解诗歌本质的缺陷。
一、新现实主义的新诗主张
恩格斯在致玛·哈克奈斯的信中说:“现实主义的意思是,除细节的真实外,还要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这里的典型环境是指政治、社会、经济的具体的生活现实。由此衍生出来的“现实主义”就是指“真实客观地再现社会现实”。但就蒲风而言,他所信奉的现实主义不同于一般的现实主义,他依据自己的艺术体验提倡的是所谓“新现实主义”:“整个社会现实都是我们写作抒情诗的好资料……我们的唯一手法,毫无疑问的应是新现实主义。”〔2〕(P34)“把握住现实,为现实而讴歌吧!”〔3〕(P1)“我们现时代的诗人不能光是陷于现实的泥沼里,而是应该活跃在指导现实,讴歌或鼓荡现实,咒诅或愤恨现实,鞭打或毁灭现实里。”〔3〕(P2)在蒲风看来,诗歌创作不仅要反映社会生活,还应该干涉现实以彰显其主体性。应该说,这些观点尽管夸大了诗歌的社会效用,但在当时还是比较新颖的。由是观之,如果我们以1936年为界把蒲风的创作分为前期和后期的话,那么蒲风前期的思想主要指向对国民党政府合法性的消解与批判,后期则指向对帝国主义侵略者的反抗与声讨。
1、为现实而歌
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中期的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是中国最为动乱和黑暗的历史时期。为了适应政治斗争形势的需要,为了更好地宣传无产阶级的革命主张,1930年3月2日,在中国共产党的指示下,“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上海成立了,它以传播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提倡发展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为己任,这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影响非常深远。几乎与此同时,中国诗歌会作为“左联的外围组织、外围团体”〔4〕(P72)成立了。
中国诗歌会自1932年9月成立之日起,就高举现实主义大旗,积极呼吁诗人要“捉住现实”。在《新诗歌》的发刊词中,高呼“我们要捉住现实/歌唱新世纪的意识”(这里的“新世纪的意识”就是指“无产阶级的意识”),并倡导诗人要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去把握现实、反映现实。这里的“现实”,其一是指以国民党为代表的各种极权统治,其二是指农民的苦难生活,其三是指当时诗坛的所谓“颓靡文风”。他们在《缘起》中声称:“在次殖民地的中国,一切都浴在急风狂雨里,许许多多的诗歌的材料,正赖我们去摄取,去表现。但是,中国的诗坛还是这样的寂寞;一般人在闹着洋化,一般人又还只是沉醉在风花雪月里……把诗歌写得和大众距离十万八千里,是不能适应这伟大的时代的。”〔5〕(P46)是时,中国诗坛上活跃着两大诗歌流派——追求象征主义的现代诗派和追求唯美主义的新月诗派。现代诗派以戴望舒为代表,他为新诗带来了新的艺术维度,并推动现代诗派走向艺术成熟;而新月诗派以徐志摩为代表,早期已在文坛声名显赫,到中国诗歌会成立之时,影响仍然极大。但在左翼文艺界看来,他们都囿于个体的情感维度和精神视域,且远离社会现实和底层民众。30年代初的中国诗坛,除了这两大诗派的诗人,自然还有郭沫若、蒋光慈、殷夫等革命诗人以及中国诗歌会的左翼诗人们。中国诗歌会诗人在艺术成就上自然无法与现代诗派和新月诗派相提并论,但诗歌主张要激进得多,所以点名批评了现代诗派和新月诗派的所谓“缺陷”,并彰显了自身的主张和立场,正如蒲风所说:“象新月派的象秋风吹动树叶的声音,或小蜜蜂的采花的弱鸣,我们是不必模仿的,我们不仅需要汽笛般的歌唱,而且更需要海洋的喊叫咆哮,不怕又是风狂,又是雨暴,我们要打着时代的大鼓向前!”〔6〕(P700)
正是出于要纠正诗坛所谓“无病呻吟”的病状,以及高扬诗歌的社会功能、密切配合革命形势的目的,中国诗歌会才定下了诗人应该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来“捉住现实”和改造现实的方针。对于这些方针,蒲风坚决贯彻执行。他说:“凡能真正呼吸着现实生活,凡能真正投身于群众的热烈而英勇的斗争中,冲击起感情之波,凡能认识艺术之应为自由解放尽点任务,无论何时都应该属于大众的一方面的,他们的正确的路都是新现实主义,亦即是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7〕(P730)蒲风用革命现实主义精神来指导自己的诗歌创作,用手中的笔作为投向敌人的武器,号召民众为自由民主解放而斗争。他又说:“最新的新现实主义着重于事体的发展的过程而不只是表面的现象的描摹。要观察、体认、了解现实,决不仅在抓住某一社会现实的现象。”〔8〕(P578)即在正确反映现实的基础上,要抓住现实的本质,要理智冷静地分析现实生活,既不可盲目乐观,也不要过分悲伤,要有革命乐观主义精神,要对未来充满信心和希望。对当时的社会生活,蒲风是这样分析的:“生活是灰黯、阴沉、悒郁、苦闷、悲哀、惨戚……另一方面,生活又是公理、正义的探求,追求光明的战斗,慷慨高歌,奋勇杀敌,严肃而积极。”〔9〕(P582)显然,30 年代的中国社会尤其是农村的生活场景非常阴暗悲惨,恰如蒲风在《妒》中所演示的那样:“云,张开黑的翅膀,/使劲地吞食了月亮。/海面黝黯、黝黯,/云儿犹在展开黑的翅膀。”但蒲风在这种社会背景下作出了自己的积极选择,那就是以战斗的姿态去探求公理和正义,以激昂的诗歌去鼓舞民众。是故他强调说:“歌唱是力量”;“诗人的任务是表现与歌唱。歌唱为唯一的武器。”〔10〕(P585)
蒲风身体力行地实践着这些诗歌主张,并没有被1927年的白色恐怖所吓倒,从第一部诗集《茫茫夜》开始,他就真实地描绘了农村的生活与斗争场景,刻画了众多英勇的革命者形象,传达了光明与黑暗搏斗的抗争意识。在《鸦声》中,他强调大众已不再是任人宰割的羔羊,他们“都起来自动反抗,统治者们无日不在魂飞魄荡”。在《从黑夜到光明》中,他告诉读者,当黑暗一点点过去,光明也会一点点到来。而代表蒲风浑身正气的力作,是1935年底出版的《六月流火》。这首长篇叙事诗真实地描绘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国共之间“围剿”与“反围剿”的残酷斗争,诗人告诉读者:人民革命斗争的胜利之火,正在以“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之势,以“火在天空,火在地上”的气势,烧出“新生命的辉煌”。
值得注意的是,1936年之前的中国虽然已遭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但国内阶级斗争仍处于白热化阶段。是故,蒲风在前半期的诗作中,大量描绘了农村生活的苦难、地主阶级的剥削、国民党政府的暴力镇压等,这都是作者适应时代的需要,要求诗歌“为现实而歌”的产物。在蒲风这里,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诗歌则是时代的号角,随着时代的风云变幻,他的诗歌主张也在随之发生改变。
2、为国防而战
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水深火热,日本帝国主义趁着中国内战频仍,快速侵占了中国大片领土。1936年1月,文艺界正式提出“国防文学”的口号,接着“国防戏剧”“国防诗歌”“国防音乐”等口号纷纷出现。站在时代前列的中国诗歌会则大力倡导“国防诗歌”和抗战诗歌,蒲风自然积极响应这些主张。
蒲风首先明确告诉诗人们,现阶段的任务是“反帝反汉奸”。〔3〕(P5)他要求诗人紧跟时代,紧密配合当时的革命任务,因为“一个诗人,他应该是时代社会的预言家,时代的先驱者”,〔3〕(P2)要为“中华民族的自由,解放”而奋斗。〔3〕(P3)面对国仇家难,蒲风仿佛一名“精神界战士”,豪情满怀地用诗歌去号召、感染同胞,来唤起民众抗击敌人的热情。蒲风认为:“论起‘国防诗歌’来,我想‘心防’最关逼切。”〔11〕(P583)关于什么是“心防”,他没有做更多的解释,但他是从人的心理、思想和意识层面去审视这一概念的。他意识到,要摧毁一个人先要摧毁他的心理防线,而日本帝国主义要瓦解的就是中华民族的心理防线。所以,提倡“国防诗歌”的目的是为了激发民众的爱国热情,是为了唤醒、鼓舞和号召民众去抗日,进而让他们以汹涌澎湃之势投入到保家卫国的斗争中去,到那时日本帝国主义必然会溃败。蒲风的国防诗歌理论彰显了他的爱国主义精神,但显然存在高估诗歌的启蒙功效等问题。
“国防诗歌”如何书写?蒲风在《怎样写“国防诗歌”》中认为,首先要“在现实里找题材”:“我们一方面想象,计划,实地去做国防工作,一方面得想象到东北民众的痛苦,义勇军的苦斗,一方面则想象到监视、攻击那些出卖民族国家的汉奸活动。”〔12〕(P688)同时,还要打起足够的热情:“所谓‘打起热情来’是为当前的凄惨但除此别无出路的英勇的抗敌战斗,为天灾人祸而流离失所的万千同胞,为一切走向胜利的新生力量……而打起同情的热情的歌唱来。”〔13〕(P720)陆机在《文赋》中说:“诗缘情而绮靡。”诗歌因情而发,是诗人主观感情的自然流露。所以,蒲风认定诗人应该与劳苦大众融为一体,真切地去感受他们的爱憎和体验他们的辛酸,如此才能使诗歌更具感染力和可接受性。而且,“这个时辰,个人不能脱离社会国家而存在,敌人杀了我一个人,割了我们一块土地,都等于杀害了自己的亲人,或割了自己的皮。”〔3〕(P8-9)至于“国防诗歌”的写作方法,蒲风认为:“我们的唯一手法,毫无疑问的应是新现实主义。”“我们应有我们的世界观,我们应有我们所要歌唱的目的、倾向,在平凡的现实及现实事故中去剪裁,组织。”〔2〕(P34)如果说,中国诗歌会成立之时强调的是阶级解放的话,那么当1936年“国防诗歌”兴起之后,它所强调的就是民族解放了。总之,蒲风认为诗人歌唱的倾向“显然为中华民族自由解放,这便是我们的‘倾向’,这便是我们的第一义性(最前进性)的歌唱”。〔14〕(P14)
客观地说,蒲风的一生非常短暂,但他一直致力于倡导和发展新诗运动。无论是在理论建构还是在揭露黑暗现实和讴歌抗日战争的创作实践过程中,蒲风一直坚守自己的诗歌主张,为实现自己的文学理想而鞠躬尽瘁。可以说,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蒲风怀着高度的历史责任感,积极投身到抗战洪流中,将诗歌的社会功能发挥到了极致,但可惜的是,他过于强化诗歌的宣传功能,这种工具理性的泛滥势必会遮蔽诗歌的审美功能,这是他所未曾预料到的。
二、全力倡导大众化诗歌
在中国新诗的发展道路上,蒲风和其他中国诗歌会成员的一大贡献就是全面推进了诗歌大众化的进程。中国是个古老的诗的国度,历代的文人墨客都给后人留下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诗歌宝藏。但不可否认的是,古典诗歌自诞生之日起就有缺陷,其中最大的缺陷就是局限于狭小的文人圈子里,它既是文人骚客阐明心志交际应酬的介体,也是贵族阶层赏花弄月的玩物,但唯独跟普通劳苦大众相距甚远。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白话新诗终于颠覆了文言旧诗一统诗坛的神话地位,并渐渐形成了一股不可遏止的文学思潮。这种翻天覆地的变化使得中国新诗有了走向大众化的可能性。但由于诗歌大众化进展缓慢,因此在新诗发展初期,它与民间社会或曰底层民众仍然相距甚远。
为了改变新诗发展的这种狭隘性,为了时代发展的需要,中国诗歌会一开始便高举“诗歌大众化”的旗帜,积极推进新诗通俗化的发展。什么是大众化呢?蒲风认为:“所谓大众化,是指识字的人看得懂,不识字的人也听得懂,喜欢听,喜欢唱。”〔14〕(P19)这一主张受到了鲁迅的赞赏和支持。鲁迅曾说过:“我以为内容且不说,新诗先要有节调,押大致相近的韵,给大家容易记,又顺口唱得来。”〔15〕(P556)鲁迅的支持使得蒲风受到了极大的鼓舞,他把推进诗歌的大众化作为自己工作的重中之重,不仅积极参与理论探讨,更在创作上亲身加以实践。蒲风对诗歌大众化的要求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诗歌内容的大众化;二是诗歌形式的大众化;三是作家自身的大众化。
1、诗歌内容的大众化
蒲风认为:“我们的写诗并非为了消愁,排遣。我们是对准大众吹送喇叭,我们的任务是要大众都清醒,奋勇前进,踏着时代的潮流的。”〔14〕(P19)写诗对于蒲风和其他中国诗歌会同仁来说,是一种庄严的社会责任,也是一个政治任务,诗人既是作家,又是战士,他的武器就是手中的笔,诗人就是“时代的前哨”和“大众的良朋”,还应该是“时代社会的预言家,”“时代的先驱者”。因此,蒲风要求诗歌要为现实而作,要真实地表现现实生活,要能够号召民众并唤起他们的激情,要能够与当时的时代精神紧密配合。
明确了诗人的任务,也就明确了诗歌书写的内容。蒲风认为:诗歌要“写前线的士兵生活,战争情况,胜利颂读”,“写农工的生活,如何的为侵略者所扰害”,“嘲笑敌国人民之如何被蒙蔽,受欺骗”〔14〕(P21);诗歌要如实地反映敌人的残酷、战士的奋勇杀敌、民众的疾苦,因为只有诗歌的内容“大众化”了,才能引起民众的情感共鸣,才能唤起他们的爱国热情,进而为民族自由解放去英勇奋斗。在蒲风这里,诗歌的现实主义精神得到了极大的张扬,诗歌第一次与社会生活毫无间隙地结合在一起,并成为教化民众的最有效最强大的手段——“诗歌已被一切诗歌工作者当作抗敌的唯一武器而使用着。”〔16〕(P39)
对于国防诗歌,蒲风认为:“它的内容应该最低限度包含这两个方面:一、以反帝及组织民众鼓吹民众锻炼民众为内容;二、以大众化为唯一条件,作为形式去传达内容。”〔17〕(P49)即:用大众化的形式去表达国防诗歌的内容。在30年代中后期的文坛上,由于民族战争的激化,“国防”成为当时诗歌创作的唯一主题和目标,虽然这种过分强调诗歌的政治功利性的倾向后来倍受批评,但无可否认的是,诗歌在特殊的战争年代里发挥了它的社会功能,从狭小的书房走向了广阔的农村,从有闲阶级走向了广大的无产阶级,这就为文学的通俗化、大众化工程立下了汗马功劳。
蒲风之所以要求诗歌内容要具有普遍性、现实性和大众性,其实是想通过大众化诗歌这种形式来影响和启蒙大众,让大众找到前进的目标,与诗人实现情感上的共鸣,进而为当时的民族解放事业作出贡献。
2、诗歌形式的大众化
蒲风一方面在题材上要求诗歌的大众化,另一方面在诗歌形式上要求采用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以便大众容易接受和乐于接受“大众化”了的诗歌。
怎样才能使诗歌让所有的人都看得懂?蒲风认为:“一、用现代语言,尤其是大众所能说的语言,为此,新诗人得积集一些大众的词汇。二、用自己的口去朗读,使能充分有朗读性。三、可能歌唱的,最好能便于大众合唱的。”〔14〕(P19)也就是说,蒲风极力强调诗歌的语言要口语化,要从俗字俗语入手,还要有音乐性,即诗与音乐的融合。这与中国诗歌会的宗旨是完全一致的。穆木天在《发刊诗》中曾说过:“我们要用俗言俚语,把这种矛盾写成民谣小调鼓词儿歌,我们要使我们的诗歌成为大众歌词,我们自己也成为大众中的一个。”同样,蒲风主张把歌谣、小调、鼓词、儿歌等民间艺术形式融入新诗,目的是为了让新诗走向大众,以便“教养、训导大众”。蒲风用自己的创作实践着自己的理论,如歌谣集《摇篮歌》、儿童诗集《儿童亲卫队》、明信片诗集《真理的光泽》,以及诸多讽刺诗、客家方言诗、歌词等,这些都是他努力探索诗歌新形式的产物。
关于新诗的形式问题,蒲风在《现阶段的诗人任务》一文中认为,可以在旧形式的基础上创造新形式:“一、旧瓶装新酒,模仿旧形式,用歌谣时调教育大众,锻炼自己。二、批判采用旧形式,接受一切长处,踢弃一切赘述及呆滞强凑的不近真实的成份。三、创造新形式——以容易使人了解,听得懂为主要目标。”在上述三项中,蒲风认为第三项最重要,那才是“新诗歌的出路”。接着,他强调可以通过三种途径使新诗走向大众化:一是组织诗歌座谈会,让新老诗人交流心得体会;二是组织读诗班,把诗歌拿到大众中去朗读,既可以教育他们,还可以检验诗歌大众化的程度,以便改进;三是组织歌咏会。毫无疑问,蒲风抓住了当时文艺宣传工作的要害,这些群众性的诗歌朗诵运动是扩大新诗影响的快捷、有效手段之一。蒲风身体力行地实践着自己诗歌大众化的理想,每到一处(如厦门、广州、青岛等地),都极大地鼓舞了当地进步诗人写诗、读诗、颂诗的热情。
蒲风还始终强调,新诗要实现大众化必须从民众喜闻乐见的民间艺术形式上入手,要批判性地吸收其欢快的调子、灵活的形式,要去除其消极呆滞远离现实的内容,要表现与民众关系紧密的现实生活,并贯之以慷慨激昂的革命热情,这样才能使新诗真正溶入到大众中去。他说:“既然平素便不惮给与民众以普通的食粮(纵使是旧瓶新酒),复又能批判的采用民众形式的长处,当你把握着了最前进性的现实而歌唱、表现时,你的作品就会有如《义勇军进行曲》等新形式之激昂,它便必定包含有可朗读性——口语性,又是甚至是方言性,报告文学性的。一切诗歌原应是可朗读的……能够达到了这种境地,这就是货真价实的诗歌大众化。”〔16〕(P45-46)如此,蒲风就抓住了普通民众长期形成的对诗歌的审美要求,而他如此看重民间艺术形式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让大众容易听、听得懂和喜欢听“大众化”诗歌。
3、作家自身的大众化
在《现阶段的诗人任务》一文中,蒲风强调说:“我们深深了解了我们即应是劳苦大众里之一员,我们不外作了大众一员的,或众多劳苦大众的所要抒唱出来的心声。”也就是说,他要求诗人不能高高在上,应该把自己溶入到劳苦大众中去,成为他们中的一员,经历他们的苦痛,感受他们的悲欢,才能写出有真情实感的诗歌来。这些主张与中国诗歌会的宗旨是一致的。〔18〕既然要成为大众中的一个,诗人当然要溶入民众生活中去,要了解他们的困苦生活。为此,蒲风倡导诗人要有实际的生活实践,他还批评说:“我们诗人的生活经验,国防知识的贫乏,这里表现了严重的问题。”“国防决不是空话。土地不会咆哮,虽然真正要咆哮的是我们的心,而我们得用工作来表示我们的怒吼。”〔12〕(P688)蒲风还认为:有了真实的生活作为创作的题材,接着要燃起热情来:“我们要有集团的感情,我们也不能少政治热情……打起热情来为国防歌唱,歌唱是力量!”〔19〕(P822)只有用自己的激情去歌唱,去感受民众的悲欢离合,才能让自己的诗感染民众,继而教化民众。而“要想打起别人的热情来,首先要解决的就是我们自身不能没有热情。而最可珍贵的是在其为铁的社会时代下的现实内容作反映上,时代的要求是,歌唱集体的感情”。那么,如何才能获得“集体的感情”呢?那就要“向生活学习,到集体的战斗的生活里去,这是新诗人的路”。〔13〕(P719-720)
对诗歌大众化的追求是蒲风一生的理想,为此他不断尝试从民歌、方言中吸收养料,如他用客家方言创作的叙事诗《林肯,被压迫民族的救星》、《鲁西北个太阳》等就是明证。此外,他也创作了不少可谱曲的歌词、大众合唱诗、明信片诗和讽刺诗等。可惜的是,由于蒲风过于强调诗歌的大众化取向,忽视了诗歌的经典化建构,加之其艺术才情的薄弱,导致他的诗很难流传久远,这不能不说是个遗憾。
三、对中国诗坛的梳理评价
蒲风不仅创建了自己的诗歌理论,也对中国诗坛进行了回顾和整理。从晚清末年到20世纪30年代末,对新诗与旧诗、诗界革命与新诗运动、新诗发展的过程与特点等诸多方面,他都作了梳理探讨。如此系统、认真地从史的角度研究新诗的发展,蒲风可谓“中国新诗史上的第一人”。〔20〕(P114)
1、建构新诗的发生理论
蒲风对新诗的诞生有自己的独特看法,这些看法对完善新诗理论、加快新诗的健康发展有明显的意义。
(1)新诗与旧诗
关于新诗与旧诗,蒲风认为,既已产生了新诗坛,就会有旧的相对立,研究新与旧之间的差别,对于更好地建设新诗有重大的意义。蒲风先从诗歌的起源说起,他通过对旧诗与新诗的定义来比较二者的区别。他认为:“旧诗是特殊阶级的文学,范围是只在特殊阶级的士大夫才子们内;而新诗的对象是各社会民众,起码目标是要想普及于各种社会的。新诗是现社会的反映,现实的写真;而旧诗只纯是个人的娱乐,幻想,只反映了一方面的特殊生活状况……旧诗,只是狭小的中国的思想和感情;而新诗是受了外国的感化,思想,感情都不象以前那么狭小,形式与内容都有大大地不同。可以说:旧诗业已发展到最后的阶段;而新诗的前途正是无穷。”〔21〕(P10-11)蒲风从诗歌的创作者、对象、目的、文字、形式、功能、情感等方面论述了旧诗的结束与新诗的发展是诗坛进化的必然结果。那么,新诗是如何诞生的呢?关于这一点,蒲风以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为依据认定: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文学属于上层建筑中意识形态的内涵,自然会随着经济基础的变革而变革。基于此,蒲风总结出新诗诞生的原因:一是社会经济变迁的结果;二是诗歌本身的演进;三是欧美、日本自由诗的影响以及知识的增加和发展。笔者认为,这些看法在当时是非常全面和深刻的,有利于校正那种认定新诗是“西学东渐的结果”的观点。当然,仅仅以进化论视角来厘定旧体诗的衰落现象未免将问题简单化了。但客观地说,蒲风较早地、充分地探讨了新诗产生的原因,这对于学界厘清对新诗的认识、完善新诗理论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2)“诗界革命”与新诗运动
“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一场摧枯拉朽的伟大运动,在这场运动中,白话新诗打破了文言旧诗的垄断地位,渐渐成为一股不可遏制的潮流。而为了建立白话新诗的主体地位,许多文人全盘否定了传统诗歌,切断了新诗与旧诗的承继关系,认为新诗的产生完全是学习西方的结果。蒲风在认真研究了“诗界革命”之后指出,“诗界革命”对诗歌的贡献至少有6点:“1、冲破了旧诗范围。2、民族思想抬头。3、采用方言俗语。4、开始趋于写实的方面。5、打破了传统的旧格式神圣观念!6、西诗中译使人们对诗有新的概念。”〔22〕(P30)而“诗界革命”的5大缺点中“最大的是没有创造新形式”。〔22〕(P30)显然,这些归纳在当时是有建设性意义的,也表明蒲风在用自己的审美理想来观照“诗界革命”。在深入研究“诗界革命”的基础上,蒲风还提出,是时代使得“诗界革命”成为过渡到新诗的桥梁,而且新时代要求有新的诗歌内容与形式去适应它。这种看法即使在今天看来也是正确的,的确,“没有‘诗界革命’,新诗运动是不会那么容易扩展,或者根本就不会产生在‘五四’前后的呵!”〔22〕(P31)
2、对“五四”以后中国诗坛现状的分析
蒲风不仅从史的角度探讨了新诗与近代文学之间的关系,廓清了人们的认识,还着手梳理了新诗从诞生之后一直到1937年的发展状况。在《五四到现在的中国诗坛鸟瞰》一文中,蒲风以重大的政治事件作为分界点,把“五四”运动之后的诗歌发展分为4个时期:尝试期和形成期(1919~1925上)、骤盛期或呐喊期(1925下 ~1927)、中落期(1928 ~1931)和复兴期(1932 ~1937)。〔23〕(P36)然后,他详细地论述了每一个时期代表性诗人及其创作得失。他认为,尝试期以胡适为代表,冲破了旧韵句法的束缚,开阔了诗歌的题材,但还没有完全摆脱旧韵的束缚。形成期以郭沫若为代表,虽然在内容上推进了一步,形式上已完全造就,但也存在社会意识模糊这一缺陷。对于骤盛期的诗人,他认为代表前进方向的诗人是蒋光慈,而另一类表现伤感悲哀情绪的诗人是穆木天、王独清和冯乃超。他把1928~1931年称为“中落期”,是觉得这一时期的诗歌倍受束缚压迫,表面上看有诗道中落的现象,故有此一说。蒲风对中国诗坛的论述具有一定的开拓性,这是文艺界第一次从文学思潮和流派的角度来研究中国新诗坛的现状,是值得肯定的。为了更好地认识30年代的中国诗坛,蒲风又辟专章论述了三大诗歌流派。在《九·一八后的中国诗坛》一文中,蒲风认为现今诗坛虽然在外表上形成了三大流派,即新月派、现代派、新诗歌派,但新现实主义是30年代唯一的主导潮流,新月派和现代派都不外在大时代下苟延残喘。他还梳理了6年来新诗歌派所倡导的耀眼的诗歌运动。这些论述很好地总结了30年代诗坛的发展状况,促进了新诗理论的建构,进一步完善了新诗批评,对新诗的发展具有借鉴性意义。当然,由于蒲风基本上是从政治事件的角度来界定新诗发展进程的,所以存在忽视诗歌自身发展的内在动因等问题。
3、对诗人的批评
蒲风不仅积极建构自己的诗歌理论,也用这些理论指导和评价诗人们的创作。蒲风非常重视文艺批评,认为文艺批评就是文艺创作,批评风气浓郁开放的时代,也是作家创作力最为兴盛的时代。历史发展的长河已经证明了这点。所谓“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永远是文学繁荣发展的先决条件。蒲风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对前辈诗人以及同时代诗人都作了大量研究,这里仅就蒲风对几个有代表性的诗人的评论情况作一点简单介绍。
首先是对徐志摩诗歌的评价。蒲风承认徐志摩是“新月诗派的盟主”,认为他前期的诗歌有写实主义的气息,后期的诗歌则“印象主义的气息极浓,形式和技巧更加精美”,且走向不被掩饰的没落。其次是对郭沫若诗歌的评价。蒲风说:“郭沫若是新诗坛上第一个成功的人。”〔24〕(P128)他认为:郭沫若的诗在内容上积极向上,代表了“五四以来中国的向上青年”;在形式上,“虽然没有独特的创造,却有的是力,由于勃发的力而融化了旧的词藻”。而其后期的诗逐渐涤除了为艺术而艺术的缺陷,扫荡了思想上的模糊,继续保持着那种不屈的反抗精神。第三是对戴望舒诗歌的评价。蒲风从戴诗的题材和内容、形式和技巧及其诗论这三大部分作了论述分析,认为戴诗充满虚无主义色彩,“永远是看的艺术,不能朗读”,更不能拿给大众唱。第四是对温流诗歌的评价。蒲风说温流“始终是一个诗歌大众化的实践者”,他充满了青春热力,他的诗歌“没有一篇不是拿真实的生活做底子”的,所以他是一个“已有相当造就的新现实主义者”。〔25〕(P182)应该说,蒲风的这些评析是有见地的,但是他对现代诗派的断然否定未免太过偏颇了。
除了上述诗人研究,蒲风的很多诗论还散见于对其他诗人的诗集的序跋、编后语中,如他对殷夫、臧克家、杨骚、任钧、李金发等诗人及其诗作的分析,这些评析虽不全然恰当,但他是从自己的新现实主义理念出发,用自己的审美理想去观照诗坛和评价诗人的,其目的无非是为了通过比对来促进诗歌的大众化运动健康发展。在30年代中国内忧外患的背景下,蒲风还积极倡导无产阶级革命,倡导诗歌为革命现实而斗争,并以此为理论指导来进行诗歌创作,确实具有一定的现实针对性。他说:“具体地叙述、研究现代中国诗坛,是逼切需要的。一般的人尚不明白诗界的进展——纵是最近的过去与现在也复莫名其妙。因之,许多毛病也就难免重被复演着。”〔26〕(P195)其实,批评是为了更好地建设,批评更是民主精神得以激发和昂扬的手段。因此,蒲风极力提倡批评,认为批评应该成为一种风气,“优良的批评是现实的指导,启发和鼓励,可领引现实作高度的跃进。而对于症结所在,则批评常直接尽其揭发矫正的责任。”〔27〕(P752)
毫无疑问,蒲风的诗论在中国新诗发展史上起到过积极的作用,在构建和完善无产阶级诗歌理论,促使新诗走向大众化、通俗化方面作出过突出贡献。虽然蒲风的诗论存在对文学本质的曲解乃至异化的严重缺陷,从总体上来说并不完美,但其在中国新诗理论史上应该有一席之地,他的诗论主张也在当下的社会文化语境中凸显了一定的可参照性意义。
〔1〕蒲风.写在前面〔A〕.抗战诗歌讲话〔M〕.上海:诗歌出版社,1938.
〔2〕蒲风.关于抒情诗写作法的意见〔A〕.抗战诗歌讲话〔M〕.上海:诗歌出版社,1938.
〔3〕蒲风.现阶段的诗人任务〔A〕.抗战诗歌讲话〔M〕.上海:诗歌出版社,1938.
〔4〕任钧.略谈一个诗歌流派——中国诗歌会〔J〕.社会科学,1984,(3).
〔5〕转引自蔡清富.蒲风的诗歌和诗论〔A〕.蒲风诗选(上)〔M〕.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1985.
〔6〕蒲风.一九三六年的中国诗坛〔A〕.蒲风选集(下)〔M〕.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1985.
〔7〕蒲风.表现主义与未来主义〔A〕.蒲风选集(下)〔M〕.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1985.
〔8〕蒲风.关于《六月流火》——自序〔A〕.蒲风选集(上)〔M〕.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1985.
〔9〕蒲风.《生活》自序〔A〕.蒲风选集(上)〔M〕.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1985.
〔10〕蒲风.《摇篮歌》自序〔A〕.蒲风选集(上)〔M〕.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1985.
〔11〕蒲风.门面话——《钢铁的歌唱》自序〔A〕.蒲风选集(上)〔M〕.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1985.
〔12〕蒲风.怎样写“国防诗歌”〔A〕.蒲风选集(下)〔M〕.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1985.
〔13〕蒲风.打起热情来〔A〕.蒲风选集(下)〔M〕.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1985.
〔14〕蒲风.关于前线上的诗歌写作〔A〕.抗战诗歌讲话〔M〕.上海:诗歌出版社,1938.
〔15〕鲁迅.致窦隐夫〔A〕.鲁迅书信集(下)〔A〕.鲁迅全集(12)〔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16〕蒲风.目前的诗歌大众化诸问题〔A〕.抗战诗歌讲话〔M〕.上海:诗歌出版社,1938.
〔17〕蒲风.诗歌大众化的再认识〔A〕.抗战诗歌讲话〔M〕.上海:诗歌出版社,1938.
〔18〕因为穆木天曾在中国诗歌会会刊的《发刊诗》中说过:“我们要使我们的诗歌成为大众歌词,我们自己也成为大众中的一个。”
〔19〕蒲风.九·一八后的中国诗坛〔A〕.蒲风选集(下)〔M〕.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1985.
〔20〕盛翠菊.试论蒲风的现实主义诗歌理论〔J〕.徐州教育学院学报,2001,(3).
〔21〕蒲风.新诗与旧诗〔A〕.中国现代诗坛〔M〕.上海:诗歌出版社,1938.
〔22〕蒲风.晚清的诗界革命〔A〕.中国现代诗坛〔M〕.上海:诗歌出版社,1938.
〔23〕蒲风.五四到现在的中国诗坛鸟瞰〔A〕.中国现代诗坛〔M〕.上海:诗歌出版社,1938.
〔24〕蒲风.郭沫若的诗〔A〕.中国现代诗坛〔M〕.上海:诗歌出版社,1938.
〔25〕蒲风.温流的诗〔A〕.中国现代诗坛〔M〕.上海:诗歌出版社,1938.
〔26〕蒲风.后记〔A〕.中国现代诗坛〔M〕.上海:诗歌出版社,1938.
〔27〕蒲风.关于文艺批评〔A〕.蒲风诗选(下)〔M〕.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19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