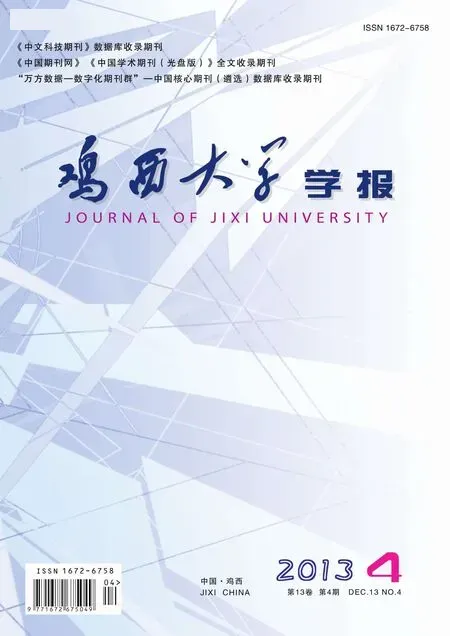幽默中的战争阴影:一九四一年的《写在人生边上》
(南通高等师范学校 人文系,江苏 南通 226100)
幽默中的战争阴影:一九四一年的《写在人生边上》
龚郑勇
(南通高等师范学校 人文系,江苏 南通 226100)
钱锺书的文字一向以幽默风趣而著名,然而没有人能绝缘于时代,钱锺书在抗战时期依然面临大时代对他个人创作的影响,出版于抗战时期的《写在人生边上》在呈现钱氏一贯的风格外,同样留有战争年代特有的阴影,受到时代的渗透,在看似不经意的幽默比喻中同样保留着战争年代特有的印痕,成为特殊年代的另类记忆。
幽默;战争;文学
钱锺书早年的散文集《写在人生边上》被学者柯灵称为“篇幅不多,而方寸间别有一天,言人所未言,见人所未见。”[1]钱锺书因之而与王了一、梁实秋三人又被称之为“战时学者散文三大家”。[2]钱锺书的这个散文小册子常常同样充满着钱氏特有的艺术风格:充满睿智的幽默;但由于这个小册子出版在抗战这一特殊的时代里,所以不可避免地保留了特定的时代印痕。所以,笔者不惴浅薄,仅想在这里浅谈一下这些时代印痕,以窥钱锺书常见的逍遥世外性格中的另一面,以待方家斧正。
一
根据孔庆茂的《钱锺书传》记载,《写在人生边上》是1941年12月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的,[3]其时钱锺书本人正远客内地,由杨绛在上海选编出版。而钱本人则在文中的序上落款的时间是1939.2.18。我们虽然现在无从考证《写在人生边上》文中每篇文章的具体写作时间,[3]有学者认为“由于随笔中有好几处提及战争和‘内地’它们有可能是作者在战争初期居于云南所写”,[4]但不管写作是在清华读书期间还是留英时期抑或云南客居时,但出版的时间却是明确的;由于出版在这个国破家亡的悲剧性时间点上,大时代对钱锺书的这个小选本的影响显然是不可避免的,作品在主动被动地接受着时代的冲击时并同样做出自己的反映,“言”与“境”两者向来是不可分的,用钱锺书在日后的《谈艺录》中的说法是:
夫言不孤立,托境方生;道不虚明,有为而发。 先圣后圣,作者述者,言外有人,人外有世。典章制度,可本以见一时之政事;六经义理,九流道术,徵文考献,亦足窥一时之风气。……龚定菴《古史钩沈论》仅道诸子之出於史,概不知若经若子若集皆精神之蜕迹,心理之徵存,综一代典,莫非史焉,岂特六经而已哉。[5]
六经皆史,六经以外的文字又何尝没有史的痕迹。由于本散文集出版时正处在太平洋战争爆发的前后,孤岛亦有风雨飘摇不复存在之感,所以之所以出版这样一本政治性不强的学者文化散文集固然是钱锺书向来远离政治的风格作风,也恐怕有政治高压因素的原因,毕竟每个人都不能脱离政治空气而单独存在,尤其是在日本人的刺刀之下,或许这也是一种不得已的自我保护。——而以后的1948年6月出版的《谈艺录》中则明确表明了身处国难之日的乱世人之苦:
《谈艺录》一卷,虽赏析之作,而实忧患之书也。……既而海水群飞,淞滨鱼烂。予侍亲率眷,兵罅偸生。如危幕之燕巢,同枯槐之蚁聚。忧天將壓,避地无之,虽欲出门西向笑而不敢也。[5]
这也恰恰说明了一旦有了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哪怕是向来淡泊名利远离政治的钱锺书也依然有表述自己不满的权利与意愿。国难当头之日,任何人都不可能置身于国难之外而无动于衷的,更何况钱锺书尚有切肤之痛:杨绛的母亲就是在1937年秋日军空袭无锡逃难时患“恶性疟疾”去世而匆匆下葬的;杨绛的三姑妈杨荫榆就是在1938年1月1日为日本兵所杀——时在巴黎的钱锺书写旧体诗《哀望》悲叹:
白骨堆山满白城, 败亡鬼哭亦吞声。熟知重死胜轻死, 纵卜他生惜此生。身即化灰尚赍恨,天为积气本无情。艾芝玉石归同尽, 哀望江南赋不成。[6]
明白这些传统文化心理和家国背景资料,我们再重新审视这本似乎无关时局的散文集时会发现它的吊诡之处正在于一方面它不得不以远离政治来获得生存的权利或保持自己的清雅风格,另一方面却又在潜意识中依然时时流露出身处乱世的忧愤。——如果说《谈艺录》为“实忧患之书也”,那么出版在这个历史敏感点上的《写在人生边上》至少也同样存有“忧患之书”的一部分。
二
抗日战争的爆发打破了知识分子宁静的日常生活,无论是涌入上海外国租界的大批难民还是迁居内地以避难的大批民众,他们都不可避免地碰到物价的飞涨和住宿等生活环境的质量下降和为国家前程担忧这些现实问题。——陌生的环境不仅提供恶劣的物质环境,同样也提供恶劣的精神文化环境和政治生态现实,这些都在这本似乎无关时局的散文集中若隐若现着。
1.无可逃避的战争成了无法回避的现实,成为悬在时人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我说:“我正在奇怪,你老人家怎会有工夫。全世界的报纸都在讲战争。在这个时候,你老人家该忙着屠杀和侵略,施展你的破坏艺术,怎会忙里偷闲来找我谈天。”[7](《魔鬼夜访钱钟书先生》)
既然战火烧得全世界都在关注,自然连书斋内的槛外人也不例外,长期以来钱锺书一直以孤悬世外、不食人间烟火的形象出现在世人的心目中,但无论怎样的高人都不可能真正脱离时代的主旋律而单独存在,只不过各人各文对于时代主流所表现出的热烈程度不一而已;更值玩味的,本文是处在这个集子中的第一篇位置上,动乱时代,谁都当不了脱离社会的鸵鸟。
“到了战争等变态时期,屋子本身就保不住了,还讲什么门和窗。”[7](《窗》)
这种对于现实的愤慨一下子就跳到了纸上,门和窗之于屋子何尝不是个体之于国家的关系,这种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隐喻抑或担忧成了每个个体的真实内心心理,成了对战争的直接控诉。只可惜,此处文字常常淹没于钱氏的长篇幽默中而为人有意无意地忽略了。
2.匮乏的物质条件让知识分子的生活水准较之从前大为下降:
内地的电灯实在太糟了!你房里竟黑洞洞跟敝处地狱一样!不过还比我那儿冷;我那儿一天到晚生着硫磺火,你这里当然做不到——听说碳价又涨了。[7](《魔鬼夜访钱钟书先生》)
飞涨的以碳价为代表的物价、经常停电以致黑漆到不如地狱的现实通过魔鬼的口叙述了出来构成了乱世特有的风景线。钱锺书在内地生活的时间是1938年10月由香港直接去昆明的西南联大,1938年夏天回沪小住;1939年秋去湖南蓝田再至1941年暑假回沪。[8]这两个时间段再加上路上的艰难跋涉构成了钱锺书刻骨铭心的记忆:军兴而后,余往返浙、赣、湘、桂、滇、黔间……形羸乃供蚤饥,肠饥不避蝇余”;[5]钱锺书很少直接谈及在内地生活时的物质上的诸多不便,但我们通过他们同时代人的困境可窥当时一斑:闻一多刻章以补家用、甚至连校长梅贻琦的夫人都要摆地摊卖“定胜糕”……
或许对于许多讲究自我空间、有着强烈自我意识的知识分子而言,物质条件的恶劣还不是最为可怕的,最为可怕的是私人生活空间受到了有意无意的干扰:
人籁还有可怕的一点。车马虽喧,跟你在一条水平线上,只在你周围闹。惟有人会对准了你头脑,在你顶上闹——譬如说,你住楼下,有人住楼上。不讲别的,只是脚步声一项,已够教你感到像《红楼梦》里的赵姨娘,有人在踹你的头。每到忍无可忍,你会发两个宏愿。一愿住在楼下的自己变成《山海经》所谓“刑天之民”,头脑生在胸膛下面,不致首当其冲,受楼上皮鞋的践踏。二愿住在楼上的人变像基督教的“安琪儿”或天使,身体生到腰部而止,背生两翼,不用腿脚走路。你存心真好,你不愿意楼上人像孙膑那样受刖足的痛苦,虽然他何尝顾到你的头脑,顾到你是罗登巴煦所谓“给喧闹损伤了的灵魂”?[7](《一个偏见》)
尽管也曾有闻一多华罗庚两家十几口人同居一室的友情,然而对于许多知识分子尤其是留学过英美的有着强烈自我意识的知识分子而言,这种无私人空间的生活尤其是一旦碰上不自觉的邻居,这样的日子可谓是一种摧残,当年战争时期是如此,日后五七干校与牛棚岁月亦是如此。——所以,梁实秋用“雅舍”来自嘲以自志之。试想像钱锺书这样出生于书香门第、父亲又是社会上知名学者,其生活水准在战前是可想而知的,但现在也斤斤计较起炭火、住宿等形而下的物质来,如果不是战争自然也无此一遭,所以也构成了对日寇侵略的一种间接控诉。
3.战争时期政客的恶劣品质成为世人的众矢之的:
例如蝙蝠的故事:……向武人卖弄风雅,向文人装作英雄;在上流社会里他是又穷又硬的平民,到了平民中间,他又是屈尊下顾的文化份子:这当然不是蝙蝠,这只是——人。[7](《读伊索寓言》)
最巧妙的政治家知道怎样来敷衍民众,把自己的野心装点成民众的意志和福利;[7](《吃饭》)
天文家的故事:……只向高处看,不顾脚下的结果,有时是下井,有时是下野或下台。不过,下去以后,决不说是不小心掉下去的,只说有意去做下属的调查和工作。……真的,我们就是下去以后,眼睛还是向上看的。[7](《读伊索寓言》)
由于当时政治时局的动荡,前方吃紧后方紧吃成为了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社会上一些与权力关系密切的政客趁机大发国难财,更加重了广大民众的不满,这在当时是一个公开的秘密,在当时的许多文学作品中都有反映;更为可怕的是,无论是略能跻身上流的待政客还是正在得势的现政客甚至已失势的前政客,其在对待民众的欺骗、谎言上以及一心只想向上攀爬、只想重新获得权势、只谋私利的心理却是惊人地相似。现在连向来自视清高、不谈政治的钱锺书也流露出了自己的不满,较之其他人其他文学作品中对于政客们的腐败行为的直接描绘揭露,钱钟书则更喜从宏观的文化心理层面进行剖析,显得更为透彻和更具有普遍性。滋生品质低劣政客的文化土壤不除,国家也恐难太平,这是钱钟书的洞察。
与鲁迅一样,钱锺书对国民性也有着敏锐的洞察力,国难时期,如果说“亡国论”是一种悲观的错误,那么那种盲目乐观的阿Q心态也同样有害,自一战始,国人就天真地有着 “公理战胜强权”的乐观,时至此时依然如此:
发现了快乐由精神来决定,人类文化又进一步。发现这个道理,和发现是非善恶取决于公理而不取决于暴力,一样重要。公理发现以后,从此世界上没有可被武力完全屈服的人。发现了精神是一切快乐的根据,从此痛苦失掉它们的可怕,肉体减少了专制。[7](《论快乐》)
这种快乐,把忍受变为享受,是精神对于物质的最大胜利。灵魂可以自主——同时也许是自欺。能一贯抱这种态度的人,当然是大哲学家,但是谁知道他不也是个大傻子?[7](《论快乐》)
鲁迅以形象感性的阿Q揭示出国民性,钱锺书则以热嘲冷讽的口气继续着这一使命;在某种程度上,鲁迅揭示的是普遍的人性,而钱则将茅头直指这种舆论的始作俑者——无耻政客及其御用文人。
4.抗战时期特殊的时代背景加重了社会舆论对知识分子的偏见甚至导致了他们的自卑:
用人瞧不起文人,自古已然,并非今天朝报的新闻。例如《汉高祖本记》载帝不好文学,《陆贾列传》更借高祖自己的话来说明:“乃公马上得天下,安事诗书?”直捷痛快,名言至理,不愧是开国皇帝的圣旨。从古到今反对文学的人,千言万语,归根还不过是这两句话。“居马上”那两句,在抗战时期读来,更觉得亲切有味。[7](《论文人》)
其实此症不但来源奇特,并且富有传染性;每到这个年头儿,竟能跟夏天的霍乱、冬天的感冒同样流行。药方呢,听说也有一个:把古今中外诗文集都付之一炬,化灰吞服。据云只要如法炮制,自然胸中气消,眼中钉拔,而且从此国强民泰,政治修明,武运昌盛!至于当代名人与此相同的弘论,则早已在销行极广的大刊物上发表,人人熟读,不必赘述。[7](《论文人》)
战乱时期,“百无一用是书生”的古训似乎得到了有力的论证,从刘邦开始的统治者从未将知识分子的作用重视过,乾隆则更是明白地说出了“倡优蓄之”的心里话,中国似乎一直滞留于前现代社会,依旧停留于单纯武力的“攻”与“守”的阶段;而西方发达国家则早就明白两个国家的战争并不单纯是战场上的军事较量,而是包括从小学教育开始的各个方面各个领域的竞争。作为留学过英国的钱锺书自然不会不明此理,只是现实实在是落后于现代社会的常识了,故其人尽管清雅,然其文间愤激之词依然可见。
由于此种有偏见文化心理的强大群众基础的客观存在,许多知识分子的心理开始分化,或许他本身就非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或许自身底气不足而自卑,也或许因抵抗不住时代的主旋律而作媚世的“抗战八股” ……:
至于一般文人,老实说,对于文学并不爱好,并无擅长。他们弄文学,仿佛旧小说里的良家女子做娼妓,据说是出于不甚得已,无可奈何。只要有机会让他们跳出火坑,此等可造之才无不废书投笔,改行从良。文学是倒霉晦气的事业,出息最少,邻近着饥寒,附带了疾病。我们只听说有文丐;像理丐、工丐、法丐、商丐等名目是从来没有的。至傻极笨的人,若非无路可走,断不肯搞什么诗歌小说。因此不仅旁人鄙夷文学和文学家,就是文人自己也填满了自悲心结,对于文学,全然缺乏信仰和爱敬。譬如十足文人的扬雄在《法言》里就说:“雕虫篆刻,壮夫不为。”可见他宁做壮丁,不做文人。……只有文人们怀着鬼胎,赔了笑脸,抱愧无穷,即使偶尔吹牛,谈谈“国难文学”、“宣传武器”等等,也好像水浸湿的皮鼓,敲擂不响。歌德不作爱国诗歌,遭人唾骂,因在《语录》 (GespracechemitEckermann)里大发牢骚,说不是军士,未到前线,怎能坐在书房里呐喊做战歌。(KriegsliederschreibenundinZimmersiteenl)。少数文人在善造英雄的时势底下,能谈战略,能做政论,能上条陈,再不然能自认导师,劝告民众。这样多才多艺的人,是不该在文学里埋没的。只要有机会让他们变换,他们可以立刻抛弃文艺,别干营生。[7](《论文人》)
梁实秋的“菜刀论” 其历史功过自有后人评说,但当年也确道出了一部分知识分子对言必谈抗战的不满;钱锺书则旁征博引委婉地揭示出这种抗战八股文的本质和产生的文人心理——于许多人而言,一切不过是干禄之具。
三
后人往往忽略掉了钱钟书自己的艺术观点和某些本该记住的文学常识,常误以为钱锺书的艺术行径和艺术思维在当时是个异类,误以为钱是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其实,钱氏也依然无法摆脱时尚潮流的影响——当时的文化思潮固然有很多,但对民国性的批判和抗日救亡图存(尤其是三四十年代)却是当时最强健的音符。钱锺书在《中国诗与中国画》里自己也说:
一个艺术家总在某些社会条件下创作,也总在某种文艺风气里创作。这个风气影响到他对题材、体裁、风格的去取,给予他以机会,同时也限制了他的范围。就是抗拒或背弃这个风气的人也受到它负面的支配,因为他不得不另出手眼来逃避或矫正他所厌恶的风气。正像列许登堡所说,模仿有正有负,“反其道以行也是一种模仿” ……[9]
神仙也是凡人做。1946年,上海警察局长兼警备司令宣铁吾出于“防共”目的下令实行“警管区制”,规定警察可以随时访问民家,并声称,英、美、法、德等民主国家都通行这种制度。当时《周报》组织了一次由通晓欧美各国国情的人对这位警察局长进行“围剿”,这其中就有化名为“邱去耳”的钱锺书。[1]写于文革中的《管锥编》现在开始被人认识到了隐寓其中的对时局的批判。[10]再往后,李慎之曾见钱锺书写“对症亦知须药换,出新何术得陈推”的感慨。[11]——这再次证明了没有人能绝缘于时代。但出版于1941年12月烽火连天的上海孤岛的《写在人生边上》却常常因其幽默风趣的文字掩盖了战争时期特有的沧桑,使得作者擅长的“皮里春秋”法几近失灵;且钱氏研究者又常常将目光专注于钱钟书的大部头著作上,这个散文集中的战争阴影常为人忽视,这不能不说是件遗憾的事。
[1]柯灵.钱钟书的风格与魅力——读《围城》《人兽鬼》《写在人生边上》[J].北京:读书,1983(1):22,27.
[2]袁良骏.战时学者散文三大家:梁实秋、钱钟书、王了一[J].北京:北京社会科学,1998(1):30-36.
[3]孔庆茂.钱锺书传[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2:99,84.
[4]陆文虎.钱钟书研究采辑(一)[G].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2:268.
[5]钱锺书.谈艺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4:266,1,184.
[6]孔庆茂.杨绛评传[M].北京:华夏出版社,1998:51-53.
[7]钱锺书集.写在人生边上·人生边上的边上·石语[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8-55.
[8]杨绛.杨绛作品精选散文(1)[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135.
[9]钱锺书.七缀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1.
[10]陈佳璇,胡范铸.一九七二—一九七五时的社会批判:lt;管锥编gt;与撰述语境的互文性分析[J].苏州:东吴学术,2012(3):102-108.
[11]李洪岩,范旭仑.为钱锺书声辩[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0:7.
ClassNo.:I206.6DocumentMark:A
(责任编辑:郑英玲)
On“LivingontheEdgeofLife”WrotebyQianZhongshuin1941
Gong Zhengyong
(Department of Humanities, Nantong Higher Normal Institute, Nantong, Jiangsu 226100,China)
Qian Zhongshu was famous for his humorous sense. However, nobody can be insulated from the times, during the anti-Japanese war . He wrote the collection of prose “Living on the Edge of Life” ,which is influenced by the anti-Japanese war. The inadvertently humorous as a metaphors also retains the fervor of the war .broke out during the special period of time.
humor;war;literature
龚郑勇,硕士,讲师,南通高等师范学校人文系。研究方向:现当代文学。
1672-6758(2013)04-0109-3
I206.6
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