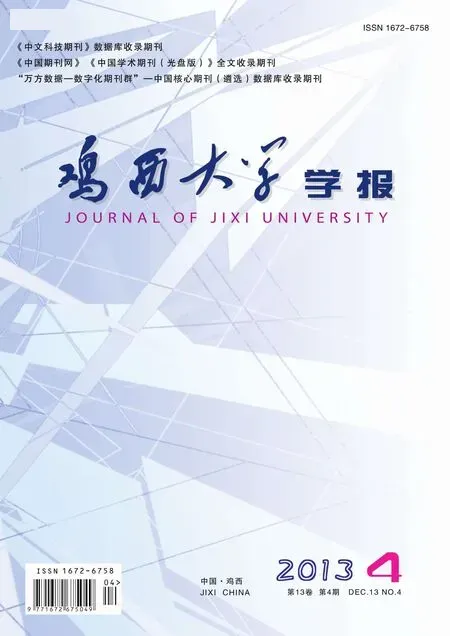甘肃藏区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问题探究
赵晓明
(甘肃民族师范学院 政法系,甘肃 合作 747000 )
甘肃藏区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问题探究
赵晓明
(甘肃民族师范学院 政法系,甘肃 合作 747000 )
人类社会中的分层与流动现象代表了社会的本质特征,随着各时期的社会发展不断地进行着更新换代。而且,某种层面上,它反映出了该时代的发展特征。拟以甘肃藏区为例,对改革开放前后的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的特征及其表象进行深入研究,并在此基础上,揭示藏区的社会结构随着社会的经济以及政治因素的变化而发生的变化。
甘肃藏区;社会分层;社会流动
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都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二者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联,当社会出现分层的时候,社会流动就是其发展的必然结果。而社会流动的过程,反过来又促进了社会分层的前进。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中人员的流动频繁,与之相对的社会阶层也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这是我们关注甘肃藏区社会分层和社会流动的主要动因。甘肃藏区包括甘南藏族自治州和天祝藏族自治县,是藏族、回族等少数民族的聚集地,因历史和现实的原因,对这一区域的研究较少。本文在前人对甘肃藏区的研究基础上,对其改革开放前、后农牧村和城镇两方面的社会流动与社会分层问题进行分析研究,以期对相关研究有所推动。
一 改革开放前甘肃藏区社会分层与流动情况
1.农牧民分层状况。
建国初期,为了确保足够的资源提供给城市,国家于一九五零年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户口制度,严重地阻碍了农牧村的人口流动。甘肃藏区的村民在以后的三十年中,受到该制度的严格限制,每年转为城市户口的村民人数不到总数的千分之二。严格的户籍制度使得城市与农牧村的社会结构产生了重大差异,城市市民阶层与农牧民阶层形成了当时的基本社会分层。这种制度的建立严重地束缚了农牧民的流动自由,并且,使得占有藏区总人口九成的农牧民失去了社会生产的积极性,对藏区的经济发展与社会安定团结非常不利。
2.城镇就业人群当中的工人和干部阶层。
在我国改革开放之前,城镇中的工作群体主要包括工人和干部,在人事管理上以此来进行区分。二者在福利待遇方面具有明显的差异性。相对工人来讲,干部的待遇要优厚得多。当时的甘肃藏区,干部的形成途径主要有五种:1.派遣。在建国的第一年,由革命老区派遣到甘南州工作的人数有八十多名。直到五三年,甘南藏族自治州人民政府成立,大批的干部被派遣到甘南地区从事政府工作;2.吸收录用。经过几年的派遣干部之后,当地的藏区民众认为其自主权受到了很大的制约,在此背景下,中央政府决定,从当地的社会当中吸收政治思想过硬,能力突出的人员填充政府管理队伍。仅五九年一年,就录用了一百一十四名当地的干部。其后,在周边的乡镇也开始实行这一录用政策。文革后,其间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全部被录用;3.教育。教育成为了青年人成为干部的又一途径,只要是获得大、中专以及本科学历文凭的学生,在毕业参加工作之后,都可以成为干部。这在当时,为很多人改变了人生命运;4.根据国家人事部门分配的干部指标而被聘用到干部岗位上的人也可以是干部编制,但这种指标是有限的;5.转业兵。当时的政策规定,只要是部队连级以上的干部转业回到地方,就可以自动转为干部编制。从建国到六一年的十几年间,天祝县先后接收了部队转业干部一百多人。
二 改革开放后甘肃藏区社会分层与流动情况
1.农牧民阶层的变化。
七九年以后,国家对藏区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及草畜双承包责任制,农牧民的经营权利获得了独立,这大大地提高了藏区民众的生产积极性。在第二年,国家对户籍的管制也做出了改进,职业的管制功能被取消。并在随后,逐渐出台了一些相关政策,使得藏区的牧民有机会脱离农牧业,从事一些自己喜欢的职业,在多领域中走上致富道路。这不仅为城市提供了大量的劳动力资源,促进其快速发展,还使得大量的农田、草地等生产资料重新分配,农牧民的养殖与种植工作逐渐走向了职业化。下面我们具体分析一下各个阶层的变化情况。
(1)农牧民阶层。该阶层主要的工作就是和土地与牧场打交道,以农牧业的经营收入作为其重要的经济来源。目前,甘肃藏区中这类人群所占的比例非常高。但是,随着城镇化进程的不断推进,数量将会逐年减少。据统计数据表明,甘南州的农牧民人数在二零零年至二零零九年间降低了百分之十左右,而城镇户口人数却每年大约增长百分之一。这一现象表明,农牧民的人数会逐年减少,直至降到一个合理的水平。
(2)农民工阶层。改革开放为社会带来了一个新名词“农民工”,这一阶层主要由两种人构成,一种是在当地的乡镇企业工作,并没有远离家乡。另一种是离开家乡,在城市中的工厂打工。在甘南州的乡镇企业经过多年的经营管理,已经初具规模,并且,对农村的产业结构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其工业产值比例逐年提高。二零零二年,甘南州乡镇企业的工业产值是七八年的两百四十倍,占到了甘南州整体工业总产值的百分之八十五以上。城市中的农民工由于受到户口的限制,无法在福利待遇方面与当地的城市居民一致。并且,农民工的各种风俗习惯都与城市居民有所差别,再加上接受教育的水平偏低,所以很难在城市中长期居住下去,所以,很多农民工都只是试探性地向城市流动。
(3)个体劳动者与个体工商业者阶层。这一阶层出现的比较晚,主要是由农牧民中思想较为开放,并且有一定专业技能的人借助改革开放的春风逐渐发展形成的。这些人中,主要从事私营企业的经营管理或者是一些乡镇企业的管理者。相对其他人在素质以及社会地位上略高一些,在当地具有非常高的发展潜力。
2.城镇干部与工人阶层变化情况。
改革开放之后,藏区的干部主要来自于高校毕业生,直到九八年公务员制度建立。而与此相对的工人阶层,主要来自于国家的招工、职工子女接班等。虽然也同样享受着国家给予的一些福利待遇和保障措施,但是,要想成为干部阶层中的一员却非易事。然而,干部的优越性随着经济建设的高速发展受到了很大的冲击。借助改革开放政策的优势,很多人纷纷下海经商,一夜间成为了名符其实的“有钱人”,从而成为人们追捧的对象,其社会地位也随之提高。并且,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渐完善,官员们的经济特权越来越变得不那么重要,其地位开始走“下坡路”。
3.城镇私营业者阶层再现。
建国初期,私营工商业呈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并招揽了众多人员为其工作。五五年,甘南州就拥有两千八百多户私营企业,遍布各行各业。尽管很多家的规模较小,但是,却占据着重要的经济地位。文化大革命的开始,为私营企业带来了致命的打击,城镇居民的就业渠道也严重缩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的开幕为城市的经济带来了新的活力,个体私营经济重新走入了人们的视线,并在国家的大力倡导下茁壮成长。城镇居民也因此形成了明显的职业分化。并且,随着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入发展,很多职工纷纷重新选择就业,这为私营企业的壮大提供了强大的推动力量。据统计分析,到九九年,天祝县城镇的个体企业数量达到了一千五百多家,与八九年相比翻了五倍。
目前,城镇个体与私营工商业的发展正方兴未艾。相对于农牧村的私营工商业者阶层来说,藏区城镇个体与私营工商业者阶层的来源构成情况要复杂得多。在改革开放初期,藏区城镇中的个体从业者主要是一些边缘群体,使得当时藏区此阶层素质较低。后来一些从国有制单位离职、辞职或停薪留职人员开始加入,但由于藏区传统文化等因素影响,人们不愿进入这一阶层,因此这一阶层的比重始终不大。这种状况到 1992 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方有所改观。在国家相关政策的推动下,藏区城镇个体与私营工商业经济发展迅速,人员素质有了极大提高,而且自我地位评价及社会地位评价也明显改观。从 20 世纪末开始,藏区个体与私营工商业者阶层无论在平均受教育水平、经济地位上,都已高于集体企业和国营企业工人,在经济地位上,有些已在公务员之上,可见其发展势头的强劲。
三 甘肃藏区社会流动与社会分层的影响因素
1.政策方面的影响。
在改革开放之前,藏区的社会阶层以及人员的流动情况很大程度上受到了政府的控制,这样很容易造成藏区民众对政府的不满情绪,从而影响到社会的安定团结。改革开放之后,随着经济体制的逐渐完善与发展,农牧民的生活状况得到了很好的改善,并且,他们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选择自己的发展道路。例如:户口制度改革之后,是否进城打工已经可以根据藏族群众的意愿决定了。
2.市场经济的影响。
以市场化为导向的社会流动机制逐渐成为社会结构变化的重要因素之一,其中,个人社会流动的后天因素变得越来越多,例如:教育程度,个人能力等。而本身的家庭出身、社会地位等因素变得越来越淡薄。甘肃藏区社会结构所表现出来的重要变化,以及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的重大变动,主要体现在各种身份制度的衰落与解体,新的分层体系与标准形成。例如:很多城市中的工人、领导在市场经济发展的促动下,转变思想,不再固守自己的生活、工作方式,纷纷利用自身的有利资源下海经商,在改革的大潮中,实现自身的另一种人生价值。
3.社会分工细化。
随着改革开放发展进程的不断加快,人们的工作更加细化,使得人们彼此之间的分工更加明确,从某种程度上讲也促进了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例如:原本的很多工业部门由于社会的发展需要,逐渐被划分为一些更为具体的部门,这些部门各自管理着自身分内的事情,彼此之间的内政互不干涉,这样就间接地将人们之间的联系程度降低,从而逐渐对社会流动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1]韩永君,何乃柱.甘肃藏区民间传统体育文化遗产发展现状与传承策略研究[J].山东体育科技,2010(03).
[2]迟玉花.当代藏区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问题——以甘肃藏区为例[J].甘肃社会科学,2012(01).
[3]陈声柏,王志庆.一位外国传教士眼中的甘南族群关系——埃克瓦尔《甘肃藏区边境文化关系》评述[J].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01).
[4]张硕勋,王晓红.论现代化转型时期藏区女性社会角色的变迁[J].甘肃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0(04).
[5]许宫堂,达光文,许开胜.甘肃天祝藏区生态补偿策略探讨[J].林业资源管理,2010(05).
[6]刘艺工.试论甘南藏区的法制环境[J].贵州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01).
[7]李晓红.甘肃省藏区三语教学的调查研究[D].西北师范大学,2011.
[8]才让拉草.民国时期甘南藏区改土归流研究[D].中南民族大学,2011.
[9]张硕勋,王晓红.论大众传播语境下甘南藏区社会流动与文化整合——以甘南藏区五村庄调查为例[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2(01).
ClassNo.:C951DocumentMark:A
(责任编辑:郑英玲)
OntheSocialStratificationandMobilityinTibetanAreasinGansuProvince
Zhao Xiaoming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Gansu National Normal University, Hezuo,Gansu 747000,China)
Social stratification and mobility represent an essential nature of human society. It reflect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imes in which people lived. Taking Tibetan areas in Gansu as an example , this article discussed its social stratification and mobility before and after the opening up to the outside world , and it reveals the changes of Tibet's social structure politically and economically.
Tibetan areas in Gansu province; social stratification; social mobility
赵晓明,硕士,讲师,甘肃民族师范学院政法系。研究方向:政治理论和民族政治学。
1672-6758(2013)04-0153-2
C951
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