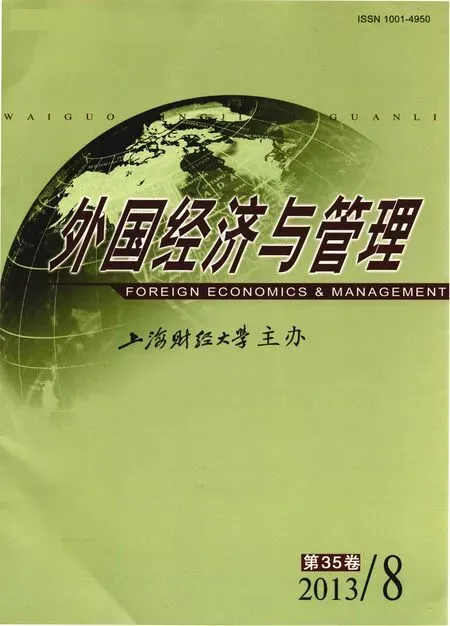企业研发网络国际化研究述评与未来展望
潘秋玥,魏 江,刘 洋
(浙江大学 管理学院,浙江 杭州 310058)
一、引 言
随着企业间竞争的不断加剧和创新格局的持续重构,研发网络国际化已经成为战略管理和技术创新研究关注的一个重点问题(刘洋等,2013)。企业研发网络的国际化主要涉及海外研发网点选址(Alcácer,2006;Leiponen和 Helfat,2006)、研发网络结点间的互动(Helble和Chong,2004)、研发人员国际流动(Criscuolo,2005)、研发网络内部知识共享与整合(Spencer,2000和2003)以及技术转移和吸收(Cohen和Levinthal,1989和1990;Tsai,2001)等重大问题。由于研发网络国际化是一个全新的议题,涉及跨国经营、技术创新和战略管理等多个领域,又兼具参与主体和过程的复杂性和动态性特点,相关的理论研究还没有形成相对连贯和稳定的逻辑体系,从而制约了企业研发网络国际化研究的深入开展,也影响了企业研发网络国际化实践向纵深发展。
本文在梳理企业研发网络国际化研究文献的基础上,从地理边界、组织边界和知识边界三个维度来界定研发网络国际化的内涵和形式,然后探讨企业研发网络国际化的动因、结果和演进路径问题,最后在分析现有研究不足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提出未来深入开展研发网络国际化研究的若干建议。
二、研发网络国际化的内涵与形式
早期的研发网络研究认为,研发网络是一种根据任务需要而组建的临时性组织,网络内部的合作也仅限于相对简单的产品开发,目的就是在技术迅速发展的条件下尽量缩小技术差距,维持适当的组织规模,并实现更高层次的垂直一体化(Mowery和David,1983;Pisano,1991)。在此基础上,Gulati(1998)进一步强调了研发网络成员联袂完成任务的功能导向。随着企业间研发合作的不断深入,学者们逐渐发现研发网络构建是一种嵌入性很强的活动,网络成员的调整会导致很高的转换成本,于是倾向于认为研发网络应该是一种持久性组织机制(Gulati等,2000;Hite和Hesterly,2001;Orsenigo等,2001),而且是一种根据多边协议创建的旨在加强技术知识共享的正式组织形式(Zirulia,2004和2012)。
迄今为止,研发是价值链上国际化程度最低的一个环节(Berry,2013)。究其原因,研发国际化尤其是研发网络国际化要面对众多挑战,要涉及跨越地理边界解决不同组织间的制度、文化和知识储备差异等问题(刘洋等,2013)。为了阐明研发网络国际化的内涵与形式,本文重点阐述研发网络国际化必然要涉及的地理、组织和知识边界拓展问题。
首先,基于地理边界拓展的研发网络国际化研究主要关注跨国公司在构建国际研发网络过程中的布点问题,旨在揭示国际研发网络结点由中心向边缘扩展的过程,即从早期由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扩展转变为现在由发展中国家和海外研发附属机构向技术发源国逆向拓展并行的过程。早期的研发网络国际化研究主要是从经济地理视角来解构起始于1980年代中期的发达国家大规模地向发展中国家设立研发机构的现象,并且认为研发网络国际化是发达国家技术密集型企业追求科技来源多样化和成本最小化的结果(Reddy,1997)。但随着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新兴经济体的崛起,研发网络国际化的拓展方向和研发流向发生了巨大变化。Von Zedtwitz和 Gassmann(2002)根据位于国际研发网络研发流上游和下游的母国和东道国经济发达水平区分了四种研发网络国际化形式,它们分别是:(1)传统型——发达国家之间的强强联合,这种形式仍是目前最主要的研发流向;(2)现代型——发达国家流向发展中国家,目前正在不断发展壮大;(3)追赶型——发展中国家流向发达国家;(4)扩张型——发展中国家流向发展中国家。MGI(2003)和Gao(2004)按照主要研发活动的地理区位区分了三种研发网络国际化形式:一是在国外设立研发分支机构并开展研发活动,这就是所谓的“内部离岸研发”;二是在母国选择非附属企业进行研发外包,即所谓的“国内研发外包”;三是在国外选择非附属企业进行研发外包,即所谓的“离岸研发外包”。
其次,基于组织边界拓展视角的研发网络国际化研究主要运用交易成本理论和资源基础观来进行分析。具体而言,交易成本理论认为,在技术复杂和环境不确定的条件下,企业可以通过交易内部化来降低沟通、协调、监督等交易成本(Williamson,1979)。研发这种风险高、投资回收期长的活动采取网络化和国际化形式,能够有效实现研发内部化,从而降低研发成本和不确定性。此后,有学者(如 Kogut,1989;Kleinknecht和 Reijnen,1992;Eisenhardt和Schoonhoven,1996;Tijssen,1998)基于资源基础观,从资源关系视角解释了研发网络国际化现象,并且认为跨组织研发合作能更有效地内化交易成本、更有效率地获取资源,是实现风险分担、资源互补和技术共享的高效手段。Helble和Chong(2004)考察了新加坡后发产业研发网络中心结点与边缘结点的跨组织互动以及核心企业与研发网络外部东道国研发机构之间跨组织互动的不同特点,结果发现通过跨组织拓展,核心企业能够利用自己的比较优势和东道国结点企业的技术优势,在全球范围内跨组织整合异质性研发资源和前沿技术信息,并且缩小与技术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Cantwell,1989;杨震宁等,2010)。
最后,基于知识边界拓展视角的研发网络国际化研究主要围绕Casson和Singh(1993)依据研发网络知识特性区分的基础型、一般型、适应型和技术支持型四种企业研发活动展开,并且特别关注在这四种研发活动中特定研发知识的探索、利用和转移效率问题。具体而言,学者Fors和Zejan(1996)以及Fors(1998)依据研发网络的知识原创性和应用范围把全球化研发活动高度概括为适应型研发和创新型研发。前者是指东道国研发机构为适应当地市场需求而改进从母公司引进的技术的研发活动,从事适应型研发的网络结点通常比较接近生产单位和产品市场;后者是指研发项目在研发网络内部具有创新性质、相关知识又可应用于全球市场的研发活动,从事创新型研发的网络结点通常都设立在“卓越中心”(center of excellence)和全球技术领先的企业和高校集群附近。Kuemmerle(1997)把研发网络国际化战略分为基于母国的开发战略(home-based-exploiting)和基于母国的扩张战略(home-based-augmenting)。前者是指通过开发式利用把母国既有的核心技术拓展应用于国外市场,旨在通过海外研发结点最大限度地实现既有核心技术的价值;而后者是指通过扩张主动搜寻和吸收海外研发结点的新知识,以充实研发网络核心企业的知识基础。

表1 研发网络国际化主要拓展维度及代表性观点
由上可见,企业研发网络国际化是指企业研发网络跨越地理和组织边界在国际范围内布设研发网点,为了实现成本内化、风险分担、知识共享而进行的跨组织协同创新和前沿技术信息交流,并通过拓展知识边界来尽可能高效率地探索、利用和转移研发知识。因此,研发网络国际化有利于企业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扩充自己的资源、能力和知识储备,也是企业全方位实施全球化发展战略的一个重要方面。
三、研发网络国际化动因、结果和演进路径
以上清晰界定了研发网络国际化的内涵及其跨越地理、组织和知识边界的拓展形式。下面,我们围绕“研发网络国际化进程受哪些因素推动”、“研发网络国际化会带来什么结果”以及“研发网络国际化如何发展演进”这三个问题来进一步解构研发网络国际化的动因、结果和演进路径。
(一)研发网络国际化动因
已有学者(如Kleinknecht和Reijnen,1992;Casson和 Singh,1993;Tijssen,1998;Todo等,2009)从资源观、能力观、知识观等多个视角分析了跨组织边界开放创新范式下的研发网络国际化动因,如分散风险、共享资源、实现比较优势、获取前沿科技信息和战略性资产等。基于前文有关研发网络国际化地理、组织和知识边界拓展的分析,在梳理相关研究文献的基础上,我们发现现有的研发网络国际化研究主要从技术学习、知识吸收和市场开拓三个方面来探究研发网络国际化的动因。
1.技术学习。企业构建国际研发网络的一个重要动因就是借助于网络化来推进其全球运营的战略布局,通过开展技术学习来实现知识溢出效应(Chiesa,1995;Pearce,1999)。许多相关研究也表明,通过设立海外研发机构来获取东道国的技术资源,正在成为跨国公司研发网络全球布点的一个重要动因(Carlsson,2006)。一般而言,企业在开始内部研发活动之前会审视外部环境(Chesbrough和Crowther,2006),一旦发现可利用的创意和技术,就会通过建立研发实验室来获取、内化,进而吸收与企业内部流程匹配的外部创意和技术,把有限的研发资源集中投放在关键环节上(Freeman,1974)。网络结点企业能够通过研发网络内部的技术流,从其他网络结点那里快速、高效地获得自己所需的研发资源,然后进行有效的整合,从而缩短技术升级周期(Peters等,1998)。值得注意的是,自1990年代中期以来,众多学者把注意力转向了旨在实现追赶目标而积极创新的广大发展中国家,致力于研究发展中国家企业积极推进自身研发网络国际化的行为,并且发现发展中国家企业通过在海外设立技术中心和研发机构能够有效拓展其外部技术资源来源并发展自身的技术能力,从而提升技术追赶效率(Florida,1997;Kuemmerle,1997 和 1999)。同时,凭借研发网络的双重功效——帮助结点企业在内部充分挖掘、开发和促进创新,从外部获取研发信息和资源(Cohen和 Levinthal,1989),研发网络国际化已经成为企业获取研发资源和专业技能、参与全球创新网络的“入场券”(Rosenberg,1990),也为新兴经济体跳跃式提升其技术能力奠定了基础(Fu等,2011)。
2.知识吸收。跨国研发机构之间的知识转移有助于研发网络结点企业获取、利用和转化知识,强化国际研发网络所涉及的母国和东道国之间的知识转移(特别是隐性知识双向转移),从而最大限度地提高国际研发网络的研发投入回报(Spencer,2003)。通过研发网络国际化,跨国公司就能实现先进知识和能力在母国以外的衍生发展,从而不断提升和更新自己的技术能力(Zander,1999)。研发网络国际化有利于企业通过广泛分布在国外的网络结点来传递和吸收只可意会的隐性知识,并且帮助企业规避因信息闭塞而不了解自己所在领域的前沿知识从而影响后续产品技术突破的风险(Spencer,2003)。Laursen和Salter(2006)通过研究开放式创新揭示了学习效应促进创新和研发活动全球化的重要作用,验证了积极的外部知识学习促进研发创新发展的作用。也有学者(如 Hale和Long,2006;Todo等,2009)沿袭Laursen和Salter的研究思路,通过考察跨国公司研发人员的国际流动以及母公司与子公司和子公司之间在这方面的交互,验证了知识员工作为重要知识载体对促进研发网络国际化建设的关键作用。
3.市场开拓。跨国公司在向外输出研发活动的过程中实施研发活动当地化策略,能够帮助它们开拓东道国的市场,再通过研发网络国际化来促进创新成果在网络内部的扩散,进而在拓宽销售渠道和开辟新市场的同时推动基于东道国情境的适应型研发。在市场导向这一重要创新前因的作用下(Jaworski和 Kohli,1996),实施以适应东道国市场为目的的产品创新和服务创新,既是企业提升和维系自身竞争力的重要前提,也是它们获得长期发展和成功的根本保证(Deshpandé等,1993)。因此,企业通过研发网络国际化,就能比较方便地为适应东道国的技术和市场条件而进行本地化,并且还能促进自身的技术更新或升级(Vázquez等,2001)。正如 Fors(1998)所指出的那样,跨国公司在海外进行研发布点的一个重要动因就是使产品研制能够与当地市场条件和顾客偏好相匹配,从而扩大海外销售市场。Von Zedtwitz和Gassmann(2002)也研究证实了市场导向在研发网络国际化中的作用,并且认为研发网络国际化是技术密集型企业在愈演愈烈的全球竞争中开发利用特定区位创新优势的一种有效手段。
表2列示了以上介绍的目前主要的研发网络国际化动因研究文献。

表2 研发网络国际化动因研究总结
(二)研发网络国际化结果
研发网络国际化通常是一个渐进的动态过程,要经历前期的海外扩张方案评估、海外研发机构布点决策,中期的海外研发分支机构或子公司建设、网络化治理,以及后期的海外研发分支机构或子公司管理、中心结点与海外结点之间的协调等阶段(De Meyer,1993;Staropoli,1998;Meyer等,2011)。随着近年来企业研发网络国际化研究的不断深入,学者们开始把研发网络国际化作为前置权变因素来考察研发网络国际化对企业提升创新绩效和能力的作用。通过文献回顾,我们发现现有的企业研发网络国际化结果研究主要是从企业研发网络地理、组织和知识边界拓展三个方面展开的。
关注企业研发网络地理边界拓展的研究主要关心经济地理学派提出的研发活动“邻近悖论”(proximity paradox)问题(Boschma和 Frenken,2010),试图辨析国际研发网络不同结点在地理上的集聚和分散究竟何者更有助于企业提升创新能力。支持研发网络地理集聚的学者主要从组织学习效率和交易成本的角度来进行分析,认为结点在地理上集聚的企业研发网络更有利于各结点相互间的信息传递和知识共享,因而能大大降低复杂环境下的沟通、协调、监管等交易成本(Ingram和Baum,1997;Parkhe,2011);而主张企业研发网络在地理上分散分布的学者则认为,地理上邻近的研发网络结点往往表现出知识同质性较高的特点,因而不利于知识扩散和技术溢出(Venaik等,2005)。地理上分散的研发活动有利于企业接近分布广泛的知识创新源,从而有利于降低跨国市场信息不对称程度(Hansen等,2005)。尽管有关“邻近悖论”的研发网络国际化研究仍存在较大的分歧,但也有学者倾向于综合上述两种观点,通过引入新的权变因素或者划分构念维度来深入探讨“邻近悖论”问题。具体来说,Lahiri(2010)实证研究全球100家半导体企业发现:地理邻近性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受到企业技术多样性和内部研发单元间联系强度的调节,因而呈现倒U形曲线关系。而Broekel和Boschma(2012)在证明“邻近悖论”时将“邻近性”概念细分为认知、社会、组织和地理四个维度,分别采用网络结点间的知识基础重叠程度、网络结点的关系嵌入程度、网络结点营利性差异(企业被界定为营利性组织,而大学、研究机构、协会为非营利性组织)以及网络结点间的相对地理距离来表征这四个维度的邻近性,采用网络回归分析技术(network regression techniques)验证了地理邻近性和社会邻近性对创新绩效的正向影响以及认知邻近性的负向影响,但没有发现组织邻近性的显著影响。
早期关注企业研发网络国际化组织边界拓展效应的研究并没有充分注意研发网络海外分支机构的管理问题(De Meyer,1991;Gerybadze等,1997;Gerybadze和 Reger,1999),近些年的相关研究开始把目光聚焦于国际研发网络跨组织管理及其对企业绩效的影响。首先,在母公司与海外子公司之间的跨组织研发管理方面,Lovett等(2009)针对设立海外子公司的目的进行的一项研究显示,跨国公司为了实施更有针对性的协调管理,会对出于发掘市场、知识和资源三种不同目的设立的海外研发子公司分别采取不同的文化、结果和行为控制手段。而在探讨母公司和研发子公司之间的关系对企业绩效影响方面,学者Gammelgaard等(2012)把跨国公司的全球研发网络关系分为组织间和组织内两个维度,分别探讨了海外子公司自治、网络关系与绩效三者之间的关系,通过问卷调查发现:随着自治程度的提高,海外子公司越来越倾向于单独行动,从而影响与跨国公司内部其他研发机构的知识分享和信息传递,进而负向影响企业绩效。Chen等(2012)在Gammelgaard等(2012)的基础上研究发现:研发活动在地理上的不断分散会导致监管成本不断增加,从而迫使企业重新采用多样、灵活的协调手段来巩固以卓越中心为枢纽的跨国研发网络。他们把研发网络国际化过程中的组织扩张分为分散、过渡和再集中三个阶段,通过比较不同阶段的跨国研发协调和交流总成本与探索式学习和利用式学习的总收益发现:研发网络国际化组织扩张的企业创新绩效效应因不同阶段而异,总体上呈现S形曲线关系;组织冗余作为资源缓冲因素负向调节研发网络国际化对创新绩效的影响(Chen等,2012)。
通过文献梳理,我们发现许多研究者(例如O’Mahony和Vecchi,2009;Zhang等,2010;Edler等,2011;Figueiredo,2011)从知识边界拓展的角度考察了研发网络国际化所引发的知识探索、利用和转移效率,科研人员跨国流动,逆向技术转移以及FDI的技术知识溢出效应和海外研发子公司的本地化嵌入等对于提升企业技术能力和绩效的影响。在研发网络国际化进程不断加快的今天,随着国际研发网络地理和组织边界的不断扩展,专家型员工海外交流时间和频次的增加大大提升了母国和东道国之间的知识和技术转移效率(Edler等,2011)。与此同时,相关研究也证实了FDI对于促进国际研发网络内部知识转移的功效。例如,Håkanson和Nobel(2000)通过对瑞典排名前20的跨国公司海外研发机构进行了问卷调研,结果发现:技术的国际开发利用通常要通过FDI,也就是通过向全资子公司转移的方式来实现;跨国公司可凭借其内部有助于知识解码和编码的“高阶组织原则”(higher order organization principles)来成为低成本、高效率的技术转移工具。Eapen(2012)也研究证实了创新搜寻和技术转移过程中的海外网络关系通过FDI对海外研发机构产生知识溢出正效应。此外,另有学者(如Figueiredo,2011;Meyer等,2011)基于知识观探讨了海外研发子公司多重关系嵌入如何影响其提升战略能力的问题。具体而言,Figueiredo(2011)研究发现海外子公司的双重嵌入性(即对内潜入跨国公司内部网络,对外嵌入东道国的外部环境)有利于提升知识密集型网络不同结点之间的互动频率和质量,进而有利于提高创新绩效。Figueiredo(2011)研究认为,跨国公司虽然是一种拥有自己权利的机构,但嵌入在不同地区、国家或次国家制度环境中,因此是一种能直接或间接嵌入其竞争优势和组织能力中的因子。Meyer等(2011)在回顾既有相关研究文献后指出:跨国公司需要在两个层次上跨异质情境管理多重嵌入性:在公司层面,必须通过构建自己的网络嵌入东道国不同的当地情境,以有效开发利用东道国的不同条件;在子公司层面,必须在公司网络内部嵌入性与东道国外部环境嵌入性之间进行平衡。
总的来说,已有的研发网络国际化研究主要从地理、组织和知识边界拓展的视角肯定了研发网络国际化作为权变因素对于跨国公司提升创新绩效、技术能力、市场能力和组织学习能力的积极作用。同时,近年来的研究也识别了吸收能力、组织冗余、技术多样性等因素在此过程中的调节作用。不过,现有研究大多仍停留在问卷调查、截面数据分析等静态研究的水平上,还没人开展网络国际化动态研究,即没人关注研发网络国际化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产业环境的变化而发生的动态变化。
(三)研发网络国际化的演进路径
在企业研发网络国际化进程中,随着参与主体的不断多元化,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企业正通过国际化从研发网络的边缘向中心靠拢,企业的研发网络通过国际化进程也逐渐改变了自己的密度、结构甚至演进路径。因此,企业研发网络国际化演进问题也引起了许多学者(如Gassmann和Von Zedtwitz,1999;Pearce和Papanastassiou,1999;Hite和 Hesterly,2001;Venkatraman,2004;Le Bas和Patel,2005)的关注。
从研发网络国际化的结构演进过程看,许多演进路径研究是围绕跨国公司母国总部与海外研发中心或子公司的关系来展开分析的。例如,Gassmann和 Von Zedtwitz(1999)在 Bartlett(1986)完成的跨国公司国际化研究的基础上,从母公司与海外研发子公司之间的权力分配、竞合关系、网络密度和研发行为导向出发,识别了研发组织在国际化过程中经历的五个不同发展阶段——民族中心、地区中心、多中心分散、集中研发、一体化研发网络(参见图1)。Gassmann和Von Zedtwitz(1999)认为,在研发国际化的早期阶段,母公司倾向于采取集中方式把核心研发技术这种“国民财富”全部留在母国,而只是通过适应型改进、生产和营销来进行国际化扩展。但随着海外业务的不断发展,对国际市场和全球研发技术的依赖程度不断加深,跨国公司的研发网络在结构上不断趋于分散。它们通过吸收东道国研发人员或者外派研发人员,与海外研发实验室进行分散化的创新搜寻和研发合作,旨在保持对当地市场的高度敏感性。在后期的研发网络国际化整合阶段,海外研发中心逐渐成为新业务拓展的重要战略单元,母公司的研发中心在保证海外研发单位一定研发自主权的同时,还会采用灵活多样的协调机制来吸引它们紧密围绕其自身的研发活动进行广泛的协作,从而实现一定程度的集中整合控制(Fischer和 Behrman,1979;Gassmann和 Von Zedtwitz,1999;Gerybadze 和 Reger,1999;杨震宁等,2010)。

图1 驱动国际研发组织演进的五种主要趋势
从研发活动国际化的动因和战略看,研发网络国际化演进也发生了一定变化。早期的国际化研发活动大多是适应型研发,发展中国家的情况更是如此(Archibugi和Iammarino,1999)。在适应型研发向创新型研发演进的过程中,研发网络国际化分别采取了短期、中期和长期三种不同的战略。短期战略旨在熟悉东道国不同的市场状况,中期战略旨在缩短产品开发周期和提升产品的市场渗透力,而长期战略则旨在利用当地知识网络及其知识溢出来构建竞争优势(Archibugi和Iammarino,1999)。后来的相关研究(如Bas和Sierra,2002;Le Bas和Patel,2005)从战略管理的视角识别了不同的研发网络国际化战略,例如重在开发东道国优势技术的技术探索型研发战略、旨在探索企业在东道国竞争优势的基于母国的开发型研发战略、针对母国和东道国技术优势的基于母国的扩张型研发战略以及针对技术导向性较弱活动的市场开发型研发战略。Bas和Sierra(2002)以及 Le Bas和Patel(2005)研究发现,初期的研发网络海外拓展大多受单一的技术导向或市场导向驱动,并且对应采用技术搜索型研发战略或市场开发型研发战略。但随着研发网络国际化的不断深入和国家间技术势差的缩小,跨国公司会根据母国和东道国相对技术优势的变化对自己的研发战略做出相应的调整,采用基于母国的开发型研发战略和扩张型研发战略来寻求更好的研发网络国际化形式。
此外,也有学者(如 Hite和 Hesterly,2001)从网络关系维度来考察研发网络国际化演进问题,并且发现在日益密集的国际研发网络中存在关系、信息和资源冗余度高而多样化程度低的问题。例如,Hite和Hesterly(2001)研究发现了在企业研发网络国际化过程中出现的三种趋势,即从高度嵌入关系朝着一般关系和嵌入关系均衡的方向发展、从强调网络聚合性向着构建新结构洞的方向发展、从强调路径依赖向着国际化整合的方向发展。此外,海外拓展的不同进入方式和控制程度的变化,也拓宽了研发网络国际化演进研究的范畴。具体而言,Zahra等(2000)按照母公司控制产品研发的程度归纳总结了研发联盟、并购、绿地投资这三种主要的研发机构设立方式,并且发现控制程度较高的国际进入方式更有利于提升技术学习的广度、深度和速度。他们的这一研究发现也得到了基于资源观的相关研究(如Gatignon和Anderson,1988;Isobe等,2000)的支持。基于资源观的相关研究表明,企业可通过加强对海外分支机构的控制来更好地利用国外市场的关键性研发资源。因此,在向发达国家拓展其研发网络的过程中,发展中国家企业一改以往通过技术引进和技术许可贸易来获取发达国家研发资源的做法,而是采用联盟、绿地投资等控制程度相对较高的方式来提升自己的技术创新能力和成功进入海外市场的几率。
四、研究总结和未来展望
本研究首先识别了研发网络国际化的组织形式,并对基于不同视角的研发网络国际化内涵和形式研究成果进行了述评。在此基础上,本研究对研发网络国际化的前因和结果研究进行了回顾,并从研发网络的组织拓展、研发活动动因与战略和研发网络的结构演进等分析视角对研发网络国际化演进研究成果进行了总结。早期的研发网络国际化研究(如Blanc和Sierra,1999)主要是基于地理边界拓展来关注跨国公司设立海外研发机构的现象,从经济地理学的视角来揭示研发网络国际化拓展对于网络内企业、科研机构、大学等结点的研发流向多样化的影响。随着知识观和能力观的崛起,研发网络国际化逐渐成为创新和战略研究的一个焦点,越来越多的学者运用知识观和能力观来解释跨国公司如何有效开展跨组织边界的合作研发以及如何通过多重嵌入来利用技术知识溢出效应以提升企业创新绩效的问题。随着相关研究的不断深入,学者们通过引入吸收能力、组织冗余、技术多样性等构念来解构研发网络国际化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以及知识转移效率和技术能力追赶之间的关系。图2是在梳理现有企业研发网络国际化研究的基础上构建的一个整合研究框架,比较形象地展示了现有相关研究的主题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

图2 研发网络国际化整合研究框架
基于以上述评,本研究认为现有的企业研发网络国际化研究仍存在一些不足。首先,就研究方法而言,现有研究大多采用问卷调查和截面数据分析等方法。虽有个别学者(如Zirulia,2004;Chin,2009;Kim 和Park,2009)进行了动态仿真研究,但总体而言,没有给予企业研发网络国际化动态演进问题应有的关注,更没有多维度、多层次地探索企业如何通过拓展地理、组织和知识边界来实现多维度研发网络国际化的问题。其次,就研发网络国际化的内涵与形式而言,现有研究大多基于不同的视角孤立地讨论地理边界、组织边界或知识边界拓展问题,而忽略了三种边界拓展之间的交互对研究结论可能产生的影响,从而限制了对企业研发网络国际化研究更深入的探讨。再次,现有相关研究很少论及国际研发网络治理问题,对该主题的探讨仍然停留在先前对于集群网络或组织间研发网络治理的分类和影响方面,缺乏对国际化研发网络治理较之于一般网络治理的特殊属性的探讨,更没有考察研发网络国际化不同阶段的治理问题。最后,关于研发网络国际化动因和结果的现有研究基本上都是针对发达国家企业特别是跨国公司的,很少关注发展中国家企业的研发网络国际化问题。由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技术、制度和文化方面存在很大的差距,因此,现有的相关研究缺乏普遍适用性。
针对以上不足,本文认为未来的研究应该从以下四个方面加以完善。
第一,采用多种研究方法开展研发网络国际化的纵向研究。尽管已有学者致力于企业研发网络国际化过程研究,但大多采用横截面数据和问卷调查方法来研究企业研发网络国际化问题。事实上,研发网络国际化是一个动态过程,因此,后续研究应该从过程视角,采用二手数据、纵向演化案例、动态仿真等不同研究方法来探索跨地理、组织和知识边界的研发网络国际化过程及其演进机制。
第二,整合研发网络地理、组织和知识边界拓展的三个维度,结合运用经济地理学、交易成本、资源基础观、能力观和知识观等理论来考察研发网络国际化过程的复杂特点和动态变化问题。现有的研究主要是从地理边界、组织边界和知识边界拓展某一单一维度来分析研发网络国际化所涉及的海外研发网点选址(Alcácer,2006)、研发网络结点间互动(Helble和Chong,2004)、研发网络内部的知识转移和吸收(Cohen和Levinthal,1989和 1990;Tsai,2001)、知 识 分 享 和 整 合(Spencer,2000和2003)问题,后续研究应该多维度、多理论地统筹考察三种边界拓展在企业研发网络国际化过程中如何互动和共演以及如何共同推动企业研发网络国际化等问题。
第三,关注动态情境下的研发网络国际化治理问题。鉴于企业研发网络国际化是在动荡多变的环境下进行的,未来研究应从静态分析转向对国际化过程的动态分析,探究影响国际研发网络关系动态变化的因素,考察国际化对于企业研发网络结构和治理的影响(Madhavan等,1998;Kenis和 Knoke,2002)。
第四,关注不同网络结点在研发网络国际化过程中的交互关系,尤其关注发展中国家网络结点与发达国家网络结点之间的研发互动问题。一方面,应该深入研究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在发展中国家发展其研发网络,并通过反向创新(reverse innovation)来实现研发反哺的实践(Govindarajan和Ramamurti,2011);另一方面,近几年,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为了克服自身的技术和市场劣势,大举实施研发网络国际化,并且获得了突破性进展,从而彻底颠覆了现有相关研究结论(Cuervo-Cazurra,2012)。因此,未来的企业研发网络国际化研究不但要继续深入探讨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如何在复杂的全球化背景下实施研发网络国际化战略,而且更应该关注发展中国家企业如何通过研发网络国际化来构建自己的研发能力,进而提升自己的研发水平等问题,以便为构建全新的企业研发网络国际化理论提供素材(Mathews,2002;Lu,2008)。
[1]Alcácer J.Location choices across the value chain:How activity and capability influence collocation[J].Management Science,2006,52(10):1457-1471.
[2]Bas C L and Sierra C.“Location versus home country advantages”in R&D activities:Some further results on multinationals’locational strategies[J].Research Policy,2002,31(4):589-609.
[3]Carlsson B.Internationalization of innovation systems:A sur-vey of the literature[J].Research Policy,2006,35(1):56-67.
[4]Chen C-J,et al.How firms innovate through R&D internationalization?An S-curve hypothesis[J].Research Policy,2012,41(9):1544-1554.
[5]Chesbrough H,et al.Beyond high tech:Early adopters of open innovation in other industries[J].R&D Management,2006,36(3):229-236.
[6]Eapen A.Social structure and technology spillovers from foreign to domestic firms[J].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2012,43(3):244-263.
[7]Eisenhardt K M and Schoonhoven C B.Resource-based view of strategic alliance formation:Strategic and social effects in entrepreneurial firms[J].organization Science,1996,7(2):136-150.
[8]Figueiredo P N.The role of dual embeddedness in the innovative performance of MNE subsidiaries:Evidence from Brazil[J].Journal of management studies,2011,48(2):417-440.
[9]Fischer W and Behrman J N.The coordination of foreign R&D activities by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J].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1979,10(3):28-34.
[10]Gassmann O and Von Zedtwitz M.New concepts and trends in international R&D organization[J].Research Policy,1999,28(2/3):231-250.
[11]Gulati R.Alliances and networks[J].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1998,19(4):293-317.
[12]Hansen M T,et al.Knowledge sharing in organizations:Multiple networks,multiple phases[J].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2005,48(5):776-793.
[13]Hite J M and Hesterly W S.The evolution of firm networks:From emergence to early growth of the firm[J].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2001,22(3):275-286.
[14]Ingram,P and Baum J A C.Opportunity and constraint:Organizations’learning from the operating and competitive experience of industries[J].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1997,18(1):75-98.
[15]Isobe T,et al.Resource commitment,entry timing,and market performance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s in emerging economies:The case of Japanese international joint ventures in China[J].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2002,43(3):468-484.
[16]Kenis P and Knoke D.How organizational field networks shape interorganizational tie-formation rates[J].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2002,27(2):275-293.
[17]Kleinknecht A and Reijnen J O N.Why do firms cooperate on R&D?An empirical study[J].Research Policy,1992,21(4):347-360.
[18]Kuemmerle W.Building effective R&D capabilities abroad[J].Harvard Business Review,1997,75(2):61-72.
[19]Lahiri N.Geographic distribution of R&D activity:How does it affect innovation quality?[J].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2010,53(5):1194-1209.
[20]Laursen K and Salter A.Open for innovation:The role of openness in explaining innovation performance among UK manufacturing firms[J].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2006,27(2):131-150.
[21]Madhavan R,et al.Networks in transition:How industry events(re)shape interfirm relationships[J].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1998,19(5):439-459.
[22]Pisano G P.The governance of innovation:Vertical integration and collaborative arrangements in the biotechnology industry[J].Research Policy,1991,20(3):237-249.
[23]Provan G,et al.Interorganizational networks at the network level:A review of the empirical literature on whole networks[J].Journal of management,2007,33(3):479-516.
[24]Spencer J W.Firms’knowledge-sharing strategies in the global innovation system:Empirical evidence from the flat panel display industry[J].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2003,24(3):217-233.
[25]Tsai W.Knowledge transfer in intraorganizational networks:Effects of network position and absorptive capacity on business unit innovation and performance[J].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2001,44(5):996-1004.
[26]Venkatraman N.Preferential linkage and network evolution:A conceptual model and empirical test in the US video game sector[J].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2004,47(6):876-892.
[27]Von Zedtwitz M and Gassmann O.Market versus technology drive in R&D internationalization:Four different patterns of managing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J].Research Policy,2002,31(4):569-588.
[28]Zander I.How do you mean “global”?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of innovation networks in the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J].Research Policy,1999,28(2/3):195-213.
[29]Zhang Y,et al.FDI spillovers in an emerging market:The role of foreign firms’country origin diversity and domestic firms’absorptive capacity[J].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2010,31(9):969-989.
[30]Zollo M and Winter S G.Deliberate learning and the evolution of dynamic capabilities[J].Organization science,2002,13(3):339-3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