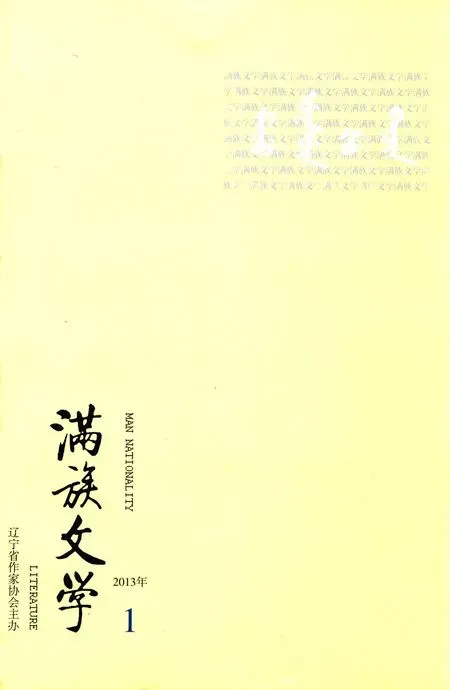故园之恋
孙成文
老屋后面,深刻在记忆中的两棵树
老屋后面有两棵树,一棵是棠梨树,一棵是杏树,是我儿时见过最大的两棵果树,长大后所见到很多同类的果树,大多也没有这两棵树那么高大、粗壮。
至于这两棵树是自然而生的还是人工栽植的,我就不很清楚了;反正,自打我记事儿起,它们就已经那么高大、那么粗壮了;至于我对这两棵树的所谓的关注,其实更多的是对脆甜棠梨和酸甜杏子的关注罢了。
从直觉上判断,那棵棠梨树是该早于那棵杏树落户我们家的;当时那棵棠梨树,我用手臂合抱不住;那棵杏树呢,倒是可以合抱过来;当然,这仅仅是我一厢情愿的猜度而已;至于梨树与杏树同期生长的速度是不是一样快,这是生物学研究的范畴,至今我也不得而知。
还是先说说那棵棠梨树吧。我印象最深的是,这棵树的树干又粗又直又长;树冠上最低的部分,与地面的距离至少也有一米八左右。这树长得相当茂盛,春季里,那缀满树冠洁白的花朵,远远望去,宛如银白色硕大的伞面,醒目在你的视野之中,那景象非常壮观,令心灵感受到一种纯粹的净化和洗礼。尽管小时候并没有更多的词汇来形容当时的感受,但现在能重温清晰的记忆,且这样来表述,心里还是算比较欣慰的。
繁花落尽的时候,地面上飘落了一场厚实的雪,那是场不死的雪;而雪的精魂,已化作了青涩的果实,精神抖擞地高挂在枝杈上,沐雨临风地生长着。
相信在孩子简单又朴素的内心世界里,最大的渴望就是紧盯着那些青涩的果子一点点长大,然后成为脆甜可口的幸福。时间一天天过去,梦便一直这样延续着;直到那一天,高远的天空下黄绿交错的叶子间,近似椭圆型、褐黄色的山楂般大小的果实挂满了枝头;无论远闻,还是近嗅,到处都弥漫着甜丝丝、香喷喷的气味,那气味诱惑又沁人心脾……
每当这个时候,奶奶的一句“这棠梨好了”,总让“小尾巴”的我欣喜不已。奶奶呢,则是操起一根细长的木棍子,踮起一双小脚,朝着树上一棍子一棍子抽去,我呢,则是在地面上铺开一块塑料布,那打下的棠梨便噼里啪啦地雨点般落下来;在我看来,奶奶是很讲究抽打技术的,轻重缓急拿捏得相当好,抽打的位置把握得也准确;因为棍子抽打力度小了,棠梨就会顽固的还挂在枝头上;力度大了呢,会打折树枝或者把棠梨打的遍体鳞伤。可是奶奶抽打下来的棠梨,一个个囫囵着呢,没有一点伤痕。
待收拾好落下来的棠梨后,奶奶总是喜欢坐在一边,微笑着看我狼吞虎咽的吃相,并一再叮嘱:慢点吃,别急!有的是呢!
那棠梨啊,真是好吃!皮薄肉脆,咬一口满是甜甜的水儿,还有一股别致的香味儿;那是一直流到心底的甜香,至今都还忘不掉。
对于那些挂在高处,奶奶的长棍子也抽打不到的棠梨,便交给猴子般的老叔来解决了。个头不高的老叔爬树技术堪称一流,脱下鞋子,抱住树干,两只脚就那么随着两只相拢的手臂移动,向上一纵一纵地,三下五除二就爬了上去,那干净利落的身手,让站在树下仰望的我好生羡慕。只见他胸前挂着一个大兜子,一会儿将这个枝头的棠梨撸下来,装进大兜子,一会儿又爬到另一个枝杈上再撸一通,看得我目瞪口呆;待大兜子装满了,他又似猴子一样的遛下了树干。
一大兜子囫囵个的棠梨照样也被我享用了。小孩嘴馋又贪心,再加上奶奶老是由着性子的宠着;棠梨吃多了,也就出问题了。晚上肚子里难受,折腾过来再折腾过去,说什么都睡不着;熬到终于睡踏实了又尿了床。自然少不得母亲的一通埋怨和斥责。可是,孩子的特色就是记吃不记打,第二天照吃不误,没办法,好吃嘛。
奶奶这个人热情好客在关屯是出了名的,每当棠梨熟了的时候,如若山下的邻里们来做客,奶奶总会拿起那根细长的木棍子,在梨树上抽打几下,一阵梨雨后,满盆的棠梨端在邻人面前;吃完了,还要给人家拿一些回去,说是给家里的孩子们吃一吃。奶奶这么做,让我心生不满;把棠梨都给了别人,自己就没得吃了。面对我的埋怨,奶奶只来那么一句“好东西不能都自己吃”,就把我打发了;当时我是无奈的,但是后来我逐渐意识到了奶奶这句话的含义;至少,我们家的棠梨从来没被谁偷过。
至于那棵杏子树嘛,就有些其貌不扬了,比棠梨树要矮上差不多一半的样子,树身也不直溜,是那种典型的歪脖子。
一般的树都是朝阳的那一面茂盛葱茏,而这棵杏树却很怪,它歪向西面,树冠也是向西倾斜,而面西的树冠依然很茂盛,初夏之后,树冠上挂满了金黄的杏子,把枝头压得很低很低,奶奶踮起小脚就可以摘到枝头上的杏子,我搬来一个小板凳踩上去也可以摘到。
那杏子个头绝对不亚于杏梅,口感也相当好;肉质在嘴里,让你感觉到一种柔软的亲切,尤其那淡淡的酸味儿里夹杂着一丝丝的甜,真是既爽口又爽心。
每到杏子熟了的时节,两个姐姐总是捷足先登,她们的个头加上板凳的高度,还有那难看的吃相,惹得我又气又急——用现在的话来说:那可真是羡慕嫉妒恨啊!只不过她们还是忌惮奶奶的招呼:“给大宝分点儿,别光顾着自己吃!”这时候她们两个才会极不情愿地“施舍”几个杏子给我,但免不了还责备我几句;看到我在姐姐面前委屈的样子,奶奶不高兴了,索性赶走了她们两个,然后也站在凳子上给我摘下来一些,看着我吃够了才算了事儿。
树上的杏子越来越少的时候,奶奶叮嘱两个姐姐不要再去摘了,剩下留给我吃。我很开心,在奶奶那里我总会受到优待的。她们两个这时候倒是对我的得意也生出嫉妒来,经常在我面前说奶奶偏心眼,还说要给我“小鞋穿”(就是找我的麻烦)。我不怕,我有奶奶当靠山呀,没办法啊,奶奶惯着我呢。
每当春天泥土完全从酣睡中苏醒过来的时候,奶奶总是颠着那一双小脚,用废水桶或者土篮子,从猪圈或者厕所里取出足量的粪水,然后在棠梨树根部用铁锹挖出一圈浅浅的坑来,说是给树“喂食”。哈,听说给小孩子喂饭,还没听说给树喂食呢。奶奶见我好奇,就简单地说小孩儿天天喂饭才能一点点长大啊,树要多结果子,也要给它喂食啊。哦,我似懂非懂地点点头,也帮着奶奶忙活起来……
可是总见奶奶给棠梨树喂食,却极少看见她给那棵杏树喂食。问奶奶缘由,奶奶一脸不屑地说那棵歪脖子杏树,就那样吧,样子也不好看如何如何。可是,毕竟那棵杏树也给了我们夏季爽口的美味儿啊,怎么会有不一样的待遇呢?就是因为它的“长相”难看吗?在我一再的坚持下,奶奶勉强地给杏树喂了不多的食。我为那棵杏树遭到不公平的待遇委屈而鸣不平,可是我拗不过奶奶,也只好那样了。每当夏季吃杏子的时候,我看着杏树发呆,再想想奶奶的做法,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滋味涌上心头。
日子就那么一天天过去,两棵树就那样安静地开着花、结着果。可是,就在奶奶去世后的第二个夏天,夜里,好大一阵子的电闪雷鸣后,那棵棠梨树被霹雳拦腰斩断。一早起来,我看见了硕大的树冠躺在地上,还有那些枝头上青涩的果子也散落一地,心里十分难过,我再也吃不到脆甜的棠梨了,那些脆甜只能属于这个夏天之前的甜美记忆了。
那棵杏树呢,那年夏季里也只挂了稀疏的果子,很快就被我和姐姐们消灭了。在秋天还没来的时候,它的叶子竟然开始打蔫,随后就干枯了。母亲说杏树是遭受了一种专门吸食树身营养的虫子的袭击,这种虫子啃食树身,在树身钻了无数个洞,产卵、生子,榨取树的营养和水分,最后树就枯萎了。我自然痛恨那些虫子,却也无奈这样的结局。
曾经带给我无限快乐和美味的两棵树,竟先后遭此厄运,可以说结局悲惨,没能寿终正寝,这也是它们的命运吧。至今想来,记忆中的这两棵树能留下的也只是美好和哀婉,也许就够了,还能奢求什么呢?
想起鲁迅在小说《社戏》里有这样一句话:从此再也没有看到过那夜似的好戏,吃到那夜似的好豆……就现在的我而言,再也不会有那样脆甜的棠梨和微酸柔软的杏子打动我的味觉,那些脆甜和微酸丝甜的感觉,不会再来,它只归属于童年的美好,只归属于心灵美好抑或伤感的沉淀……
老戏台,消逝和遗留的猜想
老戏台,在故乡关屯大庙山的西山坡上,那是每天都早早地晒在阳光里的一个角落。戏台早已不复存在,小时候乃至今天能够看到的,就是掩映在荒草之中的两座大坟茔。坟茔的上面,有一个被荒草覆盖且形状模糊的平台,料想这就是当年所谓戏台的遗迹吧。
其实,关屯人早已习惯地把那两座坟茔称作老戏台。这样的一个代名词,让我从小时候就开始猜想,这两座坟茔与一个泥土平台间到底有什么联系。
许是心理作用吧,小时候,每每见到坟茔,总有一种莫名的恐惧感,疑似有所谓的“鬼”会从那里爬出来。一次跟伙伴们钻林子藏猫猫,藏着藏着,一不小心便误入了老戏台,当看见那两座大坟茔时,吓得我嗷的一嗓子,兔子般地撒腿就跑,伙伴们也跟着四散奔逃。然后我便是大病一场,整天昏沉沉的,发着高烧说着胡话。母亲跟奶奶急得又是找大夫又是烧什么“聚魂贴”,还在夜深人静时,用水瓢轻敲水缸,接连不断地念叨着“成文魂儿快上身啊!”
我也不知道最终是什么疗法救了我的命,反正后来病是好了。奶奶心疼地叮嘱我:以后可千万别再去老戏台了,让那两个戏子见怪了,可不得了啊。
奶奶的话让我愈加好奇起来,戏子?什么是戏子啊?奶奶极其认真地解释说,就是唱戏的。为什么唱戏的叫戏子啊?奶奶有些不耐烦地说,小孩子问那么多干嘛?!后来想想,奶奶其实也不知道戏子称谓的由来,也就故作不耐烦地那么搪塞我了。
母亲见我好奇心很强,就把她从太爷那里听来的故事讲给我听。
说是大庙山建成了龙母庙之后,就在山的西面修建了一个简陋的戏台,每每遇见重大节日,南来北往朝拜的人多的时候,就请来了戏班子演戏,为那些朝拜的人们丰富点娱乐生活。据说有一天晚上台上的武生戏正演着,不知何故,竟然有两个扮相跟台上两个戏子一模一样的人混上了戏台,于是双方就真的打了起来……后来那两个演武生的戏子就死在了台下;再后来,关屯人就把那两个戏子埋在了戏台的下面。于是就有了现在的两座大坟茔。
也许是忌讳那地方死了人吧,从此戏台便不再有戏上演了,它被人们冷落着逐渐淡出视野,然后经年风剥雨蚀变得越来越破败,倒先于大庙山的龙母庙被拆掉了。
我有些惋惜,为什么是两个武生戏子死了?他们不会功夫吗?兴许死的是那两个混上戏台的坏人呢?我向母亲提出了一连串的疑问,母亲无奈地回答我说,你太爷就是这么讲的,细底究竟怎么样,我上哪儿知道啊。
是啊,太爷早已故去,我再没有机会去找他问问清楚了。
从那之后,我经常一个人傻兮兮地远远地望着西山坡上的那两座坟茔发呆,始终想知道那两个戏子与戏台更多的东西。显然,答案也就仅限于母亲告诉我的那些。
我就那么带着惋惜与遗憾望着,也带着一颗好奇的心,想象着那两个土堆下面深埋的故事。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期,当电影版的京剧样板戏《智取威虎山》在关屯上演的时候,我就情不自禁地把童祥苓扮演的杨子荣的形象,与想象中的老戏台上那两个逝去的戏子进行比对——想象他们的眼睛也是那么亮、动作也是那样地干净利落,唱腔也是那么的清脆圆润……
看完电影,我竟然又胡思乱想起来,兴许童祥苓等京剧演员就是那两个戏子的后代或者是他们徒弟的后人。这样的想法跟母亲一说,母亲竟然笑得眼泪儿都流出来了——儿子啊,你都想到哪儿去了,笑死妈了啊!为什么不会啊?我一脸认真地反问。你都哪来的那么多为什么啊,我可不知道啊,也不能瞎说啊。
我还要问什么,母亲刚才的笑脸突然一下子消失了,她板着面孔严肃地告诫我:到外面可不能这么乱问别人,也不能这么胡乱联系啊,杨子荣是革命英雄,那两个戏子是封建的牛鬼蛇神,是被批判的对象,这么联系就是反动派啊,是要被批斗的啊。这……我又糊涂了,但看着母亲那张严肃的脸,我刚要出口的话又咽了回去,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后来看到的一些人和发生的一些事,证明母亲的告诫是正确的。那时候,是不能乱说话的,无论大人还是小孩儿。
但心里面,老是在犯嘀咕:不都是演戏吗,怎么还分英雄形象和牛鬼蛇神啊?唉,真的搞不清楚了……
真正搞清楚的时候,童真已不再,只有故乡的老戏台以及相关的疑问始终在脑海里徘徊。
现在想想,关于老戏台,我认为母亲当年讲的不是故事,是传说,可信度是打了很大折扣的,有些捕风捉影的意味儿。可是,我又不愿意相信那是传说,因为那两座坟茔还在,那个地方依然被故乡人称作老戏台。一些陈年的旧事尽管沿革成了传说,但毕竟还有些影子在里面掺杂着,不可能是空穴来风吧。
无论如何,老戏台——那两个大土堆,丰富了我童年时代的猜想,也许,我的联想和想象能力的培养就是从对它的猜想开始的吧……如是,除了感谢故乡的老戏台,剩下的依然是无法抹去的猜想。
童年里关于老戏台的那么多的疑问,至今仍是一个谜。没有谁能帮我揭开,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只能在心中无奈地承认这是一个传说的事实。但,从另个层面上,我着实地感觉到,那两堆厚厚的土层下面,分明深涵着故乡关屯的一些历史和人文的东西;抓一把那里的泥土,会渗出故乡古老的文化成份;或者说,老戏台的传说,是故乡人对关屯往事的怀恋情结之所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