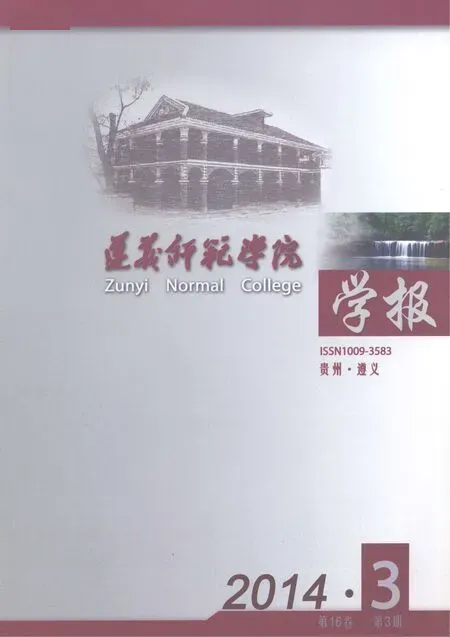中国年节文化的族群性呈现——评吴正彪教授的《苗年》
李国太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四川成都610064)
中国节日文化丰富多彩,这不仅体现在某个民族在一年的时间周期中所呈现出的节日的丰富性上,而且也体现在五十六个民族共同创造的节日文化的多样性中。在言及中国的节日文化时,我们常常首先想到的是春节。而关于春节在人们心中的重要性,只要看一看每年春运期间全国涌动的人流便可见一斑。实际上,这个在传统上被称为“过年”的习俗虽然是中国诸多民族所共享的生活经验和文化体会,但在时间的选择和内容的呈现上则因各个族群的文化差异而形成多元的景象。由此可见,中国的年节文化并不等同于以汉民族为主体的春节,它内在的丰富性还有待“发掘”。令人欣喜的是,吴正彪教授的《苗年》正是这样一部“发掘”之作。该书将一个本是天文学和物候学的概念置于具体的族群——苗族中进行考察,从而在对苗年的巡礼中体现出苗族文化自身独有的知识体系和文化传统。这本书至少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
一、将苗年置于苗族文化的整体中考察
苗年并非孤立的文化现象,它仅仅是苗人生活节律中的一个音符。如果抛开对苗族文化的整体性考察,便很难理解“年”在苗人生活中的重要性。对此,作者在广泛的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发现了“苗年”和苗历的内在关联性,从而为这一流动而又循环的节点寻找到事实的根据,他指出:“在时间的差异上,苗年总是与同一年中的其他节日流程有着明显的对应关系。如果把水稻的播种作为一年中一个与此相关的节日如“开秧门”、“祭桥”等的开始,那么“吃新节”就是这一节日时段的一个前奏,苗年自然是整个节日时段的活动高潮期。”[1]p16实际上,作者对苗年的这种思考是他长年行走在苗疆,对不同地域内苗族文化传统的体认和感悟的结果。他深刻地意识到,节日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展演一个民族的文化表征,更在于“(节日)如同一个个竹节,为人们提供了把握不可把握的时空的方法,它象征着时空段落之间有意味的交接点,自然成为生活中的高潮部分”[2]。实际上,苗人对苗年起源的叙事歌谣便呈现出这一认知:
“年从何处起?岁源月亮梢,天宇边缘来,彩色养人眼。天上争着要‘年’过,地上争着要过‘年’。只因天上手臂长,天上抢得‘年’去过,地下百姓手臂短,空手失望回家转,无奈只好游山去,植物长势作标志。庄稼种收把节过,节庆举家品美味,全家老少皆高兴。”[1]p32
在这颇具神话色彩的叙述中,蕴含着苗人对“年”之由来的认识。而“年”的标志便在于“植物长势”,而节日“举家品美味,全家老少皆高兴”的活动与世界各民族的丰收节无异。苗年、苗历与农耕文化的联系由此可见一斑。
农耕文化遵循自然的周期性规律,文化上最直接的体现在对历法的重视上,历法本身便随着周期性的循环而在一年中农事的不同关节点呈现出族群文化的特征,“年”恰好是上一个循环系统与下一个循环系统的交接点,三者的关系由此体现出来。对此,徐新建教授已有精到的评价:“对苗年的考察,最突出之处在于将其与特定的农事活动关联在一起,展示了苗族及其年节的农耕性和族群性,也就是特定的生态性和文化性。”[3]但如果将视野放得更广阔,全方位地考察农耕文化中“年”的特征,不仅可以为跨文化比较研究提供一条新的路径,也能为深入阐释每一个族群的“年”文化提供新视角。
二、关注苗年民族性与区域性的统一
《苗年》中所呈现的“苗年”是复数,因为同是苗年,在苗族的内部却存在巨大差异。不同方言区的苗族,不仅对“苗年”的称法各异,就连其在时间的选择上都具有地域特征。作为一种节日文化的苗年,在时间和空间上同一民族为何有如此大的差异?作者认为这是由于“苗年节的形成,不仅体现了各个不同支系的苗族既有对自然环境生物性适应的一面,也有对周边不同文化族群存在着社会性适应的一面。”[1]p17在“苗年与苗族的传统历法的关系”一节中,他进一步解释道:“苗历在各个苗语方言及土语区,由于居住的自然环境不同,气候条件不一样,农作物的成熟期有长短之分,因而所形成的苗历体系也存在着一定的差异,由此所导致的苗年在过节时间、节日规模、相关仪式及节日活动等存在着一定的差别”。这种民族性和地域性的统一与背离,恰好证明了苗族内部的文化多样性。节日文化地域性特征的意义又何在呢?就在于“有时某一民族节日的民族性会在文化的同化过程中逐渐被淡化,但节日的地域性却依然在时空建构上保留着不同族群相互认同和共有的文化烙印。”[1]p22这样的认知,如果没有常年行走在田野中的经历,是很难体会到的。
在多元文化主义时代,多元之“多”的涵义需要再审视,因为含混的“跨文化”概念一旦进入文化比较的层面,往往便会忽略文化持有者的多样构成。在跨文化比较研究中已有学者指出:“对西方文明开端代表作的文学人类学审视,表明原有的以西方地理观念为标准的东西方划分及民族国家划分,怎样长期发挥着束缚思想和遮蔽真相的副作用。以族群为单位的重新认识,将打开一个我们以前所未知的新世界。”[4]这种反省意义重大。但在此基础上研究者也不应忽视族群内在的文化差异性,苗年或许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三、田野调查与主位视角
吴正彪教授是出生在黔东南的苗族,又长期在苗族地区进行关于苗族语言与文化的人类学研究,这种得天独厚的优势使他能够从族群本位的视角出发考察苗年。实际上早在2006年,作者就已经完成了《苗族年历歌和年节歌的文化解读》,《苗年》可谓是那本书的姊妹篇,是作者思考苗族年节文化的深化。这种持之以恒的对本民族文化的关注,体现出作者对本民族文化的热爱。《苗年》中引述了一首苗人的歌谣这样唱道:
“为什么我们要使用自己的语言?为什么我们要配饰自己的装束?不为什么呵,只因为我们的名字叫苗族。
为什么我们要阅读自己的书本?为什么我们要弘扬自己的艺术?不为什么呵,只因为我们的名字叫苗族。
为什么我们要继承祖先留下的文化?为什么我们要保留自己的传统习俗?不为什么呵,只因为我们的名字叫苗族。”[5]
或许,这也同样契合作者写作本书的心情。《苗年》不仅对“苗年”文化作了全方位的考察,而且花了大量笔墨就苗年的价值及其保护和传承现状作了考察,这或许正是源于一个苗族知识分子内心对本民族文化的自豪感和忧虑感。
但作为一个严谨的学者,作者又十分清楚在学术研究中任何过于感情化的论断都是不可取的,因此在《苗年》中,作者总是习惯于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呈现给读者,通过当地人的讲述,使读者在“听故事”的过程中直接进入苗族人的视角去感受苗年的丰富。
四、结语
苗年仅仅是一个展现苗族文化的窗口,而苗族也仅仅是中国诸多民族和世界诸多族群中的一个,如果以“苗年”为中心延展开来,不仅能看到被单数化和平面化处理的苗族文化本身的丰富性,也可以看到中国多民族文化之“多”的现实性,从而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理论提供西南个案,为世界文化多样性提供中国的田野案例。因此,《苗年》仅仅是一个开始,是一个发掘中国多民族文化的良好开端。
[1]吴正彪.苗年[M].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2011.
[2]吴正彪.苗族年历歌和年节歌的文化解读[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6.61-62.
[3]徐新建.节日体现的文化选择[J].三峡论坛,2011,(5).
[4]叶舒宪.“世界文学”与“文学人类学”[J].中国比较文学,2011,(3).
[5]苗青.中国苗族文学丛书·西部民间文学作品选(1)[M].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