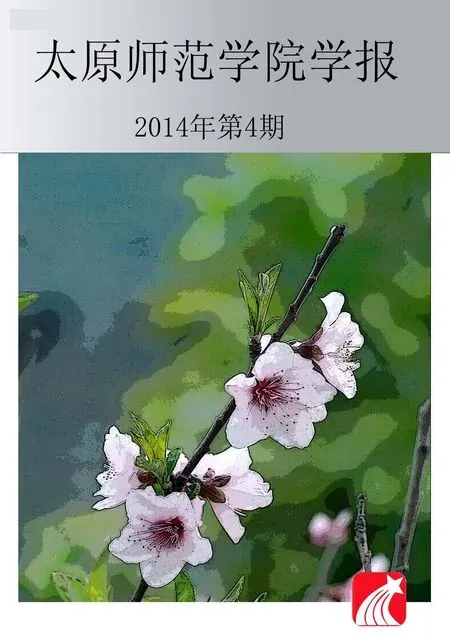《异苑》与楚地宗教生态
李根亮
(长江大学 文学院, 湖北 荆州 434023)
《异苑》是南朝宋刘敬叔撰写的志怪小说集,共收罗古今怪异之事383则,其中有多则故事涉及楚文化中心地区的民俗信仰、巫术之风、早期佛教的传播等问题。考察这些问题,对于了解六朝前后楚地的宗教生态是有一定意义的。而本文中的楚地主要是指湖北、湖南、江西北部、河南西南部等地区。
一、《异苑》与楚地的民俗信仰
楚文化并没有随着楚国的灭亡而消失,而是借助于各种文献继续留存于古人的记忆中。六朝志怪小说之一的《异苑》就保存了不少流传于楚地的各种民俗信仰,这些民俗信仰与中原文化既有联系也有区别。
1.舜帝信仰
舜帝是中华民族共同敬仰崇拜的祖先之一,传说他南巡时死去,葬于九嶷山。《山海经·海内经》云:“南方苍梧之丘,苍梧之渊,其中有九嶷山,舜之所葬,在长沙零陵界中。”《史记·五帝本纪》也记载:“舜南巡,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嶷。”由此可见,舜帝信仰最早可能起源于楚地,并逐渐流传到北方。《异苑》卷一“九嶷山舜庙”载:“衡阳山、九嶷山,皆有舜庙。每太守修理祀祭洁敬,则闻弦歌之声。汉章帝时,零陵文学奚景于冷道县祠下得笙白玉管,舜时西王母献。”[1]596这段记载说明,在汉章帝时期,古人对舜帝的祭祀已经常态化,从官方到民间把舜帝作为祭祀的对象。根据现存文献,秦始皇三十七年出游至云梦,曾望祀虞舜于九嶷山。汉武帝元封五年冬,也曾望祀虞帝于九嶷山。湖南九嶷山至今仍然保留着舜帝庙的遗迹。
2.土龙
《异苑》卷三载:“晋义熙中,江陵赵姥以酤酒为业。居室内土,忽自隆起。姥察为异,朝夕以酒酹之。尝有一物出,头似驴,而地初无孔穴。及姥死,邻人闻土下有声如哭。后人掘地,见一异物,蠢蠢而动,不测大小,须臾失之,俗谓之土龙。”[1]615这里提到的土龙与古代大多数人关于龙的印象有显著的差异。事实上,传统文化中的龙意象既生活在水里,也居住于陆地,是水陆两栖动物。如《周易·乾卦》云:“龙或跃在渊。”《管子·水地篇》云:“龙生于水,被五色而游,故神。”而《后汉书·张衡列传》则提到:“夫玄龙迎夏则凌云而奋麟,乐时也;涉冬则淈泥而潜蟠,避害也。”其中的玄龙却钻进了泥土。《淮南子·地形训》还提到了“土龙”之名:“土龙致雨,燕雁代飞。”不过在汉代以后,人们心目中的龙主要还是与水有关,龙与土地的关系反而被淡化了。古人之所以经常将龙与水联系起来,其原因应该是古代农业民族尤其是北方民族对雨水的需求及渴望。相反在南方地区,由于雨水充足,人们对龙的印象中就淡化了它与水的联系,却赋予其保佑人们家宅安宁、生活幸福的功能。
至今南方一些地区还流传着土龙神的信仰。如现在的赣西农村,就流传着一种安龙补土醮仪式。其目的是对守宅之土地龙神进行安抚,以解决房屋因龙脉轻而带来的种种不顺。[2]在华南地区,人们在建筑房屋时仍然受到民间的五土龙神信仰的影响。[3]按照风水学的说法,五土龙神是掌管五方龙脉与一家之富贵安康的。这与《异苑》中的土龙信仰有点类似。
3.河伯
《异苑》卷六“形见慰母”云:“晋太元中,桓轨为巴东太守,留家江陵。妻乳母姓陈,儿道生,随轨之郡,坠濑死。道生形见云:‘今获在河伯左右,蒙假二十日,得暂还。’”[1]646关于河伯神的来历有多种说法,有指黄河之神,如洪兴祖《楚辞补注》引《抱朴子·释鬼篇》云:“冯夷以八月上庚日渡河溺死,天帝署为河伯。”《搜神记》卷四“冯夷”也有类似记载。《史记·滑稽列传》还提到“河伯娶妇”的故事,其中的河伯被形容为可怕的恶神。《九歌·河伯》开始把河伯描写为风流潇洒的富贵公子:“鱼鳞屋兮龙堂,紫贝阙兮朱宫,灵何为兮水中?”可见北方与南方关于河伯神的描述有明显的差异。《异苑》中的桓轨之子道生在荆楚地区的巴东郡坠河而死,于是在水宫中服侍河伯。该河伯似乎不应该是黄河之神,更像是一个住在富丽堂皇宫殿中的、楚人崇拜的水神。不过从本质上看,南北方的河伯信仰都是一种对江河湖泊的自然崇拜,表现出中原文化与楚文化的交融特征。
4.赤鬼与黄父鬼
人鬼信仰(或者鬼魂信仰)是对人的灵魂的信仰。这是一种存在于古代社会的普遍精神信仰,但在不同地区有形态上的差异。《异苑》中有多则故事涉及南朝时期出现的人鬼信仰,而且显示出南方地区的特色。如《异苑》卷四“赤鬼”云:“谢晦在荆州,见壁角间有一赤鬼,长可三尺,来至其前,手擎铜盘,满中是血。晦得,乃纸盘,须臾而没。”[1]632其中的赤鬼可能是被冤杀的鬼魂,但其赤色的外形与多数人关于鬼魂的印象有明显不同。楚文化有服饰尚赤色的特征,《异苑》中对赤鬼外形的强调也许与此有关。
《异苑》卷六还提到了一种关于黄父鬼的信仰:“黄州治下有黄父鬼,出则为祟。所著衣袷皆黄,至人家,张口而笑,必得疫疠。”[1]653黄父鬼出现于黄州地区,也即现在的黄冈。黄父鬼出没的地方,必带来瘟疫之灾害。汉代小说《神异经·东南荒经》也提到黄父鬼:“东南方有人焉,周行天下,身长七丈,腹围如其长。头戴鸡父魌头,朱衣缟带,以赤蛇绕额,尾合于头。不饮不食,朝吞恶鬼三千,暮吞三百。此人以鬼为饭,以露为浆。名曰尺郭,一名食邪。道师云吞邪鬼,一名赤黄父。今世有黄父鬼。”[1]50《神异经》中的赤黄父“朝吞恶鬼三千,暮吞三百”,是恶鬼的克星,与《异苑》中的黄父鬼有本质上的不同。根据《后汉书》卷五十七“栾巴传”中李贤注引用《神仙传》原文“(豫章)郡中常患黄父鬼为百姓害,巴到,皆不知所在,郡内无复疾疫”,可知在豫章郡,即现在江西地区也存在黄父鬼的信仰。
5.龙山神
《异苑》卷七载:“晋荆州刺史桓豁所住斋中,见一人,长丈余,梦曰:‘我龙山之神,来无好意。使君既贞固,我当自去耳。’”[1]661龙山之神应该是一种自然崇拜信仰,它可能与湖北钟祥境内的龙山有关,至今龙山还保留着建于唐代贞观七年的龙山报恩寺。该龙山神的出现是为了监督荆州刺史桓豁,当发现桓豁并无恶行时便很快消失。龙山神的职能类似于道教的城隍或社神,是荆州地方的守护神。
二、《异苑》与楚地巫风
楚地多巫。《异苑》中有多则小说提到了楚地的巫风,如《异苑》卷三“邓遐治蛟”、卷八“武昌三魅”、卷九“赵侯异术”等。卷三“邓遐治蛟”言:“荆州上明浦沔水隈,潭极深,常有蛟杀人,浴汲死者不脱岁。升平中,陈郡邓遐字应遥,为襄阳太守。素勇健,愤而入水觅蛟,得之。便举拳曳著岸,欲斫杀。母语云:‘蛟是神物,宁忍杀之?今可咒令勿复为患。’遐咒而放焉。自兹迄今,遂无此患。”[1]616襄阳太守邓遐在治理蛟龙之害时,听从母亲建议对蛟龙实施咒语后将其释放,而蛟龙随后也不再作恶。这则故事提到的是一种最原始的控制自然现象的咒语巫术,不过襄阳太守究竟对蛟龙说了何种咒语不得而知。
所谓咒语是“巫师和其他施术者用来驱除鬼魅邪祟、消灭各种危害的巫术语言”,一些巫师认为“某些攻击性的语言具有特殊威力,可以随时随地地用来贯彻自己的意志,控制和改变事物的现状。”[4]45《异苑》卷九“赵侯异术”提到的也是咒语巫术:“晋南阳赵侯,少好诸异术。……侯有白米,为鼠所盗。乃披发持刀,画地作狱,四面开门,向东长啸,群鼠俱到。咒之曰:‘凡非啖者过去,盗者令止。’止者十余,剖腹看脏,有米在焉。曾徒跣须履,因仰头微吟,双履自至。”[1]680赵侯的白米为老鼠偷吃,于是施展巫术将偷吃之老鼠抓获。赵侯施术时对老鼠所言“凡非啖者过去,盗者令止”的一段话即相当于咒语。不过赵侯说出咒语之前还有一个仪式,即“披发持刀,画地作狱,四面开门,向东长啸”。这个仪式可能比咒语本身更重要。
《异苑》卷八“武昌三魅”[1]668还提到了一种古代控制动物精怪的巫术:在南朝宋高祖时,张春为武昌太守。当时有人家嫁女,其女自言“不乐嫁俗人”。巫师认为该女被邪魅所祟,就将该女带至江边“击鼓以术咒疗”。张春以为巫师欺惑百姓,命令巫师限期内捉获妖魅。巫师施展巫术后,一青蛇、一大龟、一大白鼍先后被捕获后杀死。该巫术在实施时不但行以咒语,而且还要“击鼓”。通过击鼓驱逐精怪,是古代流行的噪音驱逐鬼怪法术之一,类似于古代爆竹驱鬼法术。如在古代战争中,两军对垒时必有鼓铎之声,以壮大声势。驱逐精怪就像打仗一样,也要击鼓敲打以壮大声威。为了捉住元凶大白鼍,巫师还“以朱书龟背作符,更遣入江”,可见该巫术既要念咒也要画符。画符来自巫师对政治军事用语的模仿。符是指古代发兵、过关用的凭证,代表着命令、威严和力量。巫师画符是希望在驱逐鬼神精怪时也表现出强大的威力。
三、《异苑》与楚地佛教的传播
佛教自汉代传入中国以后,在南北朝时期影响越来越大。如东晋时的江陵和江西的庐山都是长江中游地区佛教发达的地区,《异苑》中的一些篇章就涉及佛教及其信仰在这些地区的传播问题。《异苑》卷五“慧炽见形”载:
沙门竺慧炽,新野人,住江陵四层佛寺。永初二年卒。弟子为设七日会。其日将夕,烧香竟。沙门道贤因往视炽弟子,至房前,忽暖暧若人形,详视乃慧炽也。容貌衣服,不异生时。谓贤曰:“君且食肉,美否?”曰“美”。炽曰:“我生不能断肉,今落饿鬼地狱。”道贤惧詟,未及得答。
这段记载有三个问题值得注意:一是在南朝刘宋时期江陵的四层佛寺,二是佛门为和尚圆寂举行的七日会仪式,三是佛门弟子的吃素信仰等问题。
江陵四层佛寺,现在已经看不到,《续高僧传》卷二十五“荆州四层寺释法显传七”曾提及该寺庙。根据《高僧传》等文献记载,除四层佛寺外,东晋时期在江陵还有长沙寺、竹林寺、高悝寺、赡养寺、琵琶寺等多个寺庙。由此可知佛教在荆州地区的兴盛。
佛门的七日会,应该是“打佛七”的另外一种说法,源于《阿弥陀经》等佛典。如《阿弥陀经》云:“舍利弗,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说阿弥陀佛,执持名号。若一日,若二日,若三日,若四日,若五日,若六日,若七日,一心不乱。其人临命终时,阿弥陀佛与诸圣众现在其前。是人终时,心不颠倒,即得往生阿弥陀佛极乐国土。”[5]171“打佛七”就是当人亡故时,要念“阿弥陀佛”连续七日,亡者即可往生阿弥陀佛极乐世界。《观无量寿佛经》亦云:“称佛名故,于念念中,除八十亿劫生死之罪。命终之时,见金莲花,犹如日轮,住其人前。于一念顷,即得往生极乐世界。”[5]56超度亡者,应以念佛为主,此乃最切实、最易行的获得功德之方式。从佛门的七日会仪式中,可以推断出南朝时期佛教净土宗在荆楚地区的广泛传播,而唐代时期盛行的禅宗在楚地显然还没有形成气候。
另外,从这段记载中还可以清楚看出,死去的竺慧炽和尚生前并不戒荤,因而死后坠入饿鬼地狱。当道贤和尚去祭拜他时,竺慧炽以切身体会劝诫道贤不可食荤。这可能反映出南朝时佛教徒对于和尚是否应该吃肉问题的矛盾,也侧面说明当时中国佛教徒的戒律是比较松弛的。其实佛教的五戒“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和佛教的八戒“戒杀生”、“戒偷盗”、“戒淫邪”、“戒妄语”、“戒饮酒”、“戒着香华”、“戒坐卧高广大床”、“戒非时食”并没有涉及吃不吃肉的问题。在佛教传入中国以后,要求佛教徒不吃肉的戒律更可能是受到道教的影响。
《异苑》卷五“慧远咒龙”则提到了南朝时期的另一个佛教中心庐山:“沙门释慧远栖神庐岳,常有游龙翔其前。远公有奴,以石掷中,乃腾跃上升。有顷,风云飙煜。公知是龙之所兴,登山烧香,会僧齐声唱偈。于是霹雳回向投龙之石,云雨乃除。”[1]641该记载比较神奇,但涉及净土宗的始祖慧远大师与神龙的较量。龙是道教崇拜的神灵,慧远以佛法之力将神龙降服,暗示出外来的佛教与本地宗教道教的竞争。
[1] 王根林,黄益元,曹光甫(校点).汉魏六朝小说笔记大观[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2] 杨永俊,罗陆英.对民间补土醮独尊土地龙神的文化内涵解析[J].井冈山学院学报,2006(6).
[3] 刘军.民间信仰与乡村都市化——以华南地区K村客家人的五土龙神信仰为样本[J].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08(4).
[4] 胡新生.中国古代巫术[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8.
[5] 林世田(点校).净土宗经典精华[M].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