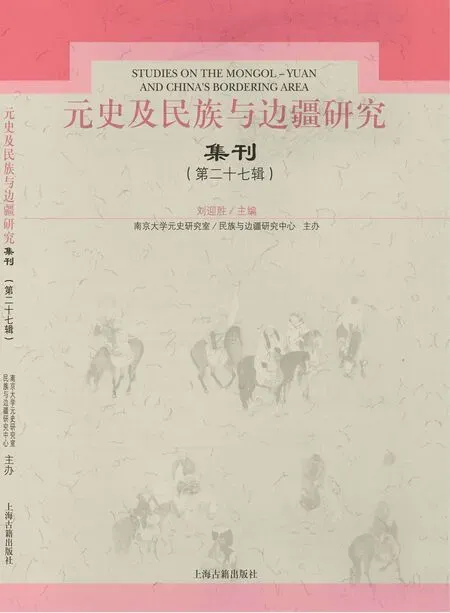《元史》订补二题*
——兼及元人碑传的谀墓与曲笔
陈 波
《元史》订补二题*
——兼及元人碑传的谀墓与曲笔
陈 波
董士选、石抹继祖二人在元代颇有儒素清白之令名,但这种历史形象并不完全符合历史真实,本文通过梳理二人碑传及相关列传记载,试图说明元人碑传多有“谀墓”或“曲笔”之处,而《元史》列传多本于碑传记载,其可靠性与真实性须加考辩,审慎利用。
董士选 石抹继祖 谀墓 曲笔
《元史》由于编修时间仓促,且出于众手,存在诸多不足之处,历来就遭到学者们的非难。就《元史》列传而言,相较其他二十四史列传,亦较为粗糙,清代学者钱大昕对此曾有激烈批评a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卷九《元史》:“古今史成之速,未有如《元史》者,而文之陋劣,亦无如《元史》者……开国功臣,首称四杰,而赤老温无传。尚主世胄,不过数家,而郓国亦无传。丞相见于表者五十有九人,而立传者不及其半……本纪或一事而再书,列传或一人而两传。”上海书店,1983年,第195页。。从具体内容看,其中一些名公巨卿、元勋世臣的传记,无非是个人功勋劳绩的系年排列,并且完美得难以找出传主哪怕丝毫的瑕疵,而揆以常理,这不免有悖于历史真实。在此,笔者试图以董士选、石抹继祖二人的传记或碑传为例,对这一问题稍加揭示,俾有益于当下正在进行的《元史》会注工作。
一、 朱清、张瑄的伏诛与董士选的出处进退
藁城董氏一族,在元代以其儒 素方正见称朝野,也颇受元朝诸帝亲信,有元一代自始至终显宦不乏其人。但是作为元朝政治舞台上极其重要的阀阅之家,不可避免地要卷入元廷政争的激烈漩涡,作为这个家族中的个人,亦难免有宦海沉浮。这里所要揭示的,就是作为董氏第三代名宦的董士选在大德七年(1303)朱清、张瑄二人受诛前后的出处进退。
之所以要言及董士选的此次宦途风波,是因为其本人与朱清、张瑄关系匪浅,宋元鼎革之际,正是随父董文炳征战的董士选亲自招降二人,使之宣力元廷b《元史》卷一五六《董文炳传》,中华书局,1976年,第3672页。。因此董士选对于朱、张二人而言,有提携之恩,自不待言,而朱清、张瑄的宦海沉浮,自然也关乎董士选的进退荣辱。而大德七年朱清、张瑄二人伏诛,对于董士选的仕途到底有无冲击,无论是《元史》本传还是记载董士选生平的《元荣禄大夫平章政事赵国董忠宣公神道碑》(《吴文正公集》卷三二,以下简称《神道碑》)皆语焉不详,似乎刻意回避。《元史·董士
选传》云:
桑哥事败,帝求直士用之,以易其弊,于是召士选论议政事,以中书左丞与平章政事彻理往镇浙西,听辟举僚属。至部,察病民事,悉以帝意除之,民大悦。有聚敛之臣为奸利,事发得罪且死,诈言所遣舶商海外未至,请留以待之,士选曰:“海商至则捕录之,不至则无如之何,不系斯人之存亡也。苟此人幸存,则元以谢天下。”遂竟其罪。a《元史》卷一五六《董士选传》,第3676—3677页。植松正《元代江南の豪民朱清张瑄について》,《東洋史研究》第27卷第3号,1968年。收入氏著《元代江南政治社會史》,汲古書院,1997年,第304页。 虞集《道园类稿》卷三七《元人珍本文集丛刊》本,第六册,第196页。
值得注意的是,此处所谓聚敛之臣,并未明言所指何人。日本学者植松正撰文谓“此处所谓聚敛之臣,当指朱清或者张瑄”,同文注七提到:“此事《董士选传》将其置于成宗即位之前,桑原氏在《蒲寿庚事迹》中也认为此乃世祖末年之事,难以理解。按大德七年董士选任江浙行省左丞,而非中书左丞,彻理亦任同省平章政事b《元朝名臣事略》卷四《平章武宁正宪王》:“(大德)七年,改浙省平章政事,其治如台,门无私谒。以转粟京师多资东南,居天下什六七,而松江填淤岁久,富民利之,当水出涂筑为围田,以故弥漫浸灌,沮洳广远,民不可稻。公发卒数万浚决,揵石堤之,导水入海,使复其故。凡身董役,经时而成,民得良田若干万顷,至今赖之。”中华书局,1996年,第70页。。且在此事与成宗即位之间,可见关于董士选与彻理经营水利事业的记载。因而此处的记载与朱清、张瑄籍没事件相关,当无疑义。《新元史》卷一四一《董士选传》则将‘聚敛之臣’一事及水利事删去。”c《元史》卷一五六《董士选传》,第3676—3677页。植松正《元代江南の豪民朱清张瑄について》,《東洋史研究》第27卷第3号,1968年。收入氏著《元代江南政治社會史》,汲古書院,1997年,第304页。 虞集《道园类稿》卷三七《元人珍本文集丛刊》本,第六册,第196页。可是《神道碑》则明言此处所谓聚敛之臣,系指桑哥的党羽沙不丁,且系事于至元二十八年(1291):
二十八年,世祖将诛桑葛,夜遣近侍召公入,谓公曰:“桑葛谗慝贪婪,朕不私一人以病天下。”命平章不忽木与公商度,桑葛及其党皆抵罪,时相独庇江淮省平章沙福丁,复立行泉府司,俾之典领,以征舶商之输。谓国家出财,资舶商往海南贸易宝货,赢亿万数,若沙福丁黜,商舶必多逃匿,恐亏国用。世祖信其言。公曰:“国家竭中原之力以平宋,不得不取偿于南方,然新附之地,人心惊疑,初阿合马以要束木贼湖广,忽辛贼江淮,民曰此圣上未之知尔。及二贼诛,民曰圣上果不知也。桑葛以沙福丁贼江淮,其毒甚于忽辛,民怨之入骨,又曰圣上亦未之知也,今桑葛之党皆逐,而沙福丁独留,恐失民心,民心一失,收之甚难,得财货之利轻,失民心之害重,何况海商家在中土,其往必复,行省自能裒其所有,何以沙福丁为?”世祖瞿然曰:“此言是也。”再三嘉奖,赐公白金五千两,授骠骑卫上将军,江淮行省左丞。d吴澄《吴文正公集》卷三二《元荣禄大夫平章政事赵国董忠宣公神道碑》,《元人珍本文集丛刊》本,第三册,第542页。
附和此说的还有虞集所撰《董忠宣公家庙碑》:“(桑)葛之党以海舶重利未还动朝廷,请复立行泉府院,以挠行省,公伐其谋而罢之,又佥行枢密院于江淮。”e《元史》卷一五六《董士选传》,第3676—3677页。植松正《元代江南の豪民朱清张瑄について》,《東洋史研究》第27卷第3号,1968年。收入氏著《元代江南政治社會史》,汲古書院,1997年,第304页。 虞集《道园类稿》卷三七《元人珍本文集丛刊》本,第六册,第196页。
但是,《元史》本纪对于此事的记载却完全不同。据《元史·成宗纪》,大德七年(1303)三月,朱、张事发的当口,董士选被枢密院及监察御史参劾曾贷钞与朱、张以牟利,成宗虽然表面上未加追究,但显然对董士选产生了怀疑,五月董士选即受命以江浙行省右丞的身份籍朱、张货财赴京,“其海外未还商舶至,则依例籍没”。a《元史》卷二一《成宗纪四》大德七年三月癸丑条(第450页):枢密院臣及监察御史言:“中丞董士选贷朱清、张瑄钞,非义。”帝曰:“台臣称贷不必问也。若言者不已,后当杖之。”又《元史》卷二一《成宗纪四》大德七年五月辛巳(第452页):命江浙行省右丞董士选发所籍朱清、张瑄货财赴京师,其海外未还商舶至,则依例籍没。 《元史》卷一九《成宗纪二》,元贞二年七月壬午(第405页):“增江西、河南省参政一员,以朱清、张瑄为之……”又同卷冬十月壬子(第406页):“赣州贼刘六十攻掠吉州,江西行省左丞董士选讨平之。”又《元史》卷一八一《元明善传》(第4172页):“辟掾行枢密院。时董士选佥院事,待之若宾友,不敢以曹属御之。及士选升江西左丞,又辟为省掾……始,明善在江西时,(朱)〔张〕瑄为其省参政,明善有马,骏而瘠,瑄假为从骑,久益壮,瑄爱之,致米三十斛酬其直。后瑄败,江浙行省籍其家,得金谷之簿,书‘米三十斛送元复初’,不言以酬马直,明善坐免;久之,有为辨白其事者,乃复掾省曹。” 《经世大典·元漕运一》,《永乐大典》卷一五九四九,中华书局,1986年影印版,第6969页。
需要注意的是,《神道碑》撰写者吴澄颇受董士选礼遇。元贞二年(1296)董士选任江西行省左丞时,经省掾元明善引见,前往拜望吴澄,为其学识所折服,遂执弟子礼,还向元廷力荐吴澄入朝b《元史》卷一七一《吴澄传》,第4011页。。由此可知吴澄与董士选有师生之谊,而董士选则于吴澄有知遇之恩。董士选对于朱、张二人有提携之恩,朱、张二人也投桃报李,元贞二年董士选与张瑄同任职于江西行省,董士选乃是张瑄的上司,张瑄还与董士选所敬重的省掾元明善交好,借其瘠马作为从骑,“致米三十斛酬其直”c《元史》卷二一《成宗纪四》大德七年三月癸丑条(第450页):枢密院臣及监察御史言:“中丞董士选贷朱清、张瑄钞,非义。”帝曰:“台臣称贷不必问也。若言者不已,后当杖之。”又《元史》卷二一《成宗纪四》大德七年五月辛巳(第452页):命江浙行省右丞董士选发所籍朱清、张瑄货财赴京师,其海外未还商舶至,则依例籍没。 《元史》卷一九《成宗纪二》,元贞二年七月壬午(第405页):“增江西、河南省参政一员,以朱清、张瑄为之……”又同卷冬十月壬子(第406页):“赣州贼刘六十攻掠吉州,江西行省左丞董士选讨平之。”又《元史》卷一八一《元明善传》(第4172页):“辟掾行枢密院。时董士选佥院事,待之若宾友,不敢以曹属御之。及士选升江西左丞,又辟为省掾……始,明善在江西时,(朱)〔张〕瑄为其省参政,明善有马,骏而瘠,瑄假为从骑,久益壮,瑄爱之,致米三十斛酬其直。后瑄败,江浙行省籍其家,得金谷之簿,书‘米三十斛送元复初’,不言以酬马直,明善坐免;久之,有为辨白其事者,乃复掾省曹。” 《经世大典·元漕运一》,《永乐大典》卷一五九四九,中华书局,1986年影印版,第6969页。。董士选贷钞与张瑄一事,大约就在江西共事时期。实际上,在董士选与桑哥一党进行斗争时,朱清、张瑄二人也往往在地方上予以呼应,早在桑哥主持尚书省时期,沙不丁在桑哥授意下立行泉府司,置上海、福州两万户府,其职司似乎只是由海道运送市舶货物。行泉府司所统海船不用新附军人,而用不习舟楫的乃颜叛军之余众,排斥朱、张的用意十分明显d《元史》卷一五《世祖纪十二》,至元二六年二月丙寅:“尚书省臣言:‘行泉府司所统海船万五千艘,以新附人驾之,缓急殊不可用。宜招集乃颜及胜纳合儿流散户为军,自泉州至杭州立海站十五,站置船五艘、水军二百,专运番夷贡物及商贩奇货,且防制海道为便。’从之。”第320页。。至元二十八年(1291),桑哥倒台,沙不丁也受到连累,朱张乘机上书控诉自海运隶属沙不丁主持的泉府司以来,“再添二府,运粮百姓艰辛,所有折耗俱责臣等,乞见怜”,要求“宜罢二府,或委他人”e《元史》卷二一《成宗纪四》大德七年三月癸丑条(第450页):枢密院臣及监察御史言:“中丞董士选贷朱清、张瑄钞,非义。”帝曰:“台臣称贷不必问也。若言者不已,后当杖之。”又《元史》卷二一《成宗纪四》大德七年五月辛巳(第452页):命江浙行省右丞董士选发所籍朱清、张瑄货财赴京师,其海外未还商舶至,则依例籍没。 《元史》卷一九《成宗纪二》,元贞二年七月壬午(第405页):“增江西、河南省参政一员,以朱清、张瑄为之……”又同卷冬十月壬子(第406页):“赣州贼刘六十攻掠吉州,江西行省左丞董士选讨平之。”又《元史》卷一八一《元明善传》(第4172页):“辟掾行枢密院。时董士选佥院事,待之若宾友,不敢以曹属御之。及士选升江西左丞,又辟为省掾……始,明善在江西时,(朱)〔张〕瑄为其省参政,明善有马,骏而瘠,瑄假为从骑,久益壮,瑄爱之,致米三十斛酬其直。后瑄败,江浙行省籍其家,得金谷之簿,书‘米三十斛送元复初’,不言以酬马直,明善坐免;久之,有为辨白其事者,乃复掾省曹。” 《经世大典·元漕运一》,《永乐大典》卷一五九四九,中华书局,1986年影印版,第6969页。,获得忽必烈同意。时任庆元路总管府海船万户的张瑄之子张文虎也乘机上奏,获准将泉府司用以运送市舶货物的船只和军队也归自己管辖f《经世大典·站赤四》(《永乐大典》卷一九四一九,第7212页):(至元二八年三月)是月江淮行省言:“蔡泽始陈:‘海道立站,摘拨水军,招募稍碇,差设头目,准备每岁下番使臣,进贡希奇物货,及巡捕盗贼,且省陆路递送之劳。以此奏准设置。’今本省再令知海道人庆元路总管府海船万户张文虎,讲究得‘下番使臣,进贡货物,盖不常有,一岁之间,唯六、七月,可以顺行,余月风信不便。莫若将福建海站船只,拨隶本处管军万户府,其在浙东者,隶于沿海管军上万户提调,听令从长区处,以远就近,屯住兵船,遇有使臣进贡物货,自泉州发舶,上下接递以致杭州,常加整治。头目军器兵仗船舶,于沿海等处,巡逻寇盗,防护商民,暇日守镇陆地,俱无妨碍,所处海站不须设置。’都省准拟。”奏奉设置,令罢去之。。对于董士选与张瑄关系之密切,蛰居江西的吴澄当然心知肚明。董士选在朱清、张瑄二人失势之后,急于与之划清界限,实际是一个政治污点。因此吴澄在为董士选作《神道碑》时,极有可能曲笔讳之,或者董氏子孙在请吴澄作神道
碑时就已经提供了虚假的家传资料。而《元史·董士选传》正是沿袭了《神道碑》的记载,使得这一段文字颇为令人费解。
大德七年的朱清、张瑄之狱,引起元廷政局的极大震荡,受此案牵连,中书平章伯颜、梁德珪、段(真)〔贞〕、阿里浑撒里,右丞八都马辛,左丞月古不花,参政迷而火者、张斯立等八名中书执政被罢免a《元史》卷二一《成宗纪四》,大德七年三月乙未,第449页。《道园类稿》卷三七《董忠宣公家庙碑》,第197页。 黄溍《金华黄先生文集》卷二七《沿海上副万户石抹公神道碑》,《四部丛刊初编》本,第5—9页。,董士选与朱清、张瑄关系匪浅,尽管亲自受命籍朱、张货财赴京,一定程度上可证明自身的清白,但似乎并不能完全洗脱嫌疑。此后不久,董士选就解职家居。对此,《神道碑》云:
又言:“近年以来,星芒垂象,霜杀蚕桑,饥馑洊臻,灾延太庙,上天之谴告至矣。皆执政非人,泽不下究,宜蠲积弊,与天下更始。”出为江浙行省右丞,徙河南,不赴。武宗立,除河南江北行省平章,亦不赴。b《吴文正公集》卷三二《元荣禄大夫平章政事赵国董忠宣公神道碑》,第544页。
尽管《神道碑》没有说明董士选不赴任的原因,不过笔者窃以为,很可能是因朱、张事件引咎告退。而《董忠宣公家庙碑》则云:
是时,吏议尚持重,官多久次不迁,好进者不快于志,兴大狱以徼倖,时上久不豫,事多留中,公复出为江浙右丞矣。俄改河南,不赴。c《元史》卷二一《成宗纪四》,大德七年三月乙未,第449页。《道园类稿》卷三七《董忠宣公家庙碑》,第197页。 黄溍《金华黄先生文集》卷二七《沿海上副万户石抹公神道碑》,《四部丛刊初编》本,第5—9页。
所记虽十分隐晦,但多少透露了董士选的此次宦途挫折与因朱、张事件而导致的政局动荡有关。无论吴澄还是虞集,或言天变,或论人事,皆是虚晃一枪,讳言其事。虞集称董士选“出入进退,信如金石,无可疑者。天下公议,以为正人,有古大臣之节”d《道园类稿》卷三七《董忠宣公家庙碑》,第198页。。就董士选生平政治行为而言,大抵不错,不过就朱、张事件而言,董士选的表现亦难免物议,使得吴澄和虞集都不能不为之文过饰非了。
二、 石抹继祖与学田纠纷
石抹继祖是元末著名儒将石抹宜孙之父,《元史》无传,关于其本人生平,详细记载于《金华黄先生文集》卷二七《沿海上副万户石抹公神道碑》(以下简称《石抹公神道碑》)e《元史》卷二一《成宗纪四》,大德七年三月乙未,第449页。《道园类稿》卷三七《董忠宣公家庙碑》,第197页。 黄溍《金华黄先生文集》卷二七《沿海上副万户石抹公神道碑》,《四部丛刊初编》本,第5—9页。。据载:“公讳明里帖木儿,别名继祖,字伯善,迪烈乣人。卒于至正七年(1347)十月二十七日,享年六十有七。其先出于梁萧氏,随萧后以族入突厥。……考讳良辅,以黑军攻五河,及湖南诸部。宋平,论功行赏,赐金虎符,历蔡州弩军万户、黄州招讨使,寻以沿海副都元帅开阃于四明,会改元帅为万户,遂以为沿海上万户府副万户,累阶昭毅大将军。……大德十一年,昭毅公以老谢事。诏以公嗣其职,初以沿海军分锁台州。”
《元史·石抹宜孙传》提到他“驭军严肃,平宁都寇,有战功;且明达政事,讲究盐策,多合时宜。为学本于经术,而兼通名法、纵横、天文、地理、术数、方技、释老之说,见称荐绅间”。a《元史》卷一八八《石抹宜孙传》,第4309页。《元史》卷一五○《石抹也先传》,第3543页。根据《石抹公神道碑》和《元史》的记载,石抹继祖乃是一位文武双全、声名极佳的镇戍军将领。
可是,根据现存宁波天一阁的《庆元儒学洋山砂岸复业公据》,这位声名极佳的镇戍军将领似乎不再无可挑剔,而是近乎双重人格b关于此碑详细内容,章国庆《元〈庆元儒学洋山砂岸复业公据〉碑考辨》(《东方博物》2008年第3期)已有详细考证,以下仅略述大概。。公据记载了一起典型的投献隐占学田案件,其经过大致是这样的:宋末元初,当地住人陈大猷等趁无人经理洋山赡学砂岸之机,谎称是祖业,将其据为己有,但又怕败露,便投托当时在赵沂王府管干的韩忠以其它名色遮庇。韩忠知此系儒学产业,故于世祖至元十九年(1282)又将其投献给昭毅大将军萧元帅庇护,并虚立价钞400贯,书写卖契,以周瑞作为担保人,付与萧元帅麾下王总领。仁宗皇庆二年(1313)二月,其子沿海翼萧万户为筹集已故父亲归葬费用,将洋山砂岸一半以中统钞100锭高价卖给胡珙和胡载父子。另一半仍由王伯秀使用(据王伯秀告:“故父王文喜买到陈复兴等洋山砂岸一半,起屋在下居住,有连至山地。”其实也是虚买,并每年向萧万户缴纳中统钞5锭。)从这里可以看出,洋山砂岸经过二次投献,被非法侵占时间长达30余年。期间,围绕投献隐占和买卖的大都涉及二代人,而且都应该是明知故犯。特别是萧元帅当时的虚买,其实是由其下属王总领出面,自己并未经手,其子萧万户出卖时也“不于韩忠元卖文契上明白批凿,俱将韩忠上首赤契交付胡珙收管”。最后仅仅被认为是“朦胧作己业,违例卖与胡珙管绍”,予以退业而已,并未受到相应处罚。
公据所谓“沿海翼萧万户”即指石抹继祖,至于“昭毅大将军萧元帅”,乃指其父石抹良辅。据《元史·石抹也先传》,可知石抹氏自也先一代到查剌、库禄满、良辅,是蒙元时期勋功赫奕的名臣宿将,他们曾先后领“黑军”,为元朝的统一大战立下了汗马功劳。此传又云:“(石抹良辅)袭黑军总管,至元十七年(1280)以功累升昭毅大将军、沿海副都元帅。二十一年,改沿海上副万户。大德十一年(1307),告老。子继祖,袭万户。”c《元史》卷一八八《石抹宜孙传》,第4309页。《元史》卷一五○《石抹也先传》,第3543页。《石抹公神道碑》则云:
驭军严肃,而恩意周浃。……遂昌愚民啸聚窃发,单骑直抵其处,责长吏失于抚,字谕富家输粟赈济,而团结保伍以自卫,不旬日诛其首乱。……公尝师事四明前进士史蒙卿……凡先生所指授,闻辄领解,然不徒守空言,而务在明体以达用。自经传子史,下至名法,纵横天文地理、数术方技、异教外书靡所不通,而韬鈐之秘则家庭所夙讲,商榷古今,亹亹忘倦。年踰强仕,即请纳禄,举仲弟祖以自代。乐台州山水之胜,买田筑室而居焉。扁宴沐之所日:“抱膝轩”,雅歌赋诗以自娱,家事付之诸子,一无所问,更自号“太平幸民”。
黄溍向我们展示的萧万户是一位智谋见长又明达世务、修身自好而不乐仕宦的贤者。可就是这位贤者,在公据中却似乎是一位“依恃镇守军势”、强卖学田的嗜利之徒。根据公据,石抹继祖以中统钞100锭高价违例卖与胡珙时,就立即引发了儒学方面先后二次诉讼。那么,他为什么要急于将洋山砂岸脱手呢?从表面上看,萧万户自己陈述得很清楚,“皇庆元年十月十五日内,父亲身故,阙少盘缠,将上项砂岸契书、税由、砧基共三纸,于胡珙处抵当钞两用度”。而黄溍却称:“粥其(意指其父石抹良辅)故庐,为舟车之费,奉枢还葬柳城,余货悉分诸弟。”石抹家族世居柳城(今辽宁朝阳南),其父石抹良辅在世时“每怀乡土之念”,身故之后,作为儿子“还葬柳城”,以遂其愿,自然是情理之中,且台州至辽宁朝阳路途遥远,奉枢归葬舟车之费确实不菲。两种说法的共同之处是筹集归葬费用,所不同的是前者“违例出卖洋山砂岸”,后者则“粥其故庐”。如果黄溍所说为实,还可以有余货悉分诸弟,那么萧万户所说显然是假的。不过黄溍的神道碑铭是根据萧万户门下士潘悼所撰行状写的,今其行状不存,因此其所说的“粥其故庐”,是不知实情所致,还是别有用意,不得而知,但不管怎么样,不能否定萧万户“违例出卖洋山砂岸”的事实。据章国庆考证,石抹继祖违例出卖洋山砂岸正处在大兴儒学之风的历史时期,又是即将开始“延祐经理”的前夕,或许并非偶然。疑惑的是此案审理结果除“退还儒学管绍”外,根据胡珙、陈复兴等各所犯罪行,“行移元委官再行议拟牒呈”,最后是“吞者伏辜,改者退业”,而对石抹继祖本人则不了了之。
由公据可知,石抹继祖其人并非如《石抹公神道碑》以及《元史》所言,是一个明达世务、亲儒好学的完人,亦有嗜利强横的一面。并且根据方志记载,他在移镇婺州之后,还有一件劣迹,发生在泰定二年(1325),当时号称神明的知平阳州事贾达赴浙省,道经金华,“适沿海翼石抹万户纵兵暴横,民甚苦之”,应民之请,亲自登门切责石抹继祖“不思振先御史之烈,而纵兵肆暴”,后者“自是肃然知惧,民赖以安”a《(嘉靖)浙江通志·官师·元》、《雍正浙江通志》卷一五六《名宦》。 参见植松正《元代江南政治社会史》第三章《阿里海牙一族と潭州》、马娟《元代畏兀儿人阿里海牙史事探析》(《元史及民族与边疆研究集刊》第18辑)。,石抹继祖四十五岁,正值壮年。由此可见,所谓石抹继祖“驭军严肃”云云,大约也是溢美是时之辞。
结 语
碑传对于传主生平的过失视而不见或者为之文饰,并非自元代才开始。古代文人应孝子顺孙之请为其先人撰写碑铭时,或碍于私情,或图其润笔,不免要对墓主生平歌功颂德,据称“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愈文集中,就充斥大量的谀墓之文,“公鼎侯碑,志隧表阡,一字之价,辇金如山”,此事在唐代开始就颇招物议b刘禹锡《刘梦得文集·外集》卷一○《祭韩吏部文》,《四部丛刊》本,第8页;洪迈《容斋随笔·续笔》卷六《文字润笔》,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286页。,被视为韩愈生平污点。而《元史》列传不少源于元代文人撰写的碑铭,亦不乏曲笔之处,上述二例,尚十分隐晦。尤为典型者,如元朝灭宋功臣阿里海牙乃因桑哥党羽要束木逼迫自杀身亡,无论是元史本传还是姚燧所撰《湖广行省左丞相神道碑》皆不置一词c《(嘉靖)浙江通志·官师·元》、《雍正浙江通志》卷一五六《名宦》。 参见植松正《元代江南政治社会史》第三章《阿里海牙一族と潭州》、马娟《元代畏兀儿人阿里海牙史事探析》(《元史及民族与边疆研究集刊》第18辑)。。又如灭宋功臣张弘范曾因盗用官钱被罢职,无论是《元史》本传抑或出土的《故镇国上将军江东道宣慰使蒙古汉军都元帅张公墓
志铭》皆讳言其事a参见张洪印《河北易县发现张弘范墓志》,《文物》1986年第2期。。相对碑传而言,似乎本纪的记载可靠得多,尽管从中所见不过是传主生平活动的蛛丝马迹,但与碑传参证,往往有出人意料的发现。
(本文作者为南京大学“中国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元史研究室/
民族与边疆研究中心讲师)
Two Topicsaboutadditionsand Corrections to YUAN SHI——A Co-discussion on Yu-muand Qu-bi in the Inscriptions of Yuan Period
chen Bo, Institute ofasian Studies,nanjing University
Dong Shixuanand Shimo Jizu both had scholarlyand clean-handed reputation in YuanPeriod, but whose historical image wasnot fully consistent w ith the historical truth. By combining inscriptionsand biographies records, thisPaper try to reveal that the inscriptions of YuanPeriod often had theProblem called Yu-muand Qu-bi. Yu-mu means the flattery on epitaph. Qu-bi means deliberate digression in w riting. Because the biographies in YUAN SHI originated from inscriptions records in general, their reliabilityand factuality should be justi fi edand then used w ith caution.
Dong Shixuan; Shimo Jizu; Yumu; Qubi
* 本文系2012年度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基金项目“元明时代的滨海民众与东亚海域交流”(项目批准号:12YJc770007)阶段性成果之一,并得到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元史》会注考证”(项目批准号:10&ZD088)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