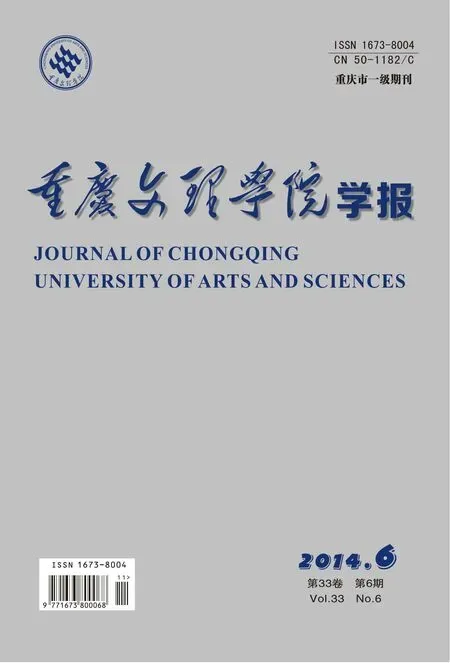文化遗产“我与他”
——法国的“关键”影响
彭兆荣
(厦门大学人类学研究所,福建厦门361005)
博导视角专题
文化遗产“我与他”
——法国的“关键”影响
彭兆荣
(厦门大学人类学研究所,福建厦门361005)
编者按:
相对于多数人文科学而言,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与保护具有更宽泛的研究范围,更明显的跨学科特征,更直接的经济效益,更紧迫的保护需求,所以它需要更多部门和学科的参与、关注与合作。本期约请的四位专家分别从人类学、法学、政府职能部门的角度,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与保护的现状展开了宏大而深入的论述。四位博导各有专攻,他们的论述既针砭时弊,又高屋建瓴,借用彭兆荣先生的说法就是:既讲“人家的”,也讲“我们的”,但共同之处在于都是针对非遗保护问题的思考。无疑,他们在提醒人们注意非遗保护工作的复杂性的同时,也为我们当下的研究提供了更多维的视角和更广阔的方向。
著名的遗产学家劳拉简·史密斯认为,世界上所有的遗产都属于无形文化遗产①;据此,我们也可以认为,世界上所有被称为“遗产”的都属于文化遗产。“非遗”当然在属之列。近代世界遗产之谓与“法国影响”甚大;无论遗产作为“
”抑或作为“事业”,都有法国身影。中国正迎来文化复振,我们自有一整套遗产道法,只是需要探索;探索的前提需要了解别人。对于西式文化遗产的“话语”而言,我们属于“他者”;对于我国的文化遗产体系而言,他们属于“他者”。中国古传的智慧告诉我们:“知己知彼”。是为理。本文既讲“人家的,”也讲“我们的。”
文化遗产;关键词;法国影响;中国道法
一
据我理解,至少依我所见,“文化遗产”“关键词”等之为“热词”虽有“被炒热”的味道,主要原因却还是与法国存有瓜葛。当今全世界“热销”的遗产事业的总推手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总部在巴黎。不过,我说的“法国影响”不是指这个,而是说世界的现代遗产作为“关键词”与法国过从甚密。
作为世界公认的遗产大国,法国是在现代国家建立的进程中遗产国家体系化的一个历史样板,它为世界遗产历史提供了一个遗产历史化、国家化、政治化的表述典范。如果说当代世界的遗产范式导源于欧洲,而欧洲的近代遗产范式导源于法国,这大抵不会有错。当代世界的许多遗产诸如法律法规、登记造册、奖励制度、遗产日等等,其原型皆出自法兰西。
以历史的眼光看,法国标志性的遗产和遗址大都与法国封建时代的国王、宗教、贵族、家族等有着密切的关联;法国王室收藏遗产文物成风:如早在弗朗索瓦一世时期(1515-1547),弗朗索瓦就开始从意大利购买大量艺术品,这其中包括著名的油画《蒙娜丽莎》在内。而截至路易十四执政期(1643-1715年),法国王室已经收集了约150座雕刻、700张素描、2000幅油画,以及其他大量美术作品。这样的行为一直延续到路易十五和路易十六时期,他们继续从意大利、佛兰德斯和西班牙大量购入各类艺术作品;这些都不足使法国获得世界性声望,真正取得世界性影响的是法国大革命,保护文化遗产先驱们的伟业,以及由此带给世界的世界性理念和保护措施。
1789年,法国爆发了世界近代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革命,推翻了封建统治,1792年,在经历几年政治斗争的反复后法兰西共和国成立。对各类既往的遗产、遗物、遗址的处理方式和态度是法国所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以下的事件值得特别的关注:1790年,法国第一个“历史建筑委员会”成立;1830年,创设历史建筑总督察一职,并配备了纪录、保护和修缮历史建筑的资金;1837年,创建了由建筑师、考古学家和政府官员组成的历史建筑委员会;1840年,历史建筑委员会编撰了欧洲最早的一份历史建筑登录名单“请求资助的历史建筑名录”。1841年2月19日颁布了一道敕令,规定了委员会的使命和责任:
●审核并批复所有由地方或科学团体要求资助的申请;
●将所有值得登记在册的历史建筑列入历史建筑清单,列入清单的要得到国家的资助必须满足三点:旨在通过该建筑激发地方自豪感;地方支持;地方投钱;
●评估并给任何对已登记历史建筑进行整改的活动以意见;
●决定是否收购濒危历史建筑。
1887年颁布的《历史建筑保护法》是法国首部文化遗产保护法案,这部法律明确了政府干预的范围;1913年通过了有关的重要法令——《历史建筑法》,它包括了许多现行法令的要点,并沿用至今。
法国大革命对世界性“遗产事业”在历史转型过程中起到了示范作用。具体地说,传统意义上的遗产在这些重要的历史事件中,从遗产的私有化逐渐地成为文化遗产的国家化(国有化)。文化遗产在国家层面的保护地位也得以确立,即文化遗产必须从私人领域“置换”出来,变成国家公民所有、成为国家相关机构进行保护的对象。这一步的跨越并不容易,大革命经历了惊心动魄的政治斗争和思想变革才最终形成。这里涉及几个重要事件和价值转型:首先,国家通过确认和确立一些重要的标志性遗产、遗物和遗址等,帮助建立新的国家形象,换言之,文化遗产成为新国家(民族国家)认同的重要资源和依据。其次,对重要的遗产、遗物和遗址的保护、整理、修复等以建立对历史的应有态度,并通过这些遗产的分类、档案处理,建立完整的历史性和专业化谱系。再次,通过国家遗产的理念和实践,建立符合新社会的公民价值。值得特别强调的是,在这个历史进程和历史事件中,法国的文化精英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代表人物是法国著名作家梅里美和雨果。
通常人们把法国视为保护文化遗产的先驱,而梅里美和雨果则被法国人视为遗产保护的先驱,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因是他们在保护本国的遗产、遗址、历史文物等方面曾发挥重要作用。他们的具体任务是为重要的遗产、遗址建立历史档案,建筑艺术,其见证过重要的事件,并集中和集结一批考古学家、艺术家和历史学家加入到具体的保护行列,其中特别重要的是编制清单。这项任务的繁重是显而易见的,梅里美估算为此预计需要编写900卷说明性的文字和250年左右的时间。事实上,在1840年,他们完成登记在册的历史建筑是1076件,然而到1849年,这一数据已接近4000件。19世纪的批评家圣·佩韦曾经这样评价:这些法国的知识精英们的工作就像是朝圣,他们遍查各地,冲向任何有尖塔、教堂塔楼和哥特式拱门的小镇,在村镇最古老的区域搜访,探查最狭窄的小巷,在任何一片有刻文和装饰的石刻面前久久停留。然而,梅里美等人的工作也受到一些地方官和教会的阻碍,他们宣称该建筑属于他们自己或地方。其中之一在于法国的历史建筑委员会的国家机构受到了地方的质疑,他们的工作也受到阻挠。
一个有名的事件发生在1832年,地方政府为加宽街道想要拆除Saint-Jean修道院,这些公共知识分子经过两年艰苦的协商,终于在1834年说服了政府放弃拆除计划,使得Saint-Jean修道院免于拆除。梅里美和他的同道们发现很多历史遗产处于濒危状态,盗抢珍贵文物,私自进行开发行动,甚至不少机构也有破坏遗产的行为。另外还有一种隐形的破坏,甚至比以上那些个体或组织性的破坏更严重,比如破坏性的修复。梅里美认为,对于历史留下的废墟,大量的修复工作和工程不能真实地保护原有的面貌和风貌,使得修复工作留下了历史的遗憾。梅里美非常担心这种重建历史所带来的危害。1844年,梅里美委托拉萨斯与杜克为修缮巴黎圣母院(1793年大革命中,巴黎市民将门洞上方“国王廊”里的二十八尊以色列和犹太国历代国王的雕塑误认为是法国国王的形象,拆下来当做旧材料卖了)的负责人。杜克虽然首次提出“整体修复”的概念,主张一座建筑及其局部的修复应保持原有的风格,修复之前应先查明每个部分的确切年代和特点,要有依据。但却用个人的判断取代了原物的真实,用“创作”代替了修复,使得巴黎圣母院“焕然一新”,被抹去了700年来的历史痕迹。现在人们普遍认为杜克的修缮毁掉了巴黎圣母院。
对于各种的破坏行为和“修复性破坏”,维克多·雨果在法国1832年第一季度的《两个世界的杂志》撰文大声疾呼(删节):
我在这里想说,并想大声地说的,就是这种对老法国的摧毁,在被我们于王朝复辟时期多次揭发以后,仍然是在进行着,而且日愈疯狂和野蛮,已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目前在法国,没有一个城市,没有一个省县,没有一个区镇,不在摧毁某一座文物建筑,或者正在预谋,或者刚刚动手,或者已经完成,这有时是被中央政府批准的,有时是被地方政府批准且被中央政府支持的,也有时是个人的行为,但地方政府知情并且予以放行。
……我们想唤醒每一个曾为了艺术或考古在法国境内出游过的人的意识,无论他去过什么地方:现在每一天都有法国的一点历史被抹去,随着曾记载过它的石头而去。每一天,都有几个字母从那本表示我们珍贵传统的书籍中隐没。在不久的将来,当所有的废墟聚成一个大的废墟的时候,我们就只有与那位特洛伊人一道喊出:“这里曾有过伟大的光荣。”……
我们的法律包罗万象、无所不管,甚至连为如何把某部委的纸箱抬过格耐尔街都能制定出一条法律。然而,为了文物建筑,为了艺术,为了法国还是法国,为了记忆,为了人类智慧的伟大结晶,为了先人集体创作的作品,为了历史,为了制止摧毁永不可再生的,为了给未来留下一个民族最神圣的东西,为了过去,为了这一切来制定一条可称之为正确的、好的、健康的、有用的、必需的并且紧急的法律,我们却没有时间了,我们却不去制定了!太可笑!太可笑!太可笑了!②
当国家通过立法精神和立法实践对遗产进行有效保护,当知识精英通过高度的历史责任感进行卓越工作时,一个同样重要的历史任务摆在了人们的面前,这就是如何把对遗产保护的立法精神和知识技能化作普通民众的自觉意识和行动,如何把这种对遗产的认识和保护化为“公民伦理”,并让每位民众自觉地行动起来,这无疑是一个比专家保护更为艰巨的任务。为此,法国政府通过设立“遗产日”,政府性的财政补贴,免费开放博物馆、遗产地、遗址,将博物馆、文物、遗产等作为教育的场所,通过节假日、各类庆典活动等普及性行为传播和提高民众遗产保护意识……以巴黎为例,从某种意义上说,巴黎就是法国人民、巴黎民众数百年来创造并保护的遗产;为普及遗产保护和文化教育,巴黎乃至整个法国的国有古迹对18岁以下的儿童不收门票,卢浮宫等33个国立博物馆、100处文化遗产和古迹,在每个月的第一个星期日免费向公众开放。每年9月第三个周末的“文化遗产日”,公立博物馆一律免费,私立博物馆票价减半。通过这一系列的举措和行为,使遗产成了现代人生活的重要部分,包括现场教育、审美活动、艺术欣赏、知识传播、旅游观光、怀旧情感等。
二
第二个与法国有关是本人所理解的“关键词”。“关键词”作为当代一种概念工具,与法国学者福科存在关系,这大概不会有太多人反对。福科以“词与物”为点,以“知识考古”为线,成为当代思想界、学术界贯彻反思原则的一个重要依据③。当人们对既往陈规在日常习惯中未加置疑,甚至误以为天经地义,并遵循贯彻之时,以“词与物”关系来思考,你会发现,那些被认为理所当然事实的未必理所当然!比如“中国屹立在世界的东方”一说已为国人所习以为常,引以为傲,可是如果以“词与物”的知识反思之,“中国(世界中心)”何时去到了“东方”,而且还是“远东”?我们终于明白:中国的“天下体系”已于近代沦为世界上另一个“中心体系”——欧洲中心——以“罗马”为中心的“他者构造”;而这已经是中学地理课本中的“常识”。
值得一说的是,福科《词与物》的写作动机及缘起还与中国古代的博物志有关;对此,福科这样说:
博尔赫斯(Borges)作品的一段落,是本书的诞生地。……这个段落引用了“中国某部百科全书”,这部百科全书写道:“动物可以划分为……”,在这个令人惊奇的分类中我们突然间理解的东西,通过寓言向我们表明为另一种思想具有异乎寻常的魅力的东西,就是我们自己的思想限度,即我们完全不能那样思考。……因为它阻碍了命名这和那,是因为粉碎或混淆了共同的名词,是因为它们事先摧毁了“句法”,不仅有我们用构建句子的句法,而且还有促使词(les mots)与物(les choses)“结成一体”,……即丧失了场所和名称“共有”的东西。……一个“要素体系”,对确立起最简单的秩序也是不可或缺的[1]。
福科在自己的著述中通过知识考古学以确立其“话语反思”,通过对“中国某部百科全书”的分类与他们自己习惯性的巨大差异而拍案惊奇,他发现“词”与“物”之间不仅缺失了共有性,“句法”也不相同,这种差异是思维性的。于是,他试图通过词与物的“人文科学考古学”方式,对其间“要素体系”所建立的最简单的秩序进行探索。这便是“词与物”的关键词的关键意义。
回到当下的关键词“遗产”,它同样足以提供人们一幅巨大的反思图景。遗产学家拜辛通过考察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法国工业遗产的发展线索,对“遗产”这个词汇概念由私而公的变化进行梳理。他认为,要考察遗产概念的转变,可以从词源学的角度入手,对于三个表示遗产概念的词,heritage、patrimony和succession进行细致的分辨。根据对法国私法(droit privé)的考察,他发现:
同样表示遗产或继承权的三个词汇,分别有着明确的内涵和外延区分。甚至直到最近,包括法国、英国、美国等在内的很多国家法律中也都还没有出现过“国家遗产”(或民族遗产,national heritage)的官方说法,heritage这个词条在相关的关于保护国家遗址及其他历史遗迹的法案中都没有出现。直到1975年,法国的公法(droit public)中才借用私法中的heritage这一词条,用“特定遗产”来指称原先的国家遗址等公有遗产概念。公法中的heritage一词,将原先私法中的heritage、patrimony、succession三个词条进行了模糊处理,而正是公法中的heritage的模糊性,使得遗产概念在由私到公的转变中产生了意义上的多重特征④。
Heritage一词强调一种过去的概念,在谱系上表达的是父子关系,其本义侧重于“从父辈继承而来”的遗物;而patrimony一词则指向的是儿子及将来,这里的遗产概念不是静止的,而是表达遗产从父辈向子辈、及将来继承人的传递。因此,patrimony一词更加具有实践意义,其持有人不仅已经获得了所有权,继承到了父辈的遗产,并且持有人自身也可能已经成为父辈,对于遗产的将来有很高的处决权。将这个遗产概念扩展到国家民族遗产概念,就为遗产从其原义中分离出文化遗产的意义提供了逻辑前提。当“公义遗产”将原先的三重意义统合之后,遗产概念开始更多的指示“现在”和“发明”的意义;但由于这一概念杂糅了太多的语境化意义和意思而成为各种附加值的依附体,成为被异化的“他者”客体。
三
回到我们现实的遗产实景,中国泱泱大国,文明悠悠久远,文化煌煌光耀,遗产赫赫大宗。我国的文化遗产与西式文化遗产迥异,而且特色鲜明,总体上看,其特色之一表现为“文化-文画-文划”的一体化形制;纵以“词与物”之知识考古也精妙绝伦。以文字书写表述为例,我国的文字起于书画,与西式字母式文字思维相距千里。唐兰在《中国文字学》中对此有过一段论述:
文字起于图画,愈古的文字,就愈像图画。图画本没有一定的形式,所以上古的文字,在形式上是最自由的。用绘画来表达文字,可以画出很复杂的图画,也可以很简单地用朱或墨涂出一个囫囵的仿佛形似的物体,在辛店期彩绘的陶器里,我们可以略微看见一些迹象。商代的铜器,利用款识来表现这种文字,有些凹下去的,有些凸起来的,也有凹凸相间的。凹的现在通称为阴文,凸的是阳文。这些款识,是先刻好了,印在范上,然后把铜铅之类熔铸成的,阴文在范上是浮雕,在范母上却是深刻,阳文在范上是深刻,在范母还是浮雕。深刻当然比浮雕容易得多,而且铸成铜器后,阳文远不如阴文的清晰美观,所以除了少数的铭字,偶然用阳文,大部分都是阴文。可见在那时雕刻的技术,已经很有进步了[2]。
而在“文化-文画-文划”形制中,刻画(划)之器具也需要非常特别,“笔”也因此成为重要的有形和无形遗产范畴。对于笔的考述,宋人苏易简之《文房四谱》之“笔谱”理之巨细:
上古结绳而理,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盖依类象形,始谓之文,形声相益,故谓之字。孔子曰:“谁能出不由户?”扬雄曰:“孰有书不由笔?”苟非书,则天地之心,形声之发,又何由而出哉?是故知笔有大功于世也。《释名》曰:“笔,述也,谓述事而言之。”又成公绥曰:“笔者,毕也,谓能毕具万物之形,而序自然之情也。”又《墨薮》云:“笔者,意也。意到即笔到焉。又吴谓之不律,燕谓之弗,秦谓之笔也。”又许慎《说文》云:“楚谓之聿,聿字从帇、一、又帇音支涉反,帇者,手之捷巧也,故从又,从巾。秦谓之笔,从聿,从竹。”郭璞云:“蜀人谓笔为不律”。虽曰蒙恬制笔,而周公作《尔雅》授成王,而已云简谓之札,不律谓之笔,或谓之点。”又《尚书中候》云:“元龟负图出,周公援笔以时文写之。”《曲礼》云:“史载笔。”《诗》云:“静女其娈,贻我彤管。”又夫子绝笔于获麟。《庄子》云:“舐笔和墨。”是知古笔其来久矣[3]。
“书-画-符-形-意”表现、表达和表述与“文化-文画-文划”相互映照;所以,古代文字刻于甲骨、金石及印于陶泥者,皆可为“书”,又不能独称为“书”;因为需要不同文化理念,不同文化元素和不同文化行为的相互支持。印即为中国一门学问、技术,包括理念、价值、历史、风格、行为、设计、书法、图像、材料、器具等,甚至与国家政治关系弥深。清人朱象贤的《印典》对此有详细梳理:
古印良可重矣,可以考前朝之官制,窥古字之精微,岂如珍厅玩好而涉丧之讥哉!……《春秋运斗枢》:“黄帝时,黄龙负图,中有玺章,文曰‘天王符玺’。”《周礼·掌节》:“货贿用玺节。”注:“玺节,如今之印章。”《录异记》:“岁星之精,坠于荆山,化而为玉;侧而视之色碧,正而视之色白。卞和得之,献楚王。后,入赵,献秦始皇。一统,琢为‘受命玺’,李斯小篆其文,历世传之,为‘传国玺’。”《后汉·祭祀志》:“自五帝,始有书契。至三王,俗化雕文,诈伪渐兴,始有印玺,以检奸萌。”今之沿袭,始自古人。不师先世成规,焉证后人之失?然而,时代推迁,变更不一,是非祥考。鲜知取法也,兹集历代,分别尊卑、质式,汇辑《制度》二卷,少备考据。马端临云:“秦以印称玺,不通臣下,用制乘舆六玺,曰‘皇帝行玺’,‘皇帝之玺’、‘皇帝信玺’、‘天子行玺’、‘天子之玺’、‘天子久玺’。又,始皇得蓝田白玉为玺,蟠虎钮,文曰‘受天之命,皇帝寿昌’。”《汉旧仪》:“秦以前民,皆以金、银、铜、犀、象为方寸玺,各服所好。汉(一作秦)以来,天子独称‘玺’,又以玉,群臣莫敢用也”[4]3-15。
将玺印之历史轮廓描绘,可知其与国家、皇帝、天子“互证之凭”,亦为中国官制的重要佐证和器物。可谓大者也!至于私人信物、民间收藏也详实可靠,其曰:“古人私印,质有金、银、铜、玉,纽有螭、龟、坛、鼻、狮、虎、兔、兽,与官印无异。又有子母印、两面印、六面印、乃官印中所无。子母者,大印之中藏以小印,多则三、四,少则一、二;两面者,其厚一、二分而无纽,上下刻文,中空一窍,以绾组也;六面印者,上下四周皆刻文字,其制正方,下及傍侧为五印,上作方纽,仿佛以鼻,成一小印也。”[4]144-145
这些对玺印的“知识考古”,说明其非小可物什,迄“国”至“家”,从“官”到“私”悉详备至。如此,由“书-画-符-形-意”表现、表达和表述于“文化-文画-文划”,具体于“文画-刻划-凹凸-阴阳-范形-拓墨”,造化成就了一个中国式的表述范式和遗产认知体验。这种特殊的文化遗产形体惟中华民族所独有!
再如,当今的“文化遗产”离不开“登记名录”之制,世界遗产也以“名录”昭告天下。这种操作性登记名录传统脱不了与法国文化遗产模式的历史干系。如果我们问:中国有自己的“登记造册”制度和传统吗?窃以为必定有、必须有、必然有!只是属于自己的传统。于省吾先生通过对甲骨文“工”做“词与物”考据时,发现并总结了“工”的几种用法,其曰:
1、工与贡古通用,但甲骨文有工无贡,贡乃后起之分别文,易繁辞之“六爻之义易以贡,”释文:“贡、京、陆、虞作工,荀作功。”管子君臣之下“而贤人列士尽功于上矣”,俞樾管子平议谓:“功当作贡。”《广雅·释言》:“贡,献也。”贡训献古籍常见。甲骨文释“工其”(后上一0·九),“工其雚”(前四·四三·四),“工其幼”(前三·二八·五)……以上各条工字皆应读为贡,“”即古典字,指简册言之。其言贡典,是就祭祀时献其典册,以致其祝告之词也。商器天工册父己毁,工册二字合文作册,工册即贡册,古文偏旁往往单复无别,此器乃祭父己乙而贡献其册告。……2、甲骨文亦有祭祀用牲时以工为贡者。3、甲骨文有以工为贡纳者。4、工亦读如字,指官吏言之。《书·尧典》之“允厘百工”,伪孔传谓:“工,官也。”[5]
此外,“工(贡)”的意义与城邑以及授邑制度有关,城邑指的是以单一血缘组织——族——为基本单位的地区性居民群,在商代,它是最主要和最基本的统治机构。其基本特点是商王授邑主以封号,并赐以土地,邑主除表示臣服外,还要提供各种服役和谷物以作报答。
在释“方”“土”时,于先生认为其为祭祀,甲骨文有关方、土之祭习见,“方”的基本意思当然是“一点四方”政治地理学的中国式大一统的格局。有资料显示,甲骨文卜辞记载的“多方”之中,属于卜辞第一期的最多,第一期的方国名33个,第2期的2个,第三期有13个,第四期23个。其中方486次。其次是土方,92次。此外还有诸如羌方、周方、召方等。这些方国以交易、进贡土等方式表示臣服⑤。
将“工”与“土(社)”“方”并置作考释,作为“国之大事”的祭祀,贡献、牺牲为祭祀的构造之重要程序和元素,即使在后来的祭祀大典中,仍然保留诸如“献殿”(贮存、造册、登记牺牲贡献专门的殿堂)之制。在商代,家养动物是商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物质来源。祭祀中所用的牛的数量相当惊人,据胡厚宣统计,在一次祭祀中用1000牛,500牛、400牛各一次,300牛的三次,100牛的九次。说明当时有一整套的登记造册制度,否则后人是无法了解的。从今天可供参考的资料看,刻制甲骨当为史前最具代表性的档案记录。“而事实上,商代的占卜是国王的重要工作,同时有许多人参加配合,其基本程序是商王本人或以其名义问卜,贞人(商王的代言人问卜),卜人执行占卜过程,占人专门解释裂纹的含义,史官专门记录占卜过程并将其刻在甲和骨上。”⑥依据上列诸案,窃以为这是我国最早的一种登记造册制度。
而“造册制度”又与“史”有涉。司马迁是西汉武帝(公元前140-前87年)时代的官方历史档案管理者;他的《史记》是中国第一部官修史书。在我国古代,祭祀不仅是社会控制的重要机制,也是与天沟通的手段。与天帝、神灵沟通需要贡献,贡献的种类、品名都需要登记造册,这便是古代的“典册制”。“典”甲骨文(册,代表权威典籍),(双手,表示捧着),表示双手奉持典册。造字本义为主持事务的官吏双手恭敬地捧着古权威圣典。《说文解字》:“典,五帝之书也。从册在丌上,尊阁之也。庄都说,典,大册也。”由此可知,典的本义就是祭祀仪礼中登记贡献的大册。后引申为典范,标准。它可指祭典行为,《书·尧典》有:“命汝典乐”;也指仪典,《周礼·大司寇》:“掌建邦之三典,轻典、中典、重典也”;又可指经典、典册,《尔雅·释言》:“典,经也。”册,甲骨文字形、像是用皮绳串连起来的大量竹片或木片。造字本义为竹片或木片串成的典册。古代用竹片书写的叫“简”,用木片书写的叫“札”或“牍”;编缀在一起叫“册”。《说文》:“册,符命也。诸侯进受于王者。象其札,一长一短,中有二编之形。古文又从竹。”《书·金滕》:“史乃册祝。”
以“文化-文画-文划”之形制,以“龟-骨-金-石”之材质,以“工(贡)-土(方)-史(册)”之词物,牵引出来的知识谱系也洋洋大观。看起来,关键词确实很关键,它不独关涉“天人合一”的思维形态,关涉“天文-地文-人文”的认知方式,关涉“一点四方”的家国地方,关涉宇宙经纬的时空制度,关涉中国式“书画-书法-书写”文化。总之,中国的文化遗产有自己的道法。
注释:
①参见劳拉简·史密斯(Laurajane Smith)最近在我国西南民族大学的一次讲座的题目。
②华新民2001年9月译自巴黎历史图书馆。参见24小时在线博客网站“老虎庙:一个人出版的杂志”:2006年8月3日日志:“雨果:向拆房者宣战!”http:// 24hour.blogbus.com/logs/2966897.html。另,感谢李春霞博士提供的相关资料。
③参见福科《词与物——人文科学考古学》,莫伟民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2年版;福科《知识考古学》,谢强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版。
④Claude-Marie Bazin Industrial Heritage in the Tourism Process in France.Translated by Kunang Helmi.In Marie-Fran?oise Lanfant,John B.Allcock&Edward M.Bruner(eds.)International Tourism:Identity and Change.London,Thousand Oaks,California:SAGE Publications,1995.pp.120-124.
⑤参见周鸿翔《殷代刻字刀的推测》,转引自张光直《商文明》,北京:三联书店,2013年版,第36页。
⑥参见张光直《商文明》,北京:三联书店,2013年版,第35页。
[1]福科.词与物——人文科学考古学[M].莫伟民,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2.
[2]唐兰.中国文字学[M].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93-94.
[3][宋]苏易简.文房四谱[M].北京:中华书局,2011:7-8.
[4][清]朱象贤.印典[M].北京:中华书局,2011.
[5]于省吾.甲骨文字释林[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232-242.
责任编辑:黄贤忠
The“Self”and the“Other”of Cultural Heritage——The Crucial Influence of France
PENG Zhaorong
(Institution of Anthropology,Xiamen University,Xiamen Fujian 361005,China)
Laurajane Smith,a well-known expert of cultural heritage,believes that all the heritage in the world belong to th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So we also believe that all named heritage in the world is cultural heritage,including the intangible heritage.Idea of modern world heritage is influenced by the France,whether the heritage as the key word or the career.With culture revival in China,we have a full set of heritage law,and what we need is the exploration.The premise of exploration is to understand the“other”.As for the utterance of western cultural heritage,we are the others;in terms of the China’s cultural heritage system,the west is the“other”.The old wisdom of China tells us that knowing self and the other party is the truth.The paper discusses the others and ourselves as well.
cultural heritage;key word;influence of France;law of doctrine in China
C915
A
1673-8004(2014)06-0001-07
2014-06-02
彭兆荣(1956-),男,福建厦门人,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厦门大学人类学研究所所长,旅游人类学研究中心主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体系探索研究”首席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