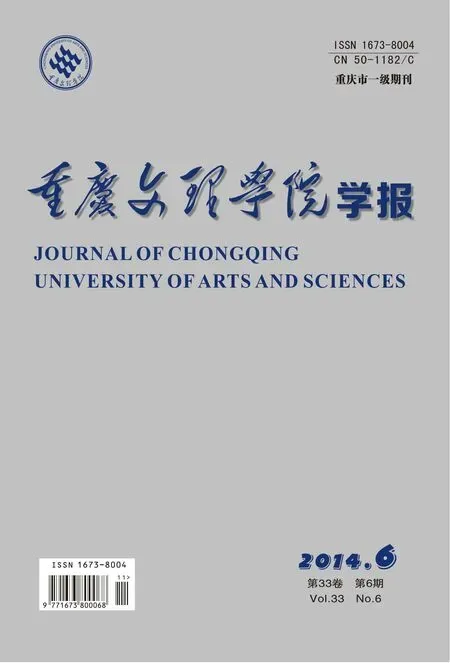人类学可以成为非遗保护工作的理论工具
徐杰舜
(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上海闵行200240)
人类学可以成为非遗保护工作的理论工具
徐杰舜
(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上海闵行200240)
对于中国学术界来说,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是天上掉下来的一个馅饼。而中国民俗学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从“天上”掉下来之时却毫无准备。反观人类学和民俗学的历史渊源,我们可以发现人类学的普同性、整体性、整合性和相对性等理论特点和理论框架都对非遗保护工作具有显著的指导作用。
非遗保护工作;人类学;理论工具;民俗学
一、面对天降的馅饼我们准备好了吗
我过去一直说,对于中国学术界而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是天上掉下来的一个馅饼,一个大馅饼。
要讨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有必要先了解什么是非物质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核心关键词分别是世代相承、传统文化和表现形式。这些与各族人民的生活密切相关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主要包括民间习俗、艺术表演、传统知识技能和与之相关的器具、手工制品等,以及与之有关的文化空间。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民族众多的文明古国,各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进程和日常生活劳作中创造了无数绚烂多彩的文化遗产,它们是中华民族智慧、历史、文明的结晶,它们是联系民族情感和维系国家文化认同感的基础。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和城市化、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推进,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生态也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不过这些冲击中,有些却意外地带来了新的机遇和警醒。
这个带来机遇和警醒的冲击,首先来自韩国。2005年11月24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第三批无形遗产名单正式发布。当韩国申报的“江陵端午祭”被正式确定为“人类传说及无形遗产著作”消息传到中国时,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围绕着端午节申遗之争,从2005年11月底开始,在中国学术界和民间都产生了极大的反响。无论如何,起源于我国,并且一直延续的一个传统节日,却被另一个国家申遗成功,这是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
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正是韩国申遗成功的冲击,引起了中国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强烈警醒和反思,中国人才开始对“人类传说及无形遗产著作”宣布制度有所了解。这一制度始于2001年,它是人类在认识到无形遗产对自身历史的重要价值和保存的必要性之后的产物。根据制度的具体规定,每个国家每两年才能申报一项无形遗产。
(一)非物质遗产在中国破坏大于保护
在过去一个多世纪以来,全球化和现代化进程对全世界范围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造成了严重的危害。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正在不断被损害,不断从这个世界消失。而这一令人忧虑的现象在近些年经济快速转型和增长的发展中国家表现得尤为突出。
总体来说,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我国对非物质遗产的破坏大于保护。许多专家认为:在中国淡漠的观念仍然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最致命的“破坏者”。他们认为,中华传统文化可谓是浩如烟海,只有极少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幸运地获得了重视和保护,而更多、更大范围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正面临被历史尘封、濒临灭绝命运。一方面我们的保护是如此的微弱,而另一方面,那些最后残存的一点星火也正由于人们的忽视和拆除而逐渐湮灭。国家非遗保护中心研究者田青叹息着说,“所谓不破不立。他们以为,一切遗留的都是落后的,一切新建的都是进步的,恨不得把一切都翻新重建一遍,以此证明自己的‘发展’”。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我们的地方政府追求的还是物质的日新月异,更关心的是城镇化和GDP。
一个最有说服力的例子来自地方戏曲。据统计,上世纪50年代,中国尚有367个传统戏曲剧种存世,然而,仅仅几十年的光景,它们已经消亡了100多种。因为没有留下任何音像记录,一些极具特色的小剧种已经由鲜活的艺术表演变成了枯燥的文献史料。即使有些幸存者还仍然勉强留存,但它们都面对着共同的困境,诸如:资金短缺、后继无人、表演技巧失传等等。
更大的危险来自于广大农村地区的普通民众,他们心中普遍厌弃农耕生活和农村的生产方式,他们中的多数人都渴望进城务工,从而过上物资充裕、设施先进的城市生活。尤其是在非物质文化遗产存留最丰富的地区,当地人渴望“过上城里人一样的生活”的美好愿望,正将无数个美丽的村寨、古老的里巷渐次湮灭。当然不仅在物资层面,在精神信仰的层面亦是如此,长期以来,反对封建迷信的大刀早已把中国民间极为丰富多彩的宗教信仰文化摧毁了。如对祖宗的崇敬信仰的打击,使中国人的尊老传统几近丧失。
(二)激活了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热情
韩国的申遗成功,唤醒了更多人对非物质遗产的关注,这是中国非物质遗产即将走上好运的开始。2006年成了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年。这年的5月,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正式发布,民俗文化类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其他遗产项目名列其中。就在这年,全国举办了有史以来第一个,也是最隆重的庆祝纪念活动。不管是在城市、在乡村,还是在民间,在政府,人们似乎都在关心着民俗文化遗产的保护,民俗文化遗产的普查和保护成为国人的热议话题,这实在是一个多年来难得一见的令人欣慰的情景。
与此同时,长期生活在大都市里的高校科研机构和研究者们也闻风而动,他们积极地筹备、谋划成立了各种的专业研究机构,来展开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工作。尤其是有些研究民俗的学者,他们热情洋溢地宣布准备进行一项宏大的科研计划,即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学”建立为一个独立的学科。
总之,韩国端午节的申遗成功,标志着世界各民族对非物质遗产开始重视了,也激活了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这就是天上掉下来的一个大馅饼。没错,好运的突然降临,为一直处于低迷沉寂状态的中国民俗学注入了巨大的热能。但现在的问题是,中国民俗学界准备好了吗?
实话实说,中国民俗学界并没有准备好。
为什么这么说?这不能不从中国民俗学界长期存在的困境说起。早在2001年初,苑利、顾军就撰文谈到了中国民俗学存在的危机,他们认为虽然自从中国民俗学复兴以来,中国民俗学取得的成就是显著的,但我们不得不清醒地意识到民俗学的学术危机依然还在①。叶涛也曾在《新时期中国民俗学论纲》中,对中国民俗学的困境和危机作了较全面的分析。他认为这种危机主要体现在这么四个方面:其一,民俗学的核心概念内涵的扩展和外延的无限膨胀;其二,民俗学从业人员的学术素养不高;其三,田野作业的科学性不足导致学术水平平庸;其四,专职研究人员太少,研究机构不健全。他认为以上四者都是严重影响学科发展、制约学术水平的重要因素,社会上的民俗研究活动虽然不少,但是这却是一种看似热闹的虚假繁荣,背后掩盖着许多潜在问题②。叶涛对中国民俗学危机的分析,正好为中国民俗学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从“天上”掉下来之时而毫无准备作了注脚③。
二、人类学可以成为非遗保护工作的理论工具
从2006年中国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以来,人们逐渐认识到人类学,尤其是文化人类学对开展非遗保护工作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为什么?
(一)人类学的学科定义与非遗保护工作有天然的血缘关系
人类学是对人类进行全面研究的学科群,它今天的研究范围正在日益扩大,但基本还是可以从生物和文化两个角度来划分。关于人类学一词,最早的文献出处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它被用于描述那些道德品质和行为举止高尚的人。1501年,德国学者亨德用其来命名他研究人体解剖结构和生理的一本新著。从此开始一直到19世纪以前,人类学这个词主要是指称人体解剖学和生理学,其意义和内涵与今天人们通常所说的体质人类学大致相近。十九世纪以后,考古学化石遗骨的发现引发了欧洲许多学者浓厚的兴趣,值得注意的是那些与遗骨相伴随的人工制品,因为它们在当时仍然在原始民族中被作为器物使用。在早期,把这些考古发现带入欧洲的人主要是海员、探险家、传教士,尔后人类学家也加入这一行列,亲自远赴异域他乡搜集发掘这方面的材料。学者们开始注意有关的报道,并把现存的原始种族的体质类型和有关原始社会文化的报道联系起来,从此人类学中断了只关注人类解剖学和生理学的传统,转而在更大的范围对人类进行更综合的研究,它包括体质、文化、考古和语言诸方面。
显然,人们对人类学的学科内容和命名有着不同的理解。欧洲人习惯把狭义的人类学定义对人类体质的研究,民族学则被用作指称更宽泛的人类文化研究。不管怎样,从十九世纪中期起,发掘人类社会“原生形态”开始成为人类学这门学科的主要任务。此后随着美国人类学历史文化学派兴起,从文化的角度研究人类行为成为人类学发展的主流方向,人们关注的问题是人类文化的起源、发展和变迁、世界范围内民族地区间的文化差异,并尝试探求人类文化的演变规律和性质。对人类的宗教巫术、原始艺术、婚姻生活、亲属关系、风俗习惯,以及各种物质生产成就等方面的研究是文化人类学最为卓越的成就。由此可见,我们今天所谓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从那时起就已经成为文化人类学研究领域的一部分,这种悠久而亲密的血缘关系,决定了人类学日后必然会成为非遗保护的理论工具。
(二)民俗学的人类学取向决定了人类学可以成为非遗保护工作的理论指导
一名人类学家在他详实的研究报告中提出:我们可以把人类学当成一个出发点去思考与之相邻的民俗学、社会学等其他四五个学科,我们会发现虽然彼此各有自己关注的研究取向和点、面,但是我们仍然可以找到田野调查和研究框架上的,彼此可以相互借鉴、有机连接的契合点和方法。他们在研究方法上存在着可以彼此协作的交接点。具体举例来说,他认为民俗学很早就有人类学的取向,这从那些早期使用功能主义的论文,以及今日使用展演论、情境论等诠释理论的民俗研究论文中都能观察到痕迹。在功能主义的早期研究框架之后,俄国普洛普的民间故事形态学首先开启以民间故事分析形式、体系及其形态学成因,确立话语的个体意义。普洛普的形态学实际是关于形式与模式的结构功能构成,及其传播变体之生成的学说,这是从传统记录民俗研究细部深掘的值得称道的成果,它使得对传统的民俗学史诗的研究有了新的理论框架④。
此外也有更多研究报告表明,事实上人类学与民俗学是两个联系紧密的学科,它们在研究方法和研究架构等诸多方面都是相通的。它们的这些内在联系,决定了人类学可以为非遗保护工作提供必要的理论指导。
(三)人类学的理论特点对非遗保护工作有积极的学术价值
从学科特征来说,普同性、整体性、整合性和相对性是人类学显著的四个理论特点。
何谓普同性,简单来说,从人类都是同一种属的角度来观察,每一个人都是平等的。不管是落后地区的人,还是发达地区的人,世界上所有现存的人类都是一样平等的,没有谁比谁更加进化,当然也包括历史上已经消亡的和现在活着的人,他们都是平等的人类。这是现代人类学的基础之一。以普同论为思考的出发点,我们就不会刻意地区分落后文化和先进文化,我们才能在主观心态上保持客观的研究立场。
整体论,又叫全貌论。就是人类学对人类生活的研究是从全局性和完整性来思考的观点,并且给一个局内的观察。全貌论对人类学和非遗研究都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只有从完整的全貌出发,我们才会有广阔的视野,才不会在具体的非遗保护工作中犯片面的错误。
整合论,有着和整体论有着类似的立场,因为人类学家们都认为世上所有的事物之间不是孤立的,而是有着千丝万缕的内在联系。他们更愿意把社会和自然当成一个系统的整体来看待。并把观察对象放置在社会和各种自然环境中研究分析,并且强调对其内在联系的挖掘。
相对性,也叫做文化相对论,它源于人类学家韦斯特马克的著作——《道德观念的起源与发展》。韦斯特马克提出人们不应该把自己的文化价值尺度当做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准则,并以此去评判其他人的另一种文化价值,他认为每一种文化都应该具有自己的独特性和价值。由于各种不同的文化具有这种相对性,所以在价值层面来说,他们都是平等的,都有独创性和相对性。简单地接受某一人群的所思所为或者放弃批评都不是文化相对主义所主张的,我们应该把文化相对论视为避免民族中心主义的一剂良药,它有助于克服那种以自我文化和传统价值观为中心的狭隘错误的判断。引导我们去以一种平等的心态把每一个文化行为、现象放入每一个具体的,甚至是完全迥异的历史环境和社会环境中去观察每一种文化的独特魅力,并加以评估和懂得去尊重它们的独特价值。而这种思考问题的立场和观点对我们的非遗保护工作也是至关重要的。
(四)人类学的地方性知识可以给非遗产保护工作一种开放的心态
基于人类学意义的地方性知识,它并非特指任何具有特定的地方特征的知识,而是一种更加关注知识生成文化环境的知识观念。它涉及特定历史条件形成的文化情景和相应的价值观念。盛晓明阐释说:“这里所谓的‘地方性知识’,不是指任何特定的、具有地方特征的知识,而是一种新型的知识观念。而且‘地方性’或者说‘局域性’也不仅是在特定的地域意义上说的,它还涉及在知识的生成与辩护中所形成的特定的情境,包括由特定的历史条件所形成的文化与亚文化群体的价值观,由特定的利益关系所决定的立场和视域等。‘地方性知识’的意思是,正是由于知识总是在特定的情境中生成并得到辩护的,因此我们对知识的考察与其关注普遍的准则,不如着眼于如何形成知识的具体的情境条件。”[1]在格尔兹的解释人类学中,关于地方性知识的一个重要观点是:“文化持有者的内部视界”⑤,强调从文化传承者的自身的视角来思考问题,而不把研究人自己的观念强加到当地文化传承者身上。
地方性知识对于非遗保护工作的理论意义在于,它给我们建立了一种新的思考文化现象的全新观念。它引导我们不仅着眼于文化现象本身,同时也对特定文化形成的历史环境和文化价值观,以及他们在特定历史场景中视野和与之相应形成的立场都予以足够的重视。采用人类学关于地方性知识观念,不仅对原来处于亚文化群体的文化和价值观予以足够的重视,而且也让整个非遗保护的研究进入多样性、丰富性和深刻性的阶段中。这对于解决以往非遗研究中平庸粗陋具有直接而明显的作用。
(五)人类学的田野考察法是非遗保护研究的显微镜和望远镜
通过田野考察等研究方法,人类学者重视发掘当地人的观念。以整体的观点来探讨人类文化生活的不同方面。通过与当地人的互动,人类学研究者直接在观察与访谈中,了解当地人的日常生活,以及他们在当地社会中真实的想法和具体行为。参与观察法,作为人类学学科的一种重要研究方法,它和社会学的访谈方法有着很大的区别。一个合乎操作规范的参与观察法一般需要研究者在观察点住一年以上的时间。在这期间,研究者和当地人同吃同住,参与他们的各种活动、学习他们的语言,和当地人一起经历四时变化。
总而言之,研究者需要融入到当地人的生活和他们独特的文化世界中去。我们不仅要观察,还要参与,不仅要参与,还要理解,不仅要理解,还要记录。注释:
①参见苑利、顾军《中国民俗学应如何走出自己的学术困境》,刊载于《西北民族研究》2001年第2期。
②参见叶涛《新时期中国民俗学论纲》,刊载于《江苏社会科学》2000年第3期。
③这个看法是否准确,请大家批评。
④参见庄孔韶《“蝗虫”法与“鼹鼠”法——人类学及其相关学科的研究取向评论》,刊载于《开放时代》,2007年第3期。
⑤参见自刘兵,卢卫红《科学史研究中的“地方性知识”与文化相对主义》,刊载于《科学学研究》2006年第1期。
[1]盛晓明.地方性知识的构造[J].哲学研究,2000(12):33-44.
[2]叶舒宪.地方性知识[J].读书,2001(5):121-125.
责任编辑:黄贤忠
Anthropology can be the Theoretical Tool for the Work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Protection
XU Jieshun
(School of Humanities,Shanghai Jiaotong University,Minxing District Shanghai 200240,China)
In terms of the China’s academic circle,the work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protection is the pennies from heaven, when the China’s folklore is unprepared.Since China began the work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n 2006,people began to know the anthropology,especially cultural anthropology which has great theoretical value to th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protection work.
folklore;anthropology;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protection work;theoretical tool
C915
A
1673-8004(2014)06-0026-04
2014-05-30
徐杰舜(1943-),男,浙江余姚人,教授,博士生导师,人类学高级论坛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