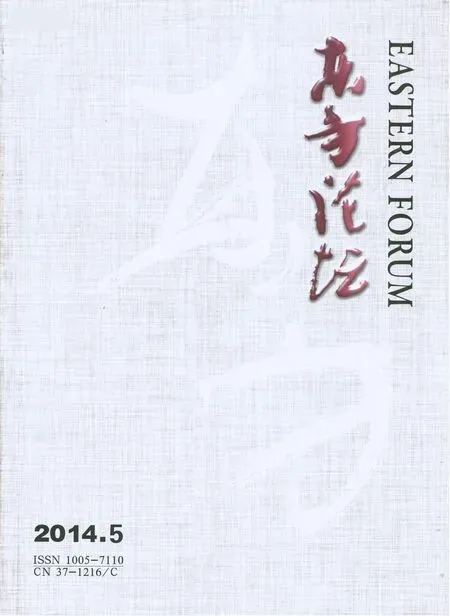清末民初自由报人林白水的办报思想与实践
周宇清
(内江师范学院 政法与历史学院,四川 内江 641112)
林白水(1874—1926年),原名獬,又名万里,字少泉,号退室学者,常署名为宣樊子、白话道人等,晚号白水。福建闽县(今闽侯县)人。他是晚清民国之际的著名报人,一生以报业名世,最终也因文字贾祸。关于对林白水的研究,近来已有不少,但这些成果,大多集中在其报业活动上,而对其附和袁世凯并为其帝制张目更是鲜有正面论述,本文是将林白水置于近代中国社会大转型的社会文化生态背景下,从社会史的角度分析其在晚清民国之际的思想倾向和政治实践,并以期窥见当时中国社会状况之一斑。
一、始终奉行“眼光向下”的办报宗旨
在那个风雨如晦的时代,处于社会底层的民众的生活是非常艰辛的,林白水深知启迪民智的重要,“欲不受欺,先得有知识,故办报宣传各类知识”[1](P26)。他先后主持、参与或创办过《杭州白话报》《译林》《学生世界》《俄事警闻》(后改为《警钟日报》)《中国白话报》 《民主报》 《时报》 《公言报》 《平和日报》《新社会报》和《社会日报》等十余种报刊。报纸,对于二十世纪初年的中国而言,还是十分重要的传媒手段,“欲觇国家之强弱,无他道焉,则于其报章之多寡良否而已矣”[2](P45),这些报纸,对于传播新知、教育民众,无疑具有重要的作用。
林白水不仅所办的报纸多,其特色也很鲜明,就是坚持用白话办报。这也是其平民意识的重要体现。中国数千年来在文体上居于正统地位的是文言文,尽管智慧的人们用这种文体创作出了大量的优秀作品,但它的缺点也是显而易见的,就是文辞古奥,一般民众耗精敝神,仍觉佶屈难解,望而生畏,故“文言之害,靡独商受之,农受之,工受之,童子受之,今之服方领习矩步者皆受之矣”[2](P39)。“愚天下之具,莫文言若;智天下之具,莫白话若”[2](P42)。“因为文字艰深,教育又不普及,以致多数人不能阅读报纸”,致使报纸“和一般国民漠不相关”[3](P64)。在此情势下,林白水毅然用白话办报,“说白话”,用的是“一般老百姓的语言,而不是一般士大夫阶级的咬文嚼字或八股文的文章”[4],使报纸与普通民众接近。林白水的白话文和和白话报刊与同时代的其他同类报刊、文体一道,共同推动了一种新的语体文——白话文的应用与普及,这为后来“五四”时期和新文化运动中的白话文运动奠定了一定的思想基础和实践基础。而白话文的推行和普及,在近代中国大转型的历史进程中具有重大的意义,它颠覆了文言文在书面语中的正统地位,从而“开辟了一个白话文学的新纪元。这正好与中国社会在‘五四’期间实现了从封建向民主的转变相适应”[5](P14)。追根溯源,可见林白水在此过程中的作用和贡献。
林白水的报纸是为普通百姓办的,阅读对象是底层群众。林白水不仅自感是个“平民”,“不谈风花雪月,也不像别的报纸,捧戏子或歌颂妓女”[4],而且对底层民众寄予了厚望,“现在中国的读书人,没有什么可望的了!可望的都在我们几位种田的、做手艺的、做买卖的、当兵的、以及那十几岁小孩子阿哥、姑娘们”。“我们不读书的这辈英雄,倘然一天明白起来,着实厉害可怕得很”[6]。民众通过阅报开阔了眼界,拓展了思路,且因读报而渐有判断力,“倘使这报馆一直开下去,不上三年包管各位种田的、做手艺的、做买卖的、当兵的,以及孩子们、妇女们,个个明白,个个增进学问,增进识见,那中国自强就着实有望了”[6]。字里行间,洋溢着对国家富强的企盼和对普通民众力量的期望。这与当时那些看不起普通民众、漠视民众力量的人迥异,林白水较早地认识到这一点,显示了他的超前意识和卓越见解。终其一生,林白水都有着极其强烈的爱国情怀,极浓烈的平民意识,他是个爱国的平民知识分子。
二、强烈的国民启蒙意识
同样是意识到当时中国普通民众知识的匮乏和现代民主观念的淡薄,林白水很注重对底层民众的教育、启蒙。他主办、主管的报纸以及他的文章,大量地充斥着这方面的内容。
教育人们应该自尊自信,要提高自身素养,认识到自身的价值,“我们做百姓的身分”,“第一件要伶俐”,看报是一条重要的途径,“天天看着白话报,自然会漫漫的伶俐起来,漫漫的在行起来,大家也漫漫的和好起来了”。做百姓的又伶俐又在行又和好,不仅不会吃亏,还有许多好处,“天下做坏事的人顶怕把伶俐人看破”,“我们做百姓的,倘能够个个伶俐,那些就称大老爷,知府大人,只怕他也没有许多小老婆好困许多绍兴酒好吃了”[7]。
林白水努力提高民众的政治参与意识,教育民众要有权利义务思想,“教全国中下等社会里头,个个都有政治上普通的智识,晓得人民于国家,如何应尽义务,如何应享权利,政府如何应该保护我们,皇帝共官吏,如何才算尽职”[8]。要懂得自己应享有的权利,“凡国民有出租税的,都应该得享各项权利,这权利叫做自由权,如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这些自由权,我们都应该享受的”[9]。教育民众破除封建等级观念,“教全国中下等社会里头,个个都有权利思想,晓得皇帝是百姓的公仆,没有什么好怕的,官吏更是百姓第二等的奴才,没有什么好惧的,他若犯了法,就把他赶了杀了,也不过共赶杀鸡犬一样,没有什么稀奇的”[8]。
针对当时中国社会的一些不良习气,如缠足、迷信、赌博和吸食鸦片等陈规陋习,林白水进行了强有力的抨击[10],有感于当时女子受教育权利的薄弱,他还“提倡女学”[11](P487),参与发起成立爱国女学校,这些都彰显了林白水的进步意识和改造社会的美好愿望。
在民众知道自我价值的同时,提醒民众,还要走出“自我”,要“合群”,重视群体的力量,“无论什么事大家都有关系的,有一件好,是大家的好,有一件歹,就是大家的歹”,大家齐心协力,就会产生巨大的力量,“不要说他们做官的害怕,就是外国人也顶害怕的哩”[7]。合群既然如此重要,许多人也都明白这个道理,但是“讲了大半天,那群力还是不能合,那团体还是不能结,这是什么缘故呢?”在林白水看来,中国人不合群的原因是“中国的人本没有公共的观念”,“上流社会”和“下流社会”之间以及这两层社会内部的不联络。有鉴于此,他疾呼“上流下流社会的人,个个不要闹脾气,排架子,存私意。从前的见解,从前的仇怨。都要丢开。……顾著公义彼此无分上下通通合起来,求达以上两个大目的”,这样,“中国前途才有一线之望。倘然不是如此,亿万人有亿万的心,自私自利,不顾大局。等到亡国灭种的时候,大家同归于尽,还有什么益处”[12](P167、169)。
林白水还教育民众要心存天下国家的观念,“天下是我们百姓的天下,那些事体全是我们百姓的事体”[7]。“你知道国家从哪里来的,还不是由我们做百姓集起来的么,没有我们百姓,就不得叫做国家。这个做皇帝的不过我们请他管管国家的事情,国家并不是他产业,所以国家的事情,我们都应该出去问问,现在俄国占了东三省,各国要来瓜分”[13],在列强环伺,国势陵夷的情势下,“我们做百姓的……,做事顶大的是保守我们自己的国土,国土保不得,就要拼命共人家相争”[14]。把反对外国的瓜分,寄托在普通民众身上。还要做争政治的事业,鼓吹用革命方式推翻清政府,“这就是政治上战争的事业,也叫做革命的事业”[14]。
“本来我国人对于‘自己’之观念甚深,而对于社会国家之观念则甚薄。‘各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家瓦上霜’之消极人生观,实为我民族积弱之由来”[15](P237),林白水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如今我们做百姓的,不晓得这国家两字,到底是怎样解说,往往把国家当做皇帝的产业,随便什么事,都不去管理,所以弄到后来,那国被人家盗卖完了,侵占完了,他自己还在鼓里睡觉哩”[10]。这种积习,显然不利于民族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林白水重视对民众进行社会国家观念的启蒙教育,使人们“渐知自己以外,尚有社会,尚有国家,去真正醒觉之期不远矣”[15](P237)。
林白水用他惯常的浅近语言宣传民主启蒙思想,在当时颇具新意和启发意义。尽管他的某些做法和思想也有些许不足,如他为了把报纸办得通俗易懂,语言过于直白有时不免流于粗疏,一定程度上减损了宣传的魅力;又如尽管他对孙中山很敬重,但他又认为孙中山晚年在广州建立革命政府和革命武装是“迷信武力,俨然为全国军阀之一员”[16],就十分不正确;但从总体上说,在那个时代,林白水这些充满战斗性的文章和立场鲜明的思想,昭示了中国社会的进步方向,其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三、社会担当意识与批判精神
林白水不仅积极宣传近代民主、启蒙思想,移风易俗,对当政的权贵也多有讥议,表现了一个进步报人的社会担当意识和无畏精神,这种大无畏精神的背后是一种对民族、国家未来的期待。
1904年,清政府派铁良到南边来搜刮财富,林白水揭发道:“这铁良一到上海,就搜出八十万两银,又到苏州括了六十万,如今正在镇江哩”。“这一刮,以后什么事都不必做了……你们各位要留心一点,铁良来时,那地方官要极力的巴结他,不能不任他括财括个饱满。铁良一去,那地方官办事一个钱都没有,又要立了许多巧名目,在你们列位身上吸髓敲脂哩”[17]。
1904年冬天,正当满朝官员正为慈禧的七十寿辰忙得不可开交的时刻,林白水撰写了这样一副对联以讽刺之:
“今日幸西苑,明日幸颐和,何日再幸圆明园?四百兆骨髓全枯,只剩一人何有幸?
五十失琉球,六十失台海,七十又失东三省!五万里版图弥蹙,每逢万寿必无疆!”[18](P102)
对联尖锐生动地批判、讽刺了清统治者只图个人安逸享乐不顾民众死活,致使国家日益陷入危殆之中的丑恶行径,脍炙人口,一时广为传颂。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国家仍然是混乱纷呈,“军既成阀,多半不利于民,有害于国”[19]。他不满“总理一年而九易”、“通讯社一年而八产”的民国政局,点名批评内阁总理段祺瑞、伍廷芳、江朝宗、李经義,议政大臣张勋、王士珍等人[20]。他还抨击张勋复辟,刊登军阀吴佩孚搬运飞机炸弹和盐务公债黑幕,揭发曹锟贿选事件,尤其令其得意的是对政客陈锦涛贿选丑闻、交通总长许世英贪赃舞弊等内幕的公开揭露,致使陈锦涛锒铛入狱,许世英畏罪辞职,后来,林白水自得地说:“公言报出版一年之间,颠覆三阁员,举发二赃案,一时有侩子手之称,可谓盛矣”[21]。
不论是在晚清还是民国,林白水攻击的都是政坛上权势煊赫的人物,而当时中国的舆论环境是很严峻的:“中国简直不是一个法治国,法律不能够保障人权;尤其是新闻界,容易犯罪。约法上的‘人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之自由’,本来是说说罢了;还加以‘报纸条例’,‘出版法’等,重重缚束”[22](P47)。民国以后,“盖自报纸条例公布,检查邮电,阅看大样,拘捕记者,有炙手可热之势也。自是而后,有督军团之祸,张勋之复辟,护法之役,直皖、直奉及江浙之战,与最近东南及东北之战,兵连祸结,岁无宁日。虽内地报馆,前仆后继,时有增益,然或仰给于军阀之津贴,或为戒严法所劫持,其言论非偏于一端,即模棱两可,毫无生气”[15](P211)。这种形势,一方面极其需要正义的声音来引导民众,一方面也使得敢于说真话很难也很可贵。
在近代中国革命史上,也有不少旗帜鲜明地鼓吹革命、抨击当道的报纸和杂志,但它们往往是某一党或某个组织主办的,背后有组织的力量。林白水虽然也曾加入光复会、同盟会,辛亥后成为共和党的一员,但在参政院去职后,成为一个“无党籍关系之超然人”[16],是没有党派背景的,是一个自由知识分子和自由报人,在这种境况下,他仍然一如既往地针砭时弊,风标独立,就显得更为可敬可佩了。林白水自己的处境也很堪忧,不仅为“资力所扼”,而且“一切环境,如警吏、侦探、印刷工人、纸店掌柜,均可随意压迫,摧其生命。避免无术,如陷重围。揶揄之鬼载途,将伯之呼不应”[23]。
林白水之所以敢这样做,是因为他看到了当时报界的不良状况:“近今言论界,较之从前,只见其退化,既不能造健全之舆论,反随不健全舆论之后,相与附和雷同。只思博人欢迎,推己销路,而是非之真,从未顾及。报馆记者既无经验之可言,又无学识之足录。其人则滑头之人,其文亦滑头之文,其迎合社会心理,揣摩社会风气,无往而不用其滑,以此而言办报,诚至可哀矣。”[24](P1166)在其内心深处,潜藏着一种报人的社会担当意识和责任感,立志“树改造报业之风声,做革命新社会之前马”[25](P923)。“艰难缔造,为社会留此公共言论机关,为平民作一发抒意见代表”[23]。林白水这般针砭时弊,尽管深为当道所忌,却为一般民众所欢迎,当其在上海时,“海上诸报,无不以刊白水之文为荣”,当其在北平办报时,“北平之中央公园,夏日晚凉,游人手报纸而诵者,皆社会日报也”[26](P256)。尤其是青年学生,劝其“放大胆子,撑开喉咙,照旧的说话”[27],这给了他很大的鼓舞,“触忌讳,冒艰险,所不敢辞”[23]。对民众也充满信心,深谓“世间还有公道,读报的,还能辨别黑白是非,我就是因文字贾祸,也很值得”[27]。
在那个世象纷纭、人情浇薄的时代,林白水以他敏锐的视角和超人的胆略,以文论政,抨击时弊,揭露封建统治者和军阀政客的丑恶行径,为社会竖起了一个正义的标杆,使人感到世间还有真理在、正气在,这对于弘扬社会正义、重铸世风是大有裨益的。林白水敢于直面社会阴暗面,充分展现了他不计个人利害得失的大无畏气概和为了国家民族前途的良苦用心。
四、纷乱时局中的短暂迷失
1913年,林白水入京,当选为国会众议院议员,并被聘为袁世凯总统府秘书兼直隶省督军署秘书长,袁世凯解散国会后,林白水回到福建,1915年再度入京,被委任为参政院参政,袁世凯复辟帝制时,林白水发表文章,撰表纪,写劝进书,为帝制张目,直到袁氏帝制失败,国会恢复,安福系当政,林白水辞去了议员的头衔,专心于新闻事业。这一段历史是林白水最为人诟病的地方,而那些推崇林白水报业思想和业绩的人,则对其这段经历往往闪烁其词,讳莫如深,其实责罚和回护都不能真正认清事情的真相,也不利于对其人和当时历史场景的理解。
辛亥革命后出现的复辟现象和林白水助袁称帝这一举动对其一生品性的影响是一个需要具体分析的问题。从全球范围来看,人类由封建专制走向民主、自由是大的趋势,但这种趋势呈现的态势、出现的早晚则因国而异。英国、法国资产阶级革命过程中都有反复,都曾出现过封建王朝的复辟,以这种现象作参照,那么,古老的东方大国中国在辛亥革命之后出现的复辟事件也就不难理解了。
再从社会运行层面来看,也有其必然性。共和政体的建立,是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的结果,并为社会未来的进一步发展提供制度保障,它“非政府所能赐予,非一党一派人所能主持,更非一二伟人大老所能负之而趋”,它是多数国民思想人格变更的表现,与多数国民的利害休戚相关,是民众生活的需求,应该是“出于多数国民之自觉与自动”[28](P178)。
而中国是一个有着两千多年封建统治的大国,传统积淀过于深厚,社会转型困难重重。晚清后期,虽然资本主义在中国有了一定的发展,但它的力量还远远未能达到突破封建主义束缚的程度,中国资产阶级从事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国的斗争,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救亡的需要。
这种情势造成了许多国民和革命者现代国家观念淡泊,不少人只是以推翻清王朝为革命的最终目的,而不知道推翻清帝以后一个更重要的任务是要建立和建设现代国家。“革命方略之所以不能行者,以当时革命党人不能真知了解于革命之目的也。革命之目的,即欲实行三民主义也”[29](P185)。“当日革命党员多注重于民族主义,而鲜留心于民权主义”[29](P190)。
不仅革命党人“不能真知了解于革命之目的”,当时纷乱的局势也使得人们对共和政治不认同,“共和宣布亘一年,政象不加善,而泯棼反远过于其旧,于是国中忧深思远之士,渐有疑共和之不吾适者,而外人旁观拟议,方且目笑存之,谓共和之在我国,不过一时幻象,曾无根柢之可以树立而持久。此等语吾闻之盖熟也,叩其论据,则谓人民程度幼稚,不能运用共和政体”[30](P2560)。在人们对共和政治怀疑之时,革命党人的“二次革命”失败后,处于强势地位的袁世凯又用非常手段解散了国会,国民党人也遭到通缉,“当时的民心,都求苟安于一时,认孙中山所主张的三民主义,完全是理想,是空谈,是玄学;不仅是没有经过训练,没有远大眼光的民众是这样,就是所谓党员,也何尝不如此呢?做官的做官,捧袁的捧袁,因政见的不同,自立政党的慢慢地离开了革命的阵线”[22](P28)。因此,辛亥革命后的复辟在当时的中国有其发生的环境和实行的基础。
林白水虽然赞成袁氏称帝,但就其一生行止看不失为一个爱国者、革命者,早在清末,林白水就在福州创设蒙学堂,“以革命学说,灌输学生”,后来,著名的黄花冈之役,“福州死难者十人,皆蒙学堂旧生也”[26](P255)。1902年3月他与蔡元培、蒋观云等发起成立“表面办理教育,暗中鼓吹革命”的中国教育会[11](P485)。1903年4月,在日本参加了以拒俄为目的的学生军,并任丙区队第二分队的分队长。“苏报案”发生后,章炳麟、邹容被捕,林白水积极营救,延请律师“代为抗辩”[11](P376)。1904年,林白水参与谋刺清吏王之春[31](P523)。林白水还曾加入光复会,1905年成为同盟会会员。因此,辛亥革命之前,不论是思想、言论、行动还是身份上,林白水都是一个地地道道的革命者,并且,“在清末的革命运动中”,“曾有过不少的贡献”[31](P535)。
在报业活动中,他积极宣传启蒙思想,启迪民众,揭露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抨击封建统治者和北洋军阀政客的专制和贪渎(如上所论),这些都是非常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事情。也因为他的直言,触动时忌,报馆五次被封,他本人也三次入狱,仅此经历,即可证明其为人和功绩了。林白水虽然一度误入歧途,但终归走出误区,几年的京官生活,使他看清了官场的种种恶习,幡然醒悟,毅然挂冠而去。后来,他本人曾对这段历史也有反思:“项城袁氏开口闭口救国救民,迨乱党既平,全国统一,则又思逞其所怀抱之帝制矣”[32],可见他也是被袁世凯的“救国救民”面孔蒙蔽的,并且对袁氏的帝制自为还是有所批评的。事物本质的暴露需要一个过程,袁世凯在清帝逊位前后的举动一度使得孙中山、黄兴等革命巨子产生错觉,遑论他人。林白水也感到曾经的革命同志误解了他,很为自己抱屈:“自革命后,我因为做了袁项城的秘书,又做了共和党党员,众议院议员,因此他们(指林白水的朋友吴稚晖、张溥泉等——引者)都认我是反对党,或是官僚派,就与我不相往来了。……大概彼此都有点误会。他的误会,是认我为官僚。”“彼此抱了这种误解,遂从此不相闻问了,想起来真正痛心得很”[33]。
在那个纷扰的年代,林白水一度成为帝制的帮凶固然可惜,但分析当时的历史环境和其一生的行止,其行为有一定的历史原因,“这个过程是难以用个人的品格来解释的”[34](P370)。可贵的是他终究迷途知返,并且以更昂扬的姿态给军阀政客以猛烈的抨击,直至罹难。正是由于他的业绩,1985年7月30日,国家民政部追认其为“革命烈士”。
总之,在近代中国社会急剧大变革的时代,林白水以一个报人的敏锐眼光和一个爱国知识精英的识见,把握住了时代的脉搏,将目光投向底层群众,窥测到他们的需要,并多方面的启蒙、教育,其实是在为中国的进步开掘、积蓄力量。他对封建统治者和北洋军阀政客的抨击,是对民众、国家尚抱有信心的表现,也是为社会的进步扫除障碍。尽管在其行程中,有一段瑕疵,但那是特殊年代、特殊环境里的短暂迷失,从其一生看,他未失去一个报人和杰出知识人的良知,可谓瑕不掩瑜,他在近代中国社会演进的过程中曾起到重要的作用。
[1] 《新闻界人物》编辑委员会.新闻界人物(四)[M].北京:新华出版社,1984.
[2] 张枬 王忍之.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一卷上册[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0.
[3] 蒋国珍.中国新闻发达史[A],民国丛书(第三编·41·)[C].上海:上海书店,1991.
[4] 孙先伟.林白水的报人生涯[J].民国春秋,1998,(2).
[5] 胡奇光.白话文运动[A],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 文字)[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8.
[6] 白话道人.《中国白话报》发刊词[N].中国白话报,第一期,中历癸卯十一月初一日.
[7] 白话道人.做百姓的身分[N].中国白话报,第一期,中历癸卯十一月初一日.
[8] 白话道人.论刺客的教育[N].中国白话报,第十七期,中历甲辰六月二十日.
[9] 白话道人.国民意见书[N].中国白话报,第五期,中历甲辰新正月初一日.
[10] 白话道人.做百姓的思想及精神[N].中国白话报,第四期,中历癸卯十二月十五日.
[11] 中国史学会.辛亥革命(一)[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
[12] 林伟功.林白水文集[M].福州:福州市新闻出版局,2006.
[13] 时事问答[N].中国白话报,第二期,中历癸卯十一月十五日.
[14] 做百姓的事业[N].中国白话报,第三期,中历癸卯十二月初一日.
[15] 戈公振.中国报学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16] 白水.吾人对中山先生之敬意[N].社会日报,中华民国十三年十二月九日.
[17] 铁良南下[N].中国白话报,第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期合印,甲辰八月三十日.
[18] 张次溪.记林白水[A].林慰君.我的父亲林白水[C].北京:时事出版社,1989.
[19] 白水.奉联将领大大觉悟[N].社会日报,中华民国十五年四月二十六日.
[20] 白水.民国六年北京之所有[N].公言报,大中华民国七年一月九号.
[21] 白水.不堪回首集(一)[N].社会日报,中华民国十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22] 张静庐.中国的新闻记者与新闻纸:下编[A].民国丛书(第三编·41·)[C].上海:上海书店,1991.
[23] 林白水卖文字办报[N].社会日报,中华民国十四年一月六日.
[24] 上海图书馆.汪康年师友书札(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25] 方汉奇.中国新闻事业编年史:上册[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0.
[26] 陈与龄.林白水先生传略[J].东方杂志,第三十二卷第十三号(1935年7月1日).
[27] 白水启事[N].社会日报,中华民国十四年十二月二十日.
[28] 任建树,张统模,吴信忠.陈独秀著作选:第一卷[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
[29] 孙中山全集:第五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5.
[30] 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第五册[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
[31] 章伯峰,顾亚.近代稗海:第十二辑[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
[32] 白水.敲门砖[N].公言报,大中华民国六年七月二十六号.
[33] 白水.答吴稚晖先生[N].社会日报,中华民国十四年十二月四日.
[34] 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