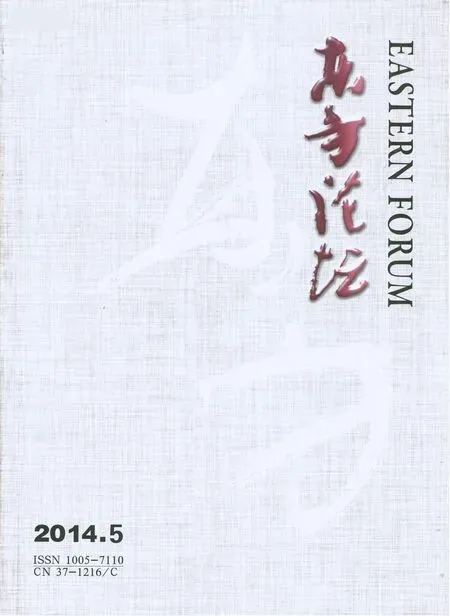辛弃疾诗歌新论
汪 洋
(首都师范大学 文学院,北京 100048)
引言
辛弃疾词为历代学者所重,其诗歌则受关注较少。就现有研究成果来说,论者大致从辛弃疾诗的内容、渊源、风格、成就等方面进行讨论。内容、成就二端论述已经较充分,其余二端则有深入探讨的空间。就渊源一端来说,现有研究大都以辛弃疾《和任帅见寄之韵三首》其三云:“剩喜风情筋力在,尚能诗似鲍参军”,《读邵尧夫诗》云:“饮酒已输陶靖节,作诗犹爱邵尧夫。”为基础,着重强调辛弃疾诗同鲍照、邵雍诗的渊源关系。①这几乎成为学界共识,代表性论文如巩本栋《作诗犹爱邵尧夫——论辛弃疾的诗歌创作》(载《南京大学学报》1999年第1 期)、冯霞《辛弃疾诗歌研究》(湘潭大学2010年硕士学位论文)等。而在辛弃疾诗歌风格一端,有学者在渊源邵雍、鲍照基础上,从“健”“淡”的宋诗审美追求论述过辛弃疾诗的宋诗风调。[1]在笔者看来,上述观点均存在可商榷之处。本文主要拟就辛弃疾诗歌的创作渊源、宋诗风调两方面进行深入探讨,祈请方家指正。
展开论述之前,先将辛弃疾诗歌创作的基本情况作一简单考察,以为全文讨论的基础。辛弃疾诗有集,收在《辛稼轩集》中。据邓广铭先生所考,其诗集在明代中期随着《辛稼轩集》的散佚而亡。[2]清代中期,法式善等人从《永乐大典》等书籍中辑出辛弃疾诗文,由辛启泰整理刻印成《稼轩集钞存》;1954年,邓广铭先生在此基础上辑成《辛稼轩诗文钞存》;1993年,邓先生又同辛更儒合作完成《稼轩诗文笺注》,此书收入辛弃疾诗142 首。本文所论辛弃疾诗歌文字、句读,即以《稼轩诗文笺注》一书为主。
笔者以为,现存辛弃疾诗歌数量虽少,但很大程度上可以反映出其创作的基本情况,理由如下。首先,辛弃疾的文学创作观十分开明,并未将填词视作为小道;且其词容量巨大,但凡诗歌中可以抒写的题材,稼轩词都有涉及。正如他所说:“不妨旧事从头记,要写行藏入笑林”(《鹧鸪天·不寐》)。辛弃疾将词当作书写行藏的工具,这必然会减少他的诗歌创作。其次,宋代文字狱特多,因诗文获罪更是常见。②宋高宗朝文字狱便很多,可谓辛弃疾眼前之事。可参考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二十六“秦桧文字之祸”条。辛弃疾惩于苏轼等人的遭际,恐惧因诗文罹祸,有意识地少写诗歌。其《水调歌头(文字觑天巧)》的《小序》说:“提干李君索余赋《秀野》《绿绕》二诗,余诗寻医久矣,姑合二榜之意,赋《水调歌头》以遗之。”文中“余诗寻医久矣”用苏轼《七月五日诗》“避谤诗寻医,畏病酒入务”之典,明显地说出他尽量不写诗是为了避免政敌借用自己的诗歌进行诽谤、陷害。最后,现存辛弃疾诗歌大部分都是从《永乐大典》中辑出。我们都知道,《永乐大典》按韵字排列,往往将相关书籍全部或大部抄入。乾隆中后期时,《永乐大典》残缺仅2422卷[3],相比全帙的22937卷,乃是一小部分。法式善等人辑刻辛弃疾诗在嘉庆中期,其时《永乐大典》保存相对完整。所以,辛弃疾诗很可能大部分已经被法式善等人辑出。因此,辛弃疾诗歌数量极有可能与现存相差不大。由上所述,故笔者认为现存辛弃疾诗歌大致可以反映出其创作的基本情况。
一、辛弃疾诗歌渊源辨正
(一)渊源鲍照、邵雍辨正
鲍照诗的主要风格是“俊逸豪放、奇矫凌厉”[4](P123),杜甫《春日怀李白》云:“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的确,辛弃疾许多诗歌俊逸豪放似鲍照,如《送别湖南部曲》《赠申孝子世宁》等数首。这同辛弃疾豪迈的个性以及生平遭际相关。论者往往忽略一个问题:雄健是一种主要的文学风格,健笔豪情也是许多诗人所共有,如庾信、李白、杜甫甚至陶渊明。辛弃疾说自己“诗似鲍参军”,只是表明自己同古人的诗风相似,并不是说自己学习鲍照。陆游《送辛幼安殿撰造朝》“稼轩落笔凌鲍谢”,则是将辛弃疾诗词同鲍照、谢灵运诗相拟,也不是说辛弃疾学习他们。辛弃疾诗除了上述的风格相似之外,找不出学习鲍照诗歌创作的痕迹。所以,辛弃疾诗歌创作学习鲍照的说法至少是不准确的。
邵雍是北宋著名理学家,其自定诗集曰《伊川击壤集》。严羽《沧浪诗话·诗体》列“以人而论”的诗体中,以邵康节体与东坡体、山谷体、后山体、陈简斋体、杨诚斋体并列,可见邵康诗在当时影响之大。那么邵雍诗被严羽列为一体,其最重要的特点是什么呢?《四库提要》云:
《击壤集》二十卷,宋邵子撰。前有治平丙午《自序》,后有元佑辛卯邢恕《序》。晁公武《读书志》云:“雍邃于易数,歌诗盖其余事,亦颇切理”。案:自班固作《咏史诗》,始兆论宗,东方朔作《诫子诗》,始涉理路。沿及北宋,鄙唐人之不知道,于是以论理为本,以修词为末,而诗格于是乎大变,此集其尤著者也。朱国桢《涌幢小品》曰:“佛语衍为寒山诗,儒语衍为《击壤集》。此圣人平易近人,觉世唤醒之妙用”,是亦一说。然北宋自嘉佑以前,厌五季佻薄之弊,事事反朴还淳,其人品率以光明豁达为宗,其文章亦以平实坦易为主,故一时作者往往衍长庆余风,王禹偁诗所谓“本与乐天为后进,敢期杜甫是前身”者是也。邵子之诗,其源亦出白居易,而晚年绝意世事,不复以文字为长,意所欲言,自抒胸臆,原脱然于诗法之外。[5](P355)
由以上材料可知:第一、《提要》认为邵雍诗的最大特点是说理,并认为《伊川击壤集》是宋诗说理“尤著者”;第二、《提要》引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说“(邵)雍邃于易数,歌诗盖其余事,亦颇切理”,又引朱国桢《涌幢小品》说邵雍诗是“儒语衍为《击壤集》”,这说明《提要》认为邵雍诗说理的主要内容是其理学思想,是说儒学之理;第三、《击壤集》中诗风朴拙、表现闲适生活意趣之作,则是学习白居易。
钱穆先生著有《理学六家诗钞》,其中论邵雍诗云:“康节诗最为创新,诚可谓之是理学诗。”又在《邵康节别传》中言:“后人读其诗,特以曾点相拟,亦未为知康节。”[6](P3)也是强调其诗创新之处在于论说其理学思想,说儒学之理。“曾点相拟”指《论语·先进》中子路、曾皙(名点)、冉有、公西华侍坐时孔子让他们“各言其志”,曾点最后发言:“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7](P154)钱宾四先生用此典也在说明邵雍诗中那种学习白居易诗的悠游闲适风格不是其诗歌的特色。邵雍自序《伊川击壤集》云:“诚为能以物观物,而两不相伤焉,盖其间情累都忘去尔,所未忘者,独有诗在焉。”也反映出其诗歌创作中自觉的理性倾向。可以说《伊川击壤集》是“研究宋诗及邵雍易学的必读之书。”[5](P10)概而言之,笔者以为:邵雍诗受其“观物”思想的影响,阐述其哲学思想是其最主要的特点,这也是邵康节体可以同东坡体、山谷体并列的主要原因。而《伊川击壤集》中闲适诸作、朴拙诗风则源于白居易。
辛弃疾《读邵尧夫诗》有云:“饮酒已输陶靖节,作诗犹爱邵尧夫。”联系上联,“犹”字应理解为并且、尚且的意思,并非特别之意。这说明辛弃疾自言其诗歌创作受到邵雍影响,但并非说自己诗歌创作的主要渊源是邵雍诗。辛弃疾诗歌中明言学习邵雍的是《有以事来请者效邵康节体作诗以答之》:
未能立得自家身,何暇将身更为人?借使有求能尽与,也只方笑已生嗔。器才满后须招损,镜太明时易受尘。终日闭门无客至,近来鱼鸟却相亲。
此诗除最后一联之外,都是议论说理之词。第一句“未能立得自家身”用《孝经·开宗明义》“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之典;第五句“器才满后须招损”用《尚书·大禹谟》“满招损,谦受益,时乃天道”之典。辛弃疾虽然不是理学家,难有邵雍那样的儒学造诣,但其学习邵康节体的诗歌说理用儒学之典,可见其对邵康节体的特点十分清楚。现存辛弃疾诗歌中明言“效邵康节体”的只此一首,其它可以算作学习邵康节体的诗作还有《偶作》《偶成三首》(其二)、《丁卯七月题鹤鸣亭》(其一)、《丁卯七月题鹤鸣亭》(其三)等10 首,不到总数的十分之一。从数量上说,邵雍诗不是其诗歌创作的主要渊源。
那么,为什么辛弃疾学习邵雍的诗歌数量较少呢?首先,辛弃疾的学问博而不渊,他对经史百家都有涉及,但是未有深入研究。就儒、释、道三家哲学来说,他对道家哲学,尤其是对《庄子》较为熟悉,这可以从他词中大量运用《庄子》典故以及用词对《庄子》中某些问题进行简单探讨看出。对于佛家思想,辛弃疾往往持怀疑态度,如其《读语孟二首》其一云:“道言不死真成妄,佛语无生更转诬。要识生死真道理,须凭邹鲁圣人儒。”便是对佛家讲“无生”的反驳。而对儒家思想,辛弃疾也未有精深的造诣,自然不能像邵雍那样在诗中说出深刻的儒学哲理。其《书停云壁》云:“学作尧夫《自在》诗,何曾因物说天机。斜阳草舍迷归路,却与牛羊作伴归。”可谓辛弃疾不擅长说哲理的自白。其次,辛弃疾本人性格豪迈,写出来的作品也大都是感情激越。辛弃疾词被称作豪放派的代表,词风悲慨豪放。即使是归隐后创作的大量闲适词中也往往也透露出牢骚满腹。其词大都是“有我之境”,蕴含着深厚的感情色彩。诗言志,辛弃疾诗歌难以达到邵雍诗中那种由悟道而得来的“虽曰吟咏性情,曾何累于性情”的境界。
(二)陶渊明对辛弃疾诗歌创作的影响
辛弃疾《鹤鸣偶作》说:“朝阳照屋小窗低,百鸟呼檐起更迟。饭饱且寻三益友,渊明康节乐天诗。”这里,辛弃疾将陶渊明诗、白居易诗、邵雍诗作为其益友,也就是学习的典范。陶渊明对辛弃疾诗歌创作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化用陶渊明诗文一端。
辛弃疾诗歌创作受陶渊明影响表现最明显的是大量化用其诗文。《稼轩诗文笺注》有没有注出者,也有注错者。这里依次列出:
“十顷芰荷三径菊”(《和任帅见寄之韵》),出自《归去来兮辞》“三径就荒,松菊犹存”。
“柴门不用常关着”(《黄沙书院》),反用《归去来兮辞》“门虽设而常关”,邓、辛误注。
“扫迹衡门下”(《即事示儿》),用《癸卯岁十二月中作与从弟敬远》“寝迹衡门下”。
《书清凉境界壁》:“云胡不归留此耶”,用《归去来兮辞》:“田园将芜,胡不归”。
“相思几欲扣停云”(《和前人观梅雪见寄》),用《停云》“停云,思亲友也”。
“姑置毋多谈,俱想增胜慨。会当携酒去,物理剖茫昧”(《和赵晋臣敷文积翠岩去颣石》),或用《还旧居》“拨置且莫念,一觞聊可挥”。
“放船画作《归来图》”(《庆云桥诗》),用《归去来兮辞》。
“由来不乐金朱事,且喜长同陇亩民”(《偶作》),用《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长吟掩柴门,聊为陇亩民”。
“渊明去我久,此意有谁知”(《感怀示儿辈》),用《饮酒》其二十“羲农去我久”。
加上邓、辛二位先生所注,辛弃疾诗歌化用陶渊明诗文者共21 首,占到七分之一,且有的诗化用不只一处。这远多于辛弃疾诗化用其他文人诗文的数量,可见辛弃疾诗歌创作受陶渊明影响之大。
辛弃疾的诗歌创作受陶渊明影响的原因,在于以下数端。首先,宋代是学习陶渊明的高峰[8](P219),自苏轼遍和陶诗,且对陶渊明诗文、人品加以极力赞扬后,崇拜、模仿陶渊明成为了时代风气。辛弃疾归隐后建堂题名“停云”,便是取陶渊明诗《停云》二字。所以,辛弃疾受其影响是时代使然。其次,这也同辛弃疾自身遭际相关。绍熙五年(1194)第二次罢官之后,辛弃疾更加厌倦宦海沉浮转而祈求如陶渊明那样的安静生活。第一次落职后辛弃疾心中满是屈原那样“忠而被谤”的牢骚话,第二次罢官便如陶渊明那样对政治、社会彻底失望了,此一时期的词作显著地体现了这种失望以及彻底归隐寻求宁静的倾向。自然的,其诗歌创作也必然受到陶渊明的影响。最后,辛弃疾诗歌创作喜欢化用前人诗句,陶渊明诗少而佳,极易成诵,自然会更多地出现在其诗歌创作中。
(三)白居易对辛弃疾诗歌创作的影响
白居易诗的朴拙风格也影响了辛弃疾的诗歌创。朴拙平淡是白居易诗歌的主要特点,其《自吟拙什,因有所怀》云:“诗成淡无味,多被众人嗤:上怪落声韵,下嫌拙言辞。时时自吟咏,吟罢有所思。苏州及彭泽,与我不同时。此外复谁爱?唯有元微之。”正因为白居易诗有语言朴拙的特点,至有“元轻白俗”之说。辛弃疾《题前岗周氏敬荣堂》中云:
泰伯古至德,以逊天下闻。周公去未远,二叔乃流言。……末俗益可嗟,有货无天伦。仓卒竟锱铢,或不暇掩亲。朝从官府去,暮与妻子论。……我观天地间,熟不爱其身。有伐其左臂,那复右者存。君看百足虫,至死身不颠。……我诗聊复尔,语拙意更真。此书君勿嗤,傥俟采诗人。
此诗既是对白居易朴拙诗风的学习,也是对《新乐府》的模仿。“语拙意更真”,是此诗特色,也可看作是辛弃疾诗歌的重要特点。辛弃疾近体诗中也不乏朴拙之作。如《哭赣十五章》:
他年驷车马,谓可高吾门。只今关心处,政在青枫根。(其四)
糊涂不成书,把笔意甚喜。举头见爷笑,持付三四纸。(其五)
汝父诚有罪,汝母孝且慈。独不为母计,仓皇去何之?(其七)
中堂与曲室,闻汝啼哭声。汝父与汝母,何处可坐行?(其九)
此组诗是辛弃疾哭子之作,大都语拙情深。《其四》 以“他年”“谓可”“只今”“政在”窜起全诗,简直明白如话。《其五》以父子相处的写字细节入诗,纯用白描。《其七》 《其九》 连用“汝父”“汝母”,不避重复,后两句隔空发问,全诗娓娓道来,不觉其为诗。这些诗都朴实无华,难以言巧,但情真意切,感人至深。
再如《书渊明诗》:“渊明避俗未闻道,此是东坡居士云。身似枯株心似水,此非闻道更谁闻?”说陶渊明“未闻道”的不是苏轼,而是杜甫,其《遣兴》 诗曰:“陶潜避俗翁,未必能达道。观其著诗集,颇亦恨枯槁。达生岂是足,默识恨不早。有子贤与愚,何其挂怀抱。”辛弃疾全诗便是针对此诗而发。四句诗是一问答,明白如话,诗味很淡,正是白居易所言“诗成淡无味”“下嫌拙言辞”。再如辛弃疾《癸亥元日题克己复礼斋》:“老病忘时节,空斋晓尚眠。儿童唤翁起,今日是新年。”写自己晚年老病情景,全诗明白如话,“今日是新年”更是朴拙至极。再如《偶题》:“逢花眼倦开,见酒手频推。不恨吾年老,恨他将病来。”写诗人年老止酒,后两句也是极平淡之句。据笔者统计,辛弃疾诗歌用语朴拙、平淡之作有20 首,约占其全部作品的七分之一,可见朴拙乃是其诗歌重要特征,亦可见白居易对他诗歌创作的影响。
白居易朴拙的诗风影响了辛弃疾诗歌创作,也是时代使然。同陶渊明一样,白居易也是宋代文人积极学习、模仿的对象。原因有二。其一,上引《四库提要》中有云:“然北宋自嘉佑以前,厌五季佻薄之弊,事事反朴还淳,其人品率以光明豁达为宗,其文章亦以平实坦易为主,故一时作者往往衍长庆余风,王禹偁诗所谓‘本与乐天为后进,敢期杜甫是前身’者是也。”这明确指出了宋人学习白居易的原因在于反拨唐末五代以来的佻薄社会风气,提倡平实坦易的创作风格。其二,白居易“中隐”的生活方式为大多数宋代士人所效法。[9]司马光、富弼等人模仿白居易“九老会”的“洛阳耆英会”更是深深影响宋代文人。在这样的社会风气之下,辛弃疾归隐后学习白居易的生活方式,进而学习其诗歌创作,将乐天诗列为“三益友”也是极自然的事。
二、辛弃疾诗歌的宋诗风调
本节则侧重从创作方法角度考察辛弃疾诗歌的宋诗风调。辛诗的宋诗风调主要体现要以下三方面:
(一)辛弃疾诗歌的理性思辨色彩
唐、宋诗的一大不同就在于“情”“理”之别。严羽《沧浪诗话》云:“本朝人尚理而病于意兴,唐人尚意兴而理在其中。”[10](P148)钱钟书《谈艺录·诗分唐宋》云:“唐诗、宋诗亦非仅朝代之别,乃体格性分之殊。天下有两种人,斯分两种诗。唐诗多以风情情韵擅长,宋诗多以筋骨思理见胜”。[11](P3)这都是在说宋诗的理性思辨色彩,辛弃疾诗有大量作品具有这一特点。前文所述学邵康节的诗歌都属于此类。此外,辛弃疾诗中还以经常用佛语说理,如《丙寅九月二十八日作,明年将告老》:
渐识空虚不二门,扫除诸幻绝根尘。此心自拟终成佛,许事从今只任真。有我故应还起灭,无求何自别冤亲?西山病叟支离甚,欲向君王乞此身。
此诗作于开禧二年(1206),辛弃疾在铅山家中。首句用《维摩诘经·不二法门品》“如我意者,于一切法无言无说,无示无识,离诸问答,是为入不二法门”;次句用《圆觉经》卷上“幻身灭故,幻心亦灭。幻心灭故,幻尘亦灭”;第五句“起灭”也为佛家用语,如《圆觉经》卷上曰:“如来藏中,无起灭故。”全诗主旨是说自己看透世间一切,无欲无求,所以可以不别“冤亲”,将要彻底归隐。
再如《书停云壁》其二:“万事随缘无所为,万法皆空无所思。惟有一条生死路,古今来往更何疑。”次句用龙树《大智度论》卷十五“菩萨知一切诸法皆空无所有”一语,全诗说万物皆空,生死齐一。再如《题金相寺净照轩诗》:“净是净空空即色,照应照物物非心。请看窗外一轮月,正在碧潭千丈深。”首句用《般若波罗密多心经》“空不异色,色不异空。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全诗说心无外物之理。据笔者统计,辛弃疾诗歌中说理之作有25 首,约占总数六分之一,足见其诗对说理的重视,当然这也是宋诗的典型特点。
(二)辛弃疾诗歌中大量用典①此节所论“典故”指“事典”,这是为了区别下文所论江西诗法中化用前人诗句这一特点,因为化用前人诗句这一创作手法,广义上也可称之为用典,即“语典”。
大量用典也为宋诗显著特点。“用事”一端是缪钺先生《论宋诗》中阐述最为用力者。钱钟书先生总结宋诗大量用典的特点时,引明代屠龙《由拳集》:“宋人又好用故实组织成诗,……用故实组织成诗,即奚不为文而为诗哉?”[12](P17)无论缪、钱二位先生对宋诗用典的褒贬态度如何,他们都认为大量用典为宋诗重要特点。邓小军师《论宋诗》对宋人用典又进一步阐释:
宋诗的特质,是借助自然意象,发挥人文优势,以表现富于人文修养的情感思想。所谓人文优势,是指相对于自然现象而言的,来源于人文生活、人文传统和人文修养的诸种艺术手段的优势。这些艺术手段包括来自人文生活事象的人文意象,取自人文传统资源的语言材料即典故,以及出自哲学、政治和人生修养的议论。……典故是人文传统的信息载体,用典是一项古为今用的艺术手段。宋诗用典之多超过了唐诗。这固然与宋人读书多有关,但更与宋人的人文情趣息息相关。[13]
通观辛弃疾诗歌,没有用典的占少数,其人文意象大大多于自然意象。上文所述辛弃疾诗歌中理性思辨色彩浓厚的作品中往往大量用典,其余大量用典的作品如《咏雪》:“书窗夜生白,城角增暮寒。未奏蔡州捷,先歌梁苑诗。餐氈怀雁使,无酒羡羔儿。农事勤忧国,明年喜可知。”前两句从侧面写大雪降;第三句用唐代李朔雪夜破蔡州擒叛匪吴元济事;第四句用谢惠连《雪赋》中汉梁孝王雪天游兔园事;第五句用西汉苏武被囚匈奴雪天以雪和旃毛充饥,后因鸿雁传书得归事;第六句用苏轼《赵伯成家有丽人诗》自注中陶穀学士遇雪烹茶事;最后两句以瑞雪兆丰年之意作结。全诗堆砌有关雪的典故,未有一字及雪而句句是咏雪,虽有自然意象之描绘,然而典故的运用是全诗的主要内容。再如《和诸葛元亮韵》:“偶泛清溪李郭船,路旁人已羡登仙。看君不似南阳卧,只是吟诗孟浩然。”前两句用东汉郭泰、李膺同舟渡河,众人望之以为神仙事;第三句用三国时诸葛亮高卧南阳事;第四句用唐代孟浩然当唐玄宗之面吟诗事;四句诗皆用典,是对友人的称赞。
据笔者统计,辛弃疾诗歌中一半及以上篇幅用典的作品有18 首。这些作品,甚至可以说直接由典故堆砌而成。这里且不说这样的写作方式该如何评价,只强调这是辛弃疾诗具宋诗风调的表现之一。
(三)辛弃疾诗歌中的江西诗法
江西诗派是宋诗的代表,而黄庭坚“点铁成金”“夺胎换骨”的理论无疑是“江西诗法”的重要内容。对于这样的诗歌方法论历来存在争议。简单地说,这一理论的本质在于充分吸收前人优秀诗歌创作成果,化用前人诗句而自出新意,甚至达到化腐朽为神奇的效果。[14](P288)辛弃疾在自己的诗歌创作中具有这样的自觉,其《再用韵》云:“欲把身心入太虚,要须勤着净功夫。古人有句须参取,穷到今年锥也无。”诗中“古人有句须参取”便可视作对“点铁成金”“夺胎换骨”的本质理解。另如辛弃疾《水调歌头·赋松菊堂》云:“诗句得活法,日月有很工”。“活法”是江西诗派诗人吕本中的诗歌理论,可见辛弃疾是自觉地接受江西诗派的诗歌理论进行创作。
辛弃疾诗歌中化用前人诗句而自出新意者很多。有的诗歌改动古人成句一字或数字,以表达新的意思。如《即事》其三:“闲花浪蕊不知名,又是一番春草生。病起小园无一事,杖藜看得绿阴成。”显然是学习王安石的《台城寺侧独行》:“春山撩乱水纵横,篱落荒畦草自生。独往独来山下路,笋舆看得绿阴成。”两诗同是描写隐居后生活,且韵脚一致;辛诗明显学自王诗,只是末句将王诗的“笋舆”易为“杖藜”,情境即变。再如《哭赣十五章》其八:“泪尽眼欲枯,痛深肠已绝。汝方游浩荡,万里挟雄铁。”后两句显然来自杜甫《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的“白鸥没浩荡,万里谁能驯”。仇兆鳌《杜诗详注》引董养性论此诗语云:“篇中皆陈情告诉之语,而无干望请谒之私,词气磊落,傲睨宇宙,可见公踬之中,英锋俊彩,未尝少挫也。”[15](P79)杜诗末句即是此意的绝好表现。而辛诗末两句说自己的儿子虽然死去,却依然挟“雄铁”游于广大旷远的太虚之境;伤悼亡子而颇具豪迈之情,化用却自有新意。
辛弃疾有的诗歌吸取古人诗意反其意而用之。如《即事》其一:“野人日日献花来,只倩渠侬取意栽。高下参差无次序,要令不似俗亭台。”此诗反用欧阳修的《谢判官幽谷种花》:“浅淡红白宜相间,先后仍须次第栽。我欲四时携酒去,莫教一日不花开。”两诗所写事情都是栽花,而且押同一韵部,次句韵字还一样,其密切关系不言而喻。不同的是:辛弃疾要求野人栽花时不必按照一定次序种植,欧阳修则要求“先后仍须次第栽”。再如《新年团拜后和主敬韵并呈雪平》第三联“今是昨非当谓梦,富研贫丑各为容”,显然是化用陶渊明《归去来兮辞》“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只是辛弃疾在“今是昨非”后用“当谓梦”做一否定,表现了他不因理想受挫而轻言放弃的品质。
当然,辛弃疾诗歌中也有化用前人诗句而不能出新意者。如“日醉得非促龄具”(《止酒》),只是将陶渊明《形神影》诗中“日醉或能忘,将非促龄具”糅合到一起。再如“苦无突兀千间避”(《和赵昌父问讯新居之作》),是将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诗意糅合在一起。辛诗中还有个别化用前人诗句而不如原诗者,如《即事示儿》“扫迹衡门下”,化用陶渊明《癸卯岁十二月中作与从弟敬远》“寝迹衡门下”,但不及原诗。陶渊明用“寝”字,是止息之意,谓完全停止对外交往,彻底归隐;而辛弃疾用“扫”字,尚有“扫”之动作。陶渊明是没有“迹”,所以不用“扫”,自然要好于辛诗。再如《书清凉境界壁》“何况人生七十少”,化用杜甫《曲江》“人生七十古来稀”而不如。
如上所言,辛弃疾运用江西诗法做诗,有成功者,有不成功者。这是“点铁成金”“夺胎换骨”这一诗法所不能避免的,即使此诗法的创始者黄庭坚,也有不成功的例子。辛诗中运用这一诗法的作品有39 首,接近全部辛诗的三分之一,且有的诗篇不只一处化自前人。那么,辛弃疾为什么会受到江西诗法如此巨大的影响呢?首先,辛弃疾生活的南宋初期,江西诗派笼罩诗坛;且辛弃疾罢官后所居住的信州,正是江西诗派的中心。适逢其时其地,不受其影响也很难。其次,辛弃疾的两位好友韩淲、赵蕃都是当时著名的江西诗派诗人;辛弃疾同二人频繁唱和,其创作受二人影响也在所难免。
有一点值得注意:上述辛弃疾诗歌宋诗风调的三个特点,在辛弃疾诗歌中往往不是单一存在。有的诗歌在说理成分较重的同时用典较多,如《和赵直中提干韵》;有的诗歌在化用前人诗句较多的同时用典较多,如《和赵昌父问讯新居之作》;有的诗歌甚至三个特点皆备,如《新年团拜后和主敬韵并呈雪平》。这更加可以说明辛弃疾诗歌是典型的宋诗。
论述既竟,可以发现三个问题。首先,辛弃疾现存诗歌数量虽然不多,但很大程度可以反映出其诗歌创作的基本情况,原因有三:一是辛弃疾对词的重视影响了他诗歌创作的数量,二是因诗歌而引起祸端的事实使辛弃疾有意少写诗歌,三是现存辛弃疾诗歌的辑佚来源证明辛弃疾诗歌存世数量与其创作数量相差不大。其次,辛诗学习鲍照、邵雍的诗歌都不多,因此并不能如当今大多数学者那样称二人为辛诗的主要创作渊源;相反,宋人普遍崇拜的白居易、陶渊明,给辛弃疾的诗歌创作带来了非常重要的影响,这与辛弃疾长期闲居、心境同陶渊明、白居易相似有密切关系。第三,辛诗是典型的宋诗,其中表现了浓厚的人文气息,这从其理性的思辨色彩、大量用典的创作方法、广泛运用江西诗法等方面,均可看出端倪。因此,重新审视辛弃疾诗歌,可以有很多新的认识。
[1] 吴慧娟.论稼轩诗的艺术渊源与其宋诗风调[J].文学遗产,2007,(1).
[2] 邓广铭.辛稼轩诗文钞存[M].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
[3] 谢保成.《永乐大典》的价值、流传与利用[A].《永乐大典》编纂600周年国际研讨会论文集[C].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
[4] 袁行霈.中国文学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
[5] 邵雍著,郭彧整理.伊川击壤集[M].北京:中华书局,2013.
[6] 钱穆.理学六家诗钞[M].北京:九州出版社,2014年.
[7] 何晏注,邢昺疏.论语注疏[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8] 李剑锋.元前陶渊明接受史[M].济南:齐鲁书社2002.
[9] 张再林.唐宋士风与词风研究:以白居易、苏轼为中心[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10] 郭绍虞.沧浪诗话校释[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
[11] 钱钟书.谈艺录[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
[12] 钱钟书.宋诗选注[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
[13] 邓小军师.论宋诗[J].文史哲,1989,(2).
[14] 莫砺锋.江西诗派研究[M].济南:齐鲁书社,1986.
[15] 仇兆鳌.杜诗详注[M].北京:中华书局,19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