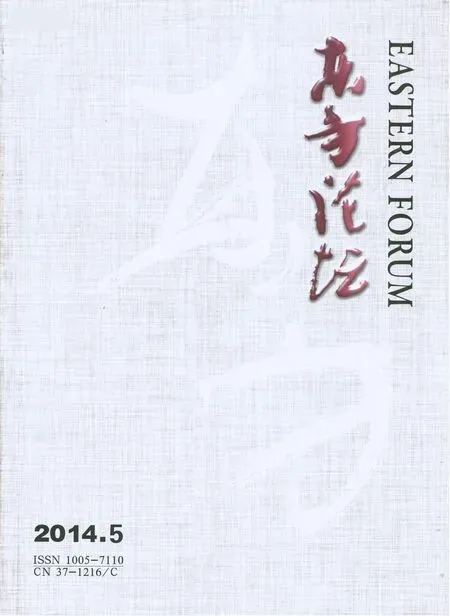贝克特小说三部曲中的身体叙事
宋玲玲 曾艳兵
(中国人民大学 文学院,北京 100872)
自20世纪下半叶以来,身体已经成为很多学科和媒体日渐关注的焦点。W.A.伊文指出,“把身体放在争论的中心不是时尚,而是迫切的需要。身体正被艺术家和作家重新评价和思考,是因为它正被科学家和工程师重新调整和建构。”①参见丹尼· 卡瓦拉罗《文化理论关键词》,张卫东、张生、赵顺宏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04 页。英国当代著名理论家伊格尔顿则说:“后现代的主体,和它的笛卡尔前辈不同,它的身体是它的身份所固有的。的确,从巴赫金到妓院,从利奥塔到紧身衣,身体变成了后现代思想关注最多的事物之一。受伤的肢体,遭难的躯干,被炫耀的或者被囚禁的身体,受压抑的或者有欲望的身体:书店里充斥着这样一些东西,值得我们自问这究竟是为什么。”[1](P69)的确,近年来身体已成为人文领域的核心话题,罗兰·巴特、福柯、德勒兹、利奥塔、德里达对身体问题的关注都已成为他们理论的焦点之一。而让德勒兹、福柯、德里达钦佩不已的爱尔兰作家塞缪尔·贝克特早已对身体问题有自己的思考和设问。日本著名的贝克特研究专家田尻芳树就认为在贝克特的小说中,对身体的言说非常普遍。他认为:“贝克特的作品经常使我们跌入一个充斥着身体感觉的世界,这种感觉根据身体不受控制的流动。身体部件和不稳定的身体表面混乱的交互作用。”[2](P12)然而,目前国内的贝克特研究中,身体问题还没有受到足够的关注和重视。有鉴于此,本文拟以贝克特的代表作小说三部曲(《莫洛伊》《马龙之死》《无法称呼的人》)为中心,对贝克特文本中的身体问题进行探讨和解析。
一、承载记忆符码的身体
在人类的文明进程中,身体忠实得承载了人类的记忆,历史是身体的历史,历史将它的痕迹铭刻在身体上。正如福柯所言“身体是来源的处所,历史事件纷纷展示在身体上,他们的冲突和对抗都铭写在身体上,可以在身体上面发现过去事件的烙印。”“历史的变迁可以在身体上找到痕迹,它在身体上刻下烙印,身体既是对‘我思’‘意识’的消解,又是对历史事件的铭写。”[3](P171)贝克特的三部曲中的主人公(《莫洛伊》的主人公莫洛伊、莫郎,《马龙之死》的主人公马龙,《无法称呼的人》的主人公“无法称呼的人”)的身体都经历了一个弱化的过程,他们显得虚弱不堪,而且随着三部曲的发展,主人公的身体越来越糟。但是,主人公的回忆中总夹杂着暴力的镜头,他们津津乐道的回忆着身体曾有过的辉煌。他们的身体见证着人类在二十世纪的遭遇,亲历着贝克特自己的荒诞经历。
莫洛伊踏上寻母之路的起始虽然一条腿已经僵硬,他还能骑自行车,但当他摆脱了卢斯重新出发寻母之时,他便骑不动自行车了,他的另一条腿也开始变硬,分不清楚哪条是好腿,哪条是坏腿了,最后他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差,哮喘病、尿毒症都发作了,虚弱不堪的莫洛伊只能闭着眼借着手腕的力量爬行。莫朗原先的生活是有秩序的,他的身体也是健康的、强悍的,但当他踏上寻找莫洛伊之旅后,身体状况便是江河日下,先是发现自己的腿痛发作,实在无法继续走下去的莫朗,让儿子去买了一辆二手的自行车,他坐着后车座到了莫洛伊的家乡——巴里巴,但在与儿子发生了一次激烈的争吵后,儿子带着所有的物品走了。没有了食物的莫朗身体更加虚弱,随身带的雨伞也无力支持他平衡,他胃痉挛、腹部胀气,最后经过了一整个冬天,他爬着回到了一切都面目全非的家。莫洛伊、莫朗还可以称他们为流浪汉,到了马龙那里情况显然更糟了。故事开篇马龙就呆在不知是什么地方的一张床上,他赤裸的盖着白被单,只有一根棍子能不时的翻动一下堆在地上的物品,把放在门口桌子上的食物勾给自己吃,马龙在一边编着小说一边等死,他听力下降、记忆力消退、失音、感觉缺氧,最后和他编造的故事中的人物一起走向了死亡。在“无法称呼的人”那里,“无法称呼的人”完全失去了空间的依傍,“坐在某个模糊的、黑暗的空间里,空间的边界他既看不见也摸不着。”[4](P245)更多的时候他只是一种飘渺、不得不继续的声音,而从外形上看也已经变成真正的非人了。作者以第一人称写道:
我没有胡子,也没有头发,我的两个肩膀上所支架起来的,是一个光溜溜的大圆球,上面没有什么线条,除了眼睛,就连眼睛也只剩下眼眶了。且不说我那明显处在远处的手心和脚掌,当然我还无法摆脱那些东西,我倒是很愿意给我自己一种鸡蛋的形状。[5](P307)
英国著名人类学家玛丽·道格拉斯认为身体是一个象征系统。“对道格拉斯来说,身体是一个整体社会的隐喻,因此身体中的疾病也仅仅是社会失范的一个象征反应,稳定性的身体也就是社会组织和社会关系的隐喻。我们对社会关系中的风险和不稳定性的观念性焦虑因此可以通过身体秩序理论得到说明。纯洁性和秩序,亵渎和神圣,并不位于现象或实践的本质中,而是位于它们和我们对某种社会总体性所具备的观念的关系中。亵渎因而是分类关系系统内部的失范。”[6](P18)贝克特小说三部曲中主人公身体的弱化、无能状态正是贝克特对刚刚经历过的二战社会状况的一种隐喻。
主人公破碎的身体,根本无法自然游牧、外溢扩张,他们备受饥饿、战争、疾病的肆虐而痛苦不堪,他们总是以拯救、追寻开始,却总是以失败、死亡告终,无论是漫游、写作还是喋喋不休的身体最后都难逃死亡的魔爪。经历过二次世界大战的贝克特恐怕永远不会忘记奥斯维辛的梦魇,眼见他的犹太朋友被凶残的纳粹一批批送入集中营,战火吞噬着无辜百姓的生命,自己除了逃亡之外却什么也做不了。作为一个孤独的思考者,贝克特对二战进行了深刻的反思。是什么导致人类如此的疯狂,那自诩为“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的人类,他那高贵的理性都到了哪里去了,对同类怎会如此的残忍?贝克特放弃了对统一理性的信仰,他让身体自己讲述自己的经历。身体无法逃离人类主体经验对社会的真实参与情境,贝克特让身体告诉我们最真实的社会存在状况。我们在贝克特的三部曲中看到了身体在现代社会中承受的痛苦、磨难,它的虚弱不堪,如此无能的身体自然无法承担起拯救的使命,它只能选择沉沦来抵抗自己的无力、无能。莫洛伊、莫朗、马龙、“无法称呼的人”,他们的身体状况清晰的宣判了这个偏离秩序、混乱无序的社会的行将消隐。
三部曲中充满了抵牾、矛盾,主人公们的身体每况愈下、无所作为,但是它们却不时地逞凶作恶,对他者施以暴力,无缘无故的剥夺他人的生存权利,并以此为傲。莫洛伊、莫朗都在森林里用拐杖袭击过陌生人。马龙不仅让自己编造的人物勒缪埃尔用斧头把两个船员砍死了,他自己更是津津有味的回忆他的暴力经历:
我杀死过多少人,往脑袋上猛击或是放火烧死。被问得如此措手不及,我只想起四个,陌生人,我从不认识任何人。……这里面还有老人,我像是在伦敦,你瞧瞧,又是伦敦,我用他的剃刀割断了他的喉咙。这就是五个了。[7](P237)
就连“无法称呼的人”的毫无逻辑性的言说中也夹杂着他把一条狗打得灵魂出窍的经历。贝克特让我们经历了一场身体的假面舞会,表面上身体充满着交流的冲动与力量,但实际上除了孤独,我们看到的还是孤独,身体自己无法统摄自身(主人公都在写作,但写的什么他自己也弄不明白),也无法和他者共存。正如法国著名哲学家南希所说“两个身体不可能同时占领同一个空间。你和我不可能同时既在我说话的空间里又在你听话的空间里”。[8](P359)这意味着身体的绝对孤独,无法交流。我们无法捕捉别人的身体,甚至对自己的身体也是陌生的。暴力在这里成了一种期许的交流,但很显然这种交流必然走向失败。把身体作为铭写的舞台,刻下贝克特对社会的感受。1939年1月7日清晨,贝克特在巴黎街头无缘无故地被一名男妓刺伤了左胸,险些丧命。事后贝克特曾与那名男妓进行了友好的交谈,当贝克特问他,是什么原因使他刺伤了自己,那名刺客竟然耸耸肩,冷淡的说道:“我不知道,先生。”从这个层面来说,贝克特的三部曲成了他的自述传,同样揭示出身体的脆弱与孤独。
在三部曲中,一方面身体如此虚弱不堪、苟延残喘;另一方面它又如此随意任意地剥夺他者的生存权。身体以它的生死盛衰揭露了现实社会的真实状况。在这个荒诞不经的社会中最真实的感受到荒诞、混乱的是身体,因为他已经摆脱了理性的束缚,可以自由地,不加粉饰地,听任本能地发出自己的呼喊。但是身体没有给人留下光明的幻影,它处处受制,随时都会遇到无法排遣的危险,同时,身体也不甘沉寂,不时的逞威会带来无法预计的灾难。身体陷入无法拯救的渊薮中,人类一直高扬的理性正是身体悲剧的元凶,理性的张扬诱导出了人类无法穷尽的欲望,理性对于身体的灾难承担着不可推卸的责任,也正因为如此,一直把理性视为高于一切的形而上主体走向了解体。身体虽然仍在上演着一幕幕悲剧,但它开始发出声音,通过那些有预见的作家,通过贝克特的小说三部曲。由此我们似乎理解了小说家的“别有用心”。
二、权力监视、压制的身体
福柯热衷于对身体与权力的关系进行讨论,在福柯看来,权力将监视、规训的能量在身体上发挥至极致,使得身体在它的控制下完全归服。在现代社会权力与身体达到了貌似和谐统一的状态,但实际上权力改头换面,以更加多样化、机制化的方式加强了对身体的控制。血粼粼的刑罚被微观的、无处不在的监视所取代,身体更加无处可藏,处处被动。贝克特以他作为作家敏感,很快便发现了这种监视权力对私人生活的冒犯。他讨厌别人窥视他的生活,尤其是私生活。甚至对人们的关注也不领情,正当人们为他的75 岁生日庆典忙碌时,他在给好朋友的信中却抱怨道:“我担心生命已经走到了尽头……在巴黎,人们小题大做,把我的生日庆典搞得像百年诞辰一样轰轰烈烈。我要在生日庆典隆重举行的那一天悄然离去。去哪里,我自己也不清楚。也许会去中国的长城吧!我要躲在长城背后,直到大浪淘尽为止。”[9](P9)在三部曲中贝克特对监视颇有微词,他的主人公身体总是被监视,权力附着其上,身体备受蹂躏,被宰制、改造、矫正和规范化,因此,身体显得那样的悲观、被动、呆滞。
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提到了边沁的全景敞视监狱,中心的瞭望塔可以将囚禁者的行为尽收眼底,而被监视者却无法了解到监视者的情况。在《莫洛伊》中莫朗与尤蒂的关系与此颇为相似。尤蒂处在高处,无所不在,他给莫朗下达命令,指挥莫朗的行动。但对尤蒂的情况莫朗却一无所知,莫朗想通过发问改变这种状况,但他的努力没有什么效果,最后还是不得不屈服于尤蒂。“显而易见,莫朗居于其中的监视世界是一个秩序井然的等级制世界,即使是其等级制隐藏在视线之外。”[10](P53)作为等级秩序中的一员,他无法冲破监视网络给他的压力。莫朗是被监视者,同时他也被纳入权力的网络中,成为监视者的一员,他监视儿子、女仆的一举一动,诸如:儿子是否去做礼拜,寻找莫洛伊的旅途中带什么物品、不带什么物品,是否吃饭,真生病还是假生病;女仆是否偷喝酒窖里的酒,几时几分做什么饭,是否合乎要求等。莫朗表现出了作为一个监视者应有的权威性。监视的网络在这个所谓规范的社会就是这么一级一级的传承下去的,展示了它无所不在的权威性。但莫朗并不想成为一个权威者,他更希望找到莫洛伊并且成为他。与莫朗不同,莫洛伊的世界是和混乱、偶然、虚弱联系在一起的,也正因如此,他成功的逃离了规训权力的宰制(警察、卢斯、农夫对莫洛伊的监视不起任何作用)。但莫朗的逃离是以失去身体为代价的,作为叛逆者他受到了规训权力的惩罚。
监视通过他自己的权力运行系统统治着社会的每个细胞,要么服从它,成为权力的顺民,从而被改造;要么造反,不听从指挥,让规训权力发挥作用。现代社会正是通过种种精致的规训技巧将暴烈的身体转化为有用而顺从的工具。在社会历史中,身体始终是各种权力的追逐目标,各种各样的权力技术都是围绕身体展开追逐的,身体最终无法逃离权力的掌控。贝克特显然意识到了这一点,但是作为一名追求自由并且目睹过权力疯狂的知识分子,贝克特让他的主人公以身体的毁灭为代价,换回了权力符码的失效。
在贝克特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莫非》里,同名主人公就认为精神病院的疯子比所谓的健康人更接近真理,他们在疯癫之中具备了正常人难以企及的智慧。《马龙之死》中马龙虚构的第二个故事的主人公麦克曼,同样是生活在精神病院的疯子,从他身上我们能否也能够得出他离真理很近的结论呢?实际上,倒并不是疯子本身有多么的高明,而是因为疯子的生命按照自身的符码行事,与主流社会的规范格格不入,“精神分裂症患者有其自己的坐标,可以任意摆正自己的位置,因为他首先可以处置的就是他自己的记录语码,这种语码与社会语码不相符,如果相符的话也只是为了戏仿它。谵妄和欲望的语码具有一种非凡的流动性。可以说,精神分裂症患者从一种语码过渡到另一种语码,故意打乱所有语码,根据向他提出的问题迅速从一个转向另一个,而对这些问题的解释从来不是相同的,得出的谱系从来不是相同的,记录同一件事的方式也从来不是相同的。”[11](P118)正因如此,精神分裂症患者是被主流意识形态遗弃的边缘人,但是主流社会决不会放任异己的疯子起来造反,破坏自己的规范。所以权力就会规训这些不按正常秩序行事的疯子的身体。在《疯癫与文明》中,福柯认为17世纪对疯人的紧闭实际上是对身体的禁闭,权力束缚着身体,让身体的狂野能量得到驯化。精神病院野蛮地将疯癫紧闭起来。身体成为规训、惩罚的对象。疯癫是异己的、反常的力量,受到排斥。个体身体最原初的神圣经验在规训中消失。通过监视来改造行为个体,将暴烈的个体变成为驯服的工具。这样才符合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对秩序的需要。因此,现代社会决不能让麦克曼自由行动,他被束缚在精神病院中,他的行为必须经过规训权力的改造,“规训权利主要是靠监视、规范化裁决和检查发挥作用的,将个人对象化,生产了个人的知识,间接的生产了个人。监视权利的存在是永久性地存在,无法摆脱,他把身体束缚在某种秩序中,确定身体的具体位置。”[3](P179)在《马龙之死》的文本中,我们总是能感到在文本的背后有一双凝视的眼睛,麦克曼在凝视的眼睛的监视、检查下安排自己的身体活动。开始的时候他只能呆在自己的屋子里,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他可以在规定的范围之内出去走走,他穿什么衣服,吃什么饭,有什么行动都是经过权力精密安排的,必须被强制执行。
“无法称呼的人”更是个地地道道的精神病患者,他喋喋不休,自说自话。当然理性不会允许这种异类的存在,它要将疯癫控制在自己的拘押范围之内。因此,我们看到在《无法称呼的人》的文本中,混乱话语中夹杂着对权力逞威的记忆,窥视、监视、惩罚的字眼更是常常出现在文本中,在“我”(不知是真实还是梦境里)对回家的记忆中,给人印象最深刻的还是周围人,包括妻子、亲人对“我”的监视。詹姆斯·阿克森认为:“《无法称呼的人》表现的是地狱的幻影,自我永远被定义的痛楚。”[13](P140)这也深刻地反映了无法称呼的人处在无所不在的监视中,失去自我的无奈。即使“无法称呼的人”只是一种遁去的声音,他也无法自由自在地按自我编码行事。贝克特是个崇尚自由的作家,他讨厌权力以任何形式侵犯个人的自由。贝克特对他的家乡爱尔兰的态度历来引起人们的好奇,不知道他缘何终身定居法国。当然,他与母亲的不合是一个重要的原因,但爱尔兰的政治气氛令他深恶痛绝,想方设法避而远之是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他不喜欢爱尔兰当时极端严格的书报检查制度,也不赞许由叶芝领军的具有很强的民族色彩的“凯尔特的曙光运动”。因为凡此种种破坏了作家对自由的坚守,这使贝克特感觉自己处在一种被监视的不安全感中,所以,他别无选择,只能逃离。
贝克特在小说中对身体的悲惨境遇充满了人道主义的同情,对监视权利的存在充满愤怒。贝克特的三部曲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窗口,让我们了解到处于社会边缘的人(疯子、罪犯、病人等等)的经历,让我们看到权力机器如何驯服身体,身体如何成为权力的施压对象。当各种权力围绕身体展开追逐时,身体的历史也就成了受难的历史。我们生存的世界应该更宽容的接受差异的存在,允许身体在千高原上自由的游牧,而不是随意剥夺别他者的身体的生存权力。
三、生命之轻的身体
福柯在其最后一本著作《性经验史》中集中探讨了性在历史中的遭遇,它的无可替代的作用。性作为身体延续的本源,其实无论曾遭遇过什么样的尴尬与不公,它始终是人类无法回避的问题。当年的赫拉克勒斯在十字路口面对两个绝色女子徘徊不前,不知如何抉择,最终他还是选择了代表美德的阿雷特,放弃了淫荡的卡吉娅,赫拉克勒斯的选择成为古老的道德律令,千百年来备受推崇。在中世纪的漫长岁月里,性更是与邪恶等同,备受压抑。文艺复兴以后,性开始以革命者的姿态出现,在劳伦斯的小说中理想的性更是拯疗社会、医治人心的良医。如今的社会,性已冲破藩篱,无所不在,性的表演成为了一场闹剧。当性和身体无限接近,甚至身体只剩下性的时候,性并没有必要和别的物质争抢生存空间,它可以轻松自在、毫不紧张,但同时它也变得毫无负重感。没有了内在性的性,成了一个轻松的能指、没有灵魂的幽灵,漫无目的,四处飘荡。在聚光灯下,性迷失在性话语的丛林中,虽然它统治了身体,但它成了身体的祭坛。贝克特的小说探讨了性在现代社会中的遭际与命运。
莫洛伊回忆了他与三个女性即卢斯(露丝)、露特(艾迪特)以及他母亲的交往,他弄不清楚她们准确的名字,甚至分不清她们是男是女。唯一留下印象的是他们曾经像动物似的本能的发泄欲望。尤其是他与自己母亲的关系很暧昧,他既把母亲当成妓女,又把返归母亲的子宫看成是解脱之道。
我母亲很愿意见到我,就是说她很愿意接待我,因为他什么也看不见的日子已经有老长时间了。我将尽力平静地讲述。我们太老了,她和我,她有我的时候是那么年轻,这就使我们像一对老伙伴,没有性别,没有亲缘,却有着同样的回忆,同样的怨恨,同样的期望。她从来不叫我儿子,再说我也受不了,而叫我唐,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不叫唐。唐可能是我父亲的名字,对,她可能把我当做我父亲了。[5](P17)
莫洛伊苦苦追寻,只想返回母亲的子宫,追寻身体的真正本源,但很显然这个任务永远都不可能实现。在一切混乱无序中,我们所看到的只是莫洛伊与母亲摆脱了伦理的束缚的交往,听任身体自由游走,将文本引向身体的无限可能性,读者借助文本得到的只是身体的狂欢,没有了古典意义上身体在卑微处的忍辱负重。俄狄浦斯杀父娶母原非本意,只是命运弄人,在不知情的情况下犯了自己不能原谅自己的错误,于是他刺瞎双眼自我流放。莫洛伊痛恨母亲把他扔进这个世界,对在母亲子宫的美好记忆念念不忘,一路艰辛寻找母亲,而他的记忆里一再重复的是和母亲的不正当关系,莫洛伊的返回更像是消解伦理的颠覆之旅,丧失了崇高性,在消解了历史道德时,人类共识性的道德良知也被彻底唾弃。正如肯尼迪所评论的“这个关于母亲形象的‘高尚主题’被降至‘卑下主题’的底部,表现的竟是离奇古怪、荒唐可笑的琐事”。[13](P110)再看看莫洛伊与卢斯(露丝)、露特(艾迪特)的交往,性更是没了禁忌,没了压力,统治起了整个身体。身体主体也因此被赋予了更多本能主义、享乐主义的内涵。在当今社会身体欲望的放纵已成为世俗潮流,性没有丝毫庄严崇高可言。
在马龙之死中,年老的马龙编写故事证明自己的存在,在颇有些自传色彩的故事中性仍旧是个绕不开的话题。麦克曼和他的女护工的爱情在叙述中占有着很大的篇幅。但我们看不到任何爱情的神圣性,他们就像两个小丑在舞台上表演着闹剧,贝克特用黑色幽默的调侃笔调写了性的沦落:
她(摩尔)使劲地张开颌骨,用一只手的食指和大拇指把又厚又肥的下唇拉向长着细胡须毛的下巴,在清一色的下齿龈中,独独地突兀着一颗长长的,黄黄的,牙根毕露的犬牙,它被雕琢成著名的基督在十字架上殉难的样子,好像是用牙钻钻的。我每天洗刷它五次,她说道,每一次都为了他的一处伤口。她用空着的那只手的食指触摸了它一下。它动了,她说,我真害怕不知哪天早晨醒来时会发现把它吞到肚子里了,还是把它拔了比较好。她松开下唇,只听啪的一响,好像棒槌敲击什么的声音,那片嘴唇就回复了原位。这一小插曲给麦克曼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促使他在感情生活中朝摩尔大大跃进了一步。到后来,等他将舌头伸进她的口中,并自由自在地在她的齿龈上滑来滑去,恰似信步于闲庭之中时,这颗耶稣受难十字架的破牙对那亲吻的快乐肯定不会感到陌生。但是,除了这些个无害的佐药之外,还有什么是爱情吗?[5](P265)
贝克特说:“对我来说,信仰是一种无聊的感觉,因此,我放弃了它。”[14](P14)贝克特用亵神式的幽默方式吊销了宗教的严肃性。十字架的基督形象是殉道者对真理的无限追逐的隐喻,是对拯救的幻想性设定。但贝克特把它转化成身体的无限隐喻,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圣子向我们宣告身体无法逃避的道德律令。贝克特把性同宗教掺杂在一起,宗教的神圣性不在,性的神秘性亦不存。在西方宗教传统中,性始终是信仰的死敌,正是为了追逐信仰的纯粹彻底,性遭到彻底的放逐。但客观上,正因为如此,性常常能挖掘出人的好奇心、神秘体验。不过,贝克特却用廉价的性颠覆了宗教的崇高性,换句话说,性摆脱了宗教的压制,可以自由的伸展手脚了,它不用再躲在角落里自哀自怜了,可以在光天化日之下大行其道了。我们不知道应该为性的畅通无阻而喝彩,还是为宗教的无所作为而悲哀?尼采的那句“上帝死了”又回响起来了,正如南希所言:“上帝的身体就是人自身的身体:这个身体是上帝为自己而造的,以‘油灰’象征着他的整个创造。‘在眼中有火;在形成言语的口中有气;在触及的手中有土;在生殖器中有水。’作为上帝自身的形象,人的身体以人身体相似于他,而且显现在位格中的创造力的权利、美的光辉及其荣耀的庙宇和颂歌。随着上帝之死,我们也失去了这个荣耀的身体,这个崇高的身体。”[8](P361)
在《无法称呼的人》中,马霍德没有了完整的形体,只剩下一个“上面满是脓包和绿头苍蝇的”所谓脑袋,但即使这样他还是很欣喜自己“没有了能动的四肢,除了阳物”,还幻想着女店老板多看他一眼。在这里,主人公的身体是残缺的,无法负载灵魂,它甚至呈现了身体原初的意象——尸体,它只是一个世界的残留物,而没有任何意义。尽管如此,性作为最后拯救的幻想物,成了主人公的救命稻草。但是性是否真有这个能力是值得怀疑的,贝克特显然并不看好它。性是身体问题的核心内容,而当今的社会色情肆意泛滥,原罪观念、性欲冲动的禁忌已然消失,性不再承担宗教、伦理的重负,漂浮在空中成为生命不能承受之轻,这种失重的状态导致性变得空虚贫乏、了无生气。性成为动物般的、自然主义的物质生活的一部分,失去最后神秘性的性成为赤裸裸的性欲冲动。
自柏拉图开始,身体被认为是灵魂的反面,长期受到压制,要达到灵魂的纯洁,必须丢弃身体的束缚。客观而言,正是在对身体的压制中,身体以一种不洁而混乱的方式,成为一种与精神、灵魂对立的冷眼旁观的他者。而自笛卡尔以来,在对知识、真理的无限追寻中,去智性的身体受到了完全的漠视,甚至失去了在场的资格,身体得到了完全的放逐。在尼采那里身体得到了解放,成为了代替上帝的拯救者,身体存在的应有权利以及审美价值得到了肯定。但不幸的是,在当代消费语境下身体被赋予了更多的本能主义、享乐主义的因素,身体欲望主要是性欲望的放纵,这成为大众文化的一种时尚。在尼采那里身体欲望还服从于古希腊的崇高庄严的情感,福柯则把对身体的规训与压抑看作是对文明社会秩序的一种控诉与批判。如今,我们所面对的现实是经济全球化浪潮使身体的欲望叙事泛滥成灾,完全失去了批判力量。放纵的身体美学无助于人类对美好社会图景的描绘。
柏拉图在《斐多篇》中记录了西方文化中第一个伟大的死亡事件——苏格拉底之死,苏格拉底之所以会选择从容赴死是因为他坚信身体的死亡会换来灵魂的永生。哲学发展到今天,身体已成为“分裂的自我中心”,回归本源,人类剩下的只有身体。我们很难设想今天的“苏格拉底”还会做出如此的选择。贝克特小说三部曲中向我们展示了身体的破碎、无奈,但是很显然贝克特没有拒绝意义,身体始终以意义的在场的姿态出现。
以上我只是从灾难、权力、伦理视角对贝克特小说三部曲中的身体问题进行了分析和论述,其实从性别、经济、语言、宗教等其他维度来论说贝克特的身体,也会有很多新的发现。当代著名哲学家德勒兹在自己的代表作《反俄狄浦斯》中一直在引用贝克特的小说三部曲为自己的“无器官身体”理论作注脚,这似乎表明,贝克特的作品和西方哲学的“身体转向”已经交融在一起。
[1] 特里·伊格尔顿.后现代主义的幻象[M].华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2] Yoshiki Tajiri.Samuel Beckett and the Prosthetic Body:the organs and senses in modernism.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07.
[3] 汪民安.福柯的界限[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4] 戴维·洛奇.小说的艺术[M].王峻岩等译.北京:作家出版社,1998.
[5] Samuel Beckett,Molloy,Malone Dies,The Unnamable[M].London:John Calder1959.
[6] 汪民安,陈永国编.后身体、权利和生命政治学[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
[7] Samuel Beckett.Molloy,Malone Dies,The Unnamable[M].London:John Calder1959.
[8] 让-吕克·南希.解构的共通体[M].夏可君编校.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7.
[9] [英]詹姆斯·诺尔森.贝克特肖像[M].王绍祥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
[10] Anthony Uhlmann.Beckett and Post structuralism[M].Londo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9.
[11] 吉尔·德勒兹.无器官的身体[A].陈永国译.汪民安,陈永国编.后身体、权利和生命政治学[C].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
[12] James Acheson.Samuel Beckett’s Artistic Theory and Practice[M].London:Macmillan Press Ltd,1997.
[13] Andrew k.kennedy.Samuel Beckett[M].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9.
[14] 卢永茂等.贝克特小说研究[M].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