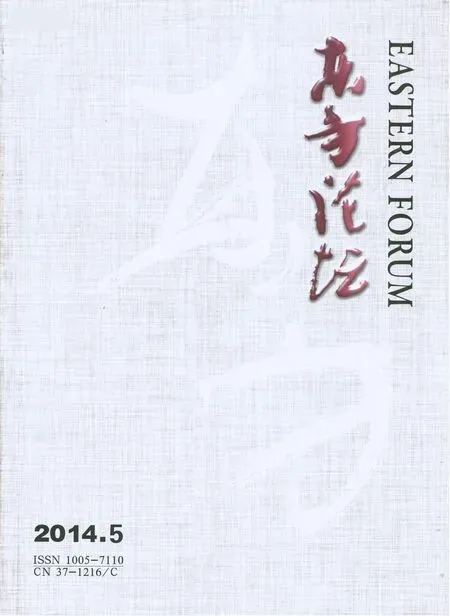论拜伦诗歌的讽刺批判精神
秦丽萍
(青岛大学 外语学院,山东 青岛 266071)
19世纪前半叶,在英国出现了一个影响深远的浪漫主义文学运动,它有两个不同的流派,一是“湖畔派”,其代表人物是华兹华斯、柯勒律治等,他们的诗歌以山川草木和乡土田园为歌咏对象,抒发对大自然的热爱和尊崇,以此逃避现实,并曲折地表达对污秽的社会现实的不满;一是“摩罗诗派”,代表人物有拜伦和雪莱,他们政治热情高涨,关注现实,批判现实,以一种反抗的姿态向社会挑战。王佐良先生说:“华兹华斯和柯尔律治是浪漫主义的创始者,拜伦使浪漫主义的影响遍及全世界,雪莱透过浪漫主义前瞻大同世界,但他们在吸收前人精华和影响后人诗艺上,作用都不及济慈。”[1]拜伦是英国浪漫主义诗史上最耀眼的一颗,他的出现,把英国浪漫主义诗歌推向了高峰。拜伦以诗歌为武器,对当时黑暗的社会现实进行批判和嘲讽,高扬人的主观精神和个性自由;拜伦在当时欧洲人的精神生活中产生了非同凡响的影响,以至于改变着(欧洲)“社会结构、价值判断标准及文化面貌”(罗素语)。
一
拜伦的诗歌创作其思想和风格有一个发展、演变的过程。
1807年拜伦的处女诗集《懒散的时刻》发表,标志着拜伦正式登上文坛,自此至1816年流亡意大利是其创作的第一个时期。这部诗集主要是爱情诗,不是很成熟,但是其诗作激情洋溢、思想大胆的诗风已初露端倪。因为反击对该诗集的恶评,拜伦又创作了长诗《英格兰诗人和苏格兰评论家》,这首诗初步显示出其诗歌强烈的批判倾向和讽刺锋芒。这篇驳论诗的出现是英国文学和美学思想史上的重大事件,它掀起了文学或文学批评生活的一个浪潮,同时也开辟了一种传统;自此以后,拜伦将英国浪漫主义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
拜伦于1809 到1811年间游历了南欧、西亚等国家,这段游历改变了拜伦对世界的看法,也加深了他对社会尤其是底层民众的认识。以这段经历为主,拜伦写作了长诗《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的头两章。这是拜伦最重要的作品之一,初步奠定了拜伦作为伟大诗人的文学史地位。长诗以叙事为主,兼以抒情和议论,拜伦诗歌的艺术风格在长诗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长诗将自然风光和风土人情尽收眼底,充满了异域色彩;同时,地中海沿岸如希腊等国家人民寻求民族解放独立、追求自由平等的强烈诉求,以及他们为此所进行的反抗和斗争,在长诗中第一次得到了反映,这不仅极大地促进了这些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而且它成为拜伦以后诗歌作品的一个重要倾向。更重要的是,长诗塑造了一个孤独、忧郁、悲观的所谓“拜伦式英雄”——哈洛尔德这一拜伦诗歌最重要的浪漫主义人物形象,他是拜伦诗歌人物形象系列的最重要代表之一,在他身上体现了拜伦的许多思想特征和精神特征。这是一个青年知识者,他厌倦了目前穷奢极欲百无聊赖的生活,他不愿与丑恶的现实同流合污。因此,他开始四处漂泊,这既是一种逃避,也是一种寻找,寻找简单纯朴的东西,寻找没有被西方近代资本主义文明污染侵蚀的地方,地中海少数民族及其人民善良质朴的品行深深地吸引了他的目光,在那里,似乎可以托付自己的情感。然而走得越远,看得越多,诗人越是失望,一切都打上了资本主义的印记,哈罗尔德于是绝望,忧郁悲戚,不能自己,“忧郁”是哈罗尔德这类拜伦式英雄最外在的也是最基本的特征。他痛感人心不古,知音难觅,到头来“旅人的心是冰冷的,旅人的眼是漠然的”,悒郁伤感终未遣散。这个形象具有深刻的现实内容和社会内涵,是19世纪初到拿破仑战争时期西方许多小资产阶级知识者意识特征和情感状态的集中体现。他们不满现实,但找不到出路;不愿与上流社会同流合污,却也不能和人民群众一起斗争,因此陷入悲观绝望之中。
1813年以后,至1816年,拜伦创作了一组“东方故事诗”,含《异教徒》 《阿比道斯新娘》《海盗》《莱拉》《柯林斯的围攻》《巴里西纳》等六部,这组诗作充满了传奇色彩。它们题材新颖,充满浪漫情调,异域风情,加上狂放的热情,拜伦浪漫主义艺术风格日臻成熟。主人公不是流放者就是流浪汉,有的没有家,像《异教徒》中的威尼斯人;有的是强人,如《海盗》中的康拉德和《阿比道斯新娘》中的塞里姆;有的是犯上者甚至是叛逆,像《莱拉》中的莱拉、《柯林斯的围攻》中的阿尔普。这些诗作中的人物形象大都是一些叛逆者,个个骁勇善战,愤世嫉俗,而且充满了冒险精神。同时,他们往往自视甚高,以品行高洁而睥睨一切;对于爱情,他(她)们忠贞不渝,愿意为爱情献出生命。然而,他们生不逢时,在与社会的对抗中,他们是失败者和牺牲品。这些形象发展了哈洛尔德所体现的拜伦主义——失望忧郁的情绪和个人式反抗,而成为典型的“拜伦式英雄”,即:高傲而倔强,忧郁而孤独,神秘而痛苦,与社会格格不入而进行彻底反抗的叛逆的英雄性格,——凡这些,均烙印着拜伦思想个性气质的深刻印记。在以后的诗剧《曼弗雷德》和《该隐》等作品中,该性格还有所继续和发展。
拜伦的叛逆态度为上流社会所不容,于是于1816年愤然离开英国,先侨居端士,后到意大利,开始了第二个时期即意大利时期的创作。流亡生涯加强了诗人的孤独与空虚,以至精神濒临危机。忧郁、悲观乃至绝望的情绪笼罩于这时期的作品中。例如自传体的长诗《梦》,苍凉寂寥之感令人压抑;《黑暗》描写太阳熄灭、沦入黑暗大地的人类逐渐死亡的景象,几乎算是诗人最阴郁的作品了。除了自身遭遇的不公正,这所谓“世界悲哀”的主题同时也反映了欧洲革命处于低潮的时代氛围在诗人心灵上的折光。然而拜伦并未就此放弃和减弱他为自由引亢高歌的理想风骨,《锡隆的囚徒》和《曼弗雷德》便是写照。前者是篇极悲壮的叙事长诗,讴歌为自由而殒身的历史英雄及其精神。后者被作者称为哲理剧,表达了诗人对于现实、人生和世界的思考,遗世而立,一种孤傲和挑战的精神仍然是这些诗作的底色。
意大利时期是从1816年10月开始的,这是拜伦诗歌创作的鼎盛时期,各种体裁的充满睿智和战斗精神的作品相继问世。最终完成《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的末两章,使这部杰作平添了更加成熟的思想和更加完整的形式;长诗《塔索的哀歌》《威尼斯颂》《但丁的预言》旨在激励处在异族压迫下的意大利人民的解放斗争;还有故事诗《别波》《马赛曲》《岛》等,尤其前者,揭示了生活的愉快和人生应有的享乐,对清教徒式的虚伪道德加以调侃,被认为是《唐璜》的准备;更有历史悲剧《马里诺·法利哀诺》 《两个弗斯卡利》 《沙达那帕拉斯》等,这些诗作或贯穿成熟的民主政治思想及反抗暴政的主题,或表现某种伊璧鸠鲁式的人生态度,均刻画了鲜明的人物形象;此外,尚有被作者称为神秘剧的《该隐》和《天与地》,前者取材圣经,却对原典作了相反的处理,把本是人神共诛的谋杀者塑造成反抗上帝权威的顶天立地的汉子,一个叱咤风云的拜伦式英雄。在这些诗作中,拜伦借助于各色主人公一直在探求这样一个问题:人生是什么,人活着的意义是什么?终于,在现实人生中,在自身的民族解放实践中拜伦把握到了生命的本质:“去到战场上,/把你的呼吸献出! /寻求一个战士的归宿吧”(《这一天我满三十六岁》);为被奴役被压迫民族的解放,为实现人类自由平等的大同理想:“为自由而战吧!”因此,他最终实现了,“为这番事业断头”。“本国既没有自由可争取,/为邻国的自由战斗!/去关心希腊、罗马的荣誉,/为这番事业断头!/为人类造福是豪迈的业绩,/报答常同样隆重,/为自由而战吧,在哪儿都可以!/饮弹,绞死,或受封!”(《本国既没有自由可争取》)对此,有研究者作了很深入的分析:这是拜伦对生命最高意义的追求——将生命的归宿、战士的归宿定位为为自由而战,饮弹,绞死,到战场上光荣而死!他视生命的价值是献身于伟大的扶助弱小的事业,尽自己最大的生命能量去照亮别人的黑暗生活,死得其所,使生命焕发光彩。这样的生死已经超脱了俗常的个体意义,而将生命的个体和群体、社会的利益连结在一起。为了他国的自由,甘冒生命的危险而勇敢前行,义无反顾,这种积极向死的精神不正是对死亡的超越、对生命意义的最高阐释与最好体现吗?拜伦这种超越生死的思想并不是一时的冲动,而是有着很深的积淀,可以说是一种献身情结。他在诗作中多次表达他寻求超越生命意义的思想,表达要为真理勇于牺牲,为了正义而死得其所的生命意识,印证他以舍生取义的向死方式实现生命的永恒意识。这种既蔑视死亡的威胁,又主动向死的人生态度,正是对死亡的一种超越,从这个层面开启生命的永恒意义,达到了永生。[2]
最后一个时期的代表巨作是《唐璜》。拜伦从1818年开始创作《唐璜》,这是一部长篇叙事诗,或可称为诗体小说,至1823年已成16000 余行,因为拜伦的去世诗作最终未能完成。它以深厚的思想容量和无与伦比的独特风格代表了浪漫主义时代欧洲诗歌创作的最高成就。主人公唐璜本是西班牙传说中的色鬼、恶棍,屡见于西方文学。但拜伦作了全新的处理:首先将时间往后拖了大约400年,把14世纪的老传说放在18世纪末叶;其次是改造了这个人物,将其写成一个天真、热情、善良的贵族青年。因与贵妇朱丽亚相爱而暴露,故去国远行。长诗就是以他整个的游踪及爱情历险为线索,加入作者本人的大量插话组成的宏伟诗篇。
今天看来,唐璜作为拜伦所有诗作中影响最深远的典型人物形象,对其内涵的发掘还远远不够。唐璜不能归在拜伦诗作任何一个形象系列中,而是他们的一个集合体;不仅如此,就形象本身而言,唐璜更是一个矛盾体,一个在情感形态、心灵世界和意识倾向方面都极其丰富复杂的人物形象,在根本意义上他体现了诗人拜伦对于人性及其繁复面貌的考察和认识,即借助于唐璜这一人物形象,拜伦把关于“人”的认识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在本质上,唐璜是一个天性崇高、情感真实的人,所以他不虚伪不做作,更无视清规戒律,相反对这一切天生厌恶和拒斥,唐璜的这一形象特征,是拜伦最为看重和推崇的,它体现了诗人对所谓近代文明之于人性扭曲的反叛。这也体现在情感尤其是爱情方面,与其前其他诗作的男主人公不同,唐璜不是一个既处处留情又朝三暮四的“情圣”,不仅全心全意,感情真挚,而且不管是哪一段感情他都认真对待,珍惜每一份感情,被迫离别或远行,总是使他对情人的思念倍加,痛苦万分,俨然一个古代的痴情骑士。他不再愤世嫉俗,像曼弗雷德那样,或者像该隐那样扮演一个横扫一切的挑战者,与他们相比,唐璜似乎缺少了某种英雄气概;但是唐璜绝不胆小懦弱,是一名战士,在战场上他不胆怯,勇往直前,遇到挑战或强敌,他不退缩,沉着勇敢,善于面对,只手搏斗,俨然一个久经沙场的勇士。然而,唐璜又的的确确是一个意志薄弱的人,缺乏主体意识,缺少信念,总是得过且过,随遇而安;尤其在各种情欲和诱惑面前,他往往变成了“俘虏”,放纵自己,于是放浪形骸,荒诞不经,在长诗中处处都是唐璜荒唐、古怪行为的记录或展示。——这时候,他与他的原型、那个传说中的唐璜貌似接近。唐璜形象最令人震撼之处在于:他又是一个具有强烈自我意识的人物:一方面随波逐流,纵欲荒唐,放纵自己,麻痹自己,一方面又鄙视自己的所作所为,痛恨自己,痛苦难耐,悔恨不已,唐璜又是一个痛苦和矛盾的灵魂,在这里,传达出的是诗人对社会的不满和对现实的反抗。——从这个意义上说,《唐璜》仍然是拜伦的“反抗文本”。
除唐璜外,长诗还刻画了一系列人物如贵族、海盗、苏丹、女王、阉臣、妃嫔、宫女、将军、议员、政客、学者……,有历史的过客,也有当代的名流;有的属艺术虚构,有的则实有其人。其中尤以妇女形象最为突出:伊内兹的装模作样,朱丽亚的热烈温柔,古尔佩霞兹的妖媚任性,卡萨林的娇奢淫逸,以及阿得玲那伶人般的做作,奥罗拉修女般的神秘,甚至宫娥罗拉的冶艳,嘉丁加的娇弱,杜杜的柔媚,都写得特色各具、神采飞扬。然而最令人难忘的,则是天真纯朴的希腊少女海甸,她“洋溢着绝无仅有的纯洁与诗意”,是一个天真无邪、只播撒爱的天使!他与唐璜牧歌式的相恋,是充满诗意的自然儿女之爱,“美丽如一个活的恋神”。诗人用光洁的笔调歌颂她的纯真,哀叹她的夭亡,对“使她纯洁的心儿最纯洁的血变成了眼泪”的悲剧爱情寄予深深的哀叹。
二
英国浪漫主义是一种思想运动,因而其内容是相当复杂的,其影响也不限于文学领域。在哲学渊源上,他们大都推崇法国思想家卢梭并深受其影响,强调效仿自然,返璞归真,这给他们的文学创作带来了注重情感的自然流露、不拘一格冲破陈规、纯朴清新的诗风,真实(truth)或情 感(emotion),个 性 化(individuality),想 象 力(imagination or fantasy),大自然(Nature),是他们最推崇并恪守的文学信条;在思想内容上,他们普遍抗拒日益扩散的工业化所带来的物质主义倾向,对社会现实或逃避,或不予合作,或干脆反抗彻底批判,这种对待现实的不同态度又把英国浪漫主义者分成了“消极的”和“积极的”两大派别(这是高尔基和苏联的分法,我们一直沿用)。后者政治热情高涨,关注现实,以宣传小册子和文学创作的方式深度介入欧洲大地上风起云涌的民族解放运动,为人们争自由求平等的民主诉求推波助澜,成为反奴役反压迫的文学,成为“反抗的文学”。而拜伦正是这一浪漫主义艺术倾向的最伟大的代表诗人。
作为浪漫主义伟大诗人,拜伦的诗歌创作主要以抒情诗和叙事诗为主,同时他还创作了一定数量的讽刺诗、传奇故事诗、诗剧等作品,就是说作为一个诗人,拜伦尝试并探索了各种诗体形式,并且取得了成功,因为无论哪一种诗歌体式不仅对当时和以后的英国文学,而且对世界文学均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虽然这些诗作其主题宗旨异常丰富,题材种类更是千差万别,语言和艺术风格多姿多彩,但是无不饱富才情与机敏,显示出诗人强有力的个性和潇洒独立的风采。这除了依靠卓越的思想和激情,也有赖于拜伦圆熟的诗艺技巧。在表现手法方面,拜伦喜欢以叙事为主,叙事与议论相结合的表达形式,同时,采用多种修辞格,不拘俗套,自由灵活,对比、夸张、铺陈、讽喻甚至调侃常常交互使用,变化无穷,形成了拜伦特有的一种“驳论式”诗格(诗体):诗人似乎无法按捺自已,随时向他的主人公和读者大发议论,而又随时以一种巧妙的方式予以“对话”,这种你来我往的驳论在《唐璜》等作品中甚至占到一半篇幅以上。这不仅使诗作内容丰富多彩,而且使文气洒脱从容。
作为一个“旨归在动作,立意在反抗”的诗人,强列的主观性抒情性和鲜明的政治倾向性是拜伦诗歌的最主要特征。其名言“诗的本身即是热情”,可谓他诗学观念的核心。作为一个浪漫主义者拜伦反对古典主义的崇尚理性,把作家的感情和想象提到首位,强调真实地表达个人对客观世界的内心反应和感受,抒发强烈的个人情感。个人与现实的对立,使他们转向主观幻想。拜伦的诗作、甚至每一行诗,都跳荡着澎湃的激情;几乎所有作品都有他自己的影子,清晰可见,其火热的内心和炽烈的性格通过主观抒情表现出来。比如《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按其体裁应该以记叙为主,但诗人侧重的是内心感受,这甚至改变了其体裁的性质和长诗的结构。拜伦诗歌的主体是叙事和议论,甚至是辩论性的,但是这种叙事和议论往往是被一种强烈的情感或汪洋恣肆般的情绪包裹着裹挟着,就是说赋予了很强烈的、诗人特有的主观色彩,打上了深深的诗人自我的印记,尤其是拜伦特别善于宣泄情绪、抒发情感,特别善于传达男女主人公丰富复杂的细微隐秘的内心世界,对此,歌德评论道:“温柔到优美感情的最纤细动人的地步。”拜伦的情感表达方式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因情因景而不同,富于变化,有时候一泻千里,有时候有节制、内敛,横溢或者含蓄,往往取决于情境与氛围,而拜伦似乎最精此道。很多情况下,“淡淡的哀愁”可以描述拜伦诗情之特殊优美的境界,这从《唐璜》主人公与朱丽亚相恋的场面、甚至仅仅朱丽亚的决别信就足可体会了。应该指出,由于拜伦是个积极入世的政治家诗人,所以其满腔激情往往升华为对自由与正义的呼唤,这就决定了拜伦大部分诗作鲜明的政治色彩或倾向性。抒情诗如此,长诗如此,诗剧亦然。总之,在拜伦,负有沉重历史感的时代豪情占居着其诗作的主导地拉。在其笔下,高山或是大海,雄奇、豪壮、粗犷,是自由的象征,力与美的凝聚,英雄性格与激情的体现,同时也是他寻找某种历史力量和现实力量的寄托之物。
拜伦诗歌第二个显著的特征是辛辣的讽刺性和批判性。拜伦的浪漫主义和讽刺才能相结合,形成了其诗作独有的强烈的讽刺激情。拜伦诗歌的政治倾向是通过辛辣的社会讽刺实现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唐璜》就是一部长篇讽刺史诗,在这部讽刺诗中拜伦作为一个诗人的力量也得到了最有力最充分的体现。“各国社会的可笑方面”作为诗作的主体内容而得以呈现,这种讽刺不仅指向诗人身处其中的19世纪初期前后的社会现实,而且具有一种纵深的历史感,在历史与现实的交汇中以一种广阔的视角对繁复变幻的社会生活深入挖掘,因而这种讽刺就不是泛泛而谈或流于社会的表面,而是由现象突入本质,揭示生活的某些倾向性特征;更重要的是,在这种讽刺的背后显现的是诗人拜伦反抗现实、与黑暗社会和一切反动势力相抗衡、不妥协的叛逆胸怀和斗争精神,在更根本的意义上则是拜伦深刻的民主与自由思想的体现。正如一位研究者所指出的,就个人气质论,拜伦主要是一位讽刺诗人,其讽刺才能和讽刺力量是无与伦比的,他发展了英国文学独特的讽刺传统,并将之推向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他的讽刺机智微妙,变化万千,耐人品味,加强了作品的战斗性和针对性。拜伦并非纯然从主观、从内心体验汲取灵感,而是紧紧盯着人类社会,这又使他的讽刺往往一针见血,入木三分,加强了作品的现实感和生命力。
拜伦诗歌第三个特征是自然崇拜和回归自然。拜伦在思想上受到卢梭的巨大影响,然而,拜伦对卢梭“回归自然”思想的接受是不全面的,换言之,拜伦按照自己的理解对其重新定义,他更强调人的情感方面,推崇情感的坦率、真诚,尤其是看重情感的自然流露;借助于诗歌创作,拜伦一方面弘扬了卢梭原始自然的思想,另一方面更加突出自然神性即人的自然性,所以他歌颂纯朴的农人、天真的小儿和纯情的少女,力图以此与污浊的现实、丑陋的人性相对抗,显然,“回归自然”在拜伦那里成为了其批判社会、反抗现实的一个重要思想武器。“拜伦最杰出的贡献就是几乎用自己全部的诗歌创作去讴歌大自然和探索人与自然的关系。在他的自然诗中,人、人心和人性的问题居于核心位置,是他诗歌创作中的主题。所以说无论是卢梭哲学的思想核心还是拜伦自然诗的主要内涵,都是在呼唤自然人性和人性的自然。而这种呼唤是以他们独特的精神途径‘回归自然’来实现的”。[3]抒情诗和自然诗是拜伦诗作的一个重要构成,虽然与华兹华斯比较,拜伦的自然诗少一些,稍逊一筹,但是也自有特点。华兹华斯的自然诗多以自然风光和乡土世界中农民的生活场景为表现内容,诗人与其所呈现的自然景象之间几乎水乳交融,无法分割,自我泯灭其中成为大自然的一部分,宁静,安宁,大自然成为游子的避难所,时时抚慰他那颗受伤的灵魂。在拜伦的自然诗中多的是山川河岳,名胜古迹,而非乡村景象,而且这些构成了其诗作的一个重要“背景”。崇山峻岭,浩瀚的海洋,风雨雷电,瀑布的轰鸣、无垠的夜空等等,是与诗人宽广的胸怀和深邃的心灵世界相呼应的,诗人反抗叛逆的挑战精神是借助于对这些雄浑的自然景象的礼赞而体现的传达的。拜伦在诗歌创作方面显示出独特的审美意识和艺术风格。他借助诗歌抒发了强烈的奔放的情感,呼唤人类应有的美好的理想生活;他按理想化的原则塑造人物形象,因此,这些人物大都具有非凡的气质、惊人的毅力和超群的智慧。拜伦“一生创作了大量的自然诗抒情诗,充分表现了他对生活的热爱,对爱情的追求以及对大自然的向往,他用朴实动人、悠扬悦耳的诗句表达了自己的喜怒哀乐和对自然对生活的真实感受”。[4]
[1] 王佐良.英国浪漫主义诗歌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
[2] 梁桂平.传统的悖离与超越:拜伦死亡观探究[J].华南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07,(4).
[3] 张晔.徜徉在大自然中的人——谈卢梭“回归自然”的思想与华兹华斯自然诗[J].《北方论丛》,2001,(6).
[4] 周淑莉.华兹华斯与拜伦诗歌中完美女性形象的对比分析[J].牡丹江大学学报,201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