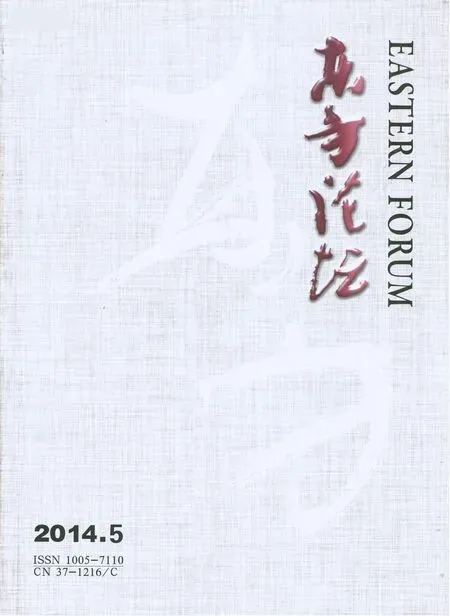“文学死了”:一个关系判断而不是价值判断的论调
赵洪涛
(湖南科技学院 中文系,湖南 永州 425100)
一
“文学死了”的呼声喧嚣雷鸣。这个论调在美国学者艾利斯·米勒的推波助澜下,在学术界的影响蔚为壮观,在《文学死了吗》一书中,他直奔主题道:“文学就要终结了。文学的末日就要到了。是时候了。不同媒体有各领风骚的时代。”[1]随后,在国内学术界引起热烈讨论。不少学者认为,在20世纪,随着现代影像技术和音像技术的革命,文学的媒介优势逐渐消失,现代影视艺术拥有比文学优越得多的媒介,它使语言艺术相形见绌。然而,我们却极少看到研究者们能够拿出确凿的证据来证明文学自身在发展中的衰亡,很多研究者基本上不谈文本与读者的接受,而是硬性的将文学架上一个框架,在一个似是而非的比较中将文学“逼上绝路”。这种研究所持的路子是从文学外围来研究文学,将文学置于一种比较关系中来研究文学,而对于文学内部的变化,则是采取一种迂回曲折的逻辑来判定,即认为外部的因素变化了,文学内部也无可避免地会发生变化。这种逻辑当然是有道理的,问题是即便是逻辑上是成立的,但不代表事实上二者是同步进行的,文学史上很多案例证明,文学与外部的变化并非是同步进行的,社会变化了,文学却依然故旧的例子比比皆是。
说“文学死了”,那应该是从文学本身去研究得出的结论,这个结论应该是在对文学存在的价值判断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而不该是在对其他艺术与媒介研究的基础上想当然的得出“文学死了”的结论。纵览人类文化发展的历史,一山存几虎的现象未必不存在,以明清文学为例,明清时代小说、戏曲获得了快速的发展,但是这并没有改变以诗、文、词为中心的状态,最终形成了明清时期多种文体共同繁荣的局面。这里以文学史的例子来说明文化形态是基于这样一种前提,即两者之间是异曲同工的。人类文化艺术的发展走向是互通有无,互相依赖的,为什么媒体的变化会必然导致文学的衰亡?视觉感官文化的兴起必然会压缩文学的生存空间?这是一种典型的二元对立型的研究思维,认为一种艺术的强大必然会导致另一种艺术的式微,它忽略了艺术之间的共存关系,无视在当代社会中,随着新媒介的发展,各种艺术都获得了长足发展的可能。再则,假如“文学死了”,与之相适应的人类文化走向必将出现变化,为何没有相应的研究证明这一点?
对此,王蒙先生有过一番持平之论:“还有一个问题呢,现在由于多媒体的发展,由于视听文艺的发展,又由于网络的发展,所以从国外就有一种怪议论,说是文学即将消亡,小说即将消亡,说人们不用看小说,看小说干什么?看电视剧就行了嘛!听爱情歌曲就行了嘛!你在床上看见一个猛男和一个靓女在那儿抱过来抱过去,滚过来滚过去,这比你看一部爱情诗过瘾多了,是不是?但是毕竟文学有文学的魅力,文学有文学的含蓄性,如果都是大吵大闹,都是那种感官刺激的东西呢,说不定是文学艺术品质的降低,是人类精神品格的悲剧!”[2]王蒙先生这番话很鲜明地表明这样的立场,即文学有自己的价值,有自己的表达方式,它无法被其他媒介和艺术取代。王蒙先生对文学的认识是切中肯綮的,在这之前他就指出:“文学失却了轰动效应”[3](P185)但是王蒙先生却不认为文学已走向没落。童庆炳等先生指出,边缘化不过是文学的常态,有什么必要“把作为常态的文学的‘边沿化’理解为文学的终结呢?”[4]类似的研究可以说是从文学自身来进行研究的,因而其结论也相对客观,不故做惊人之语。
从外围来研究文学从观念上来说是受到了韦勒克的影响,而在理论的援引方面则是受了法兰克福学派和英国的威廉斯为代表的伯明翰大学学派的影响。韦勒克最著名的理论之一是将文学研究划分为“外部研究”和“内部研究”。这种划分表现在他与沃伦合著的《文学理论》之中。韦勒克将“思想史”和“社会学”等研究划为“外部研究”,这无疑对1990年代以降的中国“文化研究”起到了理论上的启示。文学的文化研究的确把研究对象从“内”位移到“外”,研究文学与社会的关系。文化研究开拓了文学研究的路子,使学术不再拘囿于纸上谈兵,而具有了厚实的现实色彩。然而,文化研究在中国发展的过程中却剑走偏锋,在轻文学文本重日常生活的研究模式中,文学本身的研究反而被荒芜懈怠了,研究者在热衷的日常生活审美研究中“乱花渐欲迷人眼”。很难想象,在一个轻文学文本研究的时代,反而能够理直气壮地得出“文学死了”的结论,这个结论由于缺少对文学本身的价值判断而显得那么轻飘与随意。
其实,文学的“外部研究”并非是放弃传统的文学文本研究,而是在外部研究的同时丰富文学自身的研究,正如余虹教授所说的,“而是要在广阔的存在领域考察文学性的不同表现、功能与意义”。[5]俄罗斯文论专家程正民深刻指出:“文艺学研究可以从历史出发,也可以从结构出发,但如果是科学的研究,它所追求的必然是历史与结构的统一。文艺学如果从历史出发,那么历史研究的客体就是审美结构:如果从结构出发,那么也只有靠历史的阐释才能理解结构的整体意义,对结构的认识和理解只有通过历史的阐释才能得到深化。”[6](P249)将文学研究与社会历史研究结合起来,才能完整理解文学的问题。换言之,在社会历史文化的语境中,文学才会得到有效的阐释与理解。两者之间是同气连枝的关系。
与“文学死了”论相映迥异的是,“文学经典”被学术界热炒,既然文学已经是明日黄花,何以“文学经典”在不断被强化,这种文化逻辑的背后是什么?“文学经典”一直与政治,宗教等问题纠缠在一起,在中世纪,文学经典的功能在于它统治了教育、并与帝权、神权共同构成了统治性权力。利用经典为政治服务,作为统治阶级工具的现象至今也仍然存在。“文学经典”不断被强化其实意味着着权力的运作。与这种强调“文学经典”的行为形成对比的是,对文学衰亡、没落的强调。两者之间的对立,实质是话语权力的交锋。
赵毅衡先生认为文学存在着两种经典化的方式。第一种方式是通过批评家把相关文学作品与以往的经典之作进行比较,然后比较中确认其文学价值。“因此,批评性经典重估,实是比较、比较、再比较,是在符号纵聚合轴上的批评性操作”。第二种方式是大众的“群选经典化”,所谓群选,是因为其操作方式是通过投票、点击、购买、阅读观看、媒体介绍、聚积人气等等进行的,由此也形成了与“比较”迥异的“连接”遴选模式。[7]“文学死了”的论调代表的是一种精英立场,精英惯于以经典文学作为标准来衡量一切文学,这样就将大众文学排除在外,很容易得出文学没落的结论。“文学死了”的呼声背后是一种精英立场的固守与自恋,精英文学观念将多元化形态的文学浓缩成一种经典文学形态,也就是精英文化只认为经典的文学才算是真正的文学,并以此文据来评判文学的发展与建构文学史。新浪网曾发起关于“谁是今天的文化偶像”的评选。[8]在评选结果中,鲁迅、钱钟书、雷锋、金庸、王菲、张国荣等代表精英文化、革命文化和消费文化的人物赫然并列在一起。这种衡量“文化偶像”的标准是什么?文化偶像评选活动将流行歌手,革命英雄与文学经典作家一锅端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官方文化、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之间的距离,很显然,这种做法无疑取消了精英文化的特权,使之成为大众文化的消费对象,它与文化精英一向固守的立场与高高在上的姿态之间形成了一种紧张关系。
二
近几年学术界一个令人瞩目的现象就是围绕“图像转向”话题而大造声势。其实,在媒体技术日新月异的时代,不仅仅是图像变得越来越重要,声音(主要是数字音乐),文字媒介都获得了极大的发展。拿声音来说,网络音乐的无限制下载,使得人们获取音乐资源得到了很大便利,音乐在人们的生活中几乎无处不在,MP3 播放机、手机、电脑、电视上各种各样的音乐类型冲击着人们的听觉。麦克卢汉以“声音空间”来描述声音的重要性,韦尔施则宣称“走向一种听觉文化”的“听觉文化转向”。有人先入为主地将图像的地位抬到一个无以复加的高度,以此来压低文字的影响,其实稍加注意就不难发现,如今的网络文学如火如荼,学富五车的或小学毕业的作者,都喜欢在网络上随心所欲地书写,以目前人气最旺的天涯社区为例,它的一个人气较高的版块“天涯杂谈”,几年时间网友在版块中发表的帖子数量已逾五千万,而且每天都还有数以万计的帖子不断上传。网络博客和QQ 聊天成为数以亿计的网民每天的“日常作业”,而且不少以信手涂鸦为嗜好的网络写手的作品能得以结集出版或改编成电影电视剧,比如十年砍柴,慕容雪村都依靠网络写作而从寂寂无闻一跃而成为红极一时的网络作家,他们的作品点击率惊人。痞子蔡的网络作品《第一次亲密接触》和安妮宝贝的《八月未央》使一度门庭冷落的图书市场重新焕发生机。照此来看,我们是不是也到了一个“声音时代”或者“文学时代”?
对某些学者热衷于炒作“图像时代”的现象,杨乃乔有过一针见血地批判:“等视图理论者以书写把视图时代的到来在虚拟的理论空间中论证清楚后,如果还剩着一点智慧,不妨回首看一看,自己的理论还剩下多少生存空间?因为在这个时代‘我从来不阅读,更不书写,我只是看看图画而已。’”[9]杨乃乔的话虽然激烈,但绝非危言耸听。如今的学术界花样和噱头十足,今天一个理论,明天一个构想,很多不过是闭门造车的产物,既不是对现实问题的深入研究,也不是基于以前理论的一种创新,它仅仅是一种理论,正是因为这种理论缺乏现实和学理的根底,才显得浮躁,喧嚣一阵之后,就如过眼云烟一样消失无踪。现在的理论有多少是经得起实践检验和对学科的建构大有裨益的?中山大学教授高小康在《理论过剩与经验匮乏》一文中指出,现在的批评理论远离文本的阅读经验,理论的指导作用变得捉襟见肘,变成自说自话的独幕剧,理论的公共价值变得微薄。[10]当下不少作家对理论究竟有多少作用表示疑义,前几年不是有作家宣称没有学文学理论一样可以写出好作品来吗。这些说明了文艺理论满足于自身的逻辑理路,而相对忽视了理论的现实来源和对现实的介入,这其实是一种功利主义,一种只考虑理论的影响而忽视学术整体发展的功利主义。
当今社会文化多元化,后现代文化对本质的消解使不同文化呈现出各自存在的理由,何以在对后现代文化倍加推崇的学术界,总是出现一种本质论的思维?总有一些人在运用自己反对的文化理念来研究文化?因此,我们总会见到这样的自相矛盾的说法,比如有研究者一方面宣扬文学终结论,相信文学生存空间受到电影、电视等大众媒介的压迫;另一方面却又笃信“以语言为载体的文学与人类的思维、理性和想象具有更为深刻而本质的联系,任何电影技术手段对于语言的种种表达可能性望尘莫及,而且,电影在经济逻辑的支配下制造的虚假的需求特别是消费欲望的虚幻满足,并不能让我们遗忘人类的真实需求,即追求超生物性的自在、自为的人性理想,而此点恰好是作为语言艺术的文学之所长。”[11](P207)
曾有一位学生问上文学课的老师,读《三国演义》能帮我们找到就业的饭碗吗?在当代大学生的心目中,外语、计算机和经济类书籍以及传授青年各种处世技巧、成功经验的书籍,才是他们的“必修课”。我们判断文学的价值是否有用,这恰恰切中了文学的软肋,因为文学对人的影响是观念与精神上的,属于超越性的,其价值在于虚实之间。说它实,效果不是彰明较著;说它虚,它的价值通过影响人的观念而对社会产生实质性影响。当我们拿现实法则来衡量文学的时候,自然得不出文学的价值分量,然而,在急功近利的社会中,文学的价值常常被忽略,被当做是茶余饭后的无聊消遣品。这种观念在社会上的蔓延,也很容易得出“文学衰亡”的结论。但是,这种功利态度是评价文学价值的合理尺度吗?文学应该有文学的评价尺度,换个角度,若是我们拿文学的评价尺度来衡量经济,是否可以名正言顺地得出经济的没落之类的结论?
综上所述,可以发现,“文学死了”不过是一种学术噱头,它的深层是功利主义的大行其道与精英立场的自恋固守,由于没有真正涉及到文学本身的问题,只是在外部或顺应社会流行的观念来审度文学问题,因此不可能对文学的发展得出一个合乎实际的结论。这种判断中由于缺少了对文学价值的有效判断而显得十分可疑。通过对这种观念的反思,可以找出当前学术的一种弊端,即缺少一种客观的价值立场,正因为如此,很多看似发人深省的学术观点才失之于浮躁与流弊于表象。
[1] 艾利斯·米勒.秦立彦译,文学死了吗[M].桂林:广西师大出版社,2007.
[2] 王蒙.把诺贝尔文学奖看得比天还高有点下贱[EB/OL].http://www.chinanews.com/cul/2012/11-26/4359176.shtml.
[3] 王蒙.文学:失却轰动效应以后[A].王蒙文存: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4] 高磊.应该终结的文学终结论[J].文艺争鸣,2006,(1).
[5] 余虹.文学的终结与文学性蔓延——兼谈后现代文学研究的任务[J].文艺研究,2002,(2).
[6] 程正民.俄罗斯文艺学的历史主义传统与创新[A].程正民自选集[M].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7.
[7] 赵毅衡.两种经典更新与符合双轴位移[J].文艺研究,2007,(12).
[8] 新浪网.谁是今天的文化偶像[EB/OL].http://www.people.com.cn/GB/paper447/9467/876075.html.
[9] 杨乃乔.图像与叙事:论诸种叙事与知识分子的小叙述者身份[J].文艺争鸣,2005,(1).
[10] 高小康.理论过剩与经验匮乏[J].文艺争鸣,2005,(11).
[11] 朱国华.文学与权力—文学合法性的批判性考察[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