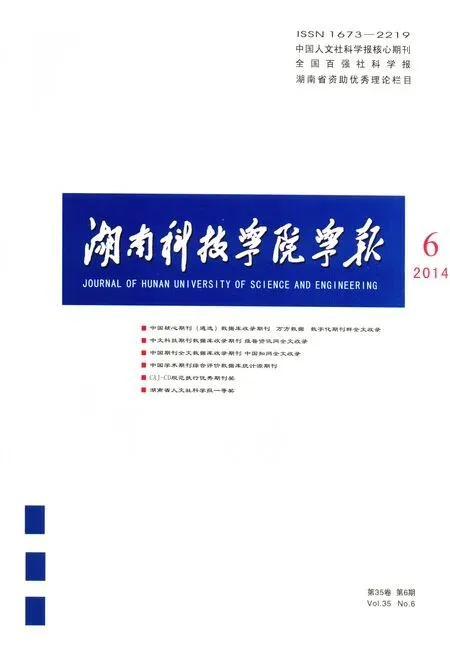《反美阴谋》的美国信念与犹太身份
杜 鹏
(南京大学 外国语学院,江苏 南京 210014)
《反美阴谋》(The Plot Against America, 2004)是菲利普·罗斯(Philip Roth,1933-)在9/11事件三周年时推出的一本力作,作为“2003-2004年间关于美国主题的杰出的历史小说”,获得了 2005年美国历史家学会奖。小说设想了1941年林白成为美国总统,推行反犹政策而导致整个美国的社会动荡,并用“伪回忆录”的形式描述了自己的家人在社会迫害下的曲折经历,将自己的童年生活与美国历史相互交织,环环相扣,创造出了一种亦真亦幻的效果。《反美阴谋》出版仅一个月就有超过百篇书评,这些评论多认为《反美阴谋》是对现实政治和社会的影射。詹森·西格尔指出《反美阴谋》的“反历史”情节挑战并修正“人们关于美国身份的观念”[1]P131;在艾伦﹒库伯看来,小说表现了犹太家庭的价值观与美国社会观念之间的冲突[2]P242。国内对该小说的研究集中于其叙事技巧和现实主义元素等方面:王守仁将《反美阴谋》定义为“后现代现实主义小说”[3]P54;朴玉则探讨了《反美阴谋》独特的历史书写策略和充满叙事张力的文本空间[4]P83。综合国内外相关研究,学界人士注意到《反美阴谋》涉及美国信念和犹太身份的主题,但多将这两个主题分开论述,未对两者的紧密关系进行侧重研究。基于此,本文将探究《反美阴谋》中体现的美国信念和犹太身份之间的联系,关注小说对“谁是美国人”这一问题的讨论,指出美国信念和犹太身份的结合对美利坚民族认同的重大意义。
一
《反美阴谋》的出版时间和售书宣传值得注意。小说出版于2004年美国大选的前四周,这一时间选择无疑具有深意,当时总统候选人布什与克里正就美国的未来走向展开激烈讨论,而小说虚构了1941年总统选举,描述了偶然的选举结果对国家和民族产生的深远影响,无疑形成与现实政治的对应关系。在售书宣传的活动中,罗斯的两张照片经常同时出现,一张是老年的罗斯端坐在美国星条旗前,象征着对美国信念的认同;另一张是他在出生地纽瓦克(Newark)的社区地图前,暗示着他的犹太身份。在作品中,主要人物的犹太身份和他们流露出的美国信念也与这两张照片相呼应,共同显示出小说对“美国特性和美利坚民族的审视”[5]P151。
美国信念由建国之父托马斯·杰弗逊等人提出,是“美国特性的关键决定因素”,其核心原则为“自由、平等、民主、民权、无歧视、法治”[6]P281。在塞缪尔·亨廷顿看来,这一理念是“盎格鲁-新教文化的产物”,因而对它的认同必须首先接受这一文化。然而,他的观点“白人中心主义倾向十分明显”[7]P71,受到众多学者的批评,因为美国信念作为普世价值,不能为单一文化所限,同时平等和自由的原则要求多种文化共同发展[8]P261。在现实生活中,美国信念不仅是一种价值观念,还通过语言、国旗、节日、国家名胜、民族英雄等形象表述为广大民众所认知。
《反美阴谋》对美国信念的这两个方面都有体现。作品中的人物熟悉美国信念的核心原则,林白反复强调民主的价值,宣称“竞选总统的目的”是为了“保护美国的民主不被世界大战所损害”[9]P30;而林白的反对者也是从美国信念出发提出抗议,罗斯福批评林白政府对民权和法治的践踏,罗斯的父母指责林白无视平等和自由的原则。作品中反复出现对美国信念的形象表述。纽瓦克犹太聚居区是故事的发生地,在此居住的犹太人“用美式英语彼此交流”,看英文报纸的人是“买意第绪语日报的十倍”, 而希伯来文字仅出现在“屠宰铺”和“犹太会堂”[9]P4。在塞缪尔·亨廷顿看来,“英语替代其母语”是一个种族“美国化”的标志[6]P281。国旗作为“国家身份的重要标志”在小说中不断出现[7]P64,主人公菲利普“每天早上在学校进行国旗宣誓”,“在集会上唱关于国旗的歌曲”[9]P4;民众挥动国旗庆祝林白或罗斯福的胜利,对美国国旗的珍视反映出对美国信念的认同。国家英雄和地理名胜也成为美国理念的另一种形象表述,菲利普的邮票显示了这一点。菲利普受罗斯福的影响开始集邮,因为罗斯福从小“就对集邮感兴趣”[9]P56,而他是菲利普“学会去爱的第一个伟人”[9]P7,代表着自由与平等的美国精神。菲利普的收藏很丰富,包括十二张华盛顿总统的邮票和十张美国国家公园的邮票,这些邮票承载着特殊的历史含义,“象征着美国自建国以来争取自由、民主的历程”[4]P87。集邮的过程成为菲利普对美国理念的认同过程。
对犹太身份的关注是《反美阴谋》的另一个焦点。犹太身份是犹太民族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形成的用来界定自身的基本特性,而坚持这一身份成为犹太民族历尽劫难却绵延不绝的重要原因。犹太身份与犹太民族的起源、发展和近两千年的流散历史联系紧密,“历史上许多次大规模种族迫害给他们的民族记忆留下了深深的印记”,也带给他们“其他族群所不具备的特征”[7]P250,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犹太教信仰与独特的犹太生活方式和传统。罗斯一家居住在纽瓦克犹太聚居区,这里“男人们一周工作五十、六十、七十甚至更多小时;女人们天天都在劳作”[9]P3,父亲赫尔曼的口头禅是“尽全力就能赢”[9]P11,尝试各种工作来贴补家用,而母亲贝丝除了照顾家庭,还承担社区和学校的义务工作,反映出犹太人吃苦耐劳和艰苦创业的特性。对犹太教的信仰凸显了罗斯一家的犹太身份,母亲贝丝在基督教主导的伊丽莎白镇度过的童年,这段经历使她“充满了对基督徒根深蒂固的不信任”[9]P14,只有在搬入纽瓦克之后,她恪守犹太教的信仰,遵循拉比的教导,重新在犹太身份上找到自信。
在林白的竞选中,犹太人被指责为“战争的鼓动者”[9]P386,因种族利益和报复纳粹而不惜将美国引入战争,损害民主,因此他认为他们是非美国的异类,将之排除在美利坚民族之外。他随后的反犹政策裹着增强“种族融合”和“美国特性”的外衣[9]P280,不断冲击着犹太人的生活,而作品中的犹太人物也表现出不同姿态:妥协、逃避、抗争、或坚守,可以说,林白政府的统治将美国信念与犹太身份的冲突推向顶点。
二
在《反美阴谋》中,美国信念和犹太身份的冲突并非源于它们本质的矛盾,而是由两者自身的局限性所导致的。一方面,美国信念的多种原则之间存在微妙的平衡,而理念本身必须由现实的国家机构进行阐释,这就容易产生对某一原则的偏重,损害这一平衡,使美国信念具有一定的脆弱性;而另一方面,犹太身份强调特有的犹太信仰和生活方式,狂热的坚持会产生极端的排他行为,降低对美国信念的认同,是犹太身份的片面性所在。
林白的当选和施政暴露出美国信念的脆弱一面,在他身上,个人主义原则凌驾于其他原则之上。林白的竞选充满个人英雄色彩,他独自一人驾驶“孤鹰号”在全国巡回演讲,将自己描述为美国和平与民主的捍卫者,煽动起美国民众对英雄的崇拜和对战争的恐惧。他的施政秉承其简单的个人作风,视犹太人为“美国最大的威胁”,向广大民众宣传犹太人的“反美阴谋”[9]P31,从而获得他们的支持推行着各种反犹政策,完全丢弃了美国信念给予所有族群的自由和平等的权利。因此,林白的民主成为多数人的暴政,促进民族融合的美国信念转化为主流族群压迫少数族群的工具,部分原则的无限扩大导致其他原则的丢弃,完全破坏了美国信念的整体平衡。
在林白当选后,罗斯一家实现了“很早就计划的华盛顿之旅”,目的是让孩子们相信“美国没有改变”[9]P55。华盛顿特区作为美国首都,是美国特性的最佳体现,而美国宪法又是美国信念的来源,对罗斯一家而言,它们是美国理念的化身,保护犹太人免受林白政府的迫害。然而,警察对美国理念的阐释使这种保护化为幻影。林白统治下的华盛顿弥漫着对犹太人的歧视,罗斯一家入住的旅馆因为他们的犹太身份取消了他们的预定,父亲赫尔曼引述林肯总统的名言“人人生来平等”向警察抗议这种歧视,而警察对平等原则的理解为“这并不是意味着所有的旅馆预定都是平等的”,并威胁要将闹事的赫尔曼关入警局[9]P71。这个国家赖以存在的种种原则在执法者的阐释中变成一纸空文,华盛顿之旅让罗斯一家见证了美国理念在反犹思潮下的脆弱。
在《反美阴谋》中,林白政府的反犹政策裹着美国信念的外衣,激起一些犹太人的抗争,对犹太身份的狂热追求成为他们的抵抗手段。这种追求既体现为个人的抗争,也表现为整体的反抗。菲利普的堂兄阿尔文代表着个体的抗争。他具有强烈的犹太意识,不满美国犹太人对欧洲同胞的漠视和对林白政府的顺从,离开美国加入加拿大部队抗击德国。这一决定象征着他对美国信念的否定,在他的眼中,林白统治下的美国对犹太人已毫无希望,美国信念中的个人追求和进取精神充满铜臭。然而,参战导致了他的个人悲剧:他在战争中失去左腿,成为“残肢”[9]P122,并因此丧失所有的犹太信仰。在播音员温切尔身上,寄托了整个犹太族群的反抗。他是“美国仅次于艾伯特·爱因斯坦的最有名的犹太人”[9]P19,宣布竞选总统以抗议林白政府的“纳粹主义”,他将犹太族群阐释为“上帝选定的种族”,是抵抗集权统治的希望,赢得了众多犹太人的支持。然而,温切尔对犹太身份的片面强调加深了犹太人和主流族群的矛盾,也背弃了美国信念中对宽容的呼吁。作品中,犹太族群的激进反抗以悲剧结束,温切尔的遇刺身亡使美国陷入种族暴乱,犹太族群面临灭顶的灾难。
罗斯向来注重标题对小说的阐释作用,英文标题中“Plot”可理解为“阴谋”,也可理解为“情节”。因此,小说既可看作是揭露反美的阴谋,又可认为是描述反美的情节,这就为读者的解读创造出丰富而含混的多重意义结构。
作品中讲述的反美阴谋层层叠加。对林白政府而言,是“犹太人对美利坚民族的阴谋”[1]P150,他们利用“对电影、报纸、电台和政府的影响和所有权”威胁着美国信念,因此,反犹政策是美国民众做出的“民主”选择[9]P14。对犹太人而言,反美阴谋是林白的种族主义对犹太族群的伤害,它既将犹太身份排除出美国特性,又无视美国信念中的平等和民权的原则。对整个美国而言,这又是 “法西斯分子颠覆美国的阴谋”[10]P193,德国纳粹妄图挑起美国的种族冲突,从而间接控制美国。
《反美阴谋》也是一段反美的情节,它构建的历史与现实的美国历史截然相反,从未发生,创造这一情节是对1940-1942年间美国社会流行的观念的重新组合,正如作者罗斯所说,“我把有真名实姓的历史人物拖进我的故事时,并没有无缘无故地将各种观点强加到他们头上”[11]。这些观念既可以产生现实历史中“最伟大的一代美国人”[2]P242,也会因偶尔的历史波动导致作品中的危机和阴谋。由此,反美情节消融了历史与虚构的对立,通过对处于重重阴谋之中的一个犹太家庭的假想式回忆,暴露出美国信念和犹太身份潜在的局限性。在小说的结尾,反历史的情节又回归现实历史,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由于美国信念与犹太身份的疏离而导致的反美阴谋是如何得以化解的?
三
《反美阴谋》围绕着“宏观的、大写的”美国历史和“微观的、小写的”家庭史双重线索展开小说叙事[4]P89,其中,对美国历史的创造性改写构架了背景,而罗斯一家的生活轨迹则成为主要故事。两条线索齐头并行,将美国的危机与罗斯家庭的命运紧密相连,探寻着解决反美阴谋的途径。
美国历史学家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认为,民族作为“想象的政治共同体”,“被想象为本质有限的”[12]P5-6,因此,民族成员间的认同和联系界定着着它的边界。在“谁是美国人”的问题上,林白认为犹太人是“外来种族”和“劣等血脉”,玷污了美国对“欧洲血脉的继承”[9]P14,将美国信念引向毁灭,是相对于“我们(美国人)”的“他们”,看得出林白对美利坚民族做出了极端狭隘的界定,犹太人被排除在美利坚民族之外,这一界定将美国引入阴谋之中。
与之相反,罗斯一家的生活史体现了美国信念和犹太身份的紧密联系。一方面,对罗斯一家而言,美国是他们的“祖国”和“三代人的故乡”,这个国家的理念已为他们认同,以至于小儿子菲利普诧异竟会有人为“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人自己的国家”而募捐[9]P4。另一方面,犹太身份强调“文化之根”的重要,促进了对美国信念的全面认识;而美国信念申明人们的普遍诉求,消融了族裔身份可能引起的偏激行为,两者是相互平衡的。“在美国拥有自己的房子”是父亲赫尔曼的“梦想”[9]P8,他的努力工作给他带来实现这一梦想的晋升机会,这些折射出他对个人主义的认同,可是这种认同并未使他丢弃自己的犹太生活:他拒绝了晋升,因为晋升意味着他要同“法西斯分子”一起工作,并要举家搬入“异教徒”主宰的联邦镇[9]P10,12。父亲拒绝像邻居特茨维尔一样移民加拿大,享受自由的犹太生活,因为那意味着自己 “成为外国人”,“祖国将变成出生地而已”[9]P301,而他“相信这个国家(美国)”,“爱这个国家”[9]P284。在小说中,罗斯一家始终保持着完整,充满亲情,显示出赫尔曼和贝丝对美国信念和犹太身份的坚守在家庭的层面上战胜了反美的阴谋。
在国家的层面上,历史的突变让美国民众把握到美国信念和族裔身份的依存关系。林白失踪后的美国陷入恐慌之中,副总统惠勒将林白政府的种族主义理念推向极致,全国进入军事管制,国会关闭,边境封锁,美国信念荡然无存,犹太人也因绑架总统的谣言成为替罪羊,面临灭族的威胁,由此引发的暴动将整个国家推向崩溃的边缘。反犹主义已转变为对美国信念的全面摒弃,对犹太人的压制已转变为对全体美国民众的暴行。危机之中,罗斯福通过在国会的压倒性胜利,开始他的第三次任期,重申对美国信念的重视,停止对犹太人的伤害,整个国家转危为安。美国信念和犹太身份者的融合将美国从危机中解救出来。
历史的偶然性是《反美阴谋》突出的重点。小说的创作始于罗斯偶然的想法,在阅读历史学家施莱辛格的自传时,他看到 1940年一些共和党孤立主义者曾想让林白竞选总统,这一历史事件让他不禁追问,“如果他们选了林德伯格做总统将会如何?”《反美阴谋》是对它的回答,小说先以林白的当选这一偶然事件从历史中打开缺口,又以林白的失踪另一偶然事件回归历史,将文学想象与历史真实交织起来,如作者罗斯所说,“呈现的现实如同施莱辛格自传里的那样是真正的美国现实, 虽然我让历史去走它并没有走过的路”[11]。作为反历史小说,《反美阴谋》使读者看到偶然性对历史的巨大改变,而这一改变又是历史必然规律的体现,因此产生对历史的追问和反思。小说出版于 9/11事件后的第三年,在小说的附录中,林白反犹演讲的时间正好是在1941年9月11日,同时,小说中林白的强腕统治也让人联想到现实中布什政府的种种政策,这些巧合暗示着小说与当代美国的联系,反映出作者罗斯对后 9/11时代美国社会的反思:在重重的反美阴谋中,罗斯的家庭依靠美国信念和犹太身份的融合走出困境,美国也战胜种族思想的影响,恢复了美国信念的完整,小说对犹太族群和美国历史的乐观态度正是来源于对美国信念和犹太身份的结合与平衡的信心。
《反美阴谋》以丰富的文学想象“改变读者认识和理解历史的方式”[1]P134,探究美国信念和犹太身份的冲突和联系,回应着后 9/11时代美国各界关于民族文化的讨论。这场讨论中,一元文化论者坚持信念立国,维护盎格鲁-新教文化的主导地位;而多元文化论者强调族裔身份,主张各族群文化的平等与自由;他们的分歧在于对美国信念和族裔身份的单方面侧重。在小说中,罗斯一家认为自己既是“美国人”,又是“犹太人”[9]P3,始终保持对美国和犹太族群的双重认同,这一界定突出了美国信念与犹太身份的结合与平衡。因此,《反美阴谋》反写了犹太身份与美国信念相冲突的文学传统,反映出“当代文学创作中的美国特性建构再次进入了传统的轨道……美国特性的文学想象也从过去激进主义的颠覆性描写转向今日建设性的重建”[13]P78。这部小说让读者看到:真正的美国特性是在美国信念的基础上不同族裔身份的平等建构,犹太人是美利坚民族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正是如此,美国最终战胜了应该发生而没又发生的反美阴谋。
[1]Siegel, Jason. The Plot Against America: Philip Roth’s Counter-Plot to American History[J]. MELUS: Multi-Ethnic Literature of the U.S. 2012(37):131-154.
[2]Cooper,Alan.It Can Happen Here, or All in the Family Values: Surviving The Plot Against America Philip[A]. Roth:New Perspectives on an American Author.Ed.Derek Parker. Royal Westport:Praeger Publishers,2005.
[3]王守仁.回忆·理解·想象·知识——论美国后现代现实主义小说[J].外国文学评论,2007,(1):48-59.
[4]朴玉.评菲利普罗斯在《反美阴谋》中的历史书写策略[J].当代外国文学,2007,(4):83-91.
[5]Morley, Catherine. Memories of the Lindbergh Administration: Plotting, Genre, and the Splitting of the Self in The Plot Against America[J]. Philip Roth Studies, 2008,(4):137-152.
[6][美]塞缪尔·亨廷顿.我们是谁[M].程克雄,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4.
[7]江宁康.美国当代文学与美利坚民族认同[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
[8]Lind,Michael. The Next American Nation[M].New York: Simon&Schuster,1995.
[9]Roth,Philip.The Plot Against America[M].New York: Vantage International, 2004.
[10]Geraci,Ginevra. The Sense of an Ending:Alternative History in Philip Roth’s The Plot Against America[J].Philip Roth Studies, 2011,(7):187-204.
[11]Roth, Philip.The Story Behind The Plot Against America[J]. 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19,2004.
[12][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M].吴叡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13]江宁康.美国民族特性的文学想象与重建[J].外国文学研究,2007,(2):72-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