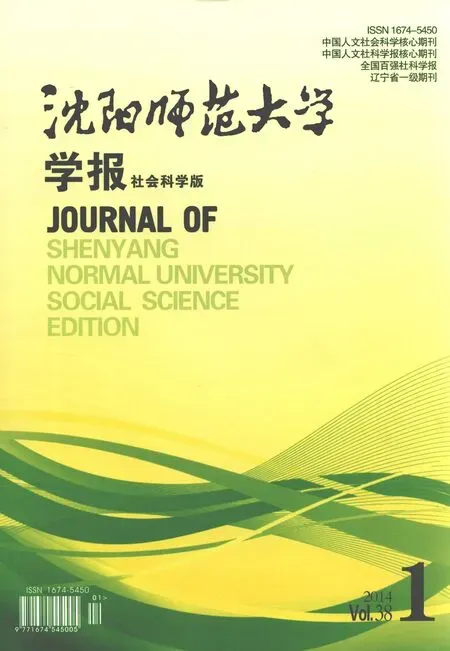从“朦胧诗论争”看“精英”与“大众”的话语分歧
王静斯
(辽宁大学 文学院,辽宁 沈阳 110036)
从“朦胧诗论争”看“精英”与“大众”的话语分歧
王静斯
(辽宁大学 文学院,辽宁 沈阳 110036)
20世纪80年代是论争的年代,至今为止,“80年代”所彰显出来的对于理想的追求,对于信念的坚守,对于公共事务的执着仍然久久镌刻于知识分子的内心并成为了只可想象而不可重临的“乌托邦”。“朦胧诗论争”作为新时期文学中最持久而尖锐的一次论争,其论争的批评方式一直潜隐于后来的批评格局中。目前,文学界存在着“精英话语”与“大众话语”疏离的窘境,因此从“朦胧诗论争”这一角度入手,分析“朦胧诗论争”的某些特点如何影响“精英话语”与“大众话语”的对立。
朦胧诗论争;“精英话语”;“大众话语”
朦胧诗论争作为新时期文学领域内规模最大,同时也是最尖锐的一次论争,共持续了九年的时间(1979—1988),期间中国社会无论从经济、政治还是文化等各个领域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随着论争的逐渐深入,论争的范围也渐次由最初的局限于诗歌领域或者说仅在文学领域内进行的“纯文学”的探讨延伸和发散到了社会领域,上升到了政治意识形态层面,那么朦胧诗论争也就由最初的“文学论争”层面的懂与不懂的问题演变成了“社会论争”中资本主义道路或是社会主义道路的选择问题。如果说以上是从共时性层面分析朦胧诗论争影响的话,从历时性方面,当朦胧诗论争的热潮过去之后,其论争过程中所形成的话语特点和批评方式也对后来乃至新世纪的批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文拟从对比“朦胧诗论争”中的双方和“大众”与“精英”这两组关系中,试图分析一种固定的批评思维和模式如何延续并作用于新世纪文学批评中,探讨这种批评方式的不足以及如何走出这种固化的模式。
一、“朦胧诗论争”中的批评模式
朦胧诗从最开始的由于晦涩难懂等原因被传统诗人以及诗歌批评家所诟病,到后来的逐渐为越来越多的研究者认识到它的价值所在,再到“新的美学原则崛起”的合法性确定,应该说其被接受的过程是艰难和曲折的。其作为向“政治叙事”、“国家叙事”、“一元的价值标准”提出挑战的具有先锋性质的“事件”,应该说在新时期的意义是重大的,甚至有些研究者将其看做先锋文学的传统之一。很多学者也从不同的角度对此次论争进行了阐释,主要是从文学与政治之间的关系以及两辈诗人之间不同的诗学观念等角度切入分析。本文认为梳理和探讨此次论争的全过程已没有过多的意义,而意义在于经由此次论争之后,留下的具有代表性的批评话语特点以及批评方式对于后来文学批评的影响,这也是朦胧诗论争历史意义和当代价值的彰显。程光炜在《批评对立面的确立——我观十年朦胧诗论争》中指出:“诗歌的批评,也许就在于对批评的‘对立面’的确立过程之中,这是人们对诗歌批评‘独特性’的一种常见的理解。”也就是说,在朦胧诗的论争过程中,朦胧诗的支持者是通过与对方的论争,甚至是批评和找出对方的弱点来确立和证明自己立场和理论正确性的。这正如拉康的镜像理论,依靠对方的存在,在对方的“镜像”当中发现自身,确证自身,使自身被凸显,即在“他者”中建构起自己的价值。而这种“他者”一旦消失,自己的理论和观点也没有了任何的立足点和存在的基础。也就是说,朦胧诗作为新兴事物,作为一种新的文学思潮,它要确立自己的合法地位,就要通过极力地驳斥对方来完成。应该说,这是自“五四”以来我们形成的一种传统,“五四”时期要提倡新文化,彰显白话文的重要性,那么其对传统采取的方式是激烈的和极端的,他们将中国的传统文化无论精华或糟粕都批判得一文不值,态度之坚决,大有不把对方置于深渊,自己就无法立足,就无法凸显自己的气势,其实这也是“革新”的必经之路。正如孙绍振所说:“没有对权威和传统的挑战甚至是亵渎的勇气,思想解放就是一句奢侈性的空话。在当艺术革新潮流开始的时候,传统、群众和革新者往往有一个互相摩擦、甚至互相折磨的阶段。”徐敬亚在其《崛起的诗群》中,为了彰显“朦胧诗”的价值,甚至将批评的触角伸向了中国的古诗。
朦胧诗相对于传统诗歌而言具有革命性的改变,它从根本上改变了诗歌的表达方式,在主题和内容方面将关注点深入到人的内心,挖掘人内心的孤独、苦闷、犹疑和彷徨。在表达技巧方面也大量地运用了西方现代派文学的技巧,运用了语言陌生化等现代派的表达方式。这些主题和表达方式与传统诗歌中的“赞歌式”的、“国家民族式”的、“明晰简单式”的风格截然不同。但从批评话语的领域考察却存在“文革”期间的“论战式”的批评模式的痕迹,这种批评模式中体现出的是情绪性和非学理化的特征。这种方式是将对方的论点归纳出来,找出对方的某种缺陷,最终以将对方否定来确立自己理论权威地位为目的的批评方式。有研究者将此种批评中呈现出来的思维称之为“本质化思维模式”。本文认为这种批评的主要特征就是批评立场的预设性和批评的武断性,不能认真地分析对方理论的优势和不足,而是为了确认自己立场的正确性,抓住对方弱点攻击,大有抛弃一切传统和文化底蕴,“重打鼓,另开张”的意思。这种批评方式具有明显的本质化思维的色彩。学者晋海学指出了本质化思维的严重危害性,“如果缺乏对由‘朦胧诗论争’所呈现出来的‘本质化思维模式’的自觉抵制能力,我们不仅会失去进入那段历史的契机,同时也无法有效地反省自身,乃至于中国当代文学虽始终在一种徘徊状态里挣扎,却一直苦于无法找到发展自身的动力”。应该说这种“本质化思维模式”一直延续,而在新世纪文学批评中起到或隐或显的作用。本文认为这是另一种意义上的权威式批评,是情感批评和不及物的批评,这种批评是溢出文学问题边界的批评,是社会意识形态内话语权的争夺,而非文学领域内的论争。正如西方学者分析中国的“朦胧诗”与西方意象派之间的异同时指出:“与意象派相反,朦胧诗人是政治社会的一部分,并且认为他们的诗歌就是参与那个政治社会。”本文认为朦胧诗之于传统诗歌的对峙,“崛起派”批评之于反对派的论争,在此过程中所呈现的纠结和摩擦,其所采取的确证自己的方式,在新世纪的批评格局中完全呈现于“精英”(精英文学或精英批评)和“大众”(大众文学或民间的批评之声)的两种文学形态的对峙中。
二、“反叛传统”批评方式的延续:“精英”与“大众”的分歧
这种批评之于“五四”运动与“崛起派”都是以批判传统的方式展开的,本文称其为“反叛传统”的批评。这种批评的惯性思维潜隐在新世纪的批评中,像是在演绎一种历史的循环。与论争不同,新世纪“精英”与“大众”的对立主要表现为后者对前者的漠视。目前,精英话语和大众话语作为两种主要的话语方式,它们之间的关系是尴尬、疏离甚至是对峙的,它们之间的分歧与朦胧诗论争中的分歧是形式不同而本质相同的。实际上,这种论争在新世纪已经愈加地由文学观念的分歧逐渐演变成为了话语权力的争夺,甚至成为了一种对“话语霸权”的向往和渴求。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新媒体和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精英文学走进了一个相对狭隘的空间,受众群体逐渐变小,而社会对于纯文学理论和精英文学作品的探讨也逐渐地止步于研究生课堂或者专门的学术会议,“圈子化”和“小众化”的特征凸显。如20世纪80年代对文学充满理想和激情的年代已经不再,人们街头巷尾议论的是官场文学、言情小说、网络文学,大众热衷的是于日常生活中具有功利性和直接性作用的话语方式。对于“精英文学”或者说“学院文学”的探讨,对于哪部文学获得了“茅盾文学奖”等高端文学领域问题的关注逐渐淡化。从某种程度上说,大众话语的发展跟“崛起派”的反传统相似,它们通过解构精英话语彰显自身,它们的话语是戏谑的,是充满反讽、戏仿、反叛、先锋等后现代的话语方式的,它将受众的旨趣作为第一要义,这一领域充斥的关键词是日常生活、碎片、散乱、无中心和价值多元。这之于精英话语对于精神的挖掘、对于信仰的坚守、对于意义的建构呈现出大异其趣的态势。那么,“大众”对于“精英”的反叛正如“崛起派”之于“赞颂式”的、“简单明晰式”的传统诗歌的支持者一样,“崛起派”解构的是传统诗歌中的“赞颂”“国家民族”;“大众狂欢”解构的是终极价值,应该说它们都是一种“反叛传统”的批评话语方式,某种程度上都是从批判对方的过程中建构自身的。那么在新世纪,建构自身的背后更表现出话语权的争夺,目前,大众话语也逐渐建立起了另一种层面上的权威。
三、批评方式“历史循环”的深层探究
这种批评方式与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到“朦胧诗崛起”确认自身的方式是相似的。“反叛传统”真的能确立自身吗,应该说,“朦胧诗”合法性的确立,“大众”话语与“精英”话语分庭抗礼局面的形成,其更源于深层的社会历史原因。一种文学思潮能够如鱼得水,顺利发展依赖于整个社会中大的文学体系和制度,“崛起派”的外在表征是一种对新的话语表达方式的认同,是对一种新的审美情感的支持,然而其内在的本质却是与社会发展进程中对于“现代化”的诉求相一致的。也就是说“朦胧诗”中对于西方现代派技法的应用,对于西方“意识流”小说中对于挖掘内心情感的借鉴,这种文学上对于“现代性”的认同正好契合了整个社会发展进程中对于“现代化”的追逐和诉求。也就是说,“崛起派”的观点契合了整个社会的文化环境,与“大历史”背景下文化体系的标准和内核是一致的,双方达成了“合谋”的关系。因此,“崛起派”所支持的“朦胧诗”的新奇的、有创新性的表达方式,和脱离“国家叙事”、脱离“颂歌式”的表达,才能够在“反叛传统”中获得优势,并使“三个美学原则的崛起”作为合法性的美学标准被人接受并确定下来。而在新世纪“精英”与“大众”话语的对峙中,“大众”话语在与“精英”话语磨合与对峙的过程中,“大众”话语显露出的无法阻挡的发展之势,这正与社会的转型、经济的发展以及科技的进步背景下对于整个社会文化体系多元化标准的转变密切相关。经济的转型、传媒的发展促使国家意识形态由原来的“政治关注”转移到了“经济关注”,主流意识形态放松对文化控制提倡多元化的同时,人们的生活节奏也不断加快以及接收信息的渠道也更加多元化,因此,“快餐文学”“大众文学”那种“直击眼球”的不需要花费多少精力阅读同时能够使人迅速放松的,没有任何沉重感和终极价值追求的文学大行其道,其也正好契合了整个时代发展的多元文化体系。因此,无论是“崛起派”的成功,还是“大众话语”的盛行,其成功的深层原因都是其表达了与社会发展路向的趋同,是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先进”战胜“倒退”的不证自明。因此,历史的循环产生于文学与政治互相缠绕的变化关系中。
通过批评对方来确认自身这种“反叛传统”的批评方式应该是由来已久的,这种批评方式是数百年来我们积累起来的文化经验,在与传统的意识形态和文学理念的纠缠与挣扎中推动历史的前进。而这种批评的缺陷显而易见,这种批评方式很容易从文学领域扩展到政治意识形态领域,发展为话语权的争夺。在“精英”与“大众”磨合与纠缠的过程中明显表现出了此种态势,与朦胧诗论争中的“崛起派”不同,大众话语在其论争的过程中采取的是另一种“反叛”,比如大众文学中的网络文学,其具有广泛的群众影响力,有稳定的受众群体和拥护者。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如前所述,这种新兴的话语方式的发展过程仍然没有脱离“反叛传统”的批评模式,只不过这种反叛不是通过激烈的言语辩论来实现的,而是通过漠视传统与忽略权威的方式展开的。而忽略权威同时又建立起了另一种权威,正如“朦胧诗论争”的目的不是在文学领域的革新,而是致力于社会领域,是一场“政治事件”一样。应该说,大众文学在反叛传统的过程中也建立起了另一种权威,是一种“去政治的政治”。也就是说,无论是“朦胧诗”最初的对于“纯文学”的标榜还是大众话语等对于民主和自由的彰显,其表面“去政治”,摆脱政治干扰的过程实际带来了一种“再政治”化的结果。正如目前网络文学所建立起来的网络话语、建立起来的各种“小圈子”,人人网、微信、微博、空间等等,使不了解网络技术,不懂得网络基本话语的人难以进入这个团体和圈子,这何尝不是另一种权威和话语权的建立,是“大众”领域内的政治,是另一种形式的“传统”,是另一种形式的“铁板一块”,这就是“反叛传统”批评模式的某种弊端的呈现。
针对以上问题,本文认为要在批评的过程中避免过分的情感因素,应该在学理化的层面上,在全面分析了解对方理论的基础上提出批评意见,而避免一知半解的、武断的、社会政治层面的归纳总结。因为某种在双方互不了解的层面上,站在自己固有立场上进行的不及物的论争也只能算是批评领域的一场闹剧,或者仅仅在政治意识形态领域获得胜利,而谈不上产生任何的学术增长点以及理论的纵深和延展。只有理性的反思这种“依靠对手”存在的武断的、固化的、缺少理论根基的批评才能够更好地推动批评的发展。
[1]程光炜.文学讲稿:“八十年代”作为方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185-188.
[2]孙绍震.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J].诗刊,1981(4):55—57.
[3]何同彬.晦涩:如何成为“障眼法”?[J].文艺争鸣,2013(2):90-91.
[4]王爱松.朦胧诗及其论争的反思[J].文学评论,2006(1):113—118.
[5]李怡.艾青的警戒与中国新诗的隐忧[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11(3):61-63.
[6]段宏鸣,罗岗.当代文艺思潮.与“朦胧诗论争”[J].南方文坛,2011(2):71-74.
[7]晋海学.论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朦胧诗论争”[J].贵州大学学报,2008(5):61-62.
I235.1
A
1674-5450(2014)01-0103-03
2013-09-12
王静斯,女,辽宁朝阳人,沈阳师范大学教师,辽宁大学文艺学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 詹 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