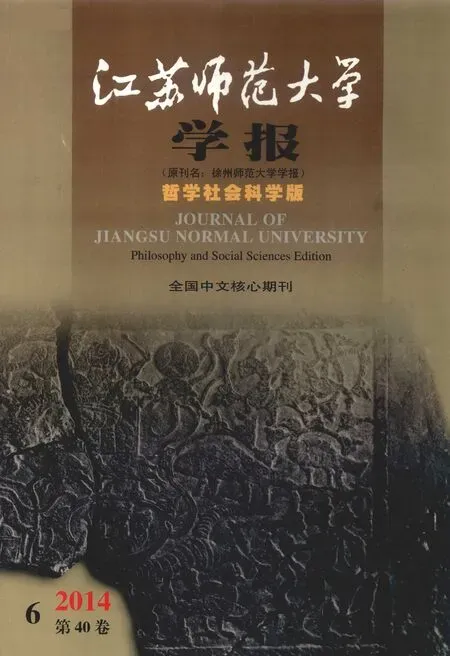马克思社会交往理论的现实基础与革命意蕴
辛 勤
(徐州工程学院思想政治理论课教研部,江苏徐州 221000)
马克思社会交往理论的现实基础与革命意蕴
辛 勤
(徐州工程学院思想政治理论课教研部,江苏徐州 221000)
马克思;“现实的人”;社会交往;交往形式;世界历史
传统思想家对社会交往的探讨,遵循“抽象的人”的解释路径;马克思探讨“现实的人”及其进行的物质生产活动,彻底颠覆了以往解释传统并开创了社会交往理论,为研究人们的社会交往找到了现实基础。生产力的发展推动社会交往逐渐走向普遍化,社会交往的世界历史意义与革命意蕴随之呈现出来。
自从人类产生以来,社会交往就伴随其中。令人遗憾的是,这项人类与生俱来的社会行为,在马克思之前的思想家们的视野中始终是一个理论死角,很少有理论家关注社会交往理论,因此,对其作出系统阐发就更显难能可贵了。马克思在探索创建唯物史观的过程中,也成为社会交往理论的创立者和全面阐发者,他从“现实的人”及其物质生产活动的角度,对人们之间的社会交往展开全面的研究。
一、马克思“社会交往”思想的形成
关于“社会交往”,马克思既没有直接给出明确定义,也没有如哈贝马斯那样专门论述交往理论,尽管如此,他的诸多论述不乏涉及社会交往思想。根据不同语境中的特定意涵,马克思曾使用“交往”、“交往形式”、“交往关系”等概念,来表达人们的社会交往状况,如人们之间的社会性交互活动、人们在经济活动中的交换行为,或是市民社会中的交往活动等。马克思对于这些概念的灵活运用,无疑将社会交往的总特征展示了出来,即从物质实践出发,在人与自然、人与人的交往中揭示人的交往关系。
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就提到交往,全文总共有8处出现“交往”一词。马克思意识到社会交往之于人的重要性,指出人为了生存延续而必须与自然界发生交往,这里所说的是人与自然的交往。同时,马克思也提到人与人交往的需要,“当共产主义的手工业者联合起来的时候……,他们也因此产生一种新的需要,即交往的需要,而作为手段出现的东西则成了目的”[1]。在马克思看来,人与自然展开的交往,既是拥有社会属性的人生存的基础,也是人们之间发生交往行为的前提条件。马克思在此揭示了交往作为人的社会关系的表现形式,是人类所特有的行为,在与自然进行物质和能量的交换过程中,人无疑具有主体能动性。由于此时青年马克思依然受到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的影响,因此,认为这种主体能动性确证了人的本质力量。马克思对社会交往的系统研究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作出的。“交往”一词在该书中出现96次,马克思从交往的本质出发,把交往分为物质交往和精神交往。他指出:“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的生活语言交织在一起的。”[2]这里所说的交往包含个人、集体、国家的物质交往和精神交往,它们构成了社会交往的总和。可见,马克思对于交往的理解,立足于人们的现实活动之上,即人们在以生产劳动为基础的物质上和以语言为纽带的精神上发生的关系,也就是基于共同需要而在人们之间建立起来的相互接触的过程。交往也经历了从简单到复杂、由单一到多样化的历史发展进程,人类文明程度越高,交往也就越发达。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带动下,人们的社会交往也随之克服了“狭隘地域”所产生的“地方性知识”,走向普遍的、广泛的交往,因而具有“世界历史性”[3]。
当然,马克思在此使用的交往概念,更多地注意到它得以发生的社会条件和历史局限,着力在表明人们之间发生关系的模式。由此,交往通常与交换并用,这也使得交往概念兼具经济学与社会学的意蕴。马克思指出:“在过去一切历史阶段上受生产力制约同时又制约生产力的交往形式,就是市民社会。”[4]那么,市民社会中的交往又是怎样一种状况呢?充满异化和自私自利。既是如此,过去一切历史时代下的交往方式,都受到马克思的批判性审视。在马克思看来,过去的思想家在看待人们的社会交往时,没有考虑到当时的社会生存条件和生产力发展状况,足见马克思所持有的历史唯物主义立场。在批判现存的资本主义社会时,马克思洞见到其中社会交往的异化,即在资本的统治下,金钱和利益成为人们交往的唯一纽带。既然这种交往方式与个人的活动密不可分,那么社会交往就在人们的感性活动中获得统一,也即人们在生产中结成复杂的社会关系。
在1846年12月28日马克思致帕·瓦·安年科夫的信中,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重视交往与社会生产力发展程度的紧密关联。马克思在信中写道:“社会——不管其形式如何——是什么呢?是人们交互活动的产物。……在人们的生产力发展的一定状况下,就会有一定的交换[commerce]和消费形式。”[5]不难看出,马克思同时在交互活动、交换行为和生产关系三个意义上使用交往概念。正是在社会生产发展到一定程度时,相应的交往方式就随之产生;同时,作为社会交往方式机制化的产物,相应的社会制度、家庭、等级也随之被确定下来,而这一切被马克思统称为市民社会。也就是说,一定的社会生产力水平决定相应的交往方式,社会的各种交往方式使得市民社会和国家的产生成为理所当然。由此,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一唯物史观的逻辑理路清晰可见。
马克思关于交往的论述,着重强调它是社会实践活动。人类区别于动物的主要标志是生产劳动,即人类的社会交往必须建立在生产实践基础之上。人是一种类存在物,任何人都不是原子式的个人,而是与其他人都处于一定的社会关系中。最基本的社会关系,是在劳动中相互“承认”而建立起来,劳动的承认“成为完全合乎人性的人与人之间交往方式”[6]。即使是在与世隔绝的孤立状态下,人也从事着社会性的活动,因为他所使用的语言以及活动所必需的物质材料,都是以社会产物的形式被人所拥有的。
关于人们活动的形式,在德国古典哲学家看来,人的活动无一不是精神的活动,或是意识在发展过程中自己活动,人的活动基础无不建立在精神的沙滩上。较之而言,马克思却让人的活动在坚实的地平上展开。他认为,人们社会交往的基本形式乃是物质交往活动,其他的一切活动,包括政治活动、宗教活动甚至是科学实验等,无不建基于此。在关乎社会历史进步的那一维度,个人的物质交往活动所推动的生产力发展就成为决定因素。历史的进步绝非来自于某种“天神意旨”,也非什么“绝对精神”外化自身的进程,而是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社会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互作用的结果。在整个历史发展进程中,充斥着人们普遍联系的交往形式,那些业已陈旧的交往形式,在新的、发达的生产力面前显得不合时宜甚至成为桎梏;而一些更加进步的交往形式,由于更加适合、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而得以盛行。一定的生产力总是呼唤与之相适应的交往形式,社会历史就在不断进步的生产力与不断变更的交往方式相互调整的推动中前进。“交往直接影响了生产力的承接、内化和创新,一个社会的发展程度取决于其内部和外部交往的广度和深度。”[7]
马克思不是学院派的理论家,在哲学改变世界的宗旨下,他对于交往概念的运用,从来不专注于字面的解释游戏以及对概念进行细致的词源学考证,而是着力阐释不断变化的社会现实,并最终内化为推动现实革命的理论力量。一旦马克思将社会交往理论运用于现实,那么历史冲突的根源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就暴露无遗。一切历史冲突的根源,都来自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首先引起意识与思想领域的冲突,进而引发政治斗争与各阶级之间的冲突。作为这一切的必然后果,共产主义革命将在两大社会阶级的对抗中爆发。
二、马克思社会交往理论的现实基础
“现实的人”及其进行着的物质交往活动,逐渐将历史行进中诸多抽象和神秘的面纱揭开,也为马克思社会交往理论奠定了现实基础。在马克思所开启的整个哲学革命中,社会交往这一论题的唯物主义路向也被开辟出来。
尽管社会交往是人类社会与生俱来的行为活动,但它却在较长时间内缺乏人们的认真关注,即使稍有关注也总是以歪曲的社会意识反映出来。这一点在宗教思想和近代哲学中得到鲜明的体现。在宗教思想家看来,人们交往活动的本质,无非是与上帝发生直接或间接的联系。基督教中所谓的神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具有圣父、圣子与圣灵的“三位一体”特征。这种“三位一体”的交往模式,就是人们在信仰领域实现与最高人格的上帝进行交往的活动。中世纪的宗教活动使得这一行为尤其明显,人们在信仰领域与上帝或其代理人发生的交往,构成了整个社会生活的重心。后来,路德和加尔文所进行的宗教改革,尽管主张人们应以“因信称义”的形式直接同上帝发生交往,那也只是将人们信仰领域的交往方式扩大罢了,并没有从唯物主义层面为社会交往提供现实基石。
宗教思想家没有为社会交往寻找到现实基础,同样,近代哲学家也没有完成这一任务。从笛卡尔奠定“我思故我在”的哲学路向开始,近代哲学无不拥有共同的形而上学根基,即思维从自身内部出发而去构建外部世界。这一思维逻辑所体现出来的原则,通常被称为“思维内在性”。依循这种原则,人们对社会交往的解释就被紧锁在“思”的原则之中。交往活动,在近代哲学家那里也表现为抽象的“自我活动”,它是“超脱任何内容同时又正是对任何内容都通用的,脱离现实的精神和现实的自然界的抽象形式、思维形式、逻辑范畴”[8]。譬如,康德眼中的交往活动,是人们在知性范畴的认识框架下,去认识世界和他人的活动,表现为在纯粹思维之中的形式化交往;而黑格尔那里的社会交往,无非也是“绝对精神”从自我意识出发所进行的一系列辩证过程,就连国家的存在以及世界历史的发展,都只是神“在大地上的行进”。总的说来,无论是在路德、加尔文等宗教思想家,还是在笛卡尔、康德、黑格尔等近代哲学家看来,发生交往的人们都表现为“抽象的人”,简言之,他们所谓的社会交往,并没有从现实的物质生产活动出发去阐释。
可见,以往人们对于社会交往活动的认识,都没有获得一个合理的现实基础,宗教思想家和近代哲学家对于这个论题的阐说,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说还不及亚里士多德。那么,社会交往活动的现实基础存在何处呢?马克思作出了自己的解答。马克思关于社会交往的论述无不指向一个事实:“现实的人”及其物质生产活动,这才是构成社会交往的现实基础。也正是这个社会交往的现实基础,才决定了人的本质,即“在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9]。后来,马克思在《穆勒评注》中关注的对象是交换关系,因而在批判对象上显现出对交往异化的重视,他已经从“基始性的主体际性关系”与“历史性的社会关系”上来看待异化的交往[10]。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将人们的社会交往活动放在市民社会中进行考察,并指出市民社会是全部历史的真正“发源地”和“舞台”。有别于以往在讨论社会交往时的一般做法,马克思非常注重人类生存的前提条件,因为社会交往的主体乃是具有感性生命的人。在此,马克思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命题,即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非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这就将人从宗教思想的信仰之中摆脱出来、从近代哲学的思维之中解放出来,成为一个具有感性生命的、实实在在的人,也就是“现实的人”。“现实的人”所从事的首要活动,是人口的生产以及物质资料的生产,它构成人与人之间相互交往的主要内容,人类也通过这些活动书写着自身的历史。在工业产生以后,人类的历史就和工业的历史发生紧密联系,因为实践的、工业的历史及其所创造出来的对象化的世界,是一本打开来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因此,马克思强调要始终将人类的历史与“工业和交换的历史联系起来研究和探讨”[11]。关于工业以及自然科学对人们交往的影响,马克思区分了维科和达尔文的研究路向。维科强调人和动物在物质上的差别,达尔文以自然史为研究对象,重视人和动物在量上的连续性研究。马克思则认为,尽管动植物的器官是自然形成的,但人们之间的社会联系却有所不同:机器大生产以前是基于血缘的自然联系;机器大生产以后,人们社会联系的血缘纽带被资本无情地打断了,人也就成为社会的人。资本的无限自我复制和自我增殖本性,导致市民社会中人们关系的淡漠,人也处于全面异化之中,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资产阶级撕下了罩在家庭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把这种关系变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12]
马克思社会交往概念不仅承载着丰富的意涵,也拥有确定无疑的现实基础。马克思主义作为无产阶级的革命学说,其全部理论都以推动无产阶级自身解放作为最终依归。
三、马克思社会交往理论的革命意蕴
马克思从来都不是一个纯粹的理论家,变革不合理的社会现实才是他真正关切的,因为“改变世界”应该成为哲学的墓志铭。马克思的社会交往理论,在向我们展示其世界历史意义的同时,也将解放全人类的革命意蕴指明出来。
首先,社会交往刺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诞生。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揭示了生产与交往之间相辅相成的关系,个人之间的彼此交往是生产得以进行的前提,而交往的方式取决于一定时代的生产水平。人们的物质生产活动,推动社会生产与社会分工的出现,规定了一定历史时期的社会生产力;社会交往活动的展开,使得该时期的社会生产力得以保持下来。一个地区或国家所创造出来的先进生产力(尤其是发明),是否会得以保存和改进,完全取决于社会交往的程度。社会交往扩大,往往使那些“地方性知识”得到普遍传播,从而有利于人类知识或生产方式的保存。如中国的丝绸、茶叶与火药等物品,经过通商而传到中亚与欧洲各地;相反的情况却是,如果一个先进民族被蛮族所征服,那么其先进的生产力乃至文化等都可能毁于一旦。
越过单一地区和民族的交往范围,马克思认识到世界范围的交往能够推动生产力的提高。由于新航路的开辟和新大陆的发现,资本主义在上升时期对外贸易的扩大,极大地加速了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资本主义国家在亚非拉广大地区进行征服与殖民的同时,也将先进的生产力带到当地,极大地冲击了殖民地原有的生产方式。譬如,当英国通过工业革命与资产阶级革命走向强盛之后,商业和工场手工业全都集中在这个新兴的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商业贸易和武力征服这种交往方式,英国开辟了广阔的世界市场,满足本国工场手工业产品的巨大市场需求。同时,在资本的原始积累过程中,商业贸易和工场手工业的扩大,伴随着蒸汽机的发明和运用,社会生产力得到巨大提高。这无疑也说明,交往的进一步扩大,推动工场手工业发展为机器大工业,此时,封建社会的那种生产关系就成为束缚。正如有研究者所认为的那样:“在世界各民族的相互交往中理解各民族的历史进程,而不是孤立地看待各民族的历史发展,是马克思考察社会发展道路的一个根本方法。”[13]
其次,社会交往推动了宏观的世界历史进程。在马克思看来,社会交往与社会分工密不可分,它们不仅共同决定着各民族和国家之间的关系,也决定了各民族内部的社会阶级结构。封建社会那种地主与农民的人身依附关系,逐渐被资本家与工人的雇佣关系所取代,整个社会的阶级结构逐渐发生调整。随着社会交往的扩大,获得巨大发展的不仅仅是工场手工业,还包括整个社会的生产运动。对此,马克思认识到,“进入流通的大量金银完全改变了阶级之间的相互关系,并且沉重地打击了封建土地所有制和劳动者”[14]。当这一切正在发生时,预示着历史发展即将进入一个新阶段,即世界历史的形成。
社会交往不仅形成世界市场,更是促进宏观的世界历史发展。世界历史将各个国家的社会发展纳入统一进程,商品和贸易犹如无坚不摧的强大武器,打碎那些落后国家的闭关自守,使得它们渐渐失去自身的地方性特征。机器大工业的迅速发展,使得生产的竞争普遍化了,广泛的竞争驱动着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内寻找原材料以及开拓广阔的世界市场。大工业所带来的商业竞争促使交往形式扩大,每个国家的每个人的需求都要在世界市场上得到满足。马克思认为,在普遍的交往发展过程中,世界各地对商品的需求,呼唤世界贸易的兴盛。这些逐渐增长的需求,通常和首先以各国产品进行交换作为保证,这样,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所创造的产品,就进入世界各国的居民消费之中。也就是说,世界市场的形成依赖于世界范围内的普遍交往,而世界历史的形成也得益于交往泛化的推动。日本学者望月清司认为,随着生产力发展与社会分工的细化,人们逐渐走向“在共同体中进行社会交往”[15]。对此,不少研究也从“市民社会”来展开马克思社会交往理论的历史意义[16]。
最后,社会交往促进人类摆脱异化走向自由解放。资本主义依托近代工业革命和科学技术,极大地解放了社会生产力,以商品经济为开路先锋取得世界性的胜利。资产阶级打破了封建主义的社会等级,无情地斩断了各种束缚人的封建羁绊,以金钱这个唯一尺度推动社会平面化的平等。然而,资产阶级却在反对封建等级和特权中逐渐走向反面。在金钱最终成为维系和评判一切社会活动的准绳下,人们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与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外就再无别的联系了。在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生产力发展与劳动人民普遍贫困的现实,以及这一现实背后不合理甚至异化的交往机制,使得无产阶级作为革命力量逐渐聚合。同时,社会化大生产与生产资料私有制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始终是资本主义不可消除的固有症结,并由此导致社会两极分化、无产阶级普遍贫困、经济危机与社会异化等问题。面对此种境况,如何建构一个更加合理的社会交往模式?唯有无产阶级通过革命斗争实现自身的政治解放,进而争取实现人类解放以达到“自由人的联合体”才有可能。
作为世界历史发展的必然,共产主义革命和全人类的解放,也将在交往的普遍化发展中到来。这一最终结果,也统一在社会交往的各个阶段上。“现实的人”及其进行的物质生产活动,对于社会交往的主体提出了要求,即人们必须是具有感性活动的自由的人。然而,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工人阶级被束缚在生产的流水线上,重复着单调而枯燥的工作,正如卓别林在电影《摩登时代》中饰演的工人一样。工人在自身与劳动产品、劳动活动、人的类本质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都发生全面异化,这些受异化统治的工人阶级,还受到资本家赤裸裸的剥削。当生产资料私有制与社会化大生产之间的矛盾无法解决时,经受层层剥削与压迫的工人阶级,终将联合起来并以阶级斗争的形式,通过暴力革命打碎资本主义的国家机器,最终使自己成为资本主义制度的“掘墓人”。此外,在广大的殖民地,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矛盾也在逐渐激化,也为工人阶级的国际联合提供了契机。
可以说,对于社会交往这一理论题域,马克思赋予了它历史唯物主义的基底。原先“抽象的人”所具有的思维内部的交往,并非社会交往存在的现实基础。马克思以“现实的人”及其物质生产活动为起点,不仅为社会交往寻找到坚定的现实基础,同时还在批判资本主义不合理的社会交往时,将无产阶级所具有的革命意蕴彰显出来。
[1][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48页。
[2][4][5][9][11][12][14][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2、88、532-533、56、80、274-275、110页。
[3]于沛:《生产力革命和交往革命: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与交往理论研究》,《北方论丛》,2009年第3期。
[6]张盾:《交往的异化:马克思〈穆勒评注〉中的“承认”问题》,《现代哲学》,2007年第5期。
[7]陈水勇:《交往何以推动社会变迁:基于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视角》,《思想战线》,2012年第5期。
[8][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76页。
[10]唐正东:《〈穆勒评注〉中“交往异化”的准确内容及其思想史地位》,《现代哲学》,2008年第4期。
[13]李素霞:《世界普遍交往与卡夫丁峡谷的跨越——兼论马克思社会交往理论的方法论意义》,《马克思主义研究》,2012年第5期。
[15][日]望月清司:《马克思历史理论的研究》,韩立新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12页。
[16]王玉珏、刘怀玉:《从“异化劳动”到“社会交往”》,《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2年第5期。
Realistic Basis and Revolutionary Implication of Marx's Theory of Social Interaction
XIN Qin
(Xuzhou Institude of Technology,Xuzhou 221000,China)
Marx;"real concerning man";social interaction;interaction forms;world history
Discussion of the social interaction for the traditional thinkers followed the"abstract man"explanation path. Marx explored the"real concerning man"and his material production activities.He overturned the traditional interpretation of the past and created a social interaction theory,which found a realistic foundation for the study of people's social interactions.The development of the productive forces gradually promoted the universalization of social interaction,the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and revolutionary implication in social interaction presented.
A81
A
2095-5170(2014)06-0109-05
[责任编辑:李文亚]
2014-06-18
辛勤,男,江苏沛县人,徐州工程学院思想政治理论课教研部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