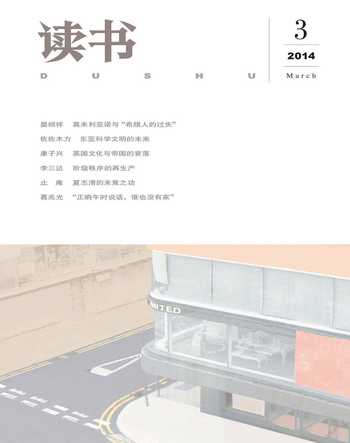西方知识界的卡珊德拉群体
卢冶
有两种世界观一直无法和解:一种是末世论,另一种是世俗的物质主义。奇怪的是,它们在今天竟走到了一起。与此同时,人类两个南辕北辙的目的—消极地苟且偷生和积极地增强生命强度,也就是犬儒主义和唯意志论,也从过去的两个世纪开始殊途同归,并分别在二十世纪的上下半叶达到了各自的峰值。在二零一二年末,“让你在绝望中相信上帝的”李安电影《少年派的奇幻漂流》和对玛雅人末日的娱乐性恐慌,成为这奇怪的世界文化图景中最好的注脚。
几乎所有的宗教都预言过这个鲜活而险恶的时代:希腊神话的黑铁时期,佛家的末法时代,还有基督教的最后审判。雷声响彻了两千年,而雨点则在两百年前才开始落下,那就是工业现代性所带来的前所未有的恐慌与希望。在电影的发明者卢米埃尔兄弟那里,火车从银幕上猛地冲向人群,成为现代性最初的视觉冲击:观众猝不及防地被抛入一个全新的“世纪末”。在那时,东西方的手工艺传统与宗教同时退场,理发店的蒸汽氤氲成火车的蒸汽,当“敬畏”这个核心被挖走时,剩下的“技术”部分就变成了新的上帝,并且在黑格尔和马克思的声音中巡行了全世界。
在今天那些将灾难3D化的电影剧情中,末日,仍然是“共同毁灭”以及一两个幸存者(或者倒霉蛋?)的老故事,然而,当这个别名为“后工业时代”或“全球资本主义景观社会”真的来临、并开始预言一个结尾的时候,它却提出了新的问题:
一、末日之后,假如一切都不会真正消逝,那要怎么办?
二、卡夫卡式的悖论—如果无意义把对它的判决也引入无意义的境地又如何?玛雅人事件过去后,我们不是已经连“末日”和审判本身都消费了么?
三、英伯玛·伯格曼曾在他的全部影片里质问上帝:我们的历史是否可以逃避地狱的惩罚?可是波德莱尔的继承者们则一直在传播着一个小道消息:下地狱似乎也包含着某种颇为高尚的东西。
—以上三点或许比“白茫茫大地”的结局更加糟糕。
关于这一切,总有一个人充满焦虑,那就是希腊神话中被神诅咒的女预言家卡珊德拉。在特洛伊城里,她的灾难性预言永远正确,却无人相信。千年的岁月中,这位不幸的先知在西方世界依然不断地转世还魂,从十七世纪的诺查丹马斯到二十世纪的本雅明,从巫师到私家侦探、诗人和艺术家,那些耸人听闻的警语化为报纸新闻与学术文章,悄悄地在城市空气中流散。
她首先以各种终结论的散布者姿态出现,宣告历史、人、艺术的终结和作者的死亡。早在那个声称苏联解体后“历史”便终结了的日本人福山之前,苏联移民亚历山大·科耶夫就于一九三三年在巴黎高等实用学院讲授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宣扬当代文化对未来的创造如何变得不再可能。常来听讲的是拉康、巴塔耶、梅洛-庞蒂,布勒东、雷蒙·阿隆,讲稿读者中则包括萨特与加缪—光是这些名字就足够后来的历史承受的了。这些讲稿成就了一个卡珊德拉的新神话:历史的终结发生在过去,而不是未来。它早在法国大革命承认了人的普遍欲望之时就发生了。这一观点在后现代理论中绵延至今,经久不衰。科耶夫本人实践了这种“终结”:他在生时并未出版哲学著作,讲稿也由他人编纂。战后,他放弃了哲学,却成为当今欧盟的缔造者之一—与其在哲学终结后继续谈论它和它的乌托邦梦想,不如一点一滴去完成它关于社会实践的遗愿。
在过去的六十年里,卡珊德拉又有了一个新名字:批判现代性的公共知识分子。自从法兰克福学派的“双璧”—霍克海默与阿多诺发现了启蒙理性怎样召唤出它自己的怪物、路易·阿尔都塞的主体询唤绑定了意识形态与国家机器以来,在美国和欧洲大陆,在文学批评、社会学、哲学拓扑学等诸领域中,在一九六八年欧洲风暴“革命最后的狂飙突进”中,现代主义的“余孽”和新崛起的后结构主义学者批量生产的学说和格言警句,警告人们资本主义和科技理性如何会像堕落天使一样把人类引向深渊。
这个时代的历史写作已开始担心它自己,其标志是呼唤以失败者的痛苦,而不是以胜利者的成就为中心的故事,这是苏珊·桑塔格、汉娜·阿伦特、爱德华·萨义德这些带着美国腔的流亡派、后殖民主义和女性主义版的卡桑德拉的声音。他们以斯大林主义革命、冷战、价值观、现代承诺、疾病的隐喻为谈资,意图掀翻资本主义和极权主义同谋书写的现代历史。在同时代的预言家同行中,他们最辛辣、最冲动、最“愤青”,总是以个人姿态反对全面阐释的大历史、反对盲目接受隐喻、反对一切可能导致乔治·奥威尔那冷冰冰的“一九八四”寓言的契机。作为“知识分子的良心”,他们掌握着重要的学术资源和发言权,然而总是站在道德制高点的立场,却令他们经常陷入“受害者和既得利益者”的双重抗辩之中。
从福柯、拉康到德里达,法国人总是活跃在语言学的前沿,试图代表整体的欧洲谱系。与科耶夫对“终结”的身体力行不同的是,尽管巴塔耶、布朗肖、罗兰·巴特、德勒兹发表了大量“作者已死”的著作,却从未强调过自己的观点没有原创性:在反对资本主义现代体系的哲学总体战中,法国人总是提供灵感和养料。可“严谨扎实”的美国人如桑塔格,可能会批评他们总是“在天上飞”,远离了大众和“他人的痛苦”。对此,他们反驳说:这种对现实的成见,这种肯定的思维,难道不正是以自身的强大而垄断着现实的美国人才具有的天真么?
让·鲍德里亚在他们当中后来居上。二零零七年去世的他可以说是媒体时代最黠慧的预言家。他的学术随笔碎言集 《冷记忆(1-5)》就是一个预言和寓言大全,对此无须多说,节录如下:“正是恶在言恶:恶会腹语”;“伟大的意识形态如同各大公司,统统都在搬迁,而梦想成为一种政治上正确的无意识”;“智能已经走开,但人工还在智能的废墟上争奇斗艳”。……假如这位伟大的哲学家、作家和摄影师活着看到二零一二年的玛雅末日,他一定会说:“当你遇到某件事,无论是吉是凶,这事本身就会带来一种狂喜。命定总是压倒对善与恶的评价。”
中国人说,鱼不知水,人不知风。而“淹没在虚拟世界中的这几代人,将永远见不到现实。”—鲍氏可怕的预言是在德里达的徒弟维利里奥那里结出果实的。当法国的卡珊德拉们关于技术理性灾难性后果的预言泛滥成灾时,这位具备科技知识的哲学家+建筑师(法国人更喜欢“跨界”)的贡献在于惟妙惟肖地描述了这后果的情状。在《解放的速度》和《战争与电影》里,读者将看到最普遍的娱乐、最日常、真切的当下生活和最恐怖的战争、最遥远的未来之间的短兵相接。那么,地铁里集体低头摁手机和在高速公路上享受失重快感的我们的未来究竟会怎样?这绝不是一个你想听到的故事。
英国人没有落后。左派艺术批评的英国领主约翰·伯格认为,后现代主义已经从全部未来之中切下了当前,日常媒体又进一步切断了过去。伯格的艺术观和政治观是相互滋养的。不论是谈论电影、绘画、动物、摄影还是别的什么,他的全部作品都弥漫着淡淡的忧伤,《讲故事的人》继承了本雅明和波德莱尔的风格,而《看》则建基于D.H.劳伦斯的遗址上。他的政治理念是左派的“总体抵抗”,其依据则是简洁的线性堕落观:在工业时代的功利主义之前,人类的精神曾有着更高的水准,此后就迅速地衰退了。这衰退遍布信仰、政治、道德和诗学,包括人与动物相互凝视、相互尊重的古老关系。与此同时,技术理性的傲慢与偏见却在疯狂地生长。艺术,或者文化的功能质变集中反映了这一切:文化原是自然与社会的中介,如今,进入文化的一切都必须切断与自然的关联。以往大自然提供的生生不息、世代交替的循环,现在由大众传播和以物易物的方式取代;前现代的图像需要长时间的欣赏和思考,而平面设计却尽可能排除沉思……这就意味着,批评意见常常孤立于当前,无力越过刺耳的声音和机会主义的偏见。这种观点与著名的社会学者齐格蒙德·鲍曼几乎完全一致。从《现代性与大屠杀》、《废弃的生命》到《流动的生活》,鲍曼的作品有着一脉相承的阴郁主题:“二战”中的大屠杀并非德意志民族的一次反常行为,而是现代性本身的固有可能。它是设计者、执行者和受害者密切合作的社会集体行动。即使在今天,大屠杀的阴影从未远离我们,被围困的个人在流沙上行走,消费主义把教育变成了出卖自我的准备……
在文学批评方面,其实不只是以对“东方主义”的批判享誉世界的萨义德喜欢音乐和艺术,更引人深思的是弗兰克·克默德。由于学识渊博,人们更愿意把这位剑桥教授直接称为批评家。一九六七年,在布林·莫尔学院六次讲座的结集《结尾的意义》里,他讨论了终末论与小说阅读和写作的关系。克默德的关键词是“虚构”,在福柯或德里达那里,它可能会被兑换成“话语”或“修辞”,但这个概念在他那里保留了浓浓的启示味道。他像莎士比亚本人那样把悲剧和梦幻融入一种神秘的整体中,当现代性的陈词滥调在他的作品中响起时,又变得像元祖级卡珊德拉那样古雅动听了。在这个对“末日”的虚拟消费与真实恐慌并存的年份,重读这本著作更显得意味深长。克氏的基本观点是:对终结的看法总是会反身影响初始与中途;是结尾,为整个故事镀上了光泽。而在这个诸神流窜的时代,不只有一个结尾,而有各种结尾。他重述了世纪末与基督教的末日之间的暧昧关系,这关系在美国导演科波拉的电影名作《现代启示录》的越战场景中得到了精确的复制:瓦格纳的旋律回荡在六十年代的越南上空。
…………
相比于预言技艺的精湛,卡珊德拉的特点是不擅长提供解决方案。对于科耶夫来说,历史的终结并不意味着探求人类乌托邦可能性的终结,他只是相信在黑格尔—马克思之后,改变世界而非解释世界的时代已经到来。但即使个人的政治实践做出了榜样,唯有靠捐弃哲学家身份才能进行的社会实践又把整个知识的价值置于何地?同样,鲍曼的《现代性与大屠杀》被认为是大屠杀研究史料与观念的集大成之作,而解决方法却可称terrible:在我们对自己的道德水准和意志品格心知肚明的情况下,如何像鲍曼呼吁的那样,令每一个个体在任何情况下都无条件地承担起他的道德责任?刚刚在伯格对传统的思恋中回过头来,我们就被维利里奥在交通、电影、建筑等各个空间里的围堵逼得走投无路;而正像其出发点是话语,其终结也是话语一样,福柯们的基本方案也正是他们的基本困境所在。另一方面,就连德勒兹本人也感到害怕:“人之后又是谁,是一个必须提问又只能浅尝辄止的问题—不然我们就只能和卡通人物厮混了。”伟大而优雅的克默德让我们知悉,当代文学的功能是在不相信开头和结尾的时代努力讲好一个关于断裂和危机的故事,但小说家如何能够完成这个高难度动作:“既能发现纯粹的连续性,又不使自己变得连续?”最后,一个如此深刻地怀疑现代性的人,如何能够同时在其生活中成为一个标准的现代性产品,看看鲍德里亚本人就知道了。
或者思想本身就以其问题,而非答案著称(还是要引用鲍德里亚:我们永远都不会知道思想是不是一种欺诈,这就是天意)。最后,本文开头的三种情况,并没有得到圆满的解答。当然,我们应该原谅卡珊德拉:十九世纪末的普通人可能怀揣着与本雅明“背向未来”的历史天使同样的疑问—光荣与梦想的时代是正在开始,还是刚刚结束?而在二十世纪末,好像所有的答案都已写好,只是要读到它,就如同从失去指针的钟上读出时间,或让机器人写下未来一样不可思议。但,批判现代性群体仍然需要保持某种对虚荣心的警惕:他们很容易把自我的价值加倍投射于发现的快感之中,其结果是,关于消极能力的预言本身变得太多了。意味深长的是,这些西方的卡珊德拉仍然是中国的人文知识人大量模仿和引用的对象。资本流动天下,但政治仍然是地域性的,扣着现代性帽子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革命之后的大同世界仍然是一个绕不过去的主题,这个更加现实的问题与终结论之间碰撞出的火花,造成了中国卡珊德拉“全盘西化”的情况。—如何处理这个矛盾?这是摆在预言家与生活在“末世”的民众面前的共同问题。它期待着一个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