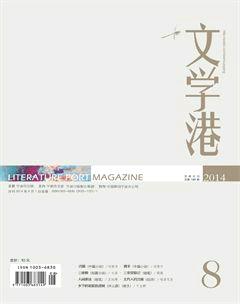三余堂散记
商震
96
一直想谈谈当下诗歌批评的状况,一直都懒得去说。就像我们经常看到有人当街扔垃圾吐痰一样,因司空见惯而认可。我这样说,并不是当下没有好的诗歌批评和好的诗歌批评家。而是好的批评和好的批评家太少。有一个现象是奇怪的,这些年都想当批评家,竟使得批评家多如牛毛。批评家多不是怪事,自诩是批评家者太多,就是怪事。最怪的是:只会浮浅地表扬也自称是批评家。为啥都想当批评家?不言自明:有利可图!骗钱者有;骗色着亦有。沽名钓誉者多;无知蒙事者多。具体例子我就不举了,给那些假批评家留点儿面子,也给自己积点儿阴德。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诗歌批评家?当然是有知识,有个人见解,有自己主张的思想者。思想者是永远醒着的人。那么,批评家应当是经验的,还是理性的?我想:没有理性支撑的人难为批评家,同样,没有经验的人也难称批评家。经验和理性不是一对天敌,对批评家来说是“人”字的一撇一捺。一个批评家,首相要对文本提出“为什么?”并能回答这个“为什么?”要在理论的范畴里自圆其说,要能征服作者和读者。不是把书本里的专业术语堆砌在一起吓唬人,也不是对作品中的字词句进行反复推论。我想大胆地说:诗歌评论绝不是科学范畴,或绝不可能成为一门科学。首先,诗歌批评一定要具有强烈的个人性,失去了个人性的批评,就是对以往理论的总结和归纳。其次,诗歌批评所关注的价值是情感,而情感恰好是科学要忽略的价值。若像分析天文地理那样去分析诗歌,像辨析石头的纹理植物的叶脉那样去辨析诗歌,诗人还能是感情动物吗?
诗人是感情动物,诗歌作品也是感情的产物,在感情世界里,怎样产生科学?
诗歌批评只能是对所批评的作品给批评家的感受做推理论述,而这个论述的检验标准是感情,不是宏大理论的卖弄。不能用一种道德代替另一种道德,更不能用书本理念代替感情。
至于那些打着批评家的幌子,挪用一些貌似高妙理论来蒙事的人,就不多说他们了。因为,他们只能蒙低俗的人。
97
做了二十几年文学编辑,最怕的事就是走到哪儿都躲不开文学。上班读文学稿子是职业需要,可是和朋友吃个饭,也要有人和你谈文学,喝个茶也有人和你谈文学,游山玩水时,也会有人跑过来和你谈文学。真烦!我当然理解那些不失时机来找我谈文学的人,可就是没人理解我这个想不失时机躲开文学的人。
能正身修德的是世道人伦;能滋养心脾的是风花雪月。所以,我从事了大半生文学,还是关注世道人伦,热爱风花雪月。
98
前些日子,看到一位久违的女士。真是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原来的一副苦哈哈的脸,现在竟是春光灿烂。一问,方知她五年内离了三次婚,并靠离婚发财了。真是生财有道啊!
我们不去说婚姻法怎样努力地保护女性而让一些女性有了靠离婚发财的“道”,也不想说用婚姻形式卖身比妓女光彩多少,只想说,用神圣的婚姻发财,不是把自己弄得只有虚情假意了吗!尽管我们每个人也不可能在婚姻状态里完全是真爱,但决不能完全是假爱吧!
我得到的体会是:虚情假意无人能得到真正的幸福,无人可得到安宁,也不可能有真正的性爱。
用肉体愚弄自己,总有一天情感会发起报复,而且会是毁灭性的报复。像民谚说的那样,“不是不报,时机未到”。发这个感慨的同时,也要发问:哪个婚姻还是可靠的?即使不怕失财,还不怕失去使用真感情的胆量嘛!
99
几年前,我曾多次想动笔写一篇小说,写一篇荒诞小说。题目都起好了,叫《今天,地铁休息》,内容是某年某月某日,北京地铁因某种原因停运一天。然后说因地铁停运带来的各种状况。混乱,大混乱!地面交通瘫痪,人如热锅上的蚂蚁。各种秩序无章可循:有党政机关的;有企事业单位的;有个人家庭的。生老病死、恩爱情仇,在地铁停运这天都会有个意想不到的爆发和结局。等等。我是想按荒诞小说去写,可我转念一想,如果地铁真的停运一天,我会怎样?我们身边的人与事会怎样?我的笔触无论如何也无法写尽那种状态的。
有写这篇荒诞小说的想法,是我多次在地铁的拥挤中产生的。
一次,早晨坐地铁上班,地铁进站,我站在人群里不用主动用力,就被后面的乘客推进车厢。进车厢后就一动不能动。我稍一低头,和我面面相觑的是一位青年女士,两个人胸贴胸无缝隙地站着。被推上车时我的双手一直是举起的,此时,我的双手是无论如何都无法放下了,放下手就要从这位女士的胸前挤过去。这可不仅仅是“瓜田李下”之嫌,身体任何部位动一下都可能招来非礼的责骂。直到下一站,车门开了,车厢内的人才可以活动一下身体,我才转过身去,背对着这位女士,才让我紧张的神情得以放松。我当时就想,这地铁会发生多少故事?尴尬的,扭曲的,温暖的,甜蜜的一定都有。
地铁六号线刚开通时,我就开始乘坐。前三天,车厢里宽敞明亮,人流有序,我感觉六号线是北京运行速度最快的地铁。三天后就拥挤不堪了。我还嘀咕:这些人都是从哪来的?我一边抱怨拥挤,一边庆幸六号线又为地面交通减轻了不小的压力,那些不用开车上班的人,又为减少大气污染做了贡献。我原来一直是乘坐公交车或打出租车上下班的。因饱受地面拥堵之煎熬,才下定决心走近两公里到地铁站,也下地铁。
有一次,我真的遇到地铁停驶。我在六号线呼家楼站换乘十号线,那天,十号线就单向停运一小时,我们所有换乘的乘客都往地面上走。哪里是走?简直就是随着人潮飘出地铁口。到了地面,依然是迈不动脚步,人挨着人地缓慢移动。公共汽车被挤得走不了,出租车没有空车。彼时,呼家楼地铁站口一片混乱。我溜着人群的边上一步一步地走到了单位。走一步念叨一句:没有地铁,真可怕。
有网友这样调侃说:地铁是活人上车,相片出来;饼干上车,面粉出来。我觉得这两句还是客观、客气的。还有两句就不好接受了:有在地铁里挤离婚的,有在地铁里挤怀孕的。等等。可以这样说:乘客在地铁里,不仅是过客,而是一天中重要的一段生活。地铁里有人间百态,有一个人的道德修养,有人生观、价值观。地铁是社会状况的一面镜子。endprint
地铁每天要运送多少人次,会有专业部门来统计。地铁里每天要发生多少故事,没人来收集。不过,可以肯定地说:社会上有什么事,地铁里就会发生什么事。
地铁,已经不是用交通工具这个简单概念可以涵盖的事物。它不只是有轨的车,是社会形态的组成部分,是城市重要的生命运输线。
大概没有哪一种事物,像地铁这样被信赖,被依赖;被抱怨,被痛恨。被嘴里怨恨心里喜欢着。
目前,北京地铁的总长度有370公里,已经是世界城市地铁排名第二,但仍然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人口和人们对地铁日益增长的依赖。据说,到了2015年,北京地铁将达到662公里,那时会怎样呢?依然不敢乐观。城市规模在不断扩大,社会分工在不断细化,人口的流动性不会减弱。我们只能期待地铁有序发展,有序运行,来保证我们各行各业的有序发展和运行。
春天来了,地铁运行在春天里,春天走了,地铁依然要运行在春天里。春天里的故事必然会次序发生。地铁里的事,是人间的事,是和你我息息相关的事。
我至今也没动笔写那篇荒诞小说,一是怕自己写得不够荒诞,被读者认为是真实事件;二是,我怕写不尽地铁真的停运一天会发生的那些荒诞事,让读者看到我的无才。最重要的是:我怕地铁真的停运一天!
100
这是我今年第一次看到蝴蝶,在云南的漾濞。
一只白色的蝴蝶,轻盈而优雅地在我眼前舞动着双翅,她白得洁净,白得夺目。我喜欢白色。我一向认为白色是最丰富的色系,它蕴藏了天下所有的色彩。
这只白色的蝴蝶,像在逛花园,像在独自散步,在漾濞的这条千年的茶马古道上,悠哉游哉,翩然跹然。我的目光追随着她,一直到花草的深处。
我是专程来看这条路,看这条千年古道的。当地人称作“老街”。
有人迹的地方,就会有路。有人迹有路,就会有历史;有历史的路,就会有让人心动的故事,就会提示今天的人们怎样走路、修路、护路。
我喜欢读史,读史是为了知今。
有一幅中国历史上所有茶马古道的线路地图,其中一条是由中原至昆明再至漾濞再至缅甸、印度。现在,我脚下的这条路,就是上边说的那条茶马古道保存最好的一段——漾濞段。
路面的石板随处残留着历史的痕迹,路边的建筑依稀可见当年的繁华,甚至可以想象当年这里人喧马嘶驼铃响的景象。这段老街,曾经是个街市,驿站。可以肯定,中国历史上发生过的事,都曾经在这里风云际会。
走在这样的老街上,并不是要刻意去挖掘那些被炒热了放凉了再炒热再放凉的故事。我一直认为,历史上所有古道、街市、驿站的故事都是大同小异的,只是人物、场景不同,细节略有所别而已。至于那些故事的社会意义、教育意义早已成为常识,“三尺小童即可背诵”了。
我走在这条老街上,一是想看看那些“衣上征尘杂酒痕”的马帮伙计们,当年走的是什么样的路;二是体会一下“古人不见今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的意境。
其实,路,就是路。只是历经了千年,便成了风景。成了风景,便有人来游览,便有我这等文人墨客神经兮兮地来发感慨。路,是不会理睬我这等人的感慨的。路听到的东西太多了,看到的东西也太多了。路把耳闻目睹的事都记录下来,却不会去传播。路珍藏着所有的风花雪月、刀光剑影。也许,那些不能言传、永久珍藏的东西,才是最真实的。
路,一直都是被动的。鲁迅先生说:“走的人多了,便成了路。”人们最初“走”出路来,是为了生存的需要,或叫经济的需要。后来,路的用处多了,人们又强加给它了政治、军事、文化等命名。
站在漾濞这条老街抬眼向山上望去,就能看到另一条盘桓在半山间的白练一样的路。那就是被誉为抗日战争生命线的滇缅公路。那条路是专为抗日战争修的供给线。当时,老百姓用最原始的方法修建成了最难修建的路。三千里公路,用三千条人命换来,为了一个民族的存亡,这里的老百姓用最朴素也是最珍贵的生命来修那条路,护那条路。那条路已载入战争史、民族史和筑路史。
想富,要修路;想生存,也要修路。
路,总是一些人在修建,一些人在毁坏。一些人在路上走过,一些人在路上倒下。从路上走过的人,会铭记自己的脚步;在路上倒下的人,就永远铭刻在路上。大部分的路都比人的寿命长,所以,人们常常会记得这样或那样的路,而在路上走过或倒下的这样和那样的人,随着时间的磨蚀,就渐渐地模糊,以至落花流水了无踪影。
现代人不太注意读史,一是活得现实,眼前的事常让人目不暇接、措手不及;二是活得轻松,认为历史的事都是“莫须有”的,明天也可以莫衷一是。这不是现代人的错。我们的历史常被“颠倒过来再颠倒过去”,人们不知该信哪一句。还有,现代生活的节奏太快了,每天紧张地学习、工作,仍然觉得自己落后。
历史是无言的,人若刻意地搬动,就会有是非,就像路。
站着的人,走躺着的路;躺着的路,承载着人类的所有悲欢。
“马上相逢无纸笔,凭君传语报平安。”“古道西风瘦马,小桥流水人家,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春风知别苦,不遣柳条青。”等等,这些与路有关的诗句,读来都是让人“怆然而涕下”的。
漾濞老街的一端是漾濞江,江上一座铁索桥名曰“云龙桥”。人走在桥上要上下左右地摇晃。桥是路,而且是更为生动的路。尤其是这种摇摇晃晃的桥。常有老人对孩子说:“我走过的桥比你走过的路都长。”老人说的桥,大概就是这种摇摇晃晃的桥。没有生活经验的孩子是不懂得路会摇晃的。历史告诉我们,那些被称作政治、军事、经济、文化要塞之路,都是摇摇晃晃的。
云龙桥边有一小日杂商店,店主人是一对中年夫妻。我们一行人走累了,在此小憩,买几瓶水。这对夫妻听说我们是外地人,是专程来看老街和云龙桥的,便把家里能坐的家什都搬出来让我们坐。一时,椅子,板凳,马扎摆了一排,还把自己家树上的果子,坛子里腌制的梅子拿出来让我们吃。我们一边感谢一边大为惊诧:“此地民风依然如此淳朴。”
路是旧的,人是新的。老百姓的生活态度几千年始终不会有太大的改变。尤其是在这远离灯红酒绿的山区。
漾濞江依然不舍昼夜地流着,茶马古道依然素面朝天。我沿着这条老街往回走,又看到了蝴蝶,是两只。是两只色彩绚丽的互相追逐的蝴蝶。有人看到蝴蝶就会想起一些浪漫的事或悲壮的事,而我,只想到了青春。
这千年老街上有彩蝶飞舞,就会有青春的脚步。
老街不老,老的都是那些“不废江河万古流”的人和事。endprint
——谨以献给漾濞5.21地震救援的消防指战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