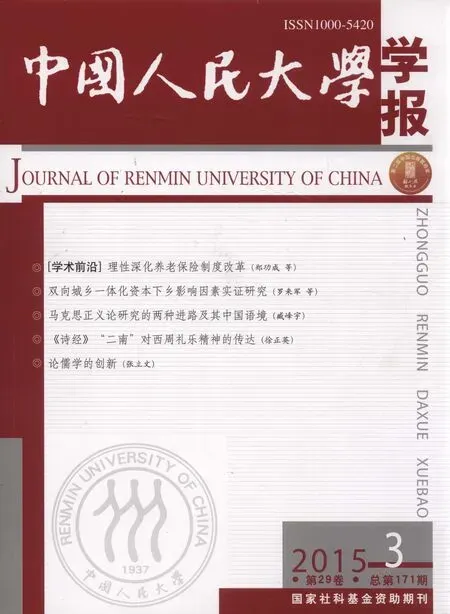西方左翼两种典型的可持续发展研究范式
李建群 刘晓勇
西方左翼两种典型的可持续发展研究范式
李建群 刘晓勇
西方左翼学者研究可持续发展主要有两种典型范式:一是以萨拉·萨卡为代表的“增长极限的研究范式”,二是以约翰·贝拉米·福斯特为代表的“物质变换的研究范式”。这两种范式的差异集中反映在对经济增长的基本态度、对社会主义的基本设想和对社会变革主体力量的分歧上。这些分歧既可以追溯到马尔萨斯及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马尔萨斯主义的批判,又呈现出形而上学时代所不具有的新特征,涉及当代全球发展的普遍困惑。深入研究西方左翼可持续发展理论及其内在张力,对推进中国社会可持续发展具有借鉴意义。
西方左翼;可持续发展;研究范式
西方左翼*苏东剧变后,由于西方左翼向右翼单向靠拢,造成左右翼界限日渐模糊,但西方政党政治的运作机制和既定选举规则仍将继续维系左右翼谱系的划分。本文之“西方左翼”专指西方社会提倡某种反资本主义方案又服膺社会主义的批判知识分子群体。理论界的可持续发展研究,依其基本范畴所构成的概念系统,形成了两种迥然不同的研究范式:一是以萨拉·萨卡(Saral Sarkar)为代表的“增长极限的研究范式”,二是以约翰·贝拉米·福斯特(John Bellamy Foster)为代表的“物质变换的研究范式”。*在西方左翼学者中,持和萨卡相似可持续发展观的还有美国学者丹尼斯·米都斯(Dennis L Meadows)、莱斯特·R·布朗(Lester Russell Brown)和英国学者特德·本顿(Ted Benton)、K·J·沃克(K.J.Walker);持和福斯特相似可持续发展观因而认同其理论的知名学者有加拿大学者尹恩·安格斯(Ian Angus),英国学者雷纳·格雷德曼(Reiner Grundmann),美国学者戴维·佩珀(David Pepper)和保罗·柏克特(Paul Burkett)。印裔德籍学者萨拉·萨卡以其对资本主义的不可持续性持“最为强烈和最有价值的批评”而培育了“左翼生态运动的理论之根”[1],成为当今世界知名的社会主义分子和绿党成员。美国俄勒冈大学教授约翰·贝拉米·福斯特作为著名左翼刊物《每月评论》和《组织与环境》的基金会主席和主编,以其具有高度原创性的可持续发展理论专著,被视为当代世界“最有号召力和思想力的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甚至被誉为“西方左翼思潮的中流砥柱”[2]。本文尝试对以萨卡和福斯特为代表的两种典型的可持续发展研究范式及其内在理论张力进行考察,以期对当代中国社会发展有所借鉴。
一、西方左翼可持续发展理论的两种基本范式
(一)萨卡的“增长极限的研究范式”
“增长极限的研究范式”是萨卡在20世纪90年代遭受“双重打击”之后深刻反省的产物。一方面,随着1989年柏林墙的倒塌,东欧的社会主义集团像多米诺骨牌一样轰然坍塌,“无论从何种意义上讲,社会主义都遭到了极大的震撼,或者说是深深的沮丧”;另一方面,自从1972年罗马俱乐部《增长的极限》发布以来,没有一个国家为保护环境而限制经济增长,甚至“在曾经发生过生态运动的地方,生态运动在所有层面都渐渐平息了下来”。[3](P1)社会剧变使得“不仅是一名社会主义者,还是西德绿党的一名积极分子”[3](P1)的萨卡深受震动,陷入了对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深刻反思。在萨卡看来,资本主义以海量资源投入换取利润畸形增长,必然不可持续,但是,作为其对立面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也会失败?在大量实证研究的基础上,萨卡得出结论:一方面,社会主义国家遭遇经济失败,“主要是因为它遭遇了增长的极限”;另一方面是因为社会主义国家遭遇了道德失败,“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没有培养出一代‘新人’”。[4](P5-6)
萨卡指出,苏东社会主义国家在建国之初曾一致认为社会主义优越性的根本表现是它可以创造比西方更快的经济发展速度,使国民物质生活水平在短期内超过欧美。这种发展理念直接促使苏东各国不计生态成本地片面追求经济增长。当这种粗放式的经济增长达到一定程度,生态的负面累积就会产生质的变化。一方面,自然资源的开采成本直线上升,另一方面,生态持续恶化使国家不得不在防灾和医疗等方面付出巨资,其结果就是增速不断放缓的经济无力支付巨额的生态和社会治理费用,国民经济陷入恶性循环,人民对政权丧失信心。萨卡认为,同样的状况之所以没有在西欧和美国发生,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西方国家利用其在国际市场上的主导地位,从第三世界大量进口廉价能源和引进技术工人,把经济发展的生态恶果转嫁到第三世界国家。苏东国家则不同,它们没有取得世界市场的主导地位,国家性质也决定了其无法推行新殖民主义政策,相反,苏联继承了沙俄扩张的负面资产,那些享有和俄罗斯相同政治地位的落后地区甚至成为经济增长的负担,这些综合因素的累积效应致使苏联很快遭遇经济增长的生态极限。
如果说经济遭遇增长极限是苏联模式崩溃的根本原因,那么道德的沦丧则对这一过程起到了明显加速作用。萨卡认为,苏联模式的失败在于国内出现了一个新阶层,这个阶层通过行政特权拥有远高于劳动阶级的生活水准,而普通民众则处于无权状态。特权阶层和官僚主义的存在使共产主义道德成为人们耻笑的对象,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不复存在。对社会主义道德的侵蚀直接打击了人们的劳动热情和奉献精神,导致生产中资源的高效配置始终无法实现,整个苏联成为“公地悲剧”的翻版。萨卡说,“人民——每一个企业、每一个政府机关或部门、每一个个体——对待国家的资源,就像哈丁的抽象牧羊人对待他们的抽象牧场一样。不仅自然资源,而且拥有资金、设备和人力的国家、拥有机器和原料的企业以及所有的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都被看成是‘公用地’,被不可持续地、不合理地掠夺和滥用。”[5](P85)“公地效应”造成的资源浪费导致整个社会经济更加迅速地滑向“生态极限”。
在萨卡看来,苏东社会主义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真正的社会主义必须能够避免遭遇“生态极限”和实现可持续发展。萨卡的生态社会主义社会具有如下基本主张:第一,当今世界上所有致力于经济发展的理论都是增长范式的衍生品,而“饱受战争、内战、社会冲突、混乱、腐败、犯罪之苦的社会……都是我们今天的经济活动的后果”。[6](P210)第二,要想实现可持续发展,一定要压缩当前的经济规模,以此营造一个与生态环境共生的局面。第三,经济收缩必然导致较低的物质生活水准,要想让人们甘于忍受较低的物质生活水平,经济收缩的后果必须均等分摊。因此,提高道德水准是任何国家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第四,经济的收缩必须借助国家计划,这种计划只有在一个资源相对丰富的大国才有可能实现。第五,严格控制人口增长,特别是控制部分不发达国家的人口爆炸是当前最迫切的任务。
(二)福斯特的“物质变换的研究范式”
与萨卡主要基于对苏东社会主义模式的反思并以实证的方法提出其可持续发展理论不同,福斯特主要基于对资本主义的反思并以文本分析的方法提出了他的可持续发展范式。在福斯特看来,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阐发的世界观是一种深刻而系统的生态世界观,这种生态世界观通过历史地考察社会与自然以人的劳动为中介所进行的物质变换过程而再现了历史发展的整体逻辑。资本主义之所以无法摆脱生态危机的威胁,正是因为资本主义使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劳动关系发生了异化,造成资本主义社会人与自然、社会与自然物质变换关系的断裂,因此,资本主义社会的任何发展从根本上说都是不可持续的。福斯特援引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农业生产的分析,认为资本主义农业对利润的追求,导致城乡的分离和能量交换的停滞。一方面,从土地产出的有机分子不能回归到土地,土地越来越贫瘠;另一方面,城市排泄的巨量有机物不能回到土地,反而去污染城市环境。福斯特指出,资本主义农业对农业工人和土地施加了双重剥削,资本和技术的增加,都不过是剥夺土地和工人程度的增加。
尽管资本主义制度造成了空前严重的生态危机,但资产阶级学者始终拒绝承认,相反,他们相信在资本主义既定体制下,可持续发展完全能够实现。福斯特依据物质变换理论对此逐一驳斥。
福斯特首先批判了资产阶级学者提出的基于市场调节的可持续发展观。在资产阶级学者看来,资本主义社会应该构建起一种彻底的“环境经济学”,即将自然资源完全推向市场,认为只要建立彻底的自然价格体系,普遍核算环境成本,就能通过市场调控避免资源枯竭。他们声称,“环境危机与其说是市场的失灵,不如说是我们会计系统的失灵”。[7](P27)。在福斯特看来,资本主义经济学家把生态要素纳入市场交易之中并不能挽救生态危机,原因首先在于大部分生态要素的价格是不可度量的,即使可以度量,交易的结果也只能是对自然更大规模的剥夺;其二在于环境保护是整体和长期的行为,而利润的取得则是受益人越少越好,资本流通的时间越短越好,为了保证利润的获得,牺牲世界上大多数人的利益是情理之中的事。资本的扩张和环境的保护相互矛盾,在利润增长的同时实现物质变换平衡和生态可持续发展在理论和实践上都不可能。
其次,福斯特批判了资产阶级学者提出的基于道德进步的可持续发展观。在全球性生态危机的重压之下,部分资产阶级学者转而求助于一种融合了环境视域与人文视域的道德革命,他们认为:“我们滥用土地是因为我们把它视为属于我们的商品。当我们把土地看做是我们属于的共同体时,我们才会怀着敬爱使用它。”[8](P36)在福斯特看来,这种道德改革的呼吁具有很大的空想性,因为它完全无视现存社会“踏轮磨坊的生产方式”。[9](P36)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投资人必须不断扩大生产才不会被市场淘汰,工人只有停留在体制内,才能保证一份维持生计的工作,没有人会留意资本主义社会下物质变换的断裂,“几乎每一个人都是其中的脚踏轮上的一部分,既不可能也不愿意从中脱落”。[10](P37)福斯特指出,相对于个人对生态的不道德,存在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更高的不道德”。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大环境中,人们的道德义愤丧失了,犬儒主义大行其道,个人只有完全融入这个不道德的社会才能得到社会的认同,企图通过道德重建而不触及社会体制的可持续发展注定不会成功。
福斯特以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劳伦斯·萨默斯(Lawrence Henry Summers)在《经济学家》上发表的文章《让他们吃掉污染》为例,指明资本主义条件下社会与自然物质变换关系的断裂和由此引发的反人道结果。他指出,发达国家的丰裕是以不发达国家的贫乏为代价的,发达国家的可持续发展也是以不发达国家的不可持续发展为代价的。福斯特基于马克思物质变换观点提出了他的可持续发展理论:第一,只有实现了物质变换均衡的发展才是真正的可持续发展,才是真正以人为本的发展。第二,要想让可持续发展成为可能,必须纠正以发展名义导致的社会与自然物质变换的断裂。“正是资本主义世界的体制中心,存在着最尖锐的不可持续性发展的问题”。[11](P76)第三,经济发展本身并不必然带来物质变换的均衡状态,“对自然的剥夺也是一部分人对另外一部分人的剥夺;环境恶化也是人类关系的恶化”。要想实现人类与自然物质变换的均衡,就必须推翻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因此,“为创建更加绿色的世界而进行的斗争也必然与消除社会不公的斗争紧紧联系在一起”。[12](P75)第四,均衡的物质变换并不追求更多物质财富,而是追求适度的经济发展,只有这样,才能满足人类的基本需求和确保长期安全。
二、两种生态可持续发展研究范式的基本分歧
我们不难看到萨卡和福斯特在建设社会主义和反对资本主义这个原则立场上的一致性。萨卡说:“我之所以反对资本主义,则是因为它所代表的其他价值观:贪婪、残酷竞争和财富与收入方面的严重不平等。”[13]福斯特也表示:“我们需要……使自然与人类社会高于资本积累,公平与公正高于个体贪婪。”[14](P76)但是,萨卡和福斯特各自的可持续发展理论的确是当代西方左翼思潮中两种具有显著区别的理论范式。这些区别包括:生态可持续发展的理论起点、阻碍生态可持续发展的根本原因以及对实现可持续发展基本途径和主体力量的判断。
(一)可持续发展的理论起点:生态中心主义还是人类中心主义?
从理论出发点看,萨卡和福斯特都对深生态学及生态中心主义持反对立场,但是,这绝不意味着二者对人类中心主义的认识趋同。福斯特支持的是人与自然均衡发展、共同进化的人类中心主义,他说:“人类与自然是相互关联的,而任何特定时期构成这一相互关联的核心则是历史上特定的生产关系形态。”[15](P178)他针对那些将马克思简单地指认为是培根那样的“支配自然的支持者”的观点持明确的批判立场:“从一贯的唯物主义立场出发,这个问题不是人类中心主义与生态中心主义相对立的问题——实际上,这种二元对立的思想对我们理解人类在生物圈中存在的、真实的、不断变化的物质条件并无裨益——而是一个两者共同进化的问题。”[16](P13)因此,针对那些把马克思主义理解为“支配自然”的朴素的人类中心主义的观点,福斯特认为它们“具有机械论的特征,它可能遭到浪漫主义、社会有机论、生机论以及后现代主义观点的反对”。[17](P13)
相比较而言,萨卡反对生态中心主义和赞成人类中心主义的理由要简单得多。在萨卡看来,我们主张人类中心主义:一方面是因为人类除了人类中心主义别无选择,“因为我们是人类,所以我们是人类中心主义……没有一个物种希望自己灭绝或增加痛苦”[18](P10);另一方面,人类中心主义具有先天的超越优势,“人类已经具备超越自身利益和其他物种利益之上的能力……如果我们认为人类只是自然界中的众多物种之一并与其他物种平等的话,我们就没有额外的道德义务去保护其他物种”。[19](P12)但事实上,人类是唯一能够抗拒自然选择的物种,他们不仅允许弱者孕育子女,为穷人提供饭食,也“希望保护那些濒临灭绝的物种” 。[20](P11)因此,“无论如何,我们似乎也无法避免人类中心主义”。[21](P13)
(二)生态可持续发展的核心障碍:资本主义抑或工业经济?
生态恶化的最终根源在哪里?福斯特认定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福斯特看来,可持续发展与资本主义无法兼容,因为“不论自然资本的修辞如何动听,资本主义体系的运行却没有本质上的改变,也不能期望它改变。把自然和地球描绘成资本,其目的主要是要掩盖为了实现商品交换而对自然极尽掠夺的现实”。[22](P28)福斯特认为,不但资本主义的增长,而且资本主义的危机,对于生态而言都是灾难,因为在经济衰退期间,资本主义会更加赤裸裸地抵制环境保护规章。“正是在资本主义世界的体制中心,存在着最尖锐的不可持续发展的问题。因此,生态斗争不能与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相分离,而当人们从剥夺地球资源的角度看问题时,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将呈现出新的含义”。[23](P76)
萨卡虽然也认为资本主义是生态危机的切近原因,但他把最终根源追溯得更远。萨卡认为,市场经济和工业社会才是生态危机的根本原因,资本主义充其量只是工业社会的表象之一。萨卡之所以详尽分析苏东社会主义的失败,就是要服务于一个结论:突破了增长极限的社会主义的工业发展和资本主义的工业发展都是生态危机的罪魁祸首。如此一来,萨卡批驳了那些试图抬出“工业社会的生态重组”或“生态社会的市场经济”等救世方案的理论家,这些人认为,“科学与技术的进一步发展以及科技的进一步强化应用,将使人类能够克服生态危机”,或者“一些局部性的经济革新,如污染许可证、生态税改革等,将会使今天的资本主义转变成生态资本主义”。[24](P3)对这些方案,萨卡一概斥之为“普遍的幻象”。萨卡把自己的解决方案称作“激进的生态社会主义”,认为挽救生态灾难的“既不是市场经济(我认为市场经济只不过是资本主义的一种婉转说法),也不是工业社会”[25](P4),而是一种既反市场经济又反工业社会的前工业社会。
(三)可持续发展的实现途径:适度经济增长还是限制经济增长?
萨卡不赞成经济增长,相反,他极力批评那些“乌托邦主义的增长崇拜者”[26],提出了“增长极限”的可持续发展范式。他说:“当前的生态危机所激发的大部分生态运动和大多数民众是支持和相信工业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的……在我看来,持这种观点的人……似乎仍然是在发展的范式中思考。”[27](P20)他进一步得出结论:“我们首先需要的是一种思维范式的转换——从一种迄今占主导的增长范式转变到我所讲的极限增长范式。”[28]由于萨卡把生态破坏的原因归结为工业社会,他甚至主张“人类从地球的大部分地区撤退,然后将腾出来的地方重新变成不受人类干预的荒野”。[29]在萨卡看来,人的幸福与否同物质丰富程度没有必然关系,只要保证了人的基本生存,社会分配的公平和道德素养的提高决定了人类的幸福程度,因此,美好的社会绝非物质丰富的工业社会,而是倒退回前工业社会的原始社会。
与之相反,福斯特认为选择一种与生态更加协调的工业社会是可能的。他说:“是否意味着那些关心地球命运的人们就应该完全放弃经济发展的目标呢?回答是否定的。”[30](P74)在福斯特看来,问题的实质不在于经济增长与否,而是“不采取一种批判的态度对待我们目前的社会形态就不可能回答这些问题。”[31](P74)“对经济的发展,生态学的态度是适度,而不是更多。”[32](P42)只要能够保障物质变换的均衡,经济增长是社会主义的内在含义。换句话说,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受制于人与人的关系,一个健全的社会制度完全有能力实现人与自然物质变换均衡基础上的经济增长。而且在现实层面上,生态社会主义必须追求经济增长,因为“在世界贫困地区,经济发展仍有必要”。[33](P74)对福斯特而言,真正的社会主义应该建立在物质富裕的基础之上。
(四)可持续发展所依靠的主体力量:生态主义者还是工人阶级?
基于对“增长”范式的否定,萨卡坦言,建设具有“非工业社会”特征的“生态经济”,工人阶级无足轻重。生态社会主义者不会“以像从前那样简单的方式为了工人阶级的物质利益而战斗”,相反,不得不告诉工人“对环境的健康而言……他们的生活水平太高了”。[34](P235)如此一来,那种相信“无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的形成,其利益与全人类的利益相一致,而且全世界的无产阶级能够并将团结起来”[35](P235)的信念,在增长极限这一事实面前显得过于荒谬。在他看来,生态社会主义者必须放弃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先锋作用的幻想,不能“无限期地等待工人阶级的领导作用”。[36](P238)相反,萨卡更多诉诸于知识分子的文化和道德引领作用,认为要想构建生态社会主义社会,作为这一运动的领导者的只能是生态社会主义者,而社会生态道德的大幅度提高,既是运动的前提又是运动的目标。
福斯特的生态可持续发展观表现出对工人阶级和工人运动更多的信赖。他认为生态社会主义者必须承认经济基础在影响意识和行为中的重要性,而工人阶级作为经济行为的集体承担者,一定会在社会变革中发挥关键性的作用。福斯特总结绿色分子保护美国西北太平洋沿岸原始森林的斗争教训,认为西方生态绿党之所以失败,正是因为他们脱离了阶级斗争的“堂吉诃德式的单打独斗”。由此,他反驳萨卡式的道德革命论,“试图通过教育和示范性生活方式实现的一种大众意识的革命是有局限的,而且可能是令人遗憾的”,而且“只有承认环境的敌人不是人类(不论是作为个体还是集体),而是我们所在的特定历史阶段的经济和社会秩序,我们才能够为拯救地球而进行的真正意义上的道德革命寻找到充分的共同基础”。[37](P43)事实上,工人阶级因受到资本家的压榨而成为资本的天然反对力量,福斯特得出结论:“忽视阶级和其他社会不公而独立开展的生态运动,充其量只能是成功地转移环境问题”[38](P97),而有效的生态斗争必须要和阶级斗争结合起来。
三、两种范式分歧的理论渊源及对两种范式的评价
当代西方左翼两种可持续发展研究范式的分歧可以指向同一个理论渊源,这就是马尔萨斯主义以及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马尔萨斯的批判。萨卡的“增长极限的研究范式”的理论依据是马尔萨斯的人口论。他说,“马克思、恩格斯及其追随者的失败之处在于,他们拒绝接受马尔萨斯在人口问题上提出的观点的真理性”[39],因此,研究可持续发展“必须从马尔萨斯开始”。[40](P134)而福斯特则直接将其“物质变换的研究范式”奠基在马克思、恩格斯对马尔萨斯的批判之上。他认为,“马克思从1844年直到1883年去世,其政治经济学的一个中心主题就是批判马尔萨斯及其著作中所代表的所有关于人口和土地之间关系的理论”,而且“对马尔萨斯土地理论的批判……成为马克思唯物主义历史观和唯物主义自然观发展史上具有标志性意义的时刻”。[41](P117)
众所周知,马尔萨斯在《人口原理》一书中提出了这样的论断:人口以几何级数增长,食物以算术级数增长,后者永远赶不上前者,这个超越历史的永恒自然规律是人类社会悲惨境遇和不可持续的根本原因,人类如不能理性地限制人口,必将陷入幸福与灾难的循环往复。在萨卡看来,人口的增长是一种内嵌于人类基因中的繁殖本能,而粮食产量则纯粹取决于自然变量,不管科学如何进步,时代如何变迁,这个法则永远有效。正是出于对马尔萨斯人口论的推崇,反对将人和自然的相互关系放在生产关系的历史维度来考察,萨卡接受了马尔萨斯的理论范式,因此,他的可持续发展模式才会将限制人口增长、限制工业社会和回归荒野等作为重要举措,所提出的依靠道德重建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观点也与马尔萨斯的道德转型论一致。
福斯特通过深入分析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经典文本,继承并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对马尔萨斯主义的批判。他首先批驳了马尔萨斯在研究方法上的错误。马尔萨斯为了替自己的研究方法辩护,声称人口按几何级数增长“已经由美国相关的增长立即得到证明”,而食物按算术级数增长,“一经宣布就立即得到证明”。[42](P106-107)福斯特援引一位学者的论述:“这些话,如果真有什么意义的话,那么一定是:几何级数在有限的证据基础之上得到承认,而算术级数则根本没有任何证据加以确认。”[43](P107)在福斯特看来,马尔萨斯的人口原理并无事实根据,主观臆测的自然法则已经被人类历史发展的事实和达尔文进化论所证伪。事实上,人与自然的关系绝非永恒的自然法则,而是动态的历史过程。他说:“马克思的分析说得明白:人类与自然是相互关联的,而任何特定时期构成这一关联的核心则是历史上特定的生产关系形态。”[44](P178)正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造成了物质变换的断裂,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就必须改变导致人与自然关系异化的生产关系,即推翻资本主义。
人类社会发展的核心动力是劳动生产力,基于人和自然是一个不可分割的统一体这一事实,劳动生产力的可持续发展就体现为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的可持续发展。资本主义社会之所以不可持续,正是因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破坏了劳动生产力发展的两个基本要素。一方面,资本以其强大的内在动力最大限度地掠夺劳动者的剩余劳动,造成对劳动力健康、智力和全面发展的破坏;另一方面,资本又有无限制地利用自然资源以占有剩余劳动的内在冲动,这必然造成自然资源储备的持续衰减和自然生态的持续恶化。正如马克思所言:“资本主义生产发展了社会生产过程的技术和结合,只是由于它同时破坏了一切财富的源泉——土地和工人。”[45](P553)因此,从根本上造成社会不可持续的原因正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而只有“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才能“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46](P926-927)这说明,只有在健全的生态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下,劳动者和自然资源遭受双重剥夺的现象才能被完全制止,对自然资源的合理规划和高效利用才能完全实现,经济发展的生态极限才能被大大推后,以至于像恩格斯所言的那样成为一种“抽象的可能性”。[47](P641)正是因为认识到一种合理的生产关系必然能培养出全面发展的劳动者,大力发展和正当使用科学技术,把对环境的破坏限定在环境自我净化能力之内,福斯特才并不反对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而是赞成一定程度的经济增长。
福斯特的合理之处也就是萨卡的迷误之处。第一,萨卡坚持用马尔萨斯的静态历史观分析人与自然的关系,把人口趋势、经济趋势或者政治生态学理解为自然法则,实际上是把人等同于草木禽兽,必将导致错误的结论。第二,萨卡反对工业社会,反对工业增长,看似对资本主义现存秩序毫不妥协,但是由于摈弃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导致他只能无可奈何地提出回归荒野的激进之策和道德革命的空想之举。正如马尔萨斯的意图是希望得出社会主义完全无用、这个世界必须“总有穷人”的结论一样,看似激进的萨卡也只能以对现存资本主义秩序的认可而告终。这说明,任何支持马尔萨斯人口原理的学者都应该认清一个实质:支持马尔萨斯的人口原理就意味着最终认可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萨卡否定科学技术发展的作用,否定经济增长的必要性,本质上还在于没有认清不同生产关系下的人的劳动的不同能动作用。在萨卡看来,发展中国家为改善生存状况而采取的经济发展举措是徒劳的,回归荒野似乎是人类最为幸福的事业,殊不知,在现有社会制度下,任何经济收缩和道德进步的主张注定是无法实现的乌托邦。
当然,萨卡的“增长极限的研究范式”并非全无道理,福斯特的“物质变换的研究范式”也并非无懈可击。萨卡的合理之处就在于真切地指明了一种现状之上的事实,即:如果当前的资本主义社会不能实现生产关系的深刻变革,不去调整制约人与自然关系的人与人的关系,经济增长的生态极限注定很快就会到来。事实上,正如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做过深入研究的法兰克福学派普遍认识到的那样,当今资本主义秩序已经出现了凝固化趋向,社会变革的可能似乎越来越渺茫。在这个社会阶层日益固化、消费主义渐成普世价值的时代里,萨卡的理论并非杞人忧天,它体现了一种超越国家与民族的人类共同责任感和危机意识。他的“增长极限的研究范式”无疑是资本狂欢时代的警世危言,是体制僵化国家的末日之钟。如前所述,萨卡以铁的事实证明,资本主义固然内在地引发生态危机,但是社会主义并不必然避免生态危机,社会主义社会发生的生态灾难同资本主义社会一样触目惊心,一个健全社会的建立显然还需要艰辛的努力和漫长的过程。在这个不断自我完善的过程中,社会主义遭遇经济发展的生态极限的可能性永远都会存在。萨卡注意到了社会发展的共时性却忽略了社会演进的历时性,福斯特注意到了社会发展的历史性却忽略了社会演进的复杂性,而社会发展恰恰是现实性和历史性的辩证统一。萨卡与福斯特的两种研究范式之争,尽管渊源于马克思和马尔萨斯,但是他们的争论却超越了那个时代形而上学的特征,触及了问题更为复杂的实践层面,触及了当今社会发展的普遍困惑,这是马尔萨斯和马克思那个时代不曾遇到过的新情况。
近40年来的高速发展使生态问题成为我国社会发展和经济增长的瓶颈。事实上,当代中国学界关于可持续发展也存在两种研究范式的激烈争论,相当一部分学者认为当前我国面临的生态危机是由人口和经济增长导致的,与社会制度无关*浙江大学教授原华荣在其“小人口”原理中就声称,人类面临的气候变暖、生物灭绝、暴力犯罪等“自然—社会危机”,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人口、经济增长导致的,与社会制度无关,非技术所能解决,因而提出口号:“持续性的症结是‘规模’而非‘均衡’。要么任其毁灭,要么缩减她的规模、速度和复杂性!”参见原华荣:《“马尔萨斯革命”和“适度人口”的“终结”——“小人口”原理》,第1卷,56页,北京,中国环境出版社,2013。,而另一部分学者则淡化甚至否认社会主义社会生态问题的严重性和紧迫性。通过对比研究萨卡和福斯特的可持续发展研究范式,我们可以得出的基本结论是: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绝不能由经济收缩来实现,对中国这样一个尚有几千万人口处在贫困线以下的发展中大国而言,适度的经济增长势在必行;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必须汲取苏东模式的教训,单纯依靠增加生产要素而实现的经济增长,是葬送国家和民族发展前途的饮鸩止渴之举;中国社会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必须依靠系统化、全方位的社会主义改革来实现,要通过对生产关系的深入改革来处理好市场经济与生态自然的物质变换关系,不断释放推进可持续发展的改革红利;我国人口基数庞大,是导致生态恶化不可否认的客观因素,这要求我们在深入改革的同时,不但要严格控制人口数量,更应采取措施优化人口结构,提高人口素质。必须承认,系统化的社会主义改革不可能一步到位,合理的生产关系的建立也极其复杂,生产关系的合理化改革永远都在路上,永远没有终点。
[1] Heide Castaneda.“Reevaluating Political Constructs of Ecology and Sustainability”.Culture&Agriculture,1999,21(3):59-60.
[2] Jacob Laksin.“Professor John Bellamy Foster:Profile”.http://www.discoverthenetwork.org/Articles/Professor%20John%20Bellamy%20Foster.htm.
[3][4][5][6][18][19][20][21][24][25][27][34][35][36][40] 萨拉·萨卡:《生态社会主义还是生态资本主义》,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8。
[7][8][9][10][11][12][14][22][23][30][31][32][33][37][38] 约翰·贝拉米·福斯特:《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
[13][26] 萨拉·萨卡:《资本主义还是生态社会主义——可持续社会的路径选择》,载《绿叶》,2008(6)。
[15][44] 埃伦·梅克辛斯·伍德,约翰·贝拉米·福斯特主编:《保卫历史:马克思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
[16][17][41][42][43] 约翰·贝拉米·福斯特:《马克思的生态学——唯物主义与自然》,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28] 萨拉·萨卡:《当代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载《国外理论动态》,2013(2)。
[29] Saral Sarkar.PachamamaandDeepEcology.http://groups.yahoo.com/group/EI-Network/message/4493。
[39] 萨拉·萨卡:《当今世界经济危机:一种生态社会主义分析》,载《北大马克思主义研究》,2010(1)。
[4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4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4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责任编辑 李 理)
On the Western Left-wing’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Research Paradigms
LI Jian-qun,LIU Xiao-yong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School,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Xi’an,Shanxi 710049)
There are two basic paradigms the Western Left-wing scholars studying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ne is represented by Saral Sarkar’s “limits of growth paradigm”, the other is represented by John Bellamy Foster’s “material transformation research paradigm”. The differences of the two paradigms are reflected in the author’s basic attitudes towards economic growth, the basic assumption of socialism and the main social force for social change. Such differences can be traced back to Thomas Malthus as well as Marx and Engels’s critique of Malthusian. Studying western leftist theory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its internal tension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promote sustainable social development in China.
western left-wing;sustainable development;research paradigms
李建群:西安交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刘晓勇:西安交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博士研究生(陕西 西安 7100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