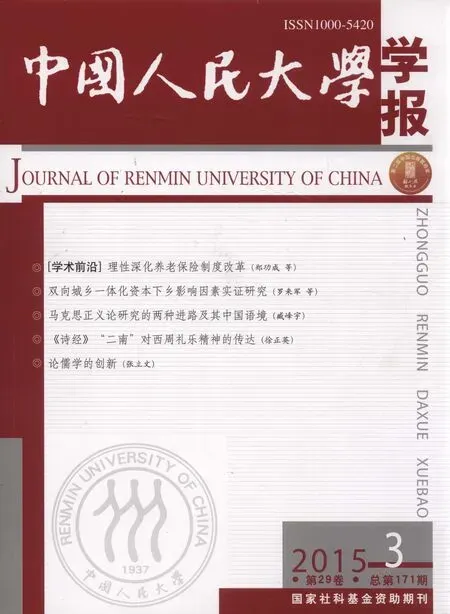从集部之末到自成体系——科学主义思潮影响下古文论研究的转型考察
顾文豪
从集部之末到自成体系
——科学主义思潮影响下古文论研究的转型考察
顾文豪
在古代文论研究现代转型的历史过程中,科学主义思潮的影响不容忽视。从古典诗文评对传统的扬弃到科学理性精神的高涨,从文论研究科学化的强调、中西融合古今对接的学术视野的形成,再到批评史体系的建构与完备,科学主义使得古代文论从古典直观形态趋向现代逻辑形态,从集部之末升等为自成体系的现代学科,重建了中国文学批评的历史图景。因此,对20世纪初科学主义思潮影响下的古代文论研究加以考察,可使我们进一步认识这一时期古代文论研究的发展进程,同时对于深入把握古代文论研究的现代转型亦有重要意义。
古代文论;科学主义;方法与进路
一、学术研究科学化意识的确立与衍化
“科学主义”,英文作“Scientism”,亦译为“唯科学主义”。严格来说,科学主义并非特指科学,而是指人们对待科学的态度和立场。关于科学主义的界说,在不同时期以及不同的观念体系中不尽相同,但不论何种形式的科学主义,最终都主张将自然科学的方法和观点扩展到非科学领域,成为理想的知识范型。正如有研究者指出,科学主义是“科学的形上之维”,是以科学为核心的科学方法的泛化延展,它坚信科学真理的绝对性、科学方法的普适性以及科学价值的扩张性,由此使得科学观念成为一种话语权威,施诸于不同知识领域。*关于“科学主义”的义界演变以及“科学主义”在中国的形成与发展过程,可参考杨国荣:《科学的形上之维——近代中国科学主义形成与衍化》,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李自强:《现代中国科学主义思潮》,郑州,郑州大学出版社,2001;段治文:《中国现代科学文化的兴起(1919—1936)》,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李丽:《科学主义在中国的历史与现实之省思》,复旦大学博士论文,2006;高瑞泉:《中国现代精神传统》,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9;汪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下卷,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
就20世纪初的中国知识界来说,随着经学时代的终结,传统的知识体系已无法应对中国的现代性危机,学科分化与独立迫在眉睫。同时,知识分子群体试图经由对科学真理的绝对推崇、科学方法的极端强调以及科学价值的确认,最终使科学为中国现代性发展提供观念支持。因此,在历史深因与现实语境的双重形塑下,在中西文化的冲撞交融下——虽然此时西方的科学主义已大致取得较为完备成熟的发展状态,超越了启蒙阶段,而现代中国的科学主义则偏于通过科学的实证方法与理性精神来开启现代性启蒙——欧洲16世纪之后诞生的现代科学渐始为中国知识分子所接受,与“民主”一词一起被肯认为现代中国的核心价值。
而随着科学在不同知识领域的日益滋蔓,其最特出的表现在于“把所有的实在都置于自然秩序之内,并相信仅有科学方法才能认识这种秩序的所有方面”[1](P17)。科学逐渐成为知识的理想形态以及判定知识合法性的重要依据,所谓“科学为正确知识之源”[2]。科学此时不仅是“救亡”与“革命”时代背景下中国现代化的必由之道,而且也被知识分子许为中国学术研究现代转型的关键所在。学者们试图以对科学精神的推举与科学方法的强调,促使人们重新审视固有文化,最终使得人文学科研究的学术言路与理论形态发生巨大变革。
为此,学者们首先对中国过往学术研究展开全面省思与批判。他们普遍认为,“中国学人大病在一空字”[3](P34),相较之下,西人学术则“愈变愈实”[4](P40),中国人“发明的东西虽不少,而对于有系统的纯正的科学建树几乎等于零”[5](P3),加以“中国人的心理偏向重综合而不喜分析,长于直觉而短于逻辑的思考”,造成中国学术缺乏“谨严的分析与逻辑的归纳”[6](P1)。亦即时人认为中国传统学术之弊乃在过于空疏、长于兴会的阐发,短于逻辑的归纳,可以情感、不能理究。
另外,由于不善综合,议论凿空,中国学术往往显得全无系统,缺乏条理。王国维批评那些国学遗老:“学问虽博,而无一贯之系统。”[7](P53)陈独秀明确宣称:“吾国人学术思想不进步之重大原因,乃在持论笼统,与辨理之不明。”[8](P253)许啸天更是激烈直言:“中国莫说没有一种有统系的学问,可怜,连那学问的名词也还不能成立!”[9](P6)对于学术研究的系统性确认,已经成为人们用以评价学术研究进步与否、科学与否的重要标准。此亦符合梁启超对科学与科学精神的定义:“有系统之真知识,叫做科学;可以教人求得有系统之真知识的方法,叫做科学精神。”[10](P3)由此,学者普遍认为用以补救中国固有学术之弊的根本途径,即是资鉴西方的科学精神与科学方法、创建符合现代科学要求的学术体系。
具体来说,这一新体系的建立主要表现在如下方面:
(一)以专精之分科成专精之学术
1919年朱希祖发表《整理中国最古书籍之方法论》一文,指出:“我们中国古书中属于历史的、哲学的、文学的,以及各项政治、法律、礼教、风俗,与夫建筑、制造等事,皆当由今日以前的古书中抽寻出来,用科学的方法,立于客观地位整理整理,拿来与外国的学问比较比较,或供世人讲科学的材料。”强调倘不用“科学的方法”,则“心思漂泊无定,是非既无定见,前后必不一致”[11](P97)。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一书亦表示:“社会日复杂,应治之学日多。学者断不能如清儒之专研古典。而固有之遗产,又不可蔑弃,则将来必有一派学者焉,用最新的科学方法,将旧学分科整治,撷其粹,存其真,续清儒未竟之绪,而益加以精严。”[12](P107)1929年何炳松《论所谓“国学”》一文倡议:“当现在分工制度和分析方法都极发达的时代……让我们大家分头都藏到‘壁角’里去,老老实实做一点文学的、史学的、哲学的、科学的或者其他各种学术的小工作。”[13]胡朴安《整理中国学术之意见》则强调中国之旧学术“若不加以整理,仍旧为经、史、子、集的系统,不但世界学者不能了解中国的学术真相,就是中国的后起者,对于中国的学术,亦渐渐生鄙弃的心”[14](P198-199)。诸家皆意在批评中国传统学术各学科畛域不清,提倡打破原先囫囵相混的学术体系,以使各学科做更精细明确的擘画,最终造成更专精细致的研究。
(二)以系统之研究清整固有文化
学科细分的最终目的是为学术研究的系统化,清整学术系统的内在逻辑,即沈兼士所言“大凡一种学问欲得美满的效果,必基于系统的充分研究”[15](P362)。如果说中国固有学术传统以“博雅”为尚,那么在科学主义思潮影响下,“系统”逐渐取而代之,成为学术研究的新判准,所谓“凡学问之事其可称科学以上者,必不可无系统”[16](P202)。
系统化的具体表现即为条贯分明,层次清晰。顾颉刚指出章学诚《文史通义》“无声无息了近一百年”,要之即因清代学者皆“为琐碎的考证束缚住了”,直到欧化近来,“大家受了些科学的影响,又是对于外国学术条理明晰,自看有愧”,才懂得章著的价值。[17](P1002)胡朴安指出:“所谓系统者,谓能搜辑多种之书,以为一种学术之汇归,使人阅之,不必他求,而能明其原委也……使深沉之学术皆有条理之可循,使散漫之书籍皆有伦类之可指。”[18](P276)黄侃虽耽溺旧学,亦认为:“夫所谓学者,有系统条理,而可以因简驭繁之法也。”[19](P2)
推及整个学术体系,有系统则乃学术分工各有专精,形成整严完全的学术系统,梁启超所谓“历史上各部分之真相未明,则全部分之真相亦终不得见。而欲明各部分之真相,非用分工的方法深入其中不可”[20](P38)。胡适率先擘画,拟订了“理想中的国学研究”中的中国文化史该有的十大门类:民族史、语言文字史、经济史、政治史、国际交通史、思想学术史、宗教史、文艺史、风俗史、制度史,宣称“国学的系统的研究,要以此为归宿”[21](P364-379)。白寿彝撰写了《整理国故介绍欧化的必要和应取的方向》一文,指出:“整理国故的学者应当作一种有系统的工作,把过去文化之起源,蜕变的事实,及所以成现在情状的原因,组成各种文化专史——如政治史、经济史、风俗史、哲学史、文学史、教育史……之类。”[22](P433-434)
由此可见,学者们普遍欲以系统之法来清整固有文化,促进学术研究科学化转型。而这种系统化建构,时贤不仅期冀在具体著作中加以实现,更试图经由个人学术实践,最终汇众沤为一海,彻底清理整个中国学术体系,务求各学科畛域严明,各知识皆有统绪,各门类皆有专家。
(三)以科学之方法重估传统价值
1919年胡适在《新思潮的意义》中指出,“整理国故”是对旧有学术思想的一个“积极的主张”,旨在“从乱七八糟里面寻出一个条理脉络来;从无头无脑里面寻出一个前因后果来;从胡说谬解里面寻出一个真意义来;从武断迷信里面寻出一个真价值来”[23](P350-351)。可见,学术研究不仅应学有专门条理分明,更要求学者去伪存真,最终找出“真意义”与“真价值”。
而所谓“真意义”的发现,其实包含着学术新对象的输入。胡适曾主张一切材料皆平等,“上自思想学术之大,下至一个字、一支山歌之细,都是历史,都属于国学研究的范围”[24](P372),即是将此前不入流的稗官小说、歌谣唱曲升等至与高文典册平起平坐的地位。顾颉刚亦宣称:“凡是真实的学问,都是不受制于时代的古今,阶级的尊卑,价格的贵贱,应用的好坏的……我们决不因为古物是值钱的骨董而特别宝贵它,也决不因为史料是帝王家的遗物而特别尊敬它,也决不因为风俗物品和歌谣是小玩意儿而轻蔑它。”[25](P13)事实上,在具体研究中,此前视为“帝王之物”的高文典册渐趋冷落,“小玩意”却身价日重。单就文学论,陈独秀、胡适、钱玄同等学者即纷纷为《水浒传》、《儒林外史》、《红楼梦》、《儿女英雄传》、《老残游记》等著作作序、考证、标点,词曲小说由叨陪末座转而登堂入室,渐被纳入文学正典。
1932年胡适因姚际恒著作的发现而致信钱玄同:“近年中国学术界的一个明显的倾向,这倾向是‘正统’的崩坏,‘异军’的复活。”[26](P570)从根本上说,以科学方法整理固有文化的学术实践,不仅意在崩坏“正统”,更旨在复活“异军”,目的是要以现代的科学方法为固有文化学术做一次重新估价。尤要注意的是,不论是“正统”的崩坏,还是“异军”的复活,都是以“科学”为正名之手段。正统之所以应崩坏,在于内容不科学、不适应现时需求;异军之所以应复活,亦在于其经由科学检验足具真价值。科学,不仅是学术研究的具体手段,也是裁断合法性的价值判准,乃至成为重构知识谱系与整体文化建构的重要力量。
综上所述,从对中国固有学术研究观念与方法的批判,到意图借鉴西方科学精神来重构学术体系,这一学术转型的要旨即在随着科学意识的张扬,使中国学术系统从囫囵笼统趋向门类分明,从条理不清趋向系统明确,并试图以历史的眼光、平等的态度、现代的思想以及科学的方法,最终重建中国人文学术的历史图景。而这种基于科学观念的学术转型,之于古代文论领域亦形迹彰明。
二、古文论研究的科学化进路
对应着整体学术研究的科学化转型,古代文论研究同样受到科学主义思潮的深刻影响。
(一)从“游客赏景”到现代批评
对科学理性以及科学方法的推崇,首先令研究者从观念上试图以更为科学、更符合现代学术公义的“文学批评”来取代传统的“诗文评”概念。
刘永济认为我国历代文学之观念,义界每多漫漶,“虽心知其意,而语焉不详,此所以终多混淆也”[27](P19)。朱自清明确提出,“文学批评”较之“诗文评”,“清楚些,确切些,尤其郑重些”,因为后者中“有一部分与文学批评无干,得清算出去”[28](P543-544)。在科学主义的影响下,研究者对中国传统文学观念加以重审,试图通过“文学批评”对“诗文评”的取代,更精准地把握文学批评的科学特质,进而推进古代文论研究的现代转型。
文学批评观念的现代转型之外,另一值得注意之处是对于古代文论研究科学化立场的强调。
以郑振铎为例。郑氏认为中国文学是“绝大的膏沃之地”,然而中国文学研究却欠发达,即因古来学者只知“赏鉴”,不懂“研究”。批评前者只是“随意的评论与谈话”,如游客赏景,后者才是“仔仔细细的考察与观照”。他认为科学的文学研究不能止步于赏鉴,应更为深入展开:关于作品、作家、一个时代、每一部文体、综叙中国文学之发展的文学史、辞书、类书、百科全书、参考书目等研究,而“这一切应该有的东西,我们都没有”[29](P2-19)。
郑振铎1931年发表的《中国文艺批评的发端》一文又指出:“文艺批评在希腊很早便已有了……在印度也很早便已有了……但在中国,则文艺批评的自觉,似乎发生得最晚。”此外,中国的文艺批评每与文学无关,“孔丘以后,直至建安以前,虽间有片段的对于文艺的评论,却都是被压抑于实用主义的重担之下的”。因此,“就文论文,不混入应用主义,纯以文艺批评家的立点来批评文学作品……当始于建安时代的曹氏”[30](P67、71)。此外,郑氏格外揄扬宋人的文学批评,认为宋人“知道求真理,知道不盲从古人,知道从书本里求得真义与本相。于是汉、唐以来许多腐儒的种种附会的像痴人说梦似的解释,便受到了最严正的纠正”。换言之,郑氏认为文学批评须具备批判性,不使对作品的析解受到功利主义的压迫,而文学批评亦须条理明晰、自具系统。故其颇为不满通常许为宋人文学批评代表的诗话、词话,批评这类书“大抵都只是记载些随笔的感想,即兴的评判,以及琐碎的故事,友朋的际遇等等,绝鲜有组织严密,修理整饬的著作”,与此相比较,他彰表元代科场士子的文法书“究竟是有组织的著作”[31](P642、917)。
郑振铎对赏鉴式批评的鄙夷、对自成系统的著作的推崇,显然深受科学主义思潮的影响,主张以客观研究取代主观赏鉴。而通过对古代文论研究科学化立场的强调,不仅从义界内涵上,更从研究方法上明确了“诗文评”与“文学批评”的差异,为古代文论研究科学化转型奠定基础。
(二)中西融通与古今对接
王国维尝主张:“学无新旧也,无中西也,无有用无用也。”[32](P365)学术研究科学化的一大特质即是打破传统学术闭关自守的局面,引进西方现代化、科学化、专门化的研究理念与方式,使原本深植于中国文化传统中的古代文论研究,经由西方现代文学研究方法的输入,最终改变观念陈旧、方法单一的研究格局,实现古代文论研究的多元更新。就中西融通方面来说,则表现为西方现代文学观念与研究方法的多元融摄。
王国维1904年发表的《〈红楼梦〉评论》,以叔本华悲观主义哲学与美学思想解读《红楼梦》,成为第一部运用西方批评理论和方法来观照中国古典文学名著的研究佳范。鲁迅的《摩罗诗力说》借鉴西方浪漫主义文学观念,重审儒家“温柔敦厚”的“诗教”传统。罗根泽《中国文学批评史》以“载道”、“缘情”两类总结中国文学批评之流派,亦取资于日本汉学家儿岛献吉郎《中国文学概论》。傅庚生《中国文学批评通论》则以美国文艺理论家艾布拉姆斯的“文学四要素”说为参照,对应中国文学批评之感情论、想象论、思想论并形式论,重构中国文学批评的阐释框架。而刘永济1924年出版的《文学论》以“参稽外籍,比附旧说”为方法,旨在建立“时地虽囿,心理玄同”的具有普适性的文学理论体系,该书注重中西比较与融通,以西方现代学术方法诠释、激活传统文论资源。
西方文学批评观念的借鉴之外,西方现代文学研究方法的学习也成为中西融通的另一方面。法国学者丹纳的“文学三要素”说对中国学者影响颇大,罗根泽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就特别注意以地理文化学的方法来观察中国文学批评因地域因素导致的文学创作的不同风尚。郑振铎根据莫尔顿《文学的近代研究》所述“文学统一的观察”、“归纳的研究”、“文学进化的观念”三点,指出文学研究应建筑在“近代的文学研究的精神”之上,其中尤为强调归纳法乃“一切学问的初步”,“文学进化的观念”则为裁断古今的判准。[33](P1-2)朱维之《中国文艺思潮史略》则受日本学者青木正儿《支那文艺思潮论》和《中国文学思想史纲》启发,尝试以文艺思潮嬗变为逻辑线索,从而全面把握中国文学思想的历史轨迹。
中西融通之外,古今对接也成为古代文论研究方法论更新的另一关键。如果说前者更多地赋予研究者以异域视野,丰富了古代文论的阐释可能,那么后者则是传统文论研究方法的深化发展,其中尤可关注的是传统历史考据学与实证主义研究方法、社会历史批评方法相对接而形成的新的研究范式。
作为中国传统学术研究方法之一的考据学,向来不免饾饤之讥,但因其重实证、不尚空谈的学术性格,反在近现代科学主义思潮的文化语境中颇受推崇,梁启超指出“清儒之治学,纯用归纳法,纯用科学精神”[34](P62),胡适坦言“中国旧有的学术,只有清代的朴学确有‘科学’的精神”[35](P216)。正因考据学与科学主义形成某种内在勾连,遂成为国学研究科学化的本土资源,涵育出以考证、注疏、校勘等方式为主的研究形态。但随着学术研究的日益精进,单纯考订文献、训诂字词的考据型研究颇遭诟病,闻一多明确宣称“训诂学不是诗”[36](P356),强调须在全面把握作品文学旨趣的基础上,才辅之以密察考辨。而将历史考据与文学批评相结合,从传统经学话语的研究模式中脱离出来,既求得历史之真,亦能了解文学之本的研究佳范,允推朱自清《诗言志辨》。
朱氏认为,“诗言志”、“思无邪”、“辞,达而已矣”等,以及《庄子》中的“神”、《孟子》中的“气”等等都是“诗文评的源头,从此江、淮、河、汉流贯我们整个文学批评史”[37](P189),因此“若有人能用考据方法将历来文评所用的性状形容词爬罗剔抉一番,分别决定它们的义界,我们也许可以把旧日文学的面目看得清楚些”[38](P22)。
前人认为诗多不可解,朱氏则认为,“单说一首诗‘好’是不够的,人家要问怎么个好法,便非先做分析的工夫不成”[39](P59、61),而分析方法则是“一层层换着剥起去”[40](P2),因为“文学批评里的许多术语沿用日久,像滚雪球似的,意义越来越多。沿用的人有时取这个意义,有时取那个意义……极其错综复杂”[41](P189)。落实到具体研究,朱氏先对文学批评意念作从字义、词义连及文义的精确考辨,重点“探索词语的应用史和语义的变迁史,以揭示文学和文学批评的发展规律”,复从具体政治文化制度变迁加以归纳、综合与比较,因此朱自清的考辨方法“既不是纯客观的‘征实’,又不是纯主观的‘发挥’,而是二者的结合”[42](P349、352)。
朱自清对中国文学批评史“中心观念”的精到把握,使得传统的历史考辨方法不再只是文献的爬梳,而转为挖掘材料的内在意涵。更重要的是,朱氏“于纵向的批评史研究之外,开辟了横向的系统研究,建构了中国诗学理论的基本框架”,同时“没有套用西方的理论框架”,而是试图“建立中国文学理论体系的新路”[43],提供了更科学的研究范式,改变了一味套用西方文学理论架构阐释中国文学批评观念的学术趋向,使得传统考据学摆脱陈旧的研究束缚,实现了方法论上的现代转型。
此外尤须一提的是,当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唯物辩证法、阶级分析法渐次输入中国,古代文论研究也因此获得全新的理论能量与研究工具。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观念与方法指导下,传统历史考辨研究从单纯的文献考订与辨伪释义,升等为对作品、作者所在时代的整体社会历史的考察,尤其着重研究作品所反映的时代生活、物质基础与社会现实,作者的阶级身份与政治倾向,大大提升了传统历史考辨研究方法的思想高度与文化意涵。
综上所述,在科学主义思潮的催动下,古代文论研究产生了强烈的方法论自觉,试图通过对西方现代文学批评观念与方法的学习运用,造成古代文论研究方法领域的新变,最终形成中西融通、古今对接的综合研究格局。
(三)由“科学”以至“学科”
朱自清尝言:“现在写中国文学批评史,有两大困难。第一,这完全是件新工作,差不多要白手成家,得自己向那浩如烟海的书籍里披沙拣金去。第二,得让大家相信文学批评是一门独立的学问,并非无根的游谈。换句话说,得建立起一个新系统来。这比第一件实在还困难。”[44](P539-540)换言之,古代文论研究要从“集部的尾巴”升等为“一门独立的学问”,具备学科独立的合法性,关键在于要“建立起一个新系统”。无论是文学研究科学化态度的强调,还是中外融通古今对接的综合研究趋向,古代文论研究的科学化进路最终谋求的即是建立现代的、科学的古代文论研究体系。
而这一由“科学”以至“学科”的学术体系营构进程,大抵有如下两大表现:
长期以来,人们普遍认为历代诗文评都欠缺系统,知识形态无非是“辨句法,备古今,纪盛德,录异事,正讹误”[45](P377)。因此如何通过科学研究最终为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内在演化绎出一条有迹可循的理论线索,就成为研究者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
1934年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完成,明确以文学观念的演变作为划分中国文学批评历史进程的依据:即文学观念演进期自周、秦以迄南北朝;文学观念复古期自隋、唐以迄北宋;最末乃文学批评完成期,南宋、金、元以后直至现代。郭氏认为:“对于文学观念的认识既得逐渐正确而清楚,也即是文学批评本身的演进,因为这本是文学批评中一个重要的中心问题。所以文学观念逐渐演进,逐渐正确,则文学批评的发展,也随之而逐渐进行。”[46](P11)在郭氏看来,不同历史阶段对于“文学”的不同认知,由此导致的文学观念与文学创作的各种嬗变,正是中国文学批评史所要处理的核心问题。因此,郭绍虞关于中国文学批评演变的分期,并非单纯依据客观历史进程所作的划分,而是基于纯文学观作出的带有鲜明价值判断的历史分期,其本质是“以纯文学观作为中国文学批评演化的内在尺度,以进化观作为中国文学批评演变的历史线索”[47](P100-105)。
相较之前的研究,郭著不仅于文献材料广搜博讨,更胜在能从历史主义的高度为中国文学批评史绎出一条演化规律与逻辑线索,在理论阐释与历史事实的关联中求得可能的融通,最终建构出一个自洽的阐释体系。尤为可感的是,其谋求为中国文学批评史发展规律作出的科学探索,使得古代文论研究科学化进程不再局限于具体个案的讨论,而是在核实文献、精要归纳以及古今比较的基础上,完成批评史的系统建构,最终大大推动了古代文论研究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发展进程。
二是对中国文学批评史书写体系的探求。如果说郭绍虞着力开显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内在演化规律,那么罗根泽更多致力于探求中国文学批评史的书写体系,亦颇助于古代文论研究的科学化进程。
罗根泽在《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序言”中表明,将汲取我国史书编写中的三种方法之长,创立一种“综合体”:“先依编年体的方法,分全部中国文学批评史为若干时期……再依纪事本末体的方法,就各期中之文学批评,照事实的随文体而异及随文学上的各种问题而异,分为若干章……然后再依纪传体的方法,将各期中之随人而异的伟大批评家的批评,各设专章叙述。”[48](P31-32)即全书先以编年体方式,将中国文学批评史划分为若干时期,复依纪事本末体再就各时期之文学批评问题辟设专章加以讨论,最末则以纪传体方法统摄历代批评家。
这一综合体的书写方式,在历史纵向叙述的主轴上,旁逸斜出,罗氏试图将古代文论研究从此前单一的或偏于批评家个人的文苑传、或偏于具体言说记录的诗话词话的研究模式中脱离出来,进而成为融合历时分析、个人观照并价值述评的现代学术话语。相较郭绍虞较多地经由西方现代文学观念的视域来厘析中国文学观念及其演变,罗根泽更致力于开掘中国文学批评自身的问题。罗著以大量原始史料为基础,聚焦于不同时期可称主流的文学批评观念,勾勒大体,发明大端,使得不同时代的观念区隔更为鲜明,文学形式规律的转变更为明晰,而经由这一叙述体例的独创,亦颇有助于中国文学批评史书写体系的建构。
自陈钟凡著《中国文学批评史》为发端,郭绍虞、罗根泽、朱东润、傅庚生踵继前迹,中国文学批评史的书写工作不妨视为是对中国文学批评史体系的建构。尤其是受到西方现代文学研究方法的影响,有感于注疏、提要、评点、笔记、序跋等传统文论研究方式或可抉发局部之胜义,试图通过文学批评史的书写寻绎中国文学批评嬗变的内在规律,真正建构出切合中国文学批评实际发展的理论系统。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批评体系的建构过程中,不论是历史分期的把握、研究对象的确定、研究方法的使用以及对古代文论经典命题、范畴的阐释、中外文论的比较参照,乃至最终对中国文学批评史演进规律的归纳,处处可见科学研究观念与方法所起的重要作用,由此“科学”以至“学科”,真正奠定了古代文论研究的学科基础,从集部之末升等为自成体系的独立学科。
三、结论与反思
通过以上对科学主义思潮影响下的古代文论研究转型过程的考察,我们大抵可以得出一些启示,并引发进一步的反思。
(一)古代文论研究科学化进程的启示
(1)古代文论研究的科学化进程与中国整体文化现代性发展相一致。不可否认,中国学术研究现代转型的文化背景源于中国政治文化的现实巨变。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科学思想顺乎其时地成为中国现代学术转型的重要因素。知识分子一方面对中国传统文化思想进行强烈批判,另一方面则大量资鉴西方现代科学研究观念与方法,以对中国传统学术文化展开科学整理和现代阐释。因此,我们可以说,古代文论研究的科学化进程与中国整体文化现代性发展相一致,必须将其置于时代文化情境中加以考察。
(2)古代文论研究科学化进程与学科制度化进程相一致。古代文论研究的科学化进路不仅意味着研究方法的科学化、研究观念的现代化,更意味着学科的制度化进程。在西方现代学术思想的规训下,学科意识逐渐加强,研究目的、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日益明确。正如华勒斯坦等人所言:“19世纪思想史的首要标志就在于知识的学科化和专业化,即创立了以生产新知识、培养知识创造者为宗旨的永久性制度结构。”[49](P8-9)而这一学科制度化进程的重要一点即是:“在知识权威的保障下重新审定‘常识’,剔除不合规范的知识,决定知识的分类标准”[50]。因此,科学主义思潮影响下的古代文论研究,不仅是研究观念与方法的科学化,更是经由科学主义洗礼、知识形态与研究范式愈加学科化与专业化、具有“基于普遍接受的方法和真理”[51](P13)的一门独立学科。
(3)古代文论研究科学化进程与学术价值类型转变相一致。古代文论研究科学化进程使得客观化、科学化、系统化的研究方法取代了原先主要以感悟、赏鉴为主的经验式研究。而对于文学审美性和自律性的强调,则导致政治功利主义的知识话语日渐式微,实现了经学话语向审美话语的转变。这一系列知识取向的转型,正是学术研究价值类型转变的鲜明反映。
而实现这一转变的具体方式,则是科学整理与现代阐释。前者凭借对于科学观念的极力阐扬及西方现代学术方法的输入,去除附着在古代文论上的政教观念,化约为符合现代学术公义的知识,落实为有待研究的学术资源;后者则依照现代文学观念加以阐释,深透了解古人言说的具体历史文化语境,寻绎中国文学批评的演进规律,以理性思辨与抽象概括开显文心。正是在资料与阐释的互动循环中,古代文论研究学科愈加发展与成熟。
(二)古代文论研究科学化进程的反思
某种意义上,科学主义思潮影响下的古代文论研究转型,其意义不仅在于使我们更为深入地了解古代文论学科科学化进路的历史过程,更在于透过这一研究了解古代文论学科的初始语境,进而从根本上明晰学科特质,为古代文论学科的进一步发展提供帮助。
首先,古代文论研究的科学化进程虽然因为西方现代文学观念与方法的引入,带来了学术研究的较大创获,但无形中也消解或弱化了中国文论较之西方文论的异质性和话语独立性,出现了以西方文论观念、框架为准的研究倾向。但作为从中国文化传统中诞育而出的古代文论学科,中国性与生俱来,而古代文论研究的真正目的绝非以中国资料注释西方观念,而是通过中西融通的研究方法来透彻发现古代文论的民族特质与本来面目。因此我们必须在承认中西方文论异质性的前提下,尽量进行中西文论思想的交流与互补,最终在保留中国特质的基础上成就世界眼光。
其次,古代文论资料转化为学术资源,自是学术研究现代转型的题中之义,但在将政教色彩抹去、单纯化约为立场中性的文学知识的同时,抑或忽视了古代文论作为文化资源的独特价值。因此,在今后的研究中,尤其是在处理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这一命题的过程中,必须充分注意古代文论知识价值之外的文化价值,在现代语境中抉发古代文论的当代意义,使之成为当下文化建设的宝贵资源。
最后则是要充分注意古代文论研究的跨学科特性。古代文论现代转型的一大表现是以专门取代博通,但流弊是随着学科分化日益明细,中国固有的博雅传统逐渐消亡,以致古代文论研究有时见木不见林。因此,在学术研究持续分化的今天,如何恢复博雅传统、充分重视古代文论研究的跨学科特质、打通学科域限来加深对于古代文论的了解,也是研究者必须思考的一大问题。
科学主义思潮影响下的古代文论研究获得了理性化、逻辑化和体系化的研究形态,从集部之末升等为自成体系的独立学科,这不仅是古代文论研究从古典走向现代的一大标志,同时其转型过程中产生的新变,也成为日后影响古代文论研究学科发展方向的重要因素。因此,不论这一转型过程的利弊若何,我们都有必要对其加以重视,从而了解晚清以来中国文学研究在中西、古今之间的复杂语境,及其对于古代文论研究学科的深远影响。
[1] 郭颖颐:《中国现代思想中的唯科学主义(1900—1950)》,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9。
[2] 任鸿隽:《吾国学术思想之未来》,载《科学》,1916(12)。
[3] 王先谦:《复毕永年》,载《虚受堂书札》,卷一,长沙,1932。
[4] 唐才常:《史学论略》,载《唐才常集》,北京,中华书局,1980。
[5] 老舍:《文学概论讲义》,载《老舍文集》,第15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
[6] 朱光潜:《诗论》,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7。
[7] 王国维:《教育小言》,载《王国维遗书》,第五册,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83。
[8] 陈独秀:《再论孔教问题》,载《陈独秀著作选编》,第1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9] 许啸天:《国故学讨论集·新序》,第1集,上海,群学社,1927。
[10] 梁启超:《科学精神与东西文化》,载《饮冰室合集:文集三十九》,北京,中华书局,1989。
[11] 朱希祖:《整理中国最古书籍之方法论》,载《朱希祖文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12][34]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13] 何炳松:《论所谓“国学”》,载《小说月报》,1929(1)。
[14] 胡朴安:《胡朴安友朋手札:中国学会创立始末》,载《历史文献》,第二辑,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99。
[15] 沈兼士:《筹划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经费建议书》,载葛信益、启功编:《沈兼士学术论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86。
[16] 王国维:《欧罗巴通史序》,载《静庵文集》,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
[17] 顾颉刚:《胡适论学往来书信选》,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
[18] 胡朴安:《胡朴安学术论著》,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
[19] 黄侃:《文字声韵训诂笔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20]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21][23][24] 胡适:《胡适文集》,第3册,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
[22] 白寿彝:《整理国故介绍欧化的必要和应取的方向》,载《白寿彝史学论集》,上册,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
[25] 顾颉刚:《国学门周刊一九二六年始刊词》,载《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周刊》,1926(2)。
[26] 胡适:《致钱玄同信》(1932年5月10日),载《胡适书信集》,上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66。
[27] 刘永济:《文学论》,北京,中华书局,2010。
[28][37][38][39][41] 朱自清:《朱自清古典文学论文集》(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29] 郑振铎:《研究中国文学的新途径》,载《小说月报》,第17卷号外《中国文学研究》专号。
[30] 郑振铎:《中国文艺批评的发端》,载《郑振铎古典文学论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31] 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32] 王国维:《国学丛刊·序》,载《王国维文集》,第四卷,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
[33] 郑振铎:《整理中国文学的提议》,载《文学旬刊》,1922(51)。
[35] 胡适:《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载《胡适文存》,第1集卷2,上海,上海亚东图书馆,1921。
[36] 闻一多:《匡斋尺牍》,载《闻一多全集》,第1卷,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
[40] 朱自清:《新诗杂话·序》,长沙,岳麓书社,2011。
[42] 李少雍:《朱自清古典文学研究述略》,载王瑶主编:《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43] 张健:《借镜西方与本来面目——朱自清中国文学批评研究》,载《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1)。
[44] 朱自清:《评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卷》,载《朱自清古典文学论文集》(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45] 许顗:《彦周诗话》,载丁福保编:《历代诗话》,北京,中华书局,2006。
[46] 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8。
[47] 闫月珍:《郭绍虞与西方文学思潮——〈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范例论析》,载《文学评论》,2010(1)。
[48] 罗根泽:《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
[49] 华勒斯坦等:《开放社会科学》,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
[50] 汪晖:《公理世界观及其自我瓦解》,载《战略与管理》,1999(3)。
[51] 沙姆韦·梅瑟·达维多:《学科规训制度导论》,载华勒斯坦等著、刘健芝等编译:《学科·知识·权力》,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
(责任编辑 张 静)
From the End of Ji to Self-Systematisation——A Study of the Transition of Chinese Ancient Literary Theory under the Influence of Scientism
GU Wen-hao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Fudan University,Shanghai 200433)
In the history of its transition, the study of Chinese ancient literary theory has been greatly affected by scientism. From the abandoning of classical poetry commentary tradition to the rising of scientific rational spirit, from the emphasis of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the formation of a wide academic vision field combining Chinese and western, ancient and modern, to the construction and improvement of the system of criticism history, scientism has led to a shift in the Chinese ancient literature theory toward modern logic formation and away from a classic intuitive form. Chinese ancient literary theory was upgraded to a modern subject with its own system from the end of Ji, which reconstructed the scene of th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ry criticism. Therefore, a probe into Chinese ancient literary theory under the influence of scientism in the early 20st not only provides a further understanding of the development of ancient literary theory at the time, but also has great significance for grasping the transition of the study of Chinese ancient literary theory.
Chinese ancient literary theory; scientism; methodology and path
顾文豪:复旦大学中文系博士研究生(上海 2004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