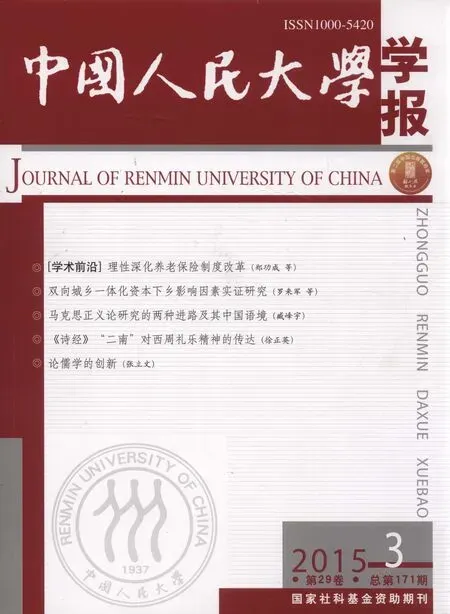论宋代文体学的核心问题:本色与破体
谷曙光
论宋代文体学的核心问题:本色与破体
谷曙光
宋代文体学的核心问题乃本色与破体的错综纠葛、相反相成。宋代的文体本色论深入细致,占优势地位,但破体相参实践也普遍而广泛,以致深刻影响了宋代文学的面貌和成就。本色与破体、理论与实践之间,有着相逆相济、相反相成的辩证关系,双方既存在张力,又有着媾和。宋代文学巨匠欧阳修和苏轼借破体为利器,恢弘文体,掀起文学高潮,堪称最为成功的文体改革家。但破体亦有具体的类型和复杂的机制。宋代文学在尊法度的基础上力主变化,借破体开一代文学之新貌。
文体;宋代;本色;破体;文学史
一、何为宋代文体学的核心问题
从文体的角度研究古典文学,可以说中国文学史亦是文体嬗变演进的历史。文献史料是文体学研究的学术资源和基石,而文体批评理论和文体创作实践则是文体学研究的两翼。宋代是具有近代指向意义的“近古”的开端,两宋三百年为中国古代社会文化的发达期之一。以文体为媒介研究宋代文学,具有宽广的学术空间。但是,研究不能不分主次和轻重,需要辨方向、识大体、抓主流,突出核心问题。开宗明义,究竟什么是宋代文体学的关键问题、核心问题?对此当代学者已有一定的学术思考。
王水照说:“在宋代,文体问题无论在创作中或在理论上都被提到一个显著的突出地位。一方面极力强调‘尊体’,提倡严守各文体的体制、特性来写作;一方面又主张‘破体’,大幅度地进行破体为文的种种尝试,乃至影响了宋代文学的整体面貌。两种倾向,互不相让,而又错综纠葛,显示出既激烈又复杂的势态。”[1](P64)张高评说:“宋代文学所以能有自家面目,除尽心于辨体,谨守规矩准绳……又致力于破体为文,争取自由挥洒空间,追求创新、开拓、发明,自是宋代文体学之一大关键。”[2](P22)吴承学说:“先体制后工拙是传统文学批评的一条普通原则。然而宋代以后,破体为文成为一种风气。”[3](P133)
显而易见,上述诸家观点的学术指向是一致的。尊体,指严守文体法度轨范;破体指打破文体间界限,相互参考借鉴。在宋代文体创作与文体批评中,尊体、辨体和破体、变体是交织缠斗、贯穿始终的重要线索。尽管在理论上,尊体占绝对优势,但破体实践也普遍而广泛,表现为“以文为诗”、“以文为赋”、“以文为四六”、“以文为词”、“以诗为词”、“以论为记”、“以古为律”等等,层出不穷。其他朝代尽管也存在类似问题,但宋代的表现无疑最典型和持久,以致深刻影响了宋代文学的面貌和成就。
一个朝代的文体学,内容丰厚复杂,但其荦荦大端不外理论与创作两端。作为宋代文体学的核心问题,一定要能涵盖理论与创作,符合居于中心位置、历时长久等特征。参照上文的分析,宋代文体学的核心问题已呼之欲出:所谓核心问题实即尊体、辨体与破体、变体的相互纠葛、相反相成。再也没有其他文体问题能够纠葛、影响、贯穿两宋三百年间的文体理论和实践。尊体与破体何以成为核心问题,双方相互纠葛的必然性是什么,该问题怎样影响了宋代文体的发展,及其在文学史上的意义等,目前学术界皆无详论,故仍需研讨。
需要指出,尊体、辨体、破体等几个理论词汇,是当代学者的概括、提炼、总结,其形成及使用有一个历史过程,而宋代的话语系统与此有所不同。据笔者考索文献,“尊体”用在文体研究上,较早是清末的况周颐用在词论方面;“辨体”的较早使用在明代,明人吴讷编有《文章辨体》、徐师曾编有《文体明辨》;“破体”更复杂,原用在书法领域,指行书小纵绳墨,超出常规之外。*关于“破体”,唐代李颀《赠张諲诗》有句“小王破体咸支策”,人皆不明破体为何意。清人倪涛《六艺之一录》引徐浩释云:“钟善真书,张称草圣,右军行法,小王破体,皆一时之妙。破体谓行书小纵绳墨,破右军之体也。”李商隐《韩碑》云“文成破体书在纸”,一说文章破体,一说仍是书法破体。古人还把破体用在形容人的性格行为上,欧阳修《新五代史·唐臣传》卷十六云:“儒士亦破体邪?仁者之勇,何其壮也!”笔者查到的时代早且较为可靠的用破体来形容文体写作的,是宋末方回评价陈师道的《雪后》诗:“此诗第一句至第六句,皆出格破体,不拘常程。”[4](P889)据此宋代已有文论家用“破体”一词。再考察宋代文献,最接近“尊体”、“辨体”含义的,是“本色”、“当行”等词,“破体”宋人又称“不主故常”、“不蹈袭”等。宋代文体学的核心问题虽说是尊体和破体,但如果考虑宋代的历史语境和话语体系,不如不用后起的词汇,而改用宋代当时的词汇。本文把尊体理论和实践总称为文体本色派,破体思维和创作叫做破体相参派,简称“本色与破体”,这样既采用了宋人词汇,又简洁明了。
二、本色:只在理论层面占优势
文体本色论一直是中国古代文体批评的重要内容。只有深刻认识各种文体体制的特点,重视文体规范,创作才有可能“得体”并进而曲尽其妙。宋人关于文体本色的论述极多,主要探讨的是各种文体的规范特征并划定其界限。与之相对的是,宋人关于破体方面的批评较少,根本无法与本色理论相比。故本色论在宋代文体学理论层面是一条主线,占优势地位。限于篇幅,此部分只分析宋代有代表性的陈师道、刘克庄、严羽三家本色论。
“本色”,原指本来的颜色,后引申为本来的面目、本行、本业等,其使用于文学批评,最早见于刘勰《文心雕龙·通变》。*参看刘勰《文心雕龙·通变》:“夫青生于蓝,绛生于蒨,虽踰本色,不能复化。”查宋代文献,本色是一个使用频率颇高的词。佛教有“本色僧”,道教有“本色道人”,做官有“本色官”,做人有“本色人”,都是指符合本行业个性、特征的本来面貌,与我们今天说的“书生本色”、“英雄本色”实乃同义。借用“本色”作为文艺品种的规范要求,亦始于宋代。宋初田锡首先使用了“本色诗人”的字样。*田锡《览韩偓郑谷诗因呈太素》中有“风骚夐古少知音,本色诗人百种心”(《咸平集》卷十五)之句。至陈师道,则把本色作为符合文体的规范要求,正式提出“本色”说。陈在评价韩愈“以文为诗”和苏轼“以诗为词”时,表示“虽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5](P309)。他认为,各种文体有其本身的体制要求,如果离开了品种特色,则虽工亦不足取。然则,文体论中的“本色”,指的是一种文体区别于其他文体的基本特质,或者说是内在规定性。陈师道强调本色,本无可厚非,但不能绝对化,忽视文体间还有发生关联、相互渗透的一面。大多数宋人认同陈师道的论点(不过程度上没有陈那么绝对),并以此为基础进一步阐发文体本色论。如两宋之际的张戒云:“论诗文当以文体为先,警策为后。”[6](P459)这实际是陈师道本色论的翻版,首要是符合体制的要求,其次才谈得上好坏。
在宋代评论家里,刘克庄是使用“本色”一词频率最高的。刘克庄笔下的本色与陈师道有无区别?刘从批评的角度提出:“诗非本色人不能评。贺(知章)、韩(愈)皆自能诗,故能重二李(李白、李贺)之诗。”[7](P4521)写诗要以诗人的眼光心智去写,评诗也要深谙诗之本色的诗人去评。李白、李贺颇享诗名,因为得到贺知章、韩愈这样能诗之人的品评。换言之,本色人就是对诗体法则规律有所悟解之人。刘克庄屡用本色品评唐宋的诗文大家,如“唐文人皆能诗,柳尤高,韩尚非本色”[8](P3996);“坡诗略如昌黎……翕张开阖,千变万态。盖自以其气魄力量为之,然非本色也”[9](P25);“后山……文师南丰,诗师豫章,二师皆极天下人本色,故后山诗文高妙一世”[10](P4024)。在刘克庄看来,韩愈、柳宗元齐名而韩不如柳,高下的标准就在于韩非本色,而柳乃本色诗人。苏轼的诗像韩愈,千变万态,力大思雄,只可惜也不是本色。陈师道之所以诗文高妙,原因在于师从的曾巩和黄庭坚“极天下之本色”——即精熟深谙诗文之法则规律。较之陈师道,刘克庄的本色论更详尽,更有条理。本色是每种文体质的规定性,诗文创作需要恪守文体界限,才能保持本色,文学批评也应由本色人以本色为标准来品评。
如果我们把刘克庄看做两宋文体本色论的开拓者,那么严羽的诗歌本色论则在理论深度上更推进了一步。严羽《沧浪诗话》中提到“本色”的先有四处,试看最重要的一条:“大抵禅道惟在妙悟,诗道亦在妙悟。且孟襄阳学力下韩退之远甚,而其诗独出退之之上者,一味妙悟而已。惟悟乃为当行,乃为本色。”[11](P12)“以禅喻诗”是严羽诗论的重要特色,具体表现就是“妙悟说”的提出。严羽认为诗歌创作的真谛即在妙悟。孟浩然解诗之妙谛,故学力远不及韩愈而诗歌反出韩之上。可知对诗而言,妙悟与学力实是两股道上跑的车,有学力的无济于诗,善妙悟者才是真正的行家里手。妙悟的艺术目标是什么?就是为了达到本色的境地。反过来说,欲诗本色,须得妙悟。妙悟是条件手段,本色是艺术追求。至此可明白,严羽本色论的本质内容是要求诗歌重感兴、尚意趣,达到“言有尽而意无穷”的艺术境地。他批评宋诗的散文化、议论化,都是以此为出发点的。故而严羽诗歌本色论是要固守诗歌特有的审美趣味,把诗与其他文体区别开来。
文体本色论产生的根源何在?在古人眼里,作文之法,首在辨体。为什么有些语言形式、章法结构、艺术风格,可以置之甲文体,却不能用于乙文体?放在甲文体上如水银泻地、熨帖恰当,置于乙文体却窒碍难通、格格不入?原因就在于不同的文体有不同的特点、规范和要求。既然划分了文体,那么创作之高下、行文之得失,在很大程度上当依体而行。于是文体本色论就与文体的发展如影随形,成为文体批评中最主要的理论维度。
三、本色理论与破体实践的错综纠葛
宋代文学的开拓性,突出地表现在创作的破体相参中,然而,宋代破体相参在理论层面基本上是匮乏甚至缺位的。这就表现出一种自相矛盾的情形:即有的作家在理论上明确反对破体相参,而实际创作中又恰恰破体为文,并取得很大成功。因此就需要进一步分析这种理论与创作不相匹配的矛盾现象。在宋代,体现本色理论和破体实践矛盾较显著的作家代表是王安石、陈师道、刘克庄等人。下面就以上述三人为例,考察他们理论和实践的差异。
在文体理论方面,王安石显然是本色派,他“评文章常先体制而后文之工拙”*今王安石文集里无此话,但宋金人文集如《山谷集》、《滹南集》,诗话笔记如《苕溪渔隐丛话》、《耆旧续闻》,类书如《记纂渊海》等都有记载,字句稍有出入,故应是王安石观点。。陈师道更是铁杆的文体本色派,他眼光犀利,先后批评过“以文为诗”、“以文为四六”、“以诗为词”、“以论为记”等,态度鲜明坚决,好像丝毫没有商量余地。刘克庄则是宋代使用“本色”评诗文最多的人。
实践方面,王、陈、刘都有破体为文的具体例证。王安石的散文和诗歌皆以议论说理见长。散文方面,王安石虽不同意“以论为记”,但他本人的纪游之文《游褒禅山记》就是一篇大发议论的典型。诗歌方面,王安石诗风的最显著特色是“以文为诗”,像造硬语、押险韵、好用典、改古人诗句为已有等,屡见不鲜,而这些都是江西诗派的先声。王安石不以词名家,但其词风与当时流行的婉丽派迥乎不同,名作如《桂枝香·金陵怀古》,苍凉悲壮,格调近于诗。陈师道以诗歌的创作成就为高,在诗艺上他是黄庭坚的坚定追随者。宋诗的几个大家,从欧阳修、王安石到苏轼、黄庭坚,再到陈师道,都与“以文为诗”脱不了干系。陈师道曾提出“宁拙毋巧,宁朴毋华,宁粗毋弱,宁僻毋俗,诗文皆然”[12](P311)的艺术主张。其实,追求老健朴拙的艺术风格,与其说适合诗歌,不如说更适于散文。陈诗的长处在朴拙精炼,短处是质木无文,明眼人一看即知,其得失都和诗之散文化密切相关。刘克庄是南宋江湖诗派中的最著名诗人。他的作品参差不齐,好的既有雄健的笔力,又具开阔的气势;差的不免生硬熟滑,泥沙俱下。他曾批评宋代理学家的诗“率是语录讲义之押韵者耳”[13](P4596),其实他自己有些作品也逃不过押韵散文的讥评。可见刘克庄的诗也贴上了“以文为诗”的标签。后村词继承了辛弃疾“以文为词”的艺术取向,喜用典、多议论,堪称辛派后劲。
通过理论与实践两方面的简明扼要分析,确实看出三人在本色理论和破体实践上存在矛盾和脱节。那么,如何对矛盾现象进行合理的解释与说明呢?
首先,古代的传统势力异常强大,文体本色论作为文体论的主要内容,一直以来就受到广泛的认同和强调。宋代各文体本身需要立规矩、讲法则,而王、陈、刘等坚持本色论,是顺理成章之事。无论变与不变、守旧或创新,掌握规矩都是基本前提。其次,面对宋代文学求新求变的大格局,王、黄、陈、刘诸人又无可避免地被卷入到破体为文的时代浪潮之中。宋代文化的总体特征可以概括为融会贯通,而宋代文人又好学深思,具备诗、词、文、书法、绘画等多方面艺术修养,于是就自然出现了一种打通各文艺门类的哲学思考,而文体间的互渗互融当是题中应有之义。再次,王、陈、刘的破体为文与宋人的艺术创新思维息息相关。宋人在文学艺术方面,颇有些创新的雄心壮志。王、陈、刘都属于有成就的文学家,他们有打通整合各种文艺形式的创新精神。为了开拓创新,宋人有时不得不借助破体为文。
要之,本色理论和破体实践表现在一个作家身上的矛盾现象在宋代屡见不鲜,涉及多方面的复杂原因,它是文体本身、社会文化、创作者等多重原因综合而形成的一种特殊现象。然则本色理论和破体实践究竟是怎样一种关系?本色理论和破体实践固然是一对矛盾,但它们也不是永远对立、不可调和的。文体本色论是基础,需要讲求传承;但在一定条件下,又有必要借助破体来促进文体的发展演进。一种文体越发达,规划就越细密繁复,到了一定程度,甚至会束缚文体的发展,成为文体变革的绊脚石,这就是相反相成的辩证法。
就文体而论,设立规矩和打破规矩都没有错,促进文体的发展才是硬道理。每种文体都必须依照情理来确定规则体制,而作家运用规则体制又因人而异,再加上时代的变化会影响文体的变迁,所谓“夫设文之体有常,变文之数无方”(《文心雕龙·通变》)。本色理论和破体实践犹如一对剪不断、理还乱的绳索,错综复杂地纠葛一处,以至于让身处其中的古人也当局者迷,看不清两者间相逆相济、相反相成的辩证关系了。金代王若虚以善议论著称,关于文体,他有一段富含辩证意味的问答:“或问:文章有体乎?曰:无。又问:无体乎?曰:有。然则果何如?曰:定体则无,大体须有。”[14](P236)“定体则无,大体须有”不失为对待文体正与变的一种圆通见解。
四、宋代最擅长破体的大家:欧阳修和苏轼
当一种文体成熟凝定之后,即包含着因循旧路、陈陈相因的危险;而此时若有豪杰巨手濡染大笔,出奇制胜,就是革新文体的英雄。宋代文坛最擅长破体相参的,无疑推欧阳修、苏轼两位文坛巨擘。诚如钱锺书所言:“名家名篇,往往破体,而文体亦因以恢弘焉。”[15](P890)破体相参实乃创新变革文体、推进文学演进的一大法门。
柳宗元在《杨评事文集后序》中发明了一个词叫“遍悟文体”[16](P1462),指对各种文体都精熟擅长。宋代的两位文坛宗师欧阳修、苏轼,诗、词、文、赋各体具备、无体不工,允称“遍悟文体”。如果把北宋的诗文革新运动看做一场文体革新的话,那么,欧阳修、苏轼就是运动中最成功的文体改革家。他们最擅长打破文体间的壁垒,不主故常、不蹈袭,而破体为文正是他们废前法、创新意,成为文坛领袖的秘诀。
破体为文理论上的可行性在于每一文体本身所具有的既稳固确定、又变通开放的双重灵活机制。应该注意,欧、苏虽是贯通百家、熔冶众体的大家,但同时都很看重遵守文章体制。他们在精熟文体规范的前提下,看到了文体间的同与异,采取“移步不换形”的科学态度进行了种种破体为文的实践。换句话说,欧、苏成功的关键在于对本色理论和破体实践这对矛盾持有辩证通脱的科学态度。
欧阳修的文体实践破体创新,但给人的感觉却是出位而不觉其破体,真正达到了一种盐溶于水的艺术境地。试看宋人怎样赞誉欧阳修的文体创新:
杨东山尝谓余曰:“文章各有体,欧阳公所以为一代文章冠冕者,固以其温纯雅正,蔼然为仁人之言,粹然为治世之音,然亦以其事事合体故也。如作诗,便几及李杜。作碑铭记序,便不减韩退之。作《五代史记》,便与司马子长并驾。作四六,便一洗昆体,圆活有理致。作《诗本义》,便能发明毛郑之所未到。作奏议,便庶几陆宣公。虽游戏作小词,亦无愧唐人《花间集》。盖得文章之全者也。”[17](P267)
欧阳修能“成为一代文章冠冕”,“得文章之全”,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兼容并包、事事合体。他的破体为文不是大刀阔斧地让一种文体变得面目全非,而是在文体间找到重合的边缘地带,于适当的范围内进行相参相融,让人觉得自然而不突兀,出新意而又似曾相识,容易为人所认可接受。
欧阳修的破体为文实践表现在诗、古文、骈文、赋几种文体上。平心而论,欧阳修最成功的破体在骈、散之间的相参相融。欧阳修在文学观念上文道并重,对骈、散二体都能客观看待,没有偏颇,他表示“偶俪之文,苟合于理,未必为非,故不是此而非彼也”[18](P1045),当时能有这种识见,真是难能可贵。他在诗文革新运动中既矫革了骈、散各自的弊端,更注意合其两长,相辅相成,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骈、散间的壁垒,骈散参融,故而其四六有散文化的倾向,是骈文中的变体;其散文又有一定的骈化,是散文中的变体;又借助散体单笔来写赋,形成文赋,使宋代辞赋得以开拓新的疆域。这就是欧阳修破体为文的最重要功绩。欧阳修的文体革新使宋代的诗歌、散文、骈文、辞赋等体裁更加丰富,功能更为完备,因此在宋代文体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时人赞曰:“盖公之文备众体,变化开合,因物命意,各极其工,其得意处虽退之未能过。”[19](P2693)在破体相参方面,欧阳修的确成就卓著,不输唐代韩愈。
苏轼是宋代另一个破体为文的大家,但他和欧阳修的表现不一样。欧阳修的风格自然平易、纡徐委婉,破体虽多却圆融晓畅,是一种渐变,让人容易接受;而苏轼的艺术魄力极大,翻新出奇的愿望也更强,打个不太恰当的比方,他的破体为文犹如战场上的一员大将,横刀立马,所向披靡,不免让人觉得豪横犀利,望之俨然。故而宋人评云:“东坡之文妙天下,然皆非本色,与其他文人之文、诗人之文不同。文非欧曾之文,诗非山谷之诗,四六非荆公之四六,然皆自极其妙。”[20](P323)
客观而论,苏轼在文艺观上是不反对文体相参互融的。苏轼曾说:“诗之美者,莫如韩退之,然诗格之变自退之始。”[21](P109)这个评价肯定了韩愈诗的富赡健美,指出其在诗歌史上具有革故鼎新的转关作用,品评角度新颖,眼光犀锐。苏轼虽未明言韩愈的变革之道,但除了诗的散文化,还能有什么呢?可以比较明显看出苏轼通脱文体观的是其词论。对词的传统观念一般是“小道”、“诗庄词媚”,但苏轼持有诗词一体的词学观,认为词“盖诗之裔”[22](P1943)。他称赞陈季常的词:“又惠新词,句句警拔,诗人之雄,非小词也。”[23](P1569)一再将诗与词相提并论,就为实现诗和词的互相贯通渗透提供了理论依据。苏轼《与鲜于子骏》云:“近却颇作小词,虽无柳七郎风味,亦自是一家。”[24](P1560)这是对其名作《江城子·密州出猎》的说明,“自是一家”的内涵颇耐人寻味,不难体会其中有“作词犹如写诗”的意思,词也应追求壮美的风格和阔大的意境。这实质是在为“以诗为词”张目。可知苏轼在文体观念上并不拘泥。
苏轼的破体实践比欧阳修更为大胆普遍,他运用文体不拘常套,在体制和手法上,呈现出由单一走向复合的趋势,善于参融众体于一炉,破旧格,生新变,扩大了文体的堂庑和疆界,最是革新文体的大家。苏轼的散文、骈文、辞赋都能突破凝固格局,骈散错落互用,奇偶相间交替,时散时骈,亦文亦赋,达到一种出神入化、行云流水的高妙境域。苏轼散文有政论、史论、记体、杂说、书札、题跋、笔记、碑志等诸多体裁,常能熔冶众体,不落俗套。他尤其擅长在散文中吸收骈语,打破文体藩篱,把叙事、说理、议论完美结合起来。罗大经《鹤林玉露》丙编卷三“东坡文”条赞誉苏文“横说竖说,惟意所到,俊辨痛快,无复滞碍”[25](P167)。
苏轼的“以文为诗”显然比欧阳修更为成功。赵翼《瓯北诗话》卷五云:“以文为诗,始自昌黎(韩愈),至东坡益大放厥词,别开生面,成一代之大观。”[26](P1195)“以文为诗”是自中唐韩愈以来众多诗人变革诗风的途径,但不免毁誉参半、泥沙俱下;只有到了苏轼,才发展到较为理想的境地,达到“成一代之大观”的高度。苏轼首先是才思敏捷,加之淹通文史,辅以纵横捭阖的笔力,滔滔汩汩的议论,于是自成创格,进入天马行空的妙境。他娴熟古今诗体,但七古最擅胜场,原因在于七古最易借鉴古文的恢张豪迈、波澜起伏。以文入诗助成苏轼宋代诗坛第一人的辉煌成就。
王若虚《滹南遗老集》卷三十六云:“东坡之文具万变,而一以贯之者也,为四六而无俳谐偶俪之弊;为小词而无脂粉纤艳之失;楚辞则略依仿其步骤,而不以夺机杼为工;禅语则姑为谈笑之资,而不以穷葛藤为胜。此其所以独兼众作,莫可端倪。”[27](P231)一言以蔽之,苏轼文备众体的原因就在不斤斤于定法,不为固有模式所拘囿,善于融会,圆通应物而能自出机杼。
综上,宋代文坛宗师欧阳修、苏轼在诗、词、文、赋诸方面的巨大成就有目共睹。借助破体为文,他们打通了宋代各种文体的疆界,让文体互补互动,为文体找到成熟后的突围之路,堪称最为成功的一代文体改革家。宋代文学的面貌在欧、苏时代焕然一新;反过来说,以欧、苏为代表的破体相参,深刻影响了有宋一代的文学面貌。
五、破体相参的类型、界限及路径
文体虽相对稳定,但也是动态的,有“弹性”,在特定时段需要调整、变化。文体相参乃是文体发展史上极其普遍的现象,它是使文体获得新鲜活力和变化发展的重要手段。陆机《文赋》云:“其为物也多姿,其为体也屡迁。”既然大千世界本来就多姿多彩,那么,反映事物的文体也必然随之发生变化。
破体相参可以表现在不同的层面,有具体的类型和复杂的机制。总结宋代种种破体为文的情况,能够概括出文体的语言、形态、功能和风格等几种维度破体参融的类型。文体间语言的变异和渗透较为常见,金代元好问《杨叔能小亨集引》云:“诗与文,特言语之别称耳。有所记叙之谓文,吟咏性情之谓诗,其为言语则一也。”[28](P1022)既然汉语文体都使用一种语言,那其中必有相通之处。譬如宋人的“以文为赋”和“以文为四六”,就有意少用那种偶俪铺排、错彩镂金的语言,而多使用散体古文的流畅平易的话语,从而弱化了赋和骈文的固有语言特征,在变异中显示出新的文体面貌。再如宋人的“以文为诗”,在语言方面往往打破传统诗歌话语系统的典雅含蓄,大量使用一些出自经、史、佛教、稗官小说的非诗化语词,更有诗人采用方言土语和歇后语入诗,“以俗为雅”,如此就让宋诗的语言呈现出一种陌生化的审美效果。
文体形态上的破体相参指文体固有形式元素发生一定程度的偏离。像宋人的“以文为诗”,有时就在音韵声律、句式结构方面大做文章。黄庭坚是典型代表,为了追求矫健奇峭的艺术效果,他的律诗时常解构常规音步,多用拗句,有意规避平仄和谐,使诗体形态有所变异。黄庭坚有三百余首七律,其中拗体占到一半,可见其生新廉悍诗风的形成颇有赖于诗体形态的破体。但是必须指出,诗体形态的散文化如果距诗的常规模式太远,过分追求反对称均衡的艺术效果,往往会丧失诗的特质,而流于押韵的散文。
文体表达方式上的破体相参表现为一种文体偏离了惯常功用、而借鉴其他文体的功能。这也是一种由来已久的文体现象,宋代散文中的记体的变迁即为明证。记体在传统表达功能上主要是叙事,议论说理本不属记体的本色,但是宋人有意地模糊了文体间的疆界,以论入记,始而记多论少,继而记、论平分秋色,甚而出现了以论为记的情形,文体表达功能的变异,使得原本的叙事文体发生了重大变革。
一种文体一旦定型,就表现为相对固定的风格,如通常所说的“诗之境阔,词之言长”。风格上的破体相参一般指固有文体风格的变异。宋代的“以诗为词”、“以文为词”最能说明这个问题。“诗言志”,文人一般用诗来表现有关政治、社会的严肃内容;而词为“艳科”,在尊前花间、舞榭歌台由伶工歌女们演唱,以抒写个人的幽约情愫为主。显然,诗与词的各自文体风格判然分明。但是,随着词体的发展和作家心态的变化,宋词的风格出现了较大的变异。苏轼“以诗为词”,自抒逸怀浩气,激情澎湃;辛弃疾“以文为词”,倾吐英雄豪情,慷慨激昂,于是宋词的风格境界为之一变,“如诗如文,如天地奇观”(刘辰翁:《辛稼轩词序》)。
语言、形态、功能、风格等几个维度破体为文的类型,并非各自为政,它们往往是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形成某种张力,共同推动文体超越固有范型,获得新的活力和能量。
通常而言,每一项意在突破陈规、有所创辟的革新都有利弊两端,破体为文自不能例外。文体之间的交叉、参融,能否取得良好的美学效果,还存在一个原则性问题,即破体为文有一定规律,并非随意为之。作家本人艺术才力的高低和文体交叉、融合是否适度都是重要的影响因素。作家如果缺乏艺术才力,往往不能把一种文体和另一种文体的章法、结构、风格等有机地融为一体,从而导致艺术风格不够和谐一致,严重的甚至损害作品的整体艺术效果。文体的规范要求虽然很多,但一般而言,每种文体都有关键性的规范要素,这是一种文体之所以成立的支配性规范、标志性特征,不容随意逾越,如果文体的交叉、融合导致支配性规范、标志性特征的移位,则会导致破体的恶例,形成文体突变乃至畸变,产生文体不分、体例驳杂的弊病。在文学批评史上,金代的刘祁较早涉及了破体的界限问题,其《归潜志》卷十二云:
文章各有体,本不可相犯。故古文不宜蹈袭前人成语,当以奇异自强。四六宜用前人成语,复不宜生涩求异。如散文不宜用诗家语,诗句不宜用散文言,律赋不宜犯散文言,散文宜不犯律赋语,皆判然各异,如杂用之,非惟失体,且梗目难通。[29](P138)
刘祁认为文各有体,不可随便相参融。他主要是从语言角度来说明文章体制的重要性的,虽然略显保守,但诸如“古文不宜蹈袭前人成语”、“四六宜用前人成语”等看法,在某种程度上已接触到了破体的语言界限问题,仍然值得重视。
破体的界限确实不好把握,原因在于一种文体和另一文体发生关系的情况千差万别,实难概括出通行无误的惯例。话虽如此,根据大量破体相参的实例,还是可以总结概括出一些带有规律性的东西。众所周知,文体分类有递进的层次,一级、二级、三级……而文体间的关系则有包孕、交叉和排斥等几种,破体的本质是在文体间的交叉重叠处发生渗透融合关系。如果两种文体风马牛不相及,则根本不会出现破体参融的情况。一般而言,文体越大,包孕越多,就越有可能与其他文体发生交叉重合的关系。这是因为,层次高的文体,涵盖范围大,定位的坐标参数多,因此就容易和其他文体盘根错节地交织在一起,破体的可能性自然较大。同理,层次越低的文体越具体化,规则固定,与其他文体交叉的可能性较小,破体的几率就小得多。像诗、词、散文、骈文这样的“大文体”,在语言、表达、结构、题材、形态、风格等构成元素上多有交叉重合,因而相互间容易发生变异关系。但像连珠、露布、檄文、弹文、上梁文、青词等层次较低的亚文体,其体制规范相当具体化、程序化,必须严格遵守,因此文体间的自由空间就小许多,故而很难打破固定的文体模式。
在宋代,文体的渗透和变化无处不在,名家名篇尤其如此。一种文体模式的定型,大多源于历史上具有独创性的作家作品,如果后来的作家一味循规蹈矩地传承固有文体模式,则此种文体必将渐趋式微。只有那些掌握文体规范而又不断超越、形成新的规范的作家,才能给文体带来新陈代谢的能量和焕然一新的审美效果。要之,既有规律,又有变化。辨别文体、遵循体制是门径;合体、得体是基础;破体、出位是深刻理解后的突破革新,是对文体范式的创造性运用。破体有界限,切不可失体。辨体—尊体—合体—破体,这是文体发展、创新的必由之路。钱锺书说:“艺事之体随时代而异,顾同时风气所扇、一人手笔所出,复因题因类而异,诗、文、书、画莫不然。”[30](P252-253)不止是文体,文学艺术的很多门类都是大致有规矩,死守则自缚。真正的大家名家总能在艺术形式上有所突破创新。
六、尊法度与主变化:宋代本色与破体的文学史意义
宋代文体学上本色与破体长期纠葛缠斗,深刻地影响了宋代文学的面貌和成就。为何“古已有之,于宋为烈”?这实在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异数”,很值得深入发掘背后的缘故。其中有政治、社会、文学等方面的原因,还关乎整个宋代文化的特质。换言之,宋代文体的本色与破体存在于宋代深厚的社会文化历史背景之下,其矛盾纠葛不是孤立的,而是带有鲜明的宋代文化特色。
整个宋代都是一个特别讲究法度的时代,北宋富弼《上仁宗乞编类三朝典故》云:“宋有天下八十余年,太祖始革五代之弊,创立法度,太宗克绍前烈,纪纲益明,真宗承两朝太平之基,谨守成宪。”[31](P105)宋人有强烈的“祖宗之法”情结,有时即便是新生的事物,也要附会于已有之法之中,以较易取得认同。“赵宋的家法,内外包容,巨细无遗”[32](P75),宋人讲究各种规则、秩序、法度、规范、规矩,故而文体学上的本色论普遍并占优势,就不足为奇了,因其背后有深厚的社会文化机制。然而,宋代的社会、政治、文化虽有“法祖宗”的一面,却还有“变法维新”的另一面。北宋的庆历新政和王安石变法,就代表了宋人对祖宗之法的修补、调整、纠正和挑战。范仲淹《答手诏条陈十事》明确标榜“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在国家“纲纪制度日削月侵”的情况下,“不可不更张以救之”。陈亮《铨选资格》亦说:“方庆历、嘉祐,世之名士常患法之不变”。那时,正是以欧阳修、苏轼等为代表的唐宋八大家中的六家,在宋代文坛纵横开阖、破体创新,掀起宋代文学高潮的时代。两宋政治历史中,“法祖宗”与“不足法”针锋相对,持续颇久,甚至形成党争,极大地影响了宋代政局和文人的命运。两者的矛盾纠葛,似乎是为宋代文体本色与破体的缠斗,找到了一个最佳的注脚。宋代文体的精神脉络,实根源笼罩于宋代社会、历史的整体氛围之中。这是值得特别关注的。
闻一多在《文学的历史动向》中说:“中国文学史的路线南宋起便转向了,从此以后是小说、戏剧的时代。”[33](P201)宋以前是以诗文等雅文体为主流的时代,而元明清则是以小说、戏剧等俗文体为中心的时代,宋代恰好处于雅俗消长的中间环节,文体学上的意义不独承前,尤在启后。试想诗和文,到宋代已经发展得相当充分了,尤其诗歌文体,唐诗已臻完美的极致,怎样才能冲出重围、继续前进?一种有益的思路就是求助于文,汲取文的特点来助成诗的新变,散文化实在是诗歌走到山穷水尽时的一条生路。在宋以前,当然也有破体为文的现象,但那毕竟是不绝如缕的点滴细流,而宋代的文体相参已由涓涓细流汇成盛极一时的轩然大波,“以文为诗”、“以文为赋”、“以文为四六”、“以文为词”、“以诗为词”、“以赋为文”、“以赋为诗”等,名目繁多,形成一股潮流。宋人处于其中,相互浸染,而文体踵事增华,文学遂蔚为大观。凡是破体的,一般都是已获得充分发展的成熟文体。宋代大规模的破体,是诗、词、文等传统优势文体让位于小说、戏剧之前,最后铸就的辉煌。
宋代破体相参盛行的缘由无疑是多方面的,前文已谈到,宋代文化的特征和文人的多闻博见是其中之一,此处再略作诠释。宋代文化的全面繁荣和高度成熟为学界所公认。王国维说:“故天水一朝人智之活动与文化之多方面,前之汉唐,后之元明,皆所不逮也。”[34](P70)陈寅恪的论断亦屡被引用:“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35](P245)文治教化的发达让宋人具有了一种难得的人文精神和理性思辨态度,他们表现出总结、参融、整合传统文化的恢弘气度。杨万里《杉溪集后序》云:“古今文章,至我宋集大成矣。”[36](P3350)文学发展到宋代,正面临着转型,词风光无限,但传统的诗、文已臻巅峰境地,迫切需要另辟蹊径;戏曲、小说等新文体蓬勃兴起,亟须向传统文体汲取艺术养料。正是在这样的文化大背景下,一代博通经史、兼擅思辨与文艺的作家群体自然萌生了打通各艺术门类的哲学、美学思考。
每一时代都存在本色与破体的矛盾,正如潘德舆《养一斋诗话》卷二所说:“汉魏诗似赋,晋诗似道德论,宋、齐以下似四六骈体,唐诗则词赋骈体兼之,宋诗似策论,南宋人诗似语录,元诗似词,明诗似八股时文。”[37](P2023)一部诗史,就是诗体不断破体相参、不断变革发展的演进史。那么,文体相参的意义究竟何在?一言以蔽之,此乃文体的革故鼎新之道。在这个问题上,钱锺书的论述最为精辟透彻,他说:“文章之革故鼎新,道无它,曰以不文为文,以文为诗而已。向所谓不入文之事物,今则取为文料;向所谓不雅之字句,今则组织而斐然成章。谓为诗文境域之扩充,可也;谓为不入诗文名物之侵入,亦可也。”[38](P29-30)钱锺书以文和诗的破体为例,深刻阐发了这个道理。承认文体而又变革文体,方能在文体成熟之后推进其发展;而各种文体的碰撞、整合又推动了文体、文学的演进。破体不仅是文体变革的不二法门、文体创新的必由之路,还是创作出经典作品的规律、文学史演进的自然法则。
金代王若虚云:“宋文视汉唐百体皆异,其开廓横放,自一代之变。”[39](P222)明人许学夷云:“宋主变,不主正,古诗、歌行,滑稽议论,是其所长,其变幻无穷,凌跨一代,正在于此。”[40](P377)“百体皆异”、“主变”就意味着不能亦步亦趋、抱残守缺。宋代文学正是在尊法度的基础上力主变化,借破体开一代文学之新貌。由此言之,以本色与破体作为宋代文体学的核心问题,是公允合适的。在本色与破体之间,有着相逆相济、相反相成的辩证关系,两者既存在张力,又有着媾和。必须深刻认识宋代文体形成和演变的社会文化渊源,才能对本色与破体各自产生的原因以及二者缠斗的必然性有透彻的体悟。研讨宋代文体、文学,抓住本色与破体这个核心,就等于找到了破解一代文体、文学演进发展的密码,可以深刻领会并准确理解宋代文体史、文学史乃至文学批评史上的诸多问题,起到纲举目张的重要作用。
[1] 王水照:《宋代文体通论》,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97。
[2] 张高评:《破体与创造性思维》,载《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3)。
[3] 吴承学:《中国古代文体学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
[4] 方回选评,李庆甲集评校点:《瀛奎律髓汇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5][12] 陈师道:《后山诗话》,载何文焕辑:《历代诗话》,北京,中华书局,1981。
[6] 张戒:《岁寒堂诗话》,载丁福保辑:《历代诗话续编》,北京,中华书局,1983。
[7] 刘克庄:《刘澜诗集》,载刘克庄著,辛更儒笺校:《刘克庄集笺校》,北京,中华书局,2011。
[8] 刘克庄:《竹溪诗序》,载刘克庄著,辛更儒笺校:《刘克庄集笺校》,北京,中华书局,2011。
[9] 刘克庄:《后村诗话》,北京,中华书局,1983。
[10] 刘克庄:《江西派诗序》,载刘克庄著,辛更儒笺校:《刘克庄集笺校》,北京,中华书局,2011。
[11] 严羽撰,郭绍虞校释:《沧浪诗话校释》,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
[13] 刘克庄:《跋恕斋诗存稿》,载刘克庄著,辛更儒笺校:《刘克庄集笺校》,北京,中华书局,2011。
[14][27][39] 王若虚:《滹南遗老集》,北京,中华书局,1985。
[15] 钱锺书:《管锥编》,北京,中华书局,1986。
[16] 柳宗元著,尹占华等校注:《柳宗元集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13。
[17][25] 罗大经:《鹤林玉露》,北京,中华书局,1983。
[18] 欧阳修:《论尹师鲁墓志》,载《欧阳修全集》,北京,中华书局,2001。
[19] 吴充:《欧阳公行状》,载《欧阳修全集》附录,北京,中华书局,2001。
[20] 曾季狸:《艇斋诗话》,载丁福保辑:《历代诗话续编》,北京,中华书局,1983。
[21] 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一七引,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
[22] 苏轼:《祭张子野文》,载《苏轼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86。
[23] 苏轼:《与陈季常十六首》,载《苏轼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86。
[24] 苏轼:《与鲜于子骏三首》,载《苏轼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86。
[26] 赵翼:《瓯北诗话》,载郭绍虞辑:《清诗话续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28] 元好问著,狄宝心校注:《元好问文编年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12。
[29] 刘祁:《归潜志》,北京,中华书局,1985。
[30] 钱锺书:《钱锺书论文文选》,广州,花城出版社,1990。
[31] 赵汝愚:《宋朝诸臣奏议》,卷一二,《君道门·法祖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32] 邓小南:《祖宗之法》,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
[33] 闻一多:《闻一多全集》,第一册,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
[34] 王国维:《宋代之金石学》,载《王国维遗书》,第五册,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83。
[35] 陈寅恪:《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证〉序》,载《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36] 杨万里著,辛更儒笺校:《杨万里集笺校》,北京,中华书局,2007。
[37] 潘德舆:《养一斋诗话》,载郭绍虞辑:《清诗话续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38] 钱锺书:《谈艺录》(四),北京,中华书局,1984。
[40] 许学夷:《诗源辨体》,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
(责任编辑 张 静)
On the Core Issues of Stylistics in Song Dynasty:“Bense” and “Poti”
GU Shu-guang
(School of Chinese Classics,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Beijing 100872)
The core issue of stylistics in Song Dynasty is the fact that Bense and Poti were mingled and reinforced each other. Though Bense dominated the stylistics world with its delicacy and depth, Poti was widely practiced in reality so that it profoundly shaped the outlook and achievements of literature in Song Dynasty. In theory and reality, Bense and Poti were in a dialectic relationship of supporting and reinforcing each other while contradicting each other. While tensions existed between the two, they were in perfect harmony. Ouyang Xiu and Su Shi, two literary giants in Song Dynasty, seized on Poti as a useful instrument to enhance stylistics and push literature to its climax.They could be called the most successful stylistics reformer. However, Poti had its own specific types and complicated mechanism. Literature in the Song Dynasty advocated changes on the basis of rules and took on a new look with recourse to Poti.
stylistics;Song Dynasty;Bense;Poti;literature history
谷曙光:文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副教授(北京1008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