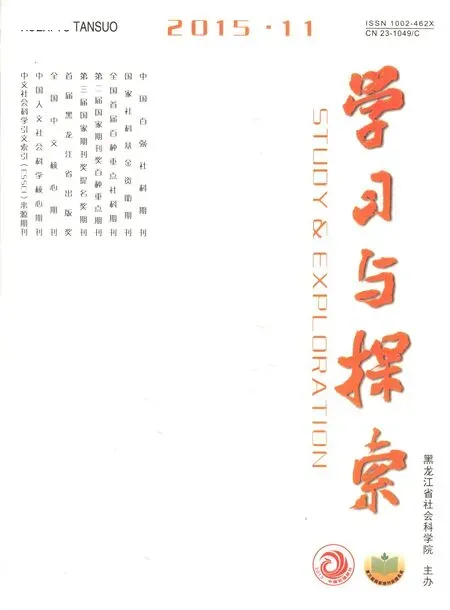论文学叙事的“空间”视角
马汉广
(黑龙江大学 文学院,哈尔滨150080)
·当代文艺理论与思潮新探索·
论文学叙事的“空间”视角
马汉广
(黑龙江大学 文学院,哈尔滨150080)
从20世纪初的现代主义文学开始,文学叙事已经表现出了从时间向空间的转向。这种转向经过了一个过程,而在这个过程中既表现了一种空间美学意识,同时也表现着人们对待世界、对待文学自身的一系列观念的转变。通过具体分析《荒原》《阿莱夫》《英仙座流星》三个小说文本,可以分析其叙事的空间视角及其文学叙事空间化的过程,以及伴随着文学空间叙事所发生的观念转变。
文学叙事;时间;空间;《荒原》;《阿莱夫》;《英仙座流星》
莱辛在《拉奥孔》中以时间艺术和空间艺术来分界文学与造型艺术理论,在此后近两个世纪里被奉为圭臬,时间性成为人们理解和把握文学艺术的核心观念。莱辛的观点代表着西方自古以来形成的文学观念,即对时间因素的重视,把情节当作是文学的一个重要因素,并构筑起情节从开端、到发展、到高潮最后到结局的叙事模式。即使是议论与抒情,人们所关注的也是面对不同时间、不同背景下思想情感的发展变化,空间,只是作为事件发生的具体场景而存在。因此,文学叙事都是在一种线性时间轴上进行的,尽管有时为了使这种叙事产生一定的波澜,叙事者可以采用一些特殊的手法,比如倒叙、插叙、平叙等等,但都不能构成对文学叙事遵循时间因果律的颠覆。
20世纪兴起的叙事学理论从一开始,也是在这样一种观念中把握文学叙事、在理论上完善了这种时间叙事模式的。比如托多罗夫从语言学的角度对文学叙事的因素分为“时间”“语体”“语式”;热奈特在《叙述话语》中更是建立起一套比较完整的时间叙事话语体系。然而随着20世纪初现代主义文学的兴起,线性时间观念被打破了,文学叙事开始进入了一种空间化的尝试,只是当时没有引起人们的广泛注意,或者说人们还依然以某种特殊的时间艺术来理解和把握这些现象。而在20世纪中期以后出现的后现代文学中,种族、性别、地域等空间问题成了其叙事的主线,各种叙事形式也变得纷繁多样,这是传统的时间艺术理论所根本无法把握的。于是人们尝试从新的理论视角对它进行新的概括。差不多同时兴起的空间理论,正好为我们理解和把握这些文学形式提供了一种新的思想武器,因而伴随着人文社会科学的空间转向,文学研究范式也出现了一种空间转向的趋势。
文学研究的空间转向大致是循着两个方向发展的,早期更多关注的是文本的形式和空间美学,后来逐渐转向对文本再现的社会文化空间的关注上。而关注文本形式就不能不研究它的叙事以及这种不同于传统时间叙事的空间叙事艺术。莫雷蒂在《欧洲小说地图》一书中曾指出:“空间不是叙事的外部,而是一种内在力量,它从内部决定叙事的发展。”[1]这也就是说,文学的空间叙事不再由线性时间的延续来决定内容的发展,而是由空间的定焦、延伸、扩展和结构关系来决定内容发展。
陆扬曾说:“就小说中的城市空间而言,19世纪的模式被认为是叙述和描写,20世纪一方面都市生活的时间节律明显加快,一方面空间的经验也变得支离破碎。普鲁斯特《追忆逝水年华》中的回忆已无形式可言,乔伊斯和弗吉尼亚·沃尔夫的意识流小说则使完整的叙述不复可能。”[2]20世纪初,现代主义文学在叙事上就已经打破了19世纪文学的线性时间模式而表现出了空间叙事的特征。回顾20世纪现代主义文学和后现代文学的发展,我们曾惊异和费解的没有故事、没有情节,时序混乱、结构零散的断裂、错位、自我相关等等现象,今天理解,这都是一种空间叙事的表现。只不过从时间叙事转向空间叙事有一个过程,而这个过程也表现着文学观念的重大变化。
一
艾略特创作的长诗《荒原》从构思上说是一个时间的结构,诗人自称此诗的创作受到了魏士登女士的《从祭仪到神话》以及弗雷泽《金枝》的影响。《荒原》采用了寻找圣杯故事作为全诗的基本框架,从宗教神话中的荒原考察到历史上曾出现的荒原,再到对现代荒原的思考,穿结起一条时间的脉络,历史、现在和未来在诗中互为对比、互为参照,构筑起诗人对现代荒原世界本质的探索,以及如何拯救的思考,这个用意是非常清楚的。但我们在读这首诗时,却无论如何都无法建立起一条明晰的时间线来。作者创作这首诗采用了零散化的手法:一是叙事的零散化,把完整的历史事件拆散分解,使之变成一堆碎片自由地拼贴在作品中,其包含的时间性自然也就成了共时性的碎片;二是引用经典的零散化,这部作品中有许多历史故事和典故,都是作者通过引用经典作品来表现的。据说整部作品引用了近60部经典作品,但都是引用的只言片语而非完整段落,也没有表达出一种完整的意思,如果不知道原作的内容这些只是一堆话语碎片而已。
虽然这是一个碎片的拼贴,但如果说这种拼贴完全是随意的、没有任何逻辑的,似乎也并不确切,因为我们还能从中理出头绪并理解它。按照艾略特的理解,二战之后的西方社会进入了一个没有信仰、没有秩序、没有上帝的混乱状态,人人都生活在欲海之中,这就是现代荒原。他从原始宗教、基督教和佛教等宗教轮回框架出发,通过对历史经验的考察,认为荒原世界的成因是两性关系的紊乱,就像自然界中的荒原的成因是生殖神患病一样;所以在诗中历史与现实的对比中,两性关系的比较是非常重要的一环。在第二章“弈棋”中,作者列举了安东尼与克里奥佩脱拉、伊尼亚斯和狄多、亚当和夏娃、铁卢与翡绿眉拉等的事例,这些事例分别出自于莎士比亚的戏剧、维吉尔的英雄史诗、弥尔顿的《失乐园》、奥维德的《变形记》,作者引用了这些作品的只言片语,也没有区分它们的具体时间先后,只是并列于此而已。例如作者对《安东尼与克里奥佩脱拉》的引述:
她坐的椅子,像擦亮的御座
在大理石上闪耀,那里的镜子
由雕刻着葡萄藤的架子框着
其中一个金色的小爱神探头望外偷看
(另一个将他的眼睛藏在翅膀后面)
使七叉烛台之焰加倍发亮
在桌上反射光彩,
而她的珠宝的光辉从缎盒里
倾注出,辉煌地升起迎接[3]72-73。
只有当我们非常熟悉原剧的文本,才知道这里有几句是引用莎士比亚原作对埃及王宫的描写,才能了解到作者这里是引用了一个经典文学的典故,否则我们只会把它当作一个场景描写看待。其他几个典故的描写也是这个情况,只有个别字句与原作品中对某个场景的描写有关,或引述、或戏仿、或反讽等,但这几段诗句各自形成了一个地标,并为我们画出了一张地图,从埃及王宫到迦太基王宫,再到伊甸园,最后到翡绿眉拉被辱后关进的那个山洞,从现实到神话、从历史到当下,全部被置于一种共时性的空间框架之中,形成一种地域差异,读者就是在作者的引导下通过这种地域差异探索其深层的文化意蕴的。
这种时间被空间化、历史化成地域差异的做法,少不了一种视角,即一种既置身事内又能超脱事外、能以清醒的态度对事件进行评注并以独特的身份、阅历、经验把所有事件贯穿起来的眼光的关注。《荒原》第三章“火的布道”中,作者明确地把俄狄浦斯杀父娶母的故事与现实荒原世界中的男男女女对比。作者引入了这种眼光:
我,铁瑞西斯,有着皱纹密布的乳房的老人
看到了这一幕,预言了其余的——
……
而我铁瑞西斯早经受过
在同一长沙发或床上演过的一切;
我,曾在墙下坐在底比斯一旁
在死尸里最低卑的中间走过[3]82-83。
铁瑞西斯是古希腊神话中的一个预言家,是俄狄浦斯故事中不可缺少的人物,他掌握着底比斯所有的秘密,所以俄狄浦斯要追查污染的根源不能不求助于他,他也是俄狄浦斯杀父娶母的见证人。作为一个瞎子,他只能用心去认识这个世界,因而能够在纷纭复杂的现象背后看到事物的本质;作为一个智者和预言家,他对人类的过去、现在、未来都了如指掌,所以能够准确地预言俄狄浦斯的命运。他还是一个有特殊经历的人,据说他本来是男人,一次路经一片树林时看到两条蛇交媾,他用拐杖敲了一下蛇头骂一句畜生,他就由男人变成了女人。七年之后再经过这片树林,又看到这两条蛇时再用拐杖敲一下蛇头骂一句畜生,他又变回了男人。赫拉因嫉妒他的聪明让他变成了一个瞎子,而阿波罗给了他预言的本领。这种独特的经历使得铁瑞西斯超越了性别的界限,又联结起了男女两个不同的性别世界,因而作为两性关系的见证人非常合适;而他在《俄狄浦斯王》中既是故事的参与者,又是一个旁观者的身份,又使他成为事件清醒的观察者和评注者,因而用他的眼光来穿结全诗中历史、现在和未来不同时间发生的事,使之摆脱时间性的束缚而被并置在一个空间延伸的框架之中,变成地域差异是最合适的人选了。艾略特在自注中说:“铁瑞西斯虽然只是个旁观者,而并非一个真正‘人物’,却是诗中最重要的一个角色,通贯全篇。”[3]81
这个眼光的引入,就把发生在不同时期的历史事件,以及存在于幻想中或者是现实中的事件,并置在一个空间框架之中。于是读者跟随着这个眼光,就像是在导游的引导下观赏一座中国古典式的园林一样,随着空间的亭台楼阁的展开,这个亭子建于唐代、那个小楼建于宋代,这副对联出自于董其昌之手,那块石头是米芾曾拜过的等等,在空间结构中体会着历史文化,在时间延伸中把握整体布局。借用中国古代绘画的一个术语:散点透视法,这种空间化的叙事方式就是一种眼光的散点透视。也正是这个人物的引入,使得那些散乱的空间地域:底比斯、埃及王宫、迦太基王宫、伦敦、现代东欧等,变成了一个完整的结构,在这个结构中每一个地方都成为一个时间的标志,因而空间的延伸表现了一种时间的本质。由此可见铁瑞西斯是作品中写出的一个人物,也是要参与到作品事件中去,并在作品结构上联结起不同地域差异的人物,作品要由铁瑞西斯的眼光本身来穿结起时间与空间,来聚焦作者和读者的注意力,告诉你应该怎样去看,去欣赏这个作品。
二
博尔赫斯的小说《阿莱夫》引起了空间理论家们的浓厚的兴趣。索亚在《后现代地理学》中讨论过这部小说,在《第三空间》中又更为细致地讨论了这部小说。当然他所感兴趣的是这个叫“阿莱夫”的空间。他说这是“一则关于复杂的空间与时间的寓言,也是非凡历险的一次邀请”。“这是一切地方都在其中的空间,可以从任何一个角度去看它,每一个事物都清清楚楚;但它又是一个秘密的、猜想的事物,充满幻象与暗示,对于它我们家喻户晓,但从来没有人彻底看清它、理解它。”“这种包容一切的同时性将无尽的世界展现在研究者面前,同时其前所未有的挑战也令人望而却步。毫无疑问,任何想运用诸如语词和文本来把握这个无所不包的空间的尝试都是不可能之举,只能以绝望而告终。因为语言和书写都是前后相继的,这样的叙事形式和叙述史方式永远只能触及第三空间非凡之同时性的皮毛。”[4]
索亚只是从列菲伏尔的空间理论出发看“阿莱夫”这个空间的意义的。但他的这番话却涉及了文学空间叙事的本质;第一,文学的空间叙事就是一种冒险,在这种冒险中塑造出一个一切地方都在其中的空间,无论我们从哪个角度、以什么方式去看这个空间,都能把所有的人、物和事看得清清楚楚,也就是将历时的时间连续变成共时的空间延伸;第二,文学的空间叙事必须面临的困境,语言和书写是前后相继的、历时性的,而通过它的历时性叙述,我们要把握的却是事物的共时性关系。因此,叙事只能触及这种空间的表层,而无法完完整整地把这种空间完全摆在我们面前,因而任何空间叙事都是一个关于空间和时间的寓言,我们也就只能通过其复杂的隐喻关系去接近这种关系的真相。博尔赫斯的《阿莱夫》正是这样一个寓言,它在处理着永恒与静止、时间与空间的问题,也在处理着语言与现实的关系问题。
小说以第一人称来叙述,从作者的恋人贝雅特丽丝·维特波的不幸逝世开始。为了抚慰自己的悲伤,也为了安慰她的家人,此后每当维特波生日那天作者都会去看望她的父亲和表哥。死亡意味着时间的终止,意味着一个永恒的瞬间,无论是对于逝者还是对于怀念她的人来说。但一个人的死亡却不能阻止世界无穷无尽的变化。“我明白不停顿的广大的世界已经同她远离,广告牌的变化是一系列无穷无尽的变化中的第一个。世界会变,但是我始终如一。”[5]326作者似乎停顿在对维特波逝世的悲伤和怀念之中,而这种怀念又是和对过去的回忆联系在一起的,可以说,开头作者即提出了这样一个时间的延续与终止的主题。因怀念而去看望她的家人,看望她的家人提起自己的回忆,而回忆又让作者更加怀念逝者,过去和现在就这样纠结在一起。但如果故事就这样发展下去,这篇小说就变成了一篇伤感的念旧之作,关键是作者要找到一个出口,把无限发展变化的大千世界的流动性和瞬间的永恒联结起来,于是就有了后面作者与死者的表哥卡洛斯·阿亨蒂诺·达内里的交往。
达内里是一个诗人,他的许多稀奇古怪的想法让作者接受不了,但似乎可以和文学联系起来形诸笔墨,于是达内里就开始向作者兜售他的长诗《大千世界》。按达内里的说法这首诗是描绘地球,也即是一种空间秩序或空间结构的,但达内里读给作者听的,却不是描绘空间秩序而是写历史。请看下面短短的四句诗:
我像希腊人一样看到了人们的城市,
工作、五光十色的时日、饥饿;
我不纠正事实,也不篡改名字,
但我记叙的航行是在房间里的卧游[5]328。
用作者的话说,这四句诗中竟然包含了三个精辟的隐喻,一是《奥德赛》中描写奥德修斯回家的情景,二是赫西俄德《工作与时日》中的诗句,三是达内里比较欣赏的诗人保尔·福尔的妙笔小诗,这三个隐喻浓缩了上下三千年的文学史,将其压缩凝聚成了这样一个瞬间。这里似乎隐含着这样的一种含义,即达内里试图将历时性的时间的连续,转换成一种共时性的空间延伸,将上下几千年的历史并置在同一空间之内。但这只是达内里所做的一个方面的工作,另一方面他也在试图将空间延伸变成一种时间的连续:“他雄心勃勃地想用诗歌表现整个地球;1941年,他已经解决了昆士兰州几公顷土地、鄂毕河一公里多的河道、维拉克鲁斯北面的一个贮气罐、康塞普西翁区的主要商行、玛丽亚娜·坎巴塞雷斯·德·阿韦亚尔在贝尔格拉诺区9月11街上的别墅,以及离布赖顿著名水族馆不远的一家土耳其浴室。”[5]329-330这话听起来近似玩笑,把一个诗人描写成一个工匠,像建造房屋或是修筑公路一样一块一块地去解决、去完成,只不过最终的成品不是一栋建筑也不是一条公路,而是一首语言描绘和叙述的诗。认真想来这又不是一个玩笑,唯其如此才更能说明达内里用诗歌来表现整个地球的探索和用心。若把达内里的这两方面工作合起来,正好解决了索亚所说的两个问题,即将历时的时间连续变成共时的空间延伸,和把这种空间关系与空间结构用历时的语言表达出来。这个问题从本质上说,是我们看世界的观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即从单纯的历史眼光转为以历史和现实、时间和空间相结合的眼光,因而必须首先解决一个视角的问题。小说接下来告诉我们达内里所做的工作,离不开他的一个独特的视角,这就是“阿莱夫”。
因为达内里的住房要被拆迁,这让他极为着急和恐慌,在电话里他告诉作者:“为了完成那部长诗,那幢房子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地下室的角落里有个阿莱夫。”并邀请作者去他家看这个阿莱夫。作者描述道:
阿莱夫的直径大约为两公分,但宇宙空间都包罗其中,体积没有按比例缩小。每一件事物都是无穷的事物,因为我从宇宙任何角度都清楚地看到。我看到浩瀚的海洋、黎明和黄昏,看到美洲的人群、一座金字塔中心一张银光闪闪的蜘蛛网,看到一个残破的迷宫,看到无数眼睛像照镜子似的近看着我,看到世界上所有的镜子,但没有一面能反映出我,我在索莱尔街一幢房子的后院看到三十年前在弗莱尔本顿街一幢房子的前厅看到的一模一样的细砖地,我看到一串串的葡萄、白雪、烟叶、金属矿脉、蒸汽、看到隆起的赤道沙漠和每一颗细沙,我在因弗内斯看到一个永远忘不了的女人,看到一头秀发、颀长的身体、乳癌,看到行人道上以前有株树的地方现在是一圈干土,我看到阿德罗格的一个庄园,看到菲莱蒙荷兰公司印行的普林尼奥《自然史》初版的英译本,同时看到每一页的每一个字母,我看到克雷塔罗的夕阳仿佛反映出孟加拉一朵玫瑰花的颜色,我看到我的空无一人的卧室,我看到阿尔克马尔一个房间里两面镜子之间的一个地球仪,互相反映,直至无穷……我看到阿莱夫,从各个角度在阿莱夫之中看到的世界,在世界中再一次看到阿莱夫,在阿莱夫中看到世界,我看到我的脸和脏腑,看到你的脸,我觉得眩晕,我哭了,因为我亲眼看到了那个名字屡屡被人们盗用、但无人正视的秘密的、假设的东西:难以理解的宇宙[5]335-337。
这是一个从任何一个角度都能看到所有地方,每一个地方都能清清楚楚、毫不混乱地观察世界的一个点,也是一个把时间凝结成空间,并把无限的空间压缩成一个一英寸左右的球的观看方式,用陆扬的话说这个阿莱夫“可谓芥子须弥,极天际地”[2]。从达内里对这个阿莱夫的依赖可以看出,这个地方是他解决上面所说的两个创作问题的关键,或者说他从这个极天际地的阿莱夫的观察中获得了灵感,学会了一种观察宇宙万物、并将这种观察变成诗歌语言的叙述方式。这种观察和叙事的方式如果和艾略特《荒原》一诗比较起来,用绘画中的术语说是定点透视,即聚焦于一点,并透过一点展开空间展布和时间延伸,将丰富而复杂的大千世界装入尺寸天地。
小说从一开始怀旧的时间框架,到了解了达内里写诗,再到诗人对“阿莱夫”的依赖,小说的叙事出现了两次转折。而以贝雅特丽丝的逝世来联结这两次转折,又不着痕迹自然而然,最后作者把笔墨集中在阿莱夫上,“阿莱夫”才是作者的真正视角所在,它取代了《荒原》中铁瑞西斯这个活动的、不固定的、具有一定的主体精神的视角,而成为一个固定的、相对客观的、没有任何先入为主主体意识的、联结着时间与空间的,独特的观察与叙事方式。同时我们也看到,作者开始写贝雅特丽丝的去世并不是闲笔,而是由她的死提出了瞬间与永恒的问题,这个问题也正是从时间到空间的入口。进入了这个入口,小说就开始了关于时间与空间问题的哲学思考,而达内里的诗歌创作的探索自然就成了小说的中心。
三
如果说《荒原》是以一些空间的地标把时间切割成许多个片段,就像在一把尺子上面标出刻度一样,而其历史、现实、未来的指向却依然是明确的;那么《阿莱夫》则是将时间和空间都凝结在一起,集中在这个“芥子须弥、极天际地”的圆点上,使之成为一种抽象化的存在,借以表现一种对时间和空间的哲学思考。而约翰·巴斯的《英仙座流星》则是一种穿越,在古代与现代、神话与现实之间的自由穿越。
这篇小说是对古希腊神话中佩尔修斯故事的重述和戏仿,小说是以佩尔修斯自述的形式开始的。升入仙界之后的佩尔修斯整天无所事事、百无聊赖,“我不知道我到底在哪里,也不知道自己欲往何处去,我完完全全迷失了方向,开始产生了幻觉,哇!”在这无聊的状态中他开始在海边的沙地上写起了文字,“写了一行长达半公里的文字”,“直到我又写了USA这三个字母,我才重新打起精神,想起自己所写的话”[6]56。这个开头给人一种似是而非的感觉:第一,佩尔修斯的感叹完全没有古代神话中的英雄那种顶天立地、舍我其谁的气概,更像是现实平庸生活中的一个普通人;第二,USA这三个字母的书写,更进一步将他的身份定义在现实的美国,一个对古代神话中的英雄无比景仰的、厌倦了平庸的现代生活的、多愁善感神经兮兮的普通美国公民;第三,主人公的双重身份表明作者对古希腊神话的重述只是一种戏仿。这点体现了约翰·巴斯神话重述的重要特征,即作者有意模糊了古代与现代、神话英雄与现实中普通人之间的界线,把主人公变成一个可以自由地穿越于这两个世界之间的、曾经建立过骄人的英雄业绩而后却变成了现实世界中的对曾经的英雄行为无限向往的普通人。
一个现实美国的普通人,又是怎样与古希腊神话联系起来的呢?或者说这种在过去与现在、神话与现实中的穿越是怎么实现的呢?小说接下来写道:“在我的想象中,作为凡人的我已经死去。等我睁开眼睛时,发现自己躺在一张床上……”醒来的佩尔修斯发现自己是在一座大理石的卧房中,这是一座从左侧墙角延伸开去的卧室,又像是法螺壳一般的空间盘绕,房间的墙上刻着浅浮雕作品,“每一组均比前一组宽一半,一共七个系列,房间盘绕着,消失在浮雕的尽头”[6]57。这段描写和维吉尔的史诗《埃涅阿斯纪》中的极为相似,埃涅阿斯在迦太基神殿前看到了有关特洛伊故事的浮雕,也包括他自己的故事,这些浮雕引起了他对自己曾经经历的回忆。但浮雕在这两部作品中作用不同,在史诗中浮雕只是引起回忆的道具,作为一个时间的起点,一旦故事的时间开始,浮雕也就失去了作用。而在《英仙座流星》中,首先浮雕具有某种不确定性,即浮雕的排列是不规则和不确定的,哪幅浮雕描绘哪个故事也是不确定的,浮雕与浮雕之间还似乎存在着某种关系,因而观看之中必须把它们联系起来看,当然按照不同的顺序联系起的浮雕,领悟到的意义也是不同的。比如下面的两段描写:
六天里我们已经重温了从宙斯的金雨到几乎最近的事情。这样,不久,或许任何一天,大理石壁上的历史就会到达我死去的那一时刻,赶上我目前的变形。
浮雕越来越长,记录的事件之间的间隔时间却越来越短,例如,从小规模的壁画Ⅰ-B,到它邻近的那一幅Ⅰ-C,中间只隔了一根柱子,却代表了将近二十年的间隔。在与它们相对的第二个系列中,壁画规模更大,间隔的时间却更短,从壁画Ⅱ-E到Ⅱ-F-1,中间间隔的小时就是我们看壁画之间睡眠的时间。是否如此,我的历史像内旋的罗盘,一圈又一圈,似乎永远在接近现在,但又永远无法到达[6]99。
其次,小说情节的展开,发生在对浮雕的不断观看和对浮雕中描绘的故事的回忆之间。作品主人公的视线并不是被浮雕描绘的故事吸引,从而完全沉浸在过去的回忆之中,而是常常回到现在,回到观看浮雕这个起点。因为浮雕描绘的故事本身具有的不确定性,所以每次当主人公走入浮雕时都仿佛走入了一个迷宫,里面错综复杂的道路时时让主人公迷失,他们就不得不回到入口来重新寻找道路。
重要的是佩尔修斯具有的双重身份,他既是神话传说中的一个英雄,又是现实生活中芸芸众生的一员,也许创造英雄业绩的时代已经太过久远,连他自己都有些记不清了;也许生活在现实中的佩尔修斯已经老了,如果没有某种外在的刺激不再能想起当初英雄的自己了。但总之,这些浮雕唤起了他的记忆,唤起了他对昔日的热情,使他产生想要再创造一次历史的冲动。然而我们知道不会有一个个体的生命会如此长久能连接起古希腊到当下现实,但在人类的记忆中,历史仿佛一条生生不息的长河,我们常常要回到源头去寻找关于我是谁、我从哪来等问题的答案。因此,个体的佩尔修斯观赏浮雕所唤起的与其说是他的个人记忆,不如说是人类的原始记忆。也就是说现实中的普通人,通过种种艺术的手段,重温了昔日祖先的英雄业绩,超越了个人经历的限制,从而也超越了平庸的现实。浮雕所代表的就是这种艺术的手段,在这些艺术手段的空间延伸中,神话与现实、历史与当下就奇妙地结合在一起了。由此可见,这一块块浮雕并非只是引起回忆的道具,实际上是参与整个作品故事、推进作品情节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或者说它就是小说中的一个重要的元素,是小说文本叙事的一种方式。这种叙事方式,这种把历史和现实都彻底地打成碎片,使之变成一个个片段,不断返回到原点即不断返回到浮雕本身的做法,又取消了每一个片段的时间属性,把它们全都并置在同一个空间中。这有些像现代网络技术中的超链接,我们通过电脑屏幕按照一定的提示随意地打开不同的链接地址,就会不受任何时空限制地任意浏览,各种信息就会铺天盖地汹涌而来,于是足不出户我们就实现了时间与空间上的穿越。
在这里,作为艺术形式的浮雕性质发生了改变。在《埃涅阿斯记》中,浮雕是根据特洛伊战争的真实情形所做的描绘,先有特洛伊战争发生,然后才有描绘这场战争的浮雕出现,每一个浮雕都有现实依据,因而它作用于人们的记忆,唤起人们头脑中关于过去的印记。而在《英仙座流星》中,浮雕描绘的故事与人的经历是同时发生的,甚至先于人的行为并对人的未来产生某种引导作用,它不仅是关乎过去的,也是关乎未来的。小说中有一段佩尔修斯和卡莱西亚关于这些浮雕的对话:“在我的一再追问下,她承认,神殿里的所有壁画都出自她手,这些年里,雅典娜不断派她的信使前来下达对壁画的具体指示。那时,她并不仅仅是神祇们、神庙,以及狂热信徒们的女仆、执行者、情人,她还是为他们编写历史的艺术家。”[6]78后来他们还有一段对话,卡莱西亚问:“‘告诉我,你是怎么知道你能在壁画Ⅱ-F-1中遇见美杜莎的?’我回答了她的问题。我心里想,我们应该有这张图画,但还是忍着没有说出我的猜测,等到明天吧。那时,假如我的猜测不是太离谱的话,壁画Ⅱ-D上面画的一定是我在特里同湖和格赖埃女妖的遭遇。”[6]91先是卡莱西亚作为雅典娜的使者来编写佩尔修斯的历史,接着佩尔修斯自己也参与到对自己的经历和未来的设计之中。而且不仅是他们的未来可以重新设计,即使是希腊神话中故事也是可以重新改写的,因为出现在小说中的古希腊神话故事已经不是那些神话本身,而是经过了空间叙事处理后的现实中的普通人所想象的和向往的,在他们的未来中能有机会去做的。
于是,约翰·巴斯的空间叙事带来了一种新的观念,文学艺术和现实人生一样,都是不确定的。就像小说开头佩尔修斯在海边沙地上写字,不管写的是什么,也不管写了多少,只要海水一涨潮就会被冲得干干净净,连痕迹都不会留下,海边的沙丘又是一块空白,又可以重新书写了。每个人的人生就是这样一个擦掉原有的痕迹、不断重新书写的过程;而文学,从原有的在人生之外讲故事的“枯竭”中走出来,就是要参与到这种人生的书写之中。而且不管是古代的文学还是神话故事,都是为了参与现实人生的书写成为现代人寻找自己、解决自身问题与矛盾的一种方式。
[1] MORETTI F.Atlas of the European Novel:1800—1900[M].London:Verso,1998:70.
[2] 陆扬.空间理论与文学空间[J].外国文学研究,2004,(4).
[3] T.S.艾略特.荒原[M].裘小龙,译.沈阳:沈阳出版社,1999.
[4] 索亚 爱.第三空间[M].陆扬,译.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72.
[5] 博尔赫斯文集·小说卷[M].王永年,等,译.海口: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6.
[6] 巴斯 约.客迈拉[M].邹亚,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
[责任编辑:修 磊]
2015-07-10
教育部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文学性的历史建构与文学研究范式转型”(13YJA751036)
马汉广(1963—),男,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现当代欧美文学与西方文论研究。
I0
:A
:1002-462X(2015)11-0128-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