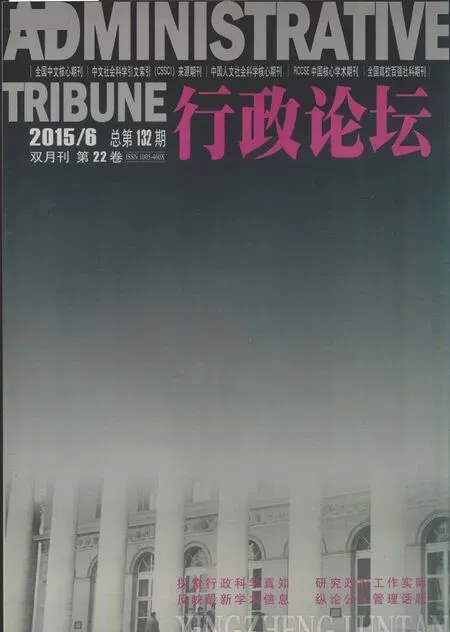权利与权力视域中的网络话语权
◎黄宝玲 (中国矿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徐州221116)
权利与权力视域中的网络话语权
◎黄宝玲 (中国矿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徐州221116)
网络话语是一个虚拟和现实交相呼应的空间环境中的话语传播模式,是社会大众表达利益诉求和彰显自身权利,并在排斥异己语言和扩散自己话语体系过程中,形成对某一社会现象和问题的支配与控制权力。权利和权力的双重彰显是网络话语权的最基本构成和最典型特色。当下网络话语权存在网络话语的权利与义务、权力与责任双向失衡的严重问题。引导网络舆论,疏导网络舆情,必须在畅通与监管网络话语权利、约束与规范网络话语权力中,构建网络话语权。
中国政治;互联网;网络话语权;网络舆情;群体事件
网络是当今世界社会大众获取信息主要依靠的媒介和途径,是表达利益诉求愿望,传播思想文化,蓄积社会舆情,影响社会大众生活的一种超越媒体界限的“政治软力量”,一定条件下会与现实社会群体事件遥相呼应而成为左右冲突进程、强度和烈度的“政治硬力量”。梳理近年来我国先后发生的重大群体事件,基本都与网络信息的极速传播和扩散有密切关联,无一不显示网络话语的传播效应。所谓话语,“是指在特定的环境中,由特定的言说主体,针对特定的问题,围绕着特定的目的,以特定的形式和手段说出或写出的言语”[1]。这种基于“特定”时空环境中的话语具有强烈排他性,一旦形成便有自己特定场域空间和意义世界。所谓话语权,是指人们在特定社会情境下围绕某一问题和现象的自由主张,以及由此形成的身份资格、言语规范、竞争冲突、控制支配和传播影响的能力。随着互联网技术的迅速发展和普及,网络话语权形成了不同于传统媒体话语的传播和影响路径,权利和权力的双重彰显成为网络话语权的典型特色。在网络虚拟的时空环境中,人们往往过多关注自己作为主体的权利,忽视自身应该承担的责任;过多排斥异己声音放大相同声音形成对社会管理的压力,忽视差异性社会发展应有的道德理性和法律规范。网络话语权缺失,不但导致严重影响社会稳定的重大群体事件时有发生,而且极易造成党执政的基础资源流失,降低党在社会大众中的认同度。梳理网络话语的权利,规范网络话语的权力,消除群体事件舆情放大器的生成可能,是当前理论界必须关注的重大现实问题。
一、权利与权力:网络话语权的基本构成
福柯指出:“话语意味着一个社会团体依据某些成规将其意义传播于社会之中,以此确立其社会地位,并为其他团体所认识的过程。”[2]也就是说,对于一个行动群体而言,话语权是制定群体行动规则和支配群体行动的一种权力。作为政治学、哲学和传播学等领域的一个时兴术语,话语权近年来引起学者们高度关注。随着互联网快速发展和迅速普及,传统意义上单边输入的话语权范式,已为多元参与和交相互动的网络话语权所打破,一个崭新的虚拟和现实交相呼应的空间环境话语传播模式,越来越成为社会大众表达利益诉求,彰显自身权利,并在排斥异己语言和扩散自己话语体系的过程中,形成对某一社会现象和问题的支配与控制的权力。权利和权力成为网络话语权的最基本构成。
(一)话语权利是网络话语主体的权利彰显
网络话语权首先是社会大众在虚拟空间环境中自主彰显的一种主体权利。戴维·伊斯顿曾在《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中指出:“政治生活自身包含着各种各样的因素或子系统,这些因素或子系统之间的相互影响、冲突、适应构成政治系统,政治系统与其他系统构成整个的社会大系统,社会大系统构成政治系统的外部环境与制约因素,政治系统要想保持稳定,不但要与外部环境保持和谐,也要使系统内部各因素、子系统能实现良性互动。”[3]伊斯顿这段话语虽然是就政治稳定而强调政治系统内外部互动的重要性,表明大众自主表达的信息“输入”是构建稳定政治环境一个极为重要环节。而现实生活中由于某些基层政府存在“输入性堵塞”,使得社会大众无法及时有效地通过畅通渠道表达自己利益诉求,而互联网络的发展无疑给社会大众提供了一个彰显自身权利的新平台。
不同于传统媒体的单边输入缺乏有效互动,网络空间使不同阶层和利益群体可以畅所欲言地自由表达个人或群体意见,为社会大众提供了“什么时间说”“什么事情说”“具体说什么”“以什么方式说”等自由的主体表达权利。权利源自对自身利益的关注,一切行动无不围绕着利益。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人们为之奋斗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4]依据对权利源出的内涵界定,我们可以基于利益表达对话语权利进行阐述。所谓话语权利,就是社会大众基于对自身利益关注而拥有的并应受到保障的客观的话语表达权利。作为话语权构成的基础,话语权利的存在既是社会大众意志自由的权利彰显,又是保持政治社会稳定所必需的社会大众对政治系统的信息输入。转型时期许多重大群体事件的发生,恰恰是因为某些基层政府在政治参与渠道、利益诉求机制、话语表达方式和权利制度保障方面,存在一定程度的不健全甚至缺位。而网络的特性给社会大众提供了一个即时、宽松、自由、包容的利益表达渠道和信息交流平台,社会大众在这个虚拟网络空间中自由平等行使自身话语权利,机会均等地接受各种不同的信息。不同于传统媒体传播政府控制“何时说”“由谁说”“怎么说”“说什么”的单向信息输出,互联网的自身特点为社会大众的自由表达和进行舆论传播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每一个接入互联网络的社会个体或群体都可以基于内心自愿或出于某种利益诉求而进行自由的言说,也恰恰是这种自由的言说给转型社会时期的利益冲突提供了一个舆情缓冲地带。
(二)话语权力是网络话语对社会的控制力
福柯指出:“为什么这个话语不可能成为另一个话语,它究竟在什么方面排斥其他话语,以及在其他话语之中同其他话语相比,它是怎样占据任何其他一种话语都无法占据的位置。”[5]这就是话语的权力。同权利源自对利益的关注一样,权力最终也是为了利益,其表现形式主要有两种:“第一,它们作为分散之力,联合、集中起来组成公共机关之权力,它们是公共机关权力之源泉、原动力;公共机关权力则是一种集合力、公力。第二,它们在公共机关权力形成之后和运行全过程,作为对公共机关公务活动的参与力和监督力。”[6]公共机关的权力源自和合成于分散社会大众个人之权力,社会大众具有参与和监督公共权力运行的权利和义务,而且这种参与和监督是不因他力的干扰和意志而转移。而所谓话语权力,就是社会大众为了维护自身权利而具有的不受外力干扰的后天参与和主观自由表达的话语权力。这种权力直接体现为作为话语主体的社会大众,为彰显自身利益诉求和贯彻自己主观意志进行一种强制性的话语表达和行为参与。正如马克斯·韦伯所言,“一个人或很多人在某一种共同体行动中哪怕遇到参加者的反抗也能贯彻自己的意志的机会”[7]。
福柯认为:“在有话语的地方就有权力,权力是话语运作的无所不在的支配力量,社会性的和政治性的权力总是通过话语去运作。”[8]话语与权力是一种不可截然分开的互相支撑下的胶着。作为话语权力的一种,所谓网络话语权力,是指作为话语主体的社会大众通过网络空间表达自身意志权利、彰显自身利益诉求的话语影响力,以及由此对现实社会行为主体和公共权力所形成的话语压力和行为参与力。网络话语权力是网络话语权得以实现的保障,它是作为话语主体的社会大众针对某一问题、现象或某种利益诉求,在网络空间进行的具有排他性和支配性的言语行动,是这一话语问题下大众参与者的权力与社会地位的相互彰显。不同于现实世界的话语权力,网络空间中的话语权力具有自身的行动轨迹、影响范畴和实际控制力,现实世界中话语权力的拥有者,并不一定能在网络空间环境中拥有相应的话语权力。网络话语的权力属性,非常充分地体现出话语的表达者不仅仅只是停留在倾诉的层面,而是很多人的共同意志和集体行动,引起公共权力对现实社会问题的关注和解决,推动现实利益诉求的实现和满足。虽然这种权力在属性上并没有得到公共权力所赋予的合法的强制性,但由于网络空间环境剔除了从一到多的言语互动中不同的声音,通过网络的技术能量极度放大了相同声音覆盖范围和力度,从而形成对现实社会行为主体的舆论压力,推动问题走向支配话语权的一方。
二、权利与权力:网络话语权的传播现状
由于网络话语参与主体身份复杂难辨,而且网络监管存在严重缺位,大量歪曲事实的网络谣言和流言在网络空间飞速散布。尤其要引起关注的是,网络话语权控制下发生的越来越多的重大群体事件,既严重地影响党在群众中的威信,也严重地影响社会稳定与国家安全。
(一)网络话语的权利与义务失衡
互联网络技术飞速发展极大拓展了社会大众自由表达利益诉求的途径,也拓宽了社会大众行使参与权利和监督公共权力的渠道。传统社会舆论的传播是程序化和制度化的,无论是广播、电视还是报纸、杂志,都有相应的政府机关及其配备的媒体官员作为“把关人”,以正确的舆论导向原则来审定、过滤和取舍媒体传播的内容,删除不符合主流意识形态需要的信息,将非主流传播媒介的零碎声音屏蔽在社会大众获取信息的主流渠道之外,把政府需要的舆论信息保留下来,并确定信息发布的时间,严格控制“何时去说”“由谁来说”“说什么内容”和“怎么去说”。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和应用,从根本上改变了信息传播单一输出模式,为社会大众提供了一个宽泛的话语平台和表达渠道,任何一个能够接入网络的信息工具,都可以将大众自身的话语传播到网络空间,并借助网络的特性来“放大”自己的声音。“在互联网这个独立的空间中,任何人在任何地方可以自由地表达其观点,无论这种观点多么奇异,都不必担心受到压制而被迫保持沉默或一致”[9]。正因如此,网络话语才以反映“最基层”、形式“最自然”、内容“最真实”、表达“最朴实”、观点“最自由”而 受 大 众 推 崇 。 在 WECHAT、BLOG、QQ、ICQ、BBS、E-MAIL等诸多网络交流平台中,社会大众在你一言我一语中表达自身利益诉求,行使自己话语权利,传统话语体系中“一元输入”变成了网络空间中“多元输出”。
必须注意的是,权利必然伴随着义务,权利与义务的相辅相成才是完善健康的民主。在权利和义务的关系上,权利对义务具有优先性,义务存在的目的在于保障权利的实现[10]。因此,社会大众在自由、平等地享受网络话语权的同时,必须承担对自己话语负责的义务。每一个人或每一个社会群体都可以通过网络平台正确、真实地表达自身利益诉求,但绝不是不受任何限制和约束地歪曲事实或谣言惑众。“网络在鼓励人们自由发表意见的同时,也滋生了个人的劣根性,个体性的发展导致孤独感、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人的自由让人无拘无束也助长了无法无天”[11]。网络谣言就是网络话语中权利与义务失衡的一种典型表现。由于缺乏传统媒体“把关人”的信息过滤,大量歪曲事实或者糅杂个人情绪的虚假信息甚至惑众的谣言在网络空间传播。网络流言蜚语之所以为社会大众所接受,是因为谣言的编造者利用现实社会发生的某一事件为诱导因素,或者利用转型转轨过程中因为合理利益诉求无法得到有效满足而滋生的消极情绪为背景,非常容易引起相同背景的社会个体的情感共鸣。这些谣言不但给社会大众提供了大量歪曲事实真相的信息,而且极易点燃群体情绪,进而发生严重危害社会稳定的群体事件。近年来先后发生的贵州瓮安事件、湖北石首事件、安徽马鞍山事件等等重大群体事件演化的拐点,恰恰是由于网络谣言的疯狂传播。
(二)网络话语的权力与责任失衡
网络话语的一个典型特点,就是在最短的时间内达到“由一到多”的“蝴蝶效应”,从而以“众人”的影响力形成对公共权力的外在压力,这种影响就是网络话语的权力效应。随着我国网民数量的激增,这种网络话语的权力效应在严重冲击传统一元化价值观的同时,日益解构传统媒体环境下政府控制和分配话语权的信息舆论传播模式,不断消解传统媒体环境下政府控制媒体把关单一信息传播的权威地位。2014年1月,中国互联网络信息发布中心(CNNIC)发布了《第33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调查统计报告》,截至2013年12月,中国网民规模达到6.18亿,全国共计新增网民5 358万人,互联网普及率达到45.8%,比2012年提升了3.7个百分点。我国网民中农村人口占比28.6%,规模达到1.77亿,相比2102年增长2 101万人。尤其要关注的是,截至2013年12月,中国手机网民规模高达5亿,比2012年增加了8 009万人,其中,使用手机上网的人群占比提升到81.0%。庞大的网民数量和源自虚拟空间场域中我一语你一言最真实的话语真相,正在将舆论信息传播的权力场域从传统媒体转向社会大众。
必须清醒的是,一些社会大众在网络空间为实现自我利益诉求而行使权利时,忽视了自身应当承担的话语权力责任。话语权力滥用是导致社会舆论危机的重要根源。一些匿名于网络空间中的社会个体或群体,为了一己之利而忘却自我道德和法律约束,肆意传播一些情绪化言论,或者发布非理性的诋毁党和政府的偏激言论,煽动大众对政府不满。尤其是当遇到突发事件时,利用网络舆论的话语优势不断误导和挑起社会大众情绪,在推动事态走向不可预知的同时,也极大降低了政府的权威。话语权力滥用导致社会大众民意被操纵。“权力是一柄双刃剑,正确使用权力,可以发挥才华,造福于民;滥用权力,则必然祸害百姓”[12]。话语权力滥用也给西方意识形态渗透提供了便利途径。作为美国新经济发展的产物,网络及网络文化的发展具有显著西方文化霸权色彩。西方敌对势力利用他们在互联网络领域的优势,大肆传播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等一些落后、腐朽甚至极端错误的信息,以庞大舆论优势冲击大众的价值判断,借助我国转型时期出现的一些暂时性问题和利益冲突,大肆制造和控制舆论以混淆视听,在严重恶化事态后果的同时,大力灌输西方意识形态,严重危及党的执政基础和执政地位。
三、权利与权力:网络话语权的建构路径
有话语的地方就有权利和权力。维护社会大众话语权利,并通过网络话语权力形成对现实问题关注的压力,这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良性发展的需要。但关键是当下大量网络话语发布主体只是在尽情享有话语的权利,而没有或者不愿意承担自己话语应负的义务;只是为了一己之利或别有用心而蛊惑大众的网络情绪,而没有承担自己话语的责任。构建畅通规范的网络话语表达渠道,约束与规范网络话语表达的权力效应,是极为重要的现实问题。
(一)在畅通与监管网络话语权利中构建网络话语权
维护自身利益诉求的渴望和现实体制下制度化参与表达困境之间的博弈与对撞,无疑使得社会大众去寻找非制度化的途径和渠道,网络空间恰恰为大众提供了便捷表达渠道。因为它以最草根的话语方式反映普通百姓的酸甜苦辣。控制网络话语权,必须立足网络话语的发展现实,在充分尊重社会大众网络话语权利的基础上,通过加大政府网站平台建设,给普通民众提供畅通的网络话语平台,让不同层面的社会个体和利益群体,都有最直接向公共权力行使自由表达权利的空间场域,使政府决策最大可能兼顾社会各方利益诉求。而公共权力机构也可以通过政府网站,就事关民生的体制决策及时与社会大众进行双向互动,以平民化的视角和贴近大众生活的话语范式,积极关注事关普通群众生活的微观社会问题,缓解社会大众不良舆情的蓄积。对于事关民众切身利益的社会事件,要通过畅通的网络渠道第一时间发出第一声音,满足社会大众的知情权利,疏导社会大众的不良情绪,根除谣言蜚语生成的土壤环境,消解社会冲突发生的可能性。
保罗·莱文森指出:“在因特网创造的环境中,纸张、装订、发运和广播的成本,全部消失了。因特网拉开架式,要把把关人砸烂。”[13]构建网络话语权,在保障通过畅通的表达渠道以获取民意所向的同时,应通过有效的网络监管,防止虚假的、极端消极个人情绪、利己主义、个人主义、拜金主义等信息和言论在网络空间肆意传播。因为“个人话语权的滥用已经成为网络祸患,使得网络不再是一个辨析真理、发表观点、交流思想的平台,而是一个宣泄情绪的场所”[14]。加强网络话语监管,首先,要加强政府网站建设。监管并不是不允许大众发出声音,而是通过制度化平台,给大众提供畅通的民意表达渠道,引导社会大众进行政治参与。“公民自由的参与、表达,在网络空间中形成相对自由的观念市场,并非是最终目的,目标是将网络空间中的政治参与纳入到政治过程中,实现政治发展”[15]。其次,要强化网民义务,提升网民的道德自律和法律意识。网络话语的言论自由、多元化发展和匿名性表达,使得一些网民根本无视话语的责任,使得一些引发社会混乱和影响社会稳定的虚假信息自己传播,而网络“把关人”在软硬件条件上的缺位和缺失,使得网络话语的负面效应被淋漓尽致地发挥出来,任何一个网络话语和谣言信息,都可以在极短的时间内达到“蝴蝶效应”。控制网络话语权,必须是社会大众在享受网络话语权利的同时,切实承担网络话语的义务。最后,要加强网络秩序建设。控制网络话语权,要立好法,把好门,随时警示网络行为主体,及时定位谣言发布者,在制度监管和技术威慑中疏导网络话语,引导网络舆论。
(二)在约束与规范网络话语权力中构建网络话语权
费尔克拉夫认为:“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实践的话语从权力关系的各种立场建立、培养、维护和改变世界……作为一种政治实践的话语,不仅仅是权力斗争的场所,而且也是权力斗争的一个至关重要的方面:话语实践利用了那些孕育了特殊的权力关系和意识形态的习俗,而这些习俗本身及它们得到表达的方式是斗争的焦点。”[16]把费尔克拉夫的观点移植到网络空间环境,作为权力斗争的场所和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网络空间环境中的话语权,是政党必须直面、重视和掌握的现代社会发展进程中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执政能力。网络话语权力,形成于网络空间众多话语主体的共同意志,是现实社会生活中“很多人”需要在网络空间中的共同反映和同质放大。网络话语权力形成过程,既是社会大众平等反映利益诉求、自主表达个人观点、直接参与政治生活、积极行使监督权利的过程,也是公共权力机关听取民意、关注民生、贴近群众执政为民的过程。公共权力如果无视这一现实,必然导致对社会不满的情绪大量累积,触发社会冲突导致执政资源流失的可能性就会大大增加。当下构建网络话语权,必须约束与规范网络话语权力形成的场域环境。
1.要强化网络话语权力场域的阵地意识。网络话语的权力影响,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对异己话语的排斥和对自身话语的无限增量与放量,来影响社会行为主体。如何抓住网络话语的权力优势,有效引导多元自由的网络话语,强化党的话语控制力,使网络阵地始终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始终成为社会大众表达合理利益诉求和有效监督公共权力的畅通渠道,是各级党的组织必须完成的“守土有责”的历史使命。“互联网是开放的,信息庞杂多样,既有大量进步、健康、有益的信息,也有不少反动、迷信、黄色的内容。互联网已经成为思想政治工作的一个新的重要阵地。国内外的敌对势力正竭力利用它同我们党和政府争夺群众,争夺青年。我们要研究其特点,采取有力措施应对这种挑战。要主动出击,增强我们在网上的正面宣传和影响力。各级领导干部要密切关注和研究信息网络发展的新动向,抓紧学习网络知识,善于利用网络开展工作,努力掌握网上斗争的主动权”[17]。对于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党的各级组织都必须始终保持高度清醒的危机意识和阵地意识,充分利用网络的积极影响宣传主流意识形态,遏制不良社会思潮对大众的消极影响,通过控制和掌握网络话语权,引导社会大众客观公正地认识转型过程中出现的暂时问题,积极主动地投身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
2.要强化对网络话语权力场域的高度关注。马克思指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18]。网络话语之所以形成对现实行为主体的权力影响,是因为民众的共同关注,是现实生活中民众的社会存在决定了他们的网络话语意识。党的权力是人民群众赋予的,党行使权力的目的就是为这些权力的赋予者服务,关注他们的需要,满足他们的利益诉求,是党不变的工作方向和执政宗旨。消解网络话语形成的权力压力,需要各级党的组织积极主动地在实际工作中真正俯下身来,深入最基层群众,了解他们的需要,倾听他们的声音,化解他们的矛盾,满足他们的利益诉求,由此从根本上消除社会大众层面形成的网络话语压力。
3.要强化对网络话语权力场域的监管力度。作为一种新兴的信息传播媒介,伴随着网络话语而形成的网络话语的权力场域,是当前不良社会舆论,尤其是西方借以对我国进行意识形态渗透的新平台。“在人类的历史上任何一种新媒介的出现,都成为政治、经济权力争夺的中心,不仅原有的社会强权会插手其间,而且新的社会势力也可能破土而出,网络时代民主社会所面临的危机,是以操纵信息为基础而衍生出来的种种变相而隐秘的政治控制手段”[19]。西方霸权利用互联网络领域的技术优势和话语能力,在网络空间环境中强势推进西方意识形态,煽动各种社会思潮冲击主流意识形态,不断推进“西化”战略。由于约束和规范的乏力,西方的网络话语利用一切途径大肆传播腐朽、堕落、错误的思想言论,以扭曲社会大众特别是党员干部的自我判断和价值判断;利用一切矛盾制造舆论混淆视听,将原本简单的人民内部矛盾推向不可知的复杂状态;利用一切可能,大肆鼓吹西方的“普世价值”,在冲击社会大众思想信仰和党性观念的同时,降低了主流意识形态的凝聚力和影响力,影响了党的执政资源和党的威信。各级党的组织要充分认识当前互联网话语权力场域的严峻形势,从维护国家安全和保持政治社会稳定的高度切实增强责任意识和危机意识,加强技术检测,做好网络信息的“把关人”,第一时间发现和删除虚假信息与社会谣言,第一时间疏导不良网络舆情,第一时间稀释社会大众的错位关注,第一时间挖出影响社会稳定的煽动性言论,第一时间封堵西方对我国政治制度的攻击和意识形态的渗透。
让-马克·夸克指出:“认同需要满意度。没有满意,就不会认同。”[20]网络话语权建构,来自社会大众对网络话语权利与权力的认同。保持畅通的网络话语表达渠道,使处于不同社会阶层大众个体和利益群体,都能自由表达自身合理利益诉求,自由行使平等的参与和监督权利,同时又能承担网络话语的义务,这是构建网络话语权的权利认同前提;自由的网络空间环境,使社会大众都可以通过网络“放大”自己的声音,形成对公共权力和行为主体现实影响力的话语权力,同时又能承担网络话语的责任,这是构建网络话语权的权力认同前提。只有网络话语的权利与义务、权力与责任一致,网络话语权才能得到真正建构。
[1]毛旻铮,李海涛.政治文明视野中的网络话语权[J].南京社会科学,2007,(5):98-102.
[2]王治河.福柯[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9:159.
[3]戴维·伊斯顿.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M].王浦劬,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99:37.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87.
[5]米歇尔·福柯.知识考古学[M].谢强,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28-29.
[6]漆多俊.论权力[J].法学研究,2001,(1):18-32.
[7]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下卷[M].阎克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246.
[8]王一川.语言乌托邦[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241.
[9]刘吉,金吾伦.千年惊醒:信息化与知识经济[M].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278.
[10]马国强.法律义务实现中的国家主义和公民参与[J].学术交流,(8):76-80.
[11]刘梅.论思想政治教育的现代方式[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2):103-106.
[12]孙载夫.谈权力[J].湖湘论坛,2002,(3):4-6.
[13]保罗·莱文森.数字麦克卢汉——信息化新纪元指南[M].何道宽,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180.
[14]李蔚.网络信息传播与网络话语权控制[J].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09,(3):110-112.
[15]虞崇胜,邹旭怡.秩序重构与合作共治:中国网络空间治理创新的路径选择[J].理论探讨,2014,(4):28-32.
[16]费尔克拉夫.话语与社会变迁[M].殷晓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3:62.
[17]江泽民文选:第 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94.
[1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2.
[19]丁未.网络空间的民主与自由[J].现代传播,2000,(6):19-24.
[20]让-马克·夸克.合法性与政治[M].佟心平,王远飞,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2.
(责任编辑:于健慧)
G206
A
1005-460X(2015)06-0014-05
2015-10-03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互联网领域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权研究”(15BKS109);教育部规划基金项目“重大群体事件围观者参与冲突的价值因素研究”(13YJA710025);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化解社会‘无直接利益冲突’对策研究”(11ZZC006);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专项任务项目“网络话语权与重大群体事件舆情引导策略研究”(14JDSZK077)
黄宝玲(1972—),女,陕西汉中人,博士生,江苏建筑职业技术学院思政部副教授,从事中国政治和群体事件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