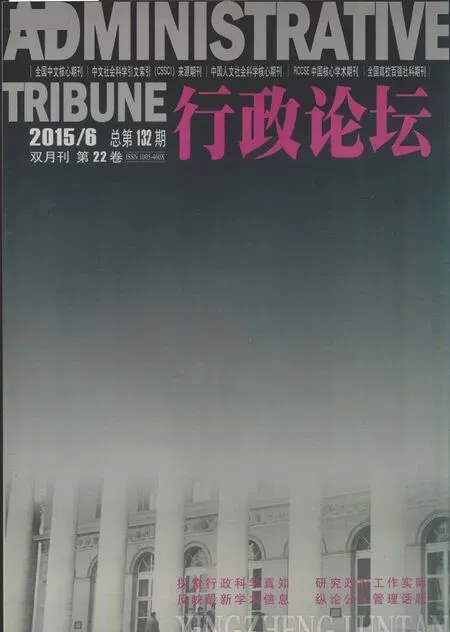化解科层行政管制与现代公共治理之间的张力:以问题意识为导向
◎陈 毅 (华东政法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上海201620)
化解科层行政管制与现代公共治理之间的张力:以问题意识为导向
◎陈 毅 (华东政法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上海201620)
尽管在边界、主体、责任和工具选择上,科层行政管制与现代公共治理存在很大的张力,但是基于新公共管理之上的现代公共治理既是对科层行政管制的反思,所追求的公共价值的治理、协同性治理和整体性治理,又是对科层行政管制代表的公共性和全局性的回归。基于问题意识的流程再造、治理主体的复合、治理对象的复合和治理工具的复合,是化解二者张力的出路。
科层行政管制;现代公共治理;风险社会;整体性治理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已成为我国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的重要战略和发展方向,可见治理问题的重要性。对于治理的讨论文献也汗牛充栋,也越来越清晰帮人们理清治理的内涵与外延,及其治理理念对我国的适应性等问题。笔者认为处理好行政权威与社会民主这对矛盾,既是一个老问题,又是解决现代公共治理难题的关键之所在,本文意在这方面深入分析,加以澄清和突出这对关系的重要性。
综观现代国家治理经历了三个比较清晰的阶段:科层行政管制阶段、新公共管理阶段和现代公共治理阶段。科层行政管制阶段具有很强烈的建构色彩,把现代性所包含的重规则、重科技理性(工具理性)和重主体性等内涵都通过科层制方式建构起来。而新公共管理阶段是一个解构过程,要求多元化、市场化、私有化和民营化,尽管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化解科层官僚制弊端,但撒切尔夫人和里根的改革最终以喜忧参半的方式宣告终结,随后的布莱尔政府和克林顿政府都选择了走“第三条道路”。现代公共治理又是一个重构过程,在新公共管理基础上开始强调“公共价值的治理”[1]、“协作性治理”[2]和“整体性治理”[3],在一个分化多元、多主体参与基础上的现代公共治理重构整体政治,是对我们政治智慧和政治技艺的重大挑战,然而,这又是身处风险社会的我们必须面对的挑战,在不确定性世界寻求确定性的解。
一、治理对象的变迁催生现代公共治理的成长
(一)时代变迁:从工业社会到风险社会
当人类进入大规模机器化大生产的工业社会,为了追求更高的生产效率,泰勒阐释的科层制得到广泛的普及,非人格化的现代企业制度和现代经理人制度大大超越传统家庭手工业作坊的局限,最大限度地调动和优化人财物资源的配置,都纷纷全球上市,人才、资本和商品在世界范围流动起来,创造了人类巨大的物质文明。然而,机器化的大生产也在惨重地打破自然和生产的平衡,人类在改造世界的同时也正在毁灭世界,资源的耗竭、环境的恶化,地震海啸等自然灾害频发,核武器的威慑、病毒的变异等等,都预示着风险社会的到来,自然风险和社会风险与日剧增。社会风险,诸如产业结构迅速升级换代带来的高失业风险使人惶恐焦虑,高强度的工作节奏、高危险的工作环境和高污染的生存状况也使人高度不安。而且正如乌尔里希·贝克所言,所有的风险社会已构成世界风险社会。哈贝马斯也强调:“全球性的危险与日俱增,它们悄悄地迫使世界上各个民族不由自主地组成一个风险共同体。”[4]因此,对于充满复杂和不确定性的风险社会的监管,对于风险的分担与分配,既关涉到最微观的民众的风险认知,也关涉到最宏观的全球风险问题,仅依靠科层行政管制已经力不从心了。由于机构臃肿,长期养成的官僚作风,部门之间的专业化分工带来的“治理碎片化”,科层之间的信息封锁与资金截流,以及行政机构被利益集团所绑架而行为扭曲等,这些都亟待通过公共治理来解决。
(二)空间转场:从“生产政治”到“消费政治”
在资本主义大生产阶段,资本家最大限度地榨取工人的剩余劳动价值,政治也更多围绕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的阶级斗争展开,阶级政治构成国家的主要组成部分。当资本家意识到只有让工人有能力消费,才能促进生产的循环,以生产为中心的阶级国家兼容了以调整分配为中心的福利国家,靠市场的保险和国家的福利保障,阶级矛盾得到了较大程度的缓和,人们的自由度得到很大程度的释放,社会被激活,充满生机。鼓励消费刺激了人们生活方式的多样性,并且越来越多的生活方式得到理解和尊重,“生活政治”的勃兴,使政治从狭隘的围绕政权进行的权力斗争走向更加广泛地围绕利益进行的权利抗争。公民权经历了从政治权利、经济权利到社会文化权利的延展和拓宽,越来越具有丰富的内涵,为了最大化维护个人切身利益,公民参与政治的激情高涨,在参与政治的过程中,参政议政的能力也得到了提升。吸纳利益相关者参与到政策制定和完善中来的协商参与模式越来越代替过去行政部门关起门来决策的模式。当然,人们在享受消费带来的生活变化的同时,也在承受过度消费所带来的恶果,加剧了社会风险,诸如消费至上带来的物欲膨胀和互相攀比,过于世俗化的生活对人们精神生活的冲击,奢靡消费对资源的巨大浪费和蚕食,消费能力差异所造成的社会隔离引发新的社会问题,等等。这里需要强调的是,消费不仅包括物质的,还包括价值消费、生活方式消费等更加多元和难以控制的层面。生活政治将政治从神坛还原给人本身,但人又使生活世界变得五味杂陈、危机四伏;消费社会释放出一个多样化充满活力的社会,但又如打开的潘多拉魔盒,我们难以驾驭它。
(三)解构理性:从科技理性到后现代性的叙事
工业社会取得巨大成就的一个重要原因源于科技的进步,这也大大提升了各类专家学者在决策中的地位,而且很多水利、电力、土木工程等理工专家从幕后走上政治前台直接决策,不断更新的科技进步助长了人们的理性狂妄,也使科学家和专家垄断了决策权,越来越使普通民众难以参与到决策的制定和监督中。然而,在一个开放的信息化时代,一方面,原来高深的科技现在变成普通人可以掌握的科普,科技的神秘性被打破;另一方面,科技进步也在挑战人们的理性,一次次科技神话被巨大的灾难所击破,诸如人们还没从切尔诺贝利核泄漏噩梦中走出来,又笼罩在福岛核泄漏的阴影中,自以为聪明的人们又成为自己的受害者。由于每个人难以克服的知识的碎片化和理性的结构性无知等,正如后现代叙事所强调没有人能够宣称自己完全掌握了正确性或真理,每个人所掌握的不过是一个有待历史检验的“事实”,最多提供给人们多一种可供参考和选择的可能,每个人仅有一种述说的权利(表达自己的意见和讲叙自己的故事),仅此而已,没有了权威,没有了圣人,而每个人又都可能是权威和圣人,最起码不盲从权威,在多听几家权威的意见后学会提升自己的鉴别能力,这些认知既大大破除了对科技理性的盲信,也大大提升了人们参与对风险社会治理的信心和必要性。与其说这是后现代叙事可能略显激进,不如说是对现代性的反思可能更贴切。在诸多反思现代性的思想家那里,都强调主体的自反性和主体间性,诸如吉登斯强调“自我的反思性投射:由自我叙述的反思性秩序来构成自我认同的过程”[5],基于此,他又非常强调“对话民主”的重要性,“那里有发达的交往自主权,这种交往构成了对话,并通过对话形成政策和行为”[6],即使对话达不成行动共识,也不能否认对话的价值,因为对话本身就是价值。这些观念的转变既催生了对多元主体参与公共治理的需求,也提供了公共治理的可能性。
时空转化演进的不确定性风险社会是对科层行政管制所构建的确定性世界的解构,催生了希望通过现代公共治理重构整体政治,这又有对科层行政管制所代表的公共性和全局性的回归之意,这也是本文想从全局的问题意识为先导来整合二者的原因。在解释之前,有必要对现代公共治理与科层行政管制之间的张力逐一澄清。
二、科层行政管制与现代公共治理之间的张力
(一)关于边界的争论:边界清晰还是跨越边界
现代民族国家的显著特征以明确的疆界划分对外享有独立的主权,以清晰的层级和职能定位对内享有完整的治权。正如Kettl所言:“边界已经构成公共行政和政府的根本。”[7]奥尔森对集体行动的研究,也明确指出大型组织的崩溃主要源于组织边界的不清晰,搭便车行为导致没有人愿意对组织共同利益负责[8]。然而,管理专家杰克·韦尔奇认为:“在传统意义上,企业以边界管理取胜,机构和业务严格划分,部分之间恪守边界。未来的企业则要靠无边界取胜,内部与外部种种围墙和藩篱全部推倒,各种障碍全部清除,使要素能够自由流通。”[9]无边界组织正是现代公共治理所需面对的,因为随着跨越行政区划之上的区域性甚至全球性公共事务的增多,信息化时代带来的无所不在“渗透性结构”使传统“内部”问题日益外溢和无界化,使基于职能和地域界分的科层行政管制日益显得软弱无力,这迫切需要从围绕共同解决的问题(诸如对全球犯罪、恐怖活动和环境污染的共同治理等)出发,模糊和超越行政管辖边界,培育一种善于从其他组织中寻找能够一起解决问题的同僚的政府管理人才,期望通过他们的协商会晤达成共识、重新设置机构和行动纲领,这也得益于现代交通的便利和信息传递的迅捷等客观条件的支持,从而走出公共治理的难题。当然,也不赞同对于全球性公共事务的治理就必然选择统一的全球政府这样一种权力集中模式,这里存在一个跨域边界的限度问题,基于可见预期和共同成长的共同体利益才有助于凝聚共同体成员的心理,跨越的边界止于何处还取决于参与者群体的能力程度,即能否驾驭得住跨越后的共同体。
(二)关于主体的争论:权威(官僚或专家)还是基于民众
20世纪初威尔逊总统提出政治与行政的二分,突出行政的自主性,使行政权威迅速增长。随后马克斯·韦伯阐释的官僚制也得到普遍认同,如何打造一个管理严密、训练有素和执行高效的官僚科层制也成为各国政府首要考虑的问题,解决如何组织生产和分配福利,以审批和监管为主要特征的“行政国家”是这一时期的显著标志。科层行政管制认为,随着对行政管理的专业化要求程度越来越高,应该由通过代议民主选举出来的代表和通过考试选拔出来的官员来替民作主,制定公共政策。当然,保留民众对政策绩效享有评估和在下次选举中享有对代表罢免的权利。而现代公共治理认为,对于一个不确定的风险社会,不能把鸡蛋都放在一个筐里,靠官僚或专家的科技理性并不完全可靠,民众也有参与和鉴别能力,群防群控、群策群力才是出路。诸如像SARS、H7N9、埃博拉等病毒的肆虐,我们不能仅靠等待科学研发的新疫苗来遏制,因为一方面疫苗还没来得及被广泛验证就匆忙用于治疗患者,这充满了未知风险;另一方面,新的病毒不断地席卷而来,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防不胜防。这就更需要在危机爆发时发动广大群众隔断传染源、配合检查和相关机构的联合行动;在平时增强自身免疫力,加强卫生防御和环境治理,才是源头治理。尽管理想状态是每个主体都平等地参与到公共治理中来,但事实上,每个人的参与能力和参与意愿存在很大的差异,既可能促成合作,也可能阻碍合作,这里存在一个对于民众的参与规模进行考量的问题。参与者不能太少,否则那些受到影响的人没有机会参与到这些涉及他们自己利益的决策中来;但也不是要把受到影响的人都纳入到决策的渠道中来,否则协商根本没办法进行,因为集体行动成本太大而导致参与没有意义,即不能回避扩大参与的收益与成本之间进行权衡的问题。因此,我们也需要辩证地看待那些不是很积极的政治参与冷漠者。
(三)关于责任的争论:集权还是分权共担
科层行政管制强调权责明晰,行政首长负责制,各级政府所担负的责任是宪法条款中明确规定的,各级政府可以按照法律的规定划分各自的责任。而结果是要么由于行政首长的权力过大,有法不依,根本游离于监督之外,难以真正履行责任;要么由于职能部门之间的分隔,而相互“踢皮球”“打太极”,没有主体真正负责;这也源于问责机制多是自上而下的行政机关内部的“同体问责”,难免官官相护,而缺乏来自外部的民主问责。在严密的科层官僚体制下,层层向下施压的“压力型体制”[10],往往结果是权力上收,事责下放,也使得地方政府眼光只瞻上而不顾下,难以真实体现民意。现代公共治理强调分权、责任共担,把与民众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事务放手让民众自己去管理,同时使享有的权利与应承担的责任相匹配,既能极大调动起民众的自主性,又能极大调动起利益相关人为他们的共同未来承担决策责任,这种既个人自主又相互协作的过程是一个动态过程,“这一过程包括自主的行动者通过正式和非正式的协商进行互动,共同创造规则和结构来管理他们的关系,确定行动方式,或就那些使他们走到一起的问题进行决策”[11]。当然,也可能导致“人人有责”的说辞变成“人人无责”的开脱。“由于协作活动中没有明显的委托人或者代理人,也没有和谐地分配组织权力,因此容易造成责任的不当分配,容易出现没有组织不负责,但也没有任何组织负全责的局面”[12]。因为集体行动的逻辑告诉我们每个人的搭便车行为(或侥幸心理)往往导致对集体不利甚至是使集体崩溃的结果,因此,我们不能想当然地认为具有共同利益的群体必然就会采取一致的积极集体行动,也可能导致集体盲从现象,尤其当这个集体被分利联盟所操纵时,盲从带来的后果就是纵容集团作恶。这也意味不能回避一个对民众进行引导的问题。“协作性领导的存在,即那些能够在多种利益之间进行斡旋,在诸多似乎敌对的利益之间进行干预,帮助他们找到立场背后的利益,从而看到可能的共同利益以实现协作的行动者,将是决定集体行动是否成功的关键”[13]。这个领导的扮演者可以是群众中的意见领袖,也可以是政府或政党组织。也即是说,分权共担责任并不是放任,也不是必然推导出“政府退却”。
(四)关于政策工具的争论:选择科层的行政权威还是民间的非正式规则
科层行政管制强调行政权威的强制作用,以中国为例,从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现代国家建设来看,建立起中央、省、市、县、乡等五级行政层级的政府,通过自上而下的国家权力下渗,直到最基层的城市居委会和农村的村委会,尽管它们名义上是自治组织,实际上是准行政性组织。中国传统靠自治的乡绅宗法社会在打土豪劣绅的革命中已经断裂,社会被挤压而国家化了,一个完整的“行政国家”被建构起来。习惯于借助“运动式治理”这种“一声令”“一刀切”“一阵风”的行政推动方式来实施对经济社会生活的管控。而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市场开始活跃,社会也逐渐被激活而回归到本原,户籍开始松动,人们流动加剧,社会组织也开始成长起来。处在一个大转型的巨型中国,一方面,借助等级制的行政权威来干预社会已力不从心,正如戈德史密斯和埃格斯所言:“传统的等级制政府模式根本就不能满足这一复杂而快速变革的时代需求,靠命令和控制程序、刻板的工作限制以及内向的组织文化和经营模式维系起来的严格的官僚制度,尤其不适宜处理那些常常要超越组织边界的复杂问题。”[14]另一方面,政府放权松绑式的改革也使市场化工具和社会化工具被借鉴过来,带来事半功倍的治理效果,尤其在经济建设对人们物质生活改善方面取得很大的治理绩效。而社会治理的问题在21世纪以来被正式提上政策议程,重建社区自治和乡村自治,利用传统、非正式规则、网络等社会资本建立起人与人之间“厚信任”关系,各地社区创新模式的尝试层出不穷,填补了在单位制衰落之后的基层社会公共空间,为解决风险社会的困境提供了民主的社会土壤。当然,这里需要澄清的是:对非正式规则的强调并不是对行政权威的抛弃,尽管非正式规则有助于制度的创新变革,为完善制度提供源源不绝的动力源泉,但行政权权威所制定的正式规则能给人们的行为以明确的预期,而降低交易成本。尽管有其制度滞后性和制度固化的不足,但对于现代治理来说不可或缺,甚至仍处于引导地位。
三、以问题为导向:走出集体行动的秩序困境
(一)基于问题的流程再造:超越基于职能的部门主义
我国目前很多政府改革还多停留在明晰政府职能、根据职能来定岗定编、进行机构重组上。但由于职责同构、部门利益作怪,诸如“权力部门化、部门利益化、利益法定化”,这些现象常常导致政府行为扭曲、条块分治、部门分割、协同沟通能力差等明显特征,即职能分割而导致治理“碎片化”,一旦发生复合型的公共危机事件,需要各地区各部门协同配合时,经常部门之间相互推诿扯皮而导致综合协调机制很难启动。而跨越部门界限和地域阻隔的流程型应急管理模式,以流程为中心就要研究问题的缘起、经过、所面临的困难,也可以根据危机的预防、孕育、爆发和平缓不同阶段制定相应的策略,寻找治理的内在规律性,以强烈的“问题意识”和“问题导向”来整合不同层级、不同类型政府、组织和机构的职责、内容、要求和时限,即“社会各部门、各单位之间发生组织联系,是围绕问题的治理而形成的一个‘问题网络’,这个网络具有强烈的问题解决意识,围绕政策问题组织在一起,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各个相关行动者有机互动,进而形成经常化的联系机制和共享的价值观念,进而构成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网络”[15]。从而,有利于推动从单部门管理到综合化管理的积极转变,实现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在应急管理过程中有机衔接和配合,形成整体合力,有效减少纵向上盲目服从、依赖上级政府和领导的现象与横向上由于职能分立、机构分离而经常出现的推诿扯皮现象。
(二)治理主体的复合:多主体之间的协同
以工业文明代表的现代性政治彰显了自足的主体性,不管是原子式的个人,还是享有法人主体资格的组织、机构和民族国家,主体利益的满足受到普遍尊重,但如果每个主体都强调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必然出现“囚徒困境”“公用地悲剧”等。而治理主体的复合强调:“参与各方看到问题的不同层面,能够建设性地利用他们的差异并寻求解决方法,这种方法和视角往往超越他们自己对于什么可能和可行的有限视角。”[16]因此,对于行政机构内部可以推广大部制改革,这也是世界范围行政改革的总体趋势,加强相关部门之间的复合联动,提高机构的执行效率,更好地实现整体性治理的目标。对于行政机构外部主体,加强行政主体、市场主体和社会主体之间的协同配合,发挥官本、资本和民本的各自优势,结合官僚代表的权威性、企业家代表的竞争性和社会组织代表的公益性,确保社会的竞争有序、兼顾效率与公平。对于公民个体,也从主体性走向主体间性,寻求合作共赢的格局。近代以来的主体,以经济成就争做“上帝的选民”,来证明自己,积极向外开拓,不断挑战自我的极限为最大荣耀,这难免在充分调动主体性的同时也让自己难以认清真实的自我。“太自我了”是对现代主体最好的阐释,这也使处在关系中的我们格格不入,使周围的环境变得非常糟糕。主体实际上也只有在被别的主体所认同的情况下,才真正享有主体资格,而不是仅自己说了算。主体如何做到自足,无欲则刚、闭门内修、反省自我有可能得到真谛,这也使我们更好地理解为什么卢梭强调“强制的自由”[17]这一概念。一个风险社会,有演进的结果,更有人为的原因,风险关涉每一个主体,只有每一个主体共同面对,自反自主性,检视自身的行为,限制自我,而不是仅考虑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满足,应学会从主体间性的视角共建合作双赢的新秩序格局,依靠民主从源头上治理风险。
(三)治理对象的复合:超越要么政治要么经济的单向思维
有学者对我国的新中国的建设总结为:前30年搞政治建设,后30年搞经济建设,再30年搞社会建设。而我们认为,国家建设根据每阶段国情特点进行排序优先发展某一方面没有错,但也要统筹兼顾,否则就会出现结构性失调。诸如一切以阶级斗争为纲,导致“文化大革命”的动荡;唯物质主义建设,又导致社会出现分化甚至“断裂”;高福利的社会建设,可能又面临财政压力和发展动力不足等问题。因此,也就能更好理解改革、发展与稳定三者统一所蕴含的深刻的道理。尤其对于风险社会的治理,不再仅表现出对问题某一方面的关注,而是一个复杂的问题系统,牵一发而动全身,往往是政治问题、经济问题、社会问题和文化问题等的复合,因为“现代社会面临的问题越来越复杂化,许多问题本身不完整、矛盾和不断变化从而使得该问题的解决成为不可能,同时也因为复杂的相互依赖关系而使得解决该类问题的一个层面的努力往往会产生或加剧另外的问题”[2]。这也是现阶段为什么我国的国家建设强调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社会文明和生态文明都不能缺少的全局建设的原因。从我国的内政外交看,也曾经把二者孤立起来,自力更生、闭关锁国,导致与二战后世界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擦肩而过。实际上,对内的改革和对外的开放为一体两面的国家战略,也只有在融入全球化的浪潮中注重本国的内政建设,才能不为世界所抛弃,对全球治理承担起应有的大国责任,才更为世界所认同和尊重。只有把治理对象看成是一个复杂的问题系统,实现问题的不同维度之间的横向复合和不同空间的纵向复合,才能更好地抓住问题的本质,进行“统筹治理”[18]。
(四)治理工具的复合:融合科层、市场和社会的优势
埃莉诺·奥斯特罗姆指出,解决“公用地悲剧”不是要么国家,要么市场这两种药方可供选择[19],她通过对共用的地下水资源、草场、公海等开发利用发现,基于自愿和对多种治理工具的综合利用,提供另一种解决集体行动的方案,即“公共池塘资源治理”。尽管科层行政管制暴露出诸多问题,对官僚制反思很有必要,但是也并不走向极端,宣称“国家退去”。我们崇拜市场,市场是最佳资源配置方式,但也不要陷入市场的神话而不能自拔,市场丛林法则带来的资源垄断是对自生自发的市场秩序的最好回击。社会自治是美好的期待,但是社会的演进也有很强的“路径依赖”,帕特南对意大利南北方的对比研究是这方面的最好证明[20];每个主体的平等参与治理也是一种美好的理念,由于能力差异、资金制约和管制门槛等多种因素影响,“无组织”、“乱哄哄”和“低效率”又是现实社会自治的表征。可见,这三方所包含的政策工具都既有优势又有不足,需要针对危机共同问题,综合运用各种政策工具的优势,取长补短,达到治理最佳效果。
[1]何艳玲.“公共价值管理”:一个新的公共行政学范式[J].政治学研究,2009,(6):62-68.
[2]刘亚平.协作性公共管理:现状与前景[J].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4):575-582.
[3]李瑞昌.公共治理转型:整体主义复兴[J].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9,(4):102-107.
[4]哈贝马斯.包容他者[M].曹卫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173.
[5]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M].赵旭东,方文,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8:274.
[6]安东尼·吉登斯.超越左与右[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127.
[7]KETTL D.Managing Boundaries in American Administration:The Collaboration Imperative[J].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2006,66(s1):10-19.
[8]OLSON M.The 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M].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1:62.
[9]罗恩·阿什克纳斯,迪夫·乌里奇,等.无边界组织[M].2版.姜文波,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5:1-7.
[10]荣敬本,崔之元,等.从压力型体制向民主合作体制的转变——县乡两级政治体制改革[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1.
[11]THOMSON A,JAMES P.Collaboration Process:Inside the Black Box[J].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2006,66(s1):20-33.
[12]AGRANOFF R,MCGUIRE M.Big Questions in Pubic Network Management Research[J].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search and Theory,2001,11(3):308-311.
[13]MILWARD H B,PROVAN K G.A Manager’s Guide to Choosing and Using Collaborative Networks[M].IBM Center for the Business of Government,2006:8.
[14]斯蒂芬·戈德史密斯,威廉·埃格斯.网络化治理[M].孙迎春,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6.
[15]唐皇凤.社会转型与组织化调控:中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组织网络研究[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179-180.
[16]GRAY B.Collaborating:Finding Common Ground for Multiparty Problems[M].San Francisco,CA:Jossey-Bass Publishers,1989:5.
[17]徐向东.自由主义、社会契约与政治辩护[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150.
[18]李瑞昌.统筹治理:国家战略与政府治理形态的契合[J].学术月刊,2009,(6):16-22.
[19]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制度安排和公用地两难处境[M]//奥斯特罗姆,非尼,皮希特.制度分析与发展的反思——问题与抉择.王诚,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81.
[20]罗伯特·帕特南.使民主运转起来[M].王列,赖海榕,译.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217.
F224;D630
A
1005-460X(2015)06-0045-05
2015-03-17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研究”(14AZD133);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现代国家构建过程中的国家自主性研究——以中国的现代国家建设为例”(11BZZ044)
陈毅(1979—),男,河南信阳人,行政管理系主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复旦大学政治学博士后研究人员,北京大学访问学者,复旦大学统一战线基地兼职研究员,从事集体行动理论和政治学基本理论研究。
——G省共建共治共享中的组织形式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