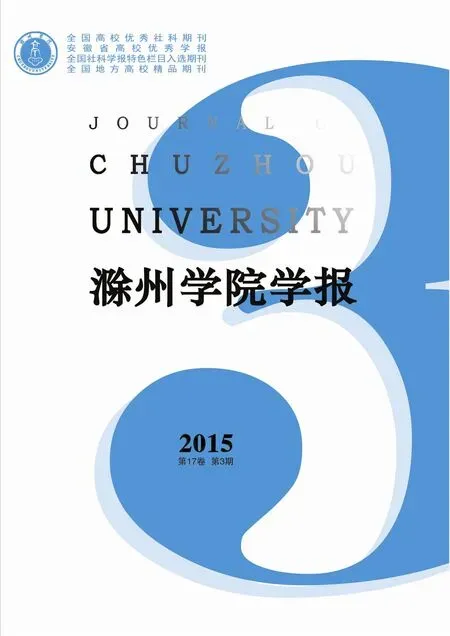琵琶与唐诗的意象融合
陈 璐,赵 娴
诗词的兴起、发展与燕乐有着密切的联系。琵琶作为燕乐中最重要的乐器之一,见证了中华两千多年历史的变迁,并随着时代的发展赋予了它越来越多的内涵。唐朝以前,“秦琵琶”是诗歌中对琵琶称呼最多的词。唐宋时期,琵琶空前流行,它在人们的心中不再是乐器,而是一种文化的象征。当时不仅流行琵琶曲的创作和弹唱,还将琵琶及意象运用到诗词歌赋中。琵琶以唐诗为素材,把美妙、清新的音乐呈现给人们;唐诗对琵琶艺术的细腻描写,使得琵琶具有了丰富的情感意蕴,形成了独特的琵琶意象,读者如闻其声。琵琶和唐诗相互影响,诗和乐相得益彰,意象融合。
一、琵琶的起源与发展
“琵琶”名称最早见于东汉,刘熙在《释名·释乐器》中首次提出:“批把本出胡中,马上所鼓也。推手前曰批,引手却曰把,象其鼓时,因以为名也。”[1]东汉应劭在《风俗通义》中也提及:“批把。谨按,此近世乐家所作,不知谁也。以手批把,因以为名。”[2]由此可知,琵琶,又叫“枇杷”或“批把”,是以演奏手法命名的乐器。最早的琵琶雏形源于秦末筑长城时,百姓在鼗鼓上作弦而成。由于这种琵琶产生于秦代,我们称之为秦琵琶。随着秦琵琶的逐渐发展完善,在汉代就形成了傅玄所说的圆盘柄直,四弦十二柱。到晋代,传说是在阮咸的手中,琵琶完成了一次重大的改革,音箱加大,柄加长,十二柱变为十三柱,这种变革就使得琵琶的音域更加宽广,表现力也增强。这种变革后的琵琶到唐代被命名为阮咸或者阮。《新唐书·元行冲传》载:“有人破古冢,得铜器似琵琶,身正圆,人莫能辨。行冲曰:“此阮咸所作器也。”命易以木,弦之,其声亮雅,乐家遂谓之阮咸。”[3]
从秦到两晋这段时期,琵琶有着各种各样的不同形制,但无论音箱形状、弦柱数目有怎样的变化,仍然具备秦琵琶直项、横抱或斜抱、手弹等的基本形态和演奏方式,我们统一称其为秦琵琶。到了南北朝时期,随着中外之间、民族之间的频繁交流,曲项琵琶作为一种新的乐器经丝绸之路传至中原。曲项琵琶源于波斯(今伊朗),其形制为梨形音箱、四弦四柱、曲项,用拨子弹奏,由于它区别于秦琵琶的直项,故被命名为曲项琵琶。据《隋书·音乐志》记载:“今曲项琵琶、竖箜篌,并出自西域,非华夏旧器。”[4]隋唐时期,曲项琵琶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和广泛的流传,在乐部中居于重要地位,“琵琶”这个名称也就逐渐由泛指“一类弹拨乐器”的统称成了特指曲项琵琶的专有名称。在唐代以后的文学作品中,琵琶多指曲项琵琶。隋唐以后,随着外来的曲项琵琶和本土的秦琵琶的不断融合,曲项琵琶不断改革演变,逐渐发展为曲项多柱琵琶,演奏姿势由横抱变成了竖抱,不仅丰富了音位、扩大了音域,而且增强了演奏技巧和效果。直到近代,琵琶才最终定型为现在的样式——六相二十四品。
“燕乐之器,以琵琶为首”[5],琵琶作为燕乐中十分重要的乐器之一,甚至可以说是燕乐中的首要乐器,其对燕乐的产生和发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新唐书·礼乐志》记载,唐高祖即位,仍隋制设九部乐(即:“清乐”“西凉乐”“龟兹乐”“天竺乐”“康国乐”“疏勒乐”“安国乐”“高丽乐”“礼毕乐”),每部都要用到十余种乐器,琵琶在其中都占有重要地位;唐太宗时增“高昌乐”一部,又以“燕乐”代替“礼毕乐”共为十部乐,“燕乐”为首。在燕乐所用到的22种乐器中,琵琶占到4种,即大小琵琶和大小五弦琵琶。[6]琵琶在隋唐宫廷燕乐中被普遍使用,具有重要的作用。国家大型乐舞中的歌舞乐均以琵琶为主奏乐器,春秋圣节皇帝举酒,殿上也独奏琵琶。“上有所好,下必盛焉。”唐代民间乐坊、茶楼酒肆也兴以琵琶为主要乐器。诗人陈去疾叹曰:“抱里琵琶最承宠,君王赦赐玉檀槽。”可见,唐代琵琶无论在宫廷和民间都具有重要的地位,可谓三千宠爱于一身,上至宫廷、下至民间,成为一种雅俗共赏的乐器。[6]琵琶的繁盛情况直接反映在唐代典型文学体裁——诗歌中。
二、唐代琵琶曲的繁荣和琵琶诗的发展历程
自东汉以来,先辈们对琵琶的了解逐渐深入,并在琵琶乐器上寄予越来越多的情感意蕴。特别是唐朝时期,燕乐的发展和繁荣,为琵琶的广泛接受和独立发展提供了重要条件,更为琵琶与唐诗的结合提供了可能,文学反映社会生活,涌现了大量的琵琶曲及琵琶诗。
(一)唐代琵琶曲的繁荣
琵琶开始是胡人在马上所弹奏的乐器,高中低音有不同的表现。高音音色嘹亮而具有韧性,中音音色婉转柔和平滑,低音音色浑然淳厚,总体上说它是一种具有较强感染力的乐器。
《唐音癸签卷十四·乐通三》详细记载唐代的琵琶曲有:“胜蛮奴、火凤、倾杯乐、郁轮袍、八十四调、西凉州、新翻羽调绿腰、枫香调、玉宸 宫调、蕤宾调、散水调、薄媚、杨下采桑、雀 蛇、胡王调、胡瓜苑、道调宫、玉宸宫、夷则宫、神林宫、蕤宾宫、无射宫、玄宗宫、黄钟宫、散水宫、仲吕宫、商调、独指泛清商、好仙商、侧商、红绡商、抹商、玉仙商、角调、双调角、醉吟角、大吕角、南吕 角、中吕角、高大殖角、蕤宾角、羽调、凤吟羽、背风香、背南羽、背平雨、应圣羽、玉宫羽、玉宸羽、风香调、大吕调□曲、凉州、伊州、胡渭州、甘州、绿腰、莫靼、倾 杯乐、安公子、水牯子、阿滥泛、湘妃怨、哭颜回……”[7]《唐音癸签》对唐代琵琶曲进行了整理,我们因此也可管窥到在唐代琵琶曲的繁荣情况。
古典琵琶曲划分为文武曲两类。唐代文曲代表作有《春江花月夜》、《琵琶行》等,在弹奏上一般是轻挑慢捻的拨动琴弦,旋律缓慢柔和,多是描写自然风光和个人的细腻情感。武曲代表作有《十面埋伏》、《霸王卸甲》等,这种曲风的弹奏一般急切高昂、节奏变换多端,表现的是战士的慷慨激昂、英勇热切、豪放豁达的感情。这种乐曲恰好和唐诗中那种豁达和含蓄的意境相契合,所以琵琶成为唐代诗人笔下的情感载体。[6]
(二)唐代琵琶诗的发展历程
琵琶和唐诗联系在一起后,在动静结合的基础上,提升了诗词的韵味,用形象的表现、细腻的笔触刻画了文学家对社会现实和个人际遇的感受。琵琶在当时社会所产生的重要影响,被文人赋予了深刻的文化内涵,在唐诗中出现的频率极高,它往往作为诗人情感表达的载体,见证着盛唐逐渐衰弱的历史,并在特定时期赋予了诗词中琵琶固定的意象。现在,琵琶弹奏者通常研读描写琵琶的文学诗词作品来理解琵琶乐器作品,在弹奏过程中将琴与诗有机融合。
《全唐诗》中包含“琵琶”二字的有129首,以琵琶意象创作的有68首,写到琵琶的诗有61首。琵琶诗同唐朝的发展一样,经过了兴起、发展、成熟到衰退的四个过程。
1.初唐琵琶诗的兴起
初唐时期的琵琶诗沿袭了南北朝的文学写作特点,词句明朗苍劲中带着柔媚华丽。这一阶段琵琶诗不再只是为咏物而写琵琶,而是开始把琵琶同塞外人文联系在一起。文学视角开始转变,这是初唐琵琶诗歌兴起之兆。初唐的琵琶诗有唐太宗的《琵琶》、李峤的《奉和七夕两仪殿会宴应制》和《琵琶》、陈叔达的《听邻人琵琶》四首,这四首琵琶诗预示着琵琶诗在唐朝的兴起和繁荣。
2.盛唐琵琶诗的发展
盛唐时期,琵琶意象诗中有7首属于边塞诗,盛唐时期琵琶边塞诗盛行的原因在于:第一,琵琶本是异域传入中原的乐器,有很强的异域色彩,这时的边塞诗很容易联想到以琵琶代表塞外风光、军旅生活以及与胡人征战的场景。第二,像王昌龄、高适、岑参都是边塞诗人,他们在用琵琶作为意象写诗时,就地取材——利用边塞题材写诗。
3.中唐琵琶诗的成熟
中唐时期共作琵琶诗45首,《全唐诗》中11首写五弦音乐的作品就有10首是在中唐时期所做。这时期的诗歌多带有沧桑、落寞、孤寂之感,没有了盛唐时期壮志满怀的豪情,更多注重诗歌的娱乐性。这种诗风的变化和当时的社会背景有着很大联系。安史之乱后,盛唐逐渐转向衰弱,以刘长卿、李益、韦应物等写琵琶诗的代表诗人,在他们的诗歌中大都表达了他们落寞、愤慨不平的心境,如韦应物的《五弦行》、顾况的《刘禅奴弹琵琶歌》等,诗词虽然表达形象、细节处理到位但也渗透出一种孤寂、遗恨的心境。
4.晚唐琵琶诗的衰退
这个时期唐朝已逐渐的由衰败走向灭亡。诗歌也渐渐的受题材所限,缺乏真情实感和创造性,多是大同小异,这时期的杰出文学家也比较少。晚唐时期的18首琵琶意象诗大多数只是写歌舞宴饮时把琵琶作为乐器写入诗中,没有赋予它任何的内涵。如方干的《陪李郎中夜宴》诗中的琵琶,换成其他的乐器,诗歌在任何方面都不会受到影响。整首诗只因乐器而发出感叹,没有对当时社会进行写照,故不能成为流传千古的诗歌。
三、琵琶赋予的意境和唐诗的融合
“意”是文学创作者自身的感情,“境”是对外在自然环境的描述与再现。“意境”讲究的是思想、内容、形式的高度统一,是通过虚虚实实的手法象征诗词中的无限意味。“意境”在诗歌中的表现就是情景交融,文学家们寄情于物,托物言志,从物中折射出情,从而达到情从物观,物因情作。因此,唐代琵琶诗中的“意境”一词蕴含着作者无尽的情感——情中有景,景中有情,让人回味无穷,深思感叹。
唐代琵琶诗中的“琵琶”并不一定是现实中的琵琶,它只是作为一种固定的情感载体,将诗人的感情寄托在琵琶这种乐器身上。唐诗的意境创造,琵琶在诗词中起到了重要作用。琵琶在诗人眼中不再只是一种乐器,而在它的身上注入了人类情感——喜怒哀乐,这一时期的诗人纷纷利用琵琶寄情,通过琵琶诗蕴含的意象来表达个人情感、创造诗歌意境。
在《全唐诗》中写到琵琶的诗有61首,初唐、盛唐、中唐、晚唐分别占4、3、46、7首,其中1首阕诗作者和时代不详;以琵琶意象创作的有68首,初唐、盛唐、中唐、晚唐分别占4、11、35、18首。综合这些琵琶诗的类别,可以将琵琶诗的意象分为五类:
(一)悲怨与欢乐
唐代琵琶演奏多有幽怨情调,后世多用“琵琶声怨”,正所谓“琵琶弦中苦调多,萧萧羌笛声相和”(刘长卿《相和歌辞·王昭君 》)、“行人刁斗风沙暗,公主琵琶幽怨多”(李颀《古从军行 》)、“千载琵琶作胡语,分明怨恨曲中论”(杜甫《咏怀古迹》)。诗中的“怨恨”是很复杂的,既有诗人“帝不见遇”之恨,也有昭君和乌孙公主“夜月魂归的思乡”之怨!而“满堂醉客争笑语,嘈囋琵琶青幕中”(刘禹锡《更衣曲》),则以琵琶的欢快演奏卫子夫侍武帝更衣得幸于元朔元年被立为皇后的欢乐情景。
(二)激昂与悲壮
唐代琵琶演奏在表达悲苦怨恨的同时往往又不失慷慨激昂、壮怀激烈。唐朝疆土辽阔,由于北方游牧民族对中原地区的烧杀抢掠,边界战争时常爆发,守卫边塞、抵御游牧民族的入侵成为唐朝社会政治生活中最为重要的大事。唐太宗实行戌边将帅立功便可入朝为相的鼓励政策使得大批有志青年投身边疆,以求立功入朝为相。这个时期,涌现了大量的边塞诗人,为了渲染悲壮、激昂的气氛往往把“琵琶”用于诗中,以边塞的自然风光、将士出塞、征战、保卫国土为题材,写了大量的以“琵琶”作为意象的边塞诗。如:“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王翰《凉州词》),“琵琶”在这里指的是征战的号角,表现了征战的那种紧张场面,以及全体战士们斗志高昂、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边塞的的恶劣环境,很难得能够享受一顿珍馐美味,将士们的心情放松与激动。从“葡萄美酒夜光杯”可以看出当时宴席的盛大,奠定了一种热烈的感情基调。就在将士们打算痛快畅饮时,琵琶却开始奏乐,那种明快、急促的旋律反射出来的是热情与奔放,展现了慷慨、激越的艺术魅力。让人听之肃然起立,向往塞外生活和风光,体现战士的豪迈豁达。又如:“凉州七里十万家,胡人半解弹琵琶。琵琶一曲肠堪断,风萧萧兮路漫漫。”(岑参《凉州馆中与诸判官夜集》),月光下的凉州城,荡漾着一片琵琶声,慢慢向夜宴过渡。宴会上的琵琶演奏更加动人,兴会淋漓,豪气纵横。诗人吸取了民歌的艺术因素,运用顶针句法,句句用韵,两句一转,构成轻快的、咏唱的情调,写出凉州的宏大、繁荣和地方色彩,把边塞生活情调和强烈的时代气息结合了起来。读者从人物的神态中,感受到盛唐的时代脉搏。
(三)同情与感慨
在古代,经济的繁荣必定会带动青楼娼馆的发展,唐代也是如此。唐代娼妓大多才貌双全,擅长琴棋书画,犹通音律。琵琶更是乐伎必会的一项技艺。中唐统治者对琵琶艺技的大力提倡,宫廷琵琶乐舞之风盛行,上行下效,琵琶及其技艺在民间也快速发展,无论是宫廷宴饮还是文人士大夫的践行聚会都少不了用琵琶胡乐助兴;晚唐更甚,文人雅士犹喜与娼妓来往,以琵琶为意象写了很多青楼女子向往美好爱情和同情她们实际际遇的诗词。该时期的琵琶诗多是咏琵琶乐和叹琵琶伎的命运,虽然科举在唐代得到了延续和进一步发展,为士人们步入仕途提供了契机,但真正能够抓住这个契机在仕途上一展风采的毕竟是少数,而大多数士人仍然不能步入仕途,即使步入仕途却很不得志,宦海沉浮,不胜枚举。[8]如李白、王昌龄、杜甫、柳宗元、白居易等。一旦仕途受挫,失去人生追求的目标,不能施展自己的才华,士人们的内心悲愤十分强烈。这种不平之鸣必然要假借某一物释放出来,诗人往往通过琵琶诗来反映自己的境遇、内心的苦闷以及个人命运的感慨。如:刘禹锡《泰娘歌》中的“从郎西入帝城中,贵游簪组香帘栊。低鬟缓视抱明月,纤指破拔生胡风。繁华一旦有消歇,题剑无光履声绝。洛阳旧宅生草莱,杜陵萧萧松柏哀。”表达了诗人对琵琶伎的欣赏及身世遭遇的同情。白居易是写琵琶意象诗最多的诗人,共作了14首琵琶诗,其中《琵琶行》独特的艺术价值就在于对琵琶艺术的诗性描写。诗中的“琵琶”是一个深浸诗人情感的道具,不管是处于有声或无声的状态,均能传情达意。全诗形象的塑造,意境的构建,情感的寄寓,结构的起、承、转、合,风格的体现,均依托“琵琶”艺术的呈现和诗性的“琵琶”文化的描写,诗情与琵琶乐韵的有机结合,有很高的艺术价值,思想性与艺术性高度融合。[9]《琵琶行》通过对琵琶女高超弹奏技艺和她不幸经历的描述,揭露了封建社会官僚腐败、民生凋敝、人才埋没等不合理现象,表达了诗人对她的深切同情,也抒发了诗人对自己无辜被贬的愤懑之情。诗中“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用琵琶伎的命运反射自己的遭遇。
(四)庄重与神秘
琵琶诗的创作背景和意象随着不同时期的社会环境改变而赋予他们很强的时代意义。随着琵琶在民间的流行,琵琶走向世俗化和大众化,在祭祀、占卜等宗教活动中渐渐成为一种必不可少的乐器。此时的琵琶诗代表的是庄严神圣、不可侵犯的意象。如:“铜柱南边毒草春,行人几日到金麟。玉镶穿耳谁家女,自抱琵琶迎海神。”(张籍《蛮中》),在祭祀活动中弹奏琵琶,琵琶声回响在大海上,人们在虔诚中等待海神的到来,烘托出一种神秘、肃穆的意境。再如:“枨枨山响答琵琶,酒湿青莎肉饲鸦。树叶无声神去后,纸钱灰出木绵花。”(王睿《相和歌辞·祠神歌·送神》),写的是祭祀活动完成后,通过祭祀物品、鸦雀无声、满天的纸钱以及琵琶弹奏的声音送神仙离去,再现祭祀那种正式、隆重的气氛。
(五)缠绵与怀古
冯小怜,北齐后主高纬的嫔妃,聪明灵巧,善弹琵琶,精于歌舞,深得高纬宠幸,与高纬坐时同席,出则同乘。李贺的《冯小怜》“湾头见小怜。请上琵琶弦。破得春风恨,今朝直几钱。裙垂竹叶带,鬓湿杏花烟。玉冷红丝重,齐宫妾驾鞭。”这首诗表现了情人间的缠绵悱恻,用琵琶音乐营造出一种风情万千的意境,给人一种只羡鸳鸯不羡仙的艺术美感,其音乐意象和外在环境相融合,使得全诗场景香艳柔糜、声色俱全。而当晚唐国破家亡之际,个人又无法改变国家动荡的局面,诗人就营造歌舞升平的景象来粉饰太平,掩饰内心的苦闷与消极思想。受社会风气的影响,该时期琵琶诗的诗风有很强的颓败气息。如:李商隐《王昭君》中的“马上琵琶行万里,汉宫长有隔生春”、周昙《简文帝》中的“曲项琵琶催酒处,不图为乐向谁云”等琵琶诗藉以咏史怀古。
[1] (汉)刘熙.释名[M].北京:中华书局,1985:107.
[2] (汉)应劭.风俗通义[M].北京:中华书局,1985:161.
[3] (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5691.
[4] (唐)魏徵,令狐德棻.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3:378.
[5] (清)凌廷堪.燕乐考原[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4.
[6] 王萍.论唐代琵琶诗之意境[J].安徽文学(下半月),2010(6).
[7] (明)胡震亨.唐音癸签[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152.
[8] 蒋玉斌.明代中晚期小说与士人的淑世心态[J].长江师范学院学报,2010(5).
[9] 曹月.琵琶的诗性和诗性的琵琶——从《琵琶行》中解读唐代琵琶文化[J].人民音乐,2004(11).